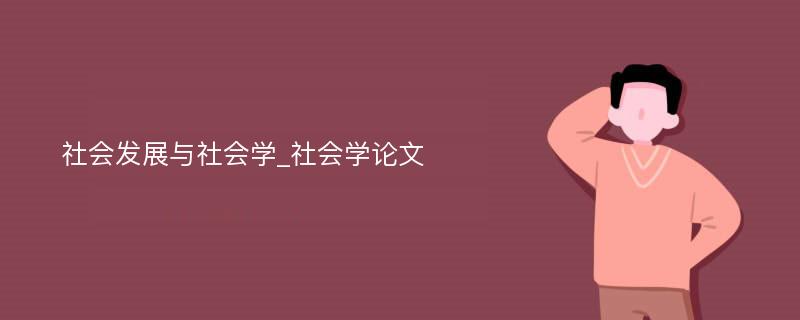
社会发展与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文章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回顾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向人们展示了学术生涯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辨证关系。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作者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紧跟着社会发展的脚步,把研究主题从村,到镇,到城,最后一直延伸到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作者坚信,社会学离开了人们的生活实际将不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发展 社会学 社会人类学方法
听说北大新办了一个教授俱乐部,这是一个新的设施,教授之间可以在此互相接触。搞一个学术性的俱乐部,创一个新制度出来,我很赞成这个事情,也自愿来参加这个聚会。思想上的交流,现在实在太少了。学术的发展,北大的风气要提高一步,这个俱乐部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今天问我讲什么好,我说讲讲社会学吧。我是60多年前进入这个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的,隔了一个甲子,能和同事们一起讲讲社会学,我很高兴,题目吗就叫“社会学与社会发展”。这个题目看来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从社会学出发来讲对于社会发展可以作出什么贡献,做些什么事。今天我想反过来,讲讲“社会发展与社会学”,就是讲社会学怎么从社会发展中吸取养料来发展自己这个学科。同时我也不讲别的,讲我自己,用自己做标本,看我如何从社会发展里边来构筑我的学术工作,在当前的激烈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中间,来发展我的思想。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重建社会学。这是我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正逢公社制度结束,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公社制度。当时我们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需要走新的路子。这就是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开始。这是一个大转变。小平同志这时出了个主意,要恢复社会学,要补课,要在各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可是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并不容易,要教师,要教材。当时我就想,教师呢,从全国各大学的文科教员里抽调出来加工。因之我们办了几个短期学习班,请了美国和香港的学者来讲他们是如何搞社会学的。教材呢,自己去找,自己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编。这是八十年代重建社会学的开始。
说起来,我们过去的社会学并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到最后一年,才有一个外国教授Robert Park来讲学,这是1933年。他说,社会学的资料在哪里呢,是在人的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在社会里边生活,没有一刻能离开它。他这一点提醒了我们:社会学不能只在书本里边去找资料,那是第二手的材料,而是要同自然科学一样,直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说你们要下到人里边去。他还带我们到天桥去,叫我们去看看和末名湖畔所见相比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下子改变了我们整个的对人文科学的看法。现在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叫联系实际。你不能关了门,在沙发里边讲,不行。要直接去看,直接去听,同人们接触,同人们谈话。所以Park带我们到监狱里,到八大胡同去见见世面,让我们不要仅仅局限在自己熟习的世界里。他对社会学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们直接去看社会,也就是要学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就是深入群众的生活,去了解社会活动的真情,然后去分析它的道理,多问几个为什么,要我们多动脑筋。这同你们自然科学一样,你要掌握很多数据,然后看出里边的规律来。
从Park得到这一点启发之后,结果我说我也要念点人类学。当时清华大学有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有个教人类学的俄国籍教授Sherokogorov,中国名字叫史禄国。他1910年从法国的大学里毕业,进入莫斯科的科学院,主要在西伯利亚从事通古斯人的研究。通古斯人居住在西伯比亚,那地方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后来给俄国并吞了。1917年,十月革命后,史禄国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里边教书,后来又来到中国教书。他在学术上有着很好的训练,同时又有很好的调查资料,写了好几本关于通古斯人的书。这时候我就找到他门上去了,安心地跟着他在清华念了2年体质人类学。我从清华毕业以后,于1936年到英国去学文化人类学。我的英国老师,是Malinowski。他和史禄国一样也主张实地调查。他说我们要进入不同民族的人的生活里边去,同他们一同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在当时他是开了一个新的为学方向,新的风气。从这一个风气里边建立了现代人类学,它的方法就是"field work",我们叫作“田野工作”。
我在英国一直呆到1938年,根据我在江苏本乡农村里的实地调查写出了论文,才回国。当时正值抗战,我经越南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已经开始了。我就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两个地方教书。我们还搞了一个调查研究所,住在呈贡乡下的一个魁星阁里边。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下乡调查;沿昆明湖跑一圈,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那是张之毅同志和我一起跑一起写的。《云南三村》就是讲内地农村的发展。从一个主要是农业的村子,叫禄村,到一个有简单的手工业如造纸、竹子编织等的村子,叫易村,一直到市镇附近的玉村。从一个完全是农业的,到有手工业的,一直到有商业的,三种不同的类型的村子,去看它们不同的地方。《云南三村》后来翻成英文,叫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们第一段的工作,一个开头,还不是有意识地跟着社会发展在走,但是我们在理论上是把从农村到手工业到商业,都作为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希望从实地调查中吸收养料来丰富我们的社会学。
解放之后我是搞民族,因为李维汉同志觉得我是研究人类学的,做少数民族研究工作正好对口,就把我从清华调出去,参加进少数民族访问团。这一段的经历,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已经做了回顾。后来,1952年搞院系调整,第一个把社会学取消了。到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编入号册,仅仅保留了教授的职衔。从57年开始到80年,这一段三十多年的时间,我是在另一个社会世界里边生活,就是同普通人的社会几乎隔绝。直到1980年,我才改正,才开始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我下了个决心,说我前面大概还有10年时间,我预备再干10年。我打个比方,说我身边只有10块钱了,这10块钱不能拿来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是要买一点我所喜欢的东西。买的什么东西,当时也没有说出来。等到1990年我80岁的时候,朋友们来庆祝我的生日,让我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的想法,我说我总结四个字:志在富民。回想一下,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江村经济》里边就已经说过,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饥饿的问题。因此我说我的一生,如果将来还有10年,那么我这10年就要用来把这个“饥饿”取消掉,可以说就是“志在富民”。
这个新开始的第一个就是关于“小城镇”。八十年代,我在江苏的农村调查里边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和公社制度之下,小城镇普遍衰弱,人口大大减少。差不多同样时候,胡耀邦同志在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小城镇衰败的情形比江苏还严重,作为农村的中心的市镇几乎消失掉了。原因就在于农产品自由交换的功能已经被国营渠道垄断,造成了计划经济之下流通渠道的不畅通,事实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于是我就决心要研究小城镇。当时尽管小城镇很箫条,但它本身有个力量在恢复,是它自己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外力作用。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我是怎么抓住这个问题的。我到吴江的一个叫盛泽镇的丝绸中心去调查,同当地的领导一起谈话、聊天。第一个问题我先问他们这个镇上人口。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大概万把人。我说解放之前我来过啊,人家也说万把人啊,怎么别的地方人口都涨了,而你们这个地方还是万把人?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口没有涨?他说原因很多啊,一时也说不清。这个问题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紧接着就到过年了,我到了苏州,住在苏州一个宾馆里边。服务员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啊,好象很不高兴的意思。我说怎么了。她说你来了,我们不能回家了。她是盛泽人。我说怎么回事。她说我们每年都要回去,可是今年过年没法回去。现在这几天挤得不得了,买票都买不到。我说为什么那么挤啊。她说都要回去过年啊。我说这么多人从哪里来的?她说上海的、无锡的这个镇上的人都要回家过节呀,所以不容易买票。而且因为我住在里边,她是服务员就不好回家过年了。这个巧了。我正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解放前十几年,这个小镇超过万把人,到现在1982年了还是一万多人,我要知道增加了的这些人到哪儿去了。现在我找到人了。他们都出去了,有去上海的,去无锡的,去其他地方的,小镇里边留不住这些人了。但是过年过节他们还是在回老家去的。这就是我跟着农村本身的发展去调查,从人口的变动里边看出一个小城镇的兴衰。兴衰的原因看来也很清楚,是因为我们流通渠道塞住了。本来小城镇是流通渠道的一个基地,一旦塞住了,人们就都跑出去了。可是中国人,他家在哪里,他过年还得回去。这是传统的力量,到现在我们也靠这个东西。外资不断地流向中国企业,靠的是出去的华侨,他们要回家乡啊。
上面说到我就是在和一个服务员的谈话里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开了一个门。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研究一个镇呢。我决定从它的兴衰开始。开始先搞一个提纲,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吴江县的七个大镇和许多小镇。我团团跑了一圈,一个镇一个镇去看,看它们的变化,这样子总结出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吗,胡耀邦同志看了很高兴,就批了,说大家都来看看,所以很出名了。
那么讲这个例子我要说明什么呢。其实我是要用它来说明是社会发展带动了我的社会学的研究。假如没有这个实际的发展,我进不去这个门,不会去搞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小城镇逐渐发展起来了,同时问题也很多,特别一个是关系到人口的布局。我们农村里边几亿剩余劳动力要出来,吸收在哪里呢?当然第一方面要限制人口,要计划生育,就是要少生点。可人还是要生出来,人口还在长。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吸收一个人至少要几万块钱。接收一个人进入北京,给他住,给他行动,工作场所,建筑和道路等等,都要花钱的。没有这么大一笔资本,不可能产生大城市。所以大城市接收不了农村里多余的人口。这批人到哪儿去,放在哪儿呢?我就想,不是可以放在小城镇里边,让它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吗。这就是小城镇现在起的作用。现在看来,过年过节,坐车很挤。可是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截住了不少农村里流出来的人口,不让他们全部到大城市里边去。什么地方截住了呢,小城镇截住了。农村里边现在必须要现代化,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这是我在《江村经济》里计算过的,一块一块地,按当时的技术需要多少工,就可以耕好这块地。多下来的,要占2/3。这些人以前是吸收在副业里边。可是吸收在副业里还不够,他们就开始搞工业。工业开始是在村子里边稿,逐步就吸收到小城镇里来。因此小城镇的发展是解决中国很多发展中问题的一条路子,也是富民的一条路子。
那么这一具体内容,今天我不去讲了,我今天讲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一个问题的。这些想法并不是我从书本里边看出来的,而是在实际生活里边我看到了小城镇的作用。有的同志也许已经听我讲过几次了。我最早是从很小的一件事情里边理解到小城镇的作用的。我当时是很喜欢抽烟的,在大学里边一直抽烟。我第一次去江村调查的时候,我到小店里边去买烟。他说你买几支烟。我说我买一条烟行不行。他说不卖,一盒都不卖,要买几支可以。嗨,我觉着有意思了。这么一个有几百户人口的村子,为什么烟要一支一支零卖呢。这就是碰到了一个问题,我就没有放松。我就问他,你们自己要抽烟怎么办。他说客人来了,我们一支一支买。真的要多的,叫航船去镇上代买。这是解放之前的事情。解放之前我们水乡一带。为什么市镇很发达,成为周围许多村子的购买中心,是因为它有一套流通的渠道,一个航船系统。江苏的水乡,交通工具主要是靠船。航船是专门来往于村庄和市镇之间的公共交通工具。航船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村民们在镇上代买日用品,另一个是在农副产品购销上充当村民和商家的中间人。从这样一个制度中,我看到了市镇在农村的流通渠道里边的作用。解放之后航船取消了,靠供销社供应,国有流通了,小城镇于是也萧条了。
所以我认为,要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抓住农村的流通渠道,这就是要发展小城镇。现在大家逐步明白了,大概这条路子是对的,中国发展的道路必须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从外国照样搬来的东西,而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的现象。我们从事实里边把它提出来,把它做理论的分析。分析出来之后,再回去,回到农民里边去,推动了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社会科学家,应当做这一个事情,做群众和政策之间的一个纽带,从实际情形里边去发现问题,再反映到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边去。
以上所讲的都是想说明我们要一路看生活,看具体的真正碰到的人,从这里边去找出一个真正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学。社会学离开了实际接触人,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的。生活里边有道理啊。现在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我们要好好理解它。这16年来,我就跟着这个发展,从村,到镇,到城,一路看它怎么发展,最后到区域经济。最近乡镇企业都在那儿找外资,搞合资企业。的确,合资企业解放了乡镇企业的资金问题,使它能维持下来。那么这一来究竟有什么意义,要研究,要想一想。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叫“有名无实的国家”,就是指跨国公司的网络。这个经济网络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超过了国家拥有的企业。现在全世界跨国的金融资本实力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我说它不是“有名无实”,而是“有实无名”,实际已经出来一个超过国家的经济实体,一个经济实力很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的联合体。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北大还没有人去追究。这篇文章又提到了一点,就这个跨国经济网络现在正在同以民族为基础组成的国家相冲突,和国家的主权概念相冲突。这是一个新问题,一个大问题,这个跨国家的实体正在形成和变化之中,这就需要我们社会学家去研究。这是我对年轻学者的期望,也是为了要说明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社会总在发展变化,而我们学者的任务就是要紧跟着现实的变化走,去抓住它。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996年12月16日在北京大学教授俱乐部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