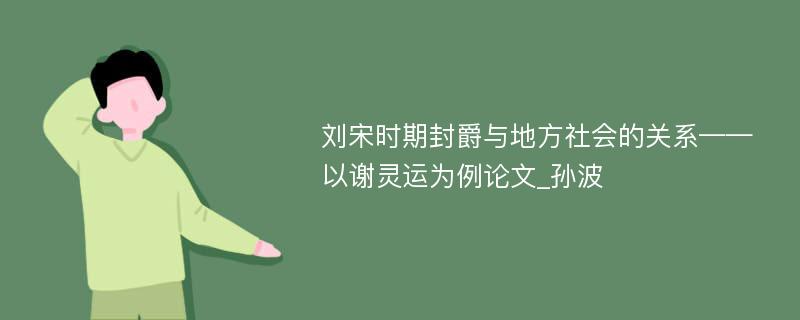
摘要:刘宋时期,封爵是封地的名义拥有者及形象代表,并无行政、财政、军事权力。为防诸侯割据,国家派遣内史和相行使行政职责。封地为其国主食秩来源地,《宋书》中,对刘宋封爵与封地之间的关系有其它朝代所不曾记载的明显变化,对研究封爵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较大价值。
关键词:刘宋时期;封爵;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赏功的需要使得封爵制发达,众多封国与郡县并存,这势必影响到地方行政与地方社会,使地方行政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史研究领域,学者大多注重于单纯的研究地方行政体制或者封爵制度,少有将二者结合的研究。[ 此课题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对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代表著作为严耕望先生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行政制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3月),此书对州郡县的设置、都督区辖区范围到州、郡、县府的组织及军镇、三长等北朝特有的制度,都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考证,尤其凸显此一时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特色与演变,是治这一时代地方行政制度者必读之书。其二,关于封爵制度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杨光辉博士的《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一书,对汉代至隋唐的爵制序列考证的比较清楚,对南朝爵制涉及较少;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重点讨论了西晋王国事务官问题,对南朝王国事务官的研究亦有参考价值。
]《宋书》中,对刘宋封爵与封地之间的关系有其它朝代所不曾记载的明显变化,对研究封爵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较大价值。
谢灵运(385—433年),生于浙江会稽,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八岁袭封康乐公,由晋入宋后,降爵为康乐侯。谢灵运生后即离乡,“送钱塘杜明师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出生到十五岁都居于钱塘,这里的“都”就是京都建康,居于乌衣巷,度过了一段世家子弟生活。二十一岁时出仕,历任晋宋两代琅琊王司马参军、刘毅记室参军、秘书丞、中书郎将、黄门侍郎、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等官职。其间两次回会稽隐居,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以“谋逆”罪名诛于广州,葬于康乐县(今江西万载县)。时人以其封地称其“谢康乐”。谢灵运袭封康乐公,无疑与康乐县有诸多关联,但没有典籍明确记载谢灵运来过康乐,康乐人民与其素未谋面,且就从政为官来讲,谢灵运并非合格的官员,康乐人民却多以谢公康乐侯子民为傲,何因?笔者认为,这与谢灵运的声望和文学成就有关,更主要与刘宋的封爵制度有关。
一、爵:封地的名义拥有者
至刘宋朝,封爵制度在中国已有千余年历史,有爵位者便是其封地的最高名义长官,《宋书》中,有爵位者名前必冠以地名,如“南康文宣公穆之”“华容文昭公弘”[ 见于《宋书》列传
]等等不胜枚举。爵位等级前冠以地名,应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地方的大小代表了爵位的等级,同样为“侯”,地大者尊;第二,说明爵位拥有者对封地享有名义上的领有权。
世祖孝建中,内史、相不再对国主称臣,但也仅仅是内史和相,相以下属官依然是国主的臣子,封地内的人民也都是他的臣民。换言之,刘宋时期,封爵一直是封地的最高政治代表,不管皇帝对封爵的种种限制,单就代表性而言,封爵当是不二之选。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魏晋南北朝多崇尚名士,谢灵运家世显赫、文学成就巨大,康乐百姓于是深以谢公为傲,康乐的历代文人雅士对他也是推崇备至,这种影响绵延至今。可见,封爵代表自己的封地当无疑问。
二、内史、相:封地的实际管理者
刘宋时期,内史、相是国家派遣的封国内的最高行政长官,“王国内史、公国相”,即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内史,公国及以下称为相。内史和相作为国家指派的管理诸侯封国的行政长官,与国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君臣相属到不臣的过程:“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 见于中华书局版《宋书·刘穆之传》
]。以此可见, “世祖孝建中”之前,封爵与封地内的行政官是名义上的君臣相属关系,虽然事实上的行政权把握于内史与相手中。孝建改制之后,名义上的君臣相属也不存在了。
受封时,“国吏”即受封者自己的事务官是封赏的一部分,因级别高低而国吏的数量和范围不等。宋承晋制,事务官应有郎中令、中尉、大农、常侍、侍郎、家令等员。他们主要负责国主教育、安全、国秩以及出入及内勤事务,或侍从诸王左右,谋议诤谏、充当幕僚。在自己的封地内,由于国主并无行政权,事务官就没了用武之地。他们后来甚至逐渐沦为国主的奴隶:南康郡公刘邕有食疮痂瘾,袭封后,“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 见于《宋书·刘穆之传》
]”。可见,国吏为了讨好主人,几乎不顾及自己的人格尊严。国吏为国主的日常活动服务,对地方社会行政影响不大。
当然,封爵作为名义上的政治高位拥有者,也有很多政治特权,比如国家征兵时,亲戚家人就可免于兵役等,这些特权大多只荫及家族,实际政治权力有限。
三、封地:封爵的食邑的供给者
刘宋的封爵实行“出仕不临国”原则,外出做官不临国,临国则不为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刘宋为防止诸侯割据,对此限制十分严格,在《宋书·朱龄石传》中,出仕为官的封爵擅自回到自己的封地还会受到夺爵的处罚,封国成为封爵的一个单纯的经济来源。有爵位者外出为官,可在国秩之外领取职官俸禄。
封爵与封地的经济联系在刘宋“世祖孝建中”后成了二者最主要的联系。封地给封爵提供“衣食租税”,这种经济特权是世袭的,但是每传一代食邑户都会减少直到国除,此法学自北魏孝文帝改制,北魏封爵加“开国”者食邑,而封户行“亲疏世减之法”:“亲王2000户,始蕃1000户,二蕃500户,三蕃300户;食租税之置: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 见于《北史》
]。刘宋的食邑户,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并不代表特定户数,食邑户若干,指代衣食租税多少的尺度。封国内的全部民户上交租税后,封爵根据食邑户数从租税总额中提取应得的秩奉,比如“邑五百户,三分食一”就是提取五百户的三分之一的租税,其余的上缴国家。所以说诸侯并没有特定的食邑户,国秩由全体封国内的人民平均分担。
综上,刘宋时期,封爵是封地的名义拥有者及形象代表,并无行政、财政、军事权力。为防诸侯割据,国家派遣内史和相行使行政职责。封地为其国主食秩来源地。值得关注的是,以孝建改制为界,封爵与封地的关系有一个明显变化。
论文作者:孙波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21
标签:封地论文; 食邑论文; 行政论文; 地方论文; 租税论文; 制度论文; 自己的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12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