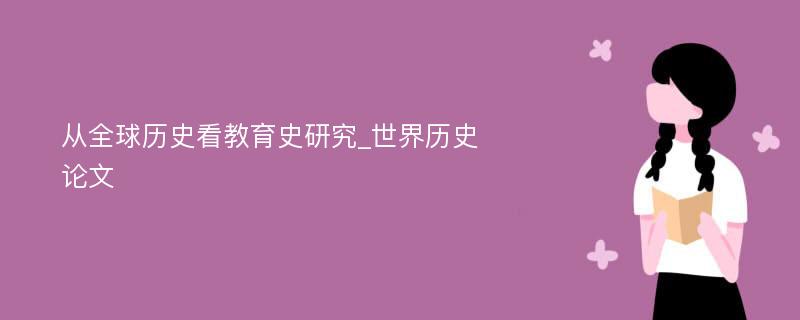
论全球史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09-0005-06
冷战以后国际史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关注不断加强。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史”与“世界史”往往重叠,但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时代,指的往往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则可以把对前现代化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包括进来。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全球史”这样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或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在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和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在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大范围的互动研究”方面有诸多成果问世。上述趋势显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同时也有重要的启发。教育史学者应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和借鉴。
一、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及其研究主题
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是一个史学流派,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首倡全球史观。1964年,他在《当代史导论》一书中提出的当代史和全球史研究的宏观体系,集中反映了其倡导的全球史观。1978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1](P193)。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不断发展,涌现出众多的通史和专题研究论著。1982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2006年,英国开始出版《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刘新成注意到,全球史“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2](P1)。全球史最著名的实践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杰里·H.本特利(Jerry H.Bentley)。夏继果与本特利主编的《全球史读本》编入的17篇论文基本反映了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直到今天全球史的发展历程,也解答了人们对于全球史的诸多疑问。在该文集的导言中,夏继果介绍了全球史的含义、研究的必要性及该文集的主要内容等,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史与旧世界史的区别。杰里·H.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指出,“世界史”这个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思是不同的:第一,它可以是对于全部世界历史进程的概述;第二,它可以只是外国历史——本国之外的世界的历史;第三,它可以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即一些历史学家从历史记载中发掘其哲学意义的努力;第四,它也可以有着强烈的宏观社会学意义,反映了跨学科的依附经济学和世界体系分析的影响;第五,越来越多的人更赞成“世界史”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不同方法。“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考察世界各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考察某一时段所有民族的历史,而是指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跨越社会的边界来清晰地比较历史经历,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或者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3](P45)。
新兴全球史倡导整体史和互动史的理念。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史是一种研究方向,研究超越欧洲和西方及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历史,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全球史研究者试图从世界各地区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入手,通过跨文化、跨地区等各种精神和物质交往互动现象来考察人类历史进程。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刘新成在梳理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出了“互动”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与“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和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2]。
从历史学研究的主题来看,近代以来,传统的西方史学专注于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民族国家始于近代欧洲,是为摆脱教权控制而产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国际格局。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和主要行为者。与此同时,与历史学科专业化发展相一致,研究的重点也日益狭窄,从各地区文化史转向了西方民族国家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学校变成了国家崇拜的场所。杰里·H.本特利认为,民族国家的确是历史分析中的重要单位,为考察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提供了背景,对于理解超出民族国家本身之外的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全球史研究者看来,历史经历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进程的产物。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仅属于民族国家或者其他表面上连贯的个体社会的观念。全球史虽然承认文化独特性、排外性的民族认同、地方知识和具体某些社会的发展经历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也已超越了专业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这些问题,明确将大范围进程纳入历史关注问题之列。”[3](P64)
施诚在《全球史研究主题评介》一文中指出:“全球史以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为研究对象,探讨超越国家和民族体系之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与全球化有关的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把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致力于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研究世界历史的进程。”[4]在他看来,可以将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归纳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全球史并非囊括人类所有历史,而主要集中探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另一类认为人类历史上全球化并非当代特有的产物,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全球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当代,应当追溯历史上的全球化进程。施诚研究了全球史研究的几个重要主题,包括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全球史中的跨文化交流研究和环境史研究。他认为,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全球史研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以国别史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世界史比较,全球史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世界史的范围,淡化了单一地区或国家,而强调全球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性。
二、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和理论方法
历史编纂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 in History)问题。在西方古代,历史循环思想(Time Was Seen as Cyclical)占据主导地位,基督教则将线性史观(Time Is Linear)引入历史研究[5]。张广勇指出,公元4世纪至5世纪是西方史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此时期兴起的基督教史学思想,打破了从前以世界作为背景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开始致力于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6](P6)。此后,对进步的信念和直线进步史观成为西方历史学编纂的主导思想。中世纪编年史家在具体叙述世界历史时,普遍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著作中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中世纪”一词,但人文主义史学家并没有把它付诸世界历史编纂实践。1700年左右,一位名叫凯勒尔(1638-1707)的作者出版了《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一书,第一次把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三分法”就逐步成为西方史学界历史分期的主流。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西欧中心论的观念在德国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中逐渐流行开来,一部世界史变成近代西欧各国制度的历史。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世界史编纂进入了西欧中心论时代,在理论上系统阐述西欧中心论的人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系统阐述了西欧中心论。后来,世界历史编纂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又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方人对进步的信念和西欧中心论受到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更是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传统三分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全球史兴起后,一些史学家从全球视野出发,对世界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期。杰里·H.本特利认为,研究世界上的人们参与跨越单个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的情况也许有益于全球历史分期的尝试。因为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包括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战争和远程贸易等。主要由于推动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边界的跨文化互动的动力不同,形成了世界历史的六个时期: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公元1000-1500年)以及现代时期(公元1500年至今)。本特利指出,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可以更好地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法,这种分期法以特定强势群体的经历来构建世界史。这样,通过关注跨文化互动的进程,历史学家们也许更乐于区分反映众多民族发展经历的传承和转变模式,而不是把源自某一强势群体的经历的历史分期强加给所有民族。但他也提醒注意以下两点忠告:第一,以跨文化互动为依据的分期不能妄称完全涵盖了古往今来的整个世界。只是在16世纪以后,跨文化互动才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全球分期的基础。第二,全球历史分期并不是历史分析中唯一有用或合适的框架。他注意到单个社会的内部发展对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的直接影响以及不同的人群参与大范围历史进程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全球历史分期通常是大致描绘历史的发展而非予以准确定位,以便为各地历史的细致差别留下波动的空间[3](P123-125)。
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认为:“理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撰写全球史所用的方法的多样性,可能与试图理解历史学本身一样复杂。全球史从社会科学中借用了分析的概念和哲学的方法,而有时候,这些概念和方法得到提炼并再度反馈给社会科学。大多数研究全球史的方法中包含了自我批评的种子,有时甚至是自我否定;其结果是,全球史学家的大量作品都是关于方法和概念的作品。”[7](P8)在她看来,“全球史”仍是一项新兴的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全球史编纂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故事?在柯娇燕看来,研究历史的语言和叙述仍受到语法、词汇和单向度时间感的限制,将形式与内容匹配起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此,全球史学家一直是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工作的。她介绍了对全球史进行界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且以大致的年代顺序编排它们,把它们整合在极为概括的范畴之下:分流、合流、传染和体系。
杰里·H.本特利深入研究了全球史的理论化(Theorizing the Global Past)问题。他注意到,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更愿意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分析,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建立在关于世界及其发展动力的理论、哲学或者意识形态等各种假定的基础上的。世界史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必要明确提出自己的前提假设。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家在为世界史建构理论框架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本特利认为,当前有关世界史的论争中有四种理论学派(Four Theoretical Schools)最为引人注目:第一种是现代化研究方法(The Modernization Approach),这个理论学派从马克斯·韦伯的比较社会学衍生而来。韦伯试图通过对欧洲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欧洲的特性,其影响在现代化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历史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种是受马克思影响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The Form of World System Analysis),认为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主要因为帝国主义和对其他社会的剥削。第三种理论研究方法注意到前两种方法的欧洲中心论特征,认为欧洲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是发展机遇带来的结果。第四种理论方法的特征是在试图说明世界历史大范围进程是从地理、生态和环境分析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中汲取灵感。在本特利看来,前两个学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后两种学派只是最近刚刚兴起的,但似乎准备对未来的历史研究施加重大的影响①。
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围绕全球史概念展开交流。但董欣洁注意到杜克大学跨文化与中国史专业的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2011年出版的《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在梳理全球史方面所做的新的学术尝试,并在《变动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样性——读〈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对该书有非常深入的述评。萨克森迈尔认为,历史学家仍局限在有关全球史的任务、责任和潜力上,并主要在民族的和地区的学术机构内展开争论,他则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关于历史学实践的内在层次、知识社会学、全球和地方趋势的新观点来纠正这种不平衡。作者还选取了美国、德国和中国作为主要个案,阐述了通往全球史的不同道路的特征,并认为历史编纂学中这种新的全球趋势,需要跨国对话、合作和交流的相应增长来支持[8]。
三、全球史与教育史研究
全球史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或历史学新学科的发展对教育史研究有多重启示,包括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诸多方面。首先是全球史的普世价值取向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全人类的命运的思考,二是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理念。第一个方面,全球史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与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又涉及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在文化认同上,一种被全世界人普遍认可的进步是技术进步,这成了现代化或全球化的基础。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是否以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取代了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全球文化是否销蚀了地方文化和传统?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而言,是否还要继续研究民族国家教育史?或在拼凑民族国家教育史的基础上编写世界教育史或全球教育史,还是运用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在世界历史上的互动,并将与外来者的交往视为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第二个方面,“认识他人”是当今国际教育哲学家推行的理念,他们主张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手段。编写一部关于人类教育互动的世界教育史教科书,无疑可以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教育的目的。在世界教育史上,正如皮亚杰早已指出的那样,夸美纽斯被西方学界公认为国际教育哲学的起源和先驱。在上述语境下,我们有创造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的可能性,即讲授一种非政治的世界教育史。
全球史流派的历史观对教育史研究是有启发的。长久以来,史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史学著作保持着浓厚的实用和文学气息。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科迄今没能在微观研究和宏观概括这两大对立的要求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我们要搞清我们学科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我们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如此全神贯注于微观研究,往往忽视了构建大的历史图景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存心忽视宏观概括的工作,相信当事实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它们自己就会讲话,但却忘记了只有我们才可以给‘事实’以声音。历史研究的这种片面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②因此,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必要从全球史视角重新思考教育史研究,这将有助于恢复在微观教育史研究和宏观教育史概括两者之间的平衡。
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史流派的研究对象的视角推进我们的教育史研究。如前所述,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术语有多重含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语境下对“全球史”或“世界史”理解的文化差异。夏继果指出,如果说在欧美世界“全球史”与“世界史”区别不大,与中国既已存在的“世界史”就差别甚大了。中国的世界史从鸦片战争以后就把中国史排除在外,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学科分类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从教育史研究方面来看,西方经典的教育史作都是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不包括中国教育史。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史研究传统一直将“中国教育史”和“西洋教育史”或“外国教育史”截然分开。虽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惯性所致,但显然已经不符合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历史观。再从教育史研究的主题来看,我们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专注于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教育史,而当今的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属于民族国家等的观念,进而关注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的文化互动进程。在教育史观和研究对象方面,我们显然应该作出适当的反映。第一,我们应该尝试编写一本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教育史》,概述全部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按照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思路,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文化教育等多重领域的“大范围的互动研究”。
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分期的观点重新思考西方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也是有意义的。教育史编纂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历史分期。对进步的信念和直线进步史观是西方教育史编纂的主导思想。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以来,“三分法”就成为西方史学界历史分期的主流。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也将世界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这在中西方都是约定俗成的。但很多全球史学者试图按照整体史和互动史的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上述传统的历史分期,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大范围的互动”的故事,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这种思路是否可以为教育史研究所借鉴值得思考。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的确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的教育史研究更好地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法,这种分期法以特定强势群体的经历来构建世界史。通过关注跨文化互动的进程,历史学家们也许更乐于区分反映众多民族发展经历的传承和转变模式,而不是把源自某一强势群体的经历的历史分期强加给所有民族。但我们不应用跨文化互动为依据的分期去完全涵盖古往今来的整个世界教育史。按照前述本特利的想法,只是在16世纪以后,跨文化互动才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全球分期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全球历史分期也不是教育史分析中唯一有用或合适的框架。民族国家教育史仍应是我们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我们的视野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应当更加宽广,关注某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教育互动研究,进一步推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研究。
全球史视角还将有助于我们推进全球教育史学史的研究。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点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应关注教育史学史研究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格局。在19世纪历史研究专业化进程中,历史学经历了从普世史(及区域史)向以国家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的转变,把民族国家视为文明和进步的动力。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写作世界史的尝试,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和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这些著作的中心内容是各种文明之间的比较,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个文明。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世界史的复兴,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加强。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进行研究的早期重要代表作是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以后,世界史的写作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沿着传统的方法,关注文明、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一些社会科学家像现代化理论家一样,把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发展看作理解现代世界的核心所在。第二种方向是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兴趣不大,其研究也不是直接从欧洲中心出发,更乐于把更早的年代的历史囊括进来。新近的发展道路被称为“科学文化”道路,使用新的非档案史料和进化生物学、环境科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化学以及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等领域的方法。对于世界史来说,第二条道路前景更加可观[9](P410-413)。我们可以参考国际历史学发展的上述两条道路来思考研究世界教育史的路径。另一方面,加强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中的地位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教育史出发来重构以往具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教育史。当今,将中国教育置于世界教育史之中,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教育和从中国教育史来反思世界教育史,成为理解中国教育史与世界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纬度。将中国教育史纳入世界教育史有助于反思世界教育史研究中的惯常概念和方法。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的讨论是有启发意义的[10]。我们可以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中国教育史表明了早期近代世界教育的多样性,有助于了解近代早期教育变革的模式;应重视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和历史编纂中的作用及价值;探讨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联系与互动;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史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推进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会带来深刻而持久历史影响的文化教育的碰撞和交流,强调其在文化教育传统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不同文化教育传统的人之间的有意识的文化教育借鉴或互惠性文化教育交流。
收稿日期:2012-08-05
注释:
①Jerry H.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Oxford:Blankwell,2002.397-400.夏继果,[美]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9-52。
②大卫·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辩护》,见夏继果、[美]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本特利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跨文化论文; 中国教育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全球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