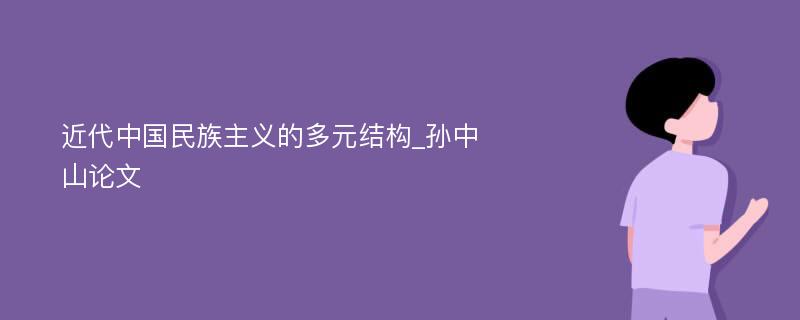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架构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既是政治家呼风唤雨的神圣口号,又是众多学者所热衷的带有信仰性质的理论,更是广大社会芸芸众生的朴素情结;他们为之热血沸腾,出生入死,却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这三种形态经常水乳交融,共同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但却始终不曾产生一种涵盖整个思潮的、严密的理论体系。
如果我们把这股思潮当作一个浑然的整体来进行观察和把握,便可以发现,无论其中有多少个派别、多少种主张和倾向,它们都围绕着下列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问题,也就是所谓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的综合扬弃问题。这两大问题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也都具有超越近代历史的特征,在今天乃至将来仍会以一种多少有些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这就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
先说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问题。
如果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很早便已经实际存在的话,那么,对这种格局的主观认同,则到了近代以后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近代,中华民族备受东西方列强的侵凌,处境日艰,中国人苦苦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西方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较为敏锐的知识界立刻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将之视为拯救中华民族的法宝。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态度。选取各自所需要的观点,结合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不同派别的民族主义理论。
在这当中,有一种在辛亥革命前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其影响日大、终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主体的理论,这就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把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当作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整体,并认为列强对中国任何一部分的侵略都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一致对付东西方列强。
梁启超在1903年首次撰文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亦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于五大陆之上。”(《饮冰室文集》十三,第75~76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进一步把这种有关中华民族的理念概括为“五族共和”,提出要“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合五大民族为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二,第48,89页)。
这种大民族主义强调,中华民族加强内部团结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一切恶魔的需要,它的最基本的奋斗目标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军事侵略、经济剥削和文化奴役,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讲得最为明确:民族主义之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主义之侵略”(《孙中山全集》九,第118~119页)。
在大民族主义之外,中国近代还出现过所谓“小民族主义”。在小民族主义中,较有影响的又有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
大汉族主义有较深厚的历史背景,只不过在十九世纪以前它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古典式的理论形态。二十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期间,在西方民族主义的激发之下,在“排满”的热浪中,大汉族主义迅速地盛极一时。特别是国粹学派中的一些人,把少数民族视为夷狄,排除于中华民族之外,以为中国的国只能是汉族的国,中国的学也只能是汉族的学。辛亥革命后,大汉族主义进而表现为一种民族同化主义。孙中山就曾提出“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尽管孙中山本人后来纠正了这种提法,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当时甚至有人不承认蒙古是一个民族。此后,大汉族主义也并未完全绝迹。当然,从总体上看,大汉族主义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潮中,只能是一股支流。它作为一种偏狭的民族主义,是与大民族主义相背离的,是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
至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分裂主义,则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极度膨涨的产物。它是建立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因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特别是与一部分外国人别有用心的煽惑分不开。另外,也受国内同时期兴起的大汉族主义的刺激,在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对待关系。这种民族分裂主义主张蒙、藏等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例如,蒙古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俗称德王)自幼便以成吉思汗家族第三十世孙自居,以继承其先祖之业为务。辛亥革命前后蒙古、西藏发生分裂叛乱活动的原因很多,但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作用,近代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理论色彩并不鲜明浓烈。这方面的公开文献很少,偶而有所表露也只是以一种很隐晦的形式出现,如不说独立而称“自治”等。然而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确实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流淌着,而且非同小可。我们形象地称这种民族分裂主义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股很有影响的暗流。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支流和暗流并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度里,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如果主要的不是由于内部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压迫和外部观念刺激所致,则很容易形成一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这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它的内部矛盾与冲突。各自都以民族主义相标榜,各自又都以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民族利益为指归,最后,不同的民族主义也就必然地成为相互攻击的目标。这自然是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起始宗旨大相径庭的,是极不利于民族主义正面功效发挥的。这也就提醒政治家和知识界在试图起用民族主义这个工具和手段时,一定要对它可能出现的多重架构保持高度的警惕,努力在培植其主流意识的同时,积极消除非主流意识,以便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正面功能。避免或减轻其负面效应。
(三)
关于中国近代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及其对二者的综合扬弃问题,是一个双倍复杂而沉重的话题。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寻找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基本途径和平手段。从“五四”时期开始,便有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必须彻底破坏中国固有的传统,而不是部分的破坏,更不是全面的继承。有些知识分子虽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的政治体制看成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根源,但他们却对之非常反感,主张严厉地抨击它们,同时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这种民族主义是与反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从陈独秀到鲁迅,从《新青年》发刊词至《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都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反传统民族主义战斗精神,都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种反传统民族主义将爱国精神与变革信念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富于感召力的,对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强烈的震撼。然而,在反传统民族主义内部,又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因为对民族传统的根本否定,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对民族自身的根本否定,这显然是与追求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同时,在科学技术落后、经济不发达而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中华民族既无足够的科技、经济实力与西方竞争,便非常有赖于民族精神力量发扬。如果将自己的传统全部放弃,则必然失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认同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又凭什么去与列强竞争呢?它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力量源泉又在何处呢?对这些问题,反传统民族主义并没有给人以满意的回答。
而另一方面,与反传统民族主义相反,中国近代又存在着一种民族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这种民族保守主义与排外主义比反传统民族主义的资格要老。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排外主义浪潮的兴起;民国初年康有为提出“保中国,则不可不先保中国魂”,并主张尊孔子为“教主”,等等。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虽不自言为民族主义,但是可以归入民族主义范畴的。他们所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法和手段,都建立在保留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一基点上,都不主张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从自身的内在逻辑看,这种理论似乎并不存在矛盾,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即然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是造成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的重要根源,又怎么可以倚仗它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呢?
正因为如此,民族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虽然迎合了中国社会深层的独特文化需求,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颇有市场,更经常地被人加以利用,但在解决中华民族在近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上却没有大的作为。
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都有自己的不足,历史是否因此而陷入了两难境地呢?从本世纪20年代前后开始,中国的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为探求出路,开始将两种对立的民族主义综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正反合。
朱执信在1919年便主张要以折衷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用以培植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他说,一个民族“若其既受压迫,则往往以现代实力之缺乏,物质上被人超越,驯至有颓丧之气,几以奋发恢复为不可能……欲救其病,则惟有以历史为根据,取已然之迹,以破其现在之无远见……则视听一新,其绝望复变而为有望。”同时,他又指出:“然单恃历史,决不足以致国民之自觉也。历史所示之繁荣,往往令颓败之国民,徒知尊古非今,则害多而益少。故必待有进步之知识,以培养其消化民族历史之力”(《朱执信集》上,第350页)。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新三民主义中,一方面把民族主义与民生、民权主义并列,使三者相互结合为用,使民族主义具有变革的精神。另一方面,在他的民族主义内部,又十分强调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洋文明相结合。他说:“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并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齐驾并驱”(《孙中山全集》九,第243~244,251页)。
孙中山的新的民族主义主张,给人以一种与现代新儒学有几分相像的感觉。他的这种主张在20~40年代曾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权威符号,被许多人加以诠释和具体化。有位作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写的一段话就很具代表性。他说:
“中华民族固有的旧道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固有的知识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特征。我们应该发扬而光大之,推忠孝之义,去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孝于民族,孝于长上;推仁爱之义,去打不平而使之平,去打倒帝国主义以自救而救东方弱小民族;推信义和平之道去联络无产阶级及东方弱小民族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以格物致知之理,探讨一切科学,以诚意正心修身之道,扩大家庭宗族团体到国族团体,进而谋世界之大同”(李茂秋《全面抗战方略》第35~36页)。
无疑,这种带有文化捏合特色的民族主义仍不是问题的答案。虽然它不再机械地主张反对民族传统或者保存民族传统,但它还是没有找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民族传统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和转化的根本途径,甚至连解决问题的方向都还未发现。它的基本主张乃在于以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本位,来消化、吸收近代西洋文明。说到底,它只不过是纳入民族主义范畴之中的“中体西用。”它想取东西文化之长而用之的愿望固然是好的,但实际上却因此给传统文化中某些带根本性的消极因素提供了庇护,使封建主义得以再次蒙混过关,甚至堂而皇之地继续在民国政治舞台上大显威风,民主思想未能深入人心。这虽然在根本上并不能归咎于民族主义,但二者确实是有一定联系的。
虽然孙中山等人所试图激发的强大的救亡御侮的民族精神力量,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过较强劲的显现,但它的代价也可以说是昂贵的。而且,离开了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它的作用便难以持久,而其代价则有可能加重。看来,仅仅用民族主义来支撑整个民族精神是不够的。反过来,民族传统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确实做好一些传统特质的改造和功能转换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变和相关政治制度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