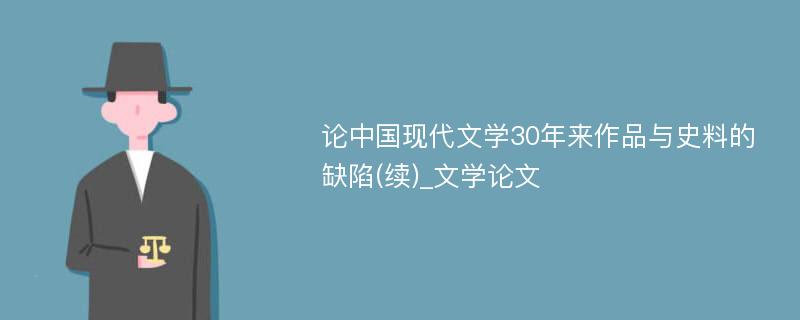
也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作品与史料复述瑕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订本论文,史料论文,瑕疵论文,也说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3)02-034-07
从笔者初次接触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7月出版)到现在,已有10年。这部教材一直伴随我的教学生涯,我也发现它在作品复述和史料运用上存在某些瑕疵,有的已经被人提及,[1]不再重复,而有些暂时还没有被人指出,鉴于目前大学生的积累欠缺,大学教师也未必能发现这些错讹,而该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作为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本科生的指定教材,印量甚大,影响甚巨,在此指出还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贤者不吝赐教。
一作品复述瑕疵
1、在该书的第三章《小说(一)》第62页,著者提及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女主人公加陵初时企图逃婚对抗,而男主人公敏明在一次离奇的佛教式的冥想中……厌却红尘,并以虔诚的祈祷感化了加陵,双双携手平静地走入绿绮湖。”
这里弄错了人物的性别,男主人公应该是“加陵”,女主人公应该是“敏明”。有原文为证:
敏明坐在席上……她底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底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
……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学加陵。他们是七八年的老同学,年纪也是一般大。他们底感情非常的好,就是新来同学也可以瞧得出来。[2](P91)
2、在这本书的第十三章《沈从文》的第217页,著者论及沈从文的《八骏图》,指出“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便在给未婚妻写的信中一一刻画了他们的虚伪处。”
但这番叙述与原文有异。原文如此:
(达士先生)发现了七个同事中有六个心灵皆不健全,便自然引起了注意另外那一个健康人的兴味。……他知道那是经济学者教授庚。
达士先生早已发现了,原来这个人精神方面极健康,七个人中只有他当真不害什么病。这件事得从另外一个人来证明,就是有一个美丽女子常常来到寄宿舍,拜访教授庚。
……教授庚与女人的沉默,证明两人正爱着,而且贴骨贴肉如火如荼的爱着。[3](P218-219)
从以上文字可以得悉教授庚“精神方面极健康”,而且有着热烈的爱情,更不是性压抑或性变态了。那么是什么导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他算在“病人”行列的这种错误呢?很可能是没有读懂原文,以及根据题目来断章取义,其实题目“八骏图”并非指八个教授都是“病马”,而是援用青岛的那位大学校长的称谓,“他似庄似谐把远道来此讲学的称为‘千里马’;一则是人人皆赫赫大名,二则是不怕路远。”故此,“八骏”指的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而非精神。
3、在该书的第三章《小说(一)》第53页,著者介绍彭家煌的小说《活鬼》:“同样喜剧味道十足的,还有《活鬼》,将财主家庭内部为了人丁兴旺而纵容媳妇偷汉、给小孩子提早娶媳,以致家中不断‘闹鬼’的现象,大加嘲弄。”
其实,此处的情节内容和主题都被说错了。实际上,小学生荷生家里“闹鬼”是在他的祖父(勤俭起家的老农)去世后,而且之前他的母亲、姐姐虽然在外偷汉但是“她们没有成绩报销出来”。待到荷生执掌家政后,她们不偷汉了,家中却不断“闹鬼”,弄得他的寡母、姐姐先后不幸惨死。而且,“财主家庭内部为了人丁兴旺而纵容媳妇偷汉、给小孩子提早娶媳”只占小说大约五分之一篇幅,说不上是该小说“大加嘲弄”的重点。小说《活鬼》讽刺的是经常给荷生讲鬼故事的学校厨子邹咸亲,他和荷生交情颇深,堪称“挚友”,但是他却在荷生的祖父死后,装神弄鬼地玩弄荷生家中的女性,还恬不知耻地与荷生商量对付“活鬼”的办法,最后当他在荷生屋外扮鬼时,被醒来的荷生一枪击中,之后销声匿迹。小说嘲讽的就是这位“一向做事稳健,纵然偶有差错,也与风化无关,博得教职员的信仰”[4](P20)和学生的信任的不显山露水、道貌岸然,但却心怀鬼胎的“活鬼”邹咸亲,同时也透露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信息。
4、在该书的第十一章《老舍》第193页,著者复述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如下:“经过三年的艰辛,祥子终于买下一辆新车,不料才半年就被匪兵抢去。他虎口逃生,路上捡到三匹骆驼,卖了三十元钱,准备积攒着买第二部车,不久又被孙侦探抢去。”
这里发生了动机错误和数量错误。事实上,那三匹骆驼并非祥子在“路上”无意之中“捡到”的,而是祥子在乱军撤退时专门等待时机有意牵走以补偿他那辆车的损失。如果是“捡到”的话,就等于发横财,并不符合作者对祥子的性格设计,也不符合作者对不公道的社会的批判。祥子把买一辆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因为他觉得在城里拥有属于自己的车就如同在乡村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能凭着自己的勤劳、个人的奋斗获得安稳的生活;所以祥子有意冒险拉走三匹骆驼。另外,三匹骆驼卖了不止著者所说的“三十元钱”,而是三十五元钱。
原文如下:
远处有了炮声,很远,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他不敢动,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他闭住了气,机会到了!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他慢慢的,闭着气,在地上爬,目的是在找到那几匹骆驼。……军营里更乱了,他找到了骆驼……他伏在骆驼旁边……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人来拉骆驼。……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他不肯再放下它们。一切都交给天了,白得来的骆驼是不能放手的!
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五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一万块更可靠,虽然一条命只换来三十五块钱的确是少一些!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绝不能,只值三十五块大洋!可是,有什么法儿呢!
5、在该书第十一章《老舍》的第191页提及“老舍早期作品中的理想市民——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其中《赵子曰》里的“赵景纯”应该改正为“李景纯”。
6、在该书的第十二章《巴金》第206-207页,著者谈到巴金后期创作的小说《憩园》:“旧主人杨老三在嫖赌饮吹中荡尽了祖传的遗产,沦落为乞丐,长期寄生虫式的生活,使他丧失了最起码的谋生能力;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又使他不屑于自食其力,只好靠偷窃为生,结果在监狱中默默死去……而故事的总叙述者‘我’是客居杨家的局外人,他对这个家庭的衰落的观察与评说时时警醒着读者”。
事实上,此处的“故事的总叙述者‘我’是客居杨家的局外人”不符合故事的真实情况,因为当时杨家公馆早已经卖给“我”的朋友姚国栋,所以只能说“我”客居姚家,不能说客居杨家,硬要这样说,也只能讲是客居杨家老宅。另外,杨老三也并非“荡尽了祖传的遗产”,就马上“沦落为乞丐”,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时间上也有出入,他是被已经工作而且收入还不错的大儿子赶出家门后才慢慢沦为乞丐,寄居大仙祠的,有原文为证:
你倒值得,你阔过,耍过,嫖过,赌过!你花钱跟倒水一样。你哪里会管到我们在家里受罪……现在我们用不着你了。你给我走!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我不承认你这样的父亲!……你马上就给我走!我看到你就生气
鉴于此,小说的主题并不单纯是“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批判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封建思想”,更有着一种“带刺的伦理”的味道:小说中有带刺的父子关系(杨老三的大儿子仇父,姚小虎骗父)。也有带刺的亲戚关系:杨老四的车撞着落魄的杨老三,作为弟弟的杨老四明知是兄长,不仅驱车扬长而去,还吐痰在兄长身上,兄弟关系冷漠如斯。姚小虎的外婆听说姚太太比她的已死的女儿贤惠(姚国栋也这样认为),心存妒忌,就有意无意地以金钱、后母不良等观念教育小虎,把开始还不算坏的小虎教育成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以一种妒忌的、放纵的方式表现出家长观念的腐蚀和控制,使得小虎成为杨老三的影子(小虎后因贪玩被水冲走而死)。
7、在该书的第二十三章《小说(三)》第396页提到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情节:“七巧因出身低贱,嫁给性无能的残废丈夫”。但是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由钱谷融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卷(第三版),以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的由金宏达、于青编的《张爱玲文集》第二卷,《金锁记》并没提到七巧丈夫的性无能,他的病是“软骨症”、“骨痨”,而且如果他是性无能的话,他不可能和七巧生了一男一女,如小说中所言:“也生男育女的——倒没闹出什么话柄儿”,因此也排除了七巧偷情生育的可能性,故此说七巧丈夫性无能,无论从病症来看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有误。
二史料运用瑕疵
8、此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7页说钱玄同“他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甚为激烈。”著者应该把这封信的题目或发表刊期写出来,因为笔者看到不少论文作者可能受该书影响,也只写个模糊的“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其实钱玄同致《新青年》的信不止一封(例如二卷六号也有),这封信的题目是《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通信”栏目第14页,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改题为《寄胡适之》,原文为“玄同年来从事教育,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
9、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7页写道:“1918年冬天创刊,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同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换言之,《新潮》月刊应该也是1918年冬天。但是第25页的本章年表中却赫然写着“1919年1月,《新潮》月刊创刊”。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表述?
经查,《新潮》月刊创刊号出版时间是1919年1月。而所以说“1918年冬天……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是把新潮社的成立时间和《新潮》月刊的创刊时间混为一谈了。据孟春的《新潮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3期),以及贾植芳等做顾问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等资料,证实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冬天,《新潮》月刊则晚出一段时间,在1919年1月创刊。
10、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14页记载“前期新月派(指1928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提倡格律诗”。第99页却说“前期新月派是1927年以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那么,到底哪一个时间正确呢?
经查,《新月》月刊由徐志摩、罗隆基等编辑,1928年3月10日创刊于上海,出至1933年6月1日四卷七期停刊,共出43期,由此可知前期新月派活动时间应该是1928年以前而非1927年之前。众所周知,前期新月派的基本阵地是北京《晨报副刊》“诗镌”,而后期新月派的基本阵地则是《新月》月刊。
11、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15页写道:浅草社“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但第28页的本章年表1925年条下却记载着“10月,陈翔鹤、陈炜谟、杨晦、冯至等在北京组成沉钟社”。
根据《沉钟》周刊创刊号(1925年10月10日),沉钟社成立于1925年10月,并非1929年秋。
12、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17页说: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
事实上,周作人《人的文学》的“非人的生活”创作观念中的“非人”并不专指“底层人们”。周作人声明“人的文学”的第二项“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此处“非人的生活”既然与“平常生活”对应,那么从逻辑上说是指“非平常生活”,并不必然指“底层人们”的生活。因此,周作人才举例说明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妓女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提倡女人殉葬殉节的文学也是非人的文学。妓女与殉葬的女人的生活都是“非人的生活”,但未必是底层人们的生活,后者就不是,殉葬的女人甚至可以或者更多是大户人家。所以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生活的“非人”与否,却在于创作态度的“严肃”与否。“简单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还是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7](P196)正如他的《平民文学》中的“平民”也并非指底层人们,而是指“世间普通男女”,因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很明显,周作人自称“我们”“普通男女”,但他却绝对不是底层人们,所以《平民文学》中的“平民”其实也就是人类或者作为类的人。故此,周作人才明确指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8](P211)。
13、该书第十六章《新诗(二)》第273页写道:“而当殷夫与他出身的阶级‘告别’(《别了,我的哥哥》),投身于革命洪流,‘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时,他就感到了‘个人’融合在无产阶级‘集体’中的喜悦与幸福。”
根据发表该诗的1930年5月10日《拓荒者》第4期、5期合刊,该诗作于1929年4月12日,其主标题是《别了,哥哥》,副标题是“作算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而且作者在该诗发表后并无修改,他生前并无诗歌结集出版,他自编的诗集《孩儿塔》中,该诗题目与发表时一样。1931年2月7日,他被国民党秘密处死,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似乎也没有时间修改此诗。鉴于以上考证,该诗题目应为《别了,哥哥》。
14、该书第14页写道:“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11月,办有《语丝》周刊”。而第27页本章年表的1924年条下记载“10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第124页本章年表的1924年11月条下记载“同月,《语丝》周刊创刊”。究竟孰对孰错?
经查,《语丝》周刊创刊号(1924年11月17日)以及泯的《语丝社》(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等资料,语丝社成立时间和《语丝》周刊创刊时间皆为1924年11月,并非同年10月。
15、该书第六章《新诗(一)》第98页说,“1923年,同时出版了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以及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而在第111页本章年表的1923年12月条下记载“同月,宗白华《流云》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经查,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宗白华的诗集应该是《流云小诗》而非《流云》。
16、该书第七章《散文(一)》第115页写道:鲁迅1919年“此期间写下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
其实,《自言自语》与《古城》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为据《鲁迅全集》,《自言自语》是鲁迅1919年8月19至9月9日连载于《国民日报》“新文艺”栏的系列散文的总称,包括《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我的兄弟》七篇,后来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7、此书第161页提到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出现了一大批表现个人走向社会历程的作品”,例如“丁玲的《一九三六年春在上海》等作品”。第232页又提及丁玲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与《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展开的是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
查阅刊载该作品的《小说月报》,题目应为《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发表在该刊1930年9月,“之二”刊载在该刊1930年11-12月。
18、该书第十三章《沈从文》第212页说沈从文“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但第223页本章年表的1922年条下记载“夏,只身抵北京”。
那么,沈从文抵达北京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年?实为1923年。根据沈从文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自述:“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到达北京的。”但是时隔将近60年,记忆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一般来说,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模糊淡化,时间隔得越长遗忘越多,时间相隔越短遗忘相对较少。根据他1931年写成(1934年出版)的《从文自传》,有两点可以作为他1923年到北京的佐证:第一,虽然没有明确写到北京闯荡的年份,但他在旅店登记簿上这样填写自己的身份:“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根据沈从文对凌宇的夫子自道,以及凌宇的考证,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12月28日,[9](P40)可知沈从文是1922年12月28日才满20岁,所以他是1923年夏天而非1922年夏天到的北京。美国学者金介甫对沈从文到达北京的年份也持1923年说。[10](P106)而凌宇因为不敢确定,则以相当模糊的言说一笔带过,不提哪一年。第二,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提到他被调进保靖报馆,后来被具有新思想的印刷工人所影响,看新出的《创造周报》和冰心的《超人》。众所周知,《创造周报》创刊于1923年5月,冰心的《超人》也于192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在此后不久沈从文被调回军队,没多久他大病(热病)40天,又因为好友陆弢在该年初夏溺死,沈从文为此苦思几日后,主动申请到北京念书,经过19天终于到达北京。[11]由此可以判断沈从文应该是1923年抵达北京的。
19、该书第十八章《散文(二)》第309页提到,何其芳的“《画梦录》就因其对现代艺术散文体裁的独特的制作,1936年被授予《大公报》文艺奖金”。但在317页本章年表1937年条下则有“5月何其芳《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大公报》1937年5月15日星期六第二版有如此公告:
本报文艺奖金揭晓
本报二十五年度文艺奖金一千元,兹由文艺奖金委员会审查委员杨今甫,朱佩弦,朱孟实,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诸先生投票推荐作家,其得全体委员过半数推荐之当选人及其作品披露如下;
曹禺(戏剧:《日出》)
芦焚(小说:《谷》)
何其芳(散文:《画梦录》)
除专函通知当选之三先生外,敬希读者诸君注意。
在当日《大公报》的同一版还配发了社评《本报文艺奖金发表》。而在第三版的《本报文艺奖金的获得人》一文中对何其芳《画梦录》有如此评价:“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一向散文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的出版雄辩地说明了散文本身怎样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这可以印证教材中的观点,即《画梦录》“对现代艺术散文体裁的独特的制作”。但是教材正文的何其芳《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时间1936年应改为1937年。
那么,《本报文艺奖金揭晓》中的“本报二十五年度文艺奖金”即1936年度文艺奖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1936年9月1日《大公报》的《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举办科学及文艺奖金启事》,“本报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刊,中间曾于民国十四年底起停刊数月,至十五年九月一日复刊,迄本年九月一日,适为复刊满十周年之期。兹为纪念起见,特举办科学及文艺两种奖学金,定名为‘大公报科学奖金’及‘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年得奖人数,科学拟以一人至四人为限,文学以一人至三人为限。即自本学年开始至学年终了为一年定期三年。如有变更,至期满另行通告。”既然说“自本学年开始至学年终了为一年。每年评选一次”,换言之,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金必须对1936年度的文艺进行评奖,因此获奖的作品都出版于1936年:芦焚的小说集《谷》1936年5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1936年7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曹禺的戏剧《日出》连载于1936年6月《文季月刊》第1卷第1至第4期,1936年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所以《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不仅做到了年限的严格(1936年),得奖人数的严格(一至三人),还做到了质量把关的严格。因为根据《大公报》1937年5月15日星期六第三版的《本报文艺奖金的获得人》:“去年(即1936年——引者注)适逢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十年的日子不算短,我们为了追怀这段艰苦的行程,决定举办‘文艺’和科学奖金……‘文艺奖金’经八个月的缜密讨论,终于有了今天公布的结果。”其严格可想而知。
20、该书第327页《曹禺》一章的年表1940年条下:“秋冬作《北京人》(五幕剧)。1941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在该书的498页的第二十八章《戏剧(三)》的年表1940年条下却赫然记着:“12月曹禺作《北京人》(三幕剧),次年12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据1941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的话剧《北京人》,以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曹禺文集》,《北京人》为三幕剧,而非五幕剧。而且,也不妨为该剧的创作时间挑点刺,一个是虚指秋冬,一个是确指12月,12月已是冬天,与前述的“秋冬”似乎不是同一时间。遍查《曹禺自传》,关于《北京人》的写作时间都没有明确记载,只说该剧是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校任教时创作的。[12](P304)但据田本相的《曹禺传》,有两个时间值得注意:一是曹禺于1940年夏天,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校遇见他的学生的姐姐方瑞(字译生),后来相恋,曹禺遂把对译生的爱倾注在剧本里面。二是根据曹禺的学生方琯德回忆,大概1940年的深秋,曹禺写作《北京人》,他把该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学生听。[13](P376)由此可知,《北京人》创作时间应该写1940年秋冬较好,而确指该年12月似乎不妥。
21、该书第二十三章《小说(三)》第380页写着:“丘东平的报告文学《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也有人当作小说来看待。”第二十七章《散文(三)》第464页认为“丘东平,他的纪实小说和文学性通讯很难分得清。《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都很有影响。”
经查,1947年上海希望社出版的丘东平的《第七连》,1983年花城出版社的丘东平的《沉郁的梅冷城》,以及高远东先生编选的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丘东平代表作·第七连》等书籍,《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应为《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
22、在该书的第二十三章《小说(三)》第398页提到徐訏“1943年发表长篇小说《风萧萧》,一纸风行,当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该年被称为‘徐訏年’”。但该书第411页本章年表的1946年条下记载:“10月徐訏《风萧萧》(长篇)由怀正文化社出版”。
《风萧萧》到底是哪一年成书出版?经查,该书1946年10月上海怀正文化社的初版本,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六》(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风萧萧》,还有作者1946年9月13日在上海写的《后记》,可知该书1943年3月1日动笔,1944年3月10日脱稿;1943年3月起在重庆《扫荡报》副刊连载。[14]学生把“一纸风行”理解成该书1943年已经成书出版,所以不清楚究竟何年出版。这也许与该段文字的表述有关,因为“一纸风行”既可以理解为作品在报刊上刊载大受欢迎,也可以理解为作品成书出版甚为畅销,总之是指杰出作品风行一时。根据以上材料,“一纸风行”指的是前者,“发表”也最好改为“连载”。
23、该书第二十章《戏剧(二)》第335页谈到夏衍,说他1936年“写了历史剧《秋瑾》(原名《自由魂》),这是以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为主角”,“夏衍在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时曾经说到,他早期创作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多幕剧《赛金花》与《秋瑾传》”,“写《秋瑾传》‘也不过是所谓忧时愤世’”。而在第340页本章年表的1936年条下则写道:“12月夏衍《自由魂》(《秋瑾传》)发表于《光明》第2卷第1号。”
这里有两个错误:一是时间错误,经查《光明》杂志,《自由魂》发表的时间是在《光明》的第2卷第1号和第2号,而非仅仅在第1号,杂志还把该剧题目置于封面,以示重要。二是题目错误:《自由魂》发表时只叫《自由魂》,如果要表示它和《秋瑾传》是同一个作品的话,那么最好改为“12月夏衍《自由魂》(后来改名为《秋瑾传》)发表”。另外,教材的同一页出现一次《秋瑾》,两次《秋瑾传》,到底怎么回事?根据有关资料:《自由魂》1937年当年正式演出时已改名《秋瑾》,1937年1月,四十年代剧社为与《赛金花》同时赴南京演出,排演夏衍新作时,演出委员会“决将‘自由魂’改名为‘秋瑾’”。此举除了“以便更加通俗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亦颇有使此两位巾帼英雄能同时与首都人仕[士]相见也”的考虑。故1944年夏衍刊行《边鼓集》时,即有《〈秋瑾〉再版代序》一篇。1950年上海开明书店重印此剧本时,亦即以《秋瑾传》名篇。[15]鉴于此,由于教材中引用夏衍的提法是《秋瑾传》,最好能统一起来。
24、该书第九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二)》的正文第157页指出“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9月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次年9月又有《宇宙风》问世,依托三个刊物为阵地,形成了一个标榜‘性灵文学’的文学流派。”但是这却与该章年表的第169页内容不同,根据年表中记载,《论语》创办时间相同;1934年4月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创刊;1935年7月,林语堂、陶亢德主编《宇宙风》半月刊创刊。另外,在第十八章《散文(二)》的第304页正文写道:“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但是这却与该章年表的第316页内容有异。据年表记载,《论语》创办时间相同;“1934年4月林语堂等主办《人间世》半月刊在上海创刊。1939年12月终刊,共出42期。”“1935年9月,林语堂主编《宇宙风》半月刊在上海创刊,1947年8月出至152期终刊。”
查《人间世》和《宇宙风》原刊,确定《人间世》半月刊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创刊,1935年12月终刊,共出42期。而《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1947年8月出至152期终刊。
25、该书第十六章《新诗(二)》提到殷夫的同一首诗,在272页题目写作《1929年的5月1日》,在273和274页均写作《1929年5月1日》,到底孰对孰错?
经查,该诗原载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五月各节纪念号》,原题应为《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1929年5月5日作。
毋庸置疑,《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修订本)是同类教材中的佼佼者,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本文之所以指出其错漏,是希望这部优秀的教材日臻完善。也希望著者能以更认真的精神对待史料的“多”与“真”,让研究回到文本自身。[16]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大公报论文; 文艺论文; 语丝论文; 骆驼论文; 风萧萧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