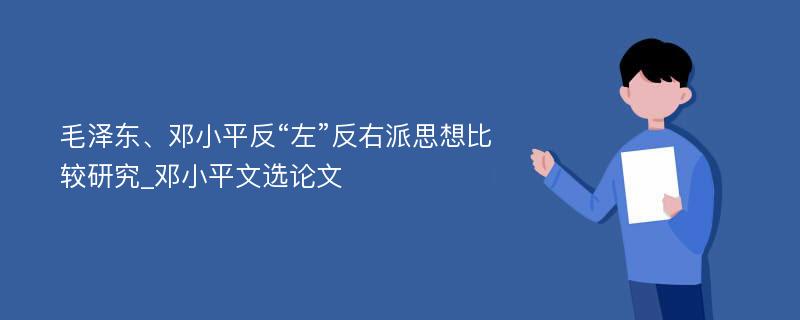
毛泽东邓小平反“左”反右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反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同“左”的和右的错误作斗争的历史。党正是在作为两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反“左”和反右的斗争后才逐渐成熟起来的。在历次反“左”和反右的斗争中,邓小平既有和毛泽东并肩战斗而结下的亲密友谊,也有因为认识分歧而被打倒的痛苦历史。比较研究两位伟人反“左”反右思想的异同,不仅有助于科学认识党史上的斗争,认识党的成长历程,更有助于为我们今后的事业提供一份宝贵的借鉴,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一、1927年到1966年,40年反“左”反右,两位伟人同大异小
1927年到1966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反“左”反右的斗争中,其思想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这40年间,他们共同经历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反对30年代王明“左”倾错误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这三次规模较大的斗争中,邓小平都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次会议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是以中央政治秘书的身份参加筹备和会务工作的,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邓小平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发言、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文字记载,但从邓小平以后的革命实践来看,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显然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三十年代,毛泽东提出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邓小平则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参与了这一理论的伟大创造。1929年12月邓小平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红七军老战士莫文华将军回忆说:“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并把它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注:《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王震将军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坚决走‘朱毛’井冈山的道路,发展革命武装,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到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农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注:《我眼中的邓小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由此可见,邓小平领导发动武装起义,自觉地走“朱毛”式的农村革命道路,这就从实践上不仅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也抵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城市中心论者,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
30年代初期,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被撤销了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以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也因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打成“毛派头子”,由于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崇高威望,“左”倾教条主义者还不敢在党外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公开批判,于是就从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福建代理省委书记罗明身上开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打击,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1984年,曾经参与这场批判的李维汉在去世前留下的回忆中说:“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注:《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毛泽东也清楚邓是代他受过,所以在第三次起用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大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注:《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从而成为邓小平复出的重要条件。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才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则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遵义会议使受排挤的毛泽东翻了身,为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受到打击的邓小平也得以解放。
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八大和八大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国内阶级斗争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从而导致了党在领导方针上的“左”的失误,特别是1957年夏天出现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的失误。到1958年,政治上的“左”扩大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搞“急过渡”、“三面红旗”,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对于这一段历史,邓小平经过冷静的历史反思,在几十年后作出中肯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因为在“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并针对“文革”前党的“左”倾错误, 邓小平坦率地承认,“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由上可见,在1927年到1966年的40年里,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反“左”反右的认识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到了“文革”前夕,邓小平对毛泽东日益膨胀的极“左”错误有了异议,除进行力所能及的抵制和纠正外,更多的时候则是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从组织上服从。“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他对毛泽东的极“左”错误在认识上和毛泽东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果从反“左”反右的角度来描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40年的关系的话,可以说是相识于反右,相知于反“左”、相悖于极“左”。
二、晚年毛泽东:名为反右,实则极左; 邓小平: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
毛泽东晚年,尤其在十年“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极“左”错误,但这种错误是以反右的形式出现的。作为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我们就不能不对左和右作具体的分析。左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反左的目标指向内部,具有自我否定性;右是站在异己的立场上说话,反右的目标指向外部,反右具有自我肯定性。党在执政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政权、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时的内外关系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敌我关系,因此反右具有自我保存的革命意义。右的错误是立场、方向性的错误,属敌我矛盾。左的错误是方法、策略问题,属于内部矛盾,这样长期以来就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执政后的共产党成为领导者和执政党,其他各派力量均处于被领导地位,这时的内外关系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代替了或至少部分代替了原来的敌我关系。因此,这时的反右行为便具有了两重性,一是反右的对象实属颠覆政权的敌对势力时,反右仍具有革命性,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二是如果反右打击的是内部不同意见、善意的批评、对党和国家阴暗面的真实的暴露,则反右属于排斥异己力量,丧失了革命性。毛泽东名为反右,实为极“左”的错误恰恰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他的这一错误的前提就在于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后中苏两党矛盾加剧,以及后来的美国侵越,印度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我国新疆、西藏,台湾当局叫喊部署反攻大陆,国内一些反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造成的各种犯罪现象增加、党内外人士对党的“左”倾错误政策的善意的批评等等,使毛泽东感到右的危险处处存在,党变修、国变色已成为现实危险,从而对国内形势作了夸大的错误估计,断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认为中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这种错误的判断必然导致将人民内部矛盾、党内不同意见、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升级到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可避免地由反右而导致极“左”错误。毛泽东反右的理论武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贯彻于“文革”的始终,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晚年虽有几次纠“左”的想法,但在反右为既定方针的框子里只能是尝浅辄止。
毛泽东重在反右,他的错误在于反右的同时忽视防“左”,只抓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走向右的反面犯了极“左”的错误。邓小平重在防“左”,他的高明在于反“左”的同时要防右。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里,邓小平在反复申述反“左”反右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不可偏废的同时,至少三次强调“左”比右危险。第一次在1987年4月30日, 邓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二次在1987年7月4日, 邓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第三次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邓小平所以坚持重点是防“左”,首先因为“左”比右顽固,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一种“左”的习惯势力,根子很深,纠正不容易,反“左”比反右难度大。其次,在党已经执政以后,政权已经比较稳定的形势下,反“左”的革命性是针对自身的,能不能反“左”,敢不敢反“左”,可以判断一个领导集团是否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多少年来反右容易扩大化,而反“左”总是不彻底,就是因为反“左”是自我革命,这比革别人的命难度大,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正是以反“左”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
毛泽东晚年对右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右的危险是夸大的,他只看到了右的危险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而没有看到“左”的危险。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只能反右,不能防“左”,以致“左”倾错误的膨胀得不到有效的制止。邓小平对“左”和右及其危险的认识则是清醒的、全面的、客观的,他认为我们当前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左”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他反“左”反右的理论武器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把双刃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就能击退一切右的进攻,因为在他看来,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中国就不会变色,右的干扰就能得到清除;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排除“左”的干扰,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能防“左”,又能防右,但最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只要不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反“左”不会导致极右,反右也不会导致极“左”,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在党的基本路线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三、晚年毛泽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名为反右, 实为极“左”的目标,邓小平坚决反对发动群众运动
毛泽东认为要达到反右(实为极“左”)的目标,最好的方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全面推行阶级斗争,以大乱求大治,彻底解决问题,这种形式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以群众运动形式进行的十年“文革”带来的只是混乱和灾难,极“左”错误借此达到顶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已对此作出了客观的评价,那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国宪法也明令禁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群众运动从此成为历史。
邓小平坚决反对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他多次强调指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在反“左”反右的方式上,他提出一系列自己的看法。对待右倾错误,邓小平认为首先领导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1986年邓小平针对学生闹事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其次,要加强教育和引导。 他指出学生闹事“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98页。)“学生闹事, 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再次,对后果严重的要依照法定程序和组织程序严肃处理。邓小平这一思想既适用于反右,也适用于反“左”。粉碎“四人帮”后,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不再搞过去的打倒批判,而是成立特别法庭,据其犯罪事实依法判决。邓小平一再指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根据法律规定“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决不能手软。
反“左”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重点,他认为反“左”的最好方式首先要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倾错误,坚持改革开放长期不变加速发展,低速度等于停步甚至后退,但是不能强制,允许看,不争论。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看准了就大胆地试,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不冒点风险,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什么事都干不成。
总之,邓小平在反“左”反右中奋力开辟的是一条稳定的道路、法制的道路、发展的道路。他要努力使中国今后的发展,牢牢固定在社会主义方向上,牢牢固定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这是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的一大特色。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