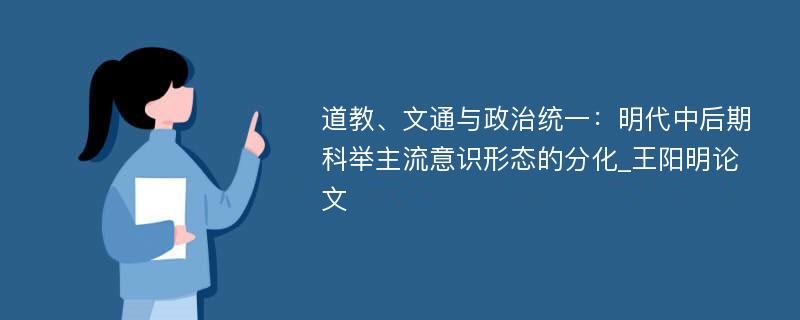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统论文,科举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后期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9-0098-08
一、明中后期“讲学”背后的道统之争
明朝建立后,继承了宋元时期的思想文化政策,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明初思想界基本上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他们大都谨守程朱之绳墨,正如《明史·儒林传》所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目,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1]这种状况固然有利于加强思想控制,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但同时也使程朱理学日趋僵化,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程朱理学的禁锢下,成化以前整个思想界都比较沉闷。最先打破这种沉闷的是成化、弘治年间的陈献章。陈献章也曾以程朱理学为宗,年近30开始跟随吴与弼学习,并反思程朱理学,“然后益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2]所谓“汩没支离者”实际上就是指程朱理学。秉持“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3]的治学理念,陈献章创立了“自得”之学,认为“道”不需外求,而是“自我得之,自我言之”;[4]他还说:“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5]陈献章的思想成为明代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故《明史·儒林传》在评价了明初“笃践履、谨绳墨”的学术特点后指出,“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6]
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心学开始兴起。王阳明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认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王阳明汲取了老庄和佛教中的心性论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重构了儒学的意识形态。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程朱理学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之一的“道统”由此开始分化,这种分化与讲学活动的兴起有关。南于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独尊的夹缝中诞生的,它要想进一步发展,在思想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培养更多的信徒。在当时来说,讲学显然是传播心学最好的方式。对此,王阳明有着明确的认识,曾多次谈及讲学的思想传播功用,他说:“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儿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说:“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8]实际上,王阳明的讲学活动和心学体系的建构基本上是同步的,早在正德初年,王阳明就开始了其讲学活动,特别是在被贬贵州“龙场悟道”期间,他一方面反省程朱理学,体悟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创立龙冈书院,从事讲学活动。[9]他还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主讲文明书院。刘瑾被处死后,王阳明先后官北京和南京,与同好一起讲学。王阳明还在家乡绍兴府和余姚县组织和主持讲学活动。在绍兴稽山书院,王阳明“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萧珍、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仁鸣、薛宗恺、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良、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作来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10]在余姚,王阳明创立了中天阁讲会,后由其弟子钱德洪主持,王阳明规定:“每月朔望初八、廿三为期”,并劝勉诸生:“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11]在先后平定了南赣的农民起义和宁王朱宸濠叛乱后,嘉靖年间王阳明又平定了广西的叛乱,其政治地位达至顶峰,学术声望日隆,从游者日众,讲学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这一点从当时固守程朱理学的士大夫对阳明心学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出,如嘉靖元年(1522年)十月,礼部给事中章侨上疏说:“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崇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12]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张履祥也说:“阳明方倡良知之学,所在聚徒开讲,效象山之高态以广其声焰。”[13]王阳明一生都以讲学为事,通过讲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王学信徒,而且使阳明心学迅速传播开来。
对于讲学之风的兴盛,嘉靖皇帝基本上持一种放任的态度,虽然在王阳明去世后,其学说一度被定为“邪说”而遭禁,但并没有真正执行,讲学活动非但没有因此而废止,反而更加活跃,从京师到地方,从都城到乡下,从书院到讲会,各地各种形式的讲学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正如王阳明的弟子王畿所说:“时江、浙、宣、歙、楚、广,会城名区皆有讲会书院,随地结会,同志士友成设皋比以待。”[14]地方上的讲会以江西、浙江最为活跃,江西省的安福县讲学组织大都称为“惜阴会”,经常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讲学活动,如刘晓惜阴会成立之初,“同志之在安成者,间月为会五日”,[15]钱德洪、王畿都曾专程从浙江来福安为惜阴会讲学。[16]浙江绍兴是王阳明的老家,他曾在这儿主持过讲学活动,王阳明去世后,这儿的讲学之风依然很兴盛。嘉靖、隆庆年间,南北两京的很多官僚也热衷于组织和参与讲学活动,如大学士徐阶“为讲会于灵济宫,使南野(欧阳德)、双江(聂豹)、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17]南京的讲学之风丝毫不亚于北京,阳明弟子欧阳德等会讲于南京,“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阱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辩相绎”。[18]耿定向督学南畿时也大力倡导和组织讲学,他和王畿、南京国子监祭酒姜宝、国子监司业周顺之等人“率六馆诸生大会于鸡鸣凭虚阁”。[19]罗汝芳、李贽等都曾在南京讲学。京师讲学之风的兴盛源于徐阶等的倡导,并带动了全国讲学风气的盛行,为此,明末的史学家谈迁评论到:“华亭讲学,为天下倡,世群而效之。”[20]
讲学实际上是争夺话语权的一种方式,是阳明心学不满于程朱理学独尊地位而向其发起的挑战,其实质是道统之争。对于阳明学派的讲学活动,程朱学派并没有无动于衷,他们意识到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是对其话语霸权的挑战,因而也大力开展讲学活动,以捍卫其话语霸权及由程朱理学建构的道统谱系。如作为程朱学派代表人物的吕柟,其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21]“所至学徒云集,为理学之宗”;[22]湛若水的讲学活动也大有与王阳明分庭抗礼之势:“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23]其他学者如吕潜等都组织过讲学活动。
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对话语权的争夺使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道统”开始分化。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道统论滥觞于孟子,唐朝时韩愈正式提出,程朱理学则大倡道统说。孟子为了争取儒家的独尊地位,一方面极力贬斥杨朱、墨子等其他各家学说,另一方面尽力把儒家学说与上古时代的统治者联系起来,建构了一个“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的儒学传承谱系;韩愈继承了孟子的学说,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正式创立“道统说”,其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宋代朱熹大力倡导“道统说”,但认为韩愈与唐代名僧大颠关系密切,排斥异端不力,因此将其排除在道统外,他还排斥同时代陆九渊的心学,而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他自己作为孟子的继承者,从而建构了一个圣圣相传的儒学谱系,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
道统说的目的在于抵制佛、道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巩固和强化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霸权。阳明心学初兴时尚无力撼动程朱理学的霸主地位,但随着讲学活动的兴起,阳明心学迅速传播并逐渐跻身于主流意识形态场域。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阳明心学被官学与科举接纳的过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及王阳明政治地位的确立,其信徒也越来越多,而且其中很多人如聂豹、徐阶、李春芳、赵贞吉、耿定向等都官居高位。在这种情况下,王学逐渐被官学和科举接纳,跻身于主流意识形态场域。隆庆二年(1568年),担任会试主考官的李春芳在其所作的程文中首次引用阳明语录。顾炎武认为自此之后“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24]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这标志着阳明心学道统地位的确立。整个明中后期,在主流意识形态场域中,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彼此颉颃,从未停止过话语权的争夺,而且大部分时间阳明心学还占据上风。嘉隆万时期,阳明心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以泰州学派为主的王学左派更是风行天下。泰州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王阳明的思想,其创始人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李贽正是沿着泰州学派的思想路径,进一步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25]李贽还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和李贽也都以讲学相尚,李贽还和同是阳明派的耿定向公开论战,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但也正是泰州学派将阳明心学引向了“异端”之路,因此,黄宗羲评价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有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坛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26]如果说王阳明致力于道统的重构,使传统的意识形态出现了裂缝的话,那么王学左派特别是李贽的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儒家的道统。
二、科举考试:文统争夺的主战场
道统必然影响到文统,而科举经义文章和策论又是文统的重要体现,因此科举就成了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争夺道统和文统的主战场。
(一)唐宋派“以古文为时文”及文统的重构
洪武年间,明太祖规定科举考试主要以程朱理学为宗,“《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27]永乐年间,明成祖又组织编纂了《五经四书大全》,“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28]进一步确立了科举考试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对此,天启、崇祯年间的制义名家艾南英说:“同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29]清代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也评论说:“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30]可见,明前期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的唯一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文统只能依附于道统。“雅正平和”、道学气浓厚的台阁体也因此居于文统的主导地位,黄宗羲对此评论道:“予谓有明之文统始于宋(濂)、方(孝孺),东里(杨士奇)嗣之。东里之后,北归西涯(李东阳),南归震泽(王鏊)、匏庵(吴宽)。”[31]李东阳、吴宽、王鏊都是明前期八股文名家,而且他们都做过会试主考官,“其取十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32]
明中后期,随着科举考试的日趋程式化,程朱理学越来越成为束缚士子们的紧箍咒,士子们因此厌倦了程朱理学,不再究心于经学义理,而是致力于揣摩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通过背诵程文墨卷和揣摩时文风气来应对科举考试,“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33]这种情势无疑会动摇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的独尊地位。实际上,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程朱理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就已经动摇,据袁黄说,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会元董玘“所批成弘间程墨,其立说皆远胜朱传”。[34]在科举考试中,程墨体现着文统,对士子起着引领作用。阳明心学初兴时,一些固守程朱理学的士大夫就借助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正学”地位打压阳明心学及其信徒,甚至斥阳明心学为“伪学”。嘉靖二年会试,程朱派的蒋冕就利用主考官出题之机,借“策问”向阳明心学发难,策问曰:“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钦?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政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乎?”[35]与试的阳明信徒对此策问大为不满,徐珊“不答而出”;钱德洪则下第而归;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则“直发师旨”,结果却被取中。[36]面对旨在诋毁阳明心学的策问,阳明弟子不但不屈从主考官的意旨,反而毫不顾忌地发挥师说,而且竟然被取中,这说明科举考试中文统已经有了分化的苗头,考官中对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看法亦有分歧。对于程朱学派借策问诋毁阳明心学,王阳明本人不怒反喜,他在钱德洪下第而归时“喜而相接”,并说道:“圣学从兹大明矣!”“吾学恶得追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37]确如王阳明所言,蒋冕的策问非但没有起到压制阳明心学的目的,反而变相地为阳明心学做了宣传,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整个嘉靖一朝,举业中试者中很多都是阳明学的信徒,其中王慎中、唐顺之、薛应旂、瞿景淳等还都是当时著名的举业大家,他们都不“拘定一家之言”,而是“洞见本源,发挥透彻”。[38]在这种情况下,文统也发生了变化。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的兴起就是文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唐宋派兴起前后,为反对台阁体雍容萎靡的文风,文坛上还相继兴起了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文风。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李攀龙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39]王世贞则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40]前后七子都只是从形式和字句上模拟古人,在思想性上则无足观。唐宋派对于前后七子的模拟剽袭之弊以及由此造成的“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41]的做法大加批判,他们师法唐宋,并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为了建构唐宋派的文统谱系,争得在科举考试中的话语权,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还将唐宋八大家的笔法融入制义,“以八家之法为功令文”,[42]唐顺之、归有光也因此而成为受士子推崇的八股文大家。他们还编选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唐顺之编纂有《文编》、《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明贤策论文粹》等,前者按体例纂辑自周至宋之文,其中大部分是唐宋名家的文章;后者则精选了唐宋名家的策论,并有唐顺之的评点。茅坤则编纂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明确提出了“唐宋八大家”。归有光编纂的《文章指南》也收录了很多唐宋文。由于这些文选类图书都是以备考的士子为主要目标读者群,加之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发达,唐宋派因此在士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顺之的《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明贤策论文粹》甫一出版就大受欢迎,以致“无籍棍徒省价翻刻”;[43]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义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44]因此深得士子青睐,以至于“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45]归有光的《文章指南》也颇受士子欢迎,并于隆庆六年(1572年)由吴县书林郑子明将书名易为《新刊批释举业古今文则》,重新刊刻。除了所编纂的文选外,他们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举业文章也借助商业出版的力量广为传播。所有这些都为唐宋派争得了在科举考试中的话语权。在唐宋派的影响下,明代的八股文也达致极盛,对此方苞评价说:“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46]
唐宋派的思想实际上源于阳明心学。唐宋派成员不仅大都推崇和信奉阳明心学,而且将心学思想融入八股文和策论中,如唐顺之提出了“本色论”,认为“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可能写出佳作,主张作文“但直摅胸臆,信手写出,虽或疏漏,然绝无烟火酸酪习气,便是宇宙间第一样绝好文字”;反之,虽然谨遵“绳墨布置”,但如果“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而没有“真精神与千古磨灭之见”,也写不出好文章,即他所说的“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47]这些思想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如出一辙,是阳明心学在包括八股文和策论在内的文学中的反映。曾师从唐顺之的举业大家袁黄还将这些渗透着心学思想的文论列入其编纂的举业用书《游艺塾续文规》中。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阳明心学的道统深刻影响了唐宋派文统的重构及科举考试。
(二)言志派文学的兴起与科举中的“离经叛道”
无论是前后七子还是唐宋派,实际上都主张复古,而且他们都尊崇儒家的诗教传统,主张“文以载道”。但是,随着泰州学派和李贽思想的风行,万历年间,传统儒学的道统谱系遭遇危机,文坛上的复古主义思潮也遭到批判,文统因此又发生变化,公安派和竟陵派由此兴起。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湖北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受李贽思想的影响,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主张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48]他还认为,人的个性各不相同,不能强求一致,“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因此文学要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49]公安派高扬“性灵说”的旗帜,对当时的文坛震动很大,在他们的影响下,晚明的许多文人加入到性灵文学的创作中。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虽然对公安派之余续末流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在文学与心性的关系上基本秉承了“公安派”的思想,仍然高举“性灵说”的旗帜。与“公安派”一样,“竟陵派”也都强调文学要表达自然的情感,如钟惺说:“夫诗,道性情者也。”[50]谭元春说:“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51]汤显祖也强烈反对当时的复古主义的模拟之风,主张文章要表达人的个性和情感。他的许多作品都以“情”字贯穿始终。汤显祖认为,“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而在于“不思而至”的“自然灵气”,他说:“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名之。”[52]“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53]性灵派文学摒弃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是文学史上的言志派,因此周作人认为“对性灵的表达乃为言志”,晚明性灵派、竟陵派文学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是“一种新文学运动”。[54]由此可见,晚明性灵派文学开启了近代言志派的文统。
无论是李贽的童心说,还是性灵派文学,都深深打上了王学左派的烙印。阳明心学本来就受佛道心性论的影响,王学左派更是援佛入儒,并汲取了老庄的思想。道统和文统的这种嬗变也直接影响了晚明的科举,使科举考试中开始出现了离经叛道的现象。八股文中弥漫着求新、求奇、求异、求趣的风气,禅宗、老庄以及其他诸子的思想也因此渗透到八股文中。李贽和公安三袁都将其文学思想融入八股文创作中,李贽撰写的八股文“直捷明快,洞然与其生平持论及讨古辨今处如贯气合”;[55]袁宏道提出,“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56]袁中道则认为,“时义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5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业思想绝非个别特立独行的文人所有,而是科举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甚至就连当时的翰林学士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如万历年间的翰林院大学士李廷机在为焦竑校正的举业用书《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中说:“夫六经之训则正也,二十九子之言则奇也。主之以至正,运之以神奇,则圣道将藉以鼓吹而为吾儒之利赖多矣,焉得辞而避之哉!”[58]翰林院编修邵景尧在为顾起元辑的《新刻顾会元注释古今捷学举业天衢》所做的序中则明确主张士子应当“本六籍以溯其源,参诸诸子百家以博其趣”。[59]其他很多举业用书也都不同程度地充斥着“离经叛道”的思想,如《新刊邵翰林评选举业捷学宇宙文芒》[60]中竟然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摘自诸子和佛老之学。朱国祚对此感叹道:“今天下之文竞趋于奇矣!”[61]由于阳明心学的影响,早在正德末年,科举考试中就出现“毁儒先,诋传注”[62]的情形,万历时期的一些举业用书更是公然批判程朱理学,如袁黄在其编纂的举业用书《游艺塾文规》和《游艺塾续文规》中就批判程朱理学,认为“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63]并借用王锡爵之子王衡的话讽刺朱熹“理欲知行动辄分为两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夹断”。[64]
由于王学左派思想的盛行以及“童心说”、“性灵说”等的影响,至万历中期,王学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程朱理学,因此王夫之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65]那些“穷经学古之儒,拘守旧闻”,也就是固守程朱传注的学者反而“困抑青衿,无所显庸于世”。[66]对隆、万时期科举考试中弃程朱而遵陆王、“参诸诸子百家以博其趣”的风气,时人李乐慨叹道:“今日试院先生出示,必言举子文字如用佛经、《老》、《庄》语者不收。据余目见中式文甚少,然何尝无佛语、《老》、《庄》家言。至序文必言平正通达,务黜奇诡,然奇诡至不能解读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体大坏,皆所好所令自相违悖致之也。后生小子看这样子,焉得心术不坏?”[67]方苞也认为隆、万时期为“明文之衰”,他说:“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68]
(三)回归程朱的努力与“文统在下”的危机
天启、崇祯年间,王学左派依然风行,言志派的文统依然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的举业文章也是延续了万历时期的文风。士子们“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69]“警辟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不纯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于其间”。[70]戴名世认为这一时期“文风坏乱,虽有一二巨公竭力搘拄,而文妖迭出,波荡复生,卒不能禁止”。[71]但是,物极必反。这一时期无论思想界还是科举考试中,都出现了回归程朱的趋势。其实,早在万历时期,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高攀龙就以程朱理学为宗,重建东林书院,以此为大本营聚会讲学,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明统综”,也就是抗衡阳明心学、维护程朱理学的道统地位,“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泉证道之失”。[72]天启、崇祯年间,脱胎于东林党的复社,也以复兴程朱理学为宗旨,其他很多文社也都以复兴程朱为己任。而且这一时期复兴程朱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制义中。如复社编纂刊行八股文选本《国表》(共六集),几社刊行《几社会义》。豫章社的艾南英有感于“今日制举业治病”不可胜道,也致力于“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73]他先后编纂了《明文定》、《明文待》、《增补文定待》、《前历试卷》、《戊辰房书删定》等八股文选本,试图借此恢复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清人阮葵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艾东乡痛天、崇文风败坏,高者阳奉孔、孟,阴归佛、老,其浅陋者又目无一卷之书,放言泛论,谬种流传,于是尊程朱,辟二氏,撰《定》、《待》二书,专主宋儒之学,文之背谬者辄涂乙,不少假借。”[74]复社、几社、豫章社等编纂的八股文选本,虽然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分歧,但回归程朱的趋势则是一致的。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的情况下,文社旨在复兴程朱理学的有组织的时文编选和评点活动,并不能挽救文统的危机,反而打破了“文统在上”的局面,孕育了新的危机。为了争得话语权,文社无不试图借选编和评点时文来影响当时的科举命题和阅卷录取工作,甚至操纵“选政”,很多民间包括文社编纂的八股文选本,其权威性已经超过了程墨。大多数士子们仍然不钻研经书义理,而是埋首于诵读时文选本,从而造成了“选者之权遂足以夺主司之势”[75]和“文章之权始在下”的局面。[76]这种“文统在下”的局面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的分化。
三、余论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由于阳明心学的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使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阳明心学开始跻身于主流意识形态场域,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必然影响到文统,而文统又直接体现在举业文章中,因此科举就成了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一个重要场域。而这一切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政统是近代的概念,最早由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意指‘政治形态’或政体发展之统绪”。[77]在传统中国,政统是以君王为代表的,君王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必须受道统的制约。表面上看,道统、文统和政统都是独立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和道德实践中,道统和文统并没有独立性,必须依附于政统,必须为政统的合法性张目。换言之,道统和文统都受到政统的钳制,必须为政统服务。明中后期,道统和文统的嬗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政统也因此而发生了些微的变化。王阳明从祀文庙之后,其政治影响也达至顶峰,其思想甚至左右朝政,正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所说:“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78]从“倡之于下”到“持之于上”,再到“遂为政事”,既体现了阳明心学对政治的影响,也揭示了学术道统影响政统的内在逻辑,说明道统不再是被动地依附于政统,而是积极地影响政统,从而使形而上的道统衍变为政治运作的指南。
“文统在下”更是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而且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话语权的下移无疑会汇聚成一种舆论力量,这种力量或多或少地会反映民意,会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制约。晚明民间舆论的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很大,明神宗之所以放弃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以及撤回矿监税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迫于舆论的压力。皇帝尚且受民间舆论的影响,各级官员特别是内阁首辅更是特别重视民间舆论,一旦遭到舆论攻击,首辅往往要向皇帝“引咎辞职”。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薛国观就是迫于复社的舆论压力被免职和赐死的。在万历年间,东林党就以舆论的力量发挥着“在野党”的作用。继东林党之后,崇祯年间,具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俨然成为了“在野党”,日本著名的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说:“他们(指复社)以全国性的力量为背景,虽说在野但是却发挥了如影子内阁般的巨大政治力量。”[79]文社能够操纵选政说明当时文社和舆论在政治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与政治权力对应的社会力量的增强,这说明晚明时期政统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晚明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分化,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但遗憾的是这种转型很快为明清易代所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