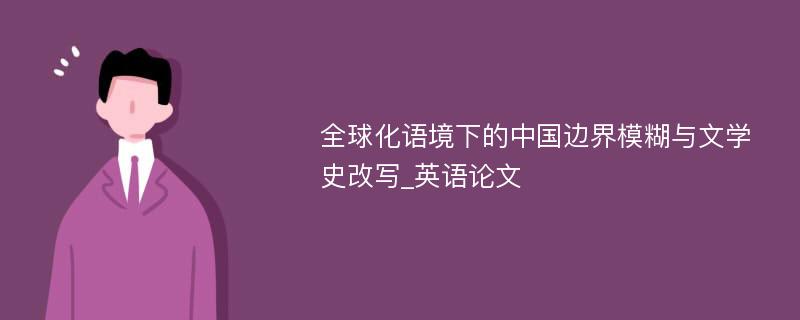
全球化语境下汉语疆界的模糊与文学史的重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疆界论文,语境论文,重写论文,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4)05-0013-04
汉语,或称“华语”,历来就是一个疆界不甚确定的语言,或者说是一个人为建构出来的现象。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民族和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民族就如同叙述一样,在神话的时代往往失去自己的源头,只有在心灵的目光中才能全然意识到自己的视野。”(注 Cf.Homi 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0,1.)汉语虽然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形成,但汉语的疆界早已超越了汉民族,甚至超越了中国的疆界,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至少在当今世界的华人社区中如此。它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现状以及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发挥何种作用?它的疆界的拓展对未来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在下面这一节里,我首先要讨论的是长期笼罩着汉语之发展的巨大阴影——英语的强势地位及未来发展走向。
全球化时代英语疆界的拓展以及英语的裂变
毫无疑问,全球化给各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定居在加拿大的时髦西班牙女郎身穿意大利服装,口中咀嚼着美国制造的口香糖,坐在一辆由亚裔越南人驾驶的奔驰车来到一家豪华的中国餐馆用餐时,已经不觉得好奇了,因为在这样一个硕大无比的“地球村”中,文化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之事实。一方面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大举入侵和深层次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弱势文化的反渗透和抵抗。所谓“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就是这样一个有效的对策。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首当其冲。对于英语国家的公民来说,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英语的普及,因为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自然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他们不需要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另一门外语,似乎也不需要为交流的困难而感到发愁。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伴随着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另一种隐伏着的危机也日益凸显了出来:面对全球化时代美国英语的大举入侵,以往被人们尊为“神圣”语言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此时此地又被放逐到了何处?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
任何一种语言要想永远保持其固有的生命力,都应当在任何时代处于一种发展的状态,都应当始终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包容状态中。英语所走过的漫长历史便是如此。当年罗马帝国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法语词汇进入英语,但这些法语词汇很快就被逐渐同化而最终成了英语语言中不可分割的表达法。英语在当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作为英语之“宗主”的大英帝国曾是19世纪末以前世界的大一统“日不落”帝国。它的公民无论旅行到何处,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和当地的人进行交流,甚至都可以见到大英帝国国旗的升降,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英语的语言文化“霸主”之地位。而到了20世纪,随着英帝国实力的日益削弱和大批原先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大英帝国确实曾受到另一些帝国的挑战。在语言文化上,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以及俄语都曾试图拓展其疆界,跻身于世界性的语言之林。但这些尝试都在英美霸主地位的置换面前黯然失色。英语的地位非但丝毫没有动摇,倒反而变得越来越牢固,英语作为一种使用范围最广的世界性语言,实际上承担着一种世界语的作用,所谓的“世界语”(Esperanto)完全是一个由少数人不切实际地制造出来的“乌托邦”式的语言,它的诞生非但未能取代英语的世界性语言之地位,反而更加加速了英语的普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正视并予以分析的。
首先,文化的殖民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殖民主义者在花了很长时间征服一个弱小民族之后,立即会想到对其民族文化进行殖民,而要想从文化上真正征服一个民族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语言作为传载文化习俗的重要手段,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往往首先进入殖民征服者们的视野,但是要让一个民族彻底改变其固有的交流方式和手段自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这方面,英语成为其殖民地的官方语言甚至母语,应当是十分成功的。而语言一旦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和表达媒介,便很难有所改变。我们至今仍可在原先的殖民地诸国和地区,如南非、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见到老殖民主义者留下的语言影响的痕迹(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如南非、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香港地区,虽然英语仍作为其官方语言,但其形式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将会越来越远离英式英语。而在台湾地区,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低于大陆的学生,年轻一代的日语水平也大大下降。甚至有人公然主张研发出一种“台语”,试图以此来取代汉语。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当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大英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时,英语的地位并没有动摇。它在很大程度上倒是与原先的民族土语和方言加以结合形成了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英语”(english)之变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或“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注:尽管不少学者喜欢使用“全球英语”(g1obal English)一词(Cf.Michael Singh et al,Appropriating English:lnnovation in the Global Busines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New York:Peter Lang,2002),但我认为这个术语隐含有“趋同”的倾向,我倒更主张用“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一词,以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英语之不同。)。它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它的出现正好体现了文化全球化的两个极致:文化的趋同性(cultural homogenization)和文化的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fication)。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也即既认识到全球化可能给文化带来某种趋同性,但另一方面又不可忽视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趋势。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有可能阻碍我们的民族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其次,一些民族——国家的自我“殖民化”也为英语的霸主地位的形成推波助澜。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实现本国和本民族的现代化首先就要与已经完成现代化大业的西方强国相认同。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历史上出现过的“全盘西化”之浪潮就说明了这一事实:为了彻底砸烂封建传统的枷锁,摧毁旧的文化及其载体语言,鲁迅、胡适、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号召大面积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以此来催生一种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话语。他们的翻译主要是通过英语的媒介来实现的,因而也导致了现代汉语的“欧化”倾向。再加之中国作家们在致力于推进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因而相当一部分现代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英语水平,至少是阅读水平,都是相当不错的。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语的霸主地位实际上已经逐步形成了。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课程中曾有一度时期主要的外国语是俄语,但文革一结束,这种英——俄语在高等学校的课程中并置的天平便迅速有所倾斜,最终形成了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大力普及和推广英语在客观上也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用途最广的第一大语言。有人称其为“自我殖民化”,当然对于这种实践的功过得失将由未来的历史学家作出评价,现在就匆忙作出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再者,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由于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的崛起和全方位称霸世界的事实,再次导致了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我们今天走进任何一家书店的外语柜台,都能轻易地找到各种出版于美国的教科书,大有压倒英式英语之势头。再加之麦当劳和好莱坞等典型的美国文化现象在全世界的走红更是使得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而美国居于西方国家之首位,因而西方化实际上也就等于美国化。要想向美国认同,唯一的途径就是要首先学好英语,以便赴美国留学(注:在这方面尤其要提及北京的新东方学校,这所民办学校的发迹完全靠的是培训“托福”和GRE的考生,可见出国留学热,尤其是“留美热”已经波及了整个青年知识阶层。这无疑也助长英语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系列的尝试终于使得美国英语取代了英式“国王的英语”或“女王的英语”之地位,使之被放逐到了边缘,但同时却大大地拓展了(美式)英语的疆界,使之稳坐世界英语之霸主的地位,并逐步将其影响向其他语言渗透。
当然,英语的普及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不利因素:它的疆界的无限制扩张以致于它作为早先的不列颠民族——国家之母语的身份的模糊。当我们今天用英语进行文化学术交流时,完全无须将其视为英美两国的民族——国家语言,而视其为一种全球性的工作语言或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话”。因此英语疆界的拓展同时取得了两方面的效果:一种(民族——国家)语言的解构和一种新的(全球性)语言的建构。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下面讨论汉语疆界的拓展也提供了对照。
汉语普及的意义与全球文化新格局的形成
英语的普及自然有其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那么作为使用范围仅次于英语的汉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前又是何种情形呢?既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全球化更为明显地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出现,那么这一现象具体体现在何处呢?就体现在边缘文化向中心的运动,也即巴巴所说的,一方面是(由西向东快速运行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则是(由东向西缓慢运行的)“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进程,也即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注:参见巴巴于2002年6月25日在清华——哈佛后殖民理论高级论坛上的主题发言《黑人学者和印度公主》(The Black Savant and the Dark princess),中译文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可以说,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和互相制约。因此用“全球本土化”这一策略也形容这种张力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诚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卷入了其中,对于谋求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来说,已经别无选择地且全方位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应当承认,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主要是发展机遇,也即全球化为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得以与西方强国进行平等竞争和对话的平台。就经济的发展而言,虽然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但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和贫富等级的差距过大所致。而在文化领域内则不然。中国虽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并在历史上有过“中央帝国”(central empire)之称谓,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丧权辱国协议的签署和大片土地的割让导致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央帝国分崩离析,并最终退居到了世界的边缘。它不得不向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列强认同,因而在全盘西化的实践之下,中国的文化几乎成了一种边缘的“殖民”文化。大批移民移居海外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跻身当地的主流文化,而要想真正跻身主流文化就得熟练地使用其语言,而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的精髓,就得进入其独特的符号和发声系统,甚至要暂时忘记自己的母语直接进行外语的思维和表达。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定居美国的华裔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中(注: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及现状,可参阅陈爱敏的博士论文《美国华裔文学与东方主义》,山东大学,2004。)。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试图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取悦主流社会的欣赏接受趣味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进行歪曲性的描写和批判,因而毫无疑问便招来了另一批人的猛烈抨击和批判(注:关于美国华裔作家之间,尤其是汤亭亭和赵建秀之间,关于中国文化本真性的争论,参见阿里夫·德里克著:《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尤其是其中两篇文章,《美国亚裔社会结构中的跨国资本和地方社群》,第82~105页,以及《从亚裔美籍人角度透视亚太区域构成》,第200~227页。)。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如哈金(原名金雪飞),则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语言优势,或者游刃有余地跻身主流文化之中,以其具有独特中国内容的英语写作打入美国市场;或者,如贝拉(原名沈镭),首先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后再由别人将其作品译成英文或日文,而最终进入国际图书市场。无论他们用英文写作或用中文写作,他们的创作实践实际上已经纳入了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被当作华裔文化语境中的“流散写作”现象来研究。而华裔英文流散写作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则在客观上起到了向非汉语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积极作用(注:关于流散写作对于推进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参阅拙作,《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当然,我们对这批精英们的努力及其成效不可忽视,但另一方面也更应该重视仍然用汉语思维和写作并试图拓展汉语的疆界使之成为一门世界性语言的人们的尝试。他们的努力虽然此时在全球化浪潮面前仍显得步伐缓慢,但其长远的效果将随着中国经济的更为迅猛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显示出来。
汉语的崛起和成为另一大世界性的语言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汉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意义,我们也许只注意到了汉语疆界的拓展之积极的方面,而有可能忽视其另一方面,也即在拓展汉语疆界的同时模糊了汉语的民族文化身份,使其也像英语一样变得日益包容和混杂。对此不少语言学家难免感到忧心忡忡。但我认为,如果果真能达到这一效果的话,倒有可能早日促使汉语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它在某些方面将起到英语所无法起到的作用,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与英语一道成为可以与之互动和互补的一种世界性语言。这一未来的前景实际上已经在下面几个方面露出了端倪。
首先,一批又一批华人的大规模海外移民致使汉语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它的疆界既是不确定的,同时又是不断扩大的。正如对华裔流散现象有着多年研究的新加坡华裔学者王赓武所概括的:“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注:Cf.Wang Gungwu,"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in Daedalus(Spring 1991) :p.181~206,especial-]y see page 184.)这五种身份在当今的海外华人作家中都不乏相当的例子,而在成功的华人作家中,第二种和第四种身份则尤为明显,而另三种身份的华人则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如何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为代价而迅速地溶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和文化并与之相认同。但具有上述第四种身份的则大有人在,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不仅本人自觉地使用汉语,同时也培养自己的后代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使得中华文化的精神后继有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事业成功后不惜筹措资金在海外兴办汉语学校,不仅向华人移民的后代教授汉语,同时也向当地的居民教授汉语。可以预见,他们的努力将在未来的年月里逐渐显示出积极的成效。
其次,汉语的大本营——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致使中国政府及其主管文化的官员们逐步认识到在全世界推广汉语的重要性,光是政府对国家对外汉语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研究项目拨款近年来就有了成十倍的增长,而各高校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海外教育学院则更是把对外汉语教学当作一种文化教育产业,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中,除了大部分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华裔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父辈或祖先当年为了跻身主流社会,不得不努力学习定居国的语言,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母语和民族文化为代价取得所定居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但中华文化的记忆从来就没有消失在他们的民族意识或无意识中,一旦这种文化记忆被召唤出来,就成了促使他们努力学习汉语掌握中华文化精神的强大动力。而他们的学成回国,则会把汉语中的最新词汇和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带到当地的华人社区,客观上起到在海外推广汉语的作用。
第三,互联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年英语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计算机时代的来临。但曾几何时,具有非凡聪明才智的中国科学家很快就开发出了各种汉语软件,使得计算机迅速在汉语世界得到普及。虽然在现阶段,互联网上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信息都是靠英文传播,但几乎各个主要的英语网站很快便有了中文版。这种中文版的网站一方面在形式上保留了原有的栏目和版块,另一方面却在内容上大大地作了更新,使之主要服务于汉语社群的网民,因而实际上成功地实现了“全球本土化”的战略。可以预见,随着汉语网站的日益增多,用汉语写作(至少是将其视为第二语言)的人数的增多,以及新的汉语软件的不断开发,用汉语传播信息的百分比也会逐步上升。对此我始终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并将继续为这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推波助澜。
综上所述,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同时也拓展了世界上主要语言的疆界,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生命力不强的语言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牺牲品,新的语言之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一大的格局中,不仅是英语,汉语也受益甚多,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时代,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也将逐步形成:它决不是一种单边的(英语)文化(culture),而是多姿多彩的(多语种)文化(cultures)。在这一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汉语文化将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汉语文学史的重新书写
语言疆界的拓展对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它将为文学史的重写带来新的契机:从简单地对过去的文学史的批判性否定进入到了一种自觉的建构,也即以语言的疆界而非国家或民族的疆界来建构文学的历史。在这方面,保尔·杰(Paul Jay)在讨论英语文学疆界的拓展及其后果时有一段话颇为富有启发意义:
有了这种意识,在不将其置于特定情境的情况下研究英美文学便越来越难了,在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历史中研究这种文学所产生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了。同时,英美两国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的明显扩张也表明,这一文学变得越来越依赖语言来界定,而非国家或民族来界定,因为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作家都用这种语言来写作。从这一观点来看,英语的全球化并非是人文学科内的激进分子旨在取代经典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主张或政治议程。英语文学确实是跨国家和跨民族的……(注:Cf.Paul Jay,"Beyond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PMLA,Vol,116,No.l(January 2001 ) :33.)
作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的汉语,难道不也面临着语言疆界的拓展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吗?在将“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这两个术语译成英文时,往往用的都是一个英文术语,而我本人对之的界定却是有所区别的,Chinese literature虽然可分别译为“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但它的开头第一个字母c却应有大小写之分,因为它包含着两个意义,也即两种身份:前者指在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产生出的文学(literature produced in China),后者则泛指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literature writte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前者应用Chinese来表达,因为它代表了特定的文学所固有的民族性,后者则应用chinese来表达,因为它反映了用(包括汉语文学在内的)所有语言撰写的文学都共有的世界性;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前者中的litera-tuer用的是单数,后者中的literatures则用的是复数。对此区别我将另文专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