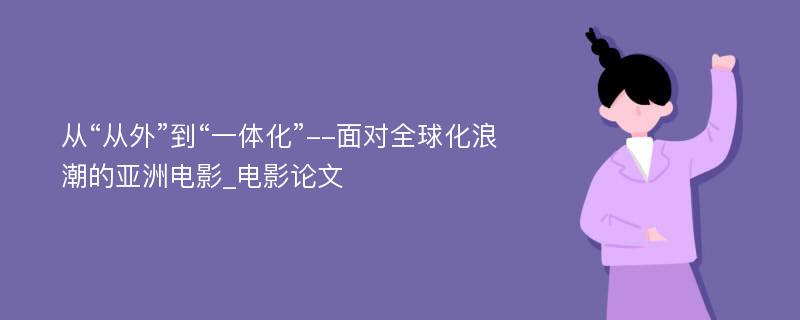
从“自外”到“融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亚洲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浪潮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电影诞生的这一百多年里,“世界”的概念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对于电影的描述也同样是如此,亚洲电影在所有主要的电影史著作中都只是篇幅很小的一个章节,大都只是对于日本、印度、中国等少数国家的影片进行一些简单的描述和观感,深入的文化和美学分析更是凤毛麟角。
我曾亲耳听到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略带轻蔑地谈起某位亚洲学者,说他的英语不太好,怎么能研究美国电影呢。这位先生却忘记了自己并不懂任何亚洲语言,而他当时正在一个讨论亚洲电影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事实上,那位亚洲学者接触到的有关美国电影的影片和资料比起英语世界中关于亚洲电影的资料不知要多多少倍。这里并无丝毫责怪这位西方学者的意思,只是为了说明在东西方之间这种信息和话语权的不对称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个“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的文化、美学观和好奇心是现今世界用以衡量亚洲电影优劣成败的准绳。这是长期以来亚洲电影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自外于世界的亚洲电影
电影是西方发明和首先发展起来的新媒介,后起的亚洲电影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对西方电影的学习。特别是亚洲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是在西方电影的带动下出现的。西方电影进入亚洲国家,让亚洲人认识了这一新的媒介。早期的西方电影在亚洲国家的放映,培育了亚洲电影最早的观众和市场,逐步推动了亚洲人自己拍摄影片的尝试。但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电影,亚洲一些国家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早在20世纪初年,中国和日本等国就相继开始了电影工业和市场的奠基,拍摄自己的影片。
但无论是无声电影时代后期的中国和日本,还是稍后发展起来的印度电影,在开始的很长时间里,国内电影市场的主要份额仍然牢牢地控制在西方电影手中,国产电影很难和欧美电影正面抗衡。生存的需要决定了民族电影必须做出美学和文化的选择。例如在中国,中国早期电影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电影公司是1922年在上海建立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公司成立之初,创始人张石川、郑正秋等看到了外国的许多影片在中国市场上很受欢迎,决定集资拍摄电影。张石川和郑正秋曾就制片方针产生过分歧。公司开始采取了张石川的方针,以市场上成功的外国影片为范例,拍摄了四部戏剧和侦探类型的短片。其中一部还邀请了一个英国演员模仿卓别林,叫做《滑稽大王游华记》。但是这些影片在市场上并不成功。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类似题材和类型的影片领域内,国产电影的整体制作经验、技术水平和投资规模都难以与市场上的主流西方电影相抗衡。之后,陷入经济困境的“明星”公司只好转而采取郑正秋的主张,拍摄了带有更多中国戏剧和文学传统的悲情家庭伦理剧《孤儿救祖记》,结果大获成功。从此“明星”公司便以不同于西方电影的题材类型,特别是接近中国传统的叙事和审美经验的艺术方法成为其他中国电影模仿的对象,在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形成时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一个公司的成功,而且是一种文化和产业策略上的成功。
整体上看,亚洲的电影一直是以面向国内观众和本民族文化圈的观众为主要市场和文化诉求的,即使有少量的跨国电影现象也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圈的现实和创造本民族文化圈的目的。虽然二战前的中国电影和战后的香港电影在东南亚国家有一定的跨国发行成就,但其对象也主要限于华人话语文化圈,并不真正具有跨文化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亚洲大片地区之后,曾致力于在占领区进行跨国的电影产业发展。但是日本电影在亚洲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建立的电影产业和发行放映体系,都是直接为其在殖民地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巩固侵略效果的政治目标服务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单向性的文化扩张,丝毫不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中国东北,日本建立了规模超过其本土电影机构的“满洲映画协会”,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发展跨国电影产业的明确政治目的。“满映”成立于1932年,在其前10年的运作中,几乎所有影片的主创人员基本都来自日本,影片从内容到风格都是高度日本化的,只能被看作是日本电影的延伸。这种电影也受到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厌恶和抵制。战时在沦陷区唯一受到广泛欢迎的女明星“李香兰”是一个隐瞒了日本人身份、被当作中国人的女演员。这多少反映了这种文化殖民政策的可悲和失败。这种赤裸裸的文化殖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立即被占领区人民所唾弃而烟消云散。二战后,由于冷战造成了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割,更把南北朝鲜半岛,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生产与市场长期分割开来。这形成了一个历史事实,在很长的时间里,其实根本没有形成过统一的亚洲电影和亚洲市场。
然而,在看到这种分割现状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分割的市场中的民族电影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亚洲国家及其电影在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的关系上都处于一种经济和文化上的弱者和他者的位置。民族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努力学习模仿而又不得不与之竞争的局面。当然,在国内电影市场形成之后,由于市场的需要,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大量直接模仿西方(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商业影片。就影片生产的数量而言,在大多数国家,这类模仿性的影片的绝对数量都占影片生产总量的很大份额。然而这些影片即使其中的一些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也很难得到广泛的社会好评。有的甚至还会由于其商业的成功而受到文化上的鄙视,这在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相当普遍。中国武侠电影的遭遇就很典型。它虽然在积累技术经验和培育观众市场等不少方面对于早期中国电影都有难以回避的贡献,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到文化人的批判,国民政府也曾下令禁映,1949年以后更是长期销声匿迹。直到李小龙风靡欧美,中国功夫的文化独特性和魅力得到西方主流话语的认可之后,才能够以比较正面的形象进入文化阶层的视野。亚洲国家优秀的、成功的民族电影在这种文化和社会语境中,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民族传统中的文化独特性的发掘和张扬,大都很重视对于各自民族风格的强调,以求在西方电影占主导的国内电影市场中能争取到本民族的观众。很长时间里,亚洲影人的成功主要基于其被国内观众的认可。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使得亚洲观众对国产电影和西方电影形成了两种很不相同的认识和评价体系,有着很不一样的欣赏期待。公众形成了一种“自外”于西方主流电影的“亚洲”的文化选择和电影观念。这并不是说亚洲人对“电影”与西方人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是说观众对于国产电影和西方电影有着不同的功能需求和艺术期待。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满足人们娱乐需求为基本诉求的好莱坞电影受到广泛欢迎。但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的迫在眉睫,类似诉求的《啼笑因缘》等国产商业影片却由于其未能直接表现这一社会现实而遭到观众激烈地抨击和冷遇。观众强烈地希望国产电影更切近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矛盾和表现爱国热情,这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迅速发展的重要的市场动因。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情景。这使得我们在亚洲电影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在不少亚洲国家,国内电影虽然常常是给看不懂或看不起外国电影的下层观众看的,但其文化策略却更像西方的艺术电影,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民族传统文化及美学情趣的表现。它深刻地影响到今天的亚洲电影在全球化电影中的文化地位和市场未来。
亚洲电影在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格局里,特别是在西方主流电影的视野里,首先是以其文化独特性而引起关注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仅有文化的独特性还是不够的。什么样的文化呈现是有审美价值的,是值得受到关注的,这是由拥有话语权力的西方世界所决定的。那些在“世界”上获得成功的亚洲电影必须是西方世界希望了解的,同时也必须是在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和知识结构体系中能够被读解出“有价值”的意义的。至于这些意义的读解在多大程度上与作者的初衷相吻合并不那么重要。
二战后,随着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起飞,与西方文化交往的增加,其文化表现也越来越具有与西方主流的可交流性。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些电影现象也开始相继引起西方主流世界的认识和关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新电影崛起的时间大多都与当地的政治变革和经济腾飞基本同步。亚洲国家地区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一方面引起西方了解亚洲民族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使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生活面临西方社会已经遇到过的类似社会和文化问题。当亚洲的艺术家能用一种基本符合西方观众关于自己文化的知识和想象、又有很明显的本民族特色的题材和表现方式,来展示那些与西方人已经面对的问题相类似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时,其思想和文化上的价值自然就比较容易得到认可。美学上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上的可沟通性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些亚洲电影成功的基础。
可是,西方将哪些东方民族电影纳入其关注的视野并不是随机的,这种关注与这些电影的生产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受世界关注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首先被西方人纳入视野的亚洲民族电影是日本电影。日本电影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最早受到关注,这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出于对敌人了解的需要大大推动了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西方日本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菊花与刀》就与此分不开。而日本在亚洲是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已经经历了近百年“脱亚入欧”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其经济和社会中已经包含了较多与西方现代社会共同性的现象和问题。这使得一些日本电影尽管在美学上与西方电影有很大不同,但其所反映的生活和文化思考却比较接近西方人的社会和文化关注,因而也比较容易得到西方观众的理解。黑泽明成为第一个被西方世界承认的世界级电影大师的亚洲人并非偶然。《罗生门》作为一部艺术构思和表现都十分精湛的艺术作品,其富于传奇性的历史故事,与现实之间的较大距离使其意义内涵具有了高度的抽象性。其中对于真实、真理以及对事物认识和表述的相对主义思想很容易引起正在经历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的西方社会的共鸣。由黑泽明开始,亚洲电影越来越多的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沟口和小津被西方人重新“发现”。大岛渚和今村昌平等也相继受到赞许。随着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关注的视野也逐渐从日本扩大到了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后来陆续有印度,中国的香港、台湾、内地,韩国,伊朗电影得到广泛关注。
在具备内涵的可沟通性和可读解性的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生活的现实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反而是越具有猎奇色彩的传统东方文化表象的影片越容易引起关注。《罗生门》、《感官王国》等影片成功固然与其精彩的艺术形象和巧妙深邃的意义表达分不开,但在本土观众看来更加切近日常生活和富于情感与艺术冲击力的《活下去》、《青春残酷物语》却较难在西方世界得到同样广泛的欢迎。当然,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表象不仅指历史的,还有对具体对象国家(地区)的现实政治和经济生活方式的文化想象。《活着》、《霸王别姬》就不仅因为具有了京剧和皮影戏等绚丽的传统文化表象,还与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机智讲述方式适应和丰富了西方人对铁幕后中国生存方式的想象分不开。
但是在“世界”上的成功和在国内得到认可并不是一回事。早期中国的武侠片和稍后印度的歌舞片等一些商业类型虽然在区域内极受欢迎却在西方难以引起共鸣。对于带着猎奇的眼光看东方电影的西方主流世界的电影观众和学者来说,东方电影的魅力离不开其文化独特性带来的新奇感。可是那些能给西方观众带来新奇感的文化表象的影片,在本土并不一定也能得到同样的认可和赞许。一些找到与西方世界沟通的途径的亚洲电影在国内却饱受争议。而且其受到的批评往往都是被指为褊狭、歪曲和丑化地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无论从黑泽明、大岛渚到陈凯歌、田壮壮和张艺谋等中国第五代早期的艺术电影都曾面临这种局面。难以抹去的受侵略、压迫和欺侮的痛苦记忆带来的矛盾心态往往使亚洲观众很难立即接受西方世界这些赞扬和“宠幸”。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本民族电影和外国电影的双重标准和“自外”意识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民族电影市场生存和艺术发展的一种推动力,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电影的跨文化沟通。
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的今天,经济一体化带来文化消费需求的日益接近,这种“自外”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冲击。近二十年,伴随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跨国媒体市场的发展极大地打破了地域性的市场壁垒,单独的民族电影市场和民族文化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本土的电影产业越来越难以只靠本土市场支撑。与此同时,由日益普遍的跨国流通的媒介产品培育出来的新一代电影观众已经越来越不再认同于对民族电影和外国电影的双重标准。民族电影再想完全“自外”于“世界”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融入世界的亚洲电影
随着亚洲电影制作经验的积累和经济技术实力的不断发展,首先在内部市场,商业类型不再是对西方已有电影类型的粗糙模仿,而逐渐形成了一些有鲜明特色并精良成熟的商业类型。香港的功夫片、枪战片使成龙和吴宇森在主流西方电影创作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亚洲文化因素也日益成为西方主流电影新的文化资源。不仅有了《花木兰》这样的题材的借鉴,还有了《午夜凶铃》等的版权交易。在与西方主流市场的联系与沟通日益发展的同时,亚洲电影更加引人注目的新现象是亚洲内部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区域性电影合作的蓬勃发展。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亚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一切都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电影走出分割独立发展的格局提供了可能性。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两岸三地新电影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崛起显现了超越政治分割的文化整合的端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广泛出现的电影生产和市场方面的融合与合作更呈现出其市场前景。
这种合作的出现不仅具有区域性市场的意义,随着亚洲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融入”不仅成为必然的趋势,而且也越来越从最初的被动应付,变成了一些亚洲电影人的主动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亚洲电影制作者开始选择有意识地“融入”以至“进入”主流电影。不再像以往那样满足于靠民族特色在本土市场上分一杯羹。努力整合区域市场内的资金、创作力量和潜在的观众资源,甚至借助期望打入自己市场的西方资本,生产高质量的“商业电影”,在区域性市场内与西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的正面抗衡和拼搏,已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在这种情景下,电影的民族特色和追求并没有完全被放弃,但同以往的机制依旧有很大的区别。民族的特色已经不再是内向的市场生存策略里所必需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武器,而是自觉地被用来作为寻找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有利生存位置的工具。继《卧虎藏龙》在“世界”市场获得成功之后,《英雄》、《十面埋伏》和《无极》等纷纷步其后尘走向“世界”。在这些影片中,来自不同国家,长着类似面孔却说着不同语言的演员们,穿着日本服装师设计的服装,混杂地使用着中国长剑和日本弯刀,中国导演讲述着日本武士的故事(《天地英雄》),香港导演演绎着韩国女子的传奇(《神话》),韩国导演搬演中国姑娘的神话(《武士》)。它们给西方观众创造出的文化新鲜感已经不再是任何单一的“民族”的,而是融合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多种民族生活和审美因素的一种“泛东方”的文化表象。这其实也反映出亚洲人已经多少认可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东方”定位。另一方面,亚洲的艺术电影也开始在全球性市场中寻找自己商业生存的位置。中国内地一些新生代电影导演在欧洲艺术电影市场的成功运作是与《英雄》、《无极》等相辅相成的另一种“融入”方式。今天,亚洲电影在西方可能仍是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上的他者”,但已经不再“自外”于“世界”之外,而是自觉地身处全球化的电影市场和文化之中了。
在看到亚洲电影“融入”世界的历史趋势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正视亚洲电影面临的困难局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好莱坞依仗强势的经济规模和技术实力席卷全球电影市场,亚洲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新一代电影观众对民族性内涵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减弱,是推动亚洲电影不能“自外”于主流电影的重要根源。“融入”世界是一个既主动又被动的过程。亚洲电影仍处于市场上的弱者和边缘的位置。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业,为了生存,不可能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流市场。由此,亚洲电影跨越国界,不仅是制作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市场需求;不仅有电影工业的国际合作,也有美学和艺术上的融合。今天的亚洲电影正在超越国界,一种新的东方电影正在形成。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同经济的全球化不能抹煞文化的多样性一样,创建统一的亚洲电影市场的追求和努力,并不能以牺牲和破坏各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为代价。对于当前的这种“东方”式的电影,在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民族国家的市场藩篱,推动区域性市场形成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要看到其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潜在威胁。这种“东方”电影所营造的文化表象,即使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其结果仍然是在继续强化着西方关于“东方”的传统文化想象,不会对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化产生任何真正具有价值的冲击。
要真正形成和发展属于整个亚洲的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到合作和整合前景的同时,我们需要认真总结亚洲各国在独立发展时的历史经验,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才能真正推动亚洲电影的形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