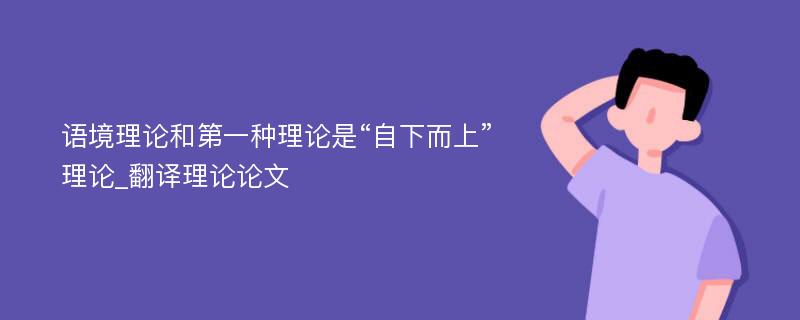
语境论与一是到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是论文,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3)03-0005-10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一是到底论”受到的最大批评之一是:一“是”到底的翻译无法贯彻始终。与此相应,语境论似乎是一个很好的立场和选择,即根据不同语境选择不同的翻译[1]。在我看来,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一是到底论与语境论本来不应该是矛盾的,而应该是相通的。它们成为两种对立的观点,这其实是有问题的。过去我一直在论述一是到底论①,很少表示赞同语境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语境论注重讨论being的词义及其翻译,而我一直强调如何理解西方哲学,注重文本分析。二是我不能同意语境论者的一些论证。基于已有的讨论②,本文试图说明,一是到底论与语境论字面上似乎是对立的,其实并不矛盾;坚持一是到底论并不会违背语境论,而主张语境论并不一定会得出反对一是到底论。不仅如此,二者的相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认识到这一点,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being,从而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
一、语境论的批评及其弱点
语境论的一个基本认识是,being是一个多义词,既有系词含义,也有存在含义,因此应该在不同语境下把它翻译为“是”或“存在”(或“在”、“有”)。基于这种认识,语境论者认为,
[论1]面对一个希腊文的多义词我们有可能用一个中文词去理解它吗?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进一步的追问是:我们有可能用一个中文词去翻译它吗?结论同样是不可能。面对希腊文eimi及其一系列变化形式,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结合具体的语境,选用最恰当的中文词汇去理解和翻译[2]。
由此可见,一是到底乃是不行的。
顺便说一下,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一直在做与being相关的文本分析,并基于这样的分析来探讨being问题。这样的分析和讨论无疑是依赖于语境的,因此在我的论述中看到和读出赞同语境论并不是什么难事。基于这样的认识,语境论者进一步认为:
[论2]……在这里我们看到王路教授同意要对语境作分析了,开始分析语境必然导向的结果是什么?不正是“一‘是’到底”的主张的瓦解吗[3]?
由此可见,“一是到底论”乃是无法坚持的。
字面上看,语境论者的观点很简单,也很清楚:既然being是多义的,就不可能一“是”到底。既然同意语境分析,那么就无法坚持一是到底论,因为对being表示“存在”的语境进行分析之后就无法用“是”来处理。在语境论者看来,一是到底论的问题和矛盾之处是显然的,根本站不住脚,因此无法实施,由此他们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质疑:
[论3]我确实不明白,在此前提下怎么可能只用一个中文词‘是’来理解和翻译多义的eimi[4]。
语境论对一是到底论的批评有很多,但是以上三段引文大概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批评的要点。我把它们概括为三个问题。第一,既然being有多种含义,怎么可能只以“是”来翻译和理解它?即只以其中某一种含义来翻译和理解它呢?第二,既然同意being的含义依赖于其语境,并且同意being有多种含义,怎么可能只以“是”来翻译和理解它呢?即对不表示系词的含义和语境丝毫也不作考虑呢?第三,基于前两个问题,怎么可能还要坚持一是到底论呢?语境论的这些问题很明确,理由似乎也很充足。面对这三个问题,一是到底论似乎处于两难境地,难以回答。但是我不这样看。在具体地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就字面意思谈一谈语境论。
我主张文本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我是赞同语境分析的。但是我从来不谈语境论,主要原因在于,我认为语境论字面上是可以有歧义的。表面上看,既然being有存在含义,那么根据语境分析,把它有存在含义的地方翻译为“存在”,当然是有道理的。同时,一是到底似乎也就站不住脚了。既然如此,所有关于being的讨论甚至争论还会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这样看来,强调being的系词含义不过是夸大了其中一种含义,至多也只是看到了其中一种含义而已。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对语境论做一种字面理解,即脱离了being的语境分析来谈being的多义性及其理解。而这样来理解和阐述对being的翻译和理解,注定是有问题的。简单的举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里的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开篇处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to on hei on”,又比如海德格尔的名著是Sein und Zeit。这里的being(on,Sein)是什么意思呢?它们应该翻译为什么呢?这里的语境又是什么呢?该如何进行语境分析呢?现有的中译文为“存在”。难道这是依据它们的语境做出分析和理解之后的结果吗?我不这样认为。即便明确了要做语境分析,在这两处也不太容易知道该如何进行语境分析。即使知道或认为being有系词和存在含义,在这两处也无法分析出being是系词含义还是存在含义。相比之下,一是到底论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翻译为“是”就可以了。
也许语境论者会认为,虽然这两处无法对being做出语境分析,因而看不出being是什么意思,但是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相关著作都是它的语境。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分析则可以看出这两处being的意思。假如是这样,那么就应该看到,与being相关,亚里士多德谈到的那些理论,比如关于范畴的理论、关于实体的理论、关于四因说的理论、关于矛盾律的理论,以及关于being的辞典解释等等,海德格尔关于传统看法的总结概括以及他自己的种种论述,特别是其中明确关于系词的讨论,以及他的举例说明(“天空是蓝色的”)等等,都是非常明确的系词意义上的论述。由此我想问,难道这些不是他们谈论being的语境吗?难道它们不应该作为翻译他们所谈being的依据吗?
以上两个例子比较典型,其实在文本中有大量语境含糊的情况,比如人们直接谈论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事物are的尺度,也是事物are not的尺度,人们直接谈论矛盾律,一事物不能同时既to be又not to be,以及人们直接谈论being或与being相关的情况,比如being of truth或truth of being。对这些含有being的文本做语境分析,如何能够得出结论说:它们所表达的乃是存在含义呢?所以,语境论不是不可以讲,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在字面上谈语境分析,其实是有缺陷的。与being相关,有一种观点认为,把being理解为存在乃是哲学的理解,而把being理解为系词则是逻辑的理解;强调being的系词含义含有一种危险的倾向,这就是把它的哲学含义排除在外。这虽然不是语境论者的观点,但是语境论无疑可以为他们提供辩护,因为对一句话、一段话,乃至一篇文章、一本书做出不同理解,无疑依赖于语境分析。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道理。比如前面提到的例子与论述及其相关语境,究竟是哲学的还是逻辑的?究竟应该做哲学的理解还是应该做逻辑的理解?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对不对姑且不论,谁又能够做出明确的区别呢?
上述问题仅仅是字面上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单纯或仅仅强调语境论,肯定是不行的。下面让我们具体讨论语境论者的观点,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二、being的多义性
论1提到being是多义词,提到它有一系列变化形式③。它强调being的多义性及其各种形式变化,并由此得出对它的翻译不能一是到底。因此这两点首先需要我们认真探讨。
being确实是一个多义词,但是它的多义性却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being有系词和存在两种含义,这种观点有两个基点,一点是关于系词的认识以及这个术语的使用,另一点是关于存在的认识以及这个词的使用。我曾经说过,我不知道这种解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就我看到的文献,早在中世纪就有了[5]。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探讨being及其相关用语的时候,人们已经明确地使用“系词”(copula)和“存在”(existence)这样两个词。我认为,明确地使用与没有明确地使用“系词”和“存在”这两个词来解释being,乃是有重大区别的。循此线索,对我们阅读相关文献乃是很有帮助的。今天人们无疑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being有系词和存在两种含义。在阅读相关文献中,人们自然可能会对出现的being及其相关用语做相应的理解。但是,就一个谈及being的特定文本而言,使用还是不使用系词和存在这样的术语,还是有重大区别的。假如它使用了这样的术语,那么对它讨论的being做相应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或者应该说,必须做这样的理解。但是假如它没有使用这样的术语,人们还要做出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道理,就是需要讨论的,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这样关于being的理解,无论是关于系词的还是关于存在的,都是当下读者做出的,而不是文本本身提供的。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亚论]事物被说“是”,可以在偶性的意义上,也可以依其自身。比如,在偶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公正的人是文雅的”,“这个人是文雅的”,“这位文雅者是人”;这正如我们说,“这位文雅者在造屋”,因为这个造屋的人恰好是文雅的,或者这位文雅人恰好是建筑师;因为在这里,“这是这”的意思是说:“这是这的一种偶性”。上述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当我们说“这个人是文雅的”,“这位文雅者是人”,或者说“这个白净的人是文雅的”或“这位文雅者是白净的”时,在一种情况,这是因为两种性质恰巧属于同一个东西,而在另一种情况,这是因为一种性质,即谓词,恰巧属于一个是者。而“这位文雅者是人”的意思说,“文雅的”是人的一种偶性。(在这种意义上,“不白的”也被说成“是”,因为以它作偶性的那个东西“是”。)这样,一事物在偶性的意义上被说成是另一事物,要么是因为二者属于相同的是者,要么是因为前者属于一个是者,要么是因为前者虽然是一种被谓述的性质,但本身是一个是者。
依自身而是恰恰表现为那些谓述形式;因为有多少种谓述形式,“是”就有多少种意义。所以,在谓述表达中,有些表示一事物是什么,有些表示量,有些表示质,有些表示关系,有些表示动作或承受,有些表示地点,有些表示时间,“是”与这些谓述表达分别是相同的。因为在“一个人是一个保持健康者”和“人保持健康”之间没有区别,在“一个人是一个行走者或收割者”与“一个人行走或收割”之间也没有区别。而且在其他情况也是如此④。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关于being的辞典解释。十分清楚,亚里士多德在讨论being,指出它是多义的;同样清楚,他没有使用“系词”和“存在”这两个术语。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这里所说的being的不同含义,是指它的系词含义还是指它的存在含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翻阅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文献,既可以看到比较一致的看法:人们都认为这段话谈论的being有系词含义;也可以看到不太一致的看法:许多人认为这里谈到了being的存在含义⑤,也有人认为这里没有谈到being的存在含义[6]。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being的论述,人们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它有系词和存在两种含义。其二,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being的系词含义,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其三,关于他说的being的存在含义,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而这些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谈论being时没有使用“存在”这一术语,而人们在讨论他的思想时使用了“存在”这个词,因而涉及对这个词所表达含义的理解和认识。
假如不预设being有系词和存在两种含义的前提来看这段话,情况大概不会是这样。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谈论being时没有使用系词和存在这样的术语。从他所谈的内容看,他谈的being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系词意义上的东西。比如他举的例子“这个人是文雅的”等等具有“S是P”这种形式。比如他谈论的谓述形式即谓词对主词的表述方式,亦即他的范畴理论,也具有“S是P”这种形式。特别是他把他举的例子明确地归结为“这是这”,并且以此来说being的意思,这无疑是以自然语言直接表达出“S是P”这种形式。因此很明显,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使用系词这个术语,但是他谈论的完全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因此他所谈的being乃是“是”,而不是“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这里谈到being的多义性:可以在偶性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依其自身的意义上说事物“是”;有多少种谓述形式,“是”就有多少种意义。这就表明,即使仅仅在系词的意义上来理解,being也是多义的。比如,“是人”与“是文雅的”意思就不一样。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同样是说being是多义的,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可以表示being的多义性,即“是”这个词本身是多义的,而今天关于系词与存在含义的解释也可以表示being的多义性。这两种多义性还是有不小区别的。前者不需要存在含义的解释,而后者借助了存在含义的解释。我强调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上述语境论者三个观点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那样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
[论4]在这一点上(即being有系词和存在含义一引者),我们看到所有学者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都认为这个希腊语词是个多义词。所有学者也都认为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到应该与其含义完全相当的词汇。[7]
亚里士多德没有用过“存在”这个术语,因此他对being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存在解释。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过系词这个术语,但是他对being的明确解释确实是系词意义上的。不仅如此,这也是学者们公认的看法。或者保守地说,在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的论述中,在学者们公认的看法中,他说的being主要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确实认为being是多义的。这就说明,即使把being看作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它也是多义的。换句话说,being的系词含义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多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就不能把它翻译为“是”呢?为什么就不能找到一个含义完全相当的汉语词汇呢?以“是”来翻译being为什么就不能表示它的多义性呢?
三、系词含义与存在含义
being的系词含义是清楚的,在人们使用了系词这个术语之后是这样,在此之前大致也是这样。而being的存在含义则完全不同。在人们使用了这个术语之后,关于being的讨论增加了这一部分内容,甚至being的存在含义成为讨论相关问题的预设前提。但是在具体讨论中,常常会有不清楚的地方,比如关于亚论的解释。人们可以认为,有了关于being的存在含义的明确认识,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多一种考虑,多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这是一种哲学的进步。假定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让我们抛开亚里士多德关于being多义性的论述,而仅在系词和存在这种意义上来考虑being的多义性。联系语境论的观点,我们就要讨论,鉴于这种多义性,是不是可以一是到底?是不是可以坚持一是到底论?
字面上可以看出,系词含义与存在含义这两种解释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句法解释,或者说,通过句法来说明语义,而后者仅仅是一种语义解释。所谓系词含义,指的是being一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即它联系主语和表语(谓语),一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这是这”。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它自身没有意义,与其所联系的表达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所以,being的系词含义是明确的,因为它的句法作用是清楚的,而它的语义可以多样,因为它可以联系各种表达,而这些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由于这种认识是明确的,因此being的系词含义一般来说是清楚的,这从它的表现形式,即“S是P”可以看出来。
相比之下,存在含义就不是那样清楚。直观上看,它似乎不是一种句法解释,理解起来好像没有语法的尺度可以依循。在讨论being问题的时候,人们强调being有存在含义,但是这种存在含义是如何表现的,却往往不受重视。好像只要being有存在含义,把being翻译为“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考虑being的存在含义,应该认真考虑它为什么会有存在含义?因为这并不是一个自明的命题。比如在亚论中,我们就看不到being的存在含义。直观上说,being一定要表示存在,才会有存在含义。那么它在什么情况下表示存在呢?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含义是如何表达的呢?
在西方哲学关于being的讨论中,大致有两种情况可以表示存在。一种情况是“上帝is”这个句子,另一种情况是含“there is(ale)”这样词组的句子⑥。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there is”这种情况讨论得不多。这大概主要是因为,这是英译中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是一种特殊的句式。卡恩在谈到希腊文being(einai)的存在用法时指出,该希腊文动词有一种特殊用法:前移至句首,以此强调它所引出的那个名词所表达的东西。这样的句子无法以同样的形式翻译为英文,因此要在being前面加上there,由此形成“there is(are)”这种表达,意思是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这种句式不具有普遍性。比如它在德语中的相应表达是“es gibt”,字面上与being(Sein)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谈论being的时候举过许多例子,少的时候可以是两个[8],多的时候可以是14个[9],但是都没有这种形式的句子。因此这种形式的句子对being含义的理解似乎不是那样重要。在我看来,人们在谈论being的时候很少谈论这种句式,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系词方式,即“S是P”表达的主要是对世界的认识,对关于人的情况的认识,谈论being与系词相关,实质上是与这种认识和关于这种认识的表达相关,因此才有意义。而there is这种方式不是这样的,因此在讨论being的时候忽略它并不影响关于being的讨论。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上帝is”是一个经常要被讨论的句子,至少是被讨论过很多的句子,我也讨论过多次[10]。这里再简单说一下。“上帝is”是关于上帝的表达,因此也可以看作表达了关于上帝的认识。由于基督教长期的影响,这个句子在哲学讨论中盛行了很长时间,对哲学造成了重大影响。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以“上帝is”来讨论being与在系词的意义上讨论being乃是不同的。讨论being,系词的含义必不可少。但是“上帝is”却不是这样:可以有它,也可以没有它,比如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就没有它。即使在一个人的讨论中,也可以有时候有它有时候没有它。比如海德格尔在讨论being的举例中,有时候有它,有时候就没有它。关键在于,即使没有它,也不影响对being的含义说明⑦。这就表明,“上帝is”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句子,没有普遍性可言。
综上所述,being的存在含义主要来自“上帝is”和“thereis”这样的表达,而“上帝is”又是其最主要来源。字面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这两种表达中,being的表达方式不是系词,因此与系词有根本性的区别。认识到这一点,则可以看出,即使being的存在含义也可以是依赖于being的句法形式的,即它不做系词的时候。实际上,对于being的存在含义,也是有人这样认识的,比如有国外哲学史家认为:“像其他学者一样,我的写作迄今一直基于一种假定:在没有谓项使用时,einai的首要含义(如果不是唯一的含义),乃是‘存在’(to exist)。”[11]“没有谓项使用”,无疑是指“S is”或“a is”这样的句式,这显然依赖于与“S是P”这种句式的区别。国内也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认定eimi是一个多义词,有‘存在’的含义,并且认定eimi在句子中不作系动词‘是’解,而作‘存在’解,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地方出现了‘存在’一词。”[12]“不作系动词‘是’解”,无疑指与“S是P”不同,因此也依赖于与系词用法的区别。这就说明,认识句子中being的存在含义,在不同程度上终归是要依赖于对系词的认识的,因为其存在含义出现在那些不是系词的情况。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总结说,being一词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系词,这也是它最主要的用法,最普遍的用法;另一种不是系词,或非系词用法,这是它比较特殊的用法,当然也是不普遍的用法。这仅仅是being一词的句法区别。从语义的角度则可以说,being的系词用法表现为它的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来自它的语法形式和作用,即“S是P”,称为系词含义。being的非系词用法也表现为它的一种含义,这种含义也来自它的语法形式和作用,即“上帝is”和“there is”这样的情况,称之为存在含义。
四、存在含义的语境
说明了being的系词含义与存在含义的区别及其识别方式,现在我们可以来谈一谈being的翻译。being的系词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翻译为“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天空是蓝色的”。需要讨论的则是其他情况。由于“there is”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也不是关于being讨论中的常见话题,因此我们不讨论它⑧。我们只讨论“上帝is”。这里的问题是:“上帝is”应该翻译为“上帝是”,还是“上帝存在”?
按照语境论的看法,“上帝is”大概应该翻译为“上帝存在”,因为这里的is明显不是系词,因此“不作系动词‘是’解,而作‘存在’解”。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提供“上帝存在”这个译文,另一个是给出这个译文的理由,即关于为什么这样翻译的认识。在我看来,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大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给出的译文却是有问题的,至少是可以质疑的。
从翻译的角度看,既然认识到这里的is表示存在,那么根据这里的语境把它翻译为“存在”,似乎不会没有道理。因为这样做似乎恰好是翻译出这个词的意思。但是,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依然是会有问题的。
首先,这种存在含义是如何认识出来的,或者,它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如前所述,这是从being一词的非系词用法识别出来的。因此这里有两个层面问题,一是可以看到being的非系词用法,二是在这种用法中读出存在含义。这在“God is”中无疑可以做到,因为其中的is与being的通常用法不同,由此可以看到这是一种非系词用法。由于看到这种与系词不同的用法,因而可以认为它具有与系词不同的含义,存在含义则是基于这种区别认识的解读结果。但是这种认识在“上帝存在”中荡然无存。因为“存在”不是系词,而是一个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词。这样,字面上我们看不到它与系词的联系,看不到它的非系词用法,因而看不到可以从非系词用法到存在含义的解读过程。而如果我们把它翻译为“上帝是”,就与“God is”对应起来:即保留了字面上being的非系词用法这种特征,又保留了把这样一种特殊用法解读为存在含义的可能性。
其次,为什么要保留这种识别存在含义的方式?应该看到,being的存在含义主要是随着“上帝is”这个命题的引入和讨论而确定下来的⑨。这个命题的要点在于它涉及being,因而与形而上学的核心相关,但是它与过去的通常讨论有所不同,衍生一些新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是一种非系词用法,因而与系词用法不同,其结果引来关于“存在”(existence)的讨论。与这种方式相关,后来产生了许多十分重要的哲学讨论。比如康德的著名论题“being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康德的讨论不仅直接与being相关,而且批评了引入existence一词所带来的问题和麻烦。由此可见,保留being的非系词特征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引入存在含义这种认识和讨论的基础。而所有这些,对于哲学讨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理解与翻译是不是一回事?论1和论3提到了对being的理解和翻译,针对“God is”这个句子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中的is是一个词,因此无论如何理解,也要把它翻译为一个中文词。按照语境论的做法,似乎应该翻译为“上帝存在”,即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而我坚持认为,应该把它的翻译为“上帝是”,即把它的非系词特征——识别其存在含义的可能性——翻译出来。这是因为,一个词与它所表达的含义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从英文的角度说,God is与God exists肯定是不同的。后者可以是前者的解释,但是前者绝不是后者的解释。对照德文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God is大概也可以翻译为Gott existiert,但是人们一定认为,应该把它翻译为Gott ist,而且这也是通常的做法,尽管人们不会反对这里的ist有存在(Existenz)含义。英德语言转换也许有便利之故,但是保留了语言的对应性,保留了being的非系词特征,因而保留了它的存在含义的解释可能性,却是不争的事实。英德语言转换是如此,西语与中文转换翻译难道不应该也是这样吗?无论怎样理解,“上帝存在”只是“上帝is”的一种含义的翻译,而不是它的一种对应翻译。理解与翻译,大体上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being这样关键的哲学点上,二者却会有重大区别。
语境论强调在不同语境下把being的不同含义翻译出来,意思绝不会只局限于“God is”这个句子。而上述以God is为例的讨论,则是针对语境论所说的所有语境。
一个词的使用有语境,一个词的意思依赖于语境,这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说being有不同含义,比如有存在含义,后者依赖于特定的语境,也是没有问题的。根据不同语境,分析出being的不同含义,并相应做出不同翻译,这样说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些笼统的说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涉及being的讨论,仅仅这样说就不够了。
首先可以问,为什么人们的认识在being的系词含义上比较一致,而在涉及存在含义时却常常会出现问题呢?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因为系词乃是being自明的用法,或者说,是它最普遍的用法。但是,假如进一步追问,什么是最自明、普遍的用法?为什么是自明、普遍的用法?似乎就要思考一下。不过,这似乎依然容易回答。它是日常语言中的通常用法,甚至是离不开的用法。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在一切命题中,“都用得着”这个being[13];比如“天至是蓝色的”,“我是快活的”。在我们“简单而通常的,几乎随意的”说话时,being“被以一种词的形式说出来,这种形式使用频繁,以致我们几乎不注意它了”。[14]而being的存在含义则不是这样。
于是可以问,being的存在含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了前面的讨论,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回答:来自它的非系词用法?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它的非系词用法呢?问题还是那样容易回答吗?前面讨论的“God is”固然是(前面提到的“there is”也可以是),此外还有什么情况呢?我这样问,目的在于把being的语境具体化,确切的说,把being的存在含义的语境具体化。在我看来,这样谈论being的语境,谈论它的存在含义,才不至于空泛。
假如认为being的存在含义来自(或主要来自)God is这种非系词用法,则可以明确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这就是,无论是系词含义还是存在含义,它们都来自being在句子中作动词时的含义。正像海德格尔所说,“这个‘是’(das Sein)乃是从动词(sein)变成的名词。因此人们说:‘是’这个词是一个动名词。定出这个语法形式之后,‘是’这个词的语言标志就得出来了”⑩。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being的时候,它是名词或以名词形式出现,而它的含义则来自它的动词。
现在可以问,除了“God is”这样的语境,或与之相关的谈论being of God这样的语境,还有什么语境能够读出being的存在含义呢?而这样的语境在西方哲学中又有多少呢?认为being有存在含义是一回事,在出现being的地方读出存在含义则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不能由于认为being有存在含义就一定会在出现being的地方读出存在含义;当然更不能由此就把being翻译为“存在”。这里的问题远不是那样简单。
五、语境的理解与翻译
我强调不能泛泛而谈语境乃是因为:说being有存在含义容易,确定和分析其存在含义的语境却不是那样容易。being在哲学讨论中出现的方式多种多样。以名词、动名词和分词(以及组合词)形式出现的情况很多。认识到它们的含义来自其动词,对其含义的认识也就会还原为对系词和非系词形式的认识。因此只要面对being及其相关用语,就有语境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说的on和海德格尔书名中的Sein。限于篇幅,这里对being的名词、动名词和分词形式的含义可以不予考虑(11),我们只考虑其动词形式。
在我看来,就being的动词表现形式来说,系词和“God is”这种形式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般不太容易发生歧义。容易产生问题的是其他一些情况。比如关于矛盾律的表述:一事物不能同时即to be又not to be。这里的to be是动词不定式。字面上看,它体现的是动词形式。由于它不是主系表结构,因此似乎不是系词形式。那么能不能把它读作非系词形式,即把这里的being理解为存在含义。或者,面对这个表达式,应该把这里的being理解为系词形式还是非系词形式,因而把它理解为系词含义还是存在含义?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普罗泰戈拉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that are they are,and of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they are not。这里的they are和they are not直接是动词表达式,字面上也不是系词形式,而似乎是非系词形式。因此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把它们理解为系词形式,则可以认识到,这是西方人谈论being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省略的方式。它省略了系词后面的表语。由于being的用法具有普遍性,因而它的通常用法也是清楚的,其系词含义不会出问题,因此,即使省略,意思也是清楚的。这样就会看到,比如这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具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表达,即关于具有“S是P”这种一般性认识的表达。
如果把它们理解为非系词形式,则可能会认为,它们表示存在,因而看不到上述情况。反过来,人们就要考虑,关于存在的表达,比如关于“存在的事物存在,以及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这样的认识的表达,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或者,这样的表达如何能够具有普遍性呢?
以上两个例子毕竟是完整的句子,因此意思是容易把握的。而在西方哲学著作中,许多地方直接谈论to be,而且不是完全的句子,比如巴门尼德的著名论题estin与ouk estin,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等等。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这里不用回答这个问题(12)。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如果把它们看作系词表达式,则可以认识到它们是省略的表达,省略了其后的表语。而如果把它们看作存在表达式,则会认为它们是非系词形式,即独立的动词形式,因而表达存在。前者体现的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句子结构,而后者不是。二者的理解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两种理解哪一种更有道理,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孰优孰劣,似乎不难分辨。正像格思里所说,在这一点上,卡恩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说,它(einai-译者注)的根本价值“不是‘存在’(exist),而是‘是如此的’(to be so),‘是这种情况’(to be the case),或‘是真的’(to be true)”。正像他指出的那样,这适合柏拉图对如下句子的解释:“各事物对我呈现什么样,它对我就是那样”,等等。“如果我们把einai的这种绝对用法理解为……一种对一般事实的肯定,比如‘什么是如此的’或‘什么是这种情况’,那么柏拉图的解释就变得完全自然的和明白可理解的(13)。
尽管是借助别人的观点,道理却清晰明确:在翻译和理解being的时候,系词的理解无疑是最重要的,含有系词的理解无疑更具有说服力。通俗一些则可以说,把being理解为存在(exist),明显地窄了,因而失去许多含义。而把being理解为系词,则会兼容它的诸多含义,并且有助于许多文本的理解。这些意思无疑是清楚的,似乎用不着多说。但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却是需要说一说的。
being以动词形式出现的语境,无疑是我们理解其含义的依据。(因而也是我们理解其名词含义的依据。)翻译某一特定语境中的being,当然要依据其语境。但是就翻译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保留其语境下being的含义,二是保留其语境。前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后者的重要性同样应该重视。这是因为它是理解being含义的依据和保证。
前面谈论“上帝is”时说到英德汉的翻译对应,如:God is,Gott ist和“上帝是”,谈到这样的翻译保留了理解其中being存在含义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些讨论与being的翻译有关,其实也与being的存在含义的语境有关。人们可以在God is中读出存在含义,主要是因为其中的being不是系词用法,即不是其通常用法,而是一种特殊用法。因此其中being的用法本身构成了它的语境。当把它译为“上帝是”(或Gott ist)的时候,不仅保留了它的存在含义,而且保留了它表示存在含义的语境,因此我们说这样的翻译是对应的。相反,如果把它翻译为God exists,即便人们认为意思不错,也不会认为它是God is的对应翻译,因为,God exists中的存在含义来自exist这个词本身,就是它的字面意思,而God is中的存在含义依赖于这里的语境,即is的具体用法。相应的中文“上帝存在”也是同样。这样的翻译对错且不论,至少失去了从being的非系词用法理解存在含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呈现了存在含义,但是消除了理解存在含义的语境。我的问题是,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这里理解存在含义的语境是否必要和重要?假如是必要或重要的,那么在相应的翻译中是否应该保留呢?
上述其他情况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把“一事物不能同时既to be又not to be”翻译为“一事物不能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把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that are they are,and of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they are not翻译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存在的事物存在、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同样只是翻译出了一种理解的结果,且不论这样的理解是否有道理,至少经过这样的翻译之后,获得这种理解的语境消失殆尽。又比如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sum”被翻译“我思故我在”,即使这种翻译不是没有道理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因为它消除了理解“在”的语境:sum是拉丁文esse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因此字面上与以上例子相似,没有或省略了表语。认识到这些,上述问题无疑可以再问一遍。
对照英语与古代语言的翻译,可以更好地说明这里的问题。矛盾律和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两个例子本身就是英译文,因此无论哲学家们有什么不同的解释,至少在翻译上保留了理解相关being的语境。笛卡尔的名言是拉丁文,英译文为“I think,therefore I am”,显然不仅翻译出sum的含义,而且也保留了理解它的语境。其中的am如果理解为系词,则是一种省略的表达;如果理解为非系词,则表示存在。在具体相关讨论中,“I exist”(我存在)这样的表达有时可见,但是把笛卡尔这句话翻译为“I think therefore,I exist”,却非常少见。这样的情况在西方哲学中随处看见,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话被译为being as being,海德格尔的书名被译为Being and Time。这样的情况只用拼音文字的相似和便利大概很难解释。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这样的翻译保留了正确理解being的可能性,因为它们保留了出现这个词的语境。格思里的话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卡恩强调einai的系词含义。因此,在古希腊文献的阅读中,应该保留对其相关用语的系词含义的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也许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只要把它翻译为existence(存在),无论如何也就做不到了。因为它从字面上就消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通俗地说,因为它破坏了系词理解的语境。
汉译面对所有西方语言,道理一样。只要把being翻译为存在,就在字面上阉割了它的系词特征,因而消除了所有关于其系词以及与系词相关理解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这样的翻译还破坏了存在理解的语境。所以,语境分析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复杂。语境翻译也同样重要。在我看来,语境论者强调语境分析没有错,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语境的翻译。这是不应该的。一是到底论的优点之一在于,它强调文本分析,因此不会反对语境分析。不仅如此,在翻译being的过程中,把系词的理解贯彻始终,不仅可以保证being的正确翻译和理解,而且可以保证其语境的翻译,从而保留了理解其各种含义的可能性。
六、一是到底论的实质
前面提到语境论对一是到底论提出的三个问题。经过以上讨论,现在可以做出回答。第一个问题,既然being有多种含义,怎么可能只以“是”来翻译和理解它?即只以其中某一种含义来翻译和理解它呢?
首先,可以在两种意义上理解being多义。在一种意义上,being乃是系词,而系词本身就是多义的。顾名思义,系词的意思源自该词在句子中的语法作用,显示一种语法功能:它联系主语和表语,与表语一起做谓语,起谓述作用。这种含义是通过它在句子中的语法作用体现的,因而是明确的。但是正由于这样一种作用,人们认为being自身没有意义,与表语一起才会有意义。由于它可以联系各种不同的表语,因而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意义。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本质、质、量、关系等等,即“有多少种谓述形式,‘是’就有多少种意义”。出于对系词的认识,人们一方面可以说,being的语法作用是明确的,即系词;另一方面也可以说,being是多义的,即它可以联系不同表语,表示不同含义。
在另一种意义上,being不是系词,比如“上帝is”。being的这种用法被认为表示存在。因此,being除系词含义外,还有存在含义,所以是多义的。
在我看来,在这两种意义上,being都可以而且也应该译为“是”。在前者,“是”乃是系词,正好对应being的系词含义,因而可以表达它的多义性,不用多说。在后者,“是”可以做系词,但是在“上帝是”中它并不是系词,因为这个句子不是主系表结构。关键在于,它正好对应“上帝is”这种句式,反映出其中being的非系词特征。既然西方哲学中把being的这样一种用法读作存在含义,汉译也应该这样做。这样,既反映出西方哲学中being的多义性,又保留了哲学哲学家们解读这种多义性的依据和可能性。
所以,以“是”来翻译being,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不仅不会混淆being的多义性,而且可以更好地体现这种多义性。依据这种认识,不仅可以理解being的系词含义,而且可以理解它的存在含义,因为这种存在含义来自being的非系词特征,即依赖于它的语境。
第二个问题,既然同意being的含义依赖于其语境,并且同意being有多种含义,怎么可能只以“是”来翻译和理解它呢?即对不表示系词的含义和语境丝毫也不作考虑呢?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一半是重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人们“同意being的含义依赖于其语境”,因而与第一个问题似乎是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依赖于对语境的分析的。比如关于being的存在含义的分析依赖于对“上帝is”这个句子的分析。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同样是依赖于语境分析,仍然可以一是到底。而且正因为是依赖于语境分析,才会坚持一是到底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前面关于being的存在含义的分析还具有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意义。认识到being的存在含义的来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它,因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出现它的语境。由于它可以以两种形式出现,因此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如果它以系词形式出现,我们的理解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假如它不是以系词形式出现,比如像前面提到的estin和ouk estin,以及“一事物不能同时既to be又not to be”等等,人们的理解可能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把being译为“是”才是正确的。因为它既保留了系词的理解,也保留了存在的理解,因为它保留了being的非系词形式,因而保留了可作存在理解的相关语境。相反,假如把这样的情况翻译为“存在”,则在字面上断送了系词理解和非系词理解的可能性,因而消除了理解存在含义来源的可能性。这样做,是否曲解西方哲学姑且不论,大打折扣却是板上钉钉的。
being的动词形式如此,它的名词形式更是如此。认识到它的名词、分词、动名词等等形式乃是它的不同变形,含义来自它的动词形式,那么有了以上讨论,其相应的语境分析也就不用多说了。
回答了前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也就不用回答了。现在我要说明,为什么一是到底论与语境论可以是相通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可以看到,语境论与一是到底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主张being的含义与其理解有关;都坚持对being的理解要依据文本分析(语境分析也是文本分析);都认为being是多义的,包括系词含义与存在含义等等。就being的含义而言,它们似乎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它们关于being的系词含义的看法大致是一致的,关于being的存在含义的看法至少有些是一致的。一是到底论与语境论有这么多共同之处,说它们可以相通也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一是到底论主张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因而把它翻译为“是”,并且把这样的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而语境论主张在它是系词含义的地方翻译为“是”,而在它是存在含义的地方则翻译为“存在”,因此无法一是到底。这样就形成了区别。
造成这种区别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否认识到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就being本身而言,这就是,是否认识到being这个词与它所表达的意思的区别。
语境论者是不是认识到这种区别姑且不论,至少从其表述来看,这种区别常常是不太清楚的。比如论1,既说到“用一个中文词去理解”being,又说到“用一个中文词去翻译”being。词是语言形式,是可以看到和听到的。理解则针对词所表达的意思而言。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的情况很多,因此对一个词做多种理解的情况并不少见。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用同一个词翻译了being之后,就不能做出多义的理解呢?即使仅仅在字面上这也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不可以用一个词来翻译being,关键在于同一个词是不是可以译出being的不同含义。我认为可以,因为“S是P”与“上帝是”,字面上含有同一个“是”,意思却不相同,前者中的“是”乃是系词含义,后者中的“是”则不是系词含义,可被称之为存在含义。这里的中文与原文相对应,意思也清楚,而且保留了相应的解释空间和可能性。语境论者没有这样的具体论述,只是认为不能,因此有关语境的论述及其结论就仅仅停留在字面上了。
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乃是有意义的。这里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的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
[论5]应该根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应该用“是”,黑格尔的理论应该用“有”,而海德格尔的理论则应该用“存在”[15]。
这里同样谈到了理解和翻译。由于对being有不同的理解,因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三个不同的词,即“是”、“有”和“存在”。它们的意思当然是不同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是什么?他们在探讨being时所说的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具体地说,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无疑都用德文,那么他们使用的乃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希腊文,与他们的语言不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问,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换句话说,希腊文on与德文Sein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不同,是由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造成的,还是由于它们从词性、词根、具体用法等等来说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词?有了这些认识,也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重要性了。
语境论者大概不太在意这样的区别。论5的结果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使用了不同的词,以此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和思想,因此也就有了上述问题。
假如我们采取一是到底论的看法,即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使用的乃是同一个词,即“是”,他们表达了对它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黑格尔的从“是”到“不”的辩证法理论,海德格尔的询问“是”的意义、通过“此是”这种出发点以及通过“在-世界-之中-是”这样一种结构来探讨“是”的理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与being相关,语境论展现的乃是一种断裂的历史。别的不说,人们看不到从“是”到“有”到“存在”有什么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充其量是解释出来的,因为至少字面上是没有的。一是到底论展现的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历史。无论是希腊文(或拉丁文)还是德文(或者英文、法文),人们看到,“是”这个词的讨论占据了形而上学的核心位置,由此也看到了对它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比如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以及形成的不同理论。
一是到底论可以赞同语境论,而语境论其实也应该是赞同一是到底论的。目前的问题在于,语境论者过于注重being有多种含义,以为由此being的翻译注定不能一是到底。而一是到底论则强调being的系词含义,认为它的通常用法是系词,即使它的存在含义也是来自它的非系词用法,因而与系词相关。因此,语境论强调了语境分析,强调了being的存在含义的翻译,却恰恰忽略了being产生存在含义的语境,忽略了在翻译中如何保留这种语境,如何不破坏这种语境。而一是到底论虽然没有怎么谈论语境分析,却可以保证正确地理解being的存在含义,而且可以保留其产生存在含义的语境,从而保留了正确理解being的可能性。
最后还可以就being的翻译再说几句。关于being的翻译,人们总是强调它是多义词,总是强调要翻译出它的存在含义。反对一是到底论,其实主要还是反对突出它的系词含义。对这一点,说实话,我是非常不能理解的。道理非常简单。把它翻译为“是”,字面上就保留了它的系词含义,而把它翻译为“存在”,字面上就消除了这种含义。在我看来,保留being的系词含义,并不会消除它的存在含义,比如“上帝是”就表示“上帝存在”,因为这不是系词用法,一如“God is”表示“God exists”。而消除了系词含义,不仅字面上就阉割了对系词的理解,而且也消除了理解存在含义的来源及其可能性,这对于理解西方哲学,当然是不利的。在语境论者看来,我强调一是到底可能有些过强了。我想,我强调的不是语言翻译,而是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无论是希腊文的on和einai,拉丁文的esse,还是英文的being或德文Sein,字面上难道会看不到系词含义吗?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说的to on hei on,还是海德格尔的书名Sein und Zeit,字面上难道会没有系词含义吗?如果我们能够把being翻译为是,并且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它,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一脉相承的关于“是”的论述,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研究是本身;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是”;贝克莱的命题乃是“是乃是被感知”;康德的著名论题是“是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海德格尔的名著乃是《是与时》;如此等等。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在如何把being及其相关用语理解和翻译为“是”上下功夫,而不必劳神去修正existence的翻译,比如把它译为“实存”、“生存”。这样做不过是本末倒置,不会反映出它们与being的区别,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being的理解。
强调语境论没有错,但是语境分析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一是到底论看似简单,其实却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认真去做。在我看来,认真思考和分析being产生存在含义的语境,思考和认识如何在being的翻译过程中忠实地保留其语境,乃是强调和论证语境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加上这部分,语境论一定会走到一是到底论。因此,一是到底论与语境论是不矛盾的,它们本来是可以相通的。
收稿日期:2013-10-25
注释:
①我被称为“一是到底论”的代表。为了简便,我在讨论中借用这一说法表示自己的观点。
②关于文本的讨论,我已经做了许多(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年、2013年);《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解读〈存在与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除了在探讨being的过程中涉及翻译问题外,近两年我也专门论述过being的翻译,(例如参见王路:《Being与翻译》,《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③论1说的是希腊文,而不是英文,但是意思一样。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说的是英文的being,以它所表示是却是西方语言中的一个相关语词,包括古代语言,如希腊文的einai,拉丁文的esse,也包括现代语言,如德文的Sein,法文的etre等等。
④Aristoteles:Metaphysik,Buecher I-VI,griech.-dt.,in d.Uebers.Von Bonitz,H.; Neu bearb.,mit Einl.U.Kommentar hrsg.Von Seidl,H.; Aristotle:The Works of Aristotle,vol.VIII,by Ross,W.D.,Oxford 1954,1017a9-1017b8.
⑤例如参见Ross,W.D.:Aristotle's Metaphysics,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Oxford 1924,p.306; Kirwan,C.:Aristotle's
⑥当然,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一个特称句子也可以表示存在,比如“一些人是聪明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东西,它是人并且是聪明的。若是从这后一种观点出发,being翻译为“是”就更有道理了,因为“有S是P”也可以表示存在。不过,这是一种关于句子,尤其是关于句子中量词的解释。所以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人们一般不讨论它,我也很少谈论这种情况。
⑦我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王路:《Being与翻译》,《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⑧语言转换有其特性,being一词也是如此。比如英文human being翻译为“人类”,德文Bewussetsein译为“意识”,其中的being(sein)都不翻译出来,既不译为“是”,也不译为“存在”。“there is”是一种专门的表达,具有特殊意义。从逻辑的观点看,它表达的是量词。比如,奎因以它为题讨论本体论承诺,把本体论的所有问题归结为“What there is?”,他给出的回答则是“Everything”。由此可见,“there is”,即being加上there,与being本身乃是有重大区别的。参见Quine:On What there is,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⑨这在中世纪的哲学讨论中非常多。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五章。
⑩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55页;译文有修正,参见。Heidegger,M.:Einfuehrung in die Metaphysik,Max Niemeyer Verlag Tuebingen 1958,s.42。
(11)我曾讨论过这些词的翻译,参见王路:《Being与翻译》。
(12)我曾详细讨论过这些问题,说明了为什么应该把他们所说的being理解为“是”,而不是“存在”。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三、六章。
(13)Guthrie,W.K.C.:The Sophis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190.格思里在该书序言中说,他的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分为两部分。该书复制了其第一部分,做了最小限度的必要的修改。我手边没有《朝文》所说的第三卷。所引部分页码与《朝文》给出的大致相符,估计应该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