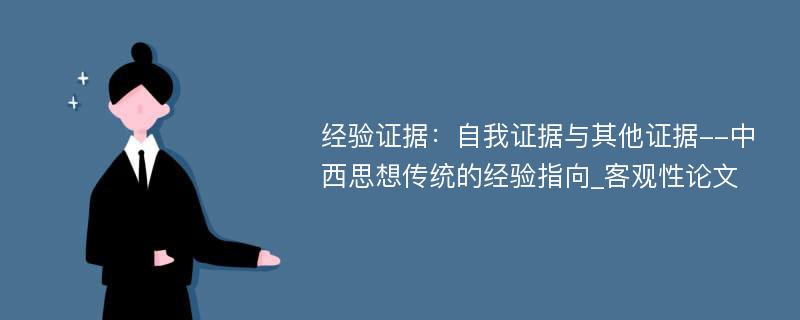
实证:自证与他证——中西思想传统中的实证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与他论文,中西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8)04-0001-09
在传统汉语中,“实证”与脱离自身感受的“空谈”相对,指的是有亲身感受。比如:“实证二空所显真理,实断二障分别随眠。”[1]“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2]“傍人篱壁、拾人涕唾”是无己见而随人言语的空谈,“实证”指的是自家自得亲证。但今日,受西方哲学影响,国内学人提及“实证”就会联想到拥有仪器设备的实验、联想到主体间之“可观察性”。表面上看,“实证”精神为中西所共奉,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知识获得确实的证据。但深究之则会发现,呈现证据之路向之差异与各自在世态度、知识形态、普遍性追求的差异密切相关。在西方,“实证”以仪器设备为中介,以外于己的客观“事实”为依托,以主体间可观察性为宗旨。中国传统世界则以“味”、“感”的态度行世,把握真理需要“味-道”,实证真理亦需要以德显道,“证”以身心来承担,以自得为宗,要求证之于“味”、“感”,以味到、感到为“实”,是证之于自、证之于内。实证道路的差异显示了中西文化系统的差异。
一 实证与他证
实证精神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近代以来的科学,以及科学文化将此实证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与形式性、客观性的普遍性追求相一致,实证的根据与目标即在于客观性、形式性、普遍性、可重复性。实证的最终要求是主体间的“可观察性”,即把理论最终质诸主体间都能直接感受到的外部实在,将主体与理论之间变成与理论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从而确保最大限度的证实。
从形式上看,实证表现为相互依存的两个部分,即理论的逻辑证明与经验证实。与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视觉优先”①文化传统相一致,理论证明与经验证实都表现出显著的视觉特性。维特根斯坦对此有着非常简洁的表述:“‘我知道’有着同‘我看见’相类似和相关联的最终意义。‘我知道他在室内,但他并不在里面’同‘我看见他在室内,但他并不在那里’相类似。‘我知道’应该表示一种关系,不是我与一个命题意义(如‘我相信’)之间而是我与一个事实之间的关系。”[3]“知”与视觉之“看”有着一致的结构与要求,即将之引导、规范、还原为主体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看”、“知”的客观性、确定性。“可观察性”即是这种实证理论的基本要求。
以抽象的逻辑形态表现出来的理论虽超越感官,但理论的逻辑证明最终表现出向视觉对应物的还原。柏拉图强调的以“心眼”把握纯粹形式性、本质性的“相”,亚里士多德将形式因规定为本质因也是建立在视觉优先基础之上的②。这个传统在古希腊以后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笛卡儿所创立的解析几何学用平面上的一点到两条固定直线的距离来确定点的距离,用坐标来描述空间上的点,即由x轴、原点、y轴构成一个斜坐标系,以(x,y)惟一地确定平面上任一点,从而使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为代数形式。几何问题可以化成代数问题,代数问题也可转换为几何问题。比如,笛卡儿引入了单位线段,以及线段的加、减、乘、除概念,从而把线段与数量联系起来,通过线段之间的关系来表现代数方程。正是基于解析几何对“数”与“形”的贯通,我们看到,近代以来物理数学化的努力一方面表现为“理”的代数化,同时就表现为“理”的几何化③。笛卡儿所提出的“清楚明白”的目标正是相应于几何“形式”的视觉特征。
证实赋予理论以客观性意义,理论的正确性同样由证实得到保障。就结果来说,理论的正确性表现在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符合”。“符合”需要同质性两者之间的对照,相应与此,理论需要转换为可见的事实。维特根斯坦将命题理解、规定为“实在的一种图像”[4]4.01即是使命题成为“可见之物”的一种努力。“图像”是“实在的一个模型”[4]2.12,是“一事实”[4]2.141。图像既是实在与事实,则它就可以与实在直接比照,一致与否成为判定图像“真”或“假”、“正确”或“不正确”的标准[4]2.21。将理论还原为“图像”,将“图像”规定为“事实”、“实在”,这样,理论就成为与“事实”、“实在”同质的客观性存在。所谓“实在的图像”也就是说命题具有图像一般“可见性”。理论成为图像,由图像而可为视觉所见,由此而可对照。图像作为具有客观性的证据更容易为不同主体所把握,主体间的一致得以可能。
实证精神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被表述得最清晰、最典型。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的许多哲学家努力把复合命题还原为可以直接与实在相比较的基本命题(原子命题),把经验概念还原为经验与料(data)。原子命题都是可观察命题,即它所反映的事态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按照理论设计而出现预期的事态能与观察到的事态进行直接的对照,当两者相一致,我们就可以说理论得到了证实。以证实为根据,理论的意义得到保障,或者说,理论获得了真实的意义。
实证的实质是将预期的事态摆放在主体间,以供主体间观察、检验。“可观察性”是证实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与必要条件。“观察”与“经验”是有差别的,“经验带有主体性,观察是去除经验中主体因素的一个途径。”[5]119经验,特别是日常经验,往往卷入主体自身体验而难以走向主体间。维也纳学派对此有着足够的警惕:
“感知和经验提供我们关于事实的知识,但它们只能引发这种知识,却不能确立它的有效性。陈述的真理性或确定性不能由瞬时经验来保证,因为科学陈述本质上都是主体间的经验,从而其有效性不能由主观经验来确立,只能依赖于主体间的基础而确立……确凿无疑的经验和不证自明的感知显然都是十分主观的、心理上的。”[6]130
“仅仅一瞥或一种体验是不能交流的。认知的功能是把关于外在世界的客观知识传递给我们。而经验却只能使我们同外在世界或内在世界发生直接关系。经验激发并丰富了我们的内心生活,但是无助于把这种生活的经验内容交流给他人。因而认知在本质上永远都是主体间的,而经验始终是私人的。”[6]133
观察是宽义经验之一种,观察命题、观察语句、观察报告是以事实性为根据,而对主体间保持着开放性。观察谓词虽属于经验范畴,但由于观察本身受到客观性的指引与规范,所以,主体间可观察又可以制约着观察的“体验性”、“约定性”倾向。
观察既包括感官的观察,也可指借助于仪器进行的观察。显然,科学理论非此种意义上的观察所限定,科学理论中存在着大量“不可观察的”东西。那么,如何看待这些“不可观察的”科学理论呢?20世纪美国著名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提出一种有意思的解决方案。他将科学定律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验定律”,另一种是“理论定律”,简称理论。他认为,“实验定律”是指:“如此被表征的一个陈述表达了事物(或事物特性)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些事物或特性是可观察的,并且,该定律能够得到对定律中所提及的事物的受控制的证实。”[7]95“理论定律”则是“并没有实指性地指称任何可观察的事物,因此,这些假定不能为术语实指地指称的观察或实验证实。”[7]95理论定律所陈述的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事物,但科学史表明,从实验资料中引出、间接地确定不能观察的事物的特征又是可能的。从理论定律的构成看,它包含三个成分:“(1)一种抽象的演算,它是该系统的逻辑骨骼;(2)一套规则,通过把抽象演算与具体的观察实验材料联系起来,这套规则实际上变为该抽象演算指定了一个经验内容;(3)对抽象演算的解释或模型,它按照那些或多或少比较熟悉的概念材料或可以形象化的材料使这个骨骼变得有血有肉。”[7]97抽象的演算具有不可观察性,但通过对应规则,它与经验内容是可以建立联系的,而且正是这样的联系才使得它对科学探究具有积极作用。不可观察的理论仍可以与可观察的经验内容建立联系,那么,后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为理论提供必要的支持。
实证精神在现代科学之“实验”活动中得到更明确、更完整地体现。“实验比观察更明确地把经验统一体中的主体成分和客体成分加以区分,从而更有效地清洗掉经验中的主体成分,保证了事实的纯粹性。”[5]123在现代科学中,观察是一种出自理论、指向理论的“看”。聚集着这种理论的“看”的活动的是“实验”,因为实验就是以理论设计为特征的活动。
当下直接给予的是期待着的、往往也是“预期的”理论化的存在,即一种特殊的“事实”。反过来,对事实的构造也使理论命题获得了直观的、客观的形态,这就为主体间的观察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理论命题成为可直接观察的事实,事实遂使理论得到最大限度的证实。“事实”一旦构造完成,它就拥有独立于主体的自性,成为独立于主体的另一“体”——客体。主体属于“内”,客体属于“外”,两者之距离也由此得到规定。
当知识、理论可还原为“客体”,理论的检验者就不再局限于创建者,我之外的“他者”皆可将理论与事实之间进行对照、检验,所以,知识、理论的实证也就成为与自证有别的“他证”。“知”既属于“知者”与“事实”这个客体之间的关系,“知者”就是不定的“任一个”。距离性、客观性正是视觉“看”活动的基本特征,它也是建立在“看”根基上的认知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看”之所“得”在“外”,就此说,将“证”最终归诸外在、客观的事实只是“看”的内在要求。
二 自得与自证
与重“视觉”、追求形式性、抽象性的古希腊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更重味觉。 “非礼勿视”(儒家)、“以道观之”(道家)表明视觉的追求都被置于人的存在的特定道路而无意于“客观性”、“形式性”。自《尚书·洪范》起,“味”一直被理解成物的“性”:“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左传》有:“天有六气,降生五味。”[8]“五味”是“五行”生发出来的,它们就是“五行”的“性”。“水味所以咸何?是其性也。”[9]味被规定为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秦汉以来流行的“神农尝味百草”的传说与此对存在的理解紧密呼应④。“物”可由“味”而得,“道”亦可“味”,此即传统强调较多的“味-道”方法论。
与重“味-道”之“味⑤”的思想传统相关,经验、思想所得之证明、证实皆表现出不同于奠基于客观性精神“看”之上的实证精神。“知道”的意义与“得道”相关联,“知道”是以我进入大道,大道进入我这种交融关系为特征的。不是“我看见”而是“我味到”、“我感到”。味之所得与己相关,而非独立自存的自在之物。与距离性的“看”相应的“所看”是形式性的“相”,与非距离性的“味”、“感”相应的“所味”、“所感”则是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象”。非距离性之“味”、 “感”使“象”与个性生命相关联,而表现出流动、变化与不确定性。“味”、“感”之所得是自身进入、参与而呈现的物与象⑥,所得之道则为内在于己的“德”,在己者属于“自”,属于“内”,因此,“证”亦在“自”在“内”。
传统德性论讲凝道成德与显性弘道,讲躬身反省,讲德性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些说法无疑都强调了“所得”中自我的参与与承担。大道不为私人所有,但公共之大道可以通过个人的修习而使道得以“立”,所谓“身修而道立”、“凝道成德”是也。所得者成于内,具体说就是,理性方面成就“自明”,即自知自身在家国天下中的位置,自知自身行为的各种意义。这样的“知”与“行”相关联,即表现为自身展开于世界中的状态、境界。表现在“思”的层面,就是将普遍的知识理论拉回到自身、落实于自身,以切身的“感”充实其意义,并能以此开展“感思”,时时回到自身。《中庸》“自诚明”与“自明诚”表达了理性意义上的“明”与德性修养意义上的“诚”之间相互促进而结为一体的亲密关系。“诚明”虽有言行等方面的“客观表现”,但其基本规定与基本要求是“足乎己无待于外”的,也就是说“己”才是最终的裁判者,外于己的他人虽有所感,但内在心灵境界的差异而往往会使他人对“诚明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张载所谓的“德性之知⑦”也恰当点出了这种“知”与“德”,乃至整个生命存在之间的相依性。所知、所得即其人之“德”,知以“德”的形态呈现。“德”的内容不仅是个人性质的知觉意识,德为道舍,德中也涵蕴着、承载着“道”,所谓“德者,道之舍”是也。
意志方面的“自主”亦将“知”、“德”引导至于“内”。“自主”首先是自主其“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以己之“欲”为起点与支点,而由己及人,自我之欲贯穿于所知所得。“可欲”[11]尽心下——“可欲之谓善”。首先是“可”己之“欲”,然后才到达他人。理解“可欲”(善)需要回到“己”本身,更需要在“己欲”中获得确证。“自主”还体现为自我主宰、勇于决断与承担,最终勇于将可欲贯通于“行动”。荀子对此有精彩论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默)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12]一切出于自身之欲,以自身之欲为根据。当然,儒家对这个“欲”有明确的伦理规定,即“欲仁”。“欲仁”要求自身以“仁”的态度在世,以仁的态度接人应物,“心”对“形”的主宰亦是“仁”对形的润泽。
“我欲仁”是起点,“斯仁至”则是“欲”的方向与目标。“仁至”即是“德成”、“得道”,即是“自得”。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1]离娄下朱熹注曰:“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藉者深远而无尽;所藉者深,则日用之间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13]自得于己,则道取得自我的形态,而己与道通。所知、所欲皆在此得以实现“自”、“己”的品格。“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之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14]自“学”而言,目标是将外在于己的知识经验化为内在的东西,以使与本己的东西相契合,达到“自得”;“得于内者”贯通内外,亦是“自得”。不管得自“内”,还是“外”,“我”始终是“得之者”,是贯通耳目与万物之“机”。陈献章对此有卓绝体会:“自得者,不累于万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15]“自得者”可安居深资、左右逢源,自足于内而无待于外,外在条件自然不能移易。
德性显于德行,著于四体,如孟子言“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1]尽心上自得于心而生色于面背四体。四体之色显于外虽“睟然”可观、可感,但它显然不属于可模式化、客观化、程式化、形式化的外物。不言而喻之四体以真诚的心灵为根据,由真诚的心灵支撑。不言而喻之四体不可证,可证的是心灵之真诚与否,以及心灵境界之高低,但心灵境界显然只可自证而不可他证、外证。一代代大儒对“慎独”的强调正基于此。
重“慎独”是因为“独”最能体现自得之我的“自”与“内”的真实状况。“独”时所表现的德是内外一致的“德”,是“诚于中,形于外”[16]之德。“独知”是“人所不知而己独知”[17],此独知于他人是未可知的“隐”或“微”,于已是“如见其肺肝然”,是“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独知对着自己开放,将最真诚的自己带到现实世界,故它一直受到儒家的推崇。王阳明不厌其烦地对其弟子强调⑧,梁漱溟则将“慎独”当作儒学的总纲⑨,这无疑都基于慎独对本己的敞开性。
不仅儒家将实证归诸自证、内证,道家追求“自知曰明”[18]第33章、强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18]第54章、“有真人而后有真知”[19]大宗师,他们在将知的方向调向生命存在的同时,也将“实证”的方向转向内在的生命修行。追求“道”的“德”化,以“德”来彰显“知”,故所知始终以生命存在为其载体,知识形态始终停留在自身之内而没有朝外在化、客观化方向迈进。特别是,当“天下”、“物”、“我”这样外在化的形式被内在心灵“悬置” (庄子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掉之后,“知”成为心灵的自由绽放活动,天下万物皆为心灵所“游”的场域。这样的万物并不能当作某种知识的实证根据,它不过是这这那那而已,心灵没有设计过它,或者说,心灵只是把它交给了物自身。这样的外物虽然脱离了本然形态,但却以其自然面貌而对他人呈现出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庄子对感官经验及个体知识普遍性的怀疑正基于此。物各有其性,各主其知,“正处”、“正味”、“正色”[19]齐物论随性而异,其“性”其“知”即其“正”(合适、恰当、正确)。“正”即其知之“证”,“正”有“各”,则“证”亦有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19]大宗师,“知”系于“人”与“物”。“人”、“物”主宰着知的立场、倾向,故庄子有是非同异“恶能正之”之叹。当然, “恶能正之”不是说不能正之,庄子正之之法是“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19]齐物论,即将人物是非同异之“正”归还每一个人与物,让各个人物自己确证其“知”。
就人来说,“休乎天钧”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拒斥机械而直接面对万物。庄子担心:“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19]天地于是,他以拒斥机械来保障物我交往的纯真性。但就“知”来说,此举无疑屏弃了他者展开物我交往所凭藉的依据,增添了他者来临的难度。对万物的“无为”使他者的实证只能一次次从头开始,一次次从头修养身心、从头展开自身生命(有真人)来使作为德性之“证”的物到来。显然,将“知”托付于特定的生命形态的结果必然使实证不断内在化。
三 “中国科学”与内证
“内证”、“自证”不仅体现在儒家、道家的形上追求方面,与形上领域保持密切一致性的所谓形下领域同样贯穿着此一要求。特别是在中医药等传统科学活动中,内证构成了它们的核心特征。这里就以中医药为例来看看传统科学的实证特征。
就药学说,在西方被视作“第二性质”的“(气)味”被当作药物的根本特征。“性味”成为对药物“性质”的把握与规定的唯一标准。所有药物都按照“四性五味”进行分类,“四性”或曰“四气”,指中药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能特征。“五味”指中药的辛、甘、酸、咸、苦五种味道。不管是“气”,还是“味”,它们都是与人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的性质。作为自然性质,“气”与“味”并不对人的客观性感官“看”呈现,而是对着主观性感官“鼻”、“口”⑩,以及整个身体呈现。“气”与“味”由对身体的作用效果而获得规定性,所得的不是外在的事实,而更多表现为对人的“内在作用”。与此相应,中医治疗依据性味理论展开,“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药物之所以能治疗则在于“性味归经”(“五味入五脏”)。“性味”因时、地、气候等要素而不同,同样的物种,或按照现代西方科学的提法,相同的种属、相同的化学结构,在中药可能会显现出相反的性味,相应就具有相反的治疗效果。“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20]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时地的差异会造成阴阳秉受的差异,从而使同一物种也会产生性味的厚薄差异,其治疗效果可能会有天壤之别。比如,大家熟知“橘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就性味说橘甘、酸,凉,枳则为甘、酸、平,橘归肺胃,枳归脾胃。如果说橘枳属于不同种类(11),那么,浙贝、川贝的性味差异更见时地与性味的紧密关系。出在浙江一带的贝母叫做浙贝,也称大贝,出在四川一带的贝母叫做川贝,浙贝较之川贝更凉,川贝的作用是清热、化痰、止咳、润肺,浙贝则主要是软坚散结。不管是味之厚薄,还是性之寒热,中药所关注的这些特性无疑皆系于品味者自身的主观感受。一直被医家奉为医药起源的神农尝百草的神话,其一直被口耳传唱事实上也在将这种识别、判断药物性质的模式神圣化、普遍化。
与中药性味说相一致,中医之望闻问切诊法,尤其是其最重要的“切”诊法,坚持的是医生零距离的介入、参与(12),进入患者的世界才能诊断“病的人”之“病”。切诊的基础是经络理论。按照传统医家的说法,通过返观是可以明察人体之经络的。李时珍《奇经八脉考》曰:“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察之。”“返观”不是外观,而是“内观”。内观何以能察到“内景隧道”呢?很多医家认为,在具备了一定的素养、能力之后就可以内视返观[21]。它所需要的是主体自身的条件而不是外在可见的仪器设备,其所得是自明自主形态的东西,归根结底是“自得”。药物的气味、药物的归经都是以自得为根据(13)。他人之“证”同样需要亲身参与:亲尝、返观,以及相应的境界修养。就切诊说,“脉象”虽由医者零距离的参与所得,但它却是被诊者自身“现”出的“象”,是自身涌现的“象”,而不是医者自身生成的“象”。当然,把握脉象需要医者自身有足够敏锐、足够高超的技能、境界才能进入,故“脉象”又好像存在于诊者那里。“事实”可通过外在于己的仪器设备等中介来呈现,“脉象”以充满个体差异的自我来呈现与承载。仪器设备可以保障事实显于外,因此,对所得之“证”是外证;由主客双方参与而呈现的象状需要以自身呈现,它必然需要“证”之于“己”,“证”之于“内”。
“自证性”在传统的诸“科学”中多有体现,《庄子·天道》借轮扁斯轮表达技术之“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而此技术是“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由自得自证而拒绝了他者,不仅技艺如此,即使在最“抽象的”数学中也不例外。按照传统数学家的说法,数学之“数”在圣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22]的创作活动中产生,故“数”与人身密切相关。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在刘徽看来,“算术之根源”就在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八卦上。因此,算术与“阴阳”相关,与“两仪四象”、“六爻”、“八卦”相通。因此,“数”既通乎物,也通乎人。类似的说法在中国数学家中还有很多,如:“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稽群伦之聚散,考二气之升降,推寒暑之迭运,步远近之殊同;观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纵横之长短;采神祇之所在,极成败之符验;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23]“序”算术是“天地之经纬”、“五常之本末”,“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换言之,天地之常、五伦之序皆合于“算”,皆可作算之“证”。人自身道德性命与数学相关联,因此,不仅在天地之间有其证,在每个人自身道德性命之内亦有其证,证既在外,也在内。人们常常以“实用性”来概括中国古典数学的特征,究其实用性的根源,就在于,“身”乃是数的两个来源之一,“身”也是“数”的实质表现。数由身呈现,故也可以“身”为“证”。以“身”呈现“数”,让数回到人自身,这正是数学最实在之“用”。
质言之,从“证”的角度看,他证、外证要求主体间的可观察性,要求证之于“目”,以“眼见为实”;自证、内证要求自明、自得,要求证之于“味”、“感”,以味到、感到为“实”。不难看出,实证道路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对何者为“实”之理解与规定的差异。把握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西文化的思想实质。
收稿日期:2008-07-08
注释:
①对于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视觉优先传统,20世纪许多哲学家都有自觉,批判者有之(如海德格尔),自觉发挥者有之(如梅洛·庞蒂、阿恩海姆)。
②柏拉图说:“诸神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它给我们带来光。眼睛在脸的上方……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柏拉图.蒂迈欧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1-43)亚里士多德则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不仅在实际活动中,就在并不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和其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7.)
③具体地说,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是要把物理代数化,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则是要把物理几何化。可参看陈省身.陈省身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71.
④如《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⑤关于中国哲学中味、感的方法论意义,可参见我的以下论文:《感思与沉思》,《中国哲学史》2004年3期;《从感看中国哲学的特质》,《学术月刊》2006年11期;《咸:从味到感》,《复旦学报》2007年4期,等。
⑥关于味如何开启物到来之路,请参看拙文《物的到来如何可能》,《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⑦见张载《正蒙·大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⑧如:“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王阳明全集》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王阳明全集》第790页)“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自家痛痒自家知。”(《王阳明全集》第791页)
⑨“慎独之‘独’,正指向宇宙生命之无对,慎独之‘慎’正谓宇宙生命不容有懈。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45)
⑩鼻、口(舌)与气、味对应。按照传统医学说法,气属阳、属天,味属阴、属地。鼻、口(舌)与气、味交即是与天地阴阳交。《素问·六微旨大论》:“言人者求之气交”,“气交”反映的是人与天地相交的状况,与天地相交状况也是生命的方向标。以鼻、口、身“体味”(玩味、品味)天地阴阳即是与天地、与大道相交,这正是生命本身的内在要求。味、感由此获得了存在论的意义。
(11)《本草拾遗》云:“书曰:‘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今江南俱有枳橘,江北有枳无橘,此自是种别,非干变易也。”按此说法,橘枳似属不同类,故性味不同。
(12)当然,我们也一再在传奇中看到高明的医家因种种而悬丝诊脉,悬丝不是为了拉开距离,而是以丝将脉之沉浮诸象传送过来。显然,切脉尤其需要敏锐的感受力,以及相应的修养境界。
(13)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中将神农设想为具有透明的玻璃肚(另一说是,神农有个玻璃肚之獐狮,神农采来百草,先由獐狮吃下,透过玻璃肚看是否有毒),似乎是为了强化性味归经理论的可证性,但“自得”之“知”终究是自知而不是他人可“视”的“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