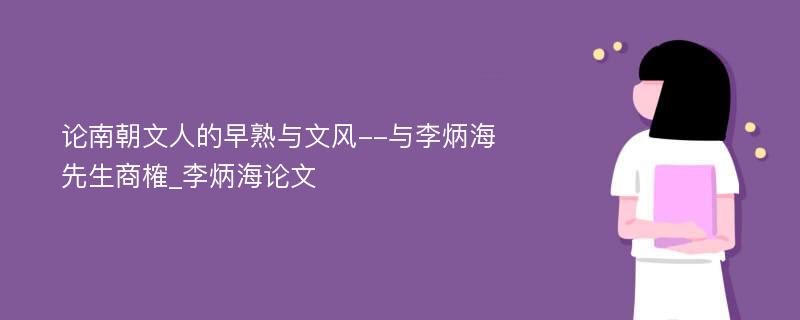
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与李炳海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文风论文,文人论文,也谈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炳海先生于1993年第3 期《江海学刊》上发表了《论南朝文人早熟与文风走向》一文(该文于同年9 月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文章认为,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词赋取士为文人早熟提供动力和时间,玄学思潮则有助于文学天才的早期开发。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注重藻饰的倾向,都和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有直接关系。不可否认,该文的观点是比较新颖的,某些地方言之有理。但笔者认为,某些地方也有不妥之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但对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这个问题,仍然有议一议的必要,这对于研究人才成长的规律及南朝文学史,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李炳海先生在文中指出:两汉作家早熟率为20%,唐代为22%,而南朝高达47%,其中一个原因,两汉和唐代主要是以经义取士,而南朝以辞赋取士。经义取士还是辞赋取士,制约着文人的早熟与晚成,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这个结论不大妥当。两汉不单单是经义取士,察举也是主要的取士制度,其科目除了“孝廉”之外,还有很多。如“秀才”,偏重文才,由郡国察举;“文学”,始于汉武帝,对杰出的文学人才“待以不次之位”,破格重用;“明法”,考察有关法律制度的知识,优秀者被任用为律吏;杂科,因随时需要而举荐的各类有专长的人才,如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造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李先生在文中指出,汉代因为是经义取士,所以有的文人社会地位不高。笔者认为,在汉代,文、史、哲没有分流,经义之作和文学之作没有截然分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代,文人对经术是颇为精通的,他们有的不被重用,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正如东方朔在《答客难》里所讲“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可见其原因不在于文人们通词赋而不通经义。到了唐代,取士的路子也是多种多样,并非主要是靠经义取士。《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唐制,取士之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上列科举之目,概括了唐代所有的科目,其中有的是主要靠词赋取士的。唐代影响比较大的进士考试,也并不是“典型的经义取士”,《唐语林》卷八:“唐朝初……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自唐初至唐末不改。时务策,往往着眼于现实问题,如白居易《进士策问五道》中第五道,问目前钱贵物轻,谷贱伤农,如果考生在天子左右,“其将何辞以对?”可见进士考试的现实性比较强。
李先生在文中还谈到,唐代进士考试加诗赋到680年才开始, 殿试加诗赋到754年才实行,从初唐到中唐二百多年的时间里, 进士科基本上是以经义取士为主的。即使这是事实,但文人早熟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如初唐四杰中,王勃六岁能文,九岁著《指瑕》,批评颜师古《汉书注》的错误;杨炯十岁应神童举及第;骆宾王七岁能诗。盛唐时期的岑参九岁属文;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可见经义取士也不能制约文人的早熟。南朝是不是主要靠词赋取士呢?也不尽然。“半部《论语》治天下”并不是宋代人的独创,南朝统治者在政治上也是崇尚经术的,因为经术对封建统治者能够起着支持作用。在考选人才时,南朝统治者没有用玄学和道教作为考试的内容,也没有用外来的佛经作为考试的内容,用的仍然是经术。刘宋开国之初,虽无国学,但仍为名儒开馆授业,为周续之讲《礼记》开馆于东郊,并在元嘉十五年(438)立儒、玄、文、史四个学馆, 各聚门徒就业。在南朝,流行着这么一种观点,“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南史》卷六十二),“经礼乐而纬国家”(《南史》卷七十二)。为此,统治者也大加提倡经术。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正月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 并规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南史》卷六)。由于“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南史》卷七十一)。整个南朝,可以说研究经术之风大盛,如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徐摛“幼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司马筠“少孤贫好学”,“及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崔灵恩“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翻开《南史》,这些例子屡见不鲜。就用人而言,南朝还是坚持考试取士制度的。宋、齐两朝一般是孝廉试经,秀才试策。梁朝曾在天监八年下令全国,只要能通一经,不论什么社会地位都可以参加考试,随才录用。如徐勉18岁入国子学,后“射策甲科,起家王国侍郎,补太学博士”(《南史》卷六十)。陈依梁制,仍有秀才、明经、高策等科。南朝虽然有的君主喜爱文学,也有的文人因辞赋写得出色而得到提拔,但就主要倾向而言,取士不是靠辞赋,而是靠经义。可见,不论是经义取士还是辞赋取士,对文人的早熟与晚成,都没有严格的制约关系。
玄学思潮是否有助于文学天才的早期开发?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玄学是一种哲学思潮,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创始人是何晏、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玄学流行时期,“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晋纪·总论》),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大多数士大夫则以“无为”为荣,务实为耻,标榜“旷达”、“清高”、“风流”,以掩盖其空虚的生活。李炳海先生在文中认为,“玄学”主要靠人的顿悟、神会,能开发人的智力,这种说法论据也不十分充分。玄学是《老子》、《庄子》、《周易》三家哲学思想的揉合,是有本可依的,不然,挥麈清谈如何解释?单靠顿悟、神会是很难谈玄说理的。再说,对于玄学这种高深莫测的哲理,几岁的孩童恐怕难以接受。另外,玄学到西晋末开始分化,最后走上了玄佛、玄儒合流的道路,至东晋后期,基本上已名存实亡了。“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整个南朝的思想潮流并不是以玄学为主,玄学的影响在逐渐淡化。至于南朝有的文人幼年就接触《老子》、《庄子》,但这不等于研究、接受玄学。《老子》、《庄子》不能同玄学划等号。《老子》、《庄子》早就产生了,而玄学却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思潮。南朝佛教盛行,佛教的大乘空观与庄老的贵无思想互相渗透、相得益彰,南朝有的文人幼年接触《老子》、《庄子》,恐怕与这一点分不开。按照李先生文中的观点,南朝以辞赋取士,玄学能促进人的早熟,但玄学产生的玄言诗,刘勰说它“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钟嵘更批评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这是很难符合辞赋取士这个标准的。词赋取士与玄学导致文人的早熟,不是互相矛盾吗?
二
那么,南朝文人早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主要有下列四种。
首先是南朝统治者重视文学,喜爱文才,形成一种时代氛围。魏晋以来,文学逐渐从经史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文学观念不断明确。自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之后,更引起了社会对文学的重视。再加上南朝皇族大都靠武功夺得天下,与世族相比,在文学上却没有优势,为了同世族抗衡,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文坛上也要取得统治地位,因而南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讲:“自宋武爱文,文帝彬彬,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到了梁朝,重视文学的风气更是大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南史》卷七十二)。对于有成就的文学之士,统治者也特别喜爱,大力提拔。由于统治者的倡导,重视文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即使在兄弟分财时,也“唯取图书而已”(《南史》卷二十二)。有的公开表示: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他们将文学与家族的声望、地位联系在一起,教育子女倾心于文学,以文显名。如王僧虔劝诫其子时说:“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书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南史》卷二十二)殷切之心,溢于言表。钟嵘在《诗品序》里也指出:“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在这种崇尚文学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的早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门阀世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陈寅恪先生曾说:“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教、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刘师培先生也指出:“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中国中古文学史》)这些门阀世家政治上有特权,经济上有优势,接受教育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很好的学习环境。门阀世家虽然出现过百无一用、甚至把马看成老虎的子弟,但也确实培养出不少文化素养很高的人物。齐、梁王室的子弟,琅琊临沂的王氏,陈郡阳夏的谢氏,东海郯县的徐氏,彭城的刘氏等,都有以文学著称的人物出现。世家大族大都重视家学教育,家族的学术传授也很普遍。如王融的母亲是临川太守谢惠宣的女儿,性敦敏,从小教王融书学;何承天的母亲是徐广的姐姐,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顾越“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另外,从一些流传的家诫、家训类的文章,也可看到南朝家教的特点,如徐勉的《诫子书》、王筠的《与诸儿书》、萧纲的《诫当阳公大心书》、颜延之的《庭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对子女进行正面教育,被后人视为家教的规范,在人才的成长、培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南朝文人成才的启蒙。《世说新语·言语》曾有一段有趣的记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世说新语·文学》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这种浓厚的文学氛围,不失时机地因人因事施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自然是一种熏陶和锻炼,而一般的平民家庭,是很难有这种条件的。再如《庾信集序》里有这样一段话:“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贵族华望盛矣哉!”作为一个“独步江南”、“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家庭,对庾信的思想和文学修养必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庾信15岁入宫为太子萧统伴读,19岁任抄撰学士,应该说与他们阀之家优越的条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次,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早期教育有关。翻开《南史》,可以发现几岁就接受教育的不乏其人,大都“少好学”,“少机警”,“幼敏悟”,“少聪慧”。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庾肩吾“八岁能赋诗”,庾子與“五岁读孝经,手不释卷”,范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任昉“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徐摛“幼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徐陵“八岁属文,十三通庄、老义”,丘迟“八岁便属文”,何逊“八岁能赋诗”。此类例子可谓数不胜数。南朝人虽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已经有意识地去做了。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教育最重要的时期是从怀孕到5至6岁这段时间,这一时期是一个人从脑细胞形成到迅速增长、形成神经网络、发展智力最快的阶段,大约50%的智力是在一个人生命的前四年形成的。7岁小儿的脑重量已经达到1280克左右, 基本接近成人的水平,大脑的功能也逐渐成熟,对他们进行教育就能获得比较明显的效果。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经过长期研究也认为,假如17岁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为一百, 那么儿童长到4岁就已经具有了50%的智力,到8岁时就有了80%的智力,剩下的20%是从8岁到17岁近10年获得的,这就是说,人的智力发展,在最初4年等于以后13年的总和。 古今中外一些著名的人物,大多数都接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音乐大师莫扎特4 岁开始作曲,6岁后开演奏会;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白居易5岁学写诗,9岁谙声韵。可见良好的早期教育,能使儿童的智能潜力得到充分挖掘,从而早秀早慧。南朝文人的早熟,就是与其家长根据儿童智力发展的最佳年龄阶段进行早期教育,从而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密不可分的。
第四,南朝文人的早熟,还有一条共同的规律,那就是个人的主观努力。不管是出身寒门还是世族,个人不努力奋斗,难以成才。正如苏轼在《琴诗》里所写:“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岂止音乐如此,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统一的结果。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刘宋王朝有个顾欢,家贫无以受业,于是到学舍壁后倚听,及长,笃志好学,躬耕诵书,夜晚燃糠自照。沈峻“家世农夫,至峻好学”,“昼夜自课,睡则以杖自击”,“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南史》卷七十一)。孔子祛“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役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同上)。袁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南史》卷七十二)。徐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及地上学书”(《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同上)。刘竣“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须发,及觉复读”(《南史》卷四十九)。沈约“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南史》卷五十七)。王僧儒“佣书以养母”,王韶之“家贫好学,尝三日绝粮而执卷不辍”(《南史》卷二十四)。这些都充分说明人的早熟和取得的业绩,离不开勤奋努力。
三
南朝文人的早熟,扩大了文学题材,丰富了文学内容,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李炳海先生在文中认为:“南朝文人大量早熟,促进了南朝文坛标新立异风气的形成。”“南朝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宫体诗浮艳轻靡;即使山水诗,有时也写得富艳精工,典丽厚重。所有这一切,都和南朝文人大批早熟有直接关系。”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尤其是“直接”二字,更没有说服力。
文风是一种普遍性、倾向性的文学现象,文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产物,受政治、经济、文学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论述魏初时的文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鲁迅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文风的特点,充分说明了文风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南朝华丽文风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作品本身看,曹丕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对华美文风的追求。到了南朝,声律之说大兴,作诗讲究平仄协调、对仗工整、词彩华丽,追求形式美成为风尚,进一步助长了文坛上追求华丽文风的风气,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里所讲,“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种文学现象,单靠部分早熟的文人是难以形成的。
魏晋以后,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文学自身的特点逐渐分明,讲究词藻美,从某方面来讲,正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把华丽文风的形成与文人的早熟联结起来,归责于他们,实在委屈了他们。众所周知,宫体诗的浮艳轻靡,是与社会上层贵族生活的日益荒淫腐败分不开的,宫体诗以雕藻绮靡的形式寄寓放荡内容,反映了梁陈时代宫廷贵族的没落生活,更和南朝文人的早熟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南朝文人虽然大多早熟,但幼年、少年时期的诗文很少有流传下来的,找不到标新立异的证据。其中有的“其文丽逸”,“文辞甚美”,“多有新意”,大都是成年以后的作品,和早熟很难牵扯到一起。用妙龄男女往往盛服美饰来比喻青少年写文章也喜欢错采镂金、铺锦列绣,这个比方也是不恰当的,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
责任编辑注:李炳海一文见本专题1993年第9期第73页
标签:李炳海论文; 南朝论文; 读书论文; 老子论文; 汉朝论文; 庄子论文; 玄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心雕龙·明诗论文; 南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