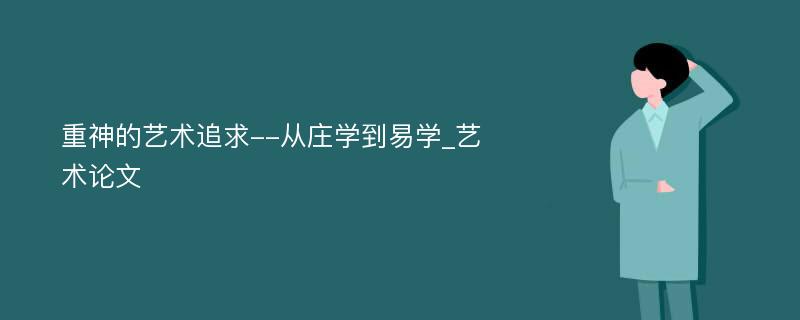
重神的艺术追求:从庄学到易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重视传神是六朝后中国诗学日益强劲的艺术追求。唤醒中国诗学中的重神意识、推动中国诗学中重神追求实现的知识范型,是庄学和《易》学。中国艺术发展史和中国艺术思想发展史同时证明,庄学唤醒了中国诗学的重神意识,《易》学把被庄学唤醒的重神意识引入可操作的实践。而中国诗学研究中,《易》学对重神追求的强化作用,至今未真正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这实是千古遗憾。
关键词 庄子 《易传》 传神论 王弼 杨万里 《文心雕龙》 《文赋》
重神是六朝后中国诗学日见强劲的艺术追求。重神意识的觉醒,以对艺术本质的透彻认识特别是对文学介质的透彻认识为先导。重神追求的实现,以艺术实践的雄厚积累特别是文学介质运用实践的雄厚积累为基础。透彻认识,需要先在的知识范型的指引。雄厚积累,需要先在的知识范型的推动。庄学和《易》学,尤其是《易》学,就是这样的知识范型。庄学唤醒了中国诗学的重神意识,《易》学把被庄学唤醒的重神意识引入可操作的实践,强化了中国诗学的重神追求。而后者似乎还未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文学的介质是语言。中国对语言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信任到怀疑的历史进程。孔子对语言达意的前景十分乐观,他认为意义传达的充分程度,和对语言组织的精心程度成正比。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说法,使孔子“足言足志”的乐观蒙上了一层阴影。孟子“以意逆志”的设计,更突出了语言特别是精心组织过的语言对意义传达的负面作用。庄子则对语言在达意实践中遇到的种种疑难进行了全面揭露和层层紧逼的追问。疑难问题的发现是知识增长的动力,视野开拓的前奏。但事有例外,意义传达的新视野并未随着疑难问题的提出顺理成章地开拓出来。原因复杂错综。错综复杂的原因里,有一种原因对延缓新视野开拓起到明显的作用,那就是由于对庄子“吊诡”表述方式的隔膜而造成的对庄子充满智慧的追问及富于创造的实践的误解。庄子充满智慧的追问和富于创造的实践,已将意义传达的新视野置于地平线上,误解使人对此视而不见。意义传达新视野的开拓,亟需“上学而下达”,把庄子用“吊诡”方式表述的智慧转译成明晰的理论语言,令其以自己的理论威力有力地介入语言操作。转译工作,是在《易》学意、象、言讨论中完成的。意、象、言讨论,始于《系辞》,成于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
《易》学有关意、象、言的讨论,是从“言不尽意”这一明确认识出发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而舞之以尽神’”。(《系辞》)这里所谓的“子曰”,是如《论语》那样属于实有其事的陈述,还是如在诸子书中习见的那样属于策略性的托言?这可以暂置勿论。一目了然的事实是,如同庄子一样,以“冒天下之道”为宗旨的《易》学也被“言不尽意”深深困扰。不同的是,庄子倾力于廓清意义传达中语言崇拜的迷雾,侧重于“上学”;《易》学立志寻找能引导意义传达走出“言不尽意”困境的有效途径,侧重于“下达”。《易》学找到的能引导意义传达走出“言不尽意”困境的有效途径,是“立象以尽意”。“象”指卦象和爻象。卦象和爻象是从繁纷复杂的外部世界抽离出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符号(八卦之象),是为“鼓而舞之以尽神”而创制的具有一定的意向性的结构(六十四卦之象)。卦象结构的意向性,使“象”指向一定的意义。卦象毕竟是一种符号,只要是符号,与它指涉的意义之间的联系就是松散的。卦象结构的意向性,总漂浮不定、含混模棱,需要语言对它加以固定,使之明朗化。此即《系辞》作者虽明知“言不尽意”却仍然坚持“系辞焉以尽其言”的原因所在。由是观之,“立象以尽意”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要抛弃语言,另创一套符号系统传达意义,而是要在处于紧张对立状态的言意之间建立一个能激活言、意的“转换”机制。此旨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阐述得最显豁:“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道不虚行,“意”必须输入到具有一定意向性结构的“象”中,否则意不能出;“象”结构的意向性,必须靠“言”来提示,否则象不能明。得“象”的转换,“言”才真正做到了阐幽显微,穷神尽化。言不妄设,顺着“言”指示的方向,才能清晰把握“象”结构的意向性,无言则象不著;顺着“象”结构意向性指示的方向,才能顺畅领悟“象”要传达的意义,无象则意不尽。得“象”的转换,“意”才真正实现了周流六虚,存神过化。由此观之,“立象”不仅仅是给意义传达增添了一个新要素,更重要的是在言意之间建立起一种转换生成的新关系。新关系使人对言和意有更为透彻的认识,“透彻”集中表现在对意义传达方式的确定和对语言活动范围的划分。“立象”使意义传达成为具有不同层次的系统。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着间隙和距离,又可以自如地转换生成;各层次按其自身的原动力运动,又与意义传达的总体性结构相联系。具有转换生成关系的新系统,使意义传达新范式的确立成为可能,新范式就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里展示的“忘言得象,忘象得意”:“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忘”是对意义传达不同层次之间转换生成的描述,即通过对言、象中的“一般”作“悬置”式的处理,把语言的活动水平提升到最高级次。惯常所认为的“忘”即抽象,实非明通之论。“意以象尽”意义传达方式的确定,“言以明象”语言活动范围的划分,把庄子“言者有言,果有言邪?未尝有言邪?”(《齐物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至言无言”(《知北游》)等“吊诡”表述中蕴含的智慧彰显出来。“忘言得象,忘象得意”,将庄子言语实践中“进技于道”的不懈追求程序化。《周易略例·明象》章所作的工作,是一种别致的理论转译工作:以“言不尽意”为经,诸家尝试性的探索为纬,编织意义传达的新图案。在这幅图案中,诸家的一切探索与讨论都指向“忘言得象,忘象得意”这一新北极。经过这样的理论转译,意义传达终于冲出了“言不尽意”的困境,语言面前终于呈现出“鼓舞尽神”的诱人前景。
庄学的形神论唤醒了艺术的重神意识。一开始(例如在《淮南子》中)只是漫不经心的引述〔1〕,在顾恺之的艺术实践中, 重神才真正成为规范艺术理想和指导艺术表现的最高原则。重神追求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发展极不平衡。当绘画已具有相当明朗的重神追求并形成颇具规模的传神理论的时候,文学仍然在“言不尽意”面前逡巡踟蹰。诗人只要能做到“形似”,就足以使诗学理论家宽慰不已了。〔2〕后世连最平庸的诗人都知道悬诸口头的“入神”追求,还没有浮现于诗学意识,那怕是最先进的诗学家的意识。这无关乎诗学家艺术眼界的高低或艺术趣味的雅俗,不平衡是由不同艺术门类使用的艺术介质的半自律性决定的。绘画艺术的介质是形象的色彩和线条,色彩和线条本身就有形象,就是形象,故绘画艺术理想较容易由写形进至传神。文学艺术的介质是抽象的文字符号。文字是陈述的工具,不是适宜于造型的手段,处于传神达意的最底层。〔3〕文学如欲传神, 首要之务在于彻底扭转言语实践的现状,使语言的活动水平得以根本性的提高,例如提高到“见诗如见画”的水平。只有待语言的活动水平达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时候,“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才有可能成为文学艺术的理想。而语言活动水平根本性的提高,又有待于把语言置于具有转换生成机制的意义传达系统(例如《易》学指示的“意—象—言”系统)中进行有目的的锤炼。六朝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陆机和刘勰正是这样做的。《文赋》和《文心雕龙》不约而同地以“意—物—言”(陆机)或“思—意(意象)—言”(刘勰)作为建构文学理论的逻辑框架,显示出他们向更深的文学理论层次挺进的雄心。《文赋》从“中区玄览,赡物思纷”入手,先解决“意物相称”,再解决“言意相逮”,逻辑井然,步步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理论方方面面的问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使文学介质的活动水平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文心雕龙》下篇专论创作与批评,《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逻辑进程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文心雕龙·序志》)“摛神性”,集中讨论情思的触发,解决“神用象通”问题;“图风势,苞会通”,集中讨论意象的营造,解决“意受于思”的问题;“阅声字”,集中讨论语言的锤炼,解决“言受于意”的问题。而这一切努力,都向着“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鼓天下之动”这一中心汇聚。和《易》学“立言明象,立象尽意”、“鼓舞尽神”的意义传达逻辑密合无间。截止六朝,只有《易》学一家,把意义传达的逻辑阶段区分得如此明晰,把意义传达的系统结构结构得如此浑融,无怪乎它对在“言不尽意”面前逡巡踟蹰的文学,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和如此强大的推动力了。还未读到过能显示陆机《易》学水准的可靠材料,只有六朝小说里见过一条记载,说陆机赴洛途中,在逆旅夜梦与王弼论《易》。小说家言固然不足为训,只能姑妄听之。但上述故事至少可以暗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大贤须《易》”〔4〕,以陆机那样的理论修为,理所应当对《易》学感兴趣,且其《易》学水准已达能与《易》学大家王弼对话的程度。至于刘勰,则无庸费辞。《文心雕龙·序志》篇公开宣布,《文心雕龙》从思想方法选择到理论形式安排都“准乎大《易》之数”。文学上的重神追求,是在盛唐获得理论明晰化的。六朝在《文赋》、《文心雕龙》等鼓舞和指引下对文学介质有目的的锤炼,为打破文学、绘画艺术理想的不平衡,为文学传神论的确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雄厚基础。盛唐诗人从未忘记六朝给予他们的这份珍贵的馈赠。〔5〕
顺便说,在强化重神追求上《易》学与诗学的因缘并未就此终结。陆机和刘勰向《易》学借鉴时,对“立象尽意”各有会心,对“忘言得意”都缺乏理论上的自觉。陆机、刘勰失之交臂的《易》学智慧,中国诗学从未忘怀。宋人、清人陆续补上了这层缺憾。两宋诗学经历了由注重“本色”(法度)向讲求“妙悟”(入神)的历史性转折。推动这一转折的动因是共同的,但促成两宋诗家完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各异,两宋诗家转折后所达诗学境界的浅深有别。〔6〕杨万里的诗学进程, 乃这一转折最明朗的表现之一,就是得益于来自《易》学的助力。杨万里《颐庵诗稿序》有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7〕去词去意,惟“味”是求,是杨万里转折后所达诗学新境界。诗“以味不以形”的诗学认识,“善诗者去词去意”的艺术追求,既源自对自己既往盲目的艺术实践的猛省,又源自对诗歌艺术本质特别是诗歌艺术介质的彻悟。而后者又分明是受《易》学的启发。〔8〕杨万里在《易论》中展示了堪与现代认识相媲美的对语言的总体认识:“言者,心之翳也。晓天下者,暗天下者也。”(《诚斋集》卷84)并在此基础上推求出“圣人”“有余不敢尽”、“有辞如未始有辞”的言语实践原则,及由此而达到的“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的语言效果。杨万里对语言的总体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推论所得,未必能全惬《易》家之心,但这些认识却能为他惟味是求的诗学追求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常州词派“意内而言外谓之词”的认识,开出词学新生面。当时人就注意到了常州词派背后炫丽的《易》学背景。阮元《茗柯文编序》云:“《易》究其原”。龚自珍《常州高材篇》更有神采飞扬的描写:“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易》学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
收稿日期:1995—03—03
注释:
〔1〕所有艺术史论著都把《淮南子·说山训》“画西施之面, 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也”视为艺术理论中重神意识的自觉,这是一个相沿成习的误解。“画西施之面”云云,是《淮南子》为了“知略而明事”设置的一个比喻。它是在证明一个经验事实:死亡或虚假的形体中不可能有神、气,并非要树立一种艺术标准:神的有无决定着人物画艺术的高下。《说林训》也有一则立意相似的比喻:“使旦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尽管绘画中常有谨“形”而失“神”(非《淮南子》所谓“神”)的现象发生,但音乐演奏中决不可能出现一个人吹竽另一个人厌窍的事。这就杜绝了把“画西施之面”云云视为艺术上重神意识自觉的任何可能性。
〔2〕参阅钟嵘《诗品·序》及对刘桢、张协、 谢灵运等列在“上品”的诗人的具体品评。《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3〕参阅陆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引。邵雍《伊川击壤集》卷18《史画吟》:“史笔善记事,画笔善状物;状物与记事,二者各得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
〔4〕殷融(东晋初人)著《大贤须易论》, 见《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中兴书》
〔5〕例如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18,四部丛刊本。杜甫《戏为六绝句》、《偶题》(文章千古事)、《解问五首》、《春日忆李白》,《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6, 19,四部丛刊本。
〔6〕曾季狸《艇斋诗话》:“后山论诗说换骨, 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见《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7〕《诚斋集》卷83,四部丛刊本。
〔8〕参《诚斋集》卷80《诚斋荆溪集序》,卷84《易论》, 四部丛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