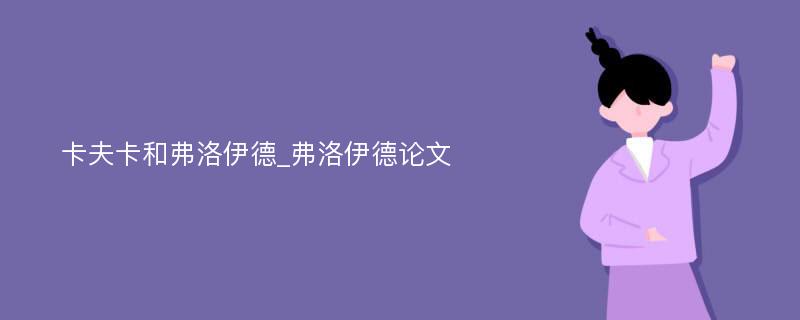
卡夫卡与弗洛伊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卡夫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3)01-0056-05
现在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和阐释卡夫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时髦的事情 了。这不仅因为如今已有许多新理论,譬如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女 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等替代了昔日风行一时的精神分析理论,还因为弗 洛伊德的理论自身也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完善或不能证实的地方,而将某种局部的真理当 作普遍的真理来使用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毕 竟有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卡夫卡又非常熟悉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方法,并在他的创作 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卡夫卡在许多地方并不满意弗洛伊德 的理论,并且,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和方法也常常有嘲讽和揶揄。因此,考察一下卡夫卡 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看看卡夫卡究竟怎样,并在何等程度上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或 者从精神分析角度梳理一下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应当是有必要,也是有意义的。
一、“焦虑的时代”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沃雷姆曾经说过,弗洛伊德“以他那骇俗惊世的文论和博大 精深、大胆新颖的思想,使一个时代的观念、生活和想象发生了一场革命……,在人类 思想的历史上,甚至在宗教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其影响能像弗洛伊德这样直 接,这样深远”[1]。毋庸置疑,卡夫卡的确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并且,由于卡夫 卡与弗洛伊德在许多地方,比如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思维方法和兴趣爱好上有着相同 或相近的地方,因此卡夫卡学习、借鉴和运用弗洛伊德的思想和理论恐怕就比一般人更 为自然,也更加自觉。
第一,就大环境而言,他们大体上都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 是一个“焦虑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从物质上毁灭了欧洲,而且从精神上彻底 埋葬了人们心中的上帝。对理性科学的怀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望,对大规模战争的 恐惧,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现代化生产中人被异化的担忧……,这一切汇合成一股汹 涌澎湃的潮流,荡涤着昔日的一切,倾斜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思考和结论。于是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信仰的替代物也就应运而生。现代人的这种焦虑感、孤独感、隔离 感、恐惧感既是精神分析派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也是卡夫卡创作的主题和源泉。
第二,就小环境而言,卡夫卡与弗洛伊德的个人身世和经历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 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比卡夫卡大27岁,死于1939年,比1924年 去世的卡夫卡多活了42岁。弗洛伊德生于莫拉维亚一个小镇弗莱堡,以后主要在维也纳 受教育和行医;而卡夫卡除了在欧洲有过几次短暂的旅行和逗留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 过布拉格。这些地方当时都属于奥匈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从奥地利的政治、经 济、文化背景来看,弗洛伊德和卡夫卡同时在那里出现,似乎是十分自然的。当时的奥 匈帝国在生产方式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它对外侵略扩张, 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在当时的欧洲它是一个相当落后的政权。在欧洲统治了7个世纪的 哈布斯堡王朝,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激化,王朝的统治正在分崩离析。19世纪迅速发展起 来的资本主义则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巨兽,既使人兴奋激动,又吞噬着无辜的一切。总之 ,“二十世纪奥地利的经济状态和道德状态已经给精神分析和神秘学说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2](p226)另外,他们都是犹太人,并且都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卡夫卡的 父亲经营纺织品、百货,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个羊毛商,只不过弗洛伊德很小的时候他 父亲的生意就败落了。他们都是受德语教育、说德语的犹太人,虽然都精通或熟悉多种 语言,但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以上生活环境和经历的相同或相近使卡夫卡比较容易理 解和接近弗洛伊德的思想和理论。
卡夫卡和弗洛伊德都是极端敏感的犹太人,当时欧洲的排犹主义情绪给他们留下了刻 骨铭心的印象。但是,他们两人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或挑战这种环境:卡夫卡越 来越多地将自己封闭起来,越来越深地去探索自己的心灵和人类的灵魂;弗洛伊德则反 而更加增强了他的反抗和叛逆情绪,并发愤图强、有所作为。面对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 ,卡夫卡变得越来越内向;弗洛伊德则变得越来越外向。有趣的是,弗洛伊德的外在成 功最终却是通过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而获得的。
第三,弗洛伊德虽然是学医,但他对哲学一直有着浓郁的兴趣。在大学里他曾连续三 年选修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教授的哲学课,并在布伦塔诺的推荐下翻译 过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哲学著作。正是这位哲学教授后来又来到了布拉格大学,他的叛逆 精神和学说成了卡夫卡及其同学的崇拜对象。布伦塔诺建立了一种描写心理学,或者说 内省心理学基础上的“经验”哲学,这一哲学对后来的胡塞尔等有很大的影响。布伦塔 诺认为,“由于与整个物理现象对立的是整个心理现象或意识体验,因此,确定真理所 在的问题就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真的现象或假的现象能在意识界的哪些局部领域里 呈现出来。为此,首先需要就心理学的东西的总体进行研究。”[3](p42)布伦塔诺将世 界分为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心理现象又可划分为表象、判断和情感行为,三者之中, 表象处于基本的地位。心理现象的根本特征是意向性,也就是说,每一心理现象必然与 一对象相关联,只有发生心理活动时,物理现象作为相关物的存在才有意义。布伦塔诺 对心理活动的重视和研究无疑对弗洛伊德和卡夫卡都有重大影响。
第四,对人的心灵的秘密的探索也许是他们的最大的共同点。弗洛伊德说:“确切地 说,我是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地是对于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 他事物。”[4](p3)弗洛伊德对人的关心,主要集中于对人的心灵的关心。他穷毕生精 力所探索的就是心灵的地狱这个迷宫的出口。弗洛伊德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在19、 20世纪之交从人类深层心理的角度提出了文明对本能压抑的问题。卡夫卡一生都在探索 生活的秘密、真理的秘密和人类内心的秘密。“生活大不可测,深不可测,就像我们头 上的星空。人只能从他自己的生活这个小孔向里窥视。”“还有比真理更大的秘密吗? 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真理也许就是生活本身。”[5](p492.468 .469)卡夫卡在窥视生活的秘密、探索真理的秘密、呼唤生命的秘密,“对卡夫卡来说 ,艺术表现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影和客观化,使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变得可以看见”[6](p1 55)。看来,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与卡夫卡可谓殊途同归。
第五,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著作《释梦》(1990)、《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1904)、 《性学三论》、《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图腾与禁忌》(1915)、《精神 分析引论》(1917)、《超越快乐原则》(1920)和《自我与本我》(1923)均发表于卡夫卡 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发展成熟期。艾伦·布洛克曾经说过,“大概没有哪一个人对二 十世纪思想、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能超过弗洛伊德了:不仅他最富于创见的作品都是在19 14年以前完成的,而且他的观点引起的争论在当时就已经展开了。”[7](p49)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增多了,人们在精神上更加空虚、苦闷和悲观,他们希望 在精神上找到救赎之路。这给精神分析学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的丰沃的土壤。这 以后,精神分析学便开始成为一种无形的酵母注入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 、政治学等各个领域。
综上所述,在这种背景下,卡夫卡完全有可能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和学说,并将其灌 注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去。但是,卡夫卡与弗洛伊德毕竟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弗洛伊德具 有英雄气概,卡夫卡更多的却是弱者胸怀;弗洛伊德爱情幸福、婚姻美满、家庭快乐, 卡夫卡则爱情失败、没有婚姻、没有家庭;弗洛伊德活着的时候就已看到他的思想和学 说风靡世界,而卡夫卡活着时却几乎默默无闻;弗洛伊德活到83岁高龄、有6个子女, 卡夫卡则只活了41岁、而且孤身一人。凡此种种,均说明卡夫卡与弗洛伊德是有距离的 ,卡夫卡不可能不假思索地选择和接受弗洛伊德。
二、“想到了弗洛伊德”
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曾经说过,“不可否认,卡夫卡的情况可以作为弗洛伊德的潜意 识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解释太容易了。事实上,卡夫卡本人对这些理论是非常熟悉的 ,但并不很重视,只是把它当作事物非常粗略的和近似的图像。他认为这些理论在细节 上并不是很恰当的,特别是关于冲突的本质。”[2](p226)卡夫卡在日记中也的确证实 了这一点,1912年9月23日,卡夫卡写道:
在22、23日夜间,从晚上10点到清晨6点,我一气呵成写完了《审判》。由于一直坐着 ,我的腿如此发僵,以至都不能将它们从桌子底下移出来。当故事情节在我面前展开时 ,我处在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之中……,夜里我多次将批评的重点落在我自己身上……, 写作期间我的情绪是:高兴,比如说,可以给布罗德的《阿卡狄亚》提供某些优秀的作 品,当然也想到了弗洛伊德。
卡夫卡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弗洛伊德,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卡夫卡对弗洛伊 德及其理论是比较熟悉的。“由于周围有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因此卡夫卡非常熟悉精 神分析理论,并且他的许多小说,譬如《一条狗的研究》、《巨鼹》、《地洞》等都或 多或少地试图建造一种象征模式,这种模式也就是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所探寻过的。”[8 ](p200)卡夫卡上大学时有一位专攻心理学的朋友奥托,他后来曾去维也纳跟随弗洛伊 德继续研究心理分析,并参加过弗洛伊德组织的“星期三晚间研讨会”。卡夫卡与他的 亲密交往,无疑使卡夫卡增加了对弗洛伊德的了解。1899年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创 办了《火炬》月刊,他在这分杂志上经常刊登攻击弗洛伊德的文章,而这分杂志卡夫卡 是非常熟悉的。卡夫卡当时还听过克劳斯的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讲座。1913年,卡夫卡 结识了一位朋友,名叫恩斯特·魏斯。他是一位犹太医生,早年在维也纳学医时他便发 现了弗洛伊德。他对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有一定影响,在卡夫卡与他的女友菲莉斯的关 系上,他甚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布罗德的回忆,卡夫卡曾经说过,他对父亲的优越地位的态度不是在“日常的思 考”中形成的,而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亲身经历到的”。他关于他父亲的“教育方法 ”的言论,他论及教学法的书信“都肯定着精神分析的观点”[2](p226)。卡夫卡还非 常重视梦的意义和作用,他的某些有关梦的观点与弗洛伊德颇有相同之处,尽管我们目 前还没有材料证明,卡夫卡曾经读过弗洛伊德的《释梦》。布罗德认为,“若没有弗洛 伊德,卡夫卡也许从来不会对自己的梦给予那么多的注意。”“卡夫卡似乎只对自己的 梦感兴趣。”[9](p2)1910年,卡夫卡第一次写日记就记下了自己的梦,他在观看了彼 得堡俄罗斯芭蕾舞团艾杜瓦夫多娃的表演两个月后,又梦见了她。他甚至在梦中请求她 再跳一次查尔达斯舞,但这时候却出来一个“潜意识的阴谋者做着使人生厌的动作,对 她说,火车就要开了”[5]((6)p4)。以后他在致女友菲莉斯的信中曾数十次谈到梦,他 说他几乎天天梦见她。卡夫卡说过,“我们只是以自然性质的无法理解的高速度走过真 正的事件之前或者之后经历它们,它们是梦幻般的、仅仅局限于我们心中的虚构。”他 还说,他的小说《司炉》是“梦呓”,是“闭着眼睛的图像”[5]((5)p153.322)。然而 ,尽管如此,卡夫卡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核心——精神分析却颇有微词。“卡夫卡在精神 分析实验室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反对这种做法。精神分析家对治疗步骤的信心使卡夫 卡不以为然。……他实际上认为,简单的将精神病的根源从表面上再现出来,对非理性 进行有意识的观察研究,并不能改变或改善病状。”[2](p231)卡夫卡在一封致密伦娜 的信中写道:
试着将它当作一种疾病来理解吧。这是心理学家骄傲地有了许多发现的诸多的病理现 象中的一种。我不把它叫做疾病,我认为心理分析的治疗方法是毫无希望的谬误。所有 这些明显的疾病,无论它们多么悲惨,都是信仰的问题,都是处在悲苦中的人试图扎根 于某片母亲土地所作的努力。[5]((10)p417)
卡夫卡反对弗洛伊德的“理性主义”,反对他所坚信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信条,反 对将信仰当作疾病来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在这些地方,他更接近的是基尔凯郭尔,而不 是弗洛伊德。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同基尔凯郭尔“十分相似,至少可以这样说 ,他和我生活在世界的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证明我是正确的”[5]((6)p259)。基尔 凯郭尔同卡夫卡一样,孤独一身,没有结婚。他有过一次终生难忘的热恋,但是,也同 卡夫卡一样,订婚一年后又解除了婚约。原因是他不能因为尘世的幸福而放弃对上帝的 崇敬,所以,在最后的抉择中,他选择了上帝,而不是他所热恋着的里贾娜,尽管他对 里贾娜终生不能忘怀。
卡夫卡和基尔凯郭尔有某种基本相同的感觉:焦虑和恐惧。这种焦虑和恐惧,在弗洛 伊德看来,就是疾病问题,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来加以克服和清除;但是,在基尔凯郭尔 看来,这却是“寻找信仰过程中所必须有的感情因素”,也正是作为个体的人应当加以 保护和坚守的情感。而卡夫卡则赞同基尔凯郭尔的观点,他认为,“信仰的行动远比身 体健康和社会的调节深奥得多,这就使信仰的行动看起来好像是普通健康的身躯和精神 的严重分裂。”[2](p249)这样,卡夫卡便将自己与精神分析家们区别开来了。总之, 弗洛伊德试图以理性来说明非理性,卡夫卡则拒绝以理性来解释非理性;在弗洛伊德那 里,所有的秘密都可以通过理性来加以揭示,在卡夫卡那里,理性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 并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弗洛伊德以理性来解释信仰,卡夫卡则以非理性来证明信仰。在 宗教和信仰问题上,卡夫卡与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什么相通之处。
三、父亲与上帝
卡夫卡对弗洛伊德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认识自然会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但是,卡 夫卡虽然受到过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他的创作却决不只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例证, 并且,他的创作从来都不拘泥于任何理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弗洛伊德的理论。他以独 特的思想和方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以及他周围的所有作家,当然,他也超越了弗洛伊德 。
父子矛盾一直是卡夫卡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卡夫卡把自己描写成他父亲的牺牲品— —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压根儿就不写其它的东西。他的天赋就在于这样写就会使他的问 题和虚弱引起人们的共鸣,那些人似乎跟他不一样,但实际上跟他又没有很大的差别。 ”[9](p390)如何理解和分析卡夫卡创作中的父子矛盾?这种父子矛盾与弗洛伊德理论的 关系如何?是因为卡夫卡了解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才有意识地去描写父子矛盾呢,还是 卡夫卡从自身的情况出发进行创作,无意中成了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例证?可惜的是, 弗洛伊德当时还不知道在文坛默默无闻的卡夫卡,不然,他读到卡夫卡后一定会欣喜若 狂,并且,凭他敏锐的艺术感受和勤奋的写作习惯,一定会留下珍贵的文字资料。我们 现在读不到弗洛伊德对卡夫卡的评论,但是,我们却很容易拿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和 理解卡夫卡,并且还很容易将卡夫卡的作品简单化、弗洛伊德化。对此,评论家克劳斯 ·曼曾经告诫我们说,“任何精神分析学家都可以把卡夫卡的那种哀怨的宗教感情—— 他的谦卑恭顺,对上帝的不相信而产生的宗教感情——解释成由一种明显的‘父亲情结 ’而产生的‘升华’。”[2](p241)
我们究竟应当将卡夫卡的父子矛盾解释为一种“俄底普斯情结”呢,还是一种“宗教 ”情结?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俄底普斯情结”就是“宗教”情结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你根本就无法将这两个问题分割开来,正如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无 法将这两个问题决然分开一样。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卡夫卡大概可以算得上最典型的“弑父娶母”病例了。卡夫卡 在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
最初几年里我记得的只有一件事。有一天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过不是因为口渴, 而可能一部分是为了给你找点麻烦,一部分是为了寻乐。在各种强烈的威胁不能生效后 ,你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抱到阳台上去,锁上门,让我一个人穿着睡衣在那里呆了一阵 子。……许多年后,我还一直保留着这种惊恐的想象:那个巨大的男人、我的父亲,审 判我的最后法庭,深夜里向我走来,毫无理由地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带到阳台上去——换 句话说,这才是他所关心的,而我则是无足轻重的。
在“父子矛盾”中,母亲似乎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在这场争夺母亲的斗争中,卡夫卡 永远是一个失败者。日后,卡夫卡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和不满,“因为我是一个年幼 的孩子,在反对父亲的斗争中失败了,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使自己离开这个战场 ,虽然他仍然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击败我。”[10](p15)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怀恨他 父亲,甚至想谋杀他父亲,这些都应当是十分自然的想法。多年以后,卡夫卡保存着有 关“阳台”的恐怖记忆,这在弗洛伊德看来便是一种幻觉、一种象征,它既是对父亲权 威的证明,又是对卡夫卡的犯罪心理的惩罚。
更有甚者,年幼的卡夫卡本来就没有获得多少母亲的关爱,而当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在1 885年和1887年出生时,卡夫卡对这两个闯来同他争夺母爱的竞争者更是怀有强烈的怨 恨。“卡夫卡一定希望他们远离他的生活,并且,在最初的想象中他试图通过魔法将他 们谋杀。”[10](p16)事情后来果然按照他的想象发展,他的幻想变成了事实。格奥克1 887年春天死于麻疹;亨利希1888年死于中耳炎。卡夫卡在无意中“谋杀”了两个年幼 的弟弟。弟弟的死给卡夫卡心灵留下了沉重的负罪感,以致于他从来都没有觉察到,而 多年后他在作品中却泄露了他的这分压抑的情感,这也许就是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犯罪、 赎罪和惩罚的原因之一。
卡夫卡的性意识、性心理也不大健康。在成长过程中卡夫卡痛恨自己的身体,他害怕 肉体的亲近。对他来说,性就是污秽的极至,是爱的对立面。1913年8月14日,他在日 记中写道,“性交是对一切幸福的惩罚。”在他看来,“你所爱的,你不能同她睡觉; 你与她睡觉的,你却并不爱。人们只爱他的朋友、母亲和妻子。”[10](p91)卡夫卡的 这种性心理障碍最后甚至导致了他的恋爱、婚姻的失败。卡夫卡的这种性心理疾病,如 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进行心理分析,就应该到他的童年往事中去寻找致病的根源。而 这样做还果然能够奏效,因为卡夫卡童年时代似乎受到过他的法语家庭教师的引诱。这 位贝丽小姐的“那种使人兴奋的肥胖,似乎更适合于给人刺激,而不是作家庭教师”。 她显然充当了卡夫卡的“第一个性意识对象”。这种被引诱的犯罪心理遏制了卡夫卡性 心理的正常发展,导致了他对女人的恐惧,并影响到他对女人的看法。这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卡夫卡作品中的女性总是些丑恶的形象,譬如《城堡》和《诉讼》中的女性便是 这样。
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他对待父母亲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卡夫卡又崇拜他 父亲,敬爱他父亲,甚至在他的感情中还夹杂着一种脉脉温情,并且他还常常为自己没 有尽到做儿子的义务而深感不安。同时,他虽然爱他的母亲,但又非常嫉恨她。所有这 些,我认为,单单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难以解释清楚的。因此,如果不将卡夫 卡的“父子矛盾”同他的宗教意识结合起来,那将不可能是一个全面的、真正的卡夫卡 。
卡夫卡对犹太教的认识和态度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并且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他对犹 太教的情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由恨到爱的过程。“卡夫卡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但同 时也是一个与犹太人社会决裂的犹太人。”[6](p112)最初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犹太 人时,他感到痛苦;但是,最后当他恨自己时,却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是因 为他不是一个充分的犹太人。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卡夫卡渐渐改变了他童年的看法。上 中学时卡夫卡常常与贝格曼一起讨论有关犹太教的问题。贝格曼以后回忆说:“那时, 卡夫卡正经历了一个无神论者和泛神论阶段,他坚决要我摆脱犹太教信仰。”[10](p66 )当然,卡夫卡最终没有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卡夫卡后来对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复兴 充满了热情。他坚持每期不漏地阅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周刊《自卫》,坚持听希伯莱语 课,并萌生了去巴勒斯坦当犹太农民的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直到他生病放弃这一计 划之前,他一直都在严肃地考虑如何移居巴勒斯坦。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热 切地希望他昔日的同学贝格曼能帮助自己实现定居巴勒斯坦国的梦想。
因此,所谓“父子矛盾”中的父亲,其实就是剥去了圣衣的上帝;反过来,卡夫卡心 目中的上帝,也就是罩上了圣环的父亲。“几乎卡夫卡的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描写父亲 的奇怪形象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审判》、《城堡》、《在流刑营》等作品都把父亲 的地位描绘为难以接近的上帝,如同《约伯书》中怪诞的上帝或者是基尔凯郭尔的《恐 惧与颤栗》中的严厉而难以对付的上帝。”[2](p230)
《判决》是卡夫卡的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写父亲判决儿子立即溺死,儿 子便飞快地跑去投河自尽,临死前儿子轻声叫道:“亲爱的父亲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 们的呀!”小说情节虽然十分荒诞,但寓意却十分深刻。小说十分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对 父母的那种爱恨交加的感情。小说中“父亲”明显具有《旧约》中耶和华上帝的特征。 另外《变形记》中的父亲、《在流刑营》中的原司令官也都属于这一类形象。卡夫卡甚 至向布罗德说过,他计划将自己的全部作品命名为“逃离父亲的范围的愿望”[6](p116 )。
《美国》是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16岁的少年卡尔·罗斯曼受到中年女 仆的引诱后,被父亲放逐到美国的生活经历。在这部小说中父亲的形象虽然没有出现, 但父亲的权威和力量却不可忽视。在犹太文化中父亲常常就等同于上帝。“犹太人信仰 上帝是和信赖家庭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并不等于祖先崇拜,不过二者的区别有时确 实模糊不清;将上帝奉为父亲往往蜕变成将父亲奉为上帝,尤其是在父亲去世时。”[1 1](p16)罗斯曼因为过失而被父亲放逐,只身来到陌生的土地开始他的流浪生涯,就像 犹太人的祖先因为违背上帝的告诫而受到惩罚一样,犹太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开 始了漫长的漂泊之旅。卡夫卡便是“把与《圣经》里令人敬畏的上帝的关系这种传统的 形象投射到了父亲身上”[6](p115)。
《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寓意是什么,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对 此一直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塞克,卡夫卡写《城 堡》就是克服自己和父亲不愉快的经验,以摆脱笼罩了他一辈子的“沃塞克阴影”。这 部小说在表现了“父子冲突”的同时,还着重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 父亲的权威,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既恐惧,又依赖 ;既憎恨,又敬爱。而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则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 征”。《城堡》的中心所在就在于表明,尘世间和宗教行为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 这种人与上帝的区别,犹太人用一句谚语表现得相当精彩,“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人类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类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也就愈远。因为 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父亲与上帝的形象在这 里已经合而为一:父亲和上帝原本是一个形象。
收稿日期:2002-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