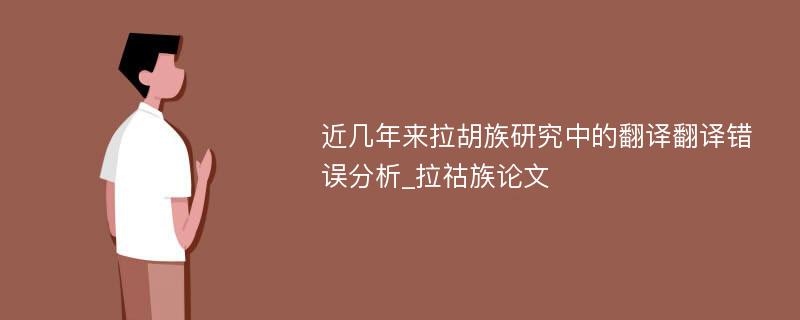
近年国内拉祜族研究中的翻译释义错误汇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祜族论文,释义论文,近年论文,错误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祜族是云南境内古老的民族之一。解放前,有关拉祜族研究的著述微乎其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不仅对云南拉祜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出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调查资料、著作和论文,而且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学者对境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拉祜族的研究文章。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拉祜族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失误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和释义错误两个方面。有些翻译(无论是音译或意译)与拉祜语相去甚远,有些释义则与其本意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我们对拉祜族历史、哲学、文化诸方面研究的科学性。今笔者拟将近年国内拉祜族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而又典型的上述失误现象汇辑起来,并试图更正之。目的在于正本清源,还事物以本来之面目,供学界同仁在拉祜族研究中加以注意和参考。
1.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思茅拉祜族传统文化调查》一书载:“龙竹棚拉祜族信仰的祖鲁佛……传到莫骨后山,在那里正式建立了葫芦寺,至今佛寺的遗址还在,信佛祖的人年节时还去遗址处烧香点蜡做功德。”〔1〕此外, 该书中还有“葫芦寺传袭的佛规”“葫芦寺派”等文。但未说明“葫芦”一词的由来,也没有解释“葫芦”一词的含义。其实,“葫芦”是拉祜语〔ra[,54]〕(国际音标注音,下同)的音译。“葫”乃“佛”的拉祜语音译,源自汉语的“佛”,语义与汉语相同。“芦”是“大”的意思,为傣语借词。“葫芦”的意思是“大佛”或“大佛圣地”,为澜沧历史上五佛之一南栅佛的一部分〔2〕。 “葫芦”是今南段一带拉祜人早期建盖的佛寺原址。据南段前任“召八”(拉祜语音译,为佛教管理者之一,由众教徒选举产生)扎努扎四八说:“葫芦是今拉祜西佛教徒的共同圣地,不属于哪家哪派。”〔3〕故南段拉祜西地区不存在什么佛教的“葫芦寺派”。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5日出版的《民族译丛》1980年第2期上载有由英国安东尼·R·沃克著,龚佩华译、张家麟校的《拉祜族的支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支系的成员身份就决定这个拉祜人操什么语言、穿什么服装或者如何建造房屋,祭献精灵以及崇奉他的至高无上的超自然的‘魁莎’”。杨毓骧先生翻译的另外一篇安东尼·R ·沃克的文章《拉祜尼(红拉祜)建新村的宗教仪式》(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的《民族研究译丛》〈11〉)里多次出现“ra[,54]”,但译者始终未译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 期刊载李增贵编译的《泰国的拉祜族》一文中云:“道士为小孩褥告(应为褥告——引者),求贵萨神接受祭品并给予保护”、“拉祜族取名方法……鸡日叫‘垓’。“第二是贵萨,拉祜人视为上帝”、“道士是村民的宗教神职人员,也是村民和贵萨之间的主要调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缅甸景栋出现了一个救世主叫毛纳贵萨。”
上文中的“魁莎”、“贵萨”可以断定是老拉祜文“ra[,54]”的音译,因为三篇文章都是介绍泰国拉祜族的。据保罗·刘易斯氏《拉祜语英语泰语词典》(Lahu—English—TaiDictionary ,Compiled by PaulLewis,Published by Thailand Lahu Baptist Convention)中的权威解释:拉祜语“ra[,54]”对译为英文的“God”(上帝)。 “ra[,54]”的实际读音是〔ra[,54]〕,即国内许多拉祜族研究著述中经常提到的“厄莎、厄霞、恩莎”等,有人把它叫作天神,有人叫作天地之神、创世神。前述数篇文章的翻译者,要么保留拉祜文“ra[,54]”,要么将拉祜文的“ra[,54]”直译为汉语的“魁、贵”。但“魁(kuí)”“贵(guì)”的声母分别是〔Kh〕〔K〕,而拉祜文“ra[,54]”的声母是〔ra[,54]〕。尽管〔K,Kh,ra[,54]〕的发音部位相同,即它们都是舌根音,但其发音方法有异,〔K,Kh〕是清塞音, 而〔ra[,54]〕是浊擦音,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无此音。〔ra[,54]〕音译为汉语的“厄、峨、俄、娥、儿、尔”等都比较接近拉祜语本音,但把它译作“魁、贵”等,则与拉祜语的读音相去太远。把拉祜语的〔ra[,54]〕(鸡)音译为“垓”,这实为将拉祜文声母“ra[,54]”的读音与汉语拼音“G ”(声母)的读音误作同一读音所致。
3.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中将“厄莎”解释成:“‘厄莎’在拉祜族的不同方言里,有厄霞、厄雅、恩莎等不同的叫法。在拉祜语言中意思是开朗、顺利、会想办法的人。拉祜人民赋予自己天神以美名,并对它衷心敬仰。”据拉祜族著名口头神话传说《牡帕密帕》(开天劈地)记载:“厄莎”是创世之神,它足智多谋,温和善良,确实具有“开朗、顺利、会想办法”等特征,但“厄莎”在拉祜语里是对无形的、超自然力的、至高无上之神的抽象概括,有其特定的哲学含义,而不是对“开朗、顺利、会想办法的人”的简单称呼。
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拉祜族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载云:“社会关系比较发达和受大乘佛教思想影响的拉祜纳支系,则认为厄霞有一位妻子地神密纳玛……此外还有……雷神姆页铁。”之后,1988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拉祜族民间文学集成》前言(以下简称《前言》)中也说:“拉祜纳则认为厄萨(即厄霞——引者)有一个妻子,就是地神密纳玛,这跟爰剑与劓女的婚事暖昧不无关系。”《前言》作者主观地认为: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中的“爰剑”是厄萨的原型,“劓女”是密纳玛的原型,这实在是有些善意的拔高了。
“厄莎”和“密纳玛”的音译接近拉祜语,但对“密纳玛”的解释却令人啼笑皆非。“密纳玛”的拉祜语原义为“黑土地”,即拉祜语对“大地”的称谓。与“地”相对的“天”叫〔ra[,54]〕(木挪玛)。《简史》和《前言》都肯定地说“密纳玛”是“厄萨”的妻子,使创世之神“厄萨”有了它所创造的“大地”妻子,而且还将“厄萨、密纳玛”与“爰剑”、“劓女”的婚事相关联,想象虽然丰富,但因对“密纳玛”的释义严重错误,故其比较的前提是错误的,显然毫无价值。至于将“雷神”译作“姆页铁”,这纯属译者新创的拉祜语。因为受大乘佛教影响较大的拉祜纳或拉祜西,都将“雷神”叫作〔ra[,54]〕(姆铁尼)〔4〕。
5.《拉祜族民间文学集成》里有个故事叫《亚珠西与左雅米》,它是讲孤儿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开头说:“从前有个孤儿,名叫亚珠西。”脚注云:“亚珠西,拉祜语意为孤儿。左雅米,拉祜语意为龙姑娘”。本来脚注已准确地译出了“亚珠西”与“左雅米”的拉祜语含义,但正文里却一直把他们当作人物的名字来使用。或许编译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或突出拉祜族民间文学的特点,然而却弄巧成掘,让懂得拉祜语的读者读起来就感到莫名其妙了。其实,这段译文按原文翻译成“从前有个孤儿,他家很穷”,也不仅不失其原意,而且开门见山,更具有拉祜族民间故事开头的叙述特点。如果我们将“从前有个孤儿,名叫亚珠西”中的“亚珠西”也译成汉语,那么就变成“从前有个孤儿,名叫孤儿”了。我想在其它汉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也不会有这种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译文。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思茅拉祜族传统文化调查》一书第253页中, 甚至将“亚珠西”解释为“独儿”,这就错上加错了。因为孤儿有男女之别,独儿子不等于孤儿。
6.有些著述中解释说:“祈祷”,拉祜语叫“搓斯俄查”;“大家庭”,拉祜语叫“底页”;“小家庭”,拉祜语叫“底谷”;“扩搭”即过年、春节,是拉祜族众多节日中最隆重的一个〔5〕。 这些解释和翻译都是错误的。
“搓斯俄查”是拉祜语〔ra[,54]〕的音译,逐字译为汉语则“人死饭吃”,即“吃死人饭”。据笔者所知,无论拉祜纳支系,还是拉祜西支系(指澜沧江以西的拉祜西),“祈祷”都不叫“吃死人饭”。虽然在祈祷时祭献祖先,但与祈祷有关的事项,拉祜语一律叫“波罗”〔ra[,54]〕、“波可”〔ra[,54]〕、“波章细章”〔ra[,54]〕、“波罗细罗”〔ra[,54]〕等等,不知“搓斯俄查”源自何处?祭献祖先也不叫“搓斯俄查”,而是叫“赕”〔ra[,54]〕,借自傣语,其意为“献”。
“底页”和“底谷”都是数量词组,意为“一间(幢)房子”和“一个家庭”,与“大家庭”和“小家庭”的拉祜语音译毫无关系。实际上,这些材料皆源自澜沧县糯福乡南段、巴卡乃等拉祜族地区。但迄今为止,这些地区的拉祜人一律称“大家庭”为〔ra[,54]〕(页路玛)、〔ra[,54]〕(页谷路)、〔ra[,54]〕(页姑路)、〔ra[,54]〕(搓姑路)等;称“小家庭”为〔ra[,54]〕(搓姑耐)、〔ra[,54]〕(页姑耐)。按拉祜西人的传统表述方法,将“大家庭”比作“蜂巢”,将“小家庭”喻作“蜂房”。“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关系比作“蜂巢”与“蜂房”的关系。把“大家庭”和“小家庭”译作拉祜语“底页”和“底谷”,是将拉祜语的数量词组误译为名词所致。
“扩塔”即拉祜语〔ra[,54]〕的音译,它是修饰词组。拉祜语称“年、节”为“扩”,称“某时”为“塔”,故“扩塔”的意思是“年节之际”或“年节期间”,它既可以指“春节期间”,也可以指其它“节日期间”。把“扩塔”释作“过年、过春节”是将修饰词组当作动宾词组使用。拉祜语称“过年(春节)”、“欢度节日”为“扩扎”〔ra[,54]〕,即“吃年”〔6〕。 受汉族影响较大的拉祜族地区称“过年(春节)”为“扩过”〔ra[,54]〕,保留着本民族语“扩”,但动词“过”则借自汉语。由于拉祜语语序为主——宾——谓结构,所以仍将汉语借词置于宾语“扩”的后面,形成宾动结构“扩过”。无论如何也不该把“过年(春节)”叫作“扩塔”。
7.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和《拉祜族简史》(1986)中记载了耿马、澜沧等县拉祜族的亲属称谓。《简史》载:“近代拉祜两支系的亲属称谓里,兄、姨表兄、舅表兄和姐夫都叫‘阿伟巴’;弟、姨表弟、舅表弟和际婿都叫‘阿里巴’,姐、姨表姐、舅表姐和嫂都叫‘阿伟玛’;妹、姨表妹和弟媳都叫‘阿里玛’”。《调查》中所记载的亲属称谓的开头也都有一个词头“阿”,如“阿奶”(祖母)、“阿布”(祖父、岳父)、“阿移”(母亲及其妹妹)、“阿巴”(父亲)等。拉祜语里,亲属称谓有对称和他称(引称),对称时用“阿”词头加亲属称谓名称,而他称(引称)时,其词头不用“阿”,而是用“俄”〔ra[,54]〕。《简史》里所指的“拉祜两支系”属澜沧境内的拉祜纳和拉祜西,书中把两支系的亲属称谓等同了起来。其实,据笔者所知,两支系的语言有差异,其亲属称谓也有区别,如拉祜纳称姐和嫂为“阿伟玛”〔ra[,54]〕,称妹和弟媳为“阿尼玛”(《简史》中把它译为“阿里玛”,误)。但迄今为止澜沧县糯福乡南段、巴卡乃、洛勐、完卡四个村公所境内的拉祜西人称姐为“阿伟”〔ra[,54]〕,称嫂和弟媳为“篾”〔ra[,54]〕,称妹为“阿娘”〔ra[,54]〕,将上述“阿”改为“俄”则为引称。有关两支系的亲属称谓异同,容另文介绍。
8.有些著述中把拉祜语“屋吉屋卡”〔ra[,54]〕简称为“屋吉”。“屋吉屋卡”(有人译作奥者奥卡)是由“屋吉”或“奥者”和“屋卡”或“奥卡”构成的四音连绵词(又叫四音格词),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完整的词。“屋吉”的“屋”是词头(前缀),“吉”是词根,其意为“种类、种族”;“屋卡”的“屋”也是前缀,“卡”是词根,其意为“宗族、血族”。“屋吉屋卡”的意思是“亲属、亲族、同族”。拉祜语四音连绵词的特点是结构稳固,常用于阐明事理,具有抽象性和极好的修辞效果。与其将“屋吉屋卡”简称为“屋吉”,还不如干脆把它意译为“亲属制度、亲族集团”,保留它一半的音译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人为地添乱,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
9.《拉祜族简史》中试图对“拉祜”一词作解释,说“拉祜语里‘拉’是虎的意思,‘祜’是没有语义的语尾词。从语义上看,拉祜是用虎来命名的族称。”许多涉及拉祜族的著述都称拉祜族是“猎虎的民族”,并解释说“拉”是虎,“祜”是“烤”和“烤肉发出的香味”。这种解释初看似乎有理有据,但我们若作仔细推敲,却错漏百出。先说“拉”〔ra[,54]〕,它在拉祜纳方言中是对“虎、豹”类的泛称,而非专指“虎”。只有在拉祜西方言中,“拉”才是对“虎”类的专称,“豹”类叫“扎咩”〔ra[,54]〕。若按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拉祜纳方言将“拉”译作“虎”便得出“拉祜是用虎来命名的族称”的结论的话,那么,同理也可以得出“拉祜是用豹来命名的族类”的另一个结论,由此还可以得出“拉祜是用虎豹来命名的族类”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结论来,岂不滑稽?
我们再看看“祜”。“拉祜”的“祜”源自拉祜语〔ra[,54]〕(宏)。清朝、民国乃至50年代初的历代文献中,都将拉祜族写作“倮黑、倮黑族”〔8〕。到1953年, 在《关于拉祜族自治区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才首次出现了“拉祜”一词的写法。该报告对“祜”解释为“代表幸福”〔9〕。很显然,这是旧词赋予新意。由此可见,“黑、 祜”都是拉祜语〔ra[,54]〕(宏)在各个时期不同意译的写法。在当今澜沧江西岸的拉祜语中,无论拉祜纳方言,还是拉祜西方言,“祜”都具有“众多、群体、更新换代、佛、勇猛”等含义,岂能说它是没有意义的语尾词呢?另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语言资料,“祜”根本没有“烤”和“烤肉发出的香味”的含义。在拉祜族古诗歌语词(口头古诗歌语)中,拉祜族还自称〔ra[,54]〕(比底依苏拉祜/拉祜雅/拉祜者)“拉祜”、“拉祜雅”、“拉祜者”都是“拉祜人(族)”的意思。“比底依苏”语义不明,待考。总之,要对“拉祜”一词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还有待于包括语言在内的新资料的发掘和考证,在此之前,不该妄对“拉祜”一词进行乱译乱释,这对学术的探讨和交流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10.关于“阿巴孤”〔ra[,5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一书中提到“阿巴孤”,说它是“佛教组织”,实属1918年澜沧仙顶营拉祜族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人称“大青白八”,其义不明。同一出版社出版的《思茅拉祜族传统文化调查》一书载云:“李竹大人八死后人们肯定他在传播佛教方面的成绩,给他取了一个佛名叫‘阿巴孤’,拉祜语意思为光辉的太阳。”这是个很罕见的解释。笔者自幼起曾多次听说过有关“阿巴孤”的种种传说,多年来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并数次向前辈询问过有关“阿巴孤”的轶事,但从未听人讲过“阿巴孤是光辉的太阳”,人们都说他是今南段村龙竹棚佛的佛祖。此人传说有二:一说他是阿不路(南段佛祖)最小的弟弟;一说他是阿不路的小儿子。但有个传说是真实的,“阿巴孤”与南段佛的传人岩当(人称李管头、李管事、阿当哈章,即哈章爷爷,因长期担任“哈章摆勐”而名)是深交〔10〕。据说“阿巴孤”仙逝前7天还邀岩当前往龙竹棚商议佛事, 并留遗嘱给岩当,希望岩当继承和发扬南段佛。还留遗嘱给家人,有朝一日他仙逝,希望李管头主持他的葬礼。岩当主持了“阿巴孤”的葬礼,并将他安葬于今龙竹棚寨后山,还陪葬了一面“仙铓 ”(阿巴孤生前使用过的铓),此铓后被人盗走,今收藏于某寨。拉祜西人将龙竹棚寨后山称作“阿巴孤独科”,意为“阿巴孤坟山”,其后代分布于今南段、洛勐和缅甸等地。据当地佛爷和老人讲,“阿巴孤”是“仙人”或“仙人转世”者之名,其意为“我佛圣祖”,而非“光辉的太阳”,也不是死后人们才给他取的佛名。〔11〕
11.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的《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中把“卡些”〔ra[,54]〕解释为“族长”、“寨头人”、“公众之主”、“村寨首领”、“管理本寨事务的头人”、“管全寨事的人”、“村寨头人”〔12〕。其实,据同书记载,“卡些”具有大小之分,管若干村寨的人叫“卡些路(隆)”〔ra[,54]〕,意为“地方长官”,只管一个村寨的叫“卡些”,意为“寨主”,本寨所有各类事务负责人叫“卡些卡列”〔ra[,54]〕。迄今为止,一些拉祜族地区仍保留着“卡些”的称谓和“卡些卡列”制度〔13〕。有些著述说“卡些卡列”是正副头人,即“卡些”为正,“卡列”为副〔14〕。据今澜沧县南段一带“卡些”后代和现任“卡些”们的解释:“卡些卡列”非正副头人(寨主),而是对所有村寨各类负责人的泛称。“卡些”可以单独称呼,如某寨“卡些”,某某“卡些”,但“卡列”就没有这种称谓。他们认为:每个村寨必须有个寨心,因此栽立寨桩;每个村寨必须有个主人,因此选个人当寨主。每个村寨有四道寨门,村寨四方有4个“卡些卡列”, 又称“阿朵阿戛”〔ra[,54]〕。这4个“卡些卡列”即“卡些”、“召八”〔ra[,54]〕、 “佛协帕”〔ra[,54]〕(又称“佛爷”,与人们所理解的佛爷有别,他只管理佛寺、香蜡等)、“章利”〔ra[,54]〕,即“铁匠”。他们由群众选举产生,任期视本人的能力和品德而定。“卡些卡列”成员的分工不同。“卡些”只管本寨行政事务(旧时也有一身兼几职的,如上文中提及的李管头,既是卡些,又是佛教传人)。“召八”只管寨神;“佛协帕”只管理佛寺;“章利”只管生产工具的制作和修理。因此,他们分别又是村寨、寨神、佛寺、工具神的象征。在任“卡些卡列”或曾任过“卡些卡列”的名人,在举行一年一度的拉祜西“扩”即春节之际,全寨人最先向他们拜年,他们也向全寨人拴白线以示祝福〔15〕。最后还要加上一笔,拉祜族的“卡些卡列”制度虽历尽沧桑,而且有些拉祜族地区早已消失,但在上述拉祜族地区却保留了下来,而且至今仍发挥着它的作用。比如在处理边民之间的民事纠纷、相互援助以及预防流行病等方面,都由双方“卡些卡列”共同协商解决,当地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只起因势利导的作用,不便直接出面干涉边民之间的民事纠纷等。“卡些卡列”还密切配合当地有关军政职能部门,组织群众建设家园,教育群众遵纪守法,协调群众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的种种关系。因此,“卡些卡列”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姿态出现于当今某些拉祜族社会,它对于促进边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增进边民之间的友谊,巩固国防,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当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
近年国内拉祜族研究中出现的翻译释义错误不止上述诸例,之所以出现类似上述错误,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们对拉祜语缺乏认识,或缺乏田野调查所必备的语言记录符号国际音标,使书写无法统一规范,甚至用欧洲语言或汉语拼音读音方法对拉祜语进行种种臆译致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拉祜族研究成果的质量,要么离题,要么面目全非。此外,著书立说者在引用他人资料时,没有对它进行认真辨析,做去伪存真的工作,而是全盘照搬,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甚至在此基础上作想当然地推测虚构,甚而杜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研究中的遗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正象不具备古汉语知识就无法阅读和研究《诗经》以及先秦以来的一系列华夏古代文化遗产一样,不具备一定的拉祜语基础,是无法深入研究丰富多彩的拉祜族历史文化的。其他民族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也应如此。
〔后记〕:笔者长期以来曾在已故语言学教授、拉祜语专家、《云南拉祜文方案》(试行)的设计者常竑恩先生指导下从事拉祜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十余年来多次深入拉祜族地区作田野调查,用拉祜文和国际音标记录、整理了大量拉祜族民间故事、谚语、宗教(主要是原始宗教和拉祜化了的大乘佛教)、年节、人名、服饰、亲属称谓、婚姻家庭、民间禁忌等方面的资料,对拉祜文化作过一些探讨,这个工作仍在进行。在拉祜文化的研究过程中还查阅和引用了许多他人的调查资料,发现其中有些资料与拉祜语有出入,笔者一直希望能看到有关纠正这些错误的文章,但至今不仅没有看到,而且有些错误还不断出现于某些著述之中(例见前文),因此不揣才疏学浅,特写此文。笔者一贯认为,调查研究中难免出错,这属于正常现象。发现错误及时更正,以求共识,这应属于科学探讨的范畴。
注释:
〔1〕文中所有着重号皆为引者所加。
〔2〕据《思茅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拉祜族部分)记载:明末清初,南明永历帝的遗臣杨德渊等将大乘佛教传入拉祜族地区,在今澜沧境内建立了五个佛教活动中心,即南栅佛、蛮大佛、东主佛、委盼佛、广明佛,澜沧历史上称为“五佛地”,“五佛”之名由此而来。
〔3〕〔11〕〔13〕〔15〕据笔者1984、1985、1987、1990、 1995(3次)的实地调查与核实所得。有关“阿巴孤”的其它内容, 笔者拟另作专论。
〔4〕“尼”是拉祜语〔ra[,54]〕的音译,它是拉祜族对神灵的泛称。澜沧江西岸拉祜族尚未形成“鬼”与“神”的区别概念。
〔5〕参见陈启新《论拉祜族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 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二期。陈启新、杨鹤书《略论拉祜族母权制及其向父权制的过渡》,同上学报,1979年第1期。 杨鹤书《澜沧拉祜族的母系大家庭》,载《思想战线》1982年第4期。 《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范玉梅编著《中国民间节日》,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拉祜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扩扎”是拉祜语〔ra[,54]〕的音译, 它的含义及文化背景见掘文《拉祜西“扩”的调查及探析》,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调查研究》1955年第1期。
〔7〕参见《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杨毓骧《拉祜族奥者奥卡双系制家庭剖析》,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晓根《拉祜族“屋吉屋卡”制度探析》, 载同上学报,1994年第3期。
〔8〕参见《清实录》卷二有关云南史料汇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91页。《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41页。
〔9〕《思茅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32页。
〔10〕岩当即《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中略有记载的“娜朱岩当家”中的岩当。据今许多卡些(头人)、佛协帕(佛爷)讲,他是南段一带有名的大卡些(大头人)和南段佛的传人,生前曾长期担任“哈章摆勐”、大卡些并主持南段佛,集政教于一身,60年代去逝于南段,葬于南段前山。他对拉祜西人的影响很大,迄今为止,人们都承认自己信仰的佛教是“阿当哈章(岩当)时代的佛,所遵行的是阿当哈章制定的佛规寨规”。据说他是“阿巴孤”最赏识的拉祜族政教首领之一。
〔12〕见该书第4、28、51、73、80、139、149页。
〔14〕见《拉祜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5页。《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39页。 晓根《拉祜族“卡些卡列”制度的产生与变异》,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