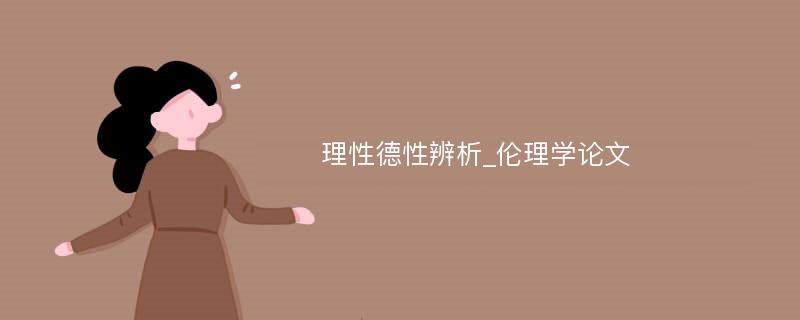
理智德性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性论文,理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5-0026-05
随着上个世纪伦理学的德性转向,德性论成为人们在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以外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德性转向一般将自己的理论源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智德性,一种是伦理德性,分别对应于灵魂的两个部分。然而,人们在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的时候,对于这两种德性的名称是否恰当,确切地说,理智德性这一称呼是否恰当却没有加以辨析。国内外的学者在谈及亚里士多德的这两种区分的时候,除了少数学者曾经提及伦理德性(moral virtue)的名称是否恰当以外①,基本没有对理智德性这一名称提出异议。而在笔者看来,伦理德性是否恰当只是与moral一词是否与道德律令同义有关。而在伦理学界,如Stephen Darwall一样使用moral这一概念却并非共识。与伦理德性这一名称是否恰当相比,更有问题的是理智德性这一名称。而这一点却没有论者提及。本文拟就用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来翻译、指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是否恰当做一探讨。
一、理智德性的含义
理智德性是亚里士多德用来指称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卓越的概念。这一德性在英文中通常被翻译为intellectual virtue。如W.D.Ross的译本、Harris Rackham的译本。而且这一翻译似乎在英语国家成为一通例。人们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时,都使用intellectual virtue这一名称。相应地,在国内,人们大都将这一德性翻译为理智德性。
Intellectual virtue的译法是否恰当,以及相应的,理智德性这一译法是否恰当,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得看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是什么,以及它包含哪些内容。
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二分,其意思是清楚的。德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含义是功能的卓越。根据灵魂的不同构成,不同的部分有相对应的不同的功能,因此,灵魂的不同的部分也就有不同的德性。“我们将灵魂的德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品格德性,一种是理智德性。……我们前面说过灵魂有两个部分——即把握规则或理性原则的部分和非理性的部分。”[1]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被称为伦理德性(moral virtue),它主要是勇敢、节制、正义等。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被称为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那么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理智德性又包含哪些呢?
在将灵魂分为理性的与非理性的两部分之后,亚里士多德继而对灵魂的理性部分进一步做了区分。“一是我们用来思考那些本原不变的事物,一种我们用来思考可变的事物;……让我们把一部分称为科学的,一部分称为计算的。”[1](14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理性的部分一分为二,以不变的事物为思考对象的是科学的②部分,以可变的事物为思考对象的是计算的部分。
具体而言,灵魂的理性部分获得真理的活动有五种:技艺(art)、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或prudence)、哲学智慧(philosophic wisdom)和直觉理性(intuitive reason)。在这五个部分之中,技艺是制造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制作出新的事物的。科学知识是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我们都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不变的,可变的事物无论是否存在,都在我们的观察之外,是我们不可知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对象是必然,因而是永恒的。”[1](147)而实践智慧与科学知识不同,它与技艺一样,是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的。“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被认为是对对他自己好和有利的东西深思熟虑的人,不是特殊的有利,诸如健康或强壮,而是对于整个的好生活的有利。……实践智慧不是科学知识或技艺,不是科学知识是因为能够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不是技艺是因为行动和制造是两类不同的事情。剩下的可能就是,(实践智慧)是一种做对人好或者坏的事情的真正的合乎理性的能力。”[1](149)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人们行动的德性,因此,实践智慧与科学知识不同的一个特征是它不仅仅与普遍的东西有关,还与特殊的、具体的东西有关,“实践智慧不仅仅思考普遍,它还必须认识特殊的东西;因为它与行动有关,行动总是与特殊的东西有关”[1](152)。科学知识虽然是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是从第一原理中推导出来的、需要证明的结论。因此,第一原理不是科学知识的对象。同样的,技艺、实践智慧和哲学智慧也不是以第一原理为对象的。剩下的只有直觉理性。“直觉理性把握第一原理。”[1](150)而智慧则是知识的完美形式。“智慧之士不仅知道从第一原理中推导出来的知识,还必须拥有关于第一原理的知识。因此智慧是直觉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结合。”[1](151)
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科学知识、智慧和直觉理性属于理性的科学的部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不变的事物为对象,形成的是普遍的知识。技艺与实践智慧属于理性的计算部分,它们以可变事物为对象,形成的知识与具体的、特殊的事物有关。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关于知识的划分中,将前一类知识称为episteme,包括物理学、数学和哲学等。将后一类知识中的关于制造的知识称为techne,关于行动的知识称为phronesis。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既包括了与理性的科学部分相对应的理论思考的德性,又包括了与理性的计算部分相对应的实践行动的德性。
二、理智主义的传奇
在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的理性部分的构成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灵魂的理性部分的两部分分别对应的是理论的知识与实践智慧。理论知识是与人的理智活动相关的,换言之,理论知识对应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intellect,它主要是关于永恒不变的东西的普遍知识。灵魂的计算部分除了与德性无关的techne之外,主要是关于行动的知识,即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也就是intelligence。而我们知道,intellect与intelligence两者之间有着种类差异(difference in kind),而不仅仅是程度的差异。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很明确的。“由于对象是不同的种类,所以灵魂中分别回应这两种对象的,也有着种类的差异(different in kind)。”[1](145-146)既然不变的永恒的对象与可变的对象是两类不同的对象,那么理性灵魂的科学部分与理性灵魂的计算的部分也必然有着种类的差异,是两类事物,不能混为一谈。对于intellect与intelligence两者之间存在着种类差异,赖尔也有着明确的论述。在赖尔看来,诸如聪明的、审慎的、有判断力的、有鉴赏力的等属于intelligence系列的词汇,关涉的是如何行动的能力,它们与是否有某类知识是属于两个系列的。赖尔举例说,一个愚蠢的棋手和聪明的棋手之间的区别,不是是否知道下棋的规则。即便聪明的棋手告诉他愚蠢的对手下棋的规则、战术的准则,他的对手接受并记下了所有这些规则,但是,他可能还是愚蠢的下棋,不会运用这些规则。赖尔在此强调的是intelligence与intellect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普遍知识与实践智慧之间的差别。掌握了普遍的知识,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将它们实际运用的智慧。实践智慧不仅仅关涉普遍知识、规则,还关涉具体的情境。实践智慧就是在具体的情境中智能地运用普遍知识、规则的能力。实际上,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清楚的认识。例如,人们经常会将一个读了很多书却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事的人称为书呆子。这个词很清楚地表明了,有没有知识和会不会做事情是断然有别的。
由此可以看出,分别与理性灵魂的科学部分相对应的intellect、与理性灵魂的计算部分相对应的intelligence有着种类的差异,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与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换言之,我们用来翻译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的intellectual virtue,它只能用来翻译理性灵魂的科学的部分的德性,它是思考不变永恒对象的理性灵魂的德性。事实上,有少数译者就是将这一部分直接翻译为intellect。它不包括理性灵魂中计算部分,即实践智慧那一部分。如果我们将整个的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翻译为intellectual virtue,那么,我们就是将一部分不属于intellect的内容包含在了intellect之中。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人的非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是伦理德性,它是与人的欲望、情感等相关的,是情感、欲望的合乎中道。它主要依靠习惯来养成。亚里士多德说人们通过做公正的事而成为公正的人,说的正是伦理德性是积习而成德的。而与人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践智慧,是人们如何行动的德性,一部分是理论思考,或曰沉思,是理智活动的德性。一方面,这两部分之间有着共同之处,即它们都与人的理性部分相关。这是它们区别于伦理德性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又有着根本差异,不能等同。从这一角度看,一个更为合适的做法是将与人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称为理性德性,而将理智德性仅仅指称与人的理智活动、理论思考相关的德性。这样就可以避免混淆理智与智能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使用理智德性来指称、翻译理性德性呢?究其原因,是与赖尔所说的理智主义的传奇密不可分的。赖尔认为近现代认识论的流行的教条是将智能归结为理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将注意力集中到发现真理或事实上,他们或者忽视做某事的方式和方法,或者试图将它还原为发现事实。他们假定智能等同于思考命题,并仅仅如此。”[2]在流行的认识论看来,智能的活动不具有独立的认识论地位,它们只是隐秘的理智活动。“做某事从来不是智能自身的活动,而是一种由隐秘的理论活动所引导和驾驭的过程。”[2]智能的活动看起来是特殊的才能,但是,它不过是隐藏在背后的理论活动而已。按照这一流行的教条,intellect自然是包括了intelligence在内的。如此一来,用intellectual virtue翻译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的德性,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那么,这一流行的教条是如何产生的呢?赖尔自己给出了答案。它源于柏拉图灵魂三分的学说。前面所描述的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三分的理论,来源于柏拉图的灵魂三分说。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三分法进一步细化。虽然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智慧,并强调了实践智慧与理论知识不同的特性,非常强调实践智慧的重要性。但是,也正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埋下了忽视实践智慧的种子。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论上同样认为理论知识是最高级、最典型的知识类型,处于金字塔的顶端。理论知识高于实践的活动,沉思的生活高于道德的、政治的生活。实践智慧则是第二位的。“亚里士多德对episteme和phronesis的关系所持的上述态度,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episteme 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实践哲学一直处于从属地位。”[3]近代科学革命以后,亚里士多德重视理论知识的倾向被进一步强化,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被狭隘化了,只有亚里士多德的episteme被看作是知识,原来被认识属于知识范围的phronesis和techne则都被排除在了知识的范围之外。换言之,近代以来的知识是能被言述的、普遍的命题性知识。而那些不能完全被言述的、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不能被称为知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近代认识论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理智上,智能也就被忽视或被认为可以还原为理智了。这一流行的教条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人们虽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对理智与智能的明确划分,却还是忽略了这种区分,用intellectual virtue一词来翻译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的德性,从而将实践智慧这一重要的德性消融在了理智活动之中。这一翻译在认识论的教条流行的年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认识论的实践转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理智与智能、能力之知(knowing how)和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之后,这一翻译的不恰当才为人们所认识到。
三、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传奇
如果将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翻译为intellectual virtue仅仅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算不上一个需要拿出来讨论的问题。但是,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理智主义的传奇的结果。而理智主义的传奇作为近现代认识论领域一个流行的教条,它影响到了哲学的其他领域,包括伦理学领域。
正如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所说的,现代道德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式。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向现代道德哲学的义务论的转变,其中贯穿着的就是理性主义的传统。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理论的创始者总是比较谨慎的,不会将一种倾向推向极致。而到了继承者那里,富有张力的一个整体的某一个方面才会被强调、突出,成为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性与非理性虽然地位有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德性的不可欠缺的部分。伦理德性离不开理性德性,理性德性也离不开伦理德性。而在理性主义逐渐成为统治原则后,人的激情、欲望不再被看作是与善相关的,而是成为了善的对立面,是人们需要予以压制、禁绝的对象。基督教的伦理学虽然鼓励对上帝的爱、对同胞的爱,但是,个人的欲望、激情却是邪恶的。到了康德那里,这一倾向表现得格外明显。道德必须与个人的激情、欲望彻底隔绝。虽然康德发明了一种似乎与人的情感有关的叫作敬畏的东西,但这种敬畏却不带有丝毫情感的色彩。对伦理学上的理性主义倾向,尼采予以了深刻而无情的鞭挞。“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4]
与伦理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并行不悖的是理智主义的倾向,或者说,理性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主要就是理智主义的倾向。理智主义在伦理学上的表现主要是忽视具体的事物,忽视实践智慧,将道德普遍化为规则、原则,最终,将道德简化为单纯的理论活动。如前所述,实践智慧是关涉如何行动的,换言之,它总是与具体的事件、情境相关的,而不仅仅是关注普遍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整个学说本来就与形而上学、物理学不一样,是关于可变的人的行动的知识,因此,这一学科也就与普遍的理论知识不一样,带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我们必须同意,对整个问题的叙述只能是纲要性的,而不是精确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我们所要求的叙述必须与研究题材相对应。而实践与‘什么对我们是好的’这类问题就如同健康问题一样,并不包含什么是确定不变的东西。而且,如果总的叙述是这样,具体行为就更不确定了。因为具体行为并不为任何科学与专业传统所统摄,行为主体只能因时因地制宜,就如在医疗与航海上一样。”[1](34-35)
这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纲要性的知识体系,本身就不能和物理学等学科一样,具有它们所具有的精确性、普遍性。而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具体的事件、情境不再构成伦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伦理学所关注的只是可以普遍化的规则。由此,伦理学摇身一变,成为了普遍化的规则、原则的体系。“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一条法则如果要在道德上生效,亦即作为一种责任的根据生效,它就必须具有绝对的必然性;‘你不应当说谎’这条诫命并不仅仅对人有效,其他理性存在者就不必放在心上,其余一切真正的道德法则亦复如是了;因此,责任的根据在这里必须不是在人的本性或者在人被置于其中的世界里面的种种状态中去寻找,而是必须先天地仅仅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而且其他任何建立在纯然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规范,甚至一种在某个方面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只要它在极小的部分上、也许仅仅在一种动因上依据经验性的根据,就虽然可以叫做一种实践的规则,却不可能叫做一种道德的法则。”[5]对普遍性、无条件性的偏好,使得康德将他的道德规则抽象成了没有任何内容的纯粹形式,因为,一旦有了内容,这一规则也就与经验性的东西有了关系,普遍性也会随之消失。
在理智主义的影响下,伦理学成了纯粹的理论活动。伦理学家思考伦理问题,构建伦理体系。学习者则通过书本学习伦理学体系,按照规则、原则行事。德性,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者被理解为理智德性。欧克肖特将被理智主义化的道德称为“反思性道德”。“在这种形式的道德生活中,活动不是由习惯所决定,而是由对道德准则的反思性应用所决定。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对道德理想的自觉追求,一是对道德规则的反思性遵守。”[6]欧克肖特认为这种道德的首要任务是用语言表达道德渴望,将它们表述为规则或者抽象的理想体系。第二个任务是能对这一抽象的理想体系进行辩护。最后是将这一规则或抽象的理想体系转化为行动。从欧克肖特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说的道德模式正是被理智主义化了的道德,主要表现为反思性的理论活动。
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的一个后果是割裂知行之间的联系。割裂这一联系的方式正是将实践智慧理智化。一旦失去了实践智慧将普遍的事物与特殊的事物连接起来的作用,被抽象为普遍规则、原则的道德也就失去了和行动的关联。
随着伦理学的这种演变,道德教育也变成了纯粹知识的灌输。传统的师徒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教育。教师以课本上的知识为教学内容,运用各种教学手段试图让学生将有关道德的概念、原理、原则以及具体的规范记住,最后以考试的方式来检验学生掌握道德知识的多少。“学校努力将一定数量的‘文化财产’传授给学生。然后,在学业结束时给学生出具一张书面证明,证明他占有了文化财产中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学校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都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复述作者的主要思想。学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沙、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可是,除了他所占有的这些知识之外,他什么也没学到。”[7]
从这个角度来看,肇始于上个世纪的伦理学的德性转向,可以被看作是对理智主义的传奇的自觉反动。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伦理学,其发展过程正是将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有着欲望、激情与理性的完整的具体的人逐渐抽离欲望、激情以及实践智慧而成为纯粹的理智活动的过程,用赖尔的话来说,就像一只活生生的鸟,现在被做成了标本。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性转向批评现代道德哲学只关注行动、而忽视了行动者。德性转向的这一批判可以说是切中要害,在古希腊,道德是关于如何过一种好的生活的,现在的道德却变得与人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完全偏离了伦理学的主题。德性的转向,这一对理智主义的反动,无疑对于恢复伦理学的实践本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伦理德性的名称来源于英文翻译moral virtue。W.D.Ross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将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翻译为moral virtue,Harris Rackham的译本也是如此。也有部分译文译为ethical virtue。然而,Stephen Darwall在其主编的Virtue Ethics一书的介绍中,却说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个非伦理德性伦理学(nonmoral virtue ethics)的例子。在他看来:“虽然翻译者经常使用‘moral virtue’来翻译与选择相关的品格的卓越,亚里士多德没有将它们与道德律(moral law)以及类似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参见Virtue Ethics,edited by Stephen Darwall,Blackwell Publishing,2003)
②这里的科学这一译法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我们所讲的科学,通常是指近代科学革命以后所兴起的自然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