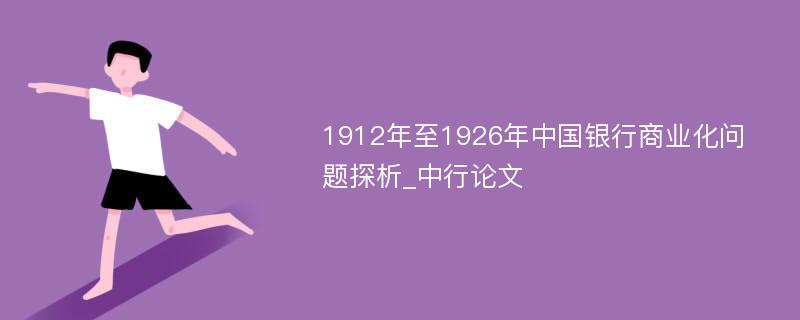
1912-1926年中国银行商业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年中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4)02-0054-08
从金融发展史上来看,银行商业化就是银行剥离其中央银行职能和政府政策性业务的过程,是摆脱政府直接经营和干预,走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之路的过程。北洋政府时期,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华资银行——中国银行,就曾为其实现商业化经营战略,在其股份制度结构安排和业务经营方针调整等方面进行过尝试和努力。
一、中国银行的成立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地的大清银行或被查封或停业,上海分行因在租界和库存充足仍能维持,原大清银行监督叶葵初、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与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人在上海组织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并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原大清银行副监督)取得联系,于1912年1月24日呈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求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其原有之官股五百万两,即行消灭,备抵此次战事地点各行所受损失及一切滥帐”;“股东等原有之大清银行股份五百万两,仍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另再加招商股五百万两”;中国银行“专招商股”,开办时可由公款协助,“俟股份招齐,即行发还”[1](P203-204)。这是一个由官股单方面承担损失,将该行改为商办的计划。财政总长陈锦涛批复“着即准行”,并在呈孙中山大总统一文中指出:以大清银行组织中国银行,一可使不费手费,便可建完全巩固之中央银行;二是承认原有商股,可保其信用,以利将来[2]。呈文经孙中山批准,财政部委任吴鼎昌、薛仙舟为正副监督,中国银行于1912年1月28日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国银行的成立,仅仅是中国银行整个建制的前奏,它既没有总行分行之别,也无则例章程可循;既未得到财政拨款充股,也未招收商股、发行股票。它的作用不过是利用原大清银行房产及商股商存,吸收公私存款,推广钞票发行,为政府销售军用公债和垫款借款,资助十分贫乏的财政。
1912年4月,南北统一,政府所在地北迁,即令在北京设中国银行筹备处。当时,熊希令任财政总长,他派吴鼎昌为筹备主任筹备开办事宜。另设大清银行清理处,清查资产负债。1912年6月,吴鼎昌与财政部会商,将大清银行官股取消,用于补偿各地分行因战争损失所致虚亏;原大清银行商股500万两连同商存676万两由中国银行换给存单,年息五厘,商股分4年摊还,商欠3年内清还,此项垫付之款,再由政府陆续拨还。7月,财政部拨到第一批官股,计银50万两。8月1日,北京中国银行正式开业,号称总行(初时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与分行无具体划分,迟至1914年9月,北京设总管理处,北京总行与北京分行才正式分开)。自北京中国银行设立以后,上海中国银行定为分行,中国银行的重心也就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
不过,这次成立的中国银行,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即已不同于1912年6月吴鼎昌主持草拟的中行则例所规定的性质。按照吴鼎昌拟订的中国银行则例草案规定,股本总额为3000万元,不论政府和私人均可认购,财政部先垫股四分之一,才正式开业。而此时的中国银行,由于原大清银行的500万两商股已改作存款,已经不存在商股了。同年9月,周学熙任财政总长,他一上台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整理财政的计划,在金融方面,他要求建立“国家银行系统”,“筹办国家银行事务所”,拟将中国银行收归国有。这与时任中国银行监督的吴鼎昌的思路相左,于是,吴鼎昌乃具文呈大总统,力陈“中国银行归为国有,流弊滋多,折衷至当,宜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定为资本3000万元,无论政府、人民均可购买”,并请辞监督之职[3](P284)。
吴鼎昌辞职后,北洋政府派孙多森主持行务。孙多森到任后,重订中国银行则例。1912年12月21日,财政部将中国银行则例草案呈交国务院,陈述拟订中行则例其大旨有三端:第一,创办中行,有主张国有者,但流弊滋多,危险殊甚,根据银行原则和各国成例,中行则例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为最宜;第二,军兴以来,金融紧迫,国民无企业之心,中行初创,若贸然招股,应者必无,既损国家信用,又延误成立日期,为早日开办,中行则例不能不规定由政府先垫股本,并拨出三分之一以上即行开办;第三,新创之中央银行,一切都须按照完全中央银行的原则办理,中行则例不能不采用完全中央银行制度[4]。1913年1月14日,大总统将则例提交参议院。后因参议院闭会,延至4月7日参议院在各方面的敦促下议决通过,15日,《中国银行则例》正式公布实施,即所谓民二则例。则例共三十条,基本内容有:确定中行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条),股份总额规定为6000万银元,计分60万股,每股100元,政府先行认垫30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由政府先缴所认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即开始营业;招募商股(第三条);公司的总裁、副总裁均由政府任命;中行享受种种特权,发行兑换券(第十二条);买卖金银及各国货币(第九条);代国家发行国币(第十四条)等等[5]。民二则例基本上接受了吴鼎昌的建议,采取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中国银行则例的颁布,确定了中国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法定地位,标志着中国银行经过一番难产终于正式诞生了。
二、修改则例,添招商股,商股逐渐占据绝对优势
按中行则例的规定,政府应先垫款1000万元,即行开业。但是,由于北洋政府财政窘迫,事实上直到1915年5月中行只有财政部陆续拨下的官股约300万元,包括1912年7月为开办京行财政部拨到的第一批官股计银50万元和1913年4月拨到的第二批现款243.0587万元[6],并无商股。这一数额仅及则例规定股本总额6000万元的5%,也仅及则例要求政府先垫股款1000万元的30%。有的书上说中行1914年所收官股股本为1000万元,这里是把财政部拨给的无市价元年六厘公债1000万元,作价700余万元包括进去了,与前面提到的300万元相加即得1000万元,1917年财政部将这部分公债全部撤走。1915年上半年,财政部又以大清银行资产抵交股本128.1万元。在这种股本有限的情况下,中行之所以能够支撑门面并使其业务获得迅速扩展,主要靠的是以代理金库为主的各种特权。至于中国银行怎样利用特权发展业务,下文将作进一步研究,在此不赘。
1915年5月,参议院对中国银行的官办商办问题曾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中,主张商办者占了上风。他们提出,各国中央银行,除苏俄、瑞典外均为商办;普法战争中,法兰西银行因系商办未遭敌抄没,且能为政府偿清赔款。是年秋,在总裁李士伟的主持下,中行开始为招商股而修改则例,并制订招募商股章程,拟定先招商股500万元。在财政无从拨款的情况下,中行行务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唯有募集商股以增大股本。修改后的则例经参议院议决通过,9月13日,由财政部公布施行。这次修改则例的主要内容有:(1)原例第十六条规定“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非有五十股以上之股东,不得充任董事监事”。新则例将五十股改为一百股。(2)原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总裁遇有董事监事全体,或股东总会会员五十人以上并占有股份金额百分之一以上者,因重要事件,请求会议,可召集临时股东总会”。新则例将百分之一改为百分之十。(3)原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员之股票权每十股有投一票之权,百股以上每五十股递增一权”。新则例改为百股以上三十股递增一权。(4)原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本则例关于股东之规定,自招满一万股起发生效力”[7]。新则例改为自招满十万股发生效力。这次则例的修改虽然削弱了一般商股的权力,但是却扩大了大商股的权力,能够起到刺激股东大量购股的作用,同时,这次则例的修改也为添招商股开了新风。这一年,从9月份招募商股到年底共招收商股231.25万元。这是中行自建立以来,股本中第一次加入商股。从此,中国银行股本在客观上构成了商股与官股的同时并存与对立。1916年,中行又增招商股19.73万元。这样,到1916年底,从中国银行股本的数量上看,若把财政部拨给的1000万元公债作价700余万元包括进去的话,已有1379.8万元,其中官股1128.1万元,占31.80%;商股250.98万元,占18.20%[1](P355)。如果不包括那1000万元公债的话,那么中国银行股本的数量为625.31万元,其中商股占37.91%。
1917年,冯国璋任大总统,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梁启超为整顿财政,启用张嘉璈为中国银行的副总裁(总裁为政客王克敏所据)。张嘉璈曾留学日本攻读银行学,原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颇有见识,1916年毅然抗拒北洋政府停兑纸币的命令,使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信誉大增[8]。张嘉璈任中行副总裁后,邀请其业师掘江归一教授来华商讨中行组织经营等问题。1917年11月5日,他提出了修改中行则例的原则和草案。在梁启超的支持下,财政部速将修正案呈交大总统,由于当时新国会尚未成立,因此修改后的中行则例,便直接由大总统在11月21日以第25号教令公布施行,即所谓民六则例。与1915年9月第一次修改后的则例比较,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1)民六则例采取不严格划定官商股、政府股份可随时售与人民的原则,鉴于原例第二条规定资本过大,不合实际,改为“先招一千万元,计十万股,政府得酌量认购,以资提倡”。(2)删除原例第三条“中国银行由政府先交所认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开始营业”等语。(3)对于原定商股招满10万股才能适用股东权利之条款,提出“凡出资者不论官商都为股东”的论点,公司招满10万股即应召开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4)原例第十六条规定总裁、副总裁定由政府简任。新则例予以严格限制,定为“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简任,非有一万股以上之股东不得充任董事及监事”。(5)原例第十七条规定“总裁、副总裁以五年为一任,董事以四年,监事以三年为一任”,现改为“总裁、副总裁任期以董事之任期为限,董事以四年为一任,监事以三年为一任”[9]。
这次中行则例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本总额6000万元,先招1000万元。这实际上确认了不论官股商股,只要招满1000万元便可成立股东总会。二是总裁、副总裁从董事中简任,任期四年。这样,尽管政府仍有最后决定任命权,但是如果没有商股大多数股东的同意,董事就不容易选出,从而也就改变了中行总裁随财政总长的进退而更换,而总裁变更大小行员又随之变更的局面,总裁、副总裁受大商股的间接控制。
民六则例公布后,财政部补交现金71.93万元,凑足官股500万元,并将原来作价充股的元年公债全部撤出。同时,续招商股,原拟招商股195.67万元,凑足商股500万元。结果招收363.65万元,超过227.38万元,总计官商股为1227.98万元。商股超过官股,中国银行股份结构第一次发生明显变化,官股约占40%,商股约占60%,资本组织渐臻完善。根据民六则例,1918年2月,中国银行第一次召开了股东总会,并选举出第一届董事9人。27日,在第一次董事会上,会议主席王克敏宣布:“本主席于数年中所希望之董事会已于今成立,实可欣幸,以后关于一切行务,均赖董事会整理。”[10]同时,政府从董事中简任王克敏、张嘉璈为正副总裁。中行股东总会的召开和董事会的产生,使股东有了保障权益的机构,取得了与政府合法交涉的地位,标志着中国银行自民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由官掌大权的名义股份有限公司向实际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化。
1918年新国会成立后,参众两院被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所控制。安福系早就对中行垂涎三尺,此次便借掌握立法权之便,妄图将中行据为己有,使其成为募集从事党派活动经费的工具,于是,以新则例不是正式通过的法案而是以“命令变更法令”为由,指使参议院于1919年4月和6月两次通过恢复中行民二则例、增加资本的议案。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地中国银行纷纷组织商股股东联合会强烈反对,指出这是“北京安福派把持政权,蓄意搜夺中行”,意在“自由任命总裁,滥发军费,再蹈五年之覆辙”,“攫取中行实权,又得垄断入股之利,且举国家银行为彼党经费来源”。对此,各省商会、军政府以及舆论界也站在商股股东一边起而指责,甚至引起外国银行团、领事团的干预和反对。7月,中行在上海召开商股股东联合会,决议在南北未统一前不议修改则例,不增加股本,并发表宣言[11]。安福系日感处境孤立,不敢再议。这场发生在中国银行与安福系之间的是维护中行新则例还是恢复旧则例的斗争,与其说是中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与把持朝政的安福系之间争夺谁掌握中行大权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银行在面临是相对独立于政府还是完全受制于政府发展道路之时的路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成为政府的提款机器还是走自主经营的企业发展道路之时的路径抉择问题。斗争的胜利与相对独立于政府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银行的商业化发展。
1921年4月下旬,中行股东会对中行章程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增加股本为3000万元,即续招股本1772.02万元,先招772.02万元,凑足2000万元。同时,对股东投票权除原则例规定外,又规定:每一股东之权数不得超过1500权,每一股东以一票为限,出席股东之代理投票权不得超过十股,董监事以得三分之二权数者,始能当选。这些修改旨在进一步扩招商股和完善股东会的选举制度。8月1日,中国银行登报招股,副总裁张嘉璈特赴上海劝募,截至12月底共招股款599.88万元。1922年,官股280万元过户为商股;又续招商股148.15万元,中国银行股本总额达到了1976.01万元,其中:官股220万元,占总股本的11.13%;商股1756.01万元,占总股本的88.87%。
在商股逐渐增加的同时,官股却在不断减少。从1919年起财政部因库款支绌便将中行股票作为租款抵押,在到期不能按约偿还时,不得不将股票作价出售,让中行办理官股过户手续,将官股股票换成普通股票。上面曾提到过1922年280万元的官股过户为商股,1923年又有215万元的官股过户为商股。这样,到1923年底,中行原有的500万元官股,就只剩下5万元了。其中,在官股过户中又增添商股100元。到此时,中行的股本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商股占到了绝对的优势,为1971.02万元,占99.74%,中行在企业组织形式上基本摆脱了北洋政府控制,已转变成为几乎完全民营的股份有限公司制的商业银行了。
表1 1912-1926年中国银行资本结构变化表 单位:万元
年份资本总额官股 商股 商股所占%
1912 50.00 50.00 0.000.00
1913-1914293.06293.06 0.000.00
1915 652.31421.06231.25 36.98
1916 662.04421.06250.98 37.91
1917-1920
1227.98500.00727.98 59.28
19211827.86500.00
1327.86 72.65
19221976.01220.00
1756.01 88.87
1923-1926
1976.02 5.00
1971.02 99.74
三、中国银行在业务经营上,由绝对地服务于政府逐渐转向服务于工商业
前面曾提到中行在初创时期利用政府所给予的各种特权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些特权主要是代理金库、发行纸币和银元国币等等。民国之初,由于中央未设金库系统,各省金库代理机构紊乱,应解中央之款常常因故梗塞,而作为财政支柱的关盐两税又须存入外国银行,因此,财政部不得不建立金库制度,于是委托中国银行暂行代理现金出纳、保管等事项。财政部还拟订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赋予中行发行特权,规定凡完纳各省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股票及交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军饷、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等等一律通用中行兑换券,不得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情形。到1915年底,中行接收各地关税21处、盐税38处,接收了直隶、江苏、浙江、广东、黑龙江等15个省的金库[12],全年经收之款1.2亿多元,占全国税收的二分之一以上。随着中行接收各地金库,其分支行号也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起来,到1915年底,中行各地分支行号已达136处,遍及22个省[1](P23)。中行的钞券发行、存放款及汇款业务也扩大到了全国。中行的存款、放款和汇款业务在依赖政府并以政府为主要业务对象中发展起来,其所获取的纯益逐年迅速上升(参见表2)。在存款方面,起初,由于中行信用未固,富商大贾储蓄多存于外国银行,因此,中国银行所吸收的存款大部分来自政府机关以及代收的关盐税等税款。存款额从1912年的200万元增加到1915年的10600万元,到1920年时已增至19025万元。在放款方面,大部分是对财政部及政府机关垫款、对各省财政厅短期放款。放款额从1912年的200万元增加到1915年的8000余万元。1916年之后突破1亿元,为10200万元,1917年为13900万元,1918年为14300万元,1919年为18400万元,1920年为17843万元,这其中对政府的放款分别占36.91%,65.74%,79.09%,63.76%,57.93%。然而,至于对工商业的放款,数量却很少,大都是购入钱庄经手的商业远期票据。在汇款方面,由于中行分支机构遍设各地,此项业务发展更为迅速,汇款额从1912年的400万元增加到1915年的17600万元,增长44倍,到1920年时已突破2亿元大关,达24124万元。在所获纯益方面,从1912年的13万元迅速上升到1915年的353万元,盈余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最盛,年达二三百万元,1920年高达421万元。而中行直到1915年9月,实际资本(不包括公债折股)才仅区区420余万元,1920年股本也只有1228万元。资本盈利率一般在30%以上,甚至在1914年达到47%,1915年达到54%。当然这也与下文将要谈到的中国银行热衷于经营政府债券密切相关。
表2 1912-1926年中国银行的营业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份存款放款汇款纯益纸币发行额持有公债额对财政部垫对政府全部公债和政府垫款
款 垫款占资本和存款的%
1912 200 200 400 13
1913180017001000 30
1914580050005500 137
1915
106008800
16000 353
1916
11400
10200
14200 294
1917
14800
13900
17600 207
1918
15100
14300
18300 37952l7 3874
4772 657164.0
1919
18100
18400
18700 3466168 3819
4878 685655.2
1920
19025
17843
24124 4216688 4845
4098 628954.9
1921
17620
17230
23565 556249 4876
4180 609956.4
1922
18698
18373136 77796010 3922
5995 57.8
1923
17805
18010151 80994706 5749
7225 62.2
1924
19994
20181128 89984784 6293
7938 57.9
1925
25927
26653135127095892 5545
7626 48.4
1926
32848
31134146137426824 5676
8428 43.8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41.
表3 1913-1926年中国银行对政府放款一览表 单位:万元
年份放款总额其中对政府占放款%持有公债面公债面值占备注
放款
值 放款%
1913 1750 144此三年对政府放款,不包括
1914 4997 406放款给政府各机关,公指数
1915 8695 654 款给财政部
1916 10189 376136.91
1917 13950 917065.74
1918 143431134479.09 3874 27.01
1919 184051173563.76 3819 20.75
1920 178431033757.93 4845 27.15
1921 172301027959.66 4876 28.30
1922 18373 991853.98 6010 32.71
1923 180091297372.04 4706 26.13
1924 201801423070.52 4784 23.71
1925 266531317149.42 5892 22.11
1926 311341410445.30 6824 21.92
资料来源:邓先宏.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A].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8,304.
注:表中1921年以后的对政府放款额,多数属于积欠性质。表3中的对政府放款包含表2中的对政府全部垫款,对政府垫款属于一种短期的放款。表中放款总额一栏与表2中放款数额不一致,这是由于统计误差造成的,它从总体上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
由于中国银行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政府所给予的各种特权,因此,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政府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中行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不单纯是“赏赐的获利机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更多的是拖累,也就是说,中行在享受政府所给予的各种权利时,也要为此付出较大的“成本”,不仅总裁、副总裁由政府简任,而且还要充当政府的财政工具,或是直接借款、垫款给政府,或是替政府经理公债,致使库存现金准备不是,出现1916年的停兑风潮以及此后长达5年之久的京钞票价低迷和难以恢复兑现问题,中行信用遭到极大损害。中行初创时期没有股东会和董事会,正副总裁全权在握,对政府负责。当时各派军阀和官僚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一旦取得对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就会向中国银行伸手,任命亲信或至少可以接受之人担任中行总裁、副总裁。因此,中行总裁、副总裁就随着总理、财长的更换而频频更换。据统计,从1912年到1916年底短短5年时间,中行正副总裁一级的行政首脑更换了19人次[13]。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为窘迫,军阀政府不得不靠举债度日。从1912年至1926年6月止,北洋政府正式发行的债券达27种,发行额达61206.2708万元[14]。中行建立之初,投资公债受能力限制,数额不大。1914年,投资280万元于三年公债。1915年,投资266万元于四年公债,并收到财政部拨交的面值1000万元的元年六厘公债充作股本。中行所持有的公债,从绝对量上看,1918年至1926年间其公债数量呈上升趋势。1918年为3874万元,而到1926年则达6824万元,增长了76%。从相对量上看,中行持有的公债约占发行总额的12%左右,居全国各银行之首。从其持有的公债面值占所放款的比例看,它在1922年以前除1919年为20.75%外,都在27%以上。不仅如此,中国银行在购置北洋政府公债的各银行中也具有突出的地位。据统计,1921年底中行等47家银行购置有价证券5607余万元(公债票占大部分),而仅中行一家就购置于2288余万元,约占总额的40%,相当于该年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22%[3](P207)。中国银行在1922年以前热衷于公债的经营,除了它作为国家银行有责任外,主要是经营公债可获厚利,一般来说,经营公债实际年利可达一分五厘至三四分之厚[15]。这是因为北洋政府所发的债券利率较高,在其所发行的27种债券中利率都在6%以上,而且代替政府销售公债还有较大的折扣,其折扣一般在五六成之间。中国银行作为债券的主要经募人和销售人与直接投资者,不仅能获得销售中折扣和经手费,而且还能在偿还中按债券100%的面值收回投资与收取利息。
中国银行由于经理国库,所以政府在库款周转不灵或入不敷出时,就要求其垫款或借款。在1915年以前垫款约数百万元,1916年5月停兑风潮之后,政府需求大增,到7月底,垫款增至1520万元。至1917年底,更增至4540万元,致使银行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与此同时,京钞的票价低迷和恢复兑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从1917年7月至1921年2月,京钞市价长期徘徊在面值的50%-70%之间,甚至经常跌破50%,接近40%,而突破70%则极为少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对中行并没有罢手,仍然要求中行继续垫借款项,1918年5月初财政部向中行商借200万元,6月中旬仍要借130万元,7月又要求垫借现洋200万元。对此,中行董事会一再反对,并多次向北洋政府提出垫款应有限制的要求,副总裁张嘉璈认为垫款一事“亟应截止”。在中行的一再反对、社会舆论的指责和京钞价格日跌的情况之下,财政部感到中行的承受力已达极限,于是,在1918年9月,允诺不再令中国、交通两行垫款,但原欠难还,中行的垫款一直保持在4000余万元的水平,1924年以后,战争剧烈,又有增加。1918年起,中行又开始对地方政府财政厅垫款,其数常在2000万元以上,故对政府全部垫款达六七千万元水平,占中行放款总额的35%-40%。如以中行的资本额和存款额代表银行可运用的资金,测算政府公债和对政府放款所占的比重,从表2中可以看出政府占用的资金经常为50%-60%[11](P843)。如果将银行代替政府销售公债时的折扣考虑进来的话,折扣一般在五六成之间,那么政府所占用的中行资金还是能达40%-50%。
在经历了停兑风潮和京钞票价低迷难以恢复兑现的“洗礼”与目睹了北洋政府内部的争斗和混战之后,中行股东会和董事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政府财政结缘的银行前途的危险性,独立于政府和向资本主义工商业靠拢的决心愈来愈坚定,于是,在业务经营上,开始了由绝对地服务于政府向服务于工商业的转变,加强了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业务联系。1918-1921年是中国银行经营方向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期。1917年11月,民六则例以大总统令公布施行,使决定总裁、副总裁的实权由政府转到了大股东手里。1918年9月,在中行董事会和股东们的多次限制和反对下,终使财政部声明以后不再要中行垫款。1919年,中行在《中国银行民国十八年报告》中,深刻总结了前几年的教训,认为其“营业方针不能不及早变更,由政府方面转移于商业方面。类如纸币之发行,不以金库支出为主,而以购买或贴现商业期票为主;顾客之招徕,不趋重于官厅之存款,而注意于商民之往来”[16]。1921年4月,中行股东会为了恢复中行元气和筹集现款解决京钞遗留问题,对其章程进行了修改,以进一步扩招商股和完善股东会选举制度,8月登报招股,副总裁张嘉璈亲赴上海劝募。从1921年以后中国银行的营业情况也能看出,其向服务于工商业转变和商业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朗了。中行的公债和政府垫款占资本和存款的比重,已从1921年的56.4%、1922年的57.8%,下降到1925年的48.4%、1926年的43.8%(参见表2)。如果把中行购买公债时的折扣考虑进来的话,上述所列的比重数据应该缩小一些。中行对政府的放款占总放款额的比重。已从1921年的59.66%、1922年的53.98%,下降到1925年的49.42%、1926年的45.30%(参见表3)。对公债和政府垫款和放款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对工商业放款和贴现的增加,说明中行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业务联系逐渐增多。
同时,为了巩固银行基础,增强自身实力,维持信用,适应营业方针的转变,中行在其内部也进行了较大幅度地整顿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裁减人员,紧缩开支。中行将总管理处原有职员300人,裁减为120余人;降低总裁、副总裁薪金,停止行员待遇中的劳功俸,取消年资加俸、普通奖、特别奖等。实行这些措施后,总行开支由1921年的450万元,减为1922年的370万元、1923年的320万元,较1921年分别减少了17.78%、28.89%。(2)调整分支机构,将分行迁入商业区。鉴于设在各省省会所在地的各分行行务常被地方军阀官僚干扰,现金准备常被抽空,中行相继将一些在省会所在地为非商业中心的分行移入商业中心,并将非商业区的原分行缩减规模,改为支行。如山东分行由济南迁于青岛,四川分行由成都迁于重庆,哈尔滨则由分行改为支行等等。同时,裁并不能自负盈亏、营业清淡的分支行处。(3)设立区域行,集中发行准备。停兑风潮以后,各分行之间为谋求自保,彼此缺少联系。这种状况使得各行现款准备分散,不仅不易调节,而且容易被各地政府、军阀强借,损害发行信用。于是,中行根据各分行间地理与业务联系,采取了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几个通商大埠建立区域行,并将发行准备集中于区域行的办法,以统筹各行资金和便利行务向商业方面转化。(4)创立发行准备公开检查制度。早在1921年“津券挤兑风潮”之时,中行天津分行就曾为消除社会对津券兑现的疑虑,聘请著名英籍会计师司塔门,邀请政府商界和银行、钱业公会代表到行公开查核帐目,点验库存,证明银行资产负债实情,登报公告。此为中行公开检查之滥觞。这个成功的经验,后为上海等其他分行采用并加以发展,定期检查成为制度。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中行能够在遭受了1921年“信交风潮”和“津券挤兑风潮”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的金融市场上站住脚跟,并获得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中行走向独立发展铺平了道路。1926年6月,张嘉璈在上海设副总裁驻沪办事处,中行经营重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银行向商业银行方向的转化。
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中国银行随改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此后,中国银行迅速发展,不仅规模愈来愈大,业务兴盛,而且由于它在建设近代比银行中的努力,业已成为以经营管理著称的金融机构。
通过以上历史回顾与分析,我们对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的企业组织性质和经营方向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虽然中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规定中行为股份有限公司和官股商股各占一半等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发展过程并不与原来的设想和则例条文所规定的相一致。中行不仅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反而伴随着其股份结构和制度的变迁与经营方针的调整,在逐步地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和干扰,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演化为商业银行,并在服务对象上逐渐地转向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分阶段讲,就是:在前期(1912-1915年9月),中行股本是清一色的官股,也无股东会、董事会之类的组织机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任命,担当此任者未必是股东、董事,总裁、副总裁之职位成了官僚进身之级,故这一时期的所谓股份有限公司是不存在的,实质上是一个享有多种特权的官办国家银行。它凭借代理金库、发行纸币和银元国币等等特权,为北洋政府提供存款、放款和汇款等业务,并在依赖政府为主要业务对象中迅速发展起来。在中期(1916-1922年),随着北洋政府对中行控制的不断加强,中行的行务和信用受到了严重影响,中行也逐渐认识到同军阀政府结缘的严重危害性,于是,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控制和干预的斗争。中行通过进一步修改则例章程、扩招商股和调整经营方向,转变成为官商合股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形式不同,它具有保障股东权益的股东会、董事会等组织机构,总裁、副总裁是由政府从董事中简任,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来自官方的干扰,与洋务运动中官掌大权的官商合办企业商股权益难保的状况相比较大大进了一步。在后期(1923-1926年),随着官股逐渐减少到只占0.25%的比重,中行经营方向和业务方针也逐渐由绝对地服务于政府转变为服务于工商业,加强了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业务联系,中行变成了几乎完全民营的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上摆脱了北洋政府的干扰,从而实现了其商业化经营战略的转变,即基本上转变成为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了。
[收稿日期]2004-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