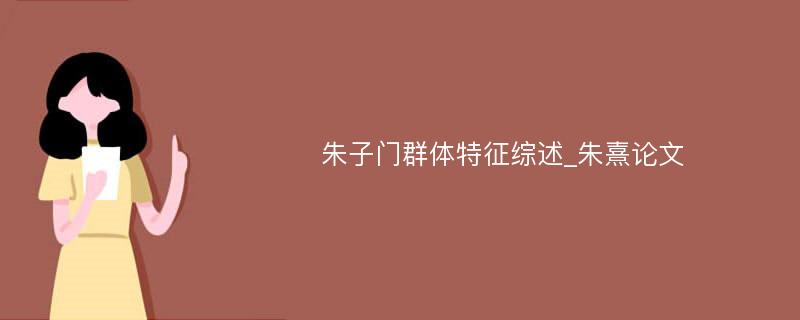
朱子门人群体特征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门人论文,群体论文,特征论文,朱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子门人是指求学于朱熹的亲传弟子。①最早关于朱子门人的记载散见于时人的著述和朱熹的文集当中。如朱熹的挚友、诗人陆游在为朱熹弟子方士繇撰写的《方士繇墓志铭》一文中说道:“朱公之徒数百千人”②,这虽然只是一个约数,但朱熹门人之众,于此可知。其后陆续有不少文献具体记录了朱子门人的姓名,如宋黎靖德编成的《朱子语类》、元代修的《宋史·道学传》、明人戴铣所著《朱子实纪》、明人宋端仪所著《考亭渊源录》、韩国李滉的《宋季元明理学通录》、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朱彝尊的《经义考》以及朱玉的《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及门姓氏》等,但所有这些考录在关于朱子门人的具体人数、所属地域等方面均存较大差异。进入现代学术研究阶段之后,主要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朱子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对于朱子门人系统全面的考证性研究也出现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有日本学者田中谦二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以及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的专著《朱子门人》。陈荣捷先生在辨析是否朱子门人的这一点上纠正了前人记载的众多错误,共考定朱子门人467位,为朱子门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进入新世纪之后,对朱子门人的考证有了新的进展。如方彦寿的《朱熹书院与门人考》,该书将朱子门人的研究与书院研究结合起来,重点考证了朱熹在其创建的四所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与考亭沧州精舍)中及门弟子276人,可以看作是陈著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又陆续有一些文章对方著和陈著进行补证。③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都是人物罗列的逐一考证,所要判定的主要问题为是否问学于朱熹,是否可以称之为朱子门人。对朱子门人的形成过程、组织特色、学术贡献等没有一个整体的考察,未从整体上对朱子门人进行某种划分类型、区别各自贡献的研究,对于朱子门人在朱子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完成、传播、传承过程等方面的学术贡献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学界对于朱子门人群体的描述往往比较笼统,对于朱子门人在整体上呈现出的一些群体特征很少关注。应该说,我们对这一南宋末年最重要的学术群体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④关于朱子门人群体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朱子学研究领域急需加强的重要课题。
笔者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并逐一参阅相关文献,最后考定留有姓名的朱子门人共计494人。⑤本文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这些朱子门人进行分类,通过这些分类揭示出朱子门人这一学术群体的整体特征,而了解这些特征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朱子门人相关研究的基础。
一、聚集过程分阶段。从绍兴十九年(1149)朱熹第一次回婺源开始,即有亲友子弟问学于朱熹,一直到朱熹庆元六年(1200)去世,五十余年的时间,朱熹授徒数百人。结合朱熹教育活动的展开、朱熹思想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扩大的阶段性特征来考察朱子门人群体集聚的全过程,大体上可以把朱子门人群体聚集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是早期门人,时间为从绍兴十九年(1149)到朱熹创立中和新说标志着理学思想真正成熟的乾道五年(1169)。朱熹重视讲学授徒,其从学弟子逐渐由少到多,问学内容从最早的请教做诗方法逐渐转向讨论儒学义理。由于此时段朱熹本人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此时弟子还不能算是严格朱子学派意义上的门人,但其中一些重要门人如蔡元定等对于朱熹思想的真正成熟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是中期门人,时间为从乾道六年(1170)到绍熙五年(1194)庆元党禁之前。乾道六年寒泉精舍的创建标志着朱子学派的真正创立,随后朱子学派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门人数量大大增加,来源区域也逐渐扩散到福建之外的地区,门人所涉阶层也更为广泛。在众多门人的参与下,朱子学的学问与义理体系逐渐建构起来并日渐丰富。
第三是晚期门人,时间为从绍熙六年(1195)直到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此时虽然朱子学被列为伪学,朱子门人群体产生了一定的分化,甚至出现变节者⑥,但依然有许多新的学子前来问学。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中期、晚期门人只是从该门人最早的从学时间来区分,这种区分旨在说明,一方面随着朱熹思想的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聚集在朱熹身边成为朱子门人,朱子学派日渐壮大,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门人在来源、问学内容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三期门人并非截然不同的三个群体,而是相互交叉的,如早期门人很可能在中期和晚期都问学于朱熹,同时也是中期门人或晚期门人。
二、问学机缘多样。从问学机缘来看,朱子门人拜师从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朱熹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辖区内的居民入室成为弟子。朱熹虽然在外仅任过几任地方官,但他每次都非常重视教育问题,整顿官学教育,修复和创建书院,开讲授徒。从同安到南康、再到漳州都吸收了大量学子来学。此为官学弟子。
第二、朱熹居家讲学时,也有不少弟子纷纷前来受学。在这方面,朱熹所创办的四所精舍、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就是典型,这四所常设性的讲学机构既是朱熹长年从事学术活动的主要地方,更是他接引各方学者授徒讲学的重要场所。这部分的弟子入学情况在方彦寿先生的《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中有专门考论。此多为朱熹居住地附近慕名而来的私学弟子。
第三、朱熹在各地游历时招收的学生。朱熹一生除了任官和居家之外,无论是回乡展墓,还是拜会学友,朱熹都喜好游历讲学,足迹所至涉及闽、浙、赣、湘、皖等地,他每到一地通常都会拜会当地学者,在当地书院讲学,因此便有不少弟子是在这些游历途中所招收。这些弟子接受朱熹的短期教导之后,或者追随朱熹一段时间,或者开始重视搜集和研读朱熹的著述,通过书信往来等形式继续向朱熹请教,从而成为朱子门人群体的一员。
此外,从弟子的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问学于朱熹,除了上面三种机缘之外,还有的是通过早期阅读程朱理学著述而认定朱熹为自己的导师而主动前往受教的,比如李方子、度正等人不惜长途跋涉,主动到朱熹的居所来拜师问学,也有由于其他学者的推荐而前来受教,这些推荐者通常是朱熹门人或是对朱熹学问非常佩服的同道,而他们与所推荐的弟子之间或是师友(如黄榦最初问学于刘清之,刘清之推荐其至朱熹处受教),或是父子兄弟(如蔡氏家族)。这就在朱子门人群体中造成了许多师生同学和父子兄弟同学的情形,这在朱子门人中不是个别现象。
三、地域分布广阔。虽然朱熹主要生活在福建,足迹所到之处也仅江西、湖南和浙江等地,但从朱子门人的籍贯可以看出朱子门人来自各地,他们或长期或短期的在朱熹处受教之后,大多回到各处继续学习,同时将朱子学说传播到各地。这一群体遍布当时南宋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一些籍贯在北方的弟子,其中以福建、江西、浙江籍门人较多,这些也是当时南宋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主要区域。这直观地反映出当时朱子学影响地域日益广泛。
据笔者统计,按籍贯来看,494位朱子门人具体的地域分布情况为:福建160人(此外4人一作福建,4人移居福建);江西86人(此外1人寓居江西);浙江73人(此外2人寓居浙江,2人迁居浙江);湖南26人;安徽14人;江苏7人(此外2人迁居江苏);四川6人;湖北5人;广东5人;河南4人;河北2人;山西1人;重庆1人;共390人有籍贯记载。有名而籍贯不可考者104人。⑦
四、社会阶层来源广泛。从朱子门人所涉及的社会阶层来看,朱子门人当中既有一般的知识分子,如地方乡绅、私塾先生,也有许多进士和各级官员,他们共同在当时南宋社会政治文化各个层次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主要介绍进士与官员的情况。
由于进士在当时基本能够代表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而朱熹门人中有多少进士,也便可以比较好地揭示朱熹学说在精英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以及朱熹学说与科举之间的相互促进兼容。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学朱熹以后所中进士,这说明朱熹学说对科举并不完全排斥,还有益于科举考试;二是中进士之后再从学于朱熹,这说明朱熹学说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强大说服力和吸引力。
科举考试在当时受到包括朱熹在内的许多学者批评,朱熹有不少弟子厌弃科举而专心读书求道,如吴楫、林用中、丁克、蔡渊、童伯羽、蔡念成、刘砥、朱飞卿、陈淳、曾兴宗等,但多数弟子并不绝对排斥科举,朱熹也并不反对自己的门人应举。在朱子门人群体中,进士及第者共计92名,多数是在朱熹生前中进士,共69人,而在朱熹之后为20人,不确定的3人。这在当时几大道学学派当中是非常突出的。据有的学者统计,张栻弟子中共有23名进士,吕祖谦弟子中有35名进士,而陆九渊弟子中有25名进士。⑧这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影响最为广泛,弟子数量最多,相对中进士的人数也就更多。
进士及第是南宋任官的重要途径,加上其他如荫补等任官制度⑨,朱子门人当中担任官职的数量又大于进士数量,共计为147人。这些担任地方和中央官职的门人,形成了当时政治领域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对于改变南宋中晚年政治社会面貌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他们在从政之余,多热衷于朱子学说的推广与宣传,对于提升朱子学说在政治领域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重视讲学著述。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著述,留下的文字数千万计。在讲学教育方面,朱子门人当中至少有25人担任过各地州县学教授乃至太学博士等职,还有其他一些门人为官时曾主管和整顿官学教育,此外朱子门人创建和讲学的书院也至少有34所。⑩这些门人在学校和书院教育过程中积极推行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传播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朱子学义理,他们的这些努力极大地扩大了朱子学在当时教育领域的影响,为朱子学在后来教育以及科举领域的制度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著述方面,也有不少朱子门人学术造诣较高,并热衷于著书立说。《朱子实纪》曾记载朱子门人中有著述的为58人,而据本人考证为91人。这些著述大多已经散佚,除了曾记录朱子语录之外,现存著述的至少有27人。现存的部分是我们研究朱子门人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这些著述多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多是对四书、五经的注疏,学习理学的心得体会,师生朋友的往来书信以及各类诗文、史学著作等,与朱熹本人的著述一起构成了朱子学派的基本文献资料。
六、兼学现象普遍。在大部分时间里,当时的学术政治环境是相对宽松的。道学各个流派纷纷出现并迅速传播,因此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一个学生曾向多个学派学习的兼学现象。如曾向陆九渊与朱熹问过学的就至少有35人:万人杰、王遇、包扬、包约、包逊、石宗昭、石斗文、吕祖俭、刘尧夫、刘定夫、刘孟容、朱季绎、孙应时、杨楫、杨方、李修己、李伯诚、周伯熊、周良、赵彦肃、赵师雍、赵师蒧、项安世(陈荣捷《朱子门人》中以为项世安)、俞延椿、胡大时、郭逍遥、诸葛千能、曹建、符叙、符初、傅梦泉、舒璘、曾极、曾祖道、潘友文。(11)此外,朱子门人当中有不少人还曾向其他学者如张栻、吕祖谦等问学。
考察朱子门人的兼学现象,可以较客观地揭示朱子门人的知识背景并非仅仅只是朱熹的学问,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从学朱熹之前还曾跟随当时的其他学者学习,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方面因后来问学朱熹而逐渐扬弃,另一方面也为朱子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冲击,这种冲击既表现在朱熹本人思想的成熟方面,也表现在朱熹之后朱子学的继续发展方面。此外,还有极少数门人问学朱熹之后转向其他学派。
七、学派贡献的差异化统一。朱子学体系庞大而复杂,朱子门人群体的学派贡献各有侧重各有差异。
就朱子门人在朱子学派当中的地位和影响来说,以蔡元定与黄榦为首大弟子。蔡元定是朱熹生前最重要的弟子,被全祖望称为“领袖朱门”(12)。他具有较高的形上思维能力,作为朱熹的对话者,不仅协助朱熹主要学术著作的编撰,而且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朱子学的研究领域,并对朱子学的传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三个儿子均为朱子门人,在朱子经学哲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黄榦则是蔡元定去世之后一直到朱熹去世之后最重要的朱子门人,他在朱子学派当中特别是朱熹去世之后具有重要影响,除了传承朱子学之外,还有两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一是朱熹之后散居各地的朱子门人主要围绕黄榦而凝集成一个学派,二是黄榦通过道统论的方式从理论上论定了朱熹在理学道统谱系中集大成者的地位,这点为朱子学的继续推广和最终官学化奠定了理论依据。此外,还有一个能够说明蔡、黄二人在朱子门人群体中重要影响的实例,即在名为记录朱熹语录的《朱子语类》当中却录有其他朱子门人所记录的蔡、黄语录,这说明在不少门人那里甚至认可了蔡、黄二人在朱子学派中仅次于朱熹的导师地位。(13)
就朱子门人的具体贡献来看,除了蔡、黄二人以及前面讲学著述部分提到的门人之外,朱熹的重要门人还有很多,他们的学派贡献体现在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在朱熹经学体系的继续完成与注疏方面,成就突出的有修撰《书集传》的蔡沉,编修礼书的黄榦与杨复,修撰《春秋集传》与《春秋集注》的张洽,撰成《诗童子问》的辅广以及《木钟集》的作者陈埴等人;在朱学义理的精致化解释方面,有撰《北溪字义》的陈淳,撰《性理字训》程端蒙等;朱熹之后在几个地方形成了朱子学的聚会讲学中心,包括以李燔、胡泳为首的南康,以甘吉甫为首的临川,以黄榦、郑文遹等为首的建阳,还有杨楫常与杨复聚会讲学;朱子学的推广者除了各地聚会讲学者之外,还有在四川传播朱子学的度正、在永嘉地区推广朱子学的叶味道与陈埴等;在朱子学的制度化过程中通过上书等途径发挥直接推动作用的弟子,如刘爚、任希夷等。此外,包括上述一些门人在内的《朱子语类》中记录朱熹语录的93位门人,均可视为朱熹逝后的重要门人。而学派贡献并非特别突出的其他朱子门人,则为一般门人。
整体而言,在朱子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聚集在朱熹周围的所有朱子门人,构成了南宋后期一个最为庞大复杂的学术群体,在朱子学形成、发展、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经学研究上丰富与完善了朱子学的研究,在义理诠释上实现了朱子学义理的精致化与规范化,并且通过同门间的学术交往等活动凝聚散居各地的朱子门人,使得整个学派的整体性得以保持,同时通过道统论建构从理论上论证朱子学的正统地位,最终使朱子门人与亲近朱子学的社会力量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借助各种具体方式实际促进朱子学的社会推广,实现朱子学与国家制度的良性互动与结合。
注释:
①弟子是偏重于从师生之间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来讲,故有所谓一传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说法,对朱熹的学生来说还有所谓传《易》弟子、传《诗》弟子、传《礼》弟子等,朱彝尊《经义考》中就有此称法;而门人则是偏重于从学派的构成来讲,一般只是指一传弟子即亲授业弟子。因此本文以朱子门人相称。
②陆游:《方士繇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版。
③如李胜:《朱熹书院与门人考补一则》,《四川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许家星:《〈朱子门人〉补证》,《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
④陈荣捷的《朱子门人之特色及其意义》(载于其著《朱子门人》)一文基于其对朱子门人的考证成果,对朱子门人群体有一整体上的描述,但一方面他的描述仅涉及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及政治态度等方面,而没有涉及其他如聚集过程、从学类型、学术贡献、学派内部影响等更为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陈荣捷的考证在总人数和不少具体人物的概况等方面都为后来研究者所考订修正,于是他对朱子门人群体的描述自然会有不少偏差。
⑤参见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之“附录1朱子门人基本情况表”,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本文下面所有统计数据以及相关具体情况除特别标注外,均参见这一部分,后文不再标注。
⑥已确定姓名的朱子学派叛徒有三位:傅伯寿、赵师雍、胡纮(参见《考亭渊源录》卷二十四下注)。
⑦高令印先生曾经统计过朱子门人的籍贯分布:福建籍175人,浙江籍75人,江西籍81,安徽籍13人,湖南籍31人,江苏籍7人,四川籍7人,广东籍4人,河南籍1人,山西籍2人,有名而籍贯不可考者112人。(详见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总计是514人。里面存在许多年代错误、记录不准确、将陈荣捷明确考证不是门人的也算在里而、没有吸收最新考证成果等问题,本文经过逐一参考陈荣捷《朱子门人》、《朱子实纪》、《宋元学案》、《儒林宗派》以及最新考证成果如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许家星《朱子门人补证》等材料,得出如上统计结论。
⑧该文也有关于朱熹弟子进士数量的统计,但主要依据方彦寿的《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因此非常不完全,相比而言,他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弟子的统计是依据《宋元学案》、《宋史》等材料,其统计更可信。见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0页。
⑨以南宋李心传记载的《嘉定四选总数》为例,嘉定六年(1213年),荫补出身官员占57%,科举出身官员占28%,其它出身官员占15%。(参见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⑩参见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之第五章第三节,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11)参考赵伟:《陆九渊门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宋元学案》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78页。
(13)黄榦追忆蔡元定时曾说“从先生(即朱熹)游者,归必过公(即蔡元定)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宋元学案》卷六十二,第1999页。)在朱子门人特别是晚期门人当中,有不少朱子门人在朱熹去世之后继续转向黄榦求学,成为黄榦门人,如陈宓等人(详见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之“附录2朱子二传门人基本情况表”,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