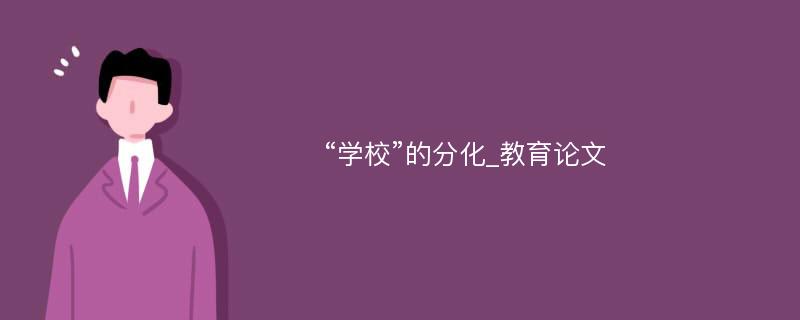
“学校”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1)01-0082-06
何谓“学校”?它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谁都明白,它是一种“教育机构”。不过,学校从来都是“教育机构”么?它是单纯的“教育机构”么?古人早有疑问,现代有识之士也多有不同意见,从这种疑问出发,在20世纪初形成“学校即社会”之说,随之而来的又有“社会即学校”之见。这些见解早已广为流传。对么?至今还少见中肯的评论。因此有必要对“学校”观念的演变作一番检讨。
一
中国古代教育实体,泛称为“学”。其中官学,或称“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但未必如此。就连作出这个判断的黄宗羲(1610-1695),也认为不尽如此;倒是古代不以学校命名的私学(如书院、家塾),或多或少近于“养士”机构。自然,这些都是有待证明的假设。
在中国,无论古代“兴学”,还是近代“废科举,兴学校”,常以复夏、商、周三代“学校”之旧为立论依据。其实,论者不会不清楚,所谓三代“学校”,同古代所兴之“学”,不是一码事,同近代“学校”更相径庭,只不过在惟有“古已有之”、方可立足观念至上的时代,才不得不如此立论而已。
关于三代“学校”同古代“学校”之别,明清之交,黄宗羲曾在关于“学校”的专论中,有过明确的表述: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之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1]
此处,关于“学校”的价值判断或有争议,而关于“学校”的事实判断,从古籍中可获参证。其中关于“学校”性质与职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1、三代“学校”(辟雍)为参政、议政之所(经黄宗羲点染,它仿佛是君主立宪制的“议会”),“养士”,寓于参政、议政之中,同汉代以后的“学校”迥异,可以撇开不议。
2、汉代以后的官学,或多或少带有“养士”职能;惟隋唐以还的“学校”,虽以“养士”名义设置,究其实,“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以致有才能学术者,“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而那种“学校”,作为科举附庸,其职能重在“取士”,论其性质,也就算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育”机构。故古代关于“学校”应有职能,“养士”还是“取士”,间或存在争议。结果,作为“养士”的“学校”,时有时无。
为明古代以“取士”为旨趣的“学校”同近代“学校”的区别,不妨从考察作为“取士机构”的“学校”入手。
中国古代取士,隋唐以前,实行选举制度(如汉代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人才的选拔,主要由地方政权推举;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作为官学的“学校”,主要为“取士”机构,并且又不单靠“学校”取士。
唐代科举考生的来源(撇开考察在任官员的制科考试不谈),有“生徒”与“乡贡”之别。“生徒”为有官学身分的学生,“乡贡”为自学应考的学子。尽管在正常年景,科举循制如期举行,惟当时“学校”作为(通过校内考试、甚至不必通过考试)确认“生徒”资格的机构,时兴时废,常常形同虚设。
明清之际,科举制度更为成熟,其中学校职能较为分明:
明清科举中,以进士科为典型。进士科考试分为三级:1、院试;2、乡试;3、会试与殿试。此外,还有作为科举预备性考试的县试与府试。按规定,府试合格,取得“童生”身份,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院试”,包括岁试与科试。岁试合格,从“童生”转为“秀才”;岁试成绩优良者,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称为“录科”。
“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会试”取中者为“贡士”;“殿试”录取者为“进士”(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与“同进士出身”之别)。[2]
值得注意的是,秀才为“县学”或“府学”生员,而生员不一定到县学、府学就读;中央官学称为“国子监”,其中的学生称为“监生”。“监生”有“举监”(举人入监)、“贡监”(秀才入监)、“荫监”(恩赐身分)及“例监”(以捐纳钱粟而得身分)之分,他们也同地方官学的“生员”一样,不一定到“国子监”就读。生员可不入学、监生可不在监,学校常常空关,庭院荒芜,这种状况早在号称教育事业发达的唐代即已存在。唐朝舒元舆曾经颇为生动地描述了在国子监的见闻:
初过于朱门,门阖沉沉。问之,曰:“此鲁圣人之宫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门,门中有厦屋。问之,曰:“此论堂也。”予愧非鸿学、方论,不敢入。导者曰:“此无人,乃虚堂尔。”予惑之,遂入。见庭广数亩,尽垦为圃矣,心益惑。复问导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导者曰:“此积年无儒论,故庭化为废地。久为官于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开堂,堂中无机榻,有苔草没地,予立其上,凄惨满眼,大不称向之意。复为导者引,又至一门,问之,曰:“此国子馆也。”入其门,其庭其堂,如入论堂,俄又历至三门馆,问之,曰:“广文也,大学也,四门也。”入其门,其庭其堂如国子,其生徒去圣人之奥,如堂馆之芜。[3]
不必以偏概全。不过,“学校废驰”,倒是史不绝书。有“废”才“兴”,“兴”而复“废”,所“兴”,大抵为“取士”之学,属制度使然;值得注意的是,古代间或有藉“学校”以“养士”的倡议。在宋代,先后有庆历兴学(范仲淹主持),熙宁、元丰兴学(王安石主持),绍圣兴学(蔡京主持)。关于庆历兴学,《宋史·选举志》载:
时(按:指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以记诵,则不足以尽人才。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卅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注: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同引《宋史·选举志一》,所记与此出入甚大;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援引《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与此亦有出入。)
范仲淹、宋祁等奏章中,批评“教不本于学校”,主张“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包含以学校“养士”之意。
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胡瑗(993-1059)为光禄寺国子监直讲,掌管太学。四方学子如蜂拥蚁集,以致原有学舍不能容纳。实行分组教习,每人至少选习一组,各以组别分地讲习。各组学子,自习为主,而先生随时召集他们讨论。[4]
宋代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创立太学“三舍法”,即在太学中设外舍、内舍和上舍。初入太学为外舍生,名额不限;外舍生合格者升入内舍,名额为200人;内舍生合格升入上舍,名额仅为100人。这是通过学校内部考试,按淘汰制取士,从而使太学兼有“取士”与“养士”职能。这种改革,在古代历史上也只是难得一现的昙花。
二
时至近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兴起,中国清朝末年,以复夏、商、周“三代”之旧、“礼失求诸野”为由,“废科举,兴学校”。实际上是以近代的“养士之学”,取代古代作为“取士之学”的官学与作为“养士之学”的私学。所兴的学校为“教育机构”。关于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孟宪承表述为:
于家庭、邻里以外,社会供给儿童发展一个特殊的环境——学校。学校是专为教育而存在的:行为的变化、技能和知识、理解的获得,在学校里有计划地进行。
在别的社会环境里:刺激是很复杂的,在这里却化成简单;是互相冲突和混乱的,在这里却选择而组成秩序;刺激和反应的联络,原须经过浪费的尝试,在这里也因指导而可以经济地构成。总之,学校是一个控制的环境。学校的发生,是人类教育上一大经济。[5]
这里陈述了作为“教育机构”(即“培养人的机构”)的学校的性质以及学校与社会环境影响的区别;问题是有别于“社会环境影响”的“教育机构”,不限于“学校”。现代社会在学校以外,还有“社会教育机构”林立。如少年宫、公共图书馆、科学技术指导站等,其中的活动有专职(或兼职)人员承担,有一定计划,对所传播的文化和施加的影响,也经一定选择。只是出于“学校教育即教育”的偏见,才无视这类“社会教育机构”的存在,或把它们不恰当地称为“校外教育机构”。
“社会教育机构”同“学校”之间,只存在“制度化”程度的区别,它们属于“制度化”程度不高的教育机构。这类机构固然不能完全代替学校,惟在文化、技术普及的意义上,因其形式灵活,又比学校更为经济,有学校所不具备的优点,也就越来越引人瞩目:
实际上在学校之外,还存在着各色各样的培育人的教育活动。不过由于这些教育活动是存在于一般社会当中,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很难能简单地说明它们是怎样地培育人。
近来,教育科学已经把这类培育人的教育实体,作为一项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因而可以从中看出整个教育,同时也可以查明学校在整个教育中是进行着什么性质的教育活动。这是教育科学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可借以更加明确学校教育的本质。[6]
为什么说恰当地肯定“社会教育机构”的价值,有助于“更加明确学校教育的本质”呢?主要是基于“社会教育机构”与“学校”的比较,可以揭示“制度化”了的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并破除“学校教育即教育”的偏见。
不仅如此,依照现代教育的眼界,随着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变化,学校就连作为“教育机构”,也不尽名副其实了。
近代学校原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载体,有别于近代以前的“非制度化”的教育实体,它一经成立,不免按照自身的逻辑,趋向于“制度化”。这种教育机构由一系列的规范构成一整套制度,保证它对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所传播的文化,加以选择和控制,使教育过程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这才不失为人类教育历史上的进步;不过,这种由整套制度维系的教育机构,仿佛是一座座孤立的“城堡”,形成特殊的“学校文化”。在近代前期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学校文化”,甚至对学生人格形成的影响也渐渐淡化。早在19世纪中叶,斯宾塞即有见及此:
一个男孩,在他整个一生,十之八九用不到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大家都熟悉的老生常谈。我们常说他在店铺和办公室里,在管理家产或家务中,在银行或铁路工作中,他费了那么多年学来的知识对他帮助很少,少到其中大部分一般地都忘记了;而如果他偶尔冒出一句拉丁文,或提到某些希腊神话,也并不是为了说明当前的问题,而是为了表现自己。[7](P54)
我们每个人都不满足于安静地在各方面充分发展我们的个性,而是很焦急地渴望使我们的个性深深地打动别人,并且多少支配他们。这个就是决定我们教育性质的东西。[7](P56)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校科目中几乎完全忽视的东西,却是同人生事业最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不是由于在他们学业据说已完成后,人们开始自己设法获得了一些知识,我们的生产就会停顿。如果不是由于这个多年累积的和在私下传播的知识,这些生产就根本不会存在。如果除我们公学所进行的教育以外别无教育,英国现在就会同在封建时代一样。[7](P70-71)
这,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宗羲关于中国古代官学的评论:士之有才能学术者,“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斯宾塞的断言,虽属偏激之辞,并非无的放矢。
在现代,所谓“学校是教育机构”,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符合事实,但又非全然如此。这是由于学校既具有“教育职能”,又不免兼有同“教育”无干的职能,即“非教育性职能”[8],而在不正常情况下,“非教育性职能”甚至压倒“教育职能”。
笼统地称“学校即教育机构”,是一种堂皇的说法。它除了符合部分事实外,主要反映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关于“学校”的价值取向,而轻信这种说法,不仅对学校中客观存在的“非教育性职能”现象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为教育而教育”的暗示。
三
在近代,把学校视为“教育机构”,确有积极意义;到了现代,随着“社会本位”取向的形成,对“学校”的认识(学校观)发生了变化。当历史跨进20世纪门槛之际,杜威在《学校与社会》(1900)一书中,开宗明义,揭示了学校观念的变化:
我们往往从个人主义观点去看学校,以为它不过是师生之间或教师和儿童的父母之间的事情。因此,最令人感兴趣的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个别儿童的进步,他的体格的正常发展,他的读、写、算能力的提高,他的史地知识的增长,态度以及敏捷、守秩序和勤劳的习惯的改善——我们正是从这类标准来判断学校的工作,这诚然是对的。但是,眼界需要扩大。[9](P27)
说明原先以为学校是“教育机构”,虽不算错,只是视野过于狭窄,它可能是“为教育而教育”、“就教育论教育”的观念。如何扩大“学校”的眼界呢?一言以蔽之:把学校看成是在社会中、由社会所设置、为社会而设置的“社会机构”:
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给它的未来的成员去安排。社会所实现的关于它自身的一切美好的想法,就这样希望通过各种新的可能途径开辟给自己的未来。[9](P27)
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讨论教育上的一个新运动,就必须特别具有比较宽阔的或社会的观点。否则,我们就会把学校制度和传统的变革看成是某些教师的任意创造……这好比把机车和电报机看成是个人的发明一样。教育方法和课程正在发生的变化,如同工商业方式的变化一样,乃是社会情况改变的产物,是适应形成中的新社会的需要的一种努力。[9](P27-28)
这是“为社会而教育”、“就社会论教育”的视角。“学校即教育机构”与“学校即社会机构”之间的区别何在?从前者到后者,除了把学校放在一定社会背景上考察外,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这,首先涉及对“社会”的界定。从表面上看来,任何一所学校,都少不得有至少一位老师与一群学生,其中少不得有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而这种学校往往是由社会组织创设的,也就难以否认它是“社会机构”。如果可以这样认定,那就表明把学校视为“教育机构”,不尽恰当;不过,按照杜威之流“比较宽阔的或社会的观点”,近代以来学校(称为“传统的学校”),且不说其教育(“学校文化”)同变化中的社会需求脱节,学校内部的关系,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均为狭窄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传统学校中的人际关系和学校文化,均缺乏“社会性”与现代社会价值。
按照“社会本位”的观点,应使学校成为“刍型的社会”。单就学校中的人际关系来说,它与传统学校的区别在于:传统学校里,聚集在一起学习的学生,彼此之间相当于生产机构早期的“简单协作”,每个学生只把学习看成是自己的事,与其他学生无干。固然,彼此之间可能有竞争,也可能互助,这种竞争只能培植个人主义,这种互助也只是个人之间的事。这种情况的发生,同脱离生活的作业(课业)相关;反之,如使各种作业成为学校生活联接的中心,即以活动为中心,学生之间就可以为完成某种共同的作业而分工,并在分工基础上协作(相当于生产机构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每个人为共同作业的完成,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分享别人的贡献。这种具有共同路线、共同精神、共同目的的学生群体,才堪称“社会”。
四
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斯宾塞从“人本位”视角提出“教育预备说”;杜威从“社会本位”视角批评“教育预备说”,提出“学校即社会说”;陶行知则以“社会即学校说”代替“学校即社会说”;徐特立对“学校即社会说”与“社会即学校说”有所评论,他的见解带有“终身教育”意味;当代教育取向,则以“终身教育”为主流。这个探索过程反映了人类关于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认识的深化。
1、杜威对“教育预备说”在理论上的失误、实践上的不良后果进行了全面分析。
“教育预备说”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为:当然,所预备的乃是成人生活的种种职责和权利。儿童在社会中不被视为有充分正式地位的成员。他们被看作候补人,列在等待批准的名单上。这个概念仅比下面一种看法稍稍前进一步,这就是认为成人生活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作为“另一种生活”的预备期。这种把教育看作预备的观念只是我们曾经批评过的关于生长的消极性质的和缺乏性质的概念的另一种形式。[10](P58)
把教育看作为将来作预备,错误不在强调为未来的需要作预备,而在把预备将来作为现在努力的主要动力。为不断发展的生活作预备的需要是巨大的,因此应该把全部精力一心用于使现在的经验尽量丰富,尽量有意义,这是绝对重要的。于是,随着现在于不知不觉中进入未来,未来也就被照顾到了。[10](P60)
2、陶行知试图以“社会即学校”说取代“学校即社会”说。确切地说,应优先考虑“社会即学校”问题。
与“教育即生活”有联带关系的,就是“学校即社会”。“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现在我还有一个比方:学校即社会,就好象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他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他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11]
3、徐特立主持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曾就办学方向问题发生分歧,一派持基础教育取向,一派持实际应用取向,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徐特立在争论总结中提到: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具有能够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于有些同志提出的要“博”要“专”,不是学校单独能解决的,还必须到社会上去钻研,在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必须经过学校和社会两个阶段,才能完成博与专。那种“学校即社会”,把两阶段混为一阶段的杜威主义是有偏向的、不对的;相反的,“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即否定学校教育的意义,想单纯以带徒弟的方法,也是一种偏向。[12]
此外,陶行知认为“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徐特立的看法稍异:他认为“学校即社会”“行不通”,是“因为我们的条件做不到”,“所以陶行知把它改为‘社会即学校’”[13],认定使学校成为“刍型的社会”,是更为艰巨的事情。
怎样看待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这些对教育影响甚大的学说?
1、所谓“教育是生活的预备”、“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都是实践口号。这类实践口号,因其旗帜鲜明,易于流传,但如此浓缩的词语,实难达意;“学校即(as,宛如)社会”,又是隐喻性的陈述,西方谚云“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而在中国,把"as"译为“即”,更曲解了原意,使其绝对化;“社会即学校”,是针对“学校即社会”提出的口号,系因另一个绝对化口号而使这个口号打上绝对化印记。其实,学校就是学校,社会就是社会,学校不等于社会,它充其量是一种特殊的小社会,倡导这些学说的教育家焉能不懂得这些简单道理?
斯宾塞“教育预备说”,并非主张脱离学生将面临的社会生活,去为未来生活作准备,相反,他坚持“人本位”取向,也赞成“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却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实质教育”取代脱离社会生活的“形式教育”。由于受时代局限,才不免忽视儿童经验的价值,但儿童经验的价值不也有限么?杜威“学校即社会说”,岂有使儿童成为“笼中鸟”之意?儿童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沟通,才是他的本意,反之,无视学校的特点,使儿童成为在天空任意翱翔的飞鸟,真能使儿童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成员么?同样,提倡“社会即学校”的陶行知,从不放弃一切办学校的机会,他所主持的学校,哪里等同于“大社会”?(注:徐特立认为,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并非要“废止学校”,而实际上认为“学校为社会中的特殊部分,即把学校扩大到社会中去,使学校社会化罢了”(《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是对“社会即学校说”善解人意的阐说。)
只是这类简略的实践口号在流传中,难免被望文生义,滋生流弊,而一个接一个教育家正是针对实践中的偏向,才提出他们用于纠正偏向的新口号。
2、关于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不同抉择的分歧,也像教育上许多其他争端一样,争议双方在方法论上共同存在的问题,是把学校教育作为人生“一次性完成”的预备,以致各种见解易于走向极端,也不难露出破绽;徐特立着眼于“学校”与“社会”两个阶段的预备,否定学校“一个阶段”完成生活预备的假设,包含现代“终身教育”思想的萌芽。
3、如果说,斯宾塞的构想以反映社会生活的课程丰富了“制度化教育”,那么,杜威与陶行知都把锋芒指向“制度化”的传统教育。只是杜威着重谋求“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的改造,而陶行知则更加关注“非制度化教育”。他们在教育改革中各有建树,对旧学校的改造异曲同工。
徐特立处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历史环境中。在根据地,曾反复出现过“正规化”教育取向(实有别于“制度化教育”)与教育中的“游击主义”取向(“非制度化教育”)之争。当时受面临的迫切任务的压力和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局限,短视的功利主义与狭隘的经验主义的影响甚大。徐特立在那种沉重压力下,坚持在保持学校特点前提下,使学校反映社会生活,并为社会服务。他对改造“制度化教育”和兴办“非制度化教育”,均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总之,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构想,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作为“社会机构”的学校的内涵。
收稿日期:2000-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