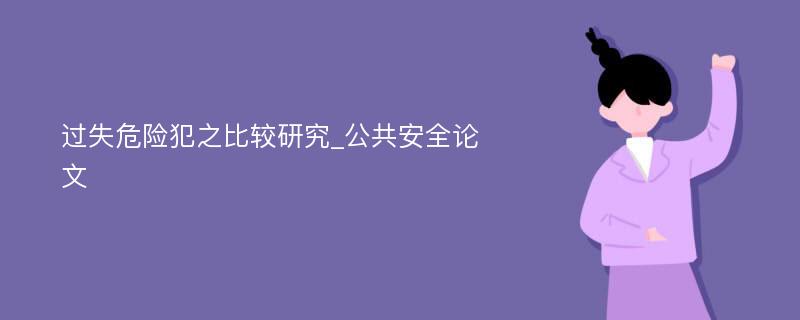
过失危险犯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失论文,危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00)04—0038—05
虽然过失危险犯在当代中外刑事立法中均有规定,但是在刑法理论上仍然存在着争议。我国刑法理论对该问题论述不多,而且刑法对过失危险犯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因此,研究过失危险犯的理论,合理借鉴外国刑法有关过失危险犯的规定,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
一、过失危险犯的立法
传统的过失犯,以过失行为造成严重的实际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即所谓的“实害犯”;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实害结果发生,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考察中外有关刑事立法,通常将一些足以造成某种严重实害结果发生的故意犯的危险犯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否认过失犯的危险犯的存在。危险犯仅属故意犯罪的一种既遂形态,与过失犯罪无关。[1](P46)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过失犯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例如,随着尖端科技在医疗、生产、运输等有关装备中的广泛运用,虽然经济效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其危险性也在激增。那些从事与致险源有关工作的人员,如果违反安全法规或者操作规程,就会过失地将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置于严重的危险状态,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不少国家刑法开始规定过失危险犯,将虽未造成实际物质危害结果但有可能造成这种危害结果的过失行为予以犯罪化,即将过失导致某种严重危险状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此相适应,“海外刑法理论一反结果为中心的过失论,提出以行为为中心的过失论。即处罚过失犯罪不是因为造成危害结果,而是因为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这昭示着过失犯罪由结果责任向行为责任转化的倾向”。[2](P70)
作为大陆法系成文法代表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在刑法典中均规定了为数不少的过失危险犯。1980年修正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刑法典有关过失危险犯的规定达16个之多,例如第310条a规定的(过失)引起火灾危险罪、第310条b(过失)引起核能爆炸罪、第311 条(过失)引爆炸药罪、第311条d(过失)释放放射线罪、第315条(过失)侵害铁路、 水路及航空交通罪、第316条(过失)酒后驾车罪、第326条(过失)污染环境的垃圾处理罪、第330条(过失)严重危害环境罪等等。 广义的日本刑法由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组成。由于日本的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的行政犯都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因而日本刑法典仅规定刑事犯(自然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刑法,这也是日本刑法典相对稳定的原因。即便这样,1907年颁布、经过多次修订的日本现行刑法典也规定了为数不少的过失危险犯。例如,日本刑法典第175 条(过失爆炸·破裂·泄漏)第1项规定,“过失使爆炸物爆炸或者激发破裂, 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产生危险的,处1年以下监禁或者20 万以下罚金”;第2项规定,“过失使煤气、电气、蒸汽、 放射线或者放射性物质漏出、流出、散发或者断绝,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产生危险的,与前项同”。在其它的条款中也对相应的过失危险犯作了规定。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在陆续颁布的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也规定了过失危险犯。例如1971年7 月开始实行的《公害罪法》(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3条(对过失犯罪的惩罚)第1项规定,“凡无视业务上必要的注意义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业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给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带来危险者,应处以2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或处以200万日元的罚金。”
除了上述德、日刑事立法中规定有大量的过失危险犯以外,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规定。在前苏联,1962年以后的苏俄刑法典中新增加的11条过失犯罪,其中就有7条涉及过失危险犯, 加上原有的过失危险犯,使此类犯罪达到21种,而且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规定的过失危险犯数量也大致相同。[3](P110)1997 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也规定有过失危险犯,例如该法典第215条(违反原子能工程安全规则)规定, “在原子能工程的布局、设计、建设和利用方面违反安全规则,如果这可能引起人员死亡或周围环境的放射性污染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 倍至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至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另外,该法典第217 条(违反有爆炸危险工程中的安全规则)、第 225条(不正确履行保护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和爆破装置的义务)、第247 条(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等也是对过失危险犯的规定。
作为判例法国家的美国,近年来也通过判例确立了惩治过失危险犯这一原则。1987年7月23日,美国一架载满乘客的波音747客机从纽约飞往伦敦,驾驶人员在降落前忘记了打开机翼升降器。在着陆前几秒钟,被地面指挥人员发现并及时通知机组人员,驾驶人员匆忙架机升高,在空中盘旋一圈放下升降器,再次着陆,才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惨祸。事后,美国法院追究了机组人员的刑事责任。他们认为,机组人员的这一过失,虽然由于发现及时而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危险性已极为严重,因而构成过失犯罪。[4](P34)
可见,不论是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或判例中都承认过失危险犯的存在,把一些置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于严重的危险状态的过失行为予以犯罪化,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考察我国的刑事立法,1997年刑法典也有过失危险犯的个别立法例,即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与其他国家刑法的有关规定相比,不仅数量偏少,而且也欠缺合理性。
二、过失危险犯的理论依据
过失危险犯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过失危险犯的理论依据,或者说应如何评价现代社会中这种给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也就是过失危险犯的立法是否有必要,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仍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主张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应予以犯罪化。他们认为:(1)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过失的危险性增大了, 根据造成的后果(主体没有预见,或者希望避免的结果)规定刑事责任,其预防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必须规定故意或过失犯罪(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不是发生的结果)承担责任的一般原则;(2 )过失引起的结果大都具有偶然性,必须根据对损害发生之前的活动有无辨认能力,在主观上能否进行控制来规定责任。在必要的场合,只要行为人违反了规范上确立的安全法规(空白罪状),不论是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还是造成有发生这些结果的实在危险(实在危险构成),都应承担刑事责任。[3](P115)
与此相反的意见则反对将仅造成某种危险的过失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他们认为:过失只有实际发生结果的,才可承担责任。其理由是,发生危害结果,几乎是判明应负责任的惟一客观尺度,它可限制应受惩罚的过失范围。没有这一尺度,惩罚过失的范围就会无限扩大,过失犯罪的潜伏性就会日益增长,有关规范的适用率就会越来越低。而且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居民的法律意识把过失的责任主要是与造成危害结果联系在一起。[3](P147—148)
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者提出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这两种理论来阻却过失行为的责任,有部分学者以该理论支持过失危险行为非犯罪化的主张。[5](P314 )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理论是否与过失危险犯相矛盾?信赖原则是指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场合,应该对他人的行为予以信任,相信他人能够实施适当的行为,并对自己的生活和正常活动予以保障。信赖原则要求在遇到需要共同防止危险的情形时,除要一起防止所遇到的危险外,还要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严格按照规定的行为行事的一种相互信赖,并以此为前提,决定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应作的事。如果从事某一危险业务的行为人依赖信赖原则不存在预见某一特定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即使预见或者出现异常情况,也不负过失责任。信赖原则似乎否认了过失犯罪危险犯的存在。容许的危险则指随着高速交通工具和日益复杂的各种现代设施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势必不可避免地给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造成或多或少的危险性,而且操作这些设施的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危险的可能性,但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考虑,应对从事危险事业的人员造成的危害结果从宽处理。可见,容许的危险理论具有限制过失犯罪主体的功用,依据该理论,过失犯罪的危险犯也无存在的余地。不过,从上述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理论的含义可以知道,二者的适用均是以行为人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为基础的,唯有此,也才能阻却过失行为之责任。但过失危险犯是以行为人故意违反有关安全法规为前提的,因此,信赖原则和容许的危险理论与过失危险犯并不矛盾。
在我国刑法学界,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以及我国刑法中是否规定有过失危险犯,认识颇不一致。否定说坚持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责任范围的客观尺度这一传统观点,认为危险犯通常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由于它不要求犯罪结果,因此必须该行为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危害性,是所谓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历来都是结果犯,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是所谓结果无价值。在没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就没有过失犯罪而言。因此,过失不存在设立危险构成的可能性。过失犯罪的危害性日益增加,这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但不能指望通过犯罪化来预防过失犯罪,出路只能是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杜绝过失于未然。[6](P191)反之, 便会无限制地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而且这种立法的社会效果不好,会加重业务人员的心理负担,不利于社会的进步。[7](P292)从主观上讲, 过失犯罪的发生是日常生活、工作、生产中注意不够、疏忽大意、鲁莽草率造成的,不像故意犯罪那样行为人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规定过失危险犯没有多少意义。[8](P131—132)
肯定说认为,以过失犯历来是结果犯否认过失犯中存在危险犯的可能,理由并不充分。危险犯其实也是一种结果犯。危险犯并非不要求结果,只是它所要求的是一种危险结果,而非实害结果,这种危险结果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过失行为人确实是不希望或者根本没有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等到危害结果发生之后,再给行为人以刑事处罚,不会产生足够的预防效力。[9](P23)然而,过失行为人违反防范规范常常是故意的,如果我们对这种容易引起严重后果的故意违法行为给予适当的刑罚震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严重后果的发生,对行为者本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若坐等严重后果发生之后才去刑事介入,那就成了十足的“马后炮”。[10](P42)
我们认为,理论的研究要为司法实践服务。某一种行为是否需要犯罪化,完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过失危险犯正是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犯罪,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事立法中加以肯定,而且如前所述,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基于这种现状,就不能无视这种立法事实,在理论上片面否认设立过失危险犯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赞同立法上设立过失危险犯的肯定说。除了上述肯定说的理由之外,关键是应正确把握危险犯究竟是否为结果犯?也就是说,危险状态是否为一种危害结果?否则,很难将过失危险犯统一到过失犯罪的一般理论中,极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
危害结果,理论界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主张。以梅芝格(Meager)为代表的广义结果说认为,凡是犯罪意图的客观化都是危害结果,不限于行为对客观外界所造成的有形变化,还包括身体的动作和其他非物质性损害;以麦耶(H.Mayer)为代表的狭义结果说认为, 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致使犯罪客体发生的事实上的损害或危险状态。[11](P68—69)显然,广义的结果说将行为与结果混为一谈,并且将危害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也包括在危害结果的范畴之内,因而危害结果不可能成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丧失了危害结果在法律上应有的意义。根据狭义的结果说,危害结果既包括危害行为对客体造成的实际损害也包括危险状态,符合实际情况,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例如,日本学者团藤重光将犯罪分为实质犯(结果犯)和形式犯(行为犯),其中实质犯又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认为大多数犯罪把侵害法益的实害或者危险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这叫实质犯。其中,把对法益产生现实侵害作为构成要件的叫实害犯,只将发生侵害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叫危险犯。[12](P116)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犯不是行为犯,而是与实害犯同是结果犯。因为危险犯也要求一定的结果,只是它要求的结果是某种危险状态,实害犯要求的结果则是实际的损害。[13](P169)因此,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实际的损害,还应包括危险状态,危险犯是一种结果犯。这样一来,过失犯罪的一般理论可以涵盖过失危险犯,过失危险犯与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有利于更新和完善过失犯罪理论。
关于我国刑法中是否规定有过失危险犯,通说是持否认的态度,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作为过失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犯毫无例外地是故意犯,不包括过失犯。[15](P32)然而考察我国的刑事立法,无论是1979年刑法典还是1997 年刑法典,都存在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1997年刑法典除了保留1979年刑法典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之外,还增加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三、过失危险犯的范围及其立法完善
外国过失危险犯的刑事立法,都是关于危害公共安全和污染、破坏环境方面的犯罪。例如,1980年德意志联邦刑法典规定的过失危险犯均集中在该法典第27章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和第28章污染环境的犯罪,其他国家刑法规定的过失危险犯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我国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两个过失危险犯,即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不过,虽然它们分别侵犯了国家关于甲类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和国家对国境卫生检疫的正常管理活动,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但实质上则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也就是说,这两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并不影响其本质特征是危害公共安全,这从其所在节名“危害公共卫生罪”中也可以看出,因此,笔者建议应将危害公共卫生罪这一节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剥离出来,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况且,在外国刑法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体系中,就有危害公共健康罪(危害公共卫生罪)的类罪名。
由于过失犯罪具有不同于故意犯罪的特点,尤其是对这种仅造成某种严重危险、实际危害结果尚未出现的过失危险犯应当予以严格限制,不能作为过失犯罪的普遍形态加以规定。基于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国外学者也主张,规定过失造成危险的构成并列入立法,只在某些场合才有其必要。[3](P147—148)参照国外有关过失危险犯的刑事立法,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在下列两类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中,有选择地规定一些过失危险犯:一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行为(包括归类于其他章节但实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行为);二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过失行为。
研究我国1997年刑法典关于过失危险犯立法例,如前所述,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刑与刑之间、罪与罪之间也不相协调。刑与刑之间不相协调主要表现在规定的两个过失危险犯与其实害犯之间刑罚失衡。过失危险犯是过失行为尚未造成实害结果,仅造成了具有该实害结果发生的实际可能性即危险状态,与过失行为已造成实害结果的传统过失犯即实害犯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过失危险犯的刑罚应轻于其实害犯的刑罚。例如,日本《公害罪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是过失危险犯,其刑罚是2 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或处以200万日元的罚金;该条第2款规定的是其实害犯,刑罚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或处以300万日元的罚金。然而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两个过失危险犯,与其相应的实害犯规定的刑罚完全相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同已引起甲类传染病实际传播的实害犯量刑幅度相同;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同已引起检疫传染病实际传播的实害犯量刑幅度也相同。这种立法例明显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造成了刑与刑之间的不相协调,在以后修改刑法时应予以纠正,即规定过失危险犯的刑罚应比其相应的实害犯低一个量刑幅度。
过失危险犯罪与罪之间不相协调则主要表现在本应犯罪化的一些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没有犯罪化。除了刑法已作出规定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和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过失危险犯之外,还有其他在社会危害性上同这两个过失危险犯相同甚至更大的过失危险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参照上述有关国家的立法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增设一些过失危险犯,但应限于前述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行为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过失行为等两类造成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具体来说,应将下列故意违反安全法规过失造成严重危险状态的过失行为规定为危险犯:
使用处于危险状态的交通工具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在醉酒状态下驾驶交通工具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设立假标志或假信号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引起重大建筑安全事故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引起重大火灾事故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引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严重危险的。
收稿日期:1999—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