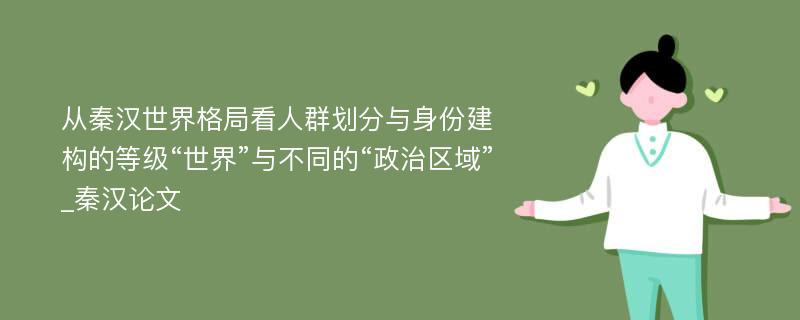
有层次的“天下”与有差别的“政区”——兼论秦汉天下格局视域下的人群划分与认同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天下论文,政区论文,秦汉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朝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继之而起的汉朝,通过进一步开疆拓土,疆域更加辽阔。表面而言,“天下一家”、“天下为一”的格局在秦汉时代由经传理想变成了社会现实,其实质却不然。不仅整个“天下”尚被沿边塞徼明确分隔为塞内、塞外两部,就连塞徼之内的各政区之间亦是差异显著。于此,一些学者如卢云、①刘瑞、②李大龙、③黎小龙、徐难于、④于逢春、⑤雷虹霁、⑥尹建东⑦等都已做过相关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以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方法继续对秦汉时期的天下格局展开研究,并将深入阐析这一格局对当时社会人群划分与认同建构的实质影响。 一、由两起争论说开去 武帝元鼎(前116-前111)中,博士徐偃在出巡关东期间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为御史大夫张汤奏劾,其罪当死。徐偃引《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为自己辩护,张汤词竭,未能予以反驳。武帝下诏让谒者给事中终军与徐偃辩难。终军以为:“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⑧因终军之诘难,徐偃“矫制颛行”之罪在《春秋》经义层面上亦得成立,其最终只得服罪受诛。从徐、终二人的言论可看出,他们立论的依据并不一样。徐说仍然停留在先秦诸侯林立、各国分疆异俗的思维定式上,由此出京师便意味着“出疆”。而终军则认为时天下为一,当践行《春秋》“王者无外”的思想,凡封域之内皆应视为天子疆土,帝国官吏外出京师不得称为“出疆”。 《论衡》中记载了另一场有关政区差异的争论:“宣帝时,凤皇下彭城,彭城以闻。宣帝诏侍中宋翁一。翁一曰:‘凤皇当下京师,集于天子之郊,乃远下彭城,不可收,与无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为一家,下彭城与京师等耳,何令可与无下等乎?’令左右通经者论难翁一,翁一穷,免冠叩头谢。”⑨在宋翁一看来,凤凰现于京师与现于彭城其意义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他遵循的显然是“《春秋》内京师而外诸夏”⑩这一反映治国次序的经义准则。于是,体现天子政治清明、德业昭彰的祥瑞只有出现在京师地区,其才符合《春秋》“自近者始也”的治国之道。而宣帝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在天下一家的现实下,京师与彭城同为帝国之域,无论祥瑞出现在哪里,其性质并无二致,都是对天子仁德的褒颂。宣帝此论又被王充用来解释“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宁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之事件,他指出:“彭城、零陵,远近同也。帝宅长远,四表为界,零陵在内,犹为近矣。”(11)反过来,王充该说也可视作是对宣帝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在同为天子辖域的意义上,四表之内,远近同一,并无“此疆尔界”之分。 上述第一例中,因张汤疏于经学,无法辩驳徐偃所引《春秋》之义。武帝就以曾为博士弟子、能辩善文的终军来诘难徐偃;第二例中,宣帝虽对宋翁一之言有所驳斥,但仍要使周遭通经者与翁一进行论辩。这一方面固然说明经学在塑造汉代天下观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其作为理论基础来辩论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春秋》包罗颇丰,论辩双方均可择取不同的《春秋》之义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而无论《春秋》“为汉制法”说是否确实可信,作为蕴涵丰富的文化元典,是书在汉代政治体制确立、政治思想生成上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天下观方面,《春秋》虽奉行京师、诸夏、夷狄由内到外、由亲到疏,彼此分隔独立之准则,但亦有主张三者可随时代发展而融为一体。或可言之,在《春秋》的世界里,“华夷之辨”为阶段性追求,“华夷一家”则是终极目标。这一点在东汉公羊大师何休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其“三世说”历史地厘清了京师、诸夏、夷狄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过“所传闻世”(据乱世)、“所闻世”(升平世)、“所见世”(太平世),京师等地域及其所居人群终能进至统一,形成所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局面。(12) 那么,促成“天下若一”的“所见世”究竟何时到来?董仲舒、何休等汉代公羊学家以鲁国昭、定、哀三公时期对应《春秋》世界的“所见世”,此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这一阶段书法的不同(“异辞”)。其于太平之世,仅是一种虚托,并非真正的“大一统”在此时实现。因为,至该阶段《春秋》终了、“西狩获麟”,(13)现实中就连“诸夏”也尚未“定于一”。到秦始皇兼并六国,又经汉武帝南征北战,沿边塞徼一再西迁南扩,秦汉帝国达到空前一统。在此塞徼环绕的疆域内,东周时期的诸夏与夷狄之地被尽置为郡县。在政治归属上,这样的“天下”之内,各地无论距离京师之远近,其地位毫无差别,均直属帝国版图。“天下为一”、“天下一家”在此层意义上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如此,公羊学派所主张与向往的真正的大一统盛世并未伴随秦王朝的统一而到来。依何休之意,在“天下若一”的时代,再无“京师”、“诸夏”、“夷狄”之分。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是一方面塞徼隔绝着“塞(徼)外蛮夷”与“中国”,(14)另一方面塞徼之内也依然存在有关“华夏”与“蛮夷”的争论与区分。这些都不免使得天下大平的治世理想在秦汉时期被大打折扣。 雷戈先生认为传统的天下观在西汉初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天下与中国之间似乎可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比如长城)”。(15)对于时人来说,长城绝不只是一种地域界限,它还是政治力量的分水岭。(16)而非但北边如此,在帝国的其他边疆也都曾有类似的界限存在,如西汉初年,汉与南越隔以南越边关、与西南夷界以巴蜀故徼等。这些塞徼边关限定着某一时期帝国统治力量所能直接到达的地域。汉武以降,汉朝国土虽在东、南方向均抵大海,但塞徼在西边(包括西南)、北边却从未消失过。由于这些塞徼的存在,现实社会中,汉人能很清晰地知道哪里为汉疆,哪里是他土。《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有东汉时期的一首歌谣:“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澜津。渡澜沧,为他人。”(17)意谓纵使汉朝德行远播、疆土外拓,然在其新扩边徼之外,“他人”仍然存在着。正因开拓疆土受制于北方勇猛强悍的游牧民族及西方从未消失的“塞外”与“他者”,使得秦汉时期由皇帝所直接统治的区域(中国)一直未能与时人视野所及之“天下”完全重合。 秦汉之世,皇帝自称“天子”。然据《礼记·曲礼下》所言“君天下曰天子”(18)及《盐铁论·备胡》中所载桑弘羊之语“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19)可知,在某些秦汉人的观念中,天子应统领包括“中国”及塞外蛮夷居地在内的整个“天下”之域。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匈奴连年犯塞、边境狼烟不绝。这导致秦汉社会的天下观出现一些变通,使得天子所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区域亦得统称为“天下”。 这样,秦汉之“天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含义及范围。与之相对应,也出现了两种相异的天下观:“只能说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前提之下,是将周边的蛮夷戎狄都统摄于理想化的‘天下’,从而‘德化被于四海’,还是以现实统治为‘天下’空间范围,在华夷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的问题”。(20)秦汉时期,这两种天下观及其所界定的“天下”范围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场合或政治动机下总会被有意地取舍。如上述《盐铁论》中桑弘羊提及之“天下”便涵盖了塞外蛮夷之地,其以此主张汉廷应该对匈奴用兵;而前举二例终军等人争论之“天下”则明显只等同于塞内“中国”。 与此同时,秦朝虽一统诸夏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各种同一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然而,帝国边地旧有的“蛮夷”族群(如秦闽中、南海、桂林等郡的越人)却并未因此而立刻同化于“华夏”。继秦而立的汉朝更是在许多全新的“蛮夷”之地设置初郡,如河西走廊、西南夷及朝鲜地区等。这些都使得秦汉华夏中国的边缘地带始终充斥着“夷狄”的身影。加上时去东周末远,秦汉士民对于某些地区本为“蛮夷”之地的记忆尚未消除,如“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等,(21)这些也会影响人们对现实中相关地域华夷身份的判别。另外,秦汉王朝幅员广阔,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作用,不同地域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绝难同一。基于以上诸种情况,前述两例中徐偃、宋翁一将京师与其他地域区分开来恐怕不能完全归因于公羊学之影响,其还应有一定的现实背景。显然,在政治地位与政治象征上,其他地区原本是无法与京师并论的。只因上述政区差异之争触及到了天子权力,各政区同归天子管辖的共性便被突出,其他内部差异则被有意识地“遮蔽”了。这从侧面表明汉代社会的“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具有明显的场景性,只有在某些特定政治场合(譬如昭示天子权力、宣示天子德行等)下才会成立。其他时刻,徼内“天下”(中国)之内部则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 从以上分析初步可知,在秦汉社会存在两种“天下”范围:一种在地域上总括“中国”与塞外蛮夷,另一种则仅包含“中国”之地。在治世理想或某些政治场景下,这两种“天下”都可以是浑然一体、远近无异的。然而,在现实社会或其他情景中却并非如此,非但塞内与塞外具有不同的政治归属与华夷身份,就连塞内各政区在华夷身份、国内地位等方面亦存在诸多差异。简言之,所谓“天下”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层次的;所谓“中国”也非同为一体,其所统辖的各政区之间差别显著。 二、有层次的“天下” 在某种意义上,秦王朝可视为秦国的扩大型。对秦国天下结构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秦帝国所统治的“天下”。从立国伊始到渐灭六国前夕,秦国与西方犬戎、义渠、大荔等羌戎之族的土地之争始终未曾停止过。因此,如何处理旧土与新域之间关系的问题很早便在秦国产生。为此,秦国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罗列如下: (1)“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去“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2)“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殴(也)。 (3)“使者(诸)侯,外臣邦,其邦徒及伪吏不来,弗坐。”可(何)谓“邦徒”、“伪使”?徒、吏与偕使而弗为私舍人,是谓“邦徒”、“伪使”。 (4)道官相输隶臣妾,收入,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者以律续食衣之。属邦。(22) 据第(1)条可知,秦称本国辖域(秦属)为“夏”,“臣邦人”所居亦包含在此之内。这一点也可得到第(2)条的证明,“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意味着“臣邦”与“秦之它邦”相异,即“臣邦”为秦之属境。但即便如此,从第(2)条中“秦”与“臣邦”对称可知,“‘臣邦’虽然已经被纳入了秦的版图,但实际上与传统上的‘秦’(指秦本土——引者注)是有着具体的区别的”。(23)第(3)条中,“诸侯”为关东韩、赵、齐等国。而对于与“诸侯”并列、与“臣邦”相对的“外臣邦”,学界一般认为其指独立于秦域之外、秦只能实施松散或间接统治的臣属之国(地)。第(4)条因出现有“属邦”二字,学者多将其归入秦处理民族(包括臣邦人、外臣邦人)事务的《属邦律》中。根据以上分析,第(4)条中细微之事无不听命于秦政府的“道官”显然只会出现在“臣邦”地区。众所周知,秦在一统六国之前便已在辖境内设置与县同级之“道”,其在地理区位、民族构成、管理方式上均有别于秦国传统设县之地(秦本土)。此又可印证前述“臣邦”既属秦国辖域,又具有一定特殊性之结论。正如刘瑞先生指出的,“臣邦”、“外臣邦”首先是与秦本土相较而言的地理概念,然后才是由彼此特殊性而引申出来的政治范畴。(24)在秦国统治的“天下”内,正因“臣邦”、“外臣邦”相比于秦本土的特殊性,“道制”、“使者”才会应势而生,从而造就不同的政治区域。综上,秦本土、臣邦、外臣邦共同构成了秦国“天下”的地域、政治格局。同时,该“天下”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秦本土与臣邦构成了秦属(秦境);秦属与外臣邦又共同组成了秦国之“天下”。 另外,秦国“天下”内的人群亦有分层。第(1)条中,“臣邦人”及“秦人”(秦族之人)所居之地被总称为“夏”,可统视他们为居住在“夏”地之人。相应的,“外臣邦人”则是居住于非“夏”地之人。另据第(2)条,“夏”地之内的人群又有“夏”、“真”之分。这里,前“夏”为地域概念——秦之属境,后“夏”及“真”则为族属概念——“夏”人、“真”人。由简文可知,“真”人是父母均为臣邦人或出生于秦属外的人,“夏”人则是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秦人且出生于秦属内的人。(25)而“夏子”可为“臣邦父秦母”所生则意味着秦国之“天下”特别是“秦属”之内的地域与人群分层并不能绝对重合。即秦本土之人并非全为“夏”人,臣邦之人亦非全为“真”人。至少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秦母及其子随臣邦父生活在臣邦之地,臣邦出现“夏”人;臣邦父随秦母生活在秦地,秦本土出现“真”人。 上述可知,从地域、政治、人群结构来看,秦国之“天下”是层次分明的。此后,虽然始皇一统六国、北方长城修筑、汉武帝开疆拓土等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导致现有天下格局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但“天下”分层这一基本特征却一直为秦汉王朝所承袭。 在政治地理结构方面,高明士先生认为:“秦朝的天下秩序,看来有三个层次,即内郡、外(边)郡、外郡之外徼……内郡之地设郡守;外郡之地设郡守,间亦设君长;外郡之外徼,亦立君长。”(26)杨军先生也指出:“对中原汉族居住区与其他民族居住区实行两种不同的统治体制,使两汉的地方管理体制……呈现出双重环状区域结构的特点。”(27)因采用不同的统治方式,秦汉王朝之“天下”亦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政治区域:内郡、边郡、外徼。而此三者又可被沿边塞徼划为“中国”与外徼两个部分。 在人群结构方面,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认为天下型国家的特征是“将九州=中国的编户百姓支配作为其核心本质;同时以在其周围存在通过贡纳关系表明从属的夷狄——异民族社会为条件,有时也包摄了对内属夷狄的支配”。(28)结合秦汉社会实际,该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仍稍显粗糙。笔者认为沿边塞徼的存在,使得秦汉“天下”之“蛮夷”可分为塞外蛮夷与塞内蛮夷两部。塞内蛮夷平常在塞内为中原士人视作“蛮夷”,但在某些特殊政治场景下(如塞内“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塞外进行区分或对抗时)则被归入“华夏”或居于“华夏”之人。总体而言,其具备一种亦华亦夷的身份。(29)此与前述秦国“臣邦人”的处境极为类似。由上,秦汉“天下”人群由编户百姓、塞内蛮夷、塞外蛮夷三部组成。其中,塞内蛮夷又可与其他二者相结合形成两种新的人群——居于“华夏”之人及“蛮夷”之人。此外,秦汉“天下”内的地域与人群分层也并不完全吻合。比如,地域中间层次的边郡就不仅为人群中间层次的塞内蛮夷所独居,秦汉边郡广泛存在着编户与塞内蛮夷杂处的现象。 由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雷虹霁也对秦汉天下格局进行了划分。她认为:“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为第一个层次的格局;汉文化内部的区域性差异是第二层次的格局。”(30)秦汉塞内蛮夷虽然被纳入郡县区,但由于“不改其本国之俗”的属国、(31)“蛮夷”之道的设置,其在塞内仍旧聚族而居,原有的部落组织、风俗习性等均得以保留。这样,在很长时间内,塞内蛮夷在文化风貌上都显异于编户而与塞外蛮夷更为接近。不光如此,在汉代,由于战败内附及政府招降政策的作用,同一民族(如匈奴、羌)经常会被分化为两部,各居塞徼内、外,而同族关系的存在往往使得二者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在短时间内很难泯灭。 由上可知,秦汉帝国之“天下”可按各种标准分为多种层次,每种标准下的层次划分各有不同,其彼此之间并不能完全对应。需要特别指出,这些有关“天下”层次的划分并不单单是学术分析的结果,其背后反映着秦汉“天下”内各地域、人群间的彼此关系。凭借这些关系,“天下”之内的编户、塞内蛮夷、塞外蛮夷可相互结合或分解而形成新的群体,建构新的认同。此种论断绝非主观臆造,其成立基于以下两个客观事实: 第一,“天下”结构下群体重组的潜在性。在各种不同标准下,“天下”地域与人群有着多种分法,且各种分法之结果并不一致。这将导致,在某一标准下归属于同一群体的两类人群在另一种标准下又会被断然分开。如塞内蛮夷与边郡编户、塞内蛮夷与塞外蛮夷等。这些客观存在的标准为各人群间的重组提供了潜在可能。 另外,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天下”不仅是有层次的,还是有轻重之分的。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指出古代中国关于“天下”的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分别,即天下等于世界、天下等于中国。他认为后者是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生命乃至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认识,前者则不过是用于化妆的颜料而已。(32)韩国学者金翰奎曾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天下”一词的不同含义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所有3375例“天下”中,单指中国的有2801例,所占比例达83%,而指中国并加上其他异族之天下的,只有64例,不过1.9%。(33)此证明在秦汉社会,“中国”是最为根本的“天下”。正因如此,秦汉帝国对“天下=世界”的追求总是以不得威胁“中国”的安全或利益为前提。如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请求罢除汉朝长城戍防。此在汉朝方面因郎中侯应的进谏而未得施行。侯应在给元帝的奏疏中大论塞防撤除将会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元帝后在给呼韩邪单于的口谕中亦有提及“关梁障塞”在维护“中国”安全上的重要作用;(34)再如建初元年(76),章帝以“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35)为由,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两汉历史上,每当对外拓边危及“中国”利益时,国内反对之声总会连绵不绝。 不仅如此,秦汉帝国“天下”内的人群也有“核心”、“次要”之分。帝国的统治必须以掌控编户齐民的户籍与赋役为基础。由此,那种以牺牲编户利益换取对“夷狄”统治的做法往往会招致非议。如匈奴浑邪王降附之初,“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汲黯认为此举是“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待浑邪降众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痛斥因与匈奴私自贸易而处死五百余“中国”百姓之举无异是在“庇其叶而伤其枝”。(36)此“枝”、“叶”说无疑是汉代中原士人对“编户”、“夷狄”在秦汉“天下”内之地位最为恰当的形象比喻。 正因秦汉“天下”内的地域、人群存在核心与边缘、枝与叶之分,使得当危机到来时,舍弃某一次要地域或人群以保护核心者成为可能。而此种舍弃极易导致相关地域、人群的重组与认同的变易。如上述章帝放弃西域之举便引致了汉朝“天下”的内缩以及西域各国“从属夷狄”身份的丧失,并随之影响到了诸国对汉朝的认同。先前与班超坚持据守以抵御龟兹进攻的疏勒在“被弃”之后,马上就有两城投降了龟兹。 第二,各种认同资源的存在使得认同生成、族群建构成为可能。划分“天下”人群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可将不同群体区分开来,亦可拉近相同标准下人群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层面上说,此类标准可被视为是一种用来促成与宣示相同认同的资源。各群体的精英人物也正可利用这些资源来促使不同群体产生彼此认同,从而建构新的族群。如针对秦国的人群分类,史党社指出:“从族群建构的角度来说,把‘臣邦’与真正‘秦人’所居之地统称为‘夏’,淡化族群与地域间的关系,应是一种促进‘蛮夷’族群产生‘秦人’认同的有益手段。”(37)时秦国尚未完成对东方的统一,团结境内“臣邦人”有利于秦对六国兼并战争的顺利进行。而此种团结或新族群建构的过程正是靠凸显相同的政治归属,忽略文化差异来进行的。这里,相同的政治归属便成为了一种认同资源。 在族群关系异常复杂的秦汉帝国的边缘地带,各族群利用各种认同资源来宣称相同认同,选择或建构某一族群身份的举动比比皆是。例如,塞内蛮夷(如“保塞蛮夷”)一方面可与编户百姓因同居塞徼之内而建构居于“华夏”的群体,促成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其又能和塞外蛮夷由相同文化、族属结成“蛮夷”群体,形成跨越边塞的族群认同。(38)再如,边郡编户(如西南夷地区的汉人)一方面可凭借相同族属、文化凸显其与内郡编户一样同属“华夏”群体;另一方面,其亦可通过同一地域的关系与塞内蛮夷结盟、通婚来刻意“蛮夷化”以寻求脱离于“华夏”之外。(39) 三、有差别的“政区” 在天下型帝国之内,“中国”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而在“中国”之内仍有各种“核心”、“边缘”之分。冀朝鼎先生曾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认为“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40)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主张中国任一区域内部都有“核心区”与“边缘地带”之分,而“区域性核心区”的形成无不与当地经济的发达密切相关。(41)鲁西奇先生指出冀氏模糊了“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的差别,认为如果国家不能有效支配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资源”,使之转化为“统治资源”,那么所谓经济发达地区就不会成为国家政权所依赖的基本经济区。他还指出施氏所论核心区首先应是经济核心区,然后才成长为政治核心区的纰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核心区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核心区。在此基础上,其以“核心区”概念来指代那种历代王朝据之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并认为不同层次的政区都拥有各自层级的“核心区”。(42)抛开是否为政权提供统治资源不论,冀氏“基本经济区”所指实际上是全国性的经济核心区,施氏“区域性核心区”则是指区域性的经济核心区。而鲁氏“核心区”因是帝国及其各级政府维系辖域统治之根本,为与其他类型核心区相区别,笔者姑且称之为“统治核心区”。 具体到秦汉,在全国经济核心区方面,冀朝鼎先生指出:“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黄河的河南—河北部分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整个两汉时期的主要(漕粮)供应基地”。(43)在全国政治、文化核心区方面,卢云先生认为:“秦与西汉时代政治中心与文化重心分别在渭水流域与齐鲁地区……而东汉时代则各自西迁东移,汇合在全国的心脏地带——洛阳周围地区”。(44)在全国统治核心区方面,鲁西奇先生认为秦、西汉的关中,东汉的洛阳周边地区先后担当过这一角色;在不同层级的统治核心区方面,一般而言,秦汉各级政区治所所在地通常聚集了该区多数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资源,其当之无愧为所辖地域的统治核心区。当然,受诸多因素影响,亦有例外,如鲁先生就分析指出东汉荆州的统治核心区为南阳郡而非荆州刺史所在之南郡。(45) 秦汉时期,因距离各类、各级“核心”远近的不同,各政区在全国或各级区域内的相应地位也会有所差异。如前汉时期的三辅、后汉时期的三河均因都城所在,政治地位在他郡之上。两汉时期,其他地方郡守常因功绩卓越擢守三辅或三河,以示褒扬。再如,“(韩)崇迁汝南太守。诏引见,赐车马剑革带。上仍敕崇曰:‘汝南,心腹之地,位次京师。’”(46)汝南“心腹之地”的地位显然是因紧邻京师洛阳而获得的。这种地理关系恰好又与其“位次京师”相一致。此类事例均表明政区距离“核心”越近,其地位也就越高。这应当是秦汉社会的常态。 从秦到东汉,各类“核心”都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转移。受此影响,各政区的地位也因距离“核心”远近的不同而出现了某些变易。如两汉时期的凉州便是如此。东汉时期,作为西汉重要兵源之地的凉州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屡遭放弃之议,境内各郡多次内徙或省废。卢云先生认为这与当地远离政治中心(洛阳)有很大关系。(47)廖伯源先生亦指出:“西汉建都长安,政治中心近西北边塞,故加强防御……光武定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又有弃凉州之议。”(48)西汉定鼎长安,于凉州为近。在与匈奴敌对,战火狼烟甚至直抵甘泉、长安的形势下,能够屏卫关中且为战争提供充足兵源的凉州当然为汉廷所重视。东汉建都洛阳,凉州悬远,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自然不若西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南匈奴、先零羌分别在并、凉二州叛乱,大将军邓骘以军费紧张、无力两方同时作战为由,主张放弃凉州,专事并州。其以补衣相喻:“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49)然依其所言,在遭遇“两无所保”的局面时,被放弃的却是凉州。这显然表明对东汉政权而言,并州要比凉州更为重要。而现实的确如此,因为相比凉州,并州更为靠近政治中心洛阳。 由上述可知,秦汉“中国”内部有着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核心”与“边缘”。因距离各类“核心”、交通网络之远近及受各种偶然性因素影响,各政区在帝国或各级区域内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这些地位还会随着各类核心的移动而产生变化。这表明无论是在横向空间还是纵向历史上,秦汉各政区在国内的各种地位都会参差不齐。所谓“万里同风”、“远近如一”只能成为一种理想或口号。 在所有这些差别中,内郡与边郡的差异最为明显且最能引起时人的关注。秦汉时代,内郡往往被视作国之“腹心”,而边郡则经常被斥为“无用之地”。(50)这是因为:第一,在地理位置上,内郡多位于或靠近全国性的各类核心区,而边郡则处于各种边缘地带。第二,在融入帝国进程上,内郡一般是七国旧地,而边郡则多为帝国扩边所新置。内郡是秦汉帝国立国之本,能为帝国统治提供更多的经济、人才资源,自然也更受重视。第三,在族属结构上,内郡是编户齐民最为集中的地域,而边郡则多是内属“蛮夷”。“天下”人群既以编户为核心,其所处地域自然更为重要。此外,就连边郡最为重要的军事职能也是为内郡服务的。 在影响边郡国内地位的所有因素中,“蛮夷”所居显得尤为特殊。在汉代,“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等思想不仅在处理边疆、民族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社会中相关地域华夷身份的判别。正因此类思想的存在,人们总是刻意提及边郡原为“寇虏之地”(51)或蛮夷旧地的历史,并以此塑造边郡现实与记忆中的“边缘”意象。这样,“蛮夷”所居甚至原为“蛮夷”所居便不自觉地将边郡在国内的地位拉低了下来。 边郡与内郡地位之差异,可通过汉代诸多“弃边”举措或言论而彰显无遗。两汉时期,每每边疆遭受危机时,“弃边”之议就会随之而起。四百多年中,凉州、朔方、沧海、益州、珠崖、儋耳等地都曾被提上过放弃议程,有的最终付诸实施,如珠崖郡等。而这些被放弃或拟放弃之地无一例外都是边郡(州),表明边郡在整个塞内“中国”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之内,哪些地方应当固守,哪些地方可被放弃,贾捐之曾有明言。汉元帝初元年间(前48-前44),因珠崖郡内连年发生叛乱,捐之上奏主张放弃珠崖,其在对策中提到:“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52)此可视作他为全国重要区域划定了一个大概范围。而同时满足“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此三项条件的地域无疑多是汉人聚居、九州之内、春秋旧地的汉朝内郡。 前有提及,秦汉“天下”以徼内“中国”为核心,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帝国会放弃拓边或舍弃次要地域及人群来保障“中国”的利益。而“弃边”这一发生在“中国”内部的行为显然与其有着相同的意味。只是这时被放弃的是“边郡”,被保障的则是“内郡”的利益。由此,对于秦汉“天下”之构造,可概述为:“天下”以“中国”为核心,“中国”又以“内郡”为核心。 同样,与“天下”的层次性相似,“政区”的差异性亦能促成族群的构建及认同的变化。各种“核心”与“边缘”的存在及政区间地位的差异容易导致核心区、中心政区人群对边缘地带、次要政区人群的歧视。如将边郡视为“无用之地”而放弃本身便是一种变相的族群歧视。(53)此将引致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边缘人群通过提高所处地域在全国的地位而寻求融入“中心”,如秦汉时期边郡地带的社会精英都曾为促成本土的“华夏化”做出过不懈努力。(54)第二,边缘人群因“中心”的疏远而脱离“中心”,从而建构新的族群,形成新的认同。这在东汉后期西南夷、凉州地区的汉人中表现尤为明显。 ①参见卢云:《区域控制与历史发展——论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重心及其相互关系》,《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②参见刘瑞:《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参见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参见黎小龙、徐难于:《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⑤参见于逢春:《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⑥参见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参见尹建东:《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⑧《汉书》卷64下《终军传》。 ⑨黄晖:《论衡校释》卷19《验符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2页。 ⑩笔者改自《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其原文为“《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何休注曰:“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 (11)黄晖:《论衡校释》卷19《验符篇》,第842页。 (12)《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 (13)《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休注曰:“上有圣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在他看来,《春秋》以麟至寓意拨乱功成,天下进至太平。 (14)参见朱圣明:《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藏于河南大学图书馆,第19—23页。《汉书》卷93《佞幸传》师古注曰“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即塞、徼是汉代对边塞的不同称谓。本文为行文方便,下面将统一写作“塞内”、“塞外”。另,秦汉时期的“中国”一词有着多种含义,本文“中国”如不作特别说明均指塞徼之内由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 (15)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16)《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在给匈奴单于的文书中提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17)《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 (18)(元)陈澔注:《礼记》卷1《曲礼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9)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7《备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5页。 (20)尹建东:《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1)《汉书》卷28下《地理志》。 (2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6、227、229、110页。 (23)刘瑞:《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24)参见刘瑞:《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25)简文虽未提及父为秦人、母为臣邦人,所生子为“真”还是“夏”的问题,然在父权发达的秦国,秦母臣邦父所生子既可为“夏”,秦父臣邦母生子更当为“夏”。这在当时似乎不成其为问题,因而也不用特别解释。且简文明言“真”人或父母均为臣邦人或生于秦属之外,那么反过来,在此之外的情况均应为“夏”人。 (26)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27)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28)[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页。 (29)参见朱圣明:《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38页。 (30)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第5页。 (31)《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师古注。 (32)参见[日]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的试论》,《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版。转引自[日]岩井茂树著、伍跃译:《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的国际秩序》,《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33)参见[韩]金翰奎:《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研究》,一潮阁1982年版,第401页。转引自[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13页。 (34)参见《汉书》卷94下《匈奴传》。 (35)《后汉书》卷88《西域传》。 (36)《史记》卷120《汲郑列传》。 (37)史党社:《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第46页。 (38)参见朱圣明:《两汉“保塞蛮夷”考论》,《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9)关于汉代西南夷地区不同人群自我认同的变化动因及其特点,可参见朱圣明:《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40)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41)参见[美]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历史的结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42)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3)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78页。 (44)卢云:《区域控制与历史发展——论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重心及其相互关系》,《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45)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6)谢承:《后汉书》卷6《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47)参见卢云:《区域控制与历史发展——论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重心及其相互关系》,《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48)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49)《后汉书》卷58《虞诩传》。 (50)《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5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4《地广》,第208页。 (52)《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 (53)参见黎小龙、徐难于:《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54)笔者曾撰文探讨过秦汉时期蜀地精英为促成本土“华夏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参见朱圣明:《从秦蜀到晋蜀:时代变迁下的蜀人身份转变及认同危机》,《厦大史学》(第4辑)。事实上,这种由边郡精英所主导的边郡“华夏化”进程在秦汉蜀地之外的其他边地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