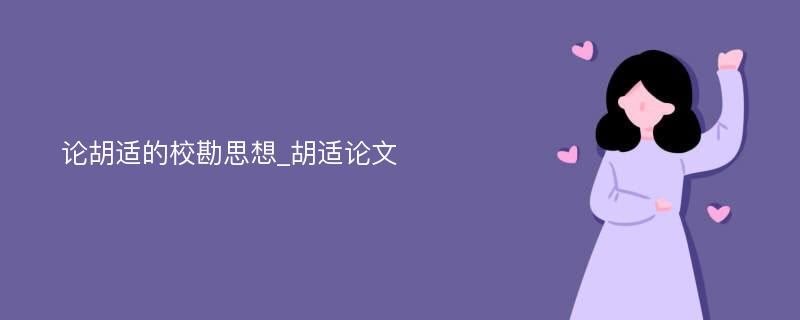
胡适校勘学思想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校勘,胡适先生说:“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1]我们认为,“用善本对校”也是胡适先生校勘学思想的核心。
所谓“善本”,清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说:其为“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即:足本、精本、旧本。[2]胡适先生同意此说。表现在他曾用蒲松龄墓碑刻文的拓本为依据,校正《山左诗钞》中的讹误,因为该拓本无脱误。我们说,本古书中,“不讹不缺之本”实为难得,少许有点脱误者也同样可视为善本。关于善本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胡适先生指出,校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3]
所谓“对校”,汉刘向《别录》说:“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即用同书不同本相校。校书主要有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而对校是最基本的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关于对校的功用,胡适先生同意陈垣先生的看法,主要有两点:校书时,“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4]胡适先生又补充道:“此外,这个对校法还有许多功用,如缺文,如错简,如倒叶,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5]
校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书之原貌。要达此目的,胡适先生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用善本对校”,他进一步指出,具体来说,要做好三个环节的校勘工作:“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6]“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7]这三步校勘工作贯穿着胡适先生的校勘学思想。
1.发现错误
胡适先生认为,发现错误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主观发现,二是客观发现;古书致误之因也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书手在写刻时不经意造成的,二是由“通人”校书时凭臆妄改所致。由书手造成的错误容易被察觉。如《汉书·食货志下》:“钱金以巨万计。”《元典章》:“每月五十五日。”像“钱金”、“每月五十五日”这样的错误,读者一看便能察觉。这种不用对校就能发现错误,胡适先生谓之是主观发现错误。由“通人”校改产生的错误不易被发现。因为经“通人”校改过的本子大多文通字顺,读来顺口,虽有讹误,也多不会引起怀疑,也就不易被发现。由这种原因产生的错误大多要通过对校才能发现,其中有的必须用善本对校才能发现。如《南齐书·高帝上》:“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舌中血出,众疑行毒害。”明监本将其校改为“殷舌中出血”,汲古阁本将其校改为“殷言中出血”。二者校改皆能读通,读者若只见其中一个本子,未见另一个本子,便不会怀疑其有误。若将这两个校改本相互对校,便能发现二者不同之处。这说明其中之一有误,或二者皆有误,但为何误,尚不知晓,因为二者皆不是善本。若用该书善本宋绍兴蜀中重刊本与它们对校,即可发现此处作“殷亡,口中出血”。说明二者校改皆误,同时也说明原本也有误。这种通过对校才能发现错误,胡适先生谓之是客观发现错误。古书中的讹误一般都要运用这种方法来发现。
2.改正错误
校书改正错误是校勘的中心工作。一书由校改和辗转钞刻等后来产生的错误如果通过校勘都能得到改正,那么它的原貌也就恢复了。胡适先生指出,校书“改正错误是最难的工作”,[8]虽然有的错误不依据善本也不用对校可以进行改正,但更多的则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9]如前面例中说的“钱金”之误,不用对校就知应改为“金钱”。又如《老子》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善本帛书《老子》甲、乙两本此处均作“自今及古”。用此善本与其对校,便知应如何改正。还有“1”中说的依据善本能够纠正明监本、汲古阁本《南齐书·高帝上》的讹误,也是一个例证。胡适先生特别提醒大家,校书改错切忌主观,因为“主观的改定无论如何工巧,终不能完全服人心”。[10]所谓“主观改定”,是指不依据任何本子,全靠分析推理所进行的改定。这样的改定,因提供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读者怀疑也就在所难免。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厚借敛,意使令,无以和民。”清孙星衍在无本据依的情况下,将其改为“任意使令”。因其不能为自己的校改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读者怀疑其校改的正确性。清王念孙《读淮南杂志·晏子一》说:“‘意’字文义不顺,孙加‘任’字以释之,亦近于牵强。”1972年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墓竹简《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此处作“急使令”。证明孙氏推理校改“牵强”,王氏等人怀疑有理。当然,有的错误虽非经对校也能发现,但不用善本与其对校却不知为何误,也就无从改起。如上面说《元典章》“每月五十五日”之误,用该书善本元刻本与其对校,方知其应是“每五月十五日”。只有用善本作依据,通过对校才能更多更准确地改正错误。陈垣先生用善本元刻《元典章》对校该书沈刻本,改正其讹误一万二千条,补其脱文一百零二页,[11]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3.提供证据
校书改错必须为其校改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胡适先生指出,“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书的书。”[12]但是,不论根据什么本子,其共同特点必须是“不讹不缺”,即符合善本的这一个条件。因为一书多有几种本子,其中有些讹误几本都有且相同。如果校者不识,用其讹误来证明自己的校改,只能说明自己校改有误,这样的证据还不如不用为好。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四年闰月辛亥,车驾藉田。诏曰:……六(仞)[稔]可期。”点较本校勘记说,其证据是:“‘稔’据南监本、局本改。”[13]朱季海《南齐书校议》指出:“此用《大招》‘五谷六仞’之文,南监臆改,局本承其误耳。”校者因不识“六仞”之义,进行了误改,并用他本之误来证明自己的改定,只能说明自己的改定是错误的。所以校书取证应持慎重态度。又如,《战国策杂志·赵策四》:“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清王念孙校改“触詟”为“触龙言”。他在《读淮南杂志·战国策二》中说:其证据是“《汉书·古今人表》正作‘左师触龙’;又《荀子·议兵篇》注曰:‘《战国策》赵有左师触龙’;《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师触龙言愿见’。皆其明证矣。”王氏为自己的校改提供了三个证据,有一定的说服力。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纵横家书》也作“触龙言”,证明王改为是。
校书改错并非都能在其他文献中找到证据。胡适先生指出,若“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也可算是一种证实。”[14]校勘时从所校书中取证,也是常用的一种证实之法。如《韩非子·孤愤篇》:“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清顾广圻校此书时,在“其可以借以美名者”中“可”字前加一“不”字。其证据是,本书中还有一些类似他校改的句子。如“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读者多认为他言之有据,“不”字加得有理。
在实际校勘工作中,并非都有善本可供对校,因为有的书虽有几种本子,但都是普通本,有的书是孤本。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时校某书竟无任何文献可供参考,也无处取证。遇到这两种情况如何进行校改和取证,胡适先生指出,在只有普通本时,“最好的方法是排比异同各本,考定其传写的先后,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标明各种异读,并揣测其所以致误的原因。”[15]如《史通·烦省》:“议者苟嗤沈约[休文,梁人。](方括号中文字为注文,下同——著者)著《宋书》,衍[字子显。]著《齐书》。”该书另一本此处作:“议者苟嗤沈约[休文,梁人,著《宋书》。]萧衍[字子显,著《齐书》。]”该书这两个本子皆为普通本。清顾广圻通过用两本互相对校和分析研究后,提出了自己的校改意见:“苟嗤沈[约,字休文,梁人,著《宋书》。]萧[衍,字子显,著《齐书》。]”[16]他指出,此讹误主要是由正文、注文混乱所致。后人多认为顾校“后出专精”,对致误之因的分析也合乎情理。胡适先生还指出,当校书无任何本子可供参考和无处取证时,校者经过推理研究只好提出一个自己认为“最近理的读法,而标明原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据何种理由。”[17]这样校改,他认为,虽提供不出证据,但也不会有“大过”。如《列子·仲尼篇》:“孤犊未尝有母,非孤犊也。”清俞樾校时认为,“非”字前脱“有母”二字。其理由是:“古书遇重字多省不书,但于字下作二画识之,故传写脱去耳。”[18]他在无任何文献作参考时,提出了自己的校改意见,并说明了校改的理由。后人多认为其改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