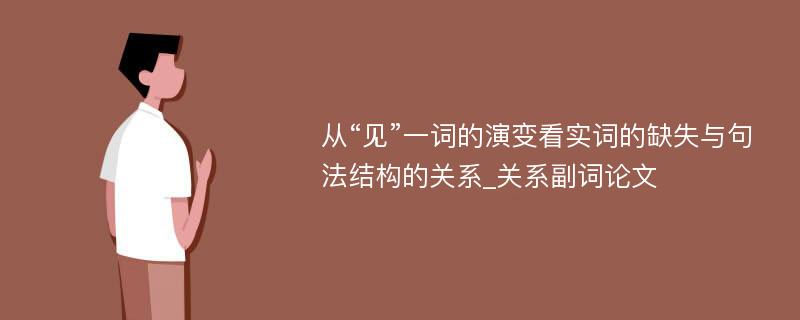
试论实词虚化与句法结构的关系——从“见”字的演变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词论文,句法论文,化与论文,试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汉语中,大部分虚词是由实词演变而来。至于如何发生演变,演变的原因及条件是什么,一般语法著作常以“实词虚化”一笔带过,未加深究。似乎实词的虚化仅仅是其词汇意义减弱的过程,仅仅是通过词义引申而产生的。这显然并不全面,亦不准确。笔者认为,实词虚化是词的性质变化。词的性质变化与句法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根本的联系。换言之,即句法结构的改变是导致实词虚化的根本原因。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将通过“见”字的演变过程,对实词虚化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见”字的本义是“看见”。《说文·见部》:“见,视也。”如:
(1)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易·系辞上》
(2)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王风·采葛》
“见”为及物动词,其后一般带名词宾语,组成结构V+O[,1](V为动词,O[,1]为名词宾语),如例(1)。宾语O[,1]亦可省略,但并不影响“见”的动词性质,如例(2)。在结构V+O[,1]不变的条件下,“见”的词义可以发生改变。如:
(3)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左传·庄公八年》
(4)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左传·恒公元年》
上面两例中,“见”字所处的结构仍是V+O[,1],未发生变化,但词义已有分别,例(3)记齐侯田猎。田猎则必见野兽,“见大豕”当属意料之中,故“见”义仍为“看见”。例(4)述华父督与孔父之妻不期而遇,事属偶然,记述的着眼点在“遇见”,而不在“看见”,下句“目逆而送之”才特写其“看”的动作情态。故此句中“见”当为“遇见”之义。
“见”由“看见”发展出“遇见”之义,是词汇意义的改变,是词义引申的结果。从词义引申的规律来看,一个词由甲义引申出乙义,是由于它们有一定联系。这种联系一旦被人们认识到,并带入词语中,就可能产生引申。在一般情况下,“看见”了某人或某物,也就“遇见”了此人此物。可以说,“遇见”是因,“看见”是果,此二义的联系是明显的。对此,古人亦有说明。《尔雅·释诂》:“遘、逢、遇、逆、见也。”郭璞注:“行而相值即是见。”《礼记·檀弓》:“遇于一哀而出涕”,又:“公叔禺人遇负杖入保者息。”郑玄并注:“遇,见也。”由此可见,“见”由“看见”向“遇见”演变是十分自然的。但这一变化仅仅是词义的变化,词性并未改变,因为其所处结构仍为V+O[,1],没有改变。有的书仅限于从引申方面探讨词义的虚化,认为由“看见”向“遇见”这样发展,就逐渐成为虚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方法论上是不完善的。我们应当进一步从结构方面进行探索。
(5)儒……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 《礼记·儒行》
(6)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墨子·七患》
上二例中“见”的词义为“遭受”,系由“遇见”义引申而成。因“见”后的宾语是不祥之事,具有感情色彩,故“见”也受其影响而带上感情色彩。但此二句中“见”字的变化不只是词义及感情色彩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原结构V+O的变化,因为结构的变化是词性变化的关键之处。例(5)中“见”的宾语由动词“死”担当,结构为V+O[,2](O[,2]为动词宾语)。例(6)中“见”的宾语是形容词“凶饥”,结构为V+O[,3](O[,3]为形容词宾语)。在一般情况下,“见”的宾语当是名词、名词性词组或代词,其内容是人或物。而(5)(6)两例中,“见”的宾语是某种情况或状态,性质也由名词改换为动词、形容词。我们知道,在句子结构中,谓语与宾语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组成一个结构段。如果宾语性质改变,必然对谓语性质有所影响,乃至使其变化。(5)(6)两例中“见”的宾语性质已变,但“见”仍为动词,充当谓语,其结构尚未明显变化,这是因为“死”是不及物动词,“凶饥”是形容词,它们均不能自带宾语。虽然作为动词和形容词,它们的语法功能本应是在句中充当谓语,但在上面例句的结构中,却失去其固有的性质特点,成为宾语。它们的语法功能未能显现出来,处于抑制状态,因而整个“V+O”结构处于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但是,O[,2]、O[,3]、代替了O[,1],结构中有了变化的因素。因此,整个结构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旦宾语的性质进一步变化,那么,这个结构的平衡态将被打破,而“见”的性质亦将改变。如:
(7)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 《韩非子·说难》
上例中“见”后的“下节”、“无心”均为动宾关系,意为“认为品节低下”、“认为不用心机”。“见”与它们所组成的结构段,已不再是V+O的形式。这首先因为,原当属宾语的“下、无”此处作为动词而自带宾语。在句中,它们的动词特点和语法功能通过支配宾语而呈显著状态,不再处于抑制状态。由于“见”后本应出现的宾语性质改变,故原V+O结构的平衡状态就被打破。其次,“下”、“无”的宾语“节”、“心”是主语“游说者”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这样,“下”、“无”虽在语法结构中直接支配“节”、“心”,但主语“游说者”也作为其语义指向,受到间接支配。由此可知,主语“游说者”并不与“见”字发生直接关系,并不发出“见”这个动作,而是与“下”、“无”相关联,可见“下”、“无”已在句中处于谓语地位。通过分析可以肯定,该句中“见”字与其后面部分所组成的结构已不再是“V+O”,而是“(R)+见+V+O[,1]”的新结构段(R为受事主语)。这种结构段,可以看作是“见”字插入了“R+V”结构中,担负着表示被动的意义。“R+V”结构一般是意念被动句,如:
(8)厉公弑。《国语·晋语》
(9)被窃钩者诛。 《庄子·箧》
因此,当“见”字处于此结构中时,其后是带宾语的动词V,“见”字的实词义弱化,在整个结构段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该结构所表示的被动意义便加在“见”上,使它产生了表示被动的语法作用。至此,“见”字由动词到助动词的演变就基本完成。
在古代汉语中,类似例(7)“R+见+V+O[,1]”结构形式的句子很少,它只是“见”字性质转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难怪杨伯峻先生仍把此句中“见”字看作谓语,认为它表示“被认为”之义。①从理论上讲,这种结构形式只能是演变中的过渡状态,不可能长久保留。因为在被动句中,谓语必须是及物动词,而形式的主语在意义范畴中,又是动词谓语所支配的对象。因此,被动句中动词谓语一般不能带宾语,这是由句子形式与意义的矛盾所决定的。例(7)中动词“下”、“无”均带宾语,与被动句一般形式不符,故其形式不可稳定,宾语O[,1]很快就会失落,而与一般形式趋于一致。例(7)的结构形式虽然少见,且不稳定,但它显示出“见”字由动词向助动词变化中结构所起的作用,对研究“见”字的演变很有启发性。
“见”字演变为助动词后,用于被动句谓语之前,表示被动的语法意义,组成了新的结构:“见[,1]+V”(见[,1]为助动词,作状语),如:
(10)盆成括见杀。 《孟子·尽心下》
(11)厚者为戮,薄者见疑。《韩非子·说难》
“见”的演变并未到此为止,随着句法结构的变化,“见”又逐渐产生了指代副词的性质。如:
(12)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朱)博见谓曰……。 《汉书·朱博传》
(13)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 《论衡·知实》
(14)唯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刘琨《扶风歌》
(15)虎贲谁见惜,御史讵相携。 庚信《乌夜啼》
有人不明白此类句中“见”字的性质及作用,把例(14)“不见明”解释为“不见得英明”。②但“不见得”乃是唐宋时期的习语,一般用于口语。如:
(16)看文字都恁地迟疑不决,只是不见得道理分明。 《朱子语类·卷120》
以后世口语释前代文言,是不恰当的。例(14)中“见”指代“李陵”,“不见明”意为“不了解他。”例(15)中的“见”字,有人以“被动语”为释,③亦显属误解。此“见”系指被虎贲射伤之“乌”,若解为被动,恰与原意乖违。例(12)的“见”指代“文学儒吏”,例(13)的“见”指代“论事者”。它们在句中所组成结构仍是“见+V”,但“见”的性质已不是表示被动的助动词,而是有指代作用的副词。因此,它们实际上已形成新的结构形式:“见[,2]+V”(见[,2]为指代副词,作状语)。
“见”的指代副词性质是如何产生的,对此,吕叔湘先生曾经论及。他认为古汉语中有两种被动句式,即“R见V于A”式与“R为A所V”式(A代施事者,R代受事者,V代动词)。两者揉合,于是又产生了“R为A所见V”式。再由此式删去“为……所”,成为“A见V”式。“为……所”一增一删之间,施事之词已由后移前,而“见”字遂发生指代作用。④
吕先生之论述涉及到词性变化与结构的关系,但其论述尚可商榷。“R为A所见V”式是被动句式,删去“为……所”后的“A见V”式则是主动句式。这一删,不仅原句结构产生变化,而且施事与受事的关系发生转变,原句意义也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语言历史中,这样的突变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既然“R与A所见V”式是由被动式“见……于”和“为……所”组合而成,那么,删去“为……所”之后留下的“见”仍应表示被动,又回到“见……于”这种被动结构中,怎能说明“见”就表示指代了呢?一种语言结构的产生,总是有其表达上的需要的。“R为A所见V”式这种叠床架屋式的被动句式,究竟在语言历史中有何意义或作用呢?按吕先生之说,似乎它的产生,只是为使“见”字的性质发生改变而产生指代作用,这是欠妥的。因为“R为A所见V”式是人为地把“见……于”式和“为……所”式揉合在一起,如果说这种人为地组合新结构是用来改换某个词的性质,是有明确目的的语法手段,显然缺乏依据。吴金华同志曾经考察过“R为A所见V”式,指出“‘为……所见’式的出现,似与当时人们讲求语音节奏有关。……与‘为……所’等被动句式相比,新兴的‘为……所见’式自有其独特的功用:‘所见’二字与双音节V相应,可以求得音节上的和谐。”⑤可见,“R为A所见V”式与“见”字的指代作用没有直接关联。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它们各自产生的时代证明这个问题。吕先生所举“R为A所见V”式三例,均为魏晋以后之例。吴金华认为“它的用例,最初出于东汉后期的文献。”⑥但是,“A见V”式(即见[,2]+V式)在东汉初已有用例,前所举例(12)(13)即是。又如:
(16)(平当)所过见称,奉使者十一人为最,迁丞相司直。 《汉书·平当传》
(17)王成……所居民富,所去见思。 《汉书·循吏传》
上二例中,“见”分别指代“平当”、“王成”。既然“A见V”式早于“R为A所见V”式,怎能说前者由后者演变而来呢?
笔者认为,“见”字的指代副词性质来源于被动句式,但并非经过“R为A所见V”式这条途径,而是发端于主语的省略。我们知道,古汉语中省略句很多,省略现象也比较复杂。句子的主语可承前面句中的主语而省,也可承宾语或定语而省。虽然作者对省略的主语是明确的,但读者却往往根据自己对句子的理解去补明主语。这样,虽然原句表层的语法结构未变,但其深层的语义结构已有了歧解。如:
(18)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 《史记·酷吏列传》
“见惮如此”的主语可以承接前句宾语“郅都”而省,“见惮”则为“被(匈奴)畏惧”,其结构为“见[,1]+V”;若承前句主语“匈奴”而省,则此句成为主动句而非被动句,“见”字失去表被动的作用。既然“见”失去其原有作用,那么按一般规律,这种情况下的“见”字当失落。但及物动词作谓语的句子,全句主干结构应是“A+V+O”(A为主语),而上例中谓语是及物动词却又不带宾语,成为“A+见+V”式,语义结构不完整,缺乏宾语O的内容。另一方面,“见”字保留句中却又失去原有表被动的作用。这样,“A+见+V”式就成了既有多余成分又有残缺部分的怪异结构。因此,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由于整个语义结构完整性的要求,多余的“见”字取得了替代缺少的宾语而指代受事者的作用,形成“见[,2]+V”结构。因此,“见惮”在这种语义结构的规定下,表示“害怕他”之意。上面这类具有歧解结构的句子,在东汉逐渐增多。如:
(19)根虽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虽切,犹不见从。 《汉书·张禹传》
(20)以尚书授太子,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 《后汉书·张酺》
(21)太子家时为奢侈物,未尝不正谏,甚见重焉。 《后汉书·张酺传》注引《东观汉记》
一般地说,语言是趋向于严密化的,语意不明确的句子将逐渐被淘汰,但上面这类歧解结构的句式由西汉到东汉是从少到多,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新结构“见[,2]+V”已具有生命力。因为新结构复现频率的加大,是其定型的必要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探知,虽然上述例句是歧解句式,但人们已在其深层语义结构中,把“见”字作为宾语内容看待,“见”字的指代性质也就逐渐产生并突出。如:
(22)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 《汉书·循史传》
上例中“辄亲见问”一句无主语。由整段记载来看,是连续叙述“孝宣”的行为,则主语当为“孝宣”,句中情态副词“亲”也表明如此。故此句虽为省略句,从形式上看,主语可是“孝宣”,也可是“刺史、守相”,成为“见[,1]+V”,或为“见[,2]+V”的歧解结构。但由于内部语义结构的制约,主语限定为“孝宣”,而“见”字指代“刺史、守相”的意义及副词性质亦被确定。
作为一种新结构的定型句式,仅有深层语义结构的定式尚不完备,其表层的语法结构当与深层的语义结构一致,避免歧解,才能最后定型。因此,“见”字用在完整的主动句中,即构成“A+见+V”式,才成为一种定型句式。“见”字的指代性质也在这新结构的定型句式中得到最终确定。前所举例(12)(13)(14)(15)均为定型句式。
“见”字产生指代性后,最初用于叙述语中,指代第三人称。后来词义范围扩大,可指代第一人称,常用于对话与书信之中,如:
(23)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汉乐府·董娇娆》
(24)生孩六月,慈父见背。李密《陈情表》
“见”的这种指代用法日益增多,成为其主要用法。而指代第三人称的用法始终未能居于主流。虽历代均有用例,但毕竟少见。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见”由助动词演变为指代副词后,它实际上指代了原来被动句中的主语,这个主语在意念上即指第三人称。但在唐代以前,第三人称代词不作主语,“上古有一个‘彼’字可用于主语,但是‘彼’字的指示性很重,又往往带感情色彩,并不是一般的人称代词。”⑦因此,“见”虽指代主语,表示第三人称,但受上述语言习惯的影响,其地位并不稳固,容易发生变化,故其他指代用法应运而生。
其二,“见”字的第一人称指代用法大量出现而成为其指代用法的主流,与古人用语的礼貌式有关。王力先生认为:“汉族自古就以为用人称代词称呼尊辈或平辈是一种没有礼貌的行为。自称为‘余’、‘我’之类也是不客气的。因此古人对于称呼有一种礼貌式,就是不用人称代词,而用名词。”⑧但使用名词有时不免受到局限,尤其在诗句中。“见”字产生了第一人称指代作用,正好适应这方面的需要。在古人看来,“见”字与“余、我”等词是不相同的,但它又可起指代作用,同时又具有客气自谦的意味,因而被广泛使用。这是汉民族文化心理作用于语言所产生的结果。
“见”成为指代副词后,也可指代“自己”,这是由对话中指代“我”的用法扩展于叙述语而形成的。如:
(25)(吕布)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董)卓几见杀之状。 《后汉书·吕布传)
(26)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快。 《后汉书·朱浮传》
(27)有獭得嘉鱼,自谓天见怜。 刘禹锡《有獭吟》
由于“见”主要用于对话中,少用于叙述语,因此这种指代“自己”的用法很少。
“见”字偶或也指代第二人称,如:
(28)武帝曰:“世间流言,我已豁怀抱。自今以后,富贵见付也。”崇祖拜谢。 《南史·垣崇祖传》
“见”字的指代作用产生之后,以指代第一人称为常用,其他用法表现出“见”的泛化现象,但它们只处于次要地位,未成为主流。因为虚词的发展是有系统性的。一方面,它会随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将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进行自我删约。否则,虚词系统将不断膨胀,以至成为混乱的无序状态。我们知道,在“见”字产生指代作用之前,指代副词“相”早已使用,它既可表示“互相”,又可偏指第一、第二、第三人称。若“见”字的指代范围再与它完全重复,则是累赘多余的。因此,虽然“见”有泛化现象,但受虚词系统自我制约规律的限制,其他用法逐渐消失,而保留其第一人称指代用法,常用以与“相”对举,保持着指代副词的有序性。如:
(29)野老时相访,山僧或见寻。 庚信《卧疾穷愁》
(30)吾相遇甚厚,何以见负?《晋书·罗企生传》
“见”成为指代副词后,首先产生第三人称指代作用,其后第一人称、己称、第二人称用法相继产生。但无论指代范围如何变化,其“见[,2]+V”的结构形式并不发生改变,因而“见”的指代副词性质亦不改变。
“见”字除了由动词演变为助动词和指代副词外,到了中古时期,又发展为助词。如:
(31)此身南北老,愁见问征途。王安石《旅思》
(32)送君不惮远,愁见独归时。黄庭坚《放言》
“愁见”、为“愁着”之意,“见”是助词。
“见”本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其后带宾语,即使演变为助动词与指代副词,也处于动词之前。而作为助词的“见”却用于动词之后,这一性质及位置的变化,经历了长久的过程,同样与语法结构密切相关。
在先秦汉语中,要表示一个动作行为的发生及其结果,常用两个动词分列于两句来表示。如:
(33)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左传·僖公五年》
(34)及战,射共王,中目。 《左传·成公十六年》
“袭、灭”、“射、中”均是动作与结果分开说明。这种情况后来有了发展,即直接将表动作与结果的两个动词组合在一起使用,形成动补结构的动词。如:
(35)余姑翦灭此而朝食。 《左传·成公二年》
(36)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见”作为动词,其词义中具有表示结果的特点,即表示“看到”。因此,在先秦时,“见”也开始用于动补结构的动词中,作为后一语素,表示结果,组成“V见”结构。如:
(37)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 《左传·哀公二年》
(38)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 《孟子·尽心上》
(39)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 《孟子·尽心下》
“见”的这种组合方式,从汉代开始大量使用。但它在这类“V见”动补结构中,虽然位置处于动词之后,但其性质仍为动词,而非助词。这是因为:第一,这只表示“看”的结果,词义没有变化,程度亦未衰减。因此,它一般只与表示“看”的动词组合。如:
(40)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41)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 (同上)
(42)项王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 《史记·项羽本纪》
第二,此时的“V见”结构动词,其后的宾语一般是名词、名词性词组或形容词性词组。这样的宾语与“见”原本单用时的组合关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不会影响“见”的性质而使其变化。
到了唐宋时期,“见”的词义有了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动作行为的范围扩大,即由“看见”表示“听见”。如:
(43)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李白《上李邕》
(44)从兹耳界应清静,免见啾啾毁誉声。 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山居重题》
(45)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 王维《赠裴旻将军》
“见”能由“看见”扩大为可表“听见”,一是因为词义的“同感引申”,即不同的感官在所产生的感觉中有近似或关联之处,因而引申出新义。⑨如“闻”本表“听见”,后引申为“嗅”。二是因为“见”有“遇见”之义,如前所举例(4)。而唐宋时期,表“遇见”义的“见”开始与“遇、逢”等动词组合,“见”在其中更重于表结果,而非“看”的动作。如:
(46)便辞父母,欲诣庵园,或于郊野之中,逢见维摩居士。 《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
(47)月底相逢见,有深深良願。 晏几道《忆闷令》
(48)遇见五祖下智皇禅师。 《祖堂集》
“见”由“看见”发展出“听见”之义后,由于词义的泛化,动作性减弱,因此它就进一步用于其他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没有什么实在意义。而动词后的宾语,也常常是动词性的结构。这样,整个结构变为“V+见[,3]+O[,4]”(见[,3]为助词,O[,4]为动词性结构宾语),其中的“见”成为助词。如前例(31)和(32)。又如:
(49)长吁解罗带,惧见上空床。 韩偓《春闺》
(50)东坡海上无消息,想见惊帆出浪花。 黄庭坚《和蒲泰亨》
(51)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簾儿低下,听人笑语。 李清照《永遇乐》
(52)谁信年时,老子情非浅。思量见,画楼天远,花倚夕阳院。 史浩《点绛唇》
(53)春日怪见难留住,撺掇元来却是他。 史弥宁《啼鹃》
(54)说与行云,且就嫦娥今夕。俄变见金蛇能紫,玉蟾能白。 刘克庄《满江红》
在“V+见[,3]+O[,4]”结构中,由于动词V不限于“看”的动作,故“见”也就失去表结果的作用;加之宾语又是一种动作行为,亦非一般“见”的对象。因此,“见”与前后动词及动词性结构相连,又不能表现自己的动词作用,就只能改变性质,成为助词。
当“见”的助词性质演变完成后,它在使用时更加灵活了,既可用于非动词的词后,也可带上非动词性的宾语,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见”的助词性质的成熟。如:
(55)我当初不合见擘口和你言盟誓,惹得你鬼病恹恹挂体。 《太平乐府·九·喻情》
(56)何时见,名娃唤酒,同倒甕头春。 周邦彦《锁阳台》
(57)兀谁可怜见我那里。 《董西厢》
(58)每日向长街上转,叫杀耶娘佛,没个可怜见。《汗衫记》
“见”由“V见”结构演变为“V+见[,3]+O[,4]”结构,导致助词“见”的产生,但并非所有“V见”结构都消失了。倒是相反,由于助词“见”的作用与几乎同时产生的助词“着”相近,在元代以后,助词“见”就逐渐消失,“着”排挤了“见”。而动补结构“V见”却一直沿用下来。如:
(59)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 《水浒传·楔子》
(60)鲁达看见挨满,也钻在人丛里听时,鲁达却不识字……。 《水浒传·第二回》
(61)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 《水浒传·第六回》
“V见”结构中还可插入其他成分。如:
(62)王观察就带了房主人,东西四下里去跟寻,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见。 《水浒传·第二回》
(63)我一地里寻官人不见,正撞着卖药的张先生。《水浒传·第六回》
在现代汉语中,“看见、听见、遇见、碰见……”等词仍在使用,表明了“V见”结构的稳固性。
从“见”字演变过程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实词虚化过程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词汇意义的变化,二是句法结构的规定。词汇意义的变化只是该词性质变化的动因,但非根本变化,它不改变原句的语法结构,因此单凭词汇意义的变化不能使一个词发生虚化。而句法结构的变化才是词的性质变化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即句法结构的改变强迫词的性质及语法功能改变,导致实词虚化。
二、实词在虚化过程中,词义程度减弱,而语法上的粘着性增强。词义越虚,粘着性越强。说明实词虚化的过程,也是该词语法意义增强的过程。如“见”作动词“看见”时,一般作谓语,但它之后可以不出现宾语,有时前面也可不出现主语,在结构上比较自由。但作为助动词时,它必须附着在动词之前,不可脱离。同时,整个结构表示的被动意义也附着在它身上,其语法意义大大增强。同样,“见”作为指代副词,也必须附着在动词之前。而且作为定型结构,“见”前还必须有主语,否则整个结构将出现歧解。这表明了虚词语法作用的重要性。
三、实词之所以会虚化,是有其表达的需要。虚化的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当虚词性质固定时,必定是一种新结构定型之时。
四、当某词产生虚词性质后,由于受虚词系统性制约,它仍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消失,如助词“见”被助词“着”排挤。如果此虚词具有多种作用,它将通过自身组织力量进行调整,突出其主要作用,以保持虚词的有序状态。如指代副词“见”最终主要用以指代第一人称的调整过程即是。
注释:
①杨伯峻《古汉语虚词》第86页 中华书局。
②王景霓等《汉魏六朝诗译注》第158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③谭正壁、纪馥华《庚信诗赋选》第193页 古典文学出版社。
④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见字之指代作用》 商务印书馆。
⑤⑥吴金华《试论R为A所见V式》《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
⑦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65页 中华书局。
⑧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75页 中华书局。
⑨参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1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