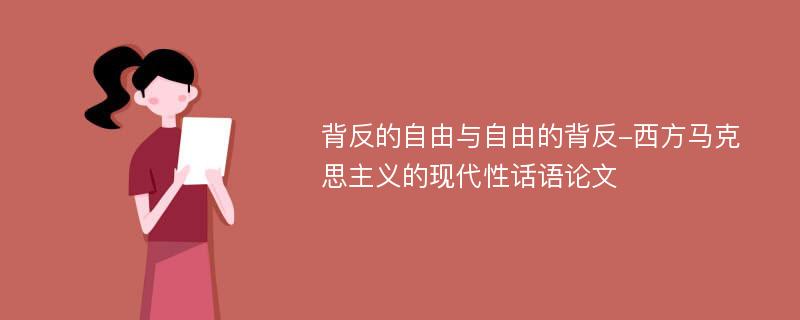
背反的自由与自由的背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话语
韩 秋 红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探讨既秉承了康德先验“自由”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形而上理想追问,又以下沉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现实生活的方式展示出自由的尘世境遇,显示其独树一帜的理论风格与批判特质。与马克思对自由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选择退回到哲学文化层面进行理论批判,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做出自我解读,以及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付诸变革实践上的不彻底性,成为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相距甚远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现代性批判
自由作为横亘西方哲学命脉、绵延古今的核心话题,不仅构成了古代与近代哲学的重要论域,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核心术语。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自由的现代性发展置于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加以拷问,既保留与继承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思想特质和价值关怀,又生发出作为20世纪所具有的现代性批判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品格。与作为现代性态度纲领的康德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仅仅驻足于“先验”世界的自由思辨,而是在继承与发扬自由意志和理性自由的人文精神与终极价值之外,追索与关照了朴实可感的尘世生活,从“天国”回到“人间”。但当其将自由的思考贯穿于物化批判、生态反思、性别歧视、消费异化以及城市空间等生活场景中——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相比——其都在揭露资本逻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上暴露出鲜明的无意与无力,无法开出切实可行的“治病药方”,呈现出在救渡自由困境的现实路向上的不彻底性与乌托邦色彩。
一 、“理性 ”与 “自由 ”:西方哲学为现代性批判开显的核心概念
谈论现代性,不能不讲到启蒙。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转向中出场的一段引人瞩目的思想运动,是以启蒙哲学为人类提供的理性、自由、主体性、合理性为时代语境与批判根基的。可以说,启蒙哲学孕育了现代性的发展。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们来看,被赞誉为“现代性态度的纲领”[1]429的康德则是在先验的范围内呈现了对现代性的思辨式理解,即对“自由”与“理性”的先验式探讨成为此后思想家们聚讼纷纭的关切与焦点。
卡西勒曾这样描述:“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共同]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为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2]3-4可以说,“自由意志”与“理性自由”作为启蒙与现代性的代名词,为康德开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提供了理论起点。康德指出,所谓启蒙,就是使人摆脱加诸于身上的蒙昧、不成熟状态,“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3]24。而“理性”与“自由”之于现代性开启的决定与基本精神价值的确立,也是通过“先验性”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与(理性)自由为“物自体”或“不可知物”,也即为信仰预留与划定地盘,来确认与完成的。
从“知性为自然立法”来讲,康德以一套先验逻辑规则系统对自然界与科学知识规定与划界,以此证明人类理性的天赋来源与自由运用。依据康德的观念,对自然界的肯认与质疑的权利是人类先天具有的,所以对于外部现象世界提供并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材料,我们能够自由地运用“直观的公理、知觉的预测、经验的类比与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4]53加以体认。对这些源自理性的先天逻辑规则的自由运用,一方面确保与证实关于自然的认识是从感性判断、知觉知识不断上升为普遍、客观与必然——正如“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于感性,由此进到知性,而终于理性”[5]261,另一方面则坚定表明了“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的理智中”,“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的规定”[6]92-93。所以在这里,康德以“知性为自然立法”的方式体现了知识的获取与对自然界的科学认知存在于理性自由的先天根据之中,表明了对自然的认知是人类自由地行使天赋理性的展现,以此呈现出其对“理性”与“自由”的先验式考察与思索。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此以人类理性自由与自由意志的运用将自然知识开掘出来,可是科学技术与自然知识得到开显并开启人类文明的历史旅程,却是以不断吞噬人类自由与理性的姿态登场、呈现。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人类对知识的盲目崇拜与科学技术的无度滥用僭越了其存在范围,人自由地创造的科学技术与自然知识以不断异化的变体带给人以不自由,直接导致了对人类“自由”的囚困与宰制。所以自由的“背反”所带来的生存困境,就此成为此后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执行统治功能作为批判与挞伐对象的重要原因。
从康德理性自由地追问“物自体”与“不可知物”,从而为信仰预留地盘来说,人类依然能够自由地保留形而上的精神信仰而不是面对“不可知之物”望而却步。对于“自由”,康德更多是以“否定性”的表达来陈述对当前事物不够成熟、不够理想,“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是如何”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对自由的理解是在不受限制的否定中不断朝着“理想性”方向前进。所以“‘自由’的‘理想’不可能是一个经验的‘概念’,不可能转化为经验的‘对象’”,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直接对应的感性材料,“不可能提供经验的‘直观’”[7]34,从而自由不可能也不会是“现实的”,而只能是“先验的”。此外,尽管康德以理性自由对现象世界(自然界)进行了知识的划分与界定,但他依然认为这些能够通过材料直观而获得认识的外部世界只是表层、表面与现象的东西,在他们之后一定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的、更为根本的“应该是”什么的东西,而这个“应该是”的东西却是无法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获得的——因为它必须“源出于(理性)‘自由’,它只是提供对感性、现存的东西说‘不’的权利,至于到底‘应是’些‘什么’,它不过问”[7]33。由此,正是坚持对这一“应该是”却又“不可知物”的“自由”的追问,康德以“自由者”的方式对这一更为完满、更加根本、更为高级、只会对其他事物进行否定、自身却必为“绝对”的“物自体”加以体认,并强调关于“‘物自体’的问题,只有‘自由者’(不受限制者)才提得出来”,“只有‘自由者’才会保持住‘否定’的权利,才会有‘本应是什么’的‘理念’(理想),才会‘悬设’一个‘目的’(目标),而不至于放弃对现存事物的追问”[7]34-35。显然,康德在这里是以自由的追思并认定这些“不可知”的“物自体”绝对存在的方式将其归入“思想”与“信仰”领域,以此形成对直观到的自然科学知识的鲜明划界。与此同时,康德进一步强调,“物自体”作为“知识”的终止,却是“思想”的开始,即“物自体”在直观经验与现象的知识界不能被把握,而只向那些能够不断否定并不断追问的“自由者”显现。所以从“物自体”不是经验世界的来客,不是“人的经验世界的‘居民’从而不会服从人为这个世界制定的法则”[7]35来说,康德是以保留信仰并为其预留领地的方式证明了人所拥有的自由是以“先验”的方式存在并发挥效力的。
卢卡奇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全面渗透、掌控人的肉体与心灵的批判,对合理化、专门化的商品生产吞噬总体的人的反思,以及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恢复、重拾并转化为真正的实践,呈现出对处于资本主义“物化”围攻下的“自由”的现实性体认。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越来越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合理化的商品生产把时间降到精确测量与标准划定的空间上,并通过“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8]153的填充,使人们的劳动与人格全部吸纳到异化状态之中,从而为物化体系的建立奠定稳固的现实基础。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里”[8]161。由于这一结构性的物化事实使“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并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8]151,商品关系便作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使人的肉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劳动与创造都“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8]168,使无产阶级失却了自由之身、阶级意识与自由变革社会的力量。所以面对由“商品拜物教”编织起的不自由的“物化”囚笼,卢卡奇认为,要戳破“物化意识”,粉碎“物化”现状对人的自由存在的宰制,将已经“被加入到异己系统”而堕入“物化”深渊的人解放出来,从而复活被资本主义社会毁灭了的人,就要重新唤醒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客统一体的阶级意识,因为“它的阶级意识在实践上变为现实”[8]296,“这种意识的突出的实践本质就表现为,相应的正确的意识意味着他的对象的改变,而且首先是,它自身的改变”[8]297。只有无产阶级变革商品拜物教与物化意识、物化现实造就的“镜像”生活,重拾阶级意识与自由权利,才能真正恢复历史的主体地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具有重新赋予无产阶级自由,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合理化等等不合理化现实,最终走向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重要路向与真实力量。
式中:Di表示省域i的机场密度,Si表示省域i的面积,ni表示省域i内的机场数量(本文中机场为定期通航机场,下同)。
二 、“天国 ”与 “人间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独特张力
除此之外,列斐弗尔在早期日常生活批判中对消费异化的思考,晚期转向对空间批判的反思,都对消费主义吞噬劳动者自由意志与自由生活、空间整合背后隐匿的资本追逐剩余价值而强行侵占、剥夺他人自由发展空间的资本逻辑,加以深刻批揭与有效揭示。更为重要的是,列氏关于日常生活异化与自由遭遇现实困境的深刻反思不同程度地对此后大卫·哈维关于“空间正义”与自由的构想,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吞噬自由的问题探讨,都敞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问题上独树一帜的理论特质。
康德在先验自由中为作为现象的知识界与作为不可追问的信仰领域各自划定了界限并保留合适地盘,使人们关于知识的追求与关于信仰的追问都在自身的先验自由中能够找到合理答案。这是因为,康德在对“我能够认识什么”的回答中揭示“自由”及其陷入背反的现代性问题,以对“至善”的追问完成其关于“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的探寻与统摄中进一步揭示“至善何以可能”的依据依然存在于“自由理性”之中。在康德那里,“至善”即意味着基于自由原则的德性与基于自然原则的幸福在精确的比例与综合的分析中所达至的匹配与契合。由于康德在“我能够认识什么”的第一个问题中已经通过“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论断将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研判理据归因于先验理性,因而关于自由原则与自然原则、德性与幸福及其关系的追问,就变成了在理性存在的范围内如何反思自由理性与意志自由的问题。为此,康德首先指认了人的自由意志由于受到经验世界或感性生活因素的掺杂、个体生命有限性的干扰而无法成为“纯粹”的自由意志,并完成“至善”的现状,而只是呈现为一个在无限努力与趋近的过程。为了从有限的生命个体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打造“纯粹”的自由意志以保证“至善”的达成,就需要在时空的绵延与生命的延展中造就灵魂的不朽与敞开生命的无限曰为“至善”。康德关于“至善”的追问借由自由意志通达灵魂不朽,灵魂不朽的设定显然只能由理性自由来完成,因而对于“至善”的追问依然回归到人类理性自由之中。其次,在探讨德性与幸福的关系时,康德反思了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葛学派的同一律式探讨,认为只有体现二者实际存在的因果关系的综合判断才是真实有效的。而综合判断并非先天判断,先天判断只能来自全知全能的上帝。当说“全知全能的上帝”时才即是综合的(全知全能)又是先天的(上帝),先天综合判断才是可能的,认识才是可能的,至善也是可能的。康德在此对上帝的引入实际上意在强调其不仅源出于人的先天自由意志,更要保持与预设其存在的人的自由意志相符合,因而无论上帝作为一种道德的保障还是补偿,都会将对德性、幸福与自由的坚持复归于自由理性,至高无上的上帝或神的出现终究是为了推出与证明人自身的理性自由。由此,“通过意志自由来实现至善,乃是一种先天的(道德的)必然”,康德所谓“至善”是一种纯粹在人的祈向中的价值极境——乃意志自由所必致;有意志自由才有对“至善”的“期望”,有意志自由才有对“至善”这一实践模型的预设。康德关于“至善何以可能”的追思以及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通过悬搁知识为信仰预留地盘的诸多探索,都以“何以可能”的否定方式的否定之否定而回溯于肯定在“先验自由”的理论脉络之中。
从人类强行给自然植入的经济理性来看,资源不竭利用、扩大再生产与竭力鼓动消费的资本逻辑,已经成为经济理性宰制自然并囚困自由的最大共谋。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将自然列为征服对象并残忍剥夺其自由发展权利的惨痛事实,高兹批揭道:“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根本的增值。”[11]32-33显然,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无极限增长的假设之下是完全不顾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自由、全面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与经济理性完全不同,“生态理性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的手段”[12]32-33,去保持资源的节约、提高物质的耐用并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生态理性不仅“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当经济活动侵害了原始的生态圈的平衡或破坏了不可再生的资源”[12]16,“企业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更使“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价值都可以量化,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的”[12]116。由此,高兹在这里用生态理性使人直面生活世界本身,关注自然应有的自由发展权利与自身的扭曲存在状态,重识被经济理性遮蔽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不自由关系以及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重拾对自然开展合理互动的实践功能与自由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对工业文明社会“自由”病症的积极把脉退回到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思辨,忘却了马克思变革社会的根本力量——“实践”,“使其只是在理论层面的自拉自唱”[14]。从将“自由”置于“消费异化”的现代性批判来看,鲍德里亚将对马克思关于商品的“生产分析”转移到现实社会的“消费批判”。鲍德里亚指出,琳琅满目的商品——“印度的披肩、美国的左轮手枪、中国的瓷器、巴黎的胸衣、俄罗斯的皮衣和热带地区的香料”[15]2——与各式各样的消费场所、消费手段——购物广场、电视导航、信用卡消费、主题公园游乐场——完全地掌控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意识,使“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5]6。在对商品消费浸入“拜物教”式的崇拜过程中,消费者为商品抽象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外的另一种“符号”价值,并将这种“符号”指认为对商品本身的替代,即给予消费者一种别样意义的身份地位、欣赏水平与社会名望程度的有效标签。由此,鲍德里亚指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5]47。在这里,鲍德里亚不仅揭示了消费者在商品及其所抽象化的“符号”功能面前的虚假意愿、不真实消费行为与自由意志的丧失,更澄明了商品被抽象为“符号”后所实施的以“编码机制”对消费者意识进行牢固操纵与深度异化的隐匿功能。基于此,鲍德里亚从商品“符号”及其“价值意义”所共同造就的“物体系”中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典型特点:不仅是“在空洞地、大量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15]13,更是一个以充斥了种种虚假需求去侵占与剥夺人类自由的“牢笼”。鲍德里亚已经将“自由”从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经济根源分析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层面的符号学批判。这种从经济分析倒退到形而上的思辨使其距离马克思关于自由、解放、商品、劳动与资本的深度剖析渐行渐远,不能像马克思那样从生产实践、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表现形式”[16]47的商品置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这一“人类历史的真正基础”之上,通过“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17]31,力图“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18]11,从而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角度去解剖资本强行占据劳动力无偿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直击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而只能在关于“符号”“编码”与“拟像”“意义”的纠缠中迷失于真实意义的世界,徒增几分堕入虚无主义的危险。
笔者曾对清末民初东西部的新式教育做过比较研究,发现鸦片战争前后新式教育即近代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授首先是从东南沿海起步的。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为了推进其传教事业,设立了一些教会学校,[2]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后,教会学校又在这些城市相继设立。[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由最初的五口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到1875年,各地的教会学校总计有800所。[4]
从将女性置于歧视与宰制对象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地位来说,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以服务员、保育员、清洁工、迎宾员、护士、秘书、保姆、接待员等等服务性、背景型、衬托式的角色出现。女性主义学者普鲁德姆将这种女性社会身份指认为是“对女性和自然进行否定的一种主要形式,称为‘背景化’,也就是将她们处理成前台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功绩显赫和成果所必要的背景”[13]21。所以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里),女性作为背景理应为作为前台的男权中心主义服务,而男性至高无上地位的获得虽以此为背景与必要依托,却不容许背景因素的丝毫掺杂与摄入。对此,波伏娃进一步将这种对女性自由、平等发展权利的压迫、歧视与剥夺诠释为“成为一个好女人的悲剧,不仅因为其贫乏的生活和受限的选择,也因为成为一个好女人就意味着变成了一个次等的人。只要‘中性的’人类理想性格依旧被奉为圭臬,女性的传统角色继续被接受,那么妇女就永远被迫将自己视为低人一等,也要接受别人的看法”[13]26-27。所以普鲁德姆进一步提出应以“生态女性主义”的方式去改写一元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宏大叙事逻辑,以女性身份的必不可少、自由发展权利的积极彰显与重要功能的合理展现为人类故事提供多元主人公,塑造多维故事线索,敞开别样书写方式,力图将现代社会发展引向一个更加自由、幸福与完整的结局。
无论是“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还是“我可以期望什么”,康德的“自由者”显然只是先验理性世界中的“自由意志”,而当它走进经验世界中,又会呈现出一番怎样的模样?现代性以其纷繁多样的生活世界场景体征出与纯粹理性世界的隔岸对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理解既与康德握手言和,又分道扬镳。这不仅体现在其对“自由”的现代性批判秉承了西方哲学形而上理想的终极追求——从康德的先验“自由”中接过现代性批判的“大旗”——又展示出其对“自由”的审思从“天国”降回“人间”,在“先验”“思辨”的维度之外开显了“尘世生活”与“现实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在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发展中进一步理解“自由”与重构现代性。无论是对物化的批判、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揭示、对人性异化的展现、对女性问题的表白、对生态问题的澄明、对消费异化的重视、对空间生产的展现等,都紧紧抓住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这个叙事框架和问题阈,力图展现“自由”的现实性境遇,展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性色彩和建构性特征。
三 、“反思 ”与 “奠基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超越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从启蒙力图祛除却又必然堕入神话的辩证法中将人类与自然自由的失落揭示出来。启蒙以来的世界是知识、权力、科学技术、主体理性的挺立彰显与急迫应用,这一文明进程必然一方面向人类自身证明“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9]1-2,一方面又向自然宣示“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9]1-2。所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启蒙对人与自然自由的剥夺与深入宰制的暴政,正是通过被其奉为重要纲领的知识与理性工具主义的操纵手段来完成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他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才能操作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才能制造它们”[9]5。马尔库塞也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自由的惨遭吞噬与不幸丧失做出反思。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无论对人身自由的操控还是对自然界的征服,都超越了技术所承诺的价值中立而成为极权主义的构成基础。技术一方面以合理化的形式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又以合理化的形式在各个领域形成统摄力,使人在技术理性和现存社会制度面前只有异议和沉默的选项,失却了表达自由的言说,从而完成对人的全面操控。发达工业社会的宰制“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10]127在“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10]127里,技术主义已经成为征服离心力、收敛个体自由、有力征服自然、完成全面封锁的重要力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与个体乃至自然自由发展权利的不断丧失,已经在这种工具理性与技术主义的合法性支持与掩护下,以一种正比例的、愈发稳定的态势增长。
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种种治疗与解决资本主义病态社会的实践方案,都只是“扬汤止沸”并未“釜底抽薪”。从大卫·哈维在“空间”问题中探讨“正义”与“自由”来看,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的分析是从对正义理论的关注转向中逐渐实现的。哈维将资本为追逐高额剩余价值、转化过剩危机而需要不断重塑与再造空间,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城市空间、对生态空间,乃至对全球空间造成的自由侵害与权利破坏置于正义的视角下加以剖析,形成了其“空间正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哈维像马克思一样从对资本的分析、对生产的批判开始对空间的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要再生产,不得不城市化。”[16]222借助于城市化的过程,资本主义以“时空修复”的方法不断完成了对自身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与全球空间的再生产。“时间修复”是指固定资本通过延缓价值再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以此缓解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空间修复”是指“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17]90。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时间—空间’修复呈现出一种更加邪恶的状态,因为它转化了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损耗的行为”[17]101。所以通过对时间—空间修复法在资本阶段性入侵、转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展更大范围资本掠夺、连续压榨生产生活空间、剥夺他人自由与平等发展权利等方面的深刻分析,哈维指出了资本如何在城市中进行自我增值,以及如何在全球空间范围内制造更大的霸权体系,“加剧了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18]232不平等、不自由待遇。而对这一事实的有效支撑,也鲜明地体现在巴黎土地的昂贵,以街区的划分来标识身份地位与社会等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计其数的跨国公司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本转移与空间侵占的不正义行为之中。可以说,哈维以空间批判的独特视域开启并审查了资本如何实现自我增殖、赚取高额剩余价值与造就更大范围乃至全球性不正义与不自由的方式所在。基于此,哈维也曾提出过通过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包容差异的政治学——“渴望变革行动的反叛建筑师能够在难以置信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状况多样性和异质性之间翻译政治抱负”[19]238,与将一些广泛的斗争统合起来的设想——在反资本主义的旗帜下将城市运动与反全球化综合起来[20]500等主张而形成的空间正义理论,特别体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的17个问题》一书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资本与劳动”“自由与控制”“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垄断与竞争”[21]等问题呈现式与方法实践式,既想补充马克思《资本论》未触及的问题,又想续写马克思的《资本论》。当其21世纪这样研究资本论,且当以“空间正义”理论为依托时,其“空间”“正义”具有的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形式性及语言学倾向,不仅成为哈维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软肋,更成为其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一方面资本需要摧毁常规的交往,即铲除空间的限制,将整个地球作为其掠夺的市场;另一方面,它不断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是发展,流通的地域越是广阔,构成资本空间流通的市场越大,资本也就更加强调在空间上扩大势力范围,以此来控制更多的地区,并用时空修复的方法消灭更大的空间,用时间填补空间的裂痕”[22]33的全方位勘察,也即以“东方从属于西方”“乡村附属于城市”“落后地区隶属于发达地区”的方式,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空间正义”进行探讨的差距所在。
老王头终于没有送回那本书,呼伦的稿子也没能按时完成。好在杂志社主编通情达理,又给了他两个月期限。呼伦重新跑了一趟书店,谢天谢地,在大书架的一个角落里,再一次发现那本书。抱着书回到家,摆好架式,呼伦想,有关丈母娘的插曲总算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他又将和云梦一起过那种安静舒闲的小日子啰。
此次新研究为脑损伤治疗方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康复治疗时,应该考虑对大脑进行适当的刺激,而不是单纯让患者静养。
内格里从全球化的历史时代出发,以“非物质劳动”概念(源自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意指一种“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置换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帝国》一书中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提供特定服务、生产文化产品或知识、发起信息交流等非物质商品的劳动”[23]294,又在《大众》一书中提出能够对“非物质劳动”做出确认的依据类型,即一方面是以符号代码、语言形象、生产观念、景象景观等为显著特征的“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一方面是“情感劳动”[23]108(近似于一种生命政治的体验)。通过对“非物质概念”内涵的体认,内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已经在以计算机规约劳动分工、模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摆脱资本控制从而自主提供内在合作性生产关系、取消资本对信息的专制与垄断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因为“非物质劳动”在“新帝国主义”时期的这些新的“特征”与“贡献”,内格里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工业劳动日渐丧失其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将“非物质劳动”指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某种意义兴起了劳动工具论、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再讨论。使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中包含“非物质劳动”的基本内涵,是“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统一——劳动不仅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4]207-208,更包含了“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4]195。当然,内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更倾向于在计算机、影像、语言、符号、代码等方面的解读,而从“劳动技术”与“劳动工具”层面对“劳动”概念的解读,是因其要探讨阶级概念或“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是包括非物质劳动的人的阶级,这样的阶级从事的劳动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这让我们在想起马克思从经济生产而不仅仅是从技术工具的非物质生产出发去追溯“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25]174,“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26]38的同时,不得不生发这样的疑问:这样的时代何以是历史的合理化进程与文明的提升,这样的正义是何种意义上的正义,这样的自由何以是人的全面发展。再一次把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至善何以可能的问题转换到自由何以可能的现代性问题上来。
[参 考 文 献 ]
[1] 汪晖.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2]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3]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7] 叶秀山.康德的“自由”、“物自体”及其他[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1).
[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1] Gorz,A.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M].Verso,1994.
[12]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Verso,1989.
[13] 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
[14] 韩秋红,孙颖.现代性理论逻辑理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运思[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4).
[15]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 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M].Baltimore:H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17]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8]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1] 大卫·哈维.关于资本主义的17个问题[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M.Hardt and A. Negri,Empire [M].Cambridge: Hard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Paradoxical Freedom and Paradox of Freedom :Modernist Discourse of Western Marxism
HAN Qiu-hong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 When it refers to the definition of freedom,western Marxism has inherited metaphysical tradition shaped by Kant. Western Marxism has also gained knowledge about freedom from the real life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Western world. These enable Western Marxism to have unique theoretical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Marx who judges freedom from modernity,Western Marxism views freedom from the aspect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understanding 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in its own way. The incompleteness of its criticism on capitalist system and practice in reform is also the reason for the great distance from 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Key words : Western Marxism;Freedom;Criticism of 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9)02-0010-07
[收稿日期 ]2018-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21)。
[作者简介 ]韩秋红,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 10.16164/j.cnki.22-1062/c.2019.02.002
[责任编辑 :秦卫波]
标签: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自由论文; 现代性批判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