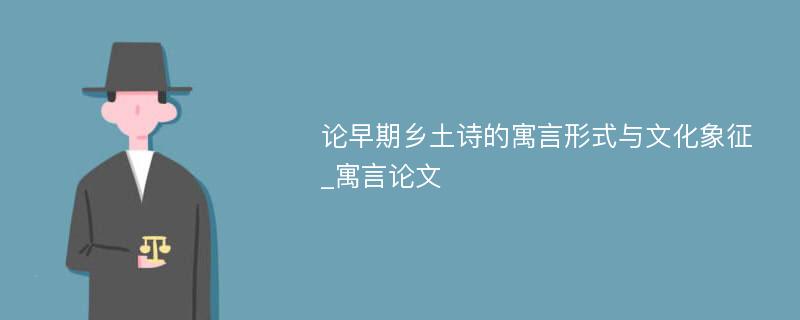
论初期白话诗的寓言形态及其文化象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诗论文,寓言论文,初期论文,形态论文,象征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寓言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寓言传统的国度。自先秦时起,寓言就在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显然,寓言是一种使其意义处身于自身之外的“亚文体”形式。作为一种记叙性文体,它或者通过人物(常常通过动、植物的拟人化)、情节,有时还包括场景的描写,构成完整的“字面”的、也就是第一层的意义,同时,又借此喻彼,表现另一层相关的人物、意念、事件或道理;它常常“以拟人手法,表现美德、邪恶、心灵状态及人物类型等抽象概念”,“用于传达训诲阐明论点。”[①]
中国寓言的发达以最具典范性的春秋时代来说,其时正值“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思想非常活跃,空气绝对自由。诸子百家和策士说客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压倒对手,就在论辨中大量使用比喻性的、言此意彼、“寓意于言”的寓言。荀卿在其《非相篇》中称:“分别以喻之,比称以明之,欣欢芬芗以送之。”就是这个意思。然而,由于寓言的“以故事为喻体,以寓意为本体”,[②]它不但不抵抗外在力量对其的侵害,反而生成于使自身作为手段的环境之中的特性,使得它并不具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本体论依据。因此,虽然“先秦哲理寓言,两汉劝戒寓言,唐宋讽刺寓言,明清诙谐寓言,共同构成了一条宏伟绚丽而曲折变化的艺术长廊”,[③]但实际上寓言几乎从未作为一种可以与小说、诗歌等文学文体并立的文体而独立繁荣过。它只能依附于其他文体而“边缘性”地存在。
在作为中国现代新诗之伟大起点的初期白话诗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依附于诗歌的寓言或“准寓言”。只要按寓言的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有故事情节,第二是有比喻寄托)来衡量,则我们虽不敢像庄子那样自称“寓言十九”,至少也可称“寓言十五”或“寓言十六”。有的差不多是严格意义上的“寓言诗”,如:寒星的《老牛》、周无的《黄蜂儿》。更多的则是在结构方式或说理比喻方式上与寓言有很多相似之处,足以称为“寓言体”或者说“具有‘寓言化’倾向”。也就是说,在初期白话诗中,寓言是最主要的一种话语形态,其数量、比重之大,远胜单纯叙事或抒情的白话新诗。
当然,这里所谓的初期白话诗是有着较为特定的所指的。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曾指出:“‘五四运动’以前,在白话诗方面尽了开辟先锋的责任的,除胡适之而外,有周作人、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康白情诸位。”[④]孙玉石也明确提出:“在胡适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格调近似的新诗作者,后来的批评家称这个诗人群体的创作为‘初期白话诗’”[⑤]。我在本文中论及的初期白话诗也大致限于这个范围。引证的主要诗歌作品,大都取自于当时刊发初期白话诗的《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杂志。这与其说是对特定概念的历史因由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诗歌事实的尊重。因为一个异常明显的事实是,新诗的发展在紧接“初期白话诗”之后的郭沫若的抒情诗歌,“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歌,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阶段,寓言体的比重就明显降低。
初略统计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在第二编中,寓言体就占了绝大多数,《老鸦》、《关不住了》、《一颗星儿》、《权威》、《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心》都足可称寓言体的白话新诗。在第一部新诗选集《分类白话诗选》“写实类”和“写意类”的白话诗中,新诗寓言体占绝大多数,而在其他几类中则成零星分布状。我们不妨对寓言体的或带有寓言化倾向的初期白话新诗作点归类和分析。
第一类可称之为“借助字面上描写的人物与情节,指代或讽喻历史人物与事件”。[⑥]茅盾曾言及“初期白话诗中有很多‘历史文件’性质的作品”[⑦],并举周作人的《偶成》、俞平伯的《他们又来了》为例。虽然,这几首诗是“‘五四运动’里‘六三运动’的一段写实”,却谈不上言此而意彼,带有比喻性的寓意,不能作寓言看。但以寓言体出现,而又具有“历史文件”性质的白话诗却不在少数。以新诗的最早尝试者胡适的诗为例,《乐观》在1919年9月29日的《星期评论》首次发表时,曾在题下以括号言明“答谢季陶先生的《可怜的他》和玄庐先生的《光》”。在收入《尝试集》时则加引言,直接道明写诗的意图是“《每周评论》于八月三十日被查禁,国内的报纸很多替我们抱不平的,我作这首诗谢谢他们。”诗中以大树喻指《每周评论》,恶势力的代表“他”因为大树的挡路而砍倒大树,“掘去树根”,“他觉得很平安了”。然而,大树“还有许多种子”,悄悄长出,“过了许多年/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那斫树的人哪里去了?”其中的“言在此,意在彼”的比喻性寓意是相当明显的,我们还不难体会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胡适在五四初期乐观理想积极向上的精神。
《一颗遭劫的星》也在诗前引言中说明此诗是为北京国民公报被封、主笔被捕之事而作的。诗歌以“热极了”来比喻社会氛围,以“好容易一颗大大的黑云出来”比喻新思想的传播,以乌云指代阻遏新思想的守旧势力,“忽然一大块黑云/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那块云越积越大,那颗星再也冲不出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顺便提一下,胡适仿佛特别喜欢用“星星”托物寓意。这在其他几首诗歌,如:《一颗星儿》、《晨星篇》中均有表现。渺小而明亮的星星似乎符合胡适作为一个信奉杜威“实用哲学”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良”、“渐变”的心态:“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努力造几颗小晨星/虽没有多大的光明/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晨星篇》)
第二类属于“观念寓言”,即“故事里的人物象征抽象的概念,故事情节用于传达训诲阐明观点。”这一类寓言在新诗中数量最多,典型地折射了初期白话诗人说理的欲望和“启蒙”的理想。
默圜的《解放》将“解放”拟人化:“解放在大海旁边立着/一群妇女围着他说道:‘那边是平等世界/吾们可以过去吗?’”集中表达,寄寓了“五四”妇女解放的主题。这首诗很能说明本文是“对现实中不可能解决的真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列维—斯特劳斯语)的本文观。在诗中,妇女似乎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待到那些“不要他们过去的人”赶到时,“他们早已过去……早已稳稳的过去!/那欢呼的声音/隔着茫茫的大海/还可以远远的听着!”
刘大白称得上是写寓言体白话新诗的重要一员。他的某些诗歌标以“新禽言之群”,就是明显借鉴中国古代“禽言诗”(寓言诗的一种)而加以创造性地发挥的。《淘汰来了》寄寓了一种改革、进步的进化论思想。“淘汰”冷酷无情,逼使人们进步:“回头一瞧,淘汰来了/那是吞灭我的利害东西哪/不向前跑,怎的避掉!”拟人化的“淘汰”则说:“你别怪我!你还得谢我拜我!要不是我苦苦地追上来,你进步怎的这样快!”
《红色的新年》也是寓言体新诗,只是更接近我国传统的“人物寓言”,而非西方传统的“动物寓言”,诗中“拿锤儿的”和“拿锄儿的”这两个人显然有寓言象征的寓意,是作为阶级类别的工人和农民的类型化。作者以叙事刻意营造了一个寓言情境:“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通过两个人的谈天,阐明了工农辛勤劳动而世道不公的事实,从而在结尾一笔点明寓意:“喂!起来!起来!/现在是什么时代?/一九一九年末日二十四时完结了,/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年!”
寒星(刘半农的化名)的《老牛》通过虚拟的辛勤劳动、“死而后已”的老牛与“肥头胖脑”、摇尾乞食的小狗的对话,明显地鄙弃了小狗似的人生观,弘扬了老牛似的人生理想。
当然,这两类寓言体有时可以交叉并存,如胡适的《威权》将抽象的概念“威权”拟人化,“他”坐在山顶上,指挥奴隶们劳动而奴隶们则蕴酿着反抗,最后,“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同时,作者又在篇末附记中点明历史因由:“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
第三类是在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只是说这类白话诗或在结构方式上或说理特点上具有某种“寓言化”的趋势。
比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通过屋里屋外,老爷叫花子不同场景的对比性描绘,最后点明:“可怜屋里与屋外/相隔只有一层纸!”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也是在细致地描写“两个扫雪的人”的基础上,于末尾加点主观抒情:“祝福你,扫雪的人!我从清早起,在雪地上走,不得不谢谢你。”陈衡哲的《鸟》以“我”入诗并作为叙述的视角,带有较浓的抒情性,很难说得上比譬说理的寓言。但此诗在把“我”(自由的鸟)与“他”(不自由的鸟)作了细致的描写和对比之后,借助于“他”的抒情,还是很像寓言地在诗末点明“自由无价”的寓意。胡适的《老鸦》虽无甚叙述性情节,但以老鸦拟人并借老鸦自况,却从而道出无异于五四人格独立之宣言:“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我不能替人家带着哨儿翁翁央央地飞/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小撮黄小米!”这类借具体表抽象意念或主观情绪的手法从根本上说有点接近寓言的方法。
恰如胡适在《蕙的风·序》中承认自己的诗的毛病在于“浅入而浅出”一样,如上所述的几类“寓言化”的“初期白话诗”,都仍处于简单比附、说理的层次上,理念往往较为浅显、易解,即便没有直接道明寓意,事与理也处于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形态上。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致上把寓言看作一个用故事作为喻体的,具有叙述长度的比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寓言和比喻本来同源。寓言是用故事作为喻体,因而有情节;一般比喻则没有情节。”[⑧]循此,我们不难发现,寓言化的初期白话诗的喻本和喻体、寓意和寓言之间仍处于几乎同时出现的一一对应的明喻阶段。而如果明喻向暗喻或隐喻靠拢,寓言就逐渐向象征转化。于是,这就涉及到初期白话诗中具有寓言式象征趋向的优秀的白话诗歌。如沈尹默的《月夜》、周作人的《小河》、刘半农的《敲冰》等公认的上乘之作,都具有这种寓言式象征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均有一个自成系统的叙事性框架,他们的寓意都较为耐人寻味,具有多义性的特点,需要依靠联想、想象等心理机能才得以完成寓言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们均以有限的形式寄寓了超越性的内容。事实上,寓言和象征本来就是两个关系相当密切的艺术范畴。寓言的基本手法,如以此喻彼,以少喻多,以具体寓抽象跟“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⑨]的象征显然有某种共通性。柯勒律治曾论及寓言或比喻与象征的关系:“比喻可以意释,而象征无法意释。”寓言只是“把抽象概念转变成图画式的语言,它本身不过是感觉对象的一种抽象……而象征的特征是在个性中半透明式地反映着特殊种类的特性,或者在特殊种类的特性中反映着一般种类的特性……最后,通过短暂,并在短暂中半透明式的反映着永恒。”[⑩]这说明,寓言或比喻与象征的差异是“同中有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喻本”和“喻指”之间结合的关系在量的程度上差异的反映。
《月夜》寄寓了独立不羁的“五四”个人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是融化在情景交融的抒情情境当中的。诗中的物象,如霜风、月光、树等,虽然没有像一般寓言那样进行拟人化的处理,但均因为渗透融贯了诗人主体的主观情思,而显得生机盎然,使得全诗在写景和抒情的表层之下,实则寄托了耐人寻味的思想和意旨。
《小河》的象征意蕴也颇为耐人寻味。一般都认为此诗象征寄托了“五四”时代思想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拦的积极意义,而我以为何尝不能理解为周作人以他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心态,面对即将酿成的大变动、大革命而表达的一种隐忧呢?这种主题“多义性”的状况正是象征艺术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敲冰》以冗长的叙述性框架,极为细致地再现了一个敲冰前行的进程。然而,“实写破冰前进,虚写应该怎样对待人生”(11)通过这个不无虚拟色彩的外部故事,却直达超越性的哲理内涵,在整体上达到了某种象征的效果。尤其是“敲冰!敲冰!/敲一尺,进一尺!/敲一程,进一程!”的复沓,铿锵有力,回环往复,无论在外部形式和乐感上,还是在阅读心理结构的整合功能上,均极大地促成了整体象征效果的发生。
二
寓言体在“初期白话诗”中的“发达”,当然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偶发性现象。它理应是时代、文化、主体等多种合力协同作用、“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12)的结果。我们甚至不妨按照西方文化批评的方法,把寓言理解为一种话语类型(如同叙事、抒情、象征等)。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抒情、象征等话语类型均晚于寓言在中国现代白话新诗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许,我们可以把寓言看作现代新诗的第一种话语类型。当然,寓言作为话语类型在“初期白话诗”中的占据主导地位,包含了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甚至反映了一定的权力关系(比如,知识分子对劳动大众的话语权力),因为话语是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概念,任何话语都有它一定的权力基础,是一定历史、文化、时代“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ious)的一种象征行为,以象征的方式既掩盖又解决现实中的重大矛盾。”(13)作为以启蒙为旗帜和目的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正是直接地选择白话诗作为武器,以寄托和宣传他们的新思想。不用说,寓言化的说理方式,正是最适合于他们的,因为寓言借具体形象而浅显地表达抽象的道理,最能达到向大众进行启蒙和宣传的效果。而且,这种讲述寓言的姿态,恰体现或暗合了五四时代知识者心仪并坚守的真理宣谕者的形象。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初期白话诗”“寓言化”本身也是“五四”时代文化的一个“寓言”。
同时,这也必然是一个有着强烈说理欲望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初期白话诗”的作者们必然不具备诗歌本体意识,而是把诗歌当成了一种说理的工具。人生、自我、人道理想……这些东西才是第一义的。正如鲁迅在论述初期小说作者时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认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14)“初期白话诗”的情况当然与此极为类似。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就曾经很清楚地表白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诗歌观念:“诗是为诗而存在的,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这话我一向怀疑。我们不去讨论、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反而争辩怎样做诗的问题,真是再傻不过的事。因为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于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便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15)
此外,从“初期白话诗”作为一种新的文体的发生来看,它可以说是作为旧诗的直接对立面,为向旧诗示威、叛逆,表明白话也能作诗而“尝试”和“实验”出来的。此正如胡适在《尝试集》代序——《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中表白的:“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半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与这种“尝试”心态相近,“初期白话诗”的先驱者中还不乏一种“敲边鼓”的心态。这就如鲁迅说的:“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旧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16)鲁迅的这种心态,跟他在《呐喊自序》中表白的“听将令”的心态何其一致。这种典型的心态也不难从“初期白话诗”诗人队伍的博杂庞大中窥豹一斑。这个诗人队伍,除了成绩不错、文学史上常提及的几位,如: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刘大白、周作人、俞平伯等之外,还包括了许多专业、兴趣和特长均在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比如:思想家和革命家陈独秀、李大钊、沈玄庐、戴季陶、朱执信,历史学家顾颉刚、傅斯年,小说家罗家伦、王统照,剧作家田汉、郑伯奇……而事实上,既使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初期白话诗人”也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专业的或极有诗歌天赋的诗人。胡适很快就被穆木天指斥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的最大的罪人”(17),刘半农也承认(似乎并不能看作是简单的自我谦虚)从1917年到1932年的15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18)
于是,在那个打破偶像,价值重估的时代,“初期白话诗”似乎理所当然地在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般的文体意义上的革命,而是被明显赋予了文体以外的时代使命。或者说,它的文体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或服从于整体的时代需求的。正如谢冕在论及“初期白话诗人”选择“诗的批判与创造作为突破口”的战略意义时所说的:“在旧文学的堡垒中,诗是发展最充分的一个品类。千年以来的无数诗人的创作实践,造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完备的艺术形式、丰富的表现手段和极稳定的一套艺术思维和运作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整套的旧诗词系统,已经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情趣习尚以及功名仕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想冲破这一切,不仅要面对艺术的不可企及的完善的挑战,而且,还要面对整个传统营垒的情感和风习的挑战。新诗这个毛头毛脚的丑小鸭,就是这样面对着数千年凝聚而成的艺术经典。”(19)
可以想见,“初期白话诗”这个“毛头毛脚的丑小鸭”是无暇顾及诗歌本文形式方面的精工雅致的。它首先要“听将令”,宣传“五四”思想,因而在“所述的故事好比是身体”和“所给予人们的教训好比是灵魂”的两极之间它理所当然用心在于“理”之灵魂,而为了宣传的得以见效,面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他们还大力提倡平民化诗风,奉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作诗如作文”的原则;其次,它还要证明白话作诗的可能,故而“注重的是‘白话’,而不是‘诗’,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而未注意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20)
另外,“初期白话诗”奉行的“经验主义”的作诗手法,客观上也从文本内部方面为寓言体的发达铺垫了道路。朱自清先生在论及“初期白话诗”时曾说:“胡适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称这时期诗为自然主义。”(21)确乎如此,胡适就曾在著名的《谈新诗》中主张:“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手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22)他批评当时“那些不满人意的诗犯的都是一个大毛病,……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23)隐含之中的纠正的方法当然是“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显而易见,这种方法正是寓言的基本手法。大体而言,具体的、“经验主义”的手法成就了“初期白话诗”的表层形态,这使得“初期白话诗”忽视想象的作用,重白描和写实,平实明白而拘泥于具象;而同时,强烈的说理欲望和抽象的哲理思想则又有意无意地使寓意发生于具体的层面(有的在篇末直接点明,有的则是一一对应、几乎无需联想地附着于叙述表层)。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发现,在《分类白话诗》中,“写实类”和“写意类”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寓言体。这是因为,对“初期白话诗”来说。既不可能有纯粹的写意(写意必在写实的基础上生发),也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写实(写实的背后往往直接或间接寄寓了寓意或象征)。
三
“初期白话诗”自产生以来,屡遭激烈的批评与非议。早自1923年开始,成仿吾、闻一多、穆木天等都先后从不同的艺术角度,对新诗的命运与发展方向提出了反思,并悬拟起新的艺术主张和新的诗歌发展道路。他们在试图把新诗进一步推向前进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反思批判的矛头,极为尖锐、激烈地对准了“初期白话诗”。这自然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确,从更高的历史和艺术的基点上看,“初期白话诗”的确在诗歌观念、艺术手法诸方面均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例如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诗歌观念、过分拘泥于具象和写实的诗歌手法,以及常被人论及的“散文化”、“非诗化”的倾向等等。
然而,当我们把“初期白话诗”进行充分的“历史化”,即:“把文化本文或批评范畴置回其产生时的特定社会及历史关联中去,复原其在特定历史上下文中的初始意义。”(24)也就是说,当我们对“初期白话诗”产生之时的时代情境、历史要求、诗人的独特心态、诗歌担负的诗之外的任务等多元历史合力有了较为切实的理解之后,我们自然会对“初期白话诗”的先驱们投以更多的理解、宽容乃至敬意。
说到底,如同“初期白话诗”是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一样,寓言,或者寓言化也是新诗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寓言在某种意义上往往发生并兴盛于文学发展的不成熟的初级阶段,而且还因为,寓言对以后新诗中抒情诗和叙事诗的相对独立并成熟均起着某种先行者的作用。《苏联百科全书》中曾对寓言下过这样的定义:“是抒情和叙事文学的一种体裁。”公本对此阐述道:“寓言必有所讽喻,或寄托一个教训,或阐发一个理念,在这意义上说,它类似哲理诗,是抒情;寓言是一种比喻,必须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性格形象,在这意义上说,它类似故事诗,是叙事。所以一般寓言,往往既是抒情的,又是叙事的。”(25)类似于黑格尔论述过的那样,(26)诗歌发展的“史诗”阶段是群体意识与个人意识融合的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的特定文类,而后来,“史诗”的抒情功能和叙事功能分别独立出来,各自发展为抒情诗和叙事诗。“初期白话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寓言诗”也可以作如是观。在短暂的寓言体阶段过后,寓言的抒情(说理)和叙事的功能也都各自从寓言中分化出来。继之而起的郭沫若的抒情诗,冰心、宗白华等的抒情小诗代表新诗发展中独立的抒情诗的出现,朱湘、冯至等人的较为成熟的叙事诗则代表了另一极的发展。
此外,“初期白话诗”的寓言化倾向(特别是某些“寓言化象征”的诗歌)还可能对以后诗歌发展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自觉运用,有一定的启迪意义。虽然,这种“寓言化象征”是一种整体性的象征,是把整个叙事性的“故事”当作比喻或象征的“喻体”,它也许跟传统诗歌中的“比”、“兴”等手法有更多的接近,而跟李金发等人接受的,以波德莱尔为肇始的,追求心灵隐秘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感”、“契合”的象征主义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它至少能为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的研究,确立中国本土的支点,启示我们去寻找中国诗人接受象征主义并使之“中国化”的内在文化心理基础,探求中西诗艺差异的“缝隙”和共鸣的“契合点”。
注释:
①⑥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寓言”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7页。
②③⑧陈蒲清《中国古代寓颜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第5页,第1页,第2页。
④⑦《文学》1937年1月1日八卷1号。
⑤《20世纪中国新诗:1917—1937》,《诗探索》,1994年第3期。
⑨劳·坡林在《声音与意义……诗学概论》中为象征下的定义,转引自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第211页。
⑩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第204页。
(11)陆耀东《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44页。
(12)阿尔图塞的理论术语,详见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64页。
(13)弗·杰姆逊的本文观,详见《历史—本文—解释》,《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14)《〈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5)《冬夜自序》。
(16)《集外集·序言》。
(17)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18)《初期白话诗稿·序》。
(19)《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2—43页。
(20)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
(21)《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22)(23)胡适《谈新诗》,《新潮》3卷1号,1919年10月。
(24)杰姆逊《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行为》(The PoliticalUncons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 Symbolic)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第108页。
(25)《先秦寓言概论》,齐鲁书社,1984年,第172页。
标签:寓言论文; 胡适论文; 诗歌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尝试集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