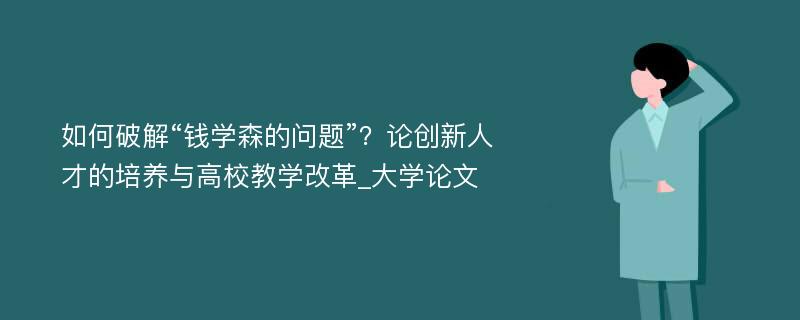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兼论创新人才培养与大学教学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改革论文,人才培养论文,大学论文,钱学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生前曾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温家宝总理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党和政府高度关切的持续热点。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人才工作和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提升到历史的新高度,突出强调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予以清晰阐述:“要注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使学生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努力为培养造就更多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做出积极贡献。”这为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指明了方向。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要“破旧立新”,首先必须搞清楚哪些是“旧”,哪些是“新”?这就需要深入知识论层面寻求答案。
深入知识论层面,审视“钱学森之问”
“范式”一词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其定义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但大体而言构成一种范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们所采纳的一般性理论假定和定律,以及应用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术。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一种单一范式所支配的。简单来讲,范式就是教科书中讲的东西。
库恩这样描述科学进步的图景:第一步由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范式逐渐明晰,科学家在范式内从事解难题的活动;第二步,由于根本性的难题不能解决,发生科学危机;第三步,危机阶段后产生科学革命,旧范式被新范式革命性地替代;第四步,由科学革命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新的范式已经确立。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知道,相对于尚未诞生的新学科,所谓旧学科就是当下的常规科学,其中的范式就是目前教科书所传授的知识核心,创建新学科所要突破的就是教科书所承载的旧范式。
目前基于常识的教育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创造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只有把旧学科范式掌握得非常熟练和深刻,才能创造出新的学科范式。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目前教育制度的基础。但以上认识中存在一个重要的悖论,创造新学科所要突破的恰好是旧学科的范式,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一种极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学生对旧的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的范式产生某种信赖(而非怀疑)、甚至信仰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的范式呢?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么教育活动就不是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而是在培养旧学科的忠诚者和维护者。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被培养为旧学科的忠诚者,那么新的范式将难以被创造出来。在以上科学进步的图景中,库恩指出了这种危险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曾经是并仍然是常规科学家,那么某一特定的科学就会囿于某一范式而不能超越它而进步,这是一种严重的缺陷。
这里,我们尝试提出一个新概念——范式陷阱。在旧的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的范式越深,旧范式因而成为陷阱而让学习者难以跳出而做出创造。地心说时代的状元们以及其他的成功者(如当时的重大项目主持人),越不愿意、也难以推翻托勒密的天文学范式而创造出哥白尼范式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
范式陷阱这个概念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因为八股和科举制度形成了巨大的范式陷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因为制度安排的学习活动而整体深陷其中、心甘情愿地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范式陷阱这个概念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在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多个革命性创新者都是大学肄业者的原因,这些人中包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DEL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戴尔,还有拍出《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这两部全球票房第一、第二、同时正在引导电影史中3D革命的导演卡梅隆,等等。没有通过现代大学持续深入的学习而陷入既有范式陷阱之中,是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范式陷阱这个概念也许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历来的状元就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都不是进士。曹雪芹、蒲松龄都是拔贡。”状元是在八股的范式陷阱中沉浸最深者,而李白、杜甫、曹雪芹却都是文学领域的创新者!
一些教育家认为,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以上回答都关注于教育体制和战略等外在方面,并未深入知识论层面。
在建立范式和范式陷阱概念后,我们可以反过来提问:我们现代的大学教育中,什么样的教育活动有可能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中更深从而制约其创造性的产生呢?这是从知识论层面审视“钱学森之问”的新视角。
减少学习总量,打破“传授型教育”怪圈
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学得还不够多!是他们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还不够精确!于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种思路,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学得更多,把知识掌握得更精确,基础要扎实!要加强基础!许多大学现在办试验班、举办各种“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学习量单纯加法的思路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福建某高校试验班一二年级教学计划的学分安排总和就达到125学分,南京某师范大学成立的相关学院即命名为“强化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坦言,自从卸任校长后他才把问题想得更清楚。“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个观念,认为知识越多,创新能力就越强;学历越高,创新的本事就越大”。他认为,以知识传授型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这样一个怪圈: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了。原因何在?范式陷阱在作怪。
我们的大学生究竟是不是学得太多了呢?以北京几所高校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专业教学计划(2001年)毕业总学时数是3260,按15学时=1学分折算学分接近217学分;北京联合大学的毕业学分要求是200左右,北京物资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学分要求为169。北京大学经过1997年和2003年两次连续的教学计划改革,才将本科毕业学分要求减少到140学分之内,成为中国大陆本科毕业学分要求最少的高校,但由于内在机理并未取得共识,因而仍有继续增加的可能。
在此,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作横向比较。美国大学在可比情况下(学时学分对应数可比),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是128学分左右;我们的邻居日本,2000-2010年间已经有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在124学分左右。横向比较,我们的学生确实学的太多,这也许使得他们陷入范式陷阱越深而难以有创造力的发展。
在此,我们也需要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层面作纵向比较。大家常常回忆西南联大时代,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创造性人才我们现在的大学还难以超越,其中包括大陆培养的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多位两弹一星元勋。根据1939年8月12日当时教育部颁行“大学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施行要点”,“文、理、商、农等学院各学系,及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三学系学生最少须修满132学分,工学院各学系及法学院法律学系学生,最少须修满142学分,方得毕业。必要时得增修学分,但增修之学分,文、理、商、农等学院各学系,及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三系,最多不得超过10学分,工学院各系及法学院之法律学系,最多不得超过8学分。”这表明西南联大当时本科毕业应修的学分数是132学分左右,这个数字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非常一致!这是西南联大把握住教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还可以将内地和港台地区作个简单比较。我国台湾也曾培养出中华民族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获化学奖的李远哲。依据台湾省“大学法施行细则”第22条:“本法第26条第三项所定学士学位毕业应修学分数,于学士学位修业期限为四年者,不得少于128学分;修业期限非四年者,应依修业期限酌予增减。大学为办理教育实验,得专案报本部核准调减前项毕业应修学分数。前二项有关毕业应修学分数及毕业条件,各大学应列入学则。”香港几所高校将于2012年将大学本科学制从英制三年改为四年,其确定的四年毕业应修学分数基本也是128学分。
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教学改革方针,成为北大之后20年教学改革的指南,并对全国高等教育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加强基础”尤其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发自内心的尊崇。从范式陷阱角度看,创新需要一定的基础,但对基础“适度”的把握十分重要,过多的基础、被过分加强的基础,那些使得我们的学生全面继承旧的知识体系,娴熟掌握已经被规范化的技巧,反而会制约创造力的发展,成为创造力的“杀手”。对于“加强基础”的口号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迈克尔·波兰尼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新学科、新知识创作的本质,“大的发现能改变我们的解释框架,因此,从逻辑上说,要不断地用我们以前的解释框架来取得这些发现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再一次看到发现是创造性的,即发现不是通过以前任何已知并可言传的程序的辛勤劳作取得的”。
对于大学学习量改革的建议很简单,以减为加。由于现在没有统一法规,考虑政治理论课的学分安排,各个大学可以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数要求至140学分(上限)。同时,建议教育部出台统一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分要求降低到120~140学分之间。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实际举措。
改革考试制度,注重怀疑态度和想象力培养
考试是教育评价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直接作用是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反作用力,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对学习内容的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考试会使学生在努力学习、深入学习的同时对范式陷阱保持高度警惕、避免陷入其中呢?
袁隆平是中科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其在杂交水稻方面的创造性贡献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袁隆平1949-1953年间就读于西南农学院,2008年百年校庆之际,西南大学(西南农学院合并进入)公布了著名校友袁隆平1950年大一下期期末考试成绩,专业成绩在班上仅相当于中等。其中英文93分;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农场实习67分。植物学等专业课成绩非常低。然而,正因为专业课程成绩低,袁隆平避免陷入了一个范式陷阱。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生物学遗传学领域也全面向前苏联老大哥学习,遗传学主要讲授社会主义遗传学,即米丘林李森克学派所主张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所谓资本主义遗传学,则是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以及之后发展的沃森和克里克DNA双螺旋模型,是不在生物学教学中传授反而受到批判的学说。那时的教科书教学内容以及考试的标准答案在现在看来几乎完全是错误的,彼时考试成绩越高的学生恰好在错误范式中陷得越深,越难以在后来做出真正的科学贡献。袁隆平学习不好,因而没有深入米丘林学派的范式陷阱;那些取得好成绩的学生、那些留校工作的好学生,从米丘林的陷阱中跳出来就很不容易,创新更无从说起。袁隆平曾说,“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因而其对杂交水稻的思考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遗传学方向。能够“猛醒得早”,是因为没有深陷入范式陷阱。“拴死在一棵树上”不就是落入范式陷阱的另一种说法吗?由此看来,趋同性思维的考试题目会促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而发散性思维的考试题目会促使学生“怀疑”态度的养成和想象力的培养。
在生活和世界运行中,发散性思维与创造性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相对于趋同性思维而言更加重要。比如,我们喜欢样式不同、功能各异的手机,具有崭新功能和美感(美感是一个多么发散的概念!)的手机才能博得更多消费者的喜爱,造成如iphone一般全球的热情和苹果公司日进斗金。还比如,我们喜欢不同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喜欢不同的歌曲和交响乐,喜欢不同的戏曲、话剧和电影,创作者和表演者为此持续努力,我们称他们为诗人、作家、作曲家、导演和各类明星。在科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第一才被尊崇,所谓第一就是寻求与以往认识的不同并成功的第一人,按照已有的模式和技术方案第二次完成被称为重复,基本没有新的认识价值……
我们来分析一份某大学“社会学方法”课程的试题。第一部分为名词解释,包含五个名词,成绩占比20%,为趋同性思维试题。第二部分为简答题,包含三个小问题,成绩占比24%,题目为“简述典型调查的优缺点”、“为什么要区分调查量表和测验量表”、“简述影响调查样本代表性的主要因素”,三个题目均为趋同性试题。第三部分为判断题,共四道小题,要求学生对一个判断做出对错的选择判断,占比20%,同样为趋同性题目。第五部分为一道统计计算与分析题目,占比20%,也为趋同性试题。该试卷中,只有一道大题具有空间非常有限的发散性,占比16%,题目是“试论述详析模式的方法和主要作用”。
以上对一门课程考试的分析确实表明,其中趋同性思维试题占了极大比例,几乎达到80%以上。当我们从这一角度看高考试题时,会发现趋同性试题所占比重更大,可以说除作文外几乎所有题目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在思维上倾向于将考生训练为趋同性思维。即使是作文,中小学和课外培训机构也发展出范文和作文模块供学生背诵。高考模式向中考、小升初和日常教学、考试蔓延,于是成功地将中国所有中小学生的思维都训练为趋同性思维。这是高考的“成就”,也是高考需要改革的关键之处。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课程方面,趋同性题目从创造性思维养成角度看还有一个巨大问题。由于趋同性考题世上有人已经知道答案(例如教师),因而学生在开始考试时潜意识中知道答案存在并已有了方向,只是教师尚未告诉自己而已。这种在范式中的解难题活动与真实的科研不同,科研探索首先需要提出真正的问题,人类整体都不知道答案,也许没有答案,因而探索存在方向性的根本问题,迷茫是必须阶段。这两种不同使得持续参与考试的学生、那些未来的研究者在思维模式方面难以习惯迷茫的探索,这同样成为对真正的科学探索和创新的制约。
与趋同性思维紧密相连的考试制度还包括“考教分离”制度和“试题库”制度。所谓考教分离“就是把课程考试从整个教学过程中剥离出来,相对独立地进行”。为方便非任课教师判卷,考教分离的试题出题者往往要给出标准答案,这无疑就使得考试成为对趋同性思维的导引。编制封闭僵化知识的“试题库”,实质就是在编制代表封闭僵化知识的范式陷阱。这些长期在我国高校教学中曾经并仍然在流行的制度都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南辕北辙。
要求学生创新和突破范式陷阱,教师必须不断创新,同时教师更加需要对既有范式陷阱保持高度警惕。因而,教师所出的考试题必须与以往所有的考试题存在不同。与试题保密制度和试题库制度内在逻辑完全不同,广泛公布试题的制度(在图书馆甚至在互联网上)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的不断改进和对该领域前沿的持续关注(科研),有利于促进试题编制的不断创新,防止范式陷阱的形成进而促进创新人才不断涌现。试题公布制度为英国许多高校所采用,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制度成功的秘密之一,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回答“钱学森之问”应当采取的关键改革之一。
粗化评价标准,避免对考分的过度追求
传统上许多高校考试成绩评价采用百分制(numerical grading system 0-100),学生成绩排队也采用百分制积点计算。百分制有其合理性,但以其为标准对学生的课程学习和总体学习进行评价会存在过分细化的倾向,因而会引导学生对既有范式精细化地学习而更易陷入范式陷阱之中。
美国高校一般对课程成绩评价采用字母制(letter grades system,又称“等第制”,分级一般为A+,A,A-,B+,B,B-,C+,C,C-and F,共10级),在对学生总体学习情况排名时转换为4分制并实行以4分制为基础的绩点(GPA,General Average Point)排序。英国高校虽然有课程考试和最后的荣誉学位考试,但最后并不给予学生包含每门课程成绩的成绩单,而只给出最后的荣誉学位考试分等。三年本科总体的分等只包含一等、二等上、二等下、三等和特别等五级,这是对学生更加粗化的成绩评定,其内在逻辑包含了对精确化学习的否定,是英国高等教育成功的另一个秘诀。
字母制粗化评价对淡化学生对过分细化成绩的追求很有效果,学生不会为追求几分之间的细微差别而计较。在对学生学习情况作综合评价时,在字母制基础上采用平均学分绩点会粗化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从而使这一评价更加合理、避免学生陷入范式陷阱。
在大学课程的考试题目中增加引导发散性思维的题目,实行考题公布制度、将百分制改为字母制评分,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又一个实际举措。
调整激励导向,支持和引领创新活动
在我们大学的奖学金体系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些大学GPA)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有的大学达到评价指标权重的70%以上。北京大学一般院系成绩占比为80%,元培学院接近85%;中国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成绩所占的比重同样达到80%。可以说,我们现行的奖学金体系都在鼓励学生更深地跳入范式陷阱。我们的学生奖励体系,特别是奖学金体系如三好生评选、奖学金评审等,都在奖励学习得非常精确、在现有范式中沉浸过深的学生,是目前促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的重要制度因素。
如果将我们大学的奖学金从奖励学习成绩转变为奖励创新,也许有助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培养出创新人才。在这一方面,剑桥大学奖学金制度同样是其持续培养出创新人才的秘密之一。按韦曙林先生的总结,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评审原则有三条,其核心是奖学金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无关,而与学生的创新工作、特别是创新性研究工作有关。
第一,奖学金设立的原则、评价标准、评选程序和经费用途,都鼓励学生开展原创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以其研究成果作为最终的考核标准。
第二、设立的多渠道奖学金,形成研究偏好目的各异、覆盖所有科学领域、覆盖全年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和资助学生多元化的格局,使研究课题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第三、学生依据专业和兴趣主动申请并提交研究计划,有些需要获得教授和导师推荐,充分调动了学生创新的积极性,并容易使学生形成研究团队。
改革奖学金制度,使奖学金从目前鼓励学生对现有范式反复深入学习因而落入范式陷阱,到鼓励和支持创新活动是我们这部分讨论获得的结论。这是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
范式与范式陷阱的概念来自于科学哲学,但因其关注知识和知识革命的本质,便与目前的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联系在一起。对这两个概念的深入探究帮助我们反思教育活动,包括学习总量、考题类型与评分制度、研究生一级学科统考、试题库制度以及我们的奖学金评价的内在缺陷等,并在反思后提出有关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我们可以采取切实的行动,去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继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