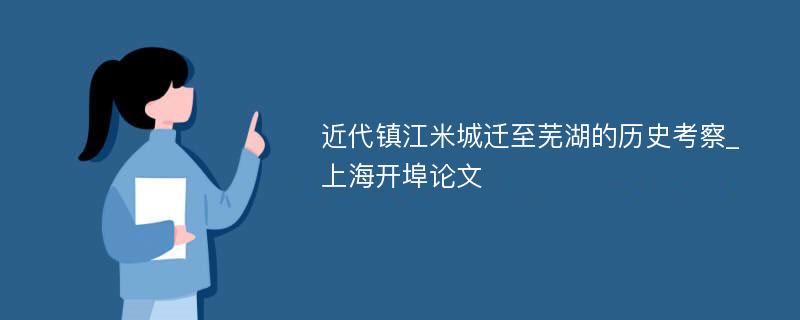
近代镇江米市移师芜湖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市论文,芜湖论文,镇江论文,近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镇江因运河、长江之利,交通地理优势突出,商业向来繁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被逼开埠通商,成为长江流域继上海之后的又一通商口岸。开埠后,江海大轮开通,各地客商纷纷来镇设庄设号,收购米麦杂粮,逐步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粮食市场。1866年,镇江米业公所成立,米市形成。镇江米市对近代镇江经济影响甚巨,柳诒徵先生说:“镇江故有米市,广潮商人及钓卫、沙网各帮,均萃于镇,轮帆迭运,为商业之大宗。”① 然而,好景不长,1877年李鸿章上书朝廷,请将镇江米市移师芜湖。1882年镇江米市正式迁至芜湖,“于是镇地商业,遂有一落千丈之势”②。对于镇江市米衰落的原因,近代米商及各业商人,皆归因于李氏对镇江米市的强行撤离。事实上,一个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受着多重因素影响的,除了宏观的政策外,还有微观的环境,包括货物来源、销路、交通条件、资金保证、市场网络、经营格局、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对近代镇江米市移师芜湖的历史考察不应简单着眼于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影响。多方面探寻两大米市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近代两地区乃至长江下游沿岸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
镇江与芜湖是近代长江下游的两个重要的中等城市,诸多共同的特性,构成了两城市形成米市的先决条件。
首先,镇江和芜湖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镇江、芜湖同处于长江南岸,襟江带河,具有利于客货往来的交通条件。镇江,地处长江与运河的十字交汇点,自古“大江横阵,群峰环抱”,水陆交通便利,其航道西接金陵,东通上海,北达淮泗,南达杭州,《宋书·文帝记》记载说:“京江襟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送四达城邑。”③ 芜湖,号称“吴头楚尾”,位于长江与青弋江的汇合处,地处“江津之要”,南通南陵、宁国、太平,西北经裕溪口可达巢湖、庐州,溯江而上直达九江、汉口,沿江而下东至南京、上海,宋代杨颢因而题诗云“山连吴楚周遭起,水会湖湘汹涌来”,芜湖的地理优势可见一斑。
其次,镇江、芜湖皆为传统的商业都市,具有良好的商业传统。镇江,素以商业而闻名,西晋时,京口(镇江古称京口)是商贾云集之地,居民多以商贩为业,东晋时的镇江已经是繁华的江南都市,六朝时,京口出现了集散、中转、销售米、谷及布、帛、丝、绢等手工业品甚至海货的大规模的市场,商业特色日趋明显。至唐朝,镇江“舸帆林立,商业繁盛”,有“银码头”之称。此后,历朝历代,镇江商业繁荣,鸦片战争前,镇江成为长江下游的商业重镇,南北货的集散地和长江中下游物资的中转港。芜湖,很早以前就是皖南地区的一个富庶的商业名城,商业传统历史悠久。芜湖经济的发展与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密不可分,唐代以来,江南经济发展迅速,受其影响芜湖经济开始起步。随着地区农业的发展,芜湖商业日趋繁荣。宋代芜湖开始筑城,并兴建了大量圩田。元朝时,芜湖出现了“聚舟车之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垺”④ 的繁荣景象。明代时,芜湖商业兴盛,“舟车辐辏,百货兴聚”⑤,皖南所产货物汇集此地并运销别处,顾祖禹称之为“商旅骈集”,鸦片战争以前,芜湖发展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
优越的地理条件,良好的商业传统赋予了两市米市发育的良好条件。但近代镇江米市为何早于芜湖多年呢?镇江开埠后,米业市场逐渐繁盛,米市很快形成。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芜湖并未形成固定的米市,芜湖大米主要集中运往镇江七濠口市场交易,而镇江则集中了苏北上、下河、淮河流域、上江两湖包括芜湖等地的米粮,镇江米市盛极一时。1866年,随着镇江米业公所的成立,镇江形成了长江下游唯一的大米市。镇江米市发展较早的原因,除了开埠早于芜湖以外,尤其是镇江交通条件固有的优势。镇江地处长江、运河的十字交汇点,运河的显著意义不言而喻。20世纪以前,我国的商品运输仍然主要靠水运,除了重要的长江航道外,大运河贸易尤为突出。明代以来,南北货运流畅,大运河贸易发展迅速,对此,吴承明先生说:运河“沿河商贾蚁集,利润丰厚……大运河自徐州以下至杭州南运河一带商运最繁”⑥。传统米市的形成,大多跟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江南经济作物产区缺粮,外地粮食高产区粮食大量输入,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稻米,沿长江进入运河,沿运河北上或南下,运河成为江南地区稻米市场的轴心,“江南地区的重要米市,几乎都分布在运河沿线以及其他水运要道上,无锡、浒墅、枫桥、平望、嘉兴、硖石、湖墅,从北而南,无不排列在运河两岸”⑦。镇江既拥有长江的黄金水道,又拥有运河的优势,米市的形成自是必然。近代镇江米市的粮食,除一部分就地销售以外,相当数量的要运往外地,北至青岛、烟台、威海卫,南至浙、闽、广诸省沿海口岸,更有大宗米粮贩运出口,销往日本南洋诸国。分析镇江米市的贸易线路,不难发现,运河贸易和长江航运所起的共同作用。芜湖境内及腹地水网交错,但因为古代漕运和运河经济的特殊地位,近代以前的芜湖米粮贸易被纳入到了以镇江为中转核心的运河、长江贸易体系中,安徽输出的大米,在芜湖集中,大多过而不留,集中到镇江七濠口市场,转至江、浙。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芜湖还是一座小城镇,人口不满两万,至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时,芜湖只是太平天国的“后方屯聚军粮之所——尚未形成米业流通渠道”⑧。
1882年,在李鸿章的干预下,镇江米市移师芜湖,芜湖米市正式形成。不可否认,李鸿章的强行干预造成了镇江米市发展的戛然而止,造就了芜湖米市的繁荣兴盛,但是影响近代镇江米市移师芜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影响米市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交通运输条件,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是市场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但交通运输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交通条件可能恶化,贸易线路也会改变。地理条件的恶化,使近代镇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镇江有着特别意义的运河的重要性日渐丧失。英国人呤俐在运河沿岸的旅行,见到了这样的情形:“河工久废,两岸的大理石已经大多剥落无存,自杭州至临清间,有数处已不能行路,河槽年久失修,石堤颓记,河水泛滥,附近人民时受其害。”⑨ 苏北北段的大运河更是多处淤塞,长期依赖苏北及淮河地区大宗米粮进行吐纳的镇江米市深受其害,虽然此时的镇江米市还能维持相当程度的繁荣,但其脆弱性已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开埠以前,镇江米市长期地处江北瓜州七濠口,以镇江人居多的米行客商往来长江两岸,交通不便可以想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米市的发展。由于其时铁路未通,米粮集散依靠水运,芜湖交通优势依旧,港湾条件良好,外有长江贯通南北诸省,内有青弋江、水阳江、清水河交汇联络腹地,安徽境内及江西东北角所产稻米沿江东下可至南京、无锡、南通、上海。因此,当镇江米市交通条件恶化的时候,芜湖米市已蓄势待起了。
对于粮食市场,吴承明先生说过:“在一定意义上,农村有多少粮食可以出售,就成为市场大小的一个界定。”⑩ 根据这样的判断,镇江米市移师芜湖又具备了一个客观的理由。镇江原非稻米产地,更非商品粮产地,其地地处丘陵,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粮食自给不足,其米市货源基本来自外地,除了附近苏北广大农村的粮食,其它绝大部分来自长江中上游的各个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安徽,其中就包括来自芜湖的大宗米粮。不同于镇江的是,芜湖素称鱼米之乡,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河港交错,盛产稻米。两宋时期,芜湖地方即大兴圩田,“圩田的兴筑使富饶的皖南青弋江平原,江北巢湖流域成为稳定的稻粮产区,是当时芜湖港主要大宗出口货源稻粮生产的腹地”(11),其时,芜湖已建有大粮仓屯粮转运。此后,芜湖农业生产稳步发展,至近代,芜湖及其周边28县包括巢湖、潜山、当涂、南陵、无为、宣城等地均有丰富的余粮,“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所存的资料记载:‘皖省米产总额(年产)共为肆仟肆佰壹拾陆万贰仟叁佰捌拾陆石,除本省消费叁仟陆佰肆拾贰万叁仟柒佰捌拾石外,剩余柒佰柒拾叁万捌仟陆佰零壹石之谱’”(12)。因而,镇江虽有米市,但其米源悉赖他省调节,而芜湖附近各县产量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13)。
清初以来,粮食的流通有很大的增长,吴承明先生把清前中期长距离的粮食流通,自北而南分为10路,分析其中两条商路,“南粮经大运河北运京畿、山西、陕西”和“安徽、江西米经长江运江浙”(14),结合镇江、芜湖两地的地理条件不难观察出,镇江、芜湖在这种粮食流通中都有着重要的商业地位。但细细地比较两地的粮食市场,芜湖具有更深的历史积淀。封建社会,由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特征,粮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货币的作用。早期的米粮交易,往往集中在稻米产区,历史上芜湖除了漕粮转运以外,其自身的米粮对外交易很早就开始了,远在宋代,随着围湖造田工程的进行,粮食得到了迅速的增产,人口也不断地增加,食盐需求量随之增长。为了获得大量的食盐,芜湖港“运粮以出,载盐而归”(15)。元代,因为战乱频繁,芜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但至明初,朝廷减免租赋,招民垦荒,芜湖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水平很快回升,“漕粮运给和商粮出口都很繁忙”(16)。明中叶至清初以来,经由芜湖港中转的物资,数量最大的是粮食和木材二宗,“明代的芜湖,已经成为长江沿线重要的商品粮集散地之一,江西、湖广的大批粮食集中到芜湖,远销苏、浙及北方各省,安徽沿江两岸圩田所产的稻米也大量外销”(17)。在此基础上,芜湖米市起源很早,清代乾嘉年间,就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其时,芜湖港口贸易仍以粮、木为大宗,湖广、四川、芜湖地方及附近的稻米,均以芜湖为中转港口。专门进行米粮交易的米行也开始出现,南市和北市是相对集中的米粮交易市场,其中,南市集中于青弋江边的南关,沿河而下至浮桥一带,贸易比较繁荣。另外还有从事碾米业的砻坊二十余家,多设在仓前铺及东河沿一带,均临近码头,便于装卸。米粮销售及碾米业的出现表明,开埠以前,芜湖米市形成已有相当的基础。镇江由于一贯的交通地位,是历代封建政府漕运的中转要地,粮食在镇江的转运不计其数,但主要集中在漕粮的转输。明代镇江曾出现了大宗商品粮的转输,有众多的粮食供应市场,各路米商在此采购粮食转运各地。清代苏松地区缺米严重,大量的商品粮通过镇江转运至上述地区,这些都为镇江米市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是,商品粮在镇江的转运并不如芜湖那样占据港口商品转输的主要地位,镇江也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芜湖那样商品粮的集散中心。所以,直至开埠以前,苏北广大地区、上下江及两湖、芜湖等地的米粮多集中于扬州附近的邵伯、仙女庙、瓜州三地集散。近代镇江米市虽然形成早于芜湖,但其历史渊源不及芜湖深厚,经营基础的脆弱使其近代遭遇强力迁移的历史命运不可改变。
近代中国有“四大米市”之说,形成最早的镇江米市,未能位列其中。相较镇江米市,芜湖米市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影响更远。20世纪初叶,芜湖米市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米谷交易市场,并位居“四大米市”之首。芜湖米市之所以后来居上,是因为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芜湖米市具备了更多适合近代经济生长的因素。
第一,从市场规模来看。镇江米市迁到芜湖以后,芜湖米市迅速发展,规模很快就超过了镇江米市,盛时,米行业89家,米号36号,砻坊业百余家,碾米厂9家。(18) 镇江米市砻坊业最多时有40户,粮号有晋康、兴记等十余户,与芜湖米市相比确有很大差距。再来比较1876~1905年两地轮运出口米的输出量,可以发现除了甲午战争时期,芜湖海关实施米禁,安徽大米“以镇为宣泄之口”,芜湖米市输出量较少以外,自1885年起,芜湖米市明显超过镇江米市,不仅同期稻米出口量高,而且两者在其鼎盛时期的输出量相比也较为悬殊。镇江海关稻米最高输出年份(1881年)为280余万担,即使甲午战争时,安徽实施米禁,徽米转口镇江,镇江海关输出量也仅有580余万担,而芜湖海关轮运出口米输出量最高年份(1905、1919年)为800余万担。(参见下表)(19)
芜湖镇江海关轮运出口米的比较表单位:关担
年代镇江 芜湖 合计
1876
2432530 243253
1877
313572104468418040
1878
1519641
1352291654870
1879
29383766336 360173
1880
1374702
2103701585072
1881
2880578
3887923269370
1882
1713602
6656322379234
1883
442285473882916167
1884
354994348390703384
1885
6900551208808
188863
1886
7298752325841
3055716
1887
5446351055822
1600457
1888
1860939473411133434
1889
2436252117089
2351714
1890
2303761520897
1751273
1891
2462403487201
3733441
1892
1536583184694
3338352
1893
1234792101144
2224623
1894
1343858
3203466
4547324
1895
5834683
8151416649824
1896
5129323137242
3650174
1898
1899141654714
1844678
1900
1976564991569
5188625
1905
6191908438093
9057283
芜湖稻米输出量逐年递增,芜湖米市日趋兴盛,时人誉为“堆则如山,出则如江”,盛况可见一斑。
第二,从市场发育程度来看。一个市场的形成、发育,既有其内在必然性,又有其自身的规律,镇江、芜湖两米市由于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市场发育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深厚的历史积淀,芜湖米市市场发育相对成熟。
首先,芜湖米市市场网络比较完善。安徽各地的稻米,集中宣城、无为、巢县、南陵、当涂、和县等中心城镇,流向芜湖,再以芜湖为起点,分运烟台、青岛、无锡销售市场和上海、广州、宁波等终极市场,形成了产地市场(一级)、中心城镇(二级)、芜湖集散市场(三级)、上海等终极市场(四级)层次分明的四级市场,显示了极强的市场包容性。镇江由于农村比较贫瘠,四乡农业生产水平不高,所属中心城镇未能形成稳定的一、二级稻米市场,作为镇江米市市场基础的苏北广大产粮区,周遭环境及运输条件的变数很大,给镇江米市带来了较多不确定的因素,市场网络的不完善影响了镇江米市的健康发展。不同的市场网络决定了两大米市不同的类属,许道夫先生将近代中国的粮食市场分为产地市场、中转市场、聚散市场、终点市场四类,其中,中转市场的职能是将该地区的收购的粮食进行转运,多放在交通便利的中心城镇,聚散市场即中级市场,为产地市场的销售市场和终点市场的来源市场。(20) 根据镇江、芜湖两市的地理位置、交通和资源条件,镇江米市隶属前者,即中转市场,而芜湖米市则是后者,即聚散市场。很显然,后者较之前者,市场发育有着较强的可塑性。
其次,芜湖米市结构完善,分工明确。1882年至1921年是芜湖米市不断发展的兴旺时期,米粮业是芜湖米市的主要支柱,它形成了五个主要的行业:(1)米粮采运业,亦称“米号”,以代各地米商购办米粮出口外销为主要业务,主要由广州、湖州、烟台、宁波四帮组成,基本操纵了芜湖米粮的粮食市场。(2)米行业,又称江广米行业,是采运业买卖粮的中间商。(3)杂粮市米行业,又名“小市行”或萝头行,是四郊农民与消费者进行粮食买卖的居间介绍人。(4)砻坊业,自备稻谷、砻米出售,同时代客加工。(5)碾米堆栈业,主要指碾米厂使用机器加工稻谷碾成糙米出售,并另设堆栈出租米行或米号。(21) 五大行业明确分工,表明芜湖米市已经具备了谷米贸易高度发展所应有的仓储、运输、加工配套的条件,形成比较完整的销售体系,确保了米粮贸易的繁荣。芜湖米市各行业内部分工也比较明确,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运营机制,以米粮采运业为例,较大的米号雇佣职工达三十人左右,其职务分工如次:“(1)经理(管事),管理全号事务。(2)管帐,办理文书会计事务。(3)档手,专司看货评价。(4)监载,专管米粮装卸。(5)跑头,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专与海关、米捐局联系。(6)管仓,仓库管理。(7)厨师、茶房,专管伙食、卫生及杂务。(8)学徒,学习业务并伺候客人。”(22) 细致的分工体现了芜湖米市的成熟的发育状况。镇江米市也有大致的分工,从已有的资料来看,镇江米市“经营粮食的有米厂、粮行、粮号和米店”(23) 四种行业,但其分工未能像芜湖米市那样明确、细致,这也是由其本身的规模所决定的。
再次,芜湖米市相对有雄厚的资金保证。镇江米市有雄厚资力的大商人,大多是外地客商,如当时收购粮食的主要是广潮帮和宁建帮,广潮帮有70余户,宁建帮也有数十户,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本地商户少,资金也较缺乏。镇江米市被撤之际,广潮、宁建外地客商被迫迁移芜湖,“尔时江督胥吏来镇江关说,索贿六千金,允仍以芜市移镇。镇商既绌于资,又乏团结,不允其请,芜市遂一成而不返”(24)。风雨欲来之际,区区六千两银子,竟成为米市不保的一大障碍,可见镇江米市资金的短缺。芜湖米市的米商大多有着雄厚的资金保证。如米粮采运业,早期经营者多为广潮等地的殷实客商投资开放,“各号资本少则一、二万两,多则三、四万两银子不等”(25)。后期,各帮米号与银钱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资金均赖银行、钱庄周转。更有一些大地主大官僚及其亲故,如李鸿章族人,其实力自非一般,他们投资经营砻坊等行业,刺激了芜湖米市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从米市的历史影响来看。镇江因为开埠较早,其米市早于四大米市形成,米粮业对近代镇江米市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为镇江同业之大宗。但米粮业并非镇江经济命脉所系。镇江开埠后,外商、洋行相继而至,国内各帮客商纷至沓来,形成了几个资金雄厚、生意兴隆的主要行业:江广业(经营糖、北货、洪油、麻香、南货等)、江绸业(经营京江绸)、木材业、绸布业(绸缎和洋布业)、钱庄业。其中,江广业是“镇江最大的综合行业,关系着镇江市面荣枯达半个世纪之久”(26)。江绸业是当时对镇江经济繁荣极有影响的一个突出行业。钱庄业则被称为“百业之首”,“其影响不仅远及苏北、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以至汉口……尤其在上海金融界,更是有口皆碑”(27)。木材业、绸布业也可谓“中兴”。因而近代镇江“数十年来,早有钱、木、江广、江绸、绸布‘五大业’之说”(28),米粮业的地位远在五大业之后。芜湖米市与近代芜湖经济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近代芜湖依托米市而兴,1882年,镇江七濠口米市迁到芜湖以后,各地粮商云集,芜湖迅即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围绕米粮贸易与加工发展起82个行业,5400多家商店,商业营业额也以米业为主体,1932年,芜湖米业一项……约占商业营业额的55%。”(29) 米捐也成为芜湖税收和财政的主要来源,“最多年代,所征税银七十余万两,占当年海关税银的一半左右”(30)。米业兴,百业兴,布业、金融业、五金业、饮食业等伴随而起。米市的发展,迅即改变了芜湖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了近代芜湖城市的发展。据统计,“在米市兴旺的年代,整个米市的从业人员约有七千人之多”(31)。相关产业的工人数目更为可观,19世纪20年代,从事相关行业长途载运的船民有30万之多(32),米业成为芜湖地方经济的主导行业。此外,芜湖米市集散范围极广,由于它是安徽省唯一开埠通商的城市,是安徽全省地产米谷的出口,20世纪,芜湖米市的销售市场由过去的江浙一带扩大到沿海的主要城市广州、宁波、烟台,对其周边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镇江东有苏、锡、常,西有南京,区位发展上并不占有优势,也并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其米粮除一大部分轮运出口外其余则销往湖州、宁波、青岛等地,因其总量不及芜湖,所产生的影响只能望其项背。
总的说来,镇江米市命运坎坷。开埠通商赋予其发展的历史机遇,未及充分发展,便走向了衰落,恰如昙花一现。相反,芜湖米市占尽天时、天利、人和,成就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因为规模大小的不同、发育程度的差异、对地区经济影响的大小,决定了两市近代米市地位的不同。影响近代米市形成、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我们决不能忽视强权或政府的决策、干预,但市场本身的发展运营规律更值得关注,如历史渊源、商业习惯、运行机制等。另外主、客观条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的变化,曾经的繁荣也可能不再。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洋米的倾销,贸易线路的改变,米市本身的行规陋习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盛极一时的芜湖米市重蹈镇江米市覆辙,走向了衰落。
注释:
①②(26)(27)(28)胡鲁璠、杨方益:《解放前镇江工商概述》,政协镇江文史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第15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2、6、6、6页。
③吕耀斗:《光绪丹徒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④陶澍:《安徽通志·舆地志》,道光十年。
⑤(30)鲍实:《芜湖通志》卷三一、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⑥⑩(14)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293、279~280页。
⑦顾希佳:《近代江南米市的经营格局》,《杭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
⑧(12)(13)(21)(22)(25)(31)马永欣:《芜湖米市春秋》,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芜湖文史资料》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4、14、16~29、19、16、46页。
⑨[英]呤俐:《太平天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11)(15)(16)(17)鲍亦骐:《芜湖港史》,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8、21、22页。
(18)(29)(32)谢国权:《近代芜湖米市与芜湖城市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9)《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安徽省》附表,转引自谢国权《近代芜湖米市与芜湖城市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0)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151页。
(23)(24)镇江工商联:《盛极一时的镇江米粮业》,政协镇江文史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第15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