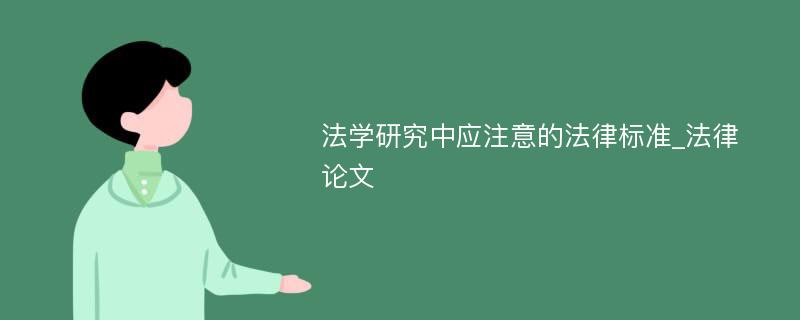
法学研究应当重视法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视论文,法学研究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 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9)04-0132-07
一、从法学角度理解法标准
什么是法标准?假如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法律,就应当明白什么是法标准。因为法律之“律”,其含义就是“标准”。因此,所谓法律,就是法之标准。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实际上指的是由具体的一系列的法规范所构成的法内容,一般以文字的形式构成法规范之文本,即所谓成文法。成文法的构成内容就是具体的一系列法规范,而每一条法规范其实都是具体的一系列法标准。所以,法标准是构成法规范的基本内容,是法规范建构的具体内容。
(一)律就是标准
按现代科学的定义,标准是对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中某些多次重复的事物给予公认的统一规定。标准的制订必须以科技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经有关各方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并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更新。按这样的定义,没有科学可能就没有标准。其实不然。按西方学术要求而称的科学只有数百年历史,但人类社会生活中确定标准却应该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汉书·律历志》中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所谓“齐远近,立民信”是指确定社会的律、度、量、衡的标准,以使社会交往能够正常、社会互信能够确立,“同律度量衡”是指统一音律、长度、容积、重量之单位及其名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其中的“律”既可指音律标准,又可指标准本身。这是因为度量衡之标准皆源于音律标准,度本起于黄钟之长,量本起于黄钟之龠,衡权本起于黄钟之重,而黄钟是音律的基点①,即“五声为本,生于黄钟之律。”(《汉书·律历志》)黄钟之律是其他音声律吕的标准,确定黄钟之律的竹管(铜管)之长是制定长度标准的依据,确定黄钟之律的竹管(铜管)中空容积是制定容量标准的依据,其中空所容黍粒重量是制定重量标准的依据。②由此引申,各类标准因而确立。“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圜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翼天子。”(《汉书·律历志》)直至据以划分天候节气,年月日时。《汉书·律历志》中记述唐都和落下闳等人制作《太初历》,说:“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歴。其法以律起歴,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度是否真起于黄钟之长,量是否真起于黄钟之龠,衡权是否真起于黄钟之重,这些留待有关专家去考证。我们所要重视的是,“律”的含义是“标准”。
明白了律是指标准,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按一定标准写的诗称为律诗,做律诗的那个标准被称为诗律或诗的格律。由此,我们也就应该能明白刑律所指的应该是刑罚的标准,包括什么人的什么行为应受刑罚的标准、刑罚程度的标准、刑罚方式的标准和刑罚步骤的标准。我们必须用心注意的是,当“诗律”成为常用的概念,诗界人士常会淡化诗律概念中的“诗”,而主要重视诗律中的“律”,因而简称诗律为“律”,如七言律诗简称为“七律”,五言律诗简称为“五律”,长篇律诗简称为“长律”。同样道理,当“刑律”成为常用的概念,刑界的人士常会淡化刑律概念中的“刑”,而主要重视刑律中的“律”,因而简称刑律为“律”,如唐代的刑律被简称为“唐律”。对诗界人士而言,诗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对于刑界人士而言,刑是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律”,是诗的要求,诗的特征;是刑的要求,刑的特征,所以不可忽略,必须明确标识。但这样一来,对于非诗界、非刑界人士而言,“律”的张扬掩盖了诗和刑的实质,使人觉得律就是诗,或律就是刑,甚至律就是法。
律不是法,刑也不是法。刑是对坏法之人给予惩罚。这种刑罚需要有标准,这标准在古代中国称为“刑律”。当然,对坏法的人加以惩罚亦需要有法,这法应该称为“刑法”,是刑罚所依据的规则。为什么需要刑罚,为什么对某些人的某些行为以刑罚惩处而不对另一些人的另一些行为施以刑罚,为什么刑罚惩处设置这样的内容而不是那样的内容,为什么刑罚的程序是这样设置而不是那样设置,这其中所依据的是“法”,法应该称为“刑法”。但具体地惩罚哪些人的哪些行为,给予哪些具体内容的惩罚,具体设置怎样的刑罚程序,则是刑罚的标准,应该称为“刑律”。法是规则,刑是惩罚,律是标准。按规则(法)办事,违规则受罚(刑),罚的标准则是律(刑律)。从商鞅开始,古代中国由秦到清,在刑罚方面所颁布施行的主要是刑罚的标准,即刑律。从秦到清,这类作为刑罚标准的刑律,一般简称为“律”。
中国古人称刑法为刑律,我们今天将刑律改称为刑法,但我们又将各类法规范皆称为法律。这其中的语源性原因,就是因为律即是标准,因为我们今天所称的法律就是各种系列的关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的标准,或者说是各种系列的由具体的权利义务标准和权力责任标准所构成的法规范。
(二)法标准是法的构成要素
法规范是对各类法主体的权利义务或权力责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标准的规定,是法给各种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所确定的具体标准,或者说,法给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确定规范,必须定出具体的法标准。人们(各种社会主体)按照法标准作为或不作为就是符合法规范,因此,所谓法标准,就是确定法规范的具体依据。
没有标准的规范不能成为规范,但标准是标准,规范是规范。假如我们对标准和规范这两个词语做点字义考古式的考察,我们可以明白,标准之标义为标定,标准之准义为准据,所谓标准即标定之准据;规范之规即规矩之规,规范之范即模范之范。规以制圆,范以制物,但圆之大小,物之巨细,须凭标准方能确定。所以,无论规范用于制物还是用于行事,大小曲直都必须有其标准。
从法制而言,法规范之确定皆须有其法标准。如,刑事法所确定的刑事规范所依据就是一系列法标准,包括什么人的什么行为应受刑罚的标准、刑罚程度的标准、刑罚方式的标准和刑罚步骤的标准等;民事法所确定的民事规范也是依据一系列法标准,即人的权利义务的标准,包括人拥有物权的标准、损人物权的赔偿标准、物权交换的行为标准(契约标准等)、物权纠纷的裁判标准等;行政法的法标准则主要应该是行政主体的权力责任标准。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其中十四周岁和十八周岁是年龄标准,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不予处罚则是处罚标准,这些法标准相互联系,构成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的法规范。
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第十四条规定:“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精神病、盲聋哑、醉酒状态,这是人的三类病态标准,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给予处罚则是四种处罚标准,这些法标准相互联系,构成另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的法规范。
法标准显然是法规范之所以成立之必需,这就是说,法标准是法之所以构成的要素。所谓要素,即必要之质素。笔者认为,法之构成要素,应该包括法标准、法规范和法规则。法规则是法规范所依据的准则,是法规范之所以如此确定的依据。法规范是对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做出具体的指示和规定,相关的法主体可据法规范作为或不作为,而法规范所指示和规定的内容,相关法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具体依据,就是法标准。法规则是法规范所包含着的内容,是只有通过对法规范内容的分析提炼,才可发现的具有规律性的法内容。而法标准是法规范之构成内容,没有法标准就不能构成真正的法规范。
二、法标准不被重视及其后果
法学研究中常涉及“标准”问题,但学者很少重视从理论上对法标准进行研究。我们能见到一些有关“标准”的法学文章,如:有讨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或证据法中的证据标准的文章,有讨论侵权法中的理性人标准和普通人标准、信托法中的投资标准、产品责任法中的缺陷标准或著作权法中独创性标准和合理使用标准的文章,也有讨论赔偿法中的赔偿标准的文章,更多的则是讨论生产安全标准或产品质量标准的文章。还有一些稍具法理意味的关于“标准”的讨论文章,如关于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良法的标准、法制现代化的标准或地方立法的标准法的文章。这些关于“标准”的法学讨论为我们进行关于法标准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但不可否认,这些文章都不是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讨论法标准问题,法标准问题在法学研究中从来没有像法规则问题、法规范问题或权利义务问题、正义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那样受到过学者的重视。
法理学很重视法规则、法规范,甚至很重视法概念,但不讨论法标准。无论是法理学专著、论文还是法理学教科书,皆不涉及法标准问题。其实,规范主要不是由概念构成,而主要是由标准构成。不重视标准就难以建构真正的规范。按理说,规范之中包含着标准,研究规范也就意味着必然会研究到标准。但法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是,因缺乏法标准的概念,也就自然缺乏研究法标准的意识,所以,即对于法规范有很多的研究,也很少有人分析法规范之中所包含的法标准,其结果是对法规范的研究也难以真正地深入。法学研究关于法规范与法规则之间时常出现的概念混淆,应该是这方面研究难以深入的症结所在。
规则是规则,规范是规范,标准是标准。法学既要重视法规则研究,也要重视法规范研究,同时也必须重视法标准研究。不重视对法标准的研究,不仅会导致法学理论对法标准的忽视,导致对法规范和法规则研究的难以深入,更可能导致立法、司法、执法之中对于法标准的忽视。事实上,长期以来法学不研究法标准,已经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这就是法制现实之中出现了许多不含法标准的法律,而司法过程和执法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忽视法标准、乱设法标准、不顾法标准的问题。
(一)立法中不重视法标准
没有法标准的法规范,在现实法制中的体现就是没有法标准的法律。
法律难于在司法和执法中具体施行、具体落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应该是法律(法规范)之中缺乏具体的法标准。
法律难于在司法和执法中施行、落实的原因有很多。我大致同意周旺生教授的一个观点,即中国法律难以实行的根源主要是立法质量差。周教授指出,“二十年来产生数以百千万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绝大多数没有起到法所应起的作用。已制定的四百个法律中,司法机关经常据以办案的只有三十几个,适用法律比较多的法院,所适用的一般也不超过五十个。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和其他许多官,眼睛所见的、知识结构所盛下的、观念所认可的,大体上就这三五十个法律。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宪法司法化问题,殊不知,岂止是宪法未能司法化,更严重的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法律也未能司法化。”他认为,立法质量问题是中国法律难以实行的根源问题,而立法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理念、技术、制度三方面,其中“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实际运作者,普遍不谙运用立法技术”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他举了宪法、婚姻法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例如,宪法中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公民的神圣职责”。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③
类似的例子很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认为,这些法律(法规范)条文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法标准。
宪法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国家规则和社会规则,或者说是确立公民的权利义务规则和国家机关的权力责任规则,而非确定具体的规范。其条款中不含有具体的标准性规定,是正常的。其中“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第四十二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第五十五条)等规定的主要问题在于会导致作为职责的劳动或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或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的难以区别,因而导致“职责”概念之法含义的虚化。宪法是确立规则的,但宪法的规则需要设立相应的法律使规则具体化为规范。在宪法之规则通过法律具体化为规范时,法标准的作用就突显出来。因此,宪法条文中虽无需出现法标准内容,但却必须为法标准的确定提供基础。所以,“光荣”和“神圣”之类皆难以确定标准的词语就存在问题,而以“光荣职责”、“神圣职责”之类虚业“职责”概念,则会使法律制定难以为职责确定法标准。
法律的功能是确定公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规范和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履行责任的规范,必须确定具体的法标准,没有标准的法规范是难以遵守和执行的。“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婚姻法第四条中的规定)即便是道德要求也嫌过于粗略。作为法规范,何为忠实,如何履行忠实,不履行忠实后果该如何,都需要做出含有标准的规定。假如这些内容在其他条款中已经含有,就不需要再设置这样的虚玄条款。婚姻法中类似的缺乏标准的规定还有,如第六条中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第十六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何为晚婚?何为晚育?多大的年龄结婚生育才算是晚婚晚育?由谁鼓励?如何鼓励?是否全社会所有的法主体都有鼓励的义务?不鼓励的后果是什么?计划生育是指计划少生育、计划多生育还是计划不生育?假如是指各类计划着的生育,这样的条款还有何实际意义?同样,“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中的规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标准是什么?鼓励的标准又是什么?国家如何鼓励?国家不鼓励或不恰当鼓励承担怎样的后果?这类缺乏具体法标准的规范,如何在司法或执法中落实?
所以,假如立法理念、技术、制度皆存在问题,那么,其中主要的问题应该是立法理念、立法技术以及立法制度都不重视法标准的问题。
(二)司法中乱设法标准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这一刑法条款的内容规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标准。一是贪污数额标准:十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不满五千元;二是处罚标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可并处没收财产),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减轻处罚、免予处罚或行政处分。这些标准相互结合构成有关贪污犯罪的认定和处罚标准。其中较难把握的内容是所谓“情节轻重”,需要另立标准才能确定,不然可能导致法官的裁量权过大。
但“情节轻重”问题与司法现实之中的“起刑点”应该没有关联。我们从刑法的这一规定中看不到任何有关“起刑点”的内容,即从这一刑法条款的规定看,即使行为人仅贪污一百元甚至是一元,都构成贪污罪。情节因素应该只是量刑的参考,不是构成犯罪与否的依据。所以,司法现实中存在的关于贪污犯罪的“起刑点”标准,是司法违背刑法规定的乱设标准。司法现实中,已没有一例五千元以下的贪污行为人被追究为贪污罪的个案。这意味着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中已有一款内容被搁置不用了,因为我们很难确认实际生活中所有五千元以下的贪污行为全都是“情节较轻的”。
1952年,刘青山贪污1.84亿元、张子善贪污1.94亿元,被枪决。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今币一元。所以,当时贪污罪的死刑标准是不到2万元。1990年代,沿海发达地区,贪污10万元判10年,20万元判无期,40—50万元判死刑。2000年,胡长清贪污受贿500多万元,判死刑,但红塔集团董事长贪污几千万元,没判死刑。深圳海关关长赵某受贿900多万元,判无期徒刑;2004年,“安徽第一贪”尹西才贪污570余万元、违法所得127万余元,财产来源不明1901万余元,判死缓。贵州省委书记贪污受贿677万元,赃款全部追回,判无期。其儿媳贪污受贿500万元,全部追回,判15年。现在一般是贪污几千万元才判处死刑,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河北省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贪污受贿4744万元,皆判死刑。对照刑法的规定,有关的法标准已被弃置不顾了。
与贪污罪有点类似的是盗窃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盗窃罪没有具体的数额规定,但与贪污罪不同,它有“数额巨大”或“多次盗窃”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缺乏具体的标准,但既然有这一要求,应该说明,盗窃犯罪的构成要求比贪污犯罪的构成要求是高一些的。但司法的现实却是相反的,从对两类犯罪的具体处罚来看,五千元以下的贪污犯罪案例不可见,五千元以下的盗窃犯罪案例却是常见的。法制现实中的具体标准与刑法规范中规定的标准是相反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法标准的混乱。
同样盗窃1000元,在陕西汉中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徒刑;在广东东莞一般只是普通治安案件,至多拘留15天。这又是一种法标准的混乱。据说,广东将全省分为三类地区确定起刑点:一类为2000元、二类为1500元、三类为1000元。这种标准设立的依据是什么,应该需要讨论。对照贪污罪的起刑点,我们更能发现刑事司法中的法标准是多么混乱。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中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一刑法规范没有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规定量的标准,应该是意味着只要存在这类虚开发票行为即属于犯罪。另一方面,这一法律规范中没有规定死刑,但法制现实中,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而获死刑者不乏其例。
全国第一例虚开增值税发票大案是浙江黄岩的陈二头、邹瑞华虚开增值税发票1.48亿元案。陈二头非法获取暴利近30万元,并造成2523万余元国家税款流失,1995年被判处死刑。浙江金华一团伙虚开增值税发票额达60多亿,1998年11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犯罪人胡银峰、吴跃冬、吕化明死刑,吴瑛死缓,潘浙江无期徒刑,吴伟堂15年徒刑。2004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899亿余元、造成国家税款大量流失的广东潮阳朱氏兄弟被武汉市中院分别判处死刑。2005年,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62万余元、骗抵税款76万余元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城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被该市花山区法院一审判处罚金40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宫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案犯胡叶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些案例促人思考:刑事司法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突破刑法规范中的法标准?如何突破法标准?突破后由谁确定新的法标准?如何确定新的法标准?
(三)执法中不顾法标准
2006年4月,江西南昌街头,一交通民警在一公里长的非通车路段上,不出示任何工作证件,不管司机在场与否,边拍摄边贴罚单,5分钟内开出16张罚单。后来面对舆论的质疑,有关交警部门解释:该交警当时因家庭纠纷,情绪不佳,作出了“情绪化”的执法行为。“情绪执法”一词因此而生。情绪执法并非个别现象。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的魏文华总经理路过竟陵镇湾坝村,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掏出手机录像。当即遭到数十名城管的围攻。在“干脆打死他算了”的叫嚣声中,魏文华当场毙命。情绪执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不顾法标准。城管执法的最大问题就是不顾法标准,没有法标准。
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新闻出版署规定淫秽出版物内容包括七种:一、淫亵性地具体描述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二、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三、淫亵性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四、具体描述乱伦、强奸或者其他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五、具体描述少年儿童的性行为;六、淫亵性地具体描述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七、其他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的淫亵性描述。这些法律规定的共同特点是,以描述性规定代替标准性规定。“淫秽”“具体描绘”“具体描述”“具体描写”“露骨宣扬”“诲淫性”“色情”“淫亵”“不能容忍”之类皆是描述性词语,都需要明确的认定标准,缺乏认定标准必然造成司法或执法中的问题。这就是立法标准的缺乏问题。这种立法的标准缺乏更导致现实中司法执法的无标准,致使淫秽物品被随意认定,相关行为人被随意处罚。相关学术界和业务界强烈要求对淫秽物品做出标准性法律规定,特别要求对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做出情色或色情的分级,是很合理很必要的。
给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按其所含的情色或色情内容做出分级,如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是很有道理的。我国在法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等方面是对人分级的,如分为完全责任能力、部分责任能力和无责任能力。依据类似责任能力的划分,对应文艺作品的分级,我们可以确定一定的法标准:三级文艺作品的读者受众只能是完全责任能力人,二级文艺作品的读者受众可以扩大至部分责任能力力人,一级文艺作品的读者受众才可以是所有的人。
三、法学研究不重视法标准的一种可能的原因
法学研究长期不重视法标准,可能有很多原因。笔者这里做点推测,分析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标准问题长期是政治话语中的问题,法学界有意回避标准问题。
政治话语中的标准问题始于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那个大讨论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成了政治话语中的一种标准语式。讨论中对于这一标准政治话语的一些误解则误导了许多学者,致使“标准”“实践”“真理”等概念关系越来越模糊。
因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标准语式,许多学者误认为实践即是标准,标准即是实践。这样的思路延伸到法学界,自然会产生法律标准即是法律实践(司法实践、执法实践)的认识,而这样一种认识既没有法学价值也缺乏法律价值。所以,法学界回避“标准”问题也就顺理成章。
但实际上,认为实践即是标准或标准即是实践,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的产生当然有其原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语,在大讨论开始的最初,其标准的表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的产生和在全国产生巨大的效应,有当时客观政治形势和背景的原因,并且应当蕴含着当时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智慧。但这种表述导致了人们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误解,进而模糊甚至混乱了“标准”“实践”“真理”等概念间的关系,这是难以否认的。我认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应该恢复恰当的理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依据标准检验真理需要实践,即实践是依据标准检验真理;一是按照真理检视标准需要实践,即实践是按照真理检视标准。所以,无论是依据标准检验真理,还是按照真理检视标准,我们都需要实践。这其中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实践是实践,真理是真理,标准是标准。标准可以做为真理的依据,真理可以作为标准的前提,标准和真理之间可以相互检视和验证,这种检视或验证可称为实践。在科学,这种检视或验证的实践称为科学实验;在社会,这种检视或验证的实践称为社会实践。
法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法律的制定和施行更只是一种社会运作。所以,法学或法律意义上的真理其实只是一些基于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共识。这些共识化为法律规范,所包含的是一些具体的关于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标准。所以,法学不必强调真理问题,只需重视规则问题和规范问题。哲学中的真理、标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到了法学,就应该是规则、标准(表述为规范,在规范中表述)和法律施行的关系问题。法律施行,即具体的司法、执法,正是按照规则检视标准,或依据标准检验规则的过程,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过程称为实践,即法律实践或法制实践。
如此说来,法标准不仅是法规范的构成内容,而且应该是检验法规则的依据。所以,法学研究没有理由不重视法标准。
注释:
①《朱子語類·樂古今》:“十二律自黄鍾而生。黄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黄鍾是,便入得樂。[道夫]”
②《汉书·律历志》中说:“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
③参阅《法律难行与立法质量——立法学和法理学专家周旺生教授访谈》一文,见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网http://w3.pku.edu.cn/academic/legislation/lilunxueshuqianyan/qy_flnxylfzhl.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