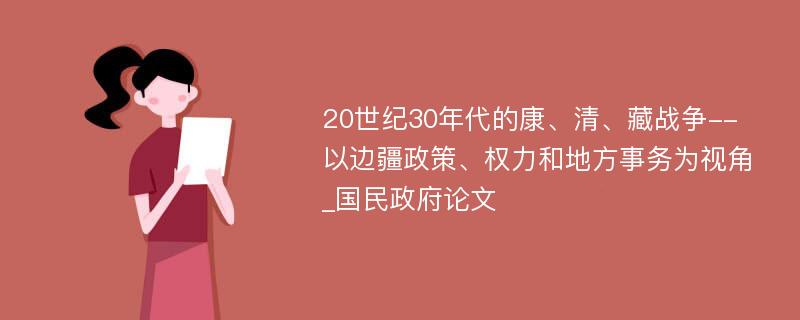
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权力论文,年代论文,战争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有关第三次康藏战争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①。这些研究大多在强调中央政府治藏以及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等议题的同时,把康区刻画成一个“边界”性质模糊的单一整体的区域。当然,这样的观察角度并非不妥,只是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对当时发生在康、青、藏边界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在康藏战争以及整个西藏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支配或被支配的复杂情形的探讨。因此,本文的任务是,把第三次康藏战争置于国民政府的边疆政治议题以及康、青、藏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的权力互动之下来加以理解,借以恢复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的丰富内涵。
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良性互动下的康藏边界战争
维持边疆地区的完整与统一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必需面临的重大课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当时的边疆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而就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来看,自1918年汉藏双方订立临时停战条约规定的7年早已期满,而汉藏悬案仍未解决,康区局势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迫使西藏在康藏边界维持一支强大的武装,由此给西藏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同时,当时流落在内地的班禅势力也被西藏地方政府视为一个重大的威胁。加上西藏财政窘困,许多日常物资均需通过汉藏边界输入②。上述种种因素促使达赖主动与国民政府接触,以改善西藏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
1929年8、9月间,时任北平雍和宫主持的贡觉仲尼先后求见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与蒋介石,转达了达赖喇喇愿与中央改善关系的诚意。国民政府遂派贡觉仲尼为慰问专员,入藏宣传中央德意。次年8月,贡觉仲尼回京复命,并被达赖喇嘛派为西藏总代表,加派楚臣丹增等为代表,常川驻京,就近接洽藏事。③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开始重新走向正常化轨道。然而,就在汉藏关系日趋改善的关键时期,康藏边界却在1930年5月发生了大金寺和白利土司之间的土地差民争端,其后,经过种种因缘际会的复杂演变,最终形成了汉藏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大金寺和白利村皆甘孜所辖之地,分隶于朱倭、白利两土司。其中有白利土司家庙之一的雅拉寺住持亚拉智古,转生于大金寺所辖的林葱之桑多家。亚拉智古在从西藏学经归来后,因白利土司之请,来主持雅拉寺。与白利土司的其他二家庙相比,雅拉寺由于其历史上的原因对白利地方更具有政治发言权,因而也造成了其它寺庙主持的嫉妒与不满,并随后拉拢土司,以排斥雅拉智古。于是,土司一方即将雅拉寺所辖土地凭证及文契一并呈缴。雅拉智古鉴于形势于己不利,遂决计回大金寺,并将雅拉寺财产及15户差民,均带归大金寺。15户佃户的划出,无疑会增加白利人民上粮支差的负担,白利人民不愿,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大金寺派代表请韩知事秉公断处,但是韩却置此案于不顾。大金寺中激烈派见县署既不受理,遂主张武力压迫,并于1930年5月21日,突占白利村,大肆焚掠,战端由此揭开。
大金寺的和平派喇嘛见事态进一步扩大,畏惧官府镇压,于是请求多方调解。而此时的韩知事已呈请辞职,不但不作任何调处,还请派军队来甘防范,企图卸责。当时驻康定的川康边防军旅长马骕见甘事日趋严重,一面函嘱驻甘罗海宽营准备用武;一面派遣参议朱宪文、军法官马昌骥前往调解。但是西康当局这样做纯系表面文章,并“无谋和诚意”④。况且“驻甘军队,亦思借此邀功,暗阻和议”。面临这种情况,大金寺又派专人到青海结古请求玉树边防部队司令马彪来函代为乞和,“复遭康定当局拒绝。复书态度强硬,有会师昌都之语”⑤。实际上用兵之形势已成。迨调解员朱宪文等离甘后,西康军政当局委42团马成龙团长为征甘先遣司令,于1930年7月8日占领亚拉寺。大金以战端既开,遂求援于藏。由此可见,在事件的开始阶段,作为当事一方的大金寺还是抱着和平的态度寻求协商解决的,其后西康军政当局的武力征讨态度是促成大金寺求援于藏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在大白事件的开始阶段,藏方并不想介入西康内部的争斗,以挑起汉藏间的军事冲突。当时西藏驻昌都的前员东代本于大白纠纷发生之初,就曾复函罗海宽营,有“遵守条约绝不干预”的表示。夷商长银巴及其他商民也认为西藏方面绝对不会参与此事,“因实无力帮助大金寺开衅”⑥。1930年7月8日,当川康军占领亚拉寺后,藏军得墨色代本在大金的邀请下,率兵进抵德格。从动机上看,藏军并非主动要求参战。而且即使在得墨色代本进抵德格后,也曾主动函商马成龙和平处理。同时,瞻化县知事张楷在8月1日的报告中也认为藏方并没有援助大金寺,“擅行肇衅”的意思。⑦藏方在大白纠纷初期的这种态度与当时西藏内部的情况颇有关系。当时西藏大局颇为安定,“从多方面观察,达赖实有倾向中央与希望早日解决中藏问题之意”。西藏人民也“一致希望中藏和好”。而且由于经济落后,西藏方面也迫切希望国民政府有所救济⑧。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方面并不希望介入大白事件而挑启战端,打破来之不易的汉藏和好的局面。而川康当局一再渲染西藏方面的军事行动无非是出于征伐有名,借此邀功而已。
二、康案谈判中的国民政府与川康当局
到了1930年8月,由于大金和川康当局的和议无望,川藏双方军队开始陆续向甘孜方向增援兵力,当时驻甘川康军队中的一部乘大金方面不备,夺取了热登咱,遂与大金正式接触。8月31日至9月2日,川康军收复白利寺,取得小胜,随后对大金寺形成围攻之势。西藏方面慑于武力,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川康军撤兵。国民政府为维护汉藏关系的大局计力持和平解决主张,要求刘文辉迅速撤兵并解决纠纷⑨。然而,康藏前线的紧张局势并未因此缓和。1930年12月,藏方援军陆续开到甘孜前线,与大金联合,康藏双方渐成对决之势。1931年2月9日,藏军趁川康军不备,开始大举猛攻,康藏战争全面爆发。
康藏战争的爆发为国民政府直接介入康藏边疆事务提供了契机。1931年3月25日,国民政府鉴于康藏局势已极险恶,非由中央派员亲赴西康实地调查,不足以明真相而资调解,遂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专门委员刘赞廷前往西康,负责调解大白纠纷。同时由蒙藏委员会电请刘文辉协助进行,并请达赖派定专员前往大金会同处理。但是唐柯三尚未动身,藏军就已经进据甘孜,随后又向炉霍、瞻化方向进逼。虽然国民政府分电达赖及川康旅长马骗停止军事行动,静候调解,但是战局还是处于不断扩大之中。当1931年5月唐柯三到达成都后不久,瞻化即告陷落。其后,藏军一面由甘孜攻炉霍,一面由江卡犯巴、盐,复由瞻化扰理化,康区南北两路均感动摇,炉城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一时之间,全康震动。
1931年6月11日,唐柯三在各方的催促下抵达康区,开始了与藏方的谈判。但是从1931年6至7月间,双方就在会议地点和甘、瞻等问题上争执不休,达不成实质性的结果。推其原因主要在于藏方在军事得手后,企图回避实质性的谈判以强占甘、瞻。这样一来,大白纠纷的谈判势必要触及关涉汉藏关系的康藏界线问题。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唐柯三的责权范围。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先就大白纠纷进行调解,康藏问题则另案办理⑩。
由于和谈的希望逐渐破灭,刘文辉于1931年9月2日、6日连续向国民政府请求以武力收复失地,表示“如中央畀以筹边全责,补助饷弹,并饬青滇协助,不但收回甘瞻,并可恢复全康。”(11)对于刘文辉的要求,蒙藏委员会出于种种考虑仍决定康藏交涉事宜由该会办理,主张和平解决。而对刘文辉再三要求饷弹一事,蒙藏委员会认为“事关军备,中央暂时恐难及此,且川军纵得饷械,亦未必即图远略。”(12)明确表示了对刘文辉的不支持与不信任。
恰在此时,国内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九一八事件的突然发生,迫使国民政府迅速解决大白纠纷,以便一致对外。而此时西藏方面在川康军武力的威慑恐吓下,也同意办理大白案件。1931年11月7日,在经过冗长的磋商后,汉藏双方终于议定了解决大白事件的8项条件(13)。该协定是在搁置康藏疆界问题下签订的,实际上默认了藏军暂时占领甘、瞻等地。这对于在该地区有着实际利益的刘文辉来说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此条件一出,立即招致川康当局的强烈反对(14),并通过种种途径向外界宣传康案谈判事实,起了舆论界,特别是旅京康籍人士更大、规模的抗议(15)。同时,西藏方面也因为格桑泽仁正在中甸就滇康边区宣慰使职和青海方面在青藏边界的界古增兵二事,表示“大白案须再延日期”(16)。迫于上述种种情形,蒙藏委员会要求唐柯三“暂勿签字”(17)。1932年2月10日,汉藏双方的交涉专员声明解除交涉责任,康案谈判宣告破裂(18)。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2年2月29日不得不决定康藏纠纷事件交刘文辉办理。(19)
三、康、青、藏战争中的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的权力诉求
青方界古增兵发生在大白事件谈判的关键时刻,不禁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事实上,正当1931年底国民政府因西藏方面抗议青海界古增兵而要求界古青军和平处理、时,据刘文辉电称,界古方面已经向藏军发动了进攻(20)。而青海方面却在1932年1月13日向蒙藏委员会表示,界古驻军系换防而非增兵(21)。就在青藏边界局势恶化的同时,川康方面也开始制定详细的对藏作战方针和步骤,其明确的目标就是压迫藏军退出金沙江两岸。随后,川康当局有关藏军异动、进攻的电文增多,战争随着康案谈判的破裂再次发生。
此时西藏所面对的是两个对手、两条战线。1932年2月,由于藏军在康藏战场失利,恐玉树驻军马彪乘机袭击,腹背受敌,而此时正好发生玉树商人与尕旦寺僧侣因销售货物的价格问题所发生的商务纠纷事件。尕旦寺僧侣在玉树商人坚不让步的情况下,转请昌都藏军司令砍郡达哇予以支持,于是藏方于1932年3月24日以千余之众,攻占大小苏莽地方,复于4月4日以兵千余将囊谦占去,致使青军退驻吉古,随后藏兵四面云集结古附近,拉卜寺之藏兵日渐增加,结古亦岌岌可危。而马步芳为了达到称霸西北,扩大地盘,充实军事实力、转移蒋介石、胡宗南对甘青权力企图之目的,就借此纠纷小题大做,故意渲染边疆紧张气氛,对青藏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2)。
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由于东北失守、淞沪战事方终,国难严重,因此迫切希望康藏边疆和平,恢复汉藏在战前形成的良好局面,以解除西顾之忧。于是分电交战各方和平调解。但是对康、青军阀来说,康藏战争正是巩固自己在边疆统治的大好时机。正当国民政府在康青藏战争中一筹莫展之时,康、青地方军阀却趁机联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同时在保卫边疆的招牌下频频向国民政府索要饷械(23)。
在青、康军队的协力反击下,西藏军队迭迭败退,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康区北路战场,1932年7月29日,川康军直抵金沙江岗拖河渡口,藏军大部向金沙江西岸退却。在康区南路,1932年8月,马成龙部会同格桑泽仁的康南民军与藏军激战于巴安,不久巴安之围告解,藏军退出金沙江以东地区(24)。而在青海南部战场,1932年8月27日至9月4日,青海方面军队先后克复大小苏莽、囊谦等地,藏兵退至昌都、类乌齐一带,至此青海南部辖境已无藏兵踪迹。随后青海部队乘胜追击,深入西康境内百余华里,占领了1919年藏军侵占之石渠、邓柯等县城,并与川军协商,克期会攻昌都(25)。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方面在加强边界防御的同时要求英印政府提供援助。但是英国却对西藏方面的要求表现得甚为犹豫和推托,只表示仅在外交上予西藏地方以支持(26)。于是,在英方的外交压力下,国民政府下令康、青军队停止进攻。随后,为了和平解决康藏问题,1932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召集各部、会及川、滇、甘、陕、青五省当局代表举行西防会议。由于西防会议上各地方势力乘边疆危机所提出的要求对国民政府来说并没有形成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康、青、藏边界的防务问题,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决议(27)。
然而在国民政府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此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时局变迁导致了康藏边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解决了西防会议上所没有解决的边界停战问题。就西藏方面来讲,由于在对抗青、康战事中失败,引起了藏内政局的动荡,加上连年战争,西藏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的境地,无力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攻。而在川康当局方面,至1932年冬,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的四川联军反对刘文辉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加上康藏地区冬季到来,两方均感难于作战,为避免两面作战,川康方面不得不与藏军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应付川局。于是,川藏双方代表遂于1932年10月8日订立冈拖停战协约,是项停战协定的订立,暂时结束了康藏地方间因大白事件所产生的两年多的军事冲突(28)。随后,青藏和议也在1933年6月15日签订。这些条约的签订至少使得青、康当局实现了当初预想的战略目标,在地区战略利益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目的。
不可思议的是,上述一系列停战协定的签订却是在事先没有征求国民政府意见的情况下完成的。岗拖和约是在国民政府所派监视青海的祭海专员陈敬修于1932年10月20日向国民政府汇报后,才得知已经签订(29)。同样,青藏条约的签订情况也是等到1933年10月7日(30),当青海省政府报送青藏和约时,才被国民政府知晓。至于岗拖和约,直到1934年3月20日,在国民政府的询问下,刘文辉才把和约文本及签订经过呈报给蒙藏委员会(31)。为杜绝此种流弊,国民政府规定:缔结条约为政府特权,“此后沿边地方长官互结条款,不得擅用条约字样,以示区别。”对青、康军阀无视中央意见而擅签条约表示了不满。(32)
四、大金僧安置、诺那入康、班禅回藏等议题中的边疆战事
1932年岗拖和约签订后的康藏边境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和平、安静。相反,自1933年以来,刘文辉的康藏边境警报便频频向国民政府传来(33)。1934年2月,藏军挟同大金娃围攻邓科,同时分别向白玉、巴安等地进攻,康藏边界战争再次发生。就此次边疆战事的起因来看,虽然藏方青年代本,确有挑起汉藏兵行的企图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大金喇嘛“鼓动的作用”(34)。实际情况表明,自1932年康藏停战以来大金僧问题已成了主导川藏战争的主要因素。
就西藏方面来说,经过1932年战争后,西藏内部的很多人对于昌都噶厦因参与大白纠纷而丢失1918年所占康东领土耿耿于怀。同时,对于大金挑衅所引起的康藏纠纷,“亦不善其所为”(35)。而此时流落在昌都的庞大的大金寺武装频频在康藏边界滋扰事端,致使康藏双方也因此时常处于战备状态,这对于汉藏双方来说都是个重压。大金寺已由西藏地方政府侵康的桥头堡变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安置大金僧成了西藏地方减轻边界压力的重要事项。而对刘文辉来说,由于在1933年四川内战中失败,退据康、雅一隅的他此时急欲通过建省来稳固地盘,因此对于关系康区防务安危的大金僧安置问题也极为重视。而此时的蒋介石不愿刘湘势力坐大,兼并川康,因而也同意让刘文辉保持西康,作为牵制刘湘的工具(36)。于是,各方利益关系的演变最终促成了大金僧安置问题的谈判。
康藏双方关于安置大金僧的谈判从1934年3月开始,经过反复讨论、磋商,直到1935年1月9日,双方始行定议,名为《川康边防总部与西藏协定安置良善大金僧规约》,共8条。此项条款为国民党中央所同意,大金寺方面也表示接受。但是,就在上述8款协议正施行间,复值诺那事变、红军过境,全康鼎沸,以致行将解决之案因而搁浅。
从1935年春开始,在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下,工农红军相继进入川、滇、黔等地。随着红军逼近康境,康藏边界的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西藏从一开始就对红色政权充满了防备之心(37)。1935年夏,当红军进入康区时,西藏地方政府一度相当惊慌,“于金沙江西岸从事调集重兵”,试图防堵(38)。而川康军,为保存实力则对蒋介石的“围剿”红军命令持阳奉阴违的态度。为此,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康区“剿匪”事宜,1935年初,国民政府趁“中央军”驻在康区钳制着刘文辉之际,任命康区著名活佛诺那为“西康宣慰使”,并组织“西康宣慰使公署”入康“宣慰”,配合政治宣传,联络地方势力,名正言顺地改良康区的政治环境。
众所周知,诺那入康宣慰的本意是排挤刘文辉势力和阻击红军,以便在刘文辉地盘里建立起国民党自己的势力。但是,和此前的格桑泽仁入康办理党务一样,诺那的入康也同样引发了西藏方面的不安与反对。驻康藏军于1936年1月,突在巴塘以西一带增兵近2000余人,“情形较昔更为严重”(39)。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康藏边疆的土著计划再次恶化了已出现改善契机的中央与康、藏地方的关系。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西康宣慰使公署并没有达到其最终目标,1936年5月,随着诺那的圆寂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调离康境,刘文辉又回到了西康权力的中心。
除了红军和诺那外,当时已经行进在青海境内的“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也同样对青、康、藏边界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1935年初,由于黄慕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没有预想的成功,于是,通过班禅返藏来解决藏事成了当时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首要任务。对于国民政府公开支持班禅武装返藏的态度,西藏方面表示坚决反对,并决心采取武力拒抗(40)。同时,英国政府也迭次向国民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以阻止仪仗队入藏。然而,班禅和他的卫队仍旧在西藏方面的抗议声中浩浩荡荡地向青藏边界行进。1936年秋天,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演变结果,使康藏边疆再次爆发了一场冲突。
据马步芳等人汇报,从1936年10月到11月初,数千名藏军陆续渡过金沙江,并进犯青边、康北等地,德格、白玉相继失守(41)。藏军此次渡河作战的原因至今尚不明了。国民政府认为此次藏军开衅的主要原因是,藏军藉陈兵边境以反对中央卫队及班禅入藏,其幕后嗾使者当为英方。康藏纠纷未能彻底解决以及诺那事件的影响,也是造成此次藏军东侵的原因之一(42)。但是据马步芳反馈给国民政府的函电所称,藏军挺进白玉、邓科、德格等地,主要在于捉拿邦达昌家族份子,无意与青、康军队发生冲突(43)。边疆战争再次显示出它的复杂与诡异。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西南边疆形势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藏方对班禅回藏的态度转而强硬,并动员拒阻。英国方面也迭次向国民政府表示,在全面抗战的时期,边疆不宜再有纠纷。国民政府也意识到,在当时国际情势下,与英保持友善关系更为急需。再三权衡之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19日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而班禅大师也因国难严重、回藏使命复生障碍而隐忧成疾,遽于同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国民政府在对藏态度上的转变以及班禅的圆寂使得对西藏的威胁解除,而西藏地方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政府在康、青、藏边疆议题上的掣肘。随后,从1938年开始,西藏地方分别与青、康地方政府陆续举行一系列的边疆和谈,并于同年8月、12月先后签订了《青藏和好规则》、《安置良善大金僧规约详细办法》。和此前的边疆会谈一样,上述一系列和约同样也是独立于国民政府的边政计划之外。1938年,由于西藏方面反对而入藏受阻被迫停留在青海的高长柱曾向国民政府建议,以藏方接受国民党中央代表入藏为举行青藏、康藏会谈的前提,同时将中央代表入藏一事列入青、康、藏会谈中,“以地方力量推行中央之意旨”,以示中央权威(44)。但是,此后一系列会谈的结果表明,国民政府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青、康、藏三方则再一次在国民政府势力不在场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青、康、藏之间的利益格局,使1930年代初期所形成的边疆紧张局势得以全面缓和。
五、结 论
本文以1930年代发生在康、青、藏边界的一系列战争为对象,并把这些战事置于康、青、藏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的权力互动以及国民政府的康藏边政事项之下进行讨论。本文认为,在康、青、藏边界战争中,相关各方均在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各自的利益诉求,并在不同程度上按自己的目的操弄着战争。从原则上说,国民政府始终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同时却利用战争的混乱积极在康、青、藏边疆进行权力建构。康、青军阀则在保卫边疆、稳定边防的幌子下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向国民政府索要更多的军事资源,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国民政府在康、青、藏边界地区的势力渗透。在战争的过程中,西藏地方政府在意识到国民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康、青军阀的情况下,被迫与康、青地方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战争。随着边疆形势和西藏内部矛盾的发展,西藏方面的战争政策经历了由观望、介入、扩张、放弃再到被迫防御的几个发展阶段,并在和青、康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后最终确定了青、康、藏之间的利益格局。就战争的结果来看,康、青军阀较战前进一步扩充和巩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西藏地方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边疆战争中失去了1918年所占据的康区大片土地。而国民政府在战争过程中所进行的多项边疆议题,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激发了康、青、藏地方势力的戒备与抵制,最后还是被迫承认康、青地方与西藏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边疆格局的划分。
注释:
①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政策》,《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刘国武:《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王燕:《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②《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报告西藏堪布在蒋介石宴席上谈话情形电》,1929年9月14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141)23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一史馆藏”。
③《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关于1927-1937蒙藏行政设施文稿》(摘录),1937年4月,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141)129。
④唐柯三:《大金白利肇事原因及康藏两军启衅之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
⑤唐柯三:《赴康日记》,《选编》,第455页。
⑥《西康政务委员会为详报大白纠纷原因经过及筹处情形计议办法致刘文辉呈》,1930年7月4日,《选编》,第6页。
⑦《西康民众驻京代表马泽昭等抄呈西康政委会路送办理交涉大白纠纷事件经过有关文件致蒙藏委员会呈》附《西康大金寺叛变情报一本》(四)《瞻化县知事张楷报告》,《选编》,第82页。
⑧《国民党国民政府文官处抄送谭云山呈报入藏考察经过及建议事项函件》,1931年7月1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2)2512。
⑨《蒙藏委员会为达赖电请撤兵大白纠纷仍希迅速调解事致刘文辉电》,1930年10月15日,《选编》,第13页。
⑩《蒙藏委员会为陈康藏纠纷调解近况并妥筹应付方略事致行政院呈》,1931年7月31日,《选编》,第162页。
(11)《唐柯三为商刘文辉同意如中央授以筹边全责可收回甘瞻恢复全康致蒙藏委员会电》,1931年9月6日,《选编》,第185页。
(12)《蒙藏委员会为径函噶伦询其会商真意并表明调解责任范围事致唐柯三电》,1931年9月18日,《选编》,第190页。
(13)《唐柯三报闻与琼让议订解决大白事件八项条件致蒙藏委员会电》,1931年11月7日,《选编》,第221-222页。
(14)管文阶:《大白纠纷始末记》,《康导月刊》第2卷第2期,1939年10月,第16页
(15)(17)《蒙藏委员会为所订康案八条暂勿签字致唐柯三电》,1931年12月21日,《选编》,第240页。
(16)《唐柯三为保刘文辉反对原议八条谈判停顿琼让借口结古增兵谓大白案须延日期等情致蒙藏委员会电》,1931年11月26日,《选编》,第228页。
(18)《唐柯三为报双方声明解除交涉责任藏局破裂在即等情致蒙藏委员会电》,1932年2月22日,《选编》,第255页。
(19)《行政院为康藏纠纷事件交刘文辉负责办理唐柯三回京报告事致蒙藏委员会指令》,1932年3月1日,《选编》,第255-256页。
(20)《刘文辉为请电示结古增兵藏兵布防等情确息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31年12月19日,《选编》,第240页。
(21)《马麟为结古驻军系换防非增兵亦未向西康越境开衅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32年1月13日,《选编》,第248页。
(22)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6页;蔡作祯口述:《青藏战役中我的经历》,李惠民笔录整理,政协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缉,1964年印,第42-43页;《军事委员会为藏兵攻占大小苏莽囊谦等地劝其不得侵犯青海事致蒙藏委员会带电》,1932年5月3日,《选编》,第263页。
(23)《刘文辉为保藏方增兵拟反攻甘瞻日内将有激战请速拨饷械等情致国民政府等电》,1932年5月24日,《选编》,第267页;《陆军新编第九师驻京通讯处未转马步芳报告藏并攻占青海苏囊地方请速拨饷械电致蒙藏委员会函》,1932年5月27日,《选编》,第269页。
(24)陈文瀚:《大白纠纷之始末及收复失地经过》,《康导月刊》第3卷第1期,第48页。
(25)《杨虎城为报击退大小苏莽藏兵并克复囊谦等地情形致军事委员会等电》,1932年10月11日,《选编》,第299页。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2页。
(27)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28)任乃强:《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边政公论》第5卷第2期,第10页。
(29)《陈敬修等为康藏和议青海不可除外应由政府统一办理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32年10月20日,《选编》,第305页。
(30)《蒙藏委员会为青藏和约应否核准请转院核示事致行政院秘书处函》,1933年10月30日,《选编》,第321页。
(31)《川康边防总指挥部驻京办事处抄报岗拖和约及签订经过致蒙藏委员会呈》,1934年3月20日,《选编》,第350页。
(32)《蒙藏委员会为沿边地方长官互订条款只能用规约不得用条约字样事致行政院呈》,1934年8月22日,《选编》,第372页。
(33)《刘文辉为报藏方集兵进逼请示方略事致国民政府等电》,1933年12月11日,《选编》,第332页;《刘文辉为报藏方南北两路及激增并不因达赖圆寂停止军事行动等情致国民政府等电》,1934年1月16日,《选编》,第338页。
(34)《蒙藏委员会为拟具恢复大金寺善后办法提案事致行政院呈》,1934年3月24日,《选编》,第354页。
(35)陈文瀚:《大白纠纷之始末及收复失地经过》,《康导月刊》第3卷第1期,第46页。
(36)张为炯:《西康建省及刘文辉的统治》,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65年印,第28-29页。
(37)《刘曼卿为译录达赖喇嘛告全藏官民书致石青阳呈》附《抄译达赖民国二十一年告全藏官民书》,1933年6月26日,《选编》,第316页。
(38)刘文辉:《西康现况及赵尔丰治康之失得》,《西北问题季刊》第2卷第1-2期合刊(康藏专号),1936年6月20日,第18页。
(39)《交通部密咨》,1936年1月14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141)2717。
(40)《蒋致余关于英帝挑拨西藏地方反对中央政府派专使护送班禅回藏等活动情形密电》,1935年9月9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141)2979。
(4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356、359页;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大法轮书局1948年版,第78页。
(42)《蒙藏委员会为拟定处理藏军东犯一案办法致行政院呈》,1936年11月,《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359页。
(43)《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388页。
(44)《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464-465页。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1930年论文; 蒙藏委员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战争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西藏建设论文; 历史论文; 刘文辉论文; 班禅喇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