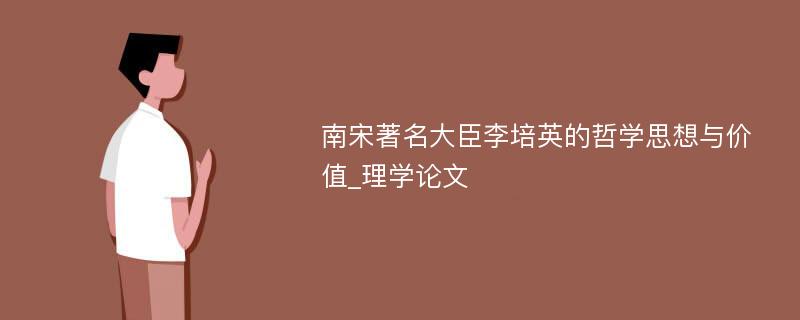
南宋名臣李昴英的哲学思维及其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价值观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名臣李昴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昴英(1201-1257),字俊明,谥忠简,南宋末番禺(今广州市海珠区鹭江村)人。宝庆三年(1227)廷对第三,官至吏部侍郎。史传均以直言敢谏、忠义爱民称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具干济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笔者亦认为,昴英的一生乃直道而行的一生,换言之,他的一生信守儒家理学,并把理学精神具体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
我们知道,理学自北宋以来不断发展,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至南宋朱熹(1130-1200)则臻于成熟,并成为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和行为准则。李昴英生活在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南宋末年,其思想的倾向带有时代的烙印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他推崇朱熹以理学的基本理论重新编注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学今有用《四书》全”(《送循倅黄必昌之官》)勉励朋友;又以“著力莫孤先世望,从头细把《四书》看”(《送演侄三首之一》)警诫自己的侄儿;并认为“《大学》、《中庸》之微旨,朱夫子发挥备矣”(题诸葛钰《北溪〈中庸〉、〈大学〉序》),指出治学之道,乃在于“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而窥圣涯”(同上)。很明显,李昴英把朱熹、陈淳一派的理学理论树立为正宗的理论。
在程朱理学的诸多理论中,昴英对“天理”、“人欲”之说情有独锺。他认为“人欲一胜,则天理必微”(《淳佑丙午十月朔奏札》);又说:“宜益克己,使人欲净尽,天理混融,以全吾固有之仁。”(《跋录曹吴雍所藏邹南谷书墨》)表面上看来,昴英关于“天理”、“人欲”之说,与传统理学关于“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无二。然传统理学,例如程朱一派,却是侧重于人自身的修养,而昴英则是侧重于为官必利国利民。于是在“理”、“欲”的问题上,他即表现出政治家特有的价值观。
什么叫“理”?程朱一派有时把它解释为万物据以生生变化的法则,所谓“人死而气散,理之常也”(《朱子语类·鬼神》),“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朱子语类·理气上》)。有时又解释为是与“气”相为表里的万物生生变化的本原,所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答王道夫》),“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理气上》)。“理”与“气”的关系,成为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昴英则没有纠缠在哲学家的这些论争上,而是按先辈儒者的说法,把“理”理解为“义理”,循着孟子关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告子上》)的定义,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
昴英说:“凡理所安,人心所同者,皆治之基。”(《端平丙申召除太傅赐金奏札》)“理”,即“人心所同者”,亦就是民心之所向,百姓日用之所求。他把理学家论述得玄之又玄的形而上之“理”,具体化为“人心所同者”,故此,他认为“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每事揆之公理,以求合天心”(《淳佑丙午侍右郎官赴阙奏札》)。在李昴英看来,“天”已不再是人类社会的主宰者,而只是人心之所向。故他强调指出:“天人之际本无二致。”(《嘉熙己亥著作郎奏札》)人心之所同,就是“理”,就是“天理”;“天理”也即是人心之所向。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理直气壮地说:“民,天民也”;“职,天职也”(同上)。他之所以把“民”的地位放到“天”的位置,是因为“民心”之所向就是“天理”;他对为官的职责赋予“天”的重任,是因为为官者必须处事以公,必须符合天心,即符合民意。所以,昴英接着说:“以吾之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转祸而福矣。”“即一人之心,合千万人之心,庶可以易乱而治矣。”(同上)
昴英这一见解,表明了他已从空谈“性”、“理”的正统理学窠臼中走了出来,而更多的是以政治家的价值观去看待“天理”与“人欲”。
他认为,读圣人书的价值,不徒表现在诵读章句,而主要是在于涵养性情,培养刚正之气(见《除正言上殿奏疏》),所谓“心正,则笔正矣”(《方帅山判序》)。但他接着指出,做到为人端正,心无邪念,不但可以“破众史百氏误,以祛天下后世惑”;更可以“锄恶束奸,恤窭伸枉”(同上)。显然,其理论的立足点乃在于生民、养民、为民除害,这一天下大治的问题。换言之,李昴英是在理学思维的基础上,以“天理”、“人欲”为基础,探求治国理民之路。
在这方面,李昴英曾作了大量的论述。他说:“君子立言,不独以书传也。苟于世教无关,于国人无裨,不过组篇镂句,落儒生口耳;虽或可托姓名以不朽,而萎然无复生意矣。”(《游忠公〈鉴虚集〉序[代]》)“雄深崛奇之文,自名一家,人争宝之,价诚金珠矣;使非切于时,无裨人之国。亦徒可玩而已矣。”(《题章公权〈进论稿〉》)他认为,研究学问的目的,必须有利于国计民生,所以,他称赞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一文虽短小,但远胜于扬雄《太玄》之洋洋数万言;又认为,柳宗元虽以文章著名,但总比不上韩愈的一篇《谏迎佛骨表》。因为刘向、韩愈能置个人生死利益于不顾,直言时弊,有益于国,有利于民。
“益国、利民”乃昴英思想的核心,亦是他一生的追求。他毫不含糊地坚持孔子儒家关于“仁者爱人”的思想,认为“君子仁民而爱物,爱出于仁,而民又先乎物者也”(《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因此,为官者的首要职责就是爱民、利民,“每谓我辈得行所志,必惠利生民为先。”(《送循州余法掾仲宣之官序》)“苟其位、其力可以利众庶,而呻吟叫呼在吾境若不闻,良心安在哉!”(《寿安院记》)
那么,如何能做到循人心之所同者,抑一己之私以利国利民呢?昴英提出一个“诚”字。他说:“政先及物,诚之流行;问无不知,惟诚故精;事至能应,惟诚故明;诚则无欲,冰蘖自清;诚则无营,轩冕甚轻。”(《祭许象州文》)传统儒家皆把“诚”作为是与“慎独”相关联的,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自我要求。孟子曾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中庸》亦曰:“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朱熹则更从理学家的立场指出,“能去其欲则无自欺,而意无不诚矣”(《朱文公文集·经筵讲义》)。理学家乃至传统儒学皆认为,能诚其意,遵循天理,做到表里如一,则无虚伪之情,更无私欲,自是天理尽见。昴英的理论思维并没有离开这一正统儒家理学的路子,他不仅把“诚”与“精”、“明”联系起来,更是把“诚”看作是“无欲”、“无营”的保证。然而,昴英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充分展示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价值追求。他说:“远民冤甚草菅芟,抗论公庭出至诚。且喜一方全性命,何妨三字减头衔。”(《闻褫阁职免新任之报二首之一》)由于“诚”,无私无欲,一以万民之心为心,以万民之生养为己责,所以能不计较个人的利益,更不惧怕“莫须有”之罪,为民请命,做到以无私无欲之心而存人心所共同之公理。
由于无私,而有理,所以便能无惧,故昴英能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犯颜直谏。他不但敢于直指先帝是昏君:“王媪拥宝扇于斜封墨敕之时,盖由中宗之昏庸。”(《淳佑丙午侍郎官赴阙奏札》)而且更敢于批评理宗对史嵩之等乱臣贼子“委曲包容,惟恐伤之,圣度恢恢,前古未有”(《再论史丞相疏》),毫不客气地指出理宗对史嵩之等人的袒护,“是陛下于正国本犹未勇也”,“是陛下去奸臣未勇也”(《淳佑丙午侍郎官赴阙奏札》)。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理宗发出严肃的警告:“倘以姑息为仁,以不断为盛德,是有春而无秋,有雨露而无霜雪雷霆,非天之所以为天也。”(《再论史丞相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理宗的行为是违逆天理的,而这个“天理”,如上所述,乃“乃千万人之心”,亦即民心之所向,民生之所需。“去欲存理”的哲学思维,在李昴英的政治活动中,表现了独具的价值内涵。
昴英“去欲存理”的哲学思维,是以社会安定、百姓长养为其归宿,而表现其理论的价值。因此,百姓在他的思想中便有了特殊的位置。他认为,圣人、治世之才,不是天生而具,更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蕴藏在千百万人之中,只要我们排除胸中的成见,唯才是用,那么人才自是取之不尽的。他说“千人之群,必有拔乎千人者;万人之聚,必有出乎万人者。谓天下果乏才,是厚诬当世也。”(《淳佑丙午侍右郎官赴阙奏札·第二札》)人才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压抑他们的成长,还是发挥他们的才智。昴英以过人的胆色,一针见血地指出:“而今日之仕进者,苦于远次而观光难,因于举削而通籍难。壮盛之年,骎寻而晚暮;劲毅之气,销蚀而巽柔。幸而一遇焉,而精神筋力已衰矣。”(同上)当权者出于一己,或其所在的小集团之私,压抑异己,使他们难于“通籍”,荒度年华。所以去掉胸中城府,以天下千万人之心为心,以他们之所同好为天下之公理,才能真正发挥天下千万人之才智,才能发理真正有用之才。故昴英又说:“苟徒采于目前,不思搜索于度外,毋乃示人以狭乎?”(《嘉熙戊戌奏札》所谓“目前”,即一己之私;所谓“狭”,即胸中森严之城府;而“度外”者,即天下千万人之所同好。这个观点显然是把理学家关于“去欲存理”的说法具体化,并应用到选拔人材的实践中。昴英以益国、利民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在此又得到一次表现。由于胸中无城府,不以一己之私为限,而是以天下万民之利益为重,因而就可以做到“不以资格拘之,不以绳索束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之功矣”(同上)。彻底打破论资排辈、亲疏有别等人为的障碍,去掉一切成见,唯才是举,就会人才辈出,国富民强;反之,则必然以一己之私,扼杀天下有用之才,祸国殃民。昴英认为,这就是所谓“出理则入欲,去私则进公”(《宝佑甲寅宗正卿上殿奏札》)。理学家关于“天理”、“人欲”的命题,在李昴英的人才观上具有了十分现实的价值内涵。
李昴英是一位敢说敢为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全部社会实践均离不开“去欲存理”的理学思维,故此他亦和正统儒者一样,重视个人的身心修养,认为人乃天地自然之一体,本性乃“善”,所谓“仁人心也,与天地心本不二。如核中有仁,生意在焉”(《寿安院记》)。但是他并没有大谈抽象的人性,而是从政治家的价值观出发,根据这公认的“仁心”、“生生万物的意态”,鞭策统治者拯民于水火,造福于天下百姓。他十分注重自我反省,认为“平居视听言动,之一或非,是先失其恭敬之本,而物欲得以乘之矣”(《广帅方右史行饮酒记》)。人心一念之差,则有动静、是非,甚至祸福之殊。他曾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明摒除物欲,做到自适其安的重要性。他说:“心有动静,地无喧寂。阮籍竹林之游,王戎后至,籍曰:‘俗子来,殊败人意!’戎谓:‘如卿之意,政易败耳!’此山林而动者。贾浪仙炼‘推敲’二字,触京尹前导而不知,此城市而静者。”(《诗隐楼记》)阮籍虽处山林,而心中有所芥蒂,故未能尽山林之美;贾岛虽处闹市,但精诚专一,故能行其所行。显然,昴英要说明的是,只要诚守本心,不受环境左右,不为利欲引诱,直道而行,与天地同体,即以天下万民之所同好为己之所好,则天理自现,而乐亦在其中。
李昴英对后世的影响是颇大的。明代著名心学家陈白沙,从自得之学中,发现昴英思想有可与共鸣之处,称赞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盖亦庶几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文溪存稿·陈白沙序》)。湛若水发展了白沙之说,更从理论的高度,概括“天理”应从“百姓日用”之间“随处体认”。这与昴英之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虽然不能就此说昴英的思想对明代陈湛心学有过什么直接的承传关系,但昴英强调以人心之所共同者为“理”,又以修养之“诚”而见此“理”,从“存天理,去人欲”中,实践利国利民、锄暴去奸的政治目的,却是透露了陈湛心学从程朱理学脱颖而出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