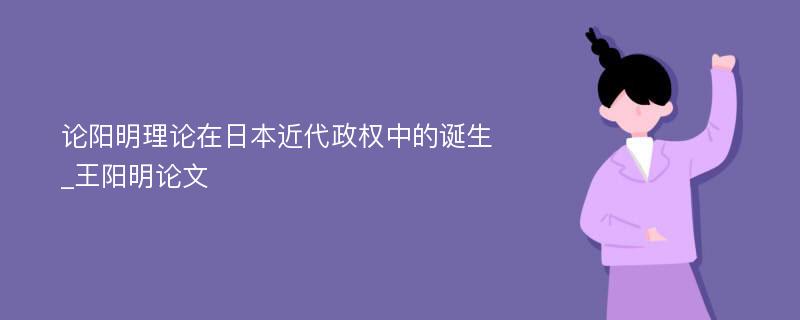
试述阳明学对日本现代化政权的催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政权论文,试述阳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阳明学是明代中期至近代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儒学派别。日本的阳明学虽起源于中国,但它受制于日本的社会历史条件,更多地表现了否定现存制度规范性和重视行动的倾向。这一特性适应了19世纪30—60年代日本封建政权向现代化政权转型的需要,对完成该社会转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世人以阳明为其号,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生活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明朝中期,痛感官方哲学——朱子理学因其思想僵化而无法通过规范社会道德来挽救社会危机,故继承、发展了南宋大儒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提出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说以及“致良知”论,创立了体系完备的阳明学(亦称“阳明心学”、“王学”)。其学说克服了朱熹理论中所存在的天理的外在强制性的理论缺陷,将“天理”移入“人心”,强调“天理”一旦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即能有效地规范主体人的行为,使之弃恶趋善,从而为解决明朝的道德崩溃和社会危机开出了一剂猛药。其理论虽是在主观上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因为其中的许多理念是直接挑战朱子理学权威的,具有反传统的倾向,所以被以后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挥,起到了王阳明未曾预料到的积极作用。
宣扬纲常伦理观念和“大义名分”思想,为幕藩体制辩护的朱子学(日本对具有本国特色的程朱理学的称谓),在17世纪初被日本德川幕府奉为官方哲学。与此同时,适应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需要,作为对官方朱子学的小规模冲击,也出现了日本的阳明学派。19世纪初中期,幕藩封建领主的统治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下级武士不满于贫困化和政治上无权,市民阶级不满于领主们经济上的盘剥和政治上的压迫。迎合下级武士、市民阶层打破现状的要求,日本的阳明学得以全面兴盛。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日本幕末志士们,多是阳明学者。他们充分发展了阳明学说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冲击朱子官学的思想桎梏,提倡思想自由;主张接受和传播“洋学”,寻求新的救国救民之道。同时,他们的无畏精神也得以培育,使之慷慨激昂地投身于“尊王攘夷”运动和倒幕运动。正是日本的阳明学促成了幕末志士的思想蜕变,鼓舞了他们的果敢行动,从而使腐败的封建幕府统治迅速被推翻,以下级武士改革派为核心的推进现代化的新政权得以建立。
二
“心即理”、“心外无理”等理念是王阳明学说的基本命题。若从本体论分析,它们是否定客观事物、否定客观事物之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但王阳明所讲的“理”,很少关注客观事物之理,而是指向朱熹所强调的作为本体论和至高无上准则的“天理”,其主要内容是封建伦理道德原则。他所谈的“心”,其内涵也主要是封建道德规范。所以,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心”与“理”是能合一的;求“理”只能在“心”中,“理岂外于吾心邪”[1] (卷二,《答顾东桥书》)。在王阳明理论体系中,“心”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最高准则。他谈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1] (卷三,《传习录下》)他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尔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 (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的上述论断,出现于长期神化孔子和以朱学为官学的社会环境下,是作为朱熹的“心与理为二”说以及“理一元论”的对立面提出的,其意是强调“心”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独立判断性,鼓吹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揭去了套在孔子和朱熹身上的神圣外衣,有利于迷信传统和权威的人士解放思想。
日本幕末的阳明学者就充分发展了这种倾向。有“明治维新先驱”之称的吉田松阴(1830—1859)是幕末阳明学派的关键人物,他年轻时先后受业于佐藤一斋(19世纪初日本阳明学的复兴者)的学生佐久间象山和叶山佐内,热心钻研阳明学。他后来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李贽)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指日本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者,但学其真,往往与吾真会耳。”[2] (P373)他提倡自得,认为“自得者,得于心也”[3] (P180)。“得字之意须善体味。得者,为吾物,成吾自由之心”[3] (P221)。可以看出,其“自得之法”是阳明学派所独有。洋学家、阳明学者横井小楠(1809—1869)在《学而篇讲义》中也谈到:“为学之义,当就我心上理解。朱注委实细备,然靠其注而理解,则朱子之奴隶,非学之真义。”[4] (三编二章“横井小楠”)在此,可看出他对“心”作为最高准则的理解。这些论述都说明,日本阳明学者强调以心解经,心贵自得;反对死读经书,要求冲决已僵化的朱子学的桎梏,实现思想自由。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只有打破了朱子学的罗网,才能接受和传播“洋学”,改革幕府政治。
三
王阳明学说重“实用”、“实功”和“行”。在此基础上,就为学之道,他有许多重“实用”、重“有用之学”和重“思”的阐述。这些合理因素,被日本幕末的阳明学者继承、发挥,为他们吸收朱子官学之外的“洋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综观王阳明对“致良知”的论述,他是重“实用”、“实功”的。他曾说:“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1] (卷二,《答欧阳崇一》)他认为,若脱离“见闻酬酢”之类的现实生活活动,“致良知”也就无从谈起;若只在语言、口头上论良知,就是“转说转糊涂”[1] (卷三,《传习录下》)。他一反朱熹分知与行为二和“知先行后”的做法,倡“知行合一”说,在知行关系上重“行”,重视“体究践履,实地用功”[1] (卷二,《答顾东桥书》)。为此,在“为学”上,他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1] (卷二,《答顾东桥书》)他说自己的治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1] (卷三,《传习录下》)。日本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是从阳明学者成长为著名洋学家的,他由阳明学而“洋学”的论述为19世纪40—50年代“洋学”在日本的大规模传播开辟了道路。受王阳明为学之道的启发,他也把学问分为有用与无用两种,认为无用之学是“读书讲学,徒为空言,不及当世之务,与清谈废事,一间耳”[5] (P256-257)。他批驳了中国的程朱理学及日本的朱子学,认为:“汉人天地说,秦汉以来,至于周张程朱之贤,影响虽多,得其实则甚少,看而厌之。”[6] (P284)他进而指出:“西学尚实测,早已破虚诬。”[7] (卷二,P26)“泰西之俗,长于物理,取以为资,岂无益哉!”[5] (P283)他提出为学上应“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6] (P413),主张用西方的科学文化补充、发展传统的学说。佐久间象山的这些论述,确实给日本下级武士学习、传播“洋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王阳明在阐述“致良知”学说和为学上,非常重视“心”和“思”,认为思虑是良知的自然发用。如:“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自能知得。”[8] (《全书》二,P64)他还谈到:“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8] (《全书》三,P80)日本的横井小楠也是从阳明学者成长为著名洋学家的,他首先利用阳明学重“心”、重“思”的观点,反对“拘执一偏”的思想僵化的学者和学派,为武士知识分子汲取西方科学文化打开通道。他说:“古之学,皆在思之一字。凡人心之知觉,诚无限矣,使广此知觉,则天下无一物为我心所遗。心之知觉即思,思而会得其筋,则天下物理,皆成我物矣。”[6] (P497)又说:“学问之规模,应致‘宇宙皆我份内”……世之学者,大抵拘执一偏,而狭小我与我心者多矣。”[6] (P498)在此,他认为阳明学的“心外无物”及“宇宙事皆我份内事”一类命题是讲人心知觉思维作用的“无限”性的;如果能充分发挥心的知觉思维作用,那就可以认识事物之理,使“天下物理皆成我物”。与佐久间象山不同,他还以儒学超越性的“道”(“三代之道”)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认为中国、日本与西方各国在“道”面前是平等的。他称赞美、英、俄诸国政治制度的理由就是他们符合“三代治教”。他说:“俄罗斯及其他诸国,不唯广设学校,犹设病院、幼儿院、聋哑院,政教悉由伦理,无不急生民之所急。殆至符合三代治教。”[6] (P445)他由此而为日本下级武士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制造了理论依据。据日本学者不完全统计,自18世纪末“洋学”的前身“兰学”初兴到明治维新前夕,有34所洋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9] (P70-71)。上述洋学塾绝大多数成立于19世纪40—60年代,是“洋学”在日本大规模传播的直接例证。“洋学”武装了改革派武士的头脑,使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德川幕府的腐败,致力于建立追赶欧美的新政权。可以说,这一成就是与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的作用密切相联的。
四
王阳明在阐述“致良知”和为学上,也极力教人无畏和立志。日本幕末的阳明学者继承和发挥了这方面的积极因素,他们不畏幕府迫害,勇敢地投身到“尊王攘夷”和武装倒幕的运动中。
王阳明曾反复说,毁谤等事情都是“自外来的”,不要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8] (《全书》六,P115)还说:“以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1] (卷三,《传习录下》)这一系列的论述,处处呈现出浓重的教人无畏的思想。他在为学和诲人“致良知”等方面,也有许多教人立志的阐述。“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1] (卷二,《答聂文蔚》,由此看出,他是以“明良知之学于天下”、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为己任的,也希望“豪杰同志之士”皆立有此志。他还曾专著《立志说》送给其弟王守文,其中说:“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1] (卷二,《传习录中》)他又对人说:“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1] (卷二,《传习录中》)
阳明学倡导的无畏和立志精神对日本幕末的阳明学者兼志士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影响很大。大盐平八郎(1794—1837)倡导以勇猛果敢的精神改造社会,“当其义,则不顾其身之祸福生死,果敢行之”[10] (P125)。这样的理念成为他1837年领导大阪平民暴动,反对幕府贪官污吏和奸商的直接精神动力。吉田松阴从阳明学的心与理不灭的主观唯心主义生死观出发,提倡不计生死的精神。他在《自警诗》中说:“士苟得正而毙,何必明哲保身。不能见机而作,犹当杀身成仁。”[4] (P389)他批判当时的幕府统治造成了“天地晦暝,人道灭绝”[3] (P163),立志用阳明学的“正人心”来改造社会,因为“洪水猛兽之害人民虽甚,洪水可抑,猛兽可驱;夷狄篡弑虽诚可憎,夷狄可兼,篡弑可诛。人心苟正,四者无足忧。苟人心不正,以何抑洪水,以何驱猛兽,以何兼夷狄,以何诛篡弑?”[3] (P163),他正是以阳明学的无畏、立志等精神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为武装倒幕和新政权改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如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阳明学的无畏精神也时刻激励着“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1827—1877),他说:“行道者,举天下不足为毁,举天下不足为誉,自信厚故也。”[4] (P390)他非常赞服佐藤一斋的立志说,他从佐藤《言志录》中手抄101条言论,借以自勉自励,其中如“象山‘宇宙内事,皆已份内事’,此谓男子担当之志如此”[11] (卷四,P256)。他曾赋感怀诗一首:“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瓦全。我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11] (卷四,P40)1868年1月,西乡率领新政府军队从京都出发,一路所向披靡,到5月迫使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率军投降,从而使倒幕运动取得基本胜利,也终于实现了他的鸿鹄之志。
总之,阳明学作为前现代的思想体系,在本体论上虽然也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使其学说包含了蔑视权威、力行实功、强调无畏和立志等思想理念。当这些思想理念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相契合,就能发挥合理的积极作用,成为反对现存体制的一种精神武器。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日本的幕府末期,阳明学通过幕末志士找到了与日本现代化的结合点,成为日本诞生现代化政权的精神动力。催生日本现代化政权的精神工具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日本的阳明学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