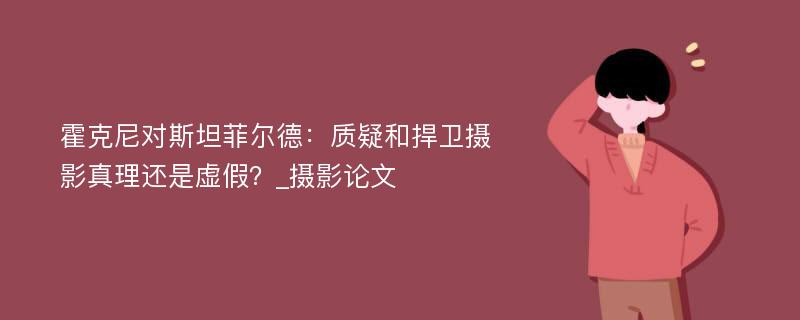
霍克尼VS斯登费尔德:对摄影的质疑和辩护Truth Or False?,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克论文,费尔德论文,False论文,Truth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月3号,伦敦奥林匹亚古董艺术拍卖会上,大卫·霍克尼在接受《卫报》专访时明确表示现代摄影艺术已经成为即将死亡的艺术。由此引来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霍克尼认为,镜头本身是缺乏独立性的,如果它曾经是表演/表现的附庸,那么如今它就是绘画的附庸。他说,摄影是“低人一等”的艺术。
斯登费尔德认为摄影从来都是为影像处理和造假提供空间的。再微妙再极端一点说,任何时候只要人们将世界框在镜头里,就构成了人们对世界的解读。
艺术家霍克尼的激进之辞
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英国著名波普艺术家,据说,他是1960年代流行艺术里最为欢欣鼓舞的标记,也是当年英伦唯一的一个将性欲与乌托邦理想作为创作核心的艺术家。健谈,优雅,和他的作品一样浑身散发着无辜的纯真,他是英国艺术的第一个流行明星。也有人认为,霍克尼之所以知名和广受欢迎,更是因为他为世界的想象力平添了一种颜色,这就是霍克尼特有的激进的“绝对的美”。
如今,霍克尼又站在了聚光灯的中心,不过这一回,似乎有点“偏”。不知道是他站偏了,还是灯打歪了?
“你知道埃德瓦·蒙克对我说什么,他说,摄影师永远也不可能表现天堂或者地狱。”3月3号,伦敦奥林匹亚古董艺术拍卖会上,大卫·霍克尼在接受《卫报》专访时这样说。在访谈中,霍克尼明确表示现代摄影艺术已经成为即将死亡的艺术。由此引来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不过,还是先看看霍克尼本人是怎么说的吧:由于数码相机和电子修片技术的普遍和泛滥,“化学时代”暗房里制造的真实与精确已经消失了,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轻易修改、加工、润色照片,而这种行为败坏了现代摄影艺术的“真实”。同时,霍克尼声称,摄影对他来说早巳经十分“无趣”。
霍克尼的眼中,再没有任何照片或影像能像伦勃朗画中一个邯郸学步的孩子那样抓住人类的温柔天性。诚如费里尼所说,一切发生在镜头之前的都是表演,霍克尼也同样认为,镜头本身是缺乏独立性的,如果它曾经是表演/表现的附庸,那么如今它就是绘画的附庸。他说,摄影是“低人一等”的艺术。
为了举例证明,霍克尼提到了他在西班牙看到的戈雅的《五月三日的枪杀》,画中,戈雅将1808年马德里大屠杀的恐怖景象淋漓尽致地汇聚笔端——“这是任何照片都不能表现的”。这增加了霍克尼对绘画的信仰,他反复强调,绘画可以做摄影所不能做到的。“我们已经不能回头。我们知道卡蒂埃·布列松没有修剪他的图片,因此他是真实摄影艺术的大师。但我们不会再有那样的摄影师了,因为摄影有了‘其他’的途径。”或许霍克尼眼中的摄影,别无他途。
数码相机的普及和泛滥以及电子修片使得拍摄的影像轻易就被强化或者歪曲,就连那些拍摄战争的照片,曾经被认为是最客观地反应真实,现在也值得怀疑了。霍克尼提到了战争摄影的一个例子:美伊战争期间,《洛杉矶时报》曾解雇了一名记者,原因是该记者为使图像更加煽情而将两幅照片重叠合成为一幅。“为什么解雇他?因为他没有运用相机说出‘我在那里而这些就发生在我眼前’。”霍克尼认为,这是摄影最基本的原则。然而,数码时代来临彻底颠覆了这陈旧的摄影观念。“你可以用任何手段随意改变任何照片,不是吗?”这样的结果则是,摄影被越来越近地推向绘画。
如果摄影不再是生硬而纯粹的真实,为什么我们不接受绘画本来就在这个位子上的事实?战争摄影像绘画一样被虚构和编造,然而绘画却可以更深地挖掘被摄影忽略的深层内涵。霍克尼用那幅著名的俄国士兵将红旗插上柏林的照片作为例子,他说:“那人把旗子插在德国议会大厦上——可难道摄影师预先知道他会这么做而事先跑到大楼上去吗?”与此相反,在霍克尼眼中,戈雅的《5月3日的枪杀》却创造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真实,一种超越了证明他是否曾经见证历史事件本身的真实。同时,霍克尼也提到毕加索和他的《朝鲜的屠杀》,毕加索没有随意地描绘涂抹暴力,而是采用极端抽象的方式表达他对战争的理解。这就是超越了真实的真实,就是美。
尽管如今霍克尼厉声申斥摄影艺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许多知名作品都和摄影艺术相关。曾经,摄影和镜头是他创作的独特视角和主题,曾经,他对通过镜头这种“垂死”的媒介观看世界有着极大的兴趣。霍克尼的经典作品《A Bigger Splash》、《比弗利山庄的家庭主妇》(1966)、《克拉克夫妇和珀西》(1970-1971)等一系列作品其实都是在形式上模仿照片的绘画作品。不过,在他的解读中,游泳池的水花,其实是为了呈现相机所不能呈现的一瞬间,其中的幸福感和不可把握感是一种内在的、情绪化的状态,在陶醉与死亡之间,不可言说。那些用画笔记录的瞬间,表现的是他对于不断追求又不断失落的“大地上的天堂”——幸福的理解。在霍克尼眼中,这就是美丽,是人类不可抗拒的东西。而美丽和纯真往往一脉相连:“人类总有能力发现美丽的事物,并为它们打开大门。”当听说有人因为通过网络下载图片而坐牢,霍克尼不禁愤愤道:“一个出于人类好奇的天性而寻找纯真和美的人,在因特网上发现了些图片,就为了下载它们坐了两年的牢。艺术批评家们怎么不批评批评这个?”这就是他认为有必要号召人们重新思考摄影艺术——思考人们看问题的方式,思考图像的巨大力量。“我们该讨论讨论‘图像’,尤其是当有人为此去坐牢的时候。”
数码技术和电子图片铺天盖地而来,甚至将影响带进了霍克尼的家庭,这是他最不可容忍的:“连我的姐姐也疯狂迷上了数码相机和电脑修片,她简直是随意修改任何照片。而且根本不在乎那些照片是否还可信,她只是‘造相’。”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和他的姐姐一样,怀着缺乏内省的热情为了美丽而“造假”,这样虚假的美丽显然和霍克尼眼中那灵犀一现的美大相径庭。
霍克尼认为,摄影,因着对真实的承诺,是一种强悍的原则,而数码技术结束了相机这个一只眼的怪物“从不说谎”的神话。“让我们来看看宗教里的社会制约。比如,教堂曾经用社会制约力控制过绘画,就好像通过镜头看世界那样。当教堂放松对绘画的控制,它自己也慢慢衰落了。如今的社会制约力就在媒体中,就在摄影的根基里。(这种控制的)延续性就在镜像和镜头里。”霍克尼说。
摄影师斯登费尔德的回应
第二天(3月4日星期四)的卫报,由二位记者重新撰写的新闻稿《不再可信的相机?》,对霍克尼的谈话做了断章取义的重构,突出了霍克尼对摄影艺术的抨击。因此,国家摄影电影和电视博物馆馆长鲁塞尔·罗伯茨(Russell Roberts)在卫报上表示霍克尼把问题“过分单纯化了”。他说,自有照相史的那一天,“造假”就相伴而存在。从1840年开始就有数不清的例子可以证明,自摄影史的最初阶段,那些原本被认为真实描述历史事件的照片就是经过高度处理和合成的。而当下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合成影像的思想成为了广大的集体意识。
由于讨论气氛的热烈颇受媒体和艺术界的关注,3月10日的卫报专栏作家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对3月4日刚刚获得“摄影廊城市组摄影艺术奖”的约尔·斯登费尔德(Joel Sternfeld)就摄影和真实的问题进行了专访。
斯登费尔德来自纽约。他的影集《美国展望》初版于1987年,被美国摄影界认为是扣住了美国乡村的脉搏,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当代美国电影和摄影艺术有重要影响。从年轻时代就手持相机横穿美国的斯登费尔德,很早就学会观察并以幽默反讽的态度展现城市与乡村风光、人与自然、科技和毁灭之间的强烈张力。他的照片往往将两种强力的冲突对比所带来的沉重内涵和轻松解嘲的视角相结合:比如,滚滚浓烟和着火的民房背景下,一个消防队员在南瓜农场买南瓜;犹他州的公路上,一群摩托车手停在路边远望着平静优美的熊湖;一只从马戏团逃出的大象精疲力竭倒在公路上,用水冲刷自己的后背……斯登费尔德对流逝的时光的痕迹有着独特的体会,《在这个地方》系列里,他拍摄了在美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地点;他尤其对城市和与之相关的“风景”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沿着高线走》系列中,他沿着纽约市郊一段废弃的高轨铁路,不断选择新视角,挖掘并描绘他眼中的纽约城市生活。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强迫人们——纽约人也包括其他的过路人——停下来,花时间看看周围的环境并且思考。带着忧伤、持久而辛辣,同时又蕴涵着滑稽大度的风格去寻找乡村和城市的真实,在斯登费尔德那里,这不仅仅存在于某个特定地点或某个特定主题,而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在“摄影廊城市组摄影展”中,他的作品被排在美术馆进门最醒目的位置。
作为职业摄影师,斯登费尔德对摄影的理解和霍克尼不尽相同,他认为摄影从来都是为影像处理和造假提供空间的。再微妙再极端一点说,任何时候只要人们将世界框在镜头里,就构成了人们对世界的解读。“比如,我对准两个人作为镜头的中心,而不选择他们后面的那个无家可归的乞丐,或者,我干脆不把那个正往左边走的谋杀犯算在镜头里。在360度里你选了35度,这就是你的照片。做到这一点可以有无穷多的选择,因为照片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
当谈到霍克尼认为过去的战争照片完全反映真实的时候,斯登费尔德说:“说到底,没有什么号称文献式的作品是完全可信的。”霍克尼的说法在斯登费尔德看来,就像认为所有非小说的作品都是现实生活一样把问题简单化了。人们永远都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艺术都是被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人们欣赏照片和阅读的过程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你要自问:我对这个作者,对他的背景了解些什么?我对这个主题了解些什么?”
提到图像处理的问题,斯登费尔德也有不同看法,他承认现在有些摄影师——比如安德里亚斯·格斯基(Andreas Gursky)——的作品是“合成图像”,这的确和1940、50年代的“诚实摄影”不尽相同。但是,安塞尔·亚当斯也一样会往镜头上泼一瓶红色滤光剂,然后花上三天在暗房里曝光遮光,增减图片的强度。这,也是影像处理。就算是大师卡蒂埃·布列松,毫无疑问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最后,斯登费尔德强调说,“摄影之所以神奇又之所以矛盾重重就在于:没有一张独立的照片在述说什么。摄影师的任务是让这种媒介说出你想让它说的话。摄影不可否认是倾向真实和似真性的,但是照片,理所当然是‘说谎’的。”
一边倒的舆论
卫报发起的讨论一时间吸引了众多艺术界从业人员的目光。从事版画复制工作的玛丽娅·莉娜(Marja-Leena)说,归根结底,这是所有和图像艺术有关的艺术家都关心的问题。曾经的暗房技术被计算机代替之后,的确给了操控和修改影像更大的空间,但是,运用任何媒介的艺术家其实都在“假造”他们的图像来表现他们眼中的图景。卫报的前任编辑埃蒙·麦克卡比(Eamonn McCabe)则认为,由于对图片的处理越来越容易,报刊图片编辑的工作的确是越加艰巨。他也承认,摄影反映真实是过去对摄影的普遍理解,尽管这种精神如今已经消失了。“但是,”他补充道,“说摄影艺术已经死亡,这有点愚蠢。应该说我们要随时对周围的事件保持警惕。”更有匿名者评论道:“如果霍克尼认为摄影曾经是反映真实的标准,那他大概一直活在象牙塔里。”所谓的“镜头不撒谎”不过是好莱坞神话,没有人会把镜头里的景象和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物相等同。一个摄影师可以有很多理由选择机械相机而非数码相机,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是因为它们更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如果真有真实存在,那么它源自摄影师,而不是他的工具,这一点对任何艺术家都一样。不是媒介,而是利用媒介传达信息的人对真实负责。
与其说霍克尼讨论的是摄影这种媒介,不如说他讨论的是艺术的本体问题;与其说他反对的是摄影这种艺术形式,不如说他反对的是人们对待图像的态度和图像操控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的现状。只是霍克尼拿摄影开刀,且不说他之成名有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在绘画中加入摄影理念,单就今天摄影越来越成为艺术诸门类中既红且专的显学,其观点又以激进立言,招来一片反对之声实是在所难免。
一场关于“真实”和“伪证”的争论要想获得完美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好像要辨别恶毒的真,丑恶的善和虚假的美一样的不可能。在这个我越不明白变化就越快的世界上,那些可以修改或者尚不可修改的颜色还在不断转动它们变化的潜能。什么是真,什么又是伪,值得质疑的又岂止是几幅图像?也许还应当包括语言和叙述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