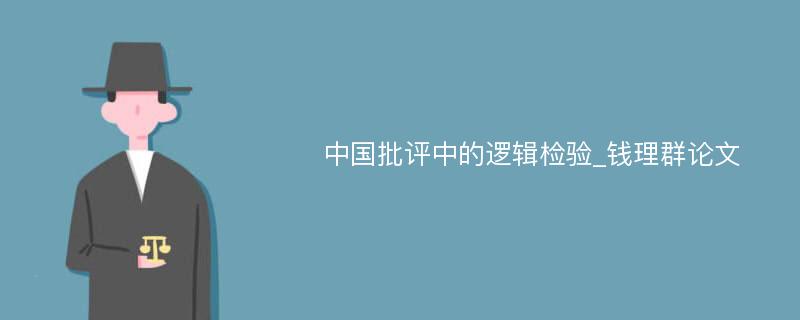
语文批评中的逻辑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语文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人都是摸象的盲人。这句话并非贬义,其中包含这样几个命题:我们都只看到或只选择或只评论了语文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的一部分都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不可以以自己看到的一部分去否定没看到或别人看到的部分。 第一点我们不需要去论证,应该是公理,如庄子在《秋水》所言“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自然要不得,天下之大,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井底之蛙。第二点,我们坦承自己是井底之蛙,并非就要妄自菲薄,井上的那一块天空,毕竟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点,既然我们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是有价值的,那别人看到的那一点也是有价值的,包容与互相借鉴就是正确的态度。然而,如果用自己的“细绳象”去否定或排斥别人的“蒲扇象”,那就是真正的盲人了。在热闹的语文批评中往往有着这样的现象,比如工具论与人文性争执、真语文对泛语文的批判、教言语与教内容的论争、文言文教学的言与文之扯皮,都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或者一合法一不合法,或者非要争个高低长短、嫡庶亲疏,在这类论争中,很多属于不会说理或不讲理的行为,虽然表面上都在费舌论证,但细细考察,却有很多逻辑陷阱。 一、立论中的对抗与排他 语文界的排他性、对抗性立论此起彼伏,实质上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在作怪:强调这个,就是否定与忽视那个;这样做,就等于不那样做;突出你重要,就显得我不重要…… 比如,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不休,本来这两者是一个硬币的天然两面,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们都是存在的,一句和稀泥的话就解决了,那就是二者统一,互相咬合,圈起手臂一起转,就行了。但论者往往一定要分个主次、先后:没有工具性何来人文性?或是没了人文性工具性有何意义?这两问分开来看都各自有道理,但正因为两个都有道理,恰恰表明其争论无价值。明智的教师,往往都会两者兼顾。 在由工具性、人文性之争变了盔甲重新战过的“正道语文”“真语文”对“非正道语文”和“非语文、泛语文”的批判中,这种排他性立论和二元对立思维特别明显。从立名来看,“正道”意味着别人的是“邪道”,“真”意味着别人的“假”和“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讨论方式。而从“正道语文”“真语文”“语文味”的相关表述中,又引出语言形式和内容之对立。比如,有人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语言教学,引用钱梦龙先生的“语文学习的魂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得出“文本的内容(包括思想)不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文本的语言形式才应当成为其主要内容”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发现,钱先生的“魂”是个比喻说法,而一旦引申为“根本”和“主要”,它就有了对抗性、排他性,事实上,不同的学段、学情、文本和习得目标,其教学重心也应该有所不同。文本的形式离不开内容,讲内容又离不开形式,这是一个不能不接受的现实,形式和内容交织、渗透在一起,而非简单的座位并列和先后、上下的关系,既然如此,非要争哪个是主要,哪个是核心,估计一百年也没有结果。倪文锦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道》一文,对什么是“正道”也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为了说明语言形式比语言内容更重要,倪教授列举了几位古代词人表达忧愁的实例:如同样写愁,李后主的《虞美人》、秦观的《江城子》、李清照的《武陵春》便各不相同。倪教授据此而得出如下结论:“当下学生表达中的困难,症结不在内容,而恰恰是语言的贫乏和缺乏多样化的表达方法。所谓‘茶壶里煮水饺——有货倒不出’就是这一现象的形象写照。”湖北的杨先武老师则指出其设喻的问题:诚然,当下学生“语言的贫乏和缺乏多样化的表达方法”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因为情感淡薄、思想贫乏、精神“缺钙”而造成内容干瘪、观点模糊、假话盈篇的状况更是十分普遍;我们不能只看到学生存在“茶壶里煮水饺——有嘴倒不出”的现象,而看不到“茶壶里”本就缺少“水饺”甚至没有“水饺”的状况。倪教授的举例,是为了证明“哪一个更重要”,是为了“排位”;杨老师同样用比喻表明了“无法排位”。我们设想,如果把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定位于“基础”,而不是“最”和“更”,它的对抗性就会消失,而不至于产生“谁的比喻更有道理”的纷争。 二、引论中的诉诸权威 说理者往往喜欢引用名家的话,但是,“引用”的基本作用是告诉人们,曾经哪位名人说过、思考过,他曾提出什么看法。这种引用,属于丰富材料,呈现脉络线索,如果用它们来证明,就需警惕“诉诸权威”的问题——很简单,权威的话,往往有着特殊背景。在言语形式和文本内容之争中,“正道语文”“真语文”共同主张以语言或言语为中心,文本内容是次要的或附带实现的价值。他们往往以叶圣陶的话作为依据。 叶圣陶先生在谈到把“国语”“国文”的名称改为“语文”时所做的解释:“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但这只是说明“语文”这门课程命名的来由(这个命名一直存在着争议),并不能把它当做语文课程的定义。同时,还应注意到一个问题,当年“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及其他早期教育家提出的观点,有其时代背景,是基于全面受教育权的普及、扫盲需要,用普及型教育取代少数人享有的、脱离生活实际的读经教育,当时如此定位语文教学是合理的、迫切的。但问题是,现在的语文是不是还是“语言学习”这个主要任务——如果是,我们的文学教育、经典阅读教育、思维发展、写作教育的目标都将变得“小学化”或身份可疑。在我们的语文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人主张三类分科:语言语法类(或名汉语)、写作类、文学阅读类,虽未在今天正式分家,但恰好说明了我们的语文课的课程内容一直未定,它包含了古代、现代语言文字、文章、经学、文学、文化等多种附着物、寄生物,姑且名为“语文”——甚至不是一个明确的学科。语文课程内容极宽广,边界模糊,特定教学时空更有不同选择,揣摩一个文本的语言文字是语文学习,教师出于某种需要,在学了某课文之后,专门用一节课拓展某问题做文学哲学拓展是语文学习,请莫言做一个讲座也是语文学习。你能说这行为是非语文的? 现在有个话语很流行,因其形象受到追捧,即“语文课不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因为“语文课不是政治课,不是历史课,不是文化课……”,甚至“不是文学课”。这诸多“不是”,目的是剥除那些泛滥的“非语文本位”的东西,去“伪”求“真”。然而,我们可以反问:语文课为什么就不是包含了政治、历史、文化、情感等等内容在内的“大课”(美国语文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只需要坚持这些内容不脱离文本教学就行,而如果用“不是什么”来“排他”,并树一个假想敌“非语文”“歪道语文”,一方面会忽视了语文课程内容的繁杂性,一方面又会把很多尺度问题、效率问题、具体文本问题、特定教学内容问题或教师的实施水平问题统统变成了严格的是与非的问题。“画线”和“站队”的二元对立思维错杀了语文学习中的有效内容和方式,造成师生的小心翼翼、举步维艰,这对语文教学来说并非幸事。 三、视域和视角问题 “言语形式中心”论者常常混淆了“教材文本阅读教学语文课”和“语文学习”。后者是个大系统,前者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从立论者的列举中还可以发现,“正道语文”、“真语文”的主张更多是针对语文教材篇目的精读指导课,那么,泛读呢?大量阅读的要求怎么办呢?会以语言为中心还是以内容、思想为中心?又倘若我们面对的文本是《论语》中的几句话,该以内容为中心来整理孔子的思想,还是一定要以语言分析和运用为中心? 笔者并非持“文本内容说”来反对“语言形式说”,只是主张二者不要对立,如果视域和视角不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必以自己所见之岭去定义别人所见之峰。浙江的王尚文教授也是“正道语文”“真语文”的极力坚持者,我们来看他举的一个例子: 《荷花淀》中水生把参军的事实告诉妻子后,水生嫂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一位中学老师就这一言语形式中的那个句号作了如下分析:这个句子里的句号不能改为逗号。“如果改为逗号,那么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是假,拖后腿是真;采用句号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水生嫂深明大义,支持丈夫参军;另一方面又需要丈夫的爱怜。前者刁滑,后者温柔而多情。”这既是最生动的语感训练,又是最切实的语言知识教学,也让学生从中看到两种人格的对立,受到情感的陶冶,可以说是纲举目张的典型教例。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讲解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写作方法等等,但必须突出言语形式,使之服务于言语形式的教学。明确了言语形式应当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教学内容,语文教学轻装前进的问题也许就能迎刃而解了。 笔者非常认同王教授所举的教例,不自谦的话,我也肯定会这么教;问现在的很多喊“语言形式中心论”的教师,也说就该这么教;再问好几位不同意“语言形式中心论”,主张内容、情感更重要的教师,他们也说就这样教。既然如此,大家争的是什么?做的是同一件事,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至于你说是基于形式学习达成内容情感,还是把内容情感当凭借去达成语言形式学习,究竟有什么差别呢?也许只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纠缠的意义何在?至于王教授隐含批判的“(凭空)讲解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写作方法”,那只能说明可能是教师的教学水平有问题,而不是“内容中心说”或强调人文性带来的必然结果。也许我们该考虑的是语文教学可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而不是不基于“做”,先纠结于意识形态。胡适的话很有意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也许是我们现在面对诸多语文学科属性之争的最好态度。 四、摆事实中的“稻草人”现象 什么是“稻草人”现象?所谓“稻草人”谬误,是先把对方的观点或行为变成一个容易推翻的版本,然后将其驳倒从而得分。在对方来说往往觉得很冤——我没那样说过,我不是那样做的,但批评者是不管的,他是有的放矢,只不过这个“的”是他自己造的。如“真语文”论者郑逸农教授曾经批评某位语文老师把语文课上成“非语文课”——他的依据是这位老师的课堂上有歌声、有京剧、有对爱情的讨论。他是这样批评的: 教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才看了一遍课文,就由作者对母亲的愧疚自责引发开去,例数历史上孝敬父母的典型故事,讨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母亲,如何珍惜母爱,如何做一个孝顺的子女,于是教室里会响起《世上只有妈妈好》之类的歌声;教学鲁迅的《祝福》,初识文本,就由祥林嫂的不幸引发开去,讨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畅谈今天社会男女平等的幸福,教育学生要珍惜今天的幸福,并讨论如何做一个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女人,教室里可能还会响起《女人花》之类的歌声;教学沈从文的《边城》,还没疏通文本,就从翠翠的朦胧爱情和傩送的出走引发开去,讨论如何看待他们的爱情,再讨论我们今天应该有怎样的爱情观…… 这个批评的问题在哪儿呢?首先,我们认为如果一位教师在上语文课时把语文课上成京剧课、音乐欣赏课、爱情价值观课,自然是离开了语文,但那位教师的课堂上只是“有”——根据需要适当的“有”,自然是可以的,并不代表全是这样或主要是这样,你不能批评说这位教师把语文课上成了音乐课、爱情课。这位专家在批评时,也是知道这个区别的,所以在上面这段“设例”的话中,特地并一直在自设前提“才看了一遍课文”“初识文本”“还没梳通文本”。依据这些自设的前提,就树了一个“稻草人”,要打倒它,太容易,因谁都知道这是很糟糕的现象,问题是那位语文教师根本不是这回事。 五、论据中的“背锅”现象 什么是“背锅”呢?俗称“背黑锅”,即不是某人的错,却因为那个错误与其有一定关联,于是在批评时,这个错误就成了某人的罪状。 在近年兴起的对“人文性过头”的批判中,这种现象特别多,很多不属于人文性的东西,由于是伴着人文性的提倡出现的,所以“人文性过头”似乎成了一个事实。语文界较早提出“纠偏”的是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他在《为语文教学招“魂”》一文中指出,当前的“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系列‘失魂落魄’的症状,很有必要为它招一招‘魂’”。钱先生所说的症状主要是:有些人“为了张扬‘人文性’,增大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把课堂弄得“花花哨哨,热热闹闹”,但一堂课教下来,学生对课文却很生疏,“如同没有学过一样”。随后,不断有人撰文或在各种场合对此发表看法。如曹文轩教授认为:“目前的语文教育现状实际已经暴露了这几年人文教育力量过于强大和工具性教育相对薄弱的缺陷。”陆俭明教授也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语文课上过于强调人文性和文学素养的教育。”专家们的出发点自然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审视。 一是专家们所说的人文性过头现象是否是人文性?批评者们在批评时往往会举一些课例,比如,教学《品质》,大谈如何让商品通过广告畅销;教学《罗布泊,消逝的仙湖》,让学生探讨如何进行环境的保护,并给当地政府提出环保方面的建议……于是,结论出现了:这是强调人文过头,因为人文而走偏了的语文教学。笔者同意这些课例的问题存在,但这个问题不是人文问题,是假人文、冒牌人文,真正的人文是从课文文本中的言语形式和内容实质有机呈现出来的,如果教学紧紧依托于它,这个人文性就不会过头,不仅不过头,而且与文本细读、与深刻领会密切相关,必须张扬之挖掘之,而上述课例中所提的“人文”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文,相反,人文性不是过头,而是未实现。但一些专家却把这些因教师对人文性理解浅薄和贴标签的账记到了人文性的头上,斥之为“人文性过头”,让真正的人文性背了黑锅。 二是专家们真的长期深入常态课堂去发现或调查了吗?不少专家基本都是不在一线课堂的教授或先辈,他们的取样是他们听到的公开课、示范课。钱梦龙先生在批评语文课改中的错误倾向时就承认,上述偏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展示课”上,大量见于日常语文教学的仍然是“顺着‘应试’的旧轨道,我行我素,抱残守缺”。而王尚文先生、李海林先生、严华银先生以及其他人所提到的“泛语文”“非语文”等现象,也几乎都是以公开课、示范课为依据的。众所周知,这些公开课、示范课对于教师来说意味着精心准备、理念贯注,正是因为这样的用力而努力添加“人文因子”,结果又因对人文性的理解不够而用力过猛,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事实上,常态的民间课堂,最大的问题和最多的时间是“应试,还是应试”,拆零,肢解,把鉴赏弄成做阅读题,把所谓的浅文深教弄成生抠死挖。现实的语文教学一直在围着考试指挥棒转,考什么就教什么,什么情感体验、价值思辨都被逼到可有可无的境地,也就是说现实的语文教学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纠正为考试而教的问题。如此,以公开课而不是真实的常态课为依据来批评人文性过头,不仅仅是以偏概全,也是打倒“稻草人”现象,面对事实强大的应试教学现象,来纠人文性之偏,真让人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感慨。 六、论证中的强加因果 事件甲之后发生了事件乙,因此就说事件甲导致了事件乙。但有时时间上似乎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实质上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相互关联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 “真语文”“正道语文”和“语文味”的支持者们强调“言语形式为核心,而不是内容,尽管形式和内容密切不可分”,“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有篇文章的题目是“比精神底子更重要的是……”,作者是一位特级教师,对一线教学应该有发言权。文章标题省略号的内容,作者在文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即“语言的底子”。对这个“谁更重要”的问题,笔者暂且搁置,但可以先看其论证。该文中指出“精神的底子”一说是钱理群提出来的,“一直到现在,‘精神的底子’都是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与性质讨论中的热闹话题”,然后叙述: 可惜的是,在其(钱理群)十多年孜孜追求的打好“精神底子”的“立人”教育实践中,令人神往的“精神的底子”却遭遇到始料不及的尴尬与悲哀。……2004年他亲自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学生讲授“鲁迅作品解读”,可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直至难以为继。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地减少到只有二十多人……其结果依然让他尴尬不已。2012年9月9日,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他不无凄然地发出告别宣言,说今后只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了。 其实,这位具有顽强精神的教授一直没有弄清楚他“节节败退”的主要原因,应在于——目标异化,消解了语文学科的特点。 这位老师所说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就是“语言形式作为教学的中心”。他认为钱理群教授所强调的“立人”和“精神的底子”都是“消解了语文学科的特点”,“曲解了语文教育目的,干扰了语文教学,自然得不到中学师生的拥护”,在作者的分析中,其论证逻辑可疑。钱理群的“实验”及最后的“凄然告别”固然是实情,但学生越来越少,以至选修课开不下去,是否就是钱理群的“精神底子说”有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因果?——选修课开不下去,不一定是学生不喜欢,很可能因为高考压力和作业占据大量精力,而不是钱理群课讲得不好;即使真是课讲得不好,学生不喜欢,也许是因为钱理群不适合中学教学,并不代表钱教授的“精神底子说”不对;我们还知道一句话,“真理往往在少数人和孤独者手里”。从这个事上看,钱理群的尴尬和无奈是确定的,凄然也是确定的,但不代表他提倡和主张的不对,甚至,他的尴尬和凄然正体现出语文教学乃至整个教育界“精神底子”的薄弱和他的悲剧英雄形象的可敬,也许又正可表明钱理群的“立人观”和“精神底子说”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以其“无奈的告别”来证明“精神底子说消解了语文学科的特点和干扰了语文教学”是强加的因果关系,并反映出“以成败论英雄”的心理。 语文批评不合逻辑和不正常说理的现象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提倡争鸣,鼓励商榷,问题也许可以越辩越明,道理越说越开,但前提是理性论述、包容异见、欢迎讨论,而不是争夺话语权,因为我们都是摸象的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