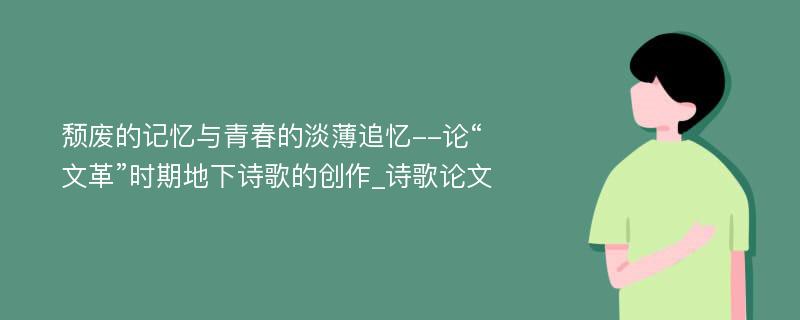
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颓废论文,地下论文,时期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2-0103-04
“文化大革命”时期,白洋淀像一个“诗歌摇篮”,孕育了一支诗歌劲旅——“白洋淀诗群”,这是伴随着1968年底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出现的一个知青诗人群。芒克、根子、多多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位诗人。多多于1969年至1975年在白洋淀插队期间,受到根子诗歌《三月与末日》(1971)的震动而拿起诗笔①,此后,他创作了《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组诗《万象》、《致太阳》、《手艺》、《日瓦格医生》等30多首诗②,形成诗歌生涯的第一次高峰。多多在“文革”时期的诗歌既有沉思特定政治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洞察力,亦有超越甚至异质于中国本土日常经验和审美习惯的艺术个性;他以一种“政治解剖学”的手法为“文革”历史书写了一段颓废的纪念,同时也以革命创伤记忆的见证为一代人祭献了一份青春的“薄奠”。
一、时代旁观者的“政治解剖学”
多多是“白洋淀诗群”中最具哲学气质的一位诗人,这种哲学气质基于他自身对“现实事件”的敏感认知和悟性,当然也来自于他自身对哲学的倾心与自觉的探究。据当年的一些朋友回忆,多多“喜欢哲学”③,“是一个读书在当时来说最多的一个,并且极有口才,雄辩滔滔。所以,他给出的评价,通常带有一种权威性”④。多多的哲学气质使他比一般人更容易深入到事件本质,也比一般人多了些深刻,但他的哲学气质没有使他的诗歌超然于现实成为纯粹超验的玄想,而是更接近现实的底色。尤其在对时代的认知中,他表现出一种穿透历史表象的洞察力,这是在迷狂的“文革”政治语境中的一种清醒,正是这份清醒使他的诗歌成为“政治解剖学”的文学范本。
无疑,多多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文学的政治性经常被误读的时代,指出“政治性”似乎并不是一种荣誉,而有可能被误读为一种贬义。尤其在西方学者视野中,“政治性”常常成了代替艺术性阅读与评价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尺⑤。这使得在揭示多多诗歌精神内核的同时,也部分地把对诗人的阅读、评价引向一种歧途,遮蔽了多多诗歌艺术本身的魅力和价值。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或国家,个人可以超越政治而独立存在,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尤其严重,个人“不谈政治”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政治生活甚至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全部,而“政治性”也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诗人与中国诗歌根本无法回避的诗歌质素。但多多从根本上并没有忘记诗歌本身所首要遵循的艺术性原则,在他的诗中,总能找到时代和历史遗留下的蛛丝马迹,这使其诗歌的“政治性”意味非常明显,但与多多的“政治性”相关的是“个人性”,他对时代的洞察首先基于个人理性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多多对政治的解剖首先来自个人性的现实经验,其次才是集体性的政治经验,所以,他诗中的“政治解剖学”并没有“堕落”为抗议性的政治口号铺叙或政治激情的泛滥,而是以极其严肃的自控能力和理性辨识能力把握住一种本质性的东西。仅从政治性的艺术表现与转化这一角度及其所达到的高度来看,多多与同时代的北岛非常相似。尽管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城堡中,但二人的精神距离应该是最为接近的,他们在同样阴郁的时代,面对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公敌,在决斗中拿起了同样的武器,并且,他们二人诗歌的审美效果也达到一种审美的近似值。
多多始终置身于与个体生命休戚相关的时代,个体经验经过他的政治解剖,沉浸在时代与历史的巨大背景中,从而使他的诗歌摒弃了空洞和飘渺而具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沉甸甸”的分量。他在诗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色彩符码,黑色(有时用灰色)常常成为时代的主色调:黑色的天空,漆黑的城市,黑色的尸体,黑夜以及黑夜的女人。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乌鸦》(1974),全诗没有彩色或亮色,而只有“沉甸甸”的、高密度的黑色,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黑色视域中,“火葬场”、“灰烬”、“黑色”的“乌鸦群”、“殡葬的天使”、“黄昏的天空”等语词的繁复使用,使整首诗在布满黑色的氛围中潜藏着死亡的事实,而黑色联系的正是现实世界的死亡与恐怖。因为在“文革”现实世界里,人们人为地制造了无数死亡。多多从不忌讳死亡幽灵在他诗歌地带盘旋、飞舞,相反,他有意让死亡气息在诗中到处弥漫、扩散,从而揭示出在司空见惯的死亡中时代的残酷和生命的无助。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文化心理和审美感知里,“黑色的乌鸦”常常带着不祥、阴郁的死亡预示,“天使”却象征着圣洁,往往携带着新生、爱、梦幻等美好事物一起降临,而诗人却把“乌鸦”称之为“黑色的殡葬的天使”。可以说,“乌鸦”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充当了对历史悲剧透视的预示者和悼亡者,而诗人充当的角色似乎也如此。殡葬透露的死亡气息,在“天使”与“乌鸦”之间形成一种不符合审美经验和文化习惯的不适与不和谐的紧张,这种紧张给全诗造成了一种压抑、冷酷的美学基调。同时,“音乐标点”的修辞与后面省略号的使用亦在突兀感与悠长无尽之间形成一种审美张力,这种突兀的沉寂在“旁观者”的目击中从远景转化为近景,“旁观者”在转移视线的同时也转移了诗歌的主题。
在《乌鸦》这首诗中,始终有一个隐身在事件背后、未露面的观众——他是旁观者,是目击者,也是观察家,但他并非冷漠的看客,更像是诗人自己。这样,生命与死亡的每一幕都清晰地摄入他的眼底,而他则用诗歌为目击的一切作注释。又如《致太阳》(1973),多多仍然不动声色地对“太阳”的神圣性以及“造神运动”中的“太阳崇拜”给以颠覆与拆解。在中国当代革命化叙事的文学写作经验里,“太阳”、“红太阳”的意象具有确定性所指和强烈的政治隐喻特征,并且常常上升到有如图腾崇拜的“太阳神”地位,尤其在癫狂的“文革”,“太阳”的意旨总是汇集到具体而现实的国家领袖——一代青年的精神之父身上。“太阳”也是多多诗歌频繁使用的一个意象,如《战争》(1972):“下午的太阳宽容地依在墓碑上”,以及《夏》(1975):“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留下少年,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而在《致太阳》中,诗人通过两种关系的建立,彻底完成了对“权力力学”中“太阳”的控诉与“太阳神话”的颠覆,同时也表达了一代青年对“父亲”的叛逆。诗中仍然保留了太阳的“神”性,但又分明把太阳人格化了,这样就在“我”与“太阳”之间缔结了一种人际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人(我)与“宇宙”的对话关系。而太阳“在黑夜中长睡”则暗示了“给我们光明”的太阳实际上的盲目与昏聩,“枕着我们的希望”更加深了“我们”命运的无望。“给”、“让”奠定了双方的施受关系,即太阳以神圣之名,以“灵魂的君王”之名掠夺了一代人的灵魂和精神,而“我们”的结局却是轮回式的“出生然后死亡”。太阳“从东方升起”或许是“东方红,太阳升”的诗歌转述,正是在这种转述中多多再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在“红太阳”的普照下是沉醉的大地、老迈昏聩的“君王”以及沉睡在苦难中的人民:“醉醺醺的土地上/人民那粗糙的脸和呻吟着的手/人民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苦难//马灯在风中摇曳/是睡熟的夜和醒着的眼睛/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鼾声”(《无题》),透过“一望无际的苦难”,多多勾画出一幅暗夜般的时代图景。在对“太阳神”的真相揭示之后,诗人为“文革”时期荒诞的“造神运动”和“领袖崇拜”得出结论:太阳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并不自由、神圣、珍贵、高高在上,而是肮脏、低贱、人尽可用,它的“光芒万丈”只是等同于“四海通用”。贯穿此诗的反讽是多多完成“政治解剖学”的常用手法。
如果说食指为一个时代和一代青年记录下了一种历史创伤记忆的图景和表象,使历史具有了某种实证性;那么,多多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睿智的眼光和深深的悲悯来俯视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的悲剧命运。他像一个总结历史经验的智者或史官,不提供表象,而只把从表象得来的结论说出来,正像他在生活中给别人的感觉一样:“我当时认为多多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评论家。”⑥多多的语言具有一种结论性,语言与意象的目的就是说出真相。仅就“文革”时期的诗歌而论,芒克与北岛的理性常是在感觉中升华理性,而多多的理性则是直接得出结论。
多多的诗歌可以理解为诗人自己与一代人的自传,但他却以“非自传性”的口吻来撰写他们的心灵传记,以下定义的语法规则来构思诗意。在他的诗中,以第一人称的“我”作为“自我”的代称,几乎从来都是“缺席”的“在场”,但自我却又无处不在“第一现场”。自我是时代戏剧的参与者,却在剧情上演的同时清醒过来,并在最后一幕逃逸出来,实现了对舞台的“出场”。如在《青春》(1973)中,多多借用情爱激情写下了革命激情中的虚妄和逃离虚妄的清醒,隐约可见的是诗人在狂热的时代中所独有的阴郁和冷峻:“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溜出来了,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溜出来了”的诗人意味着自我从“第一现场”的“参与者”转而成为“旁观者”和“目击者”,这个“旁观者”拥有的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这一视角对于现场,即现实表象似乎更接近于客观化,更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更便于观察一切,洞悉一切,看透一切。同时,因为“我”的退场,也把个体经验扩展为一代人的集体经验。这样,他的自传就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群体性的传记;既是写给自己的,又是写给时代的。
二、词与物之间:一个严格的“手艺人”
多多的诗歌写作像是在操练一门“手艺”,而他本人则像一个严格的“手艺人”。多多修炼的手艺,并不纯粹是技巧的打磨和推敲,而是包含了对思想的冶炼和提纯。多多以短诗居多,但他的短诗又不是芒克式与北岛式的抒情小诗,多多几乎从不抒情,而是通过不断删割、刮削等手段来雕刻陷落于历史漩涡中混沌与芜杂的感情与经验,变未名为有名,变无形为有形,变暧昧为清晰,这种风格与他的哲学气质密切相关,也与他作为时代的目击者身份相吻合。
多多的诗歌有一种叛逆之美,在他特有的政治意象里,“煽动”起的是思想的野蛮破坏。比如《夏》(1975):“花仍在虚假地开放/凶恶的树仍在不停地摇曳/不停地坠落它们不幸的儿女。”又如《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如果抽去了这首诗的时代背景,也许它的主题将会暧昧不明,然而它的“文革”背景决定了它清晰可解的思想内涵。“革命的血腥”、“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干燥的喉咙”、“野蛮的眼罩”、“发黑的尸体”、“冒烟的队伍”……名词与它的定语之间,以及词与物之间再一次构成冲突的、具有压迫感的张力。词与词之间超乎寻常的跳跃性,带给阅读者的是视觉的不断挪移,不断挪移产生不断的陌生,一次次的陌生最终化为“审美的惊异”,而“审美的惊异”正根源于心灵的“震惊体验”。在《无题》(1974)中多多再一次传达出对“革命化”时代的“震惊体验”:“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门声……”
写于1974年的这首诗是在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代下定义,而多多仍用一个“旁观者”的冷眼目睹这一场带血的政治狂欢和虚妄的政治游戏。 “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所执著的政治性行为(“流尽血”或“继续发射”),不过是虚妄而毫无意义的“死亡接力赛”,所谓的不同阶级最终都化为萦绕在“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中的一个个阴魂。“文革”的“红色恐怖”给诗人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也带来了强烈的“震惊体验”,“红色恐怖的敲门”就是命运(或曰厄运)的敲门,诗中“急促”一词的运用造成一种非常紧张的心理感觉,它动感地传达了时代的恐怖气氛,一种岌岌可危的、朝不保夕的、随时都可能受到恐怖袭击的动荡。多多在色彩学的选用上,体现了明显的“隐喻性”,“灰色的”月亮、“漆黑的”城市、“红色恐怖”构成一幅阴冷而又带着血腥气息的时代图画,而一些枯燥的政治概念和术语如“阶级”、“人民”、“民族”、“队伍”、“革命者”、“革命”、“解放”、“信仰”、“社会”、“历史”、“中国”等时代的政治语汇,通过多多的“政治解剖学”却焕发了某种残酷的“诗意”。又如《日瓦格医生》(1974):“东方,是一片持久黑暗的庄重/矗立着褪色的宗教的城墙/多少个野蛮豪华的年代/在今天,度尽了/多少扇有罪的血腥的铁门/在今天,被打开了:/疯子,成群地奔跑出来/高举着开天辟地的铁匠的旗/好像无数叛逆的黑帆/在天边辉煌地招展。”
多多有一种说出真相的智勇,他在诗中呈现出的形象是冷峻、孤傲的,他几乎把抒情压缩到最低点。在他的诗中,很少感情与事件的铺陈,也很少过渡性的词汇,而是直接以“下定义”的方式把隐蔽在历史表象中的真相揭示出来,或者说让真相自己敞开。在运思方式上,与芒克偏向于灵感的顿悟和瞬间感觉的把握不同的是,多多的感觉与经验分明都经过了沉淀、结晶与提炼。在语言的运用上,多多诗歌的语言干脆、直接、硬朗,他不用语言的皮毛掩盖或曰装饰其思想的质地,相反,他常常是以“下定义”的发言直奔主题。在他的语法规则中,词与物之间构成了合谋的关系,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对应的,其语言充分体现了词语本身的命名性,这种命名实际是个人在历史空洞化之后的自我指认与自我命名。如果说芒克随心所欲,是自然诗人,多多则字斟句酌,更像苦吟诗人。多多对语言的打磨与北岛有相似之处,在政治性的诗歌美学中,冷峻的怀疑主义思想底色的调度,有时多多甚至超过了北岛。北岛有一个从清新向冷峻的清晰过渡,而在多多留下的诗作中是缺少这种过渡迹象的。多多最大限度地释放了语言的所指功能,在其诗歌的语言库藏中没有单纯的能指符号,而对于时代下结论的思想方式使他无法不对词语的意义沉迷。他对词语的“量”表现了一种克制与节省,这种克制与节省又不单纯限于语言的自控,而更是一种情感与精神层面上的自控。他善于“打磨”文字,甚至到了精雕细琢的地步。不过,与其说他在“打磨”文字,不如说他在“打磨”自己的情感。多多在精雕细琢的打磨中,有时也留下“版本不一”的疑惑与“刀挫斧凿”的刻痕。正如宋海泉所说:“毛头对自己的诗改了又改,精雕细琢。很多作品发表时同我当年看到的已大不相同。”⑦但同时他也确证了多多的诗歌在最初的时候已具备了基本的品质:“当时,我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他诗作中所讲的一切,仅吃惊于他惊世骇俗的诗句,同时也隐隐感到一种罪恶的喻意与悲凉。”⑧可以说,多多的诗中理性的规约使激情得到收敛,现代性的思考品质使诗歌的内涵远离了浅薄,而节俭的语言却承载了密集深厚的思想。
三、革命创伤记忆的青春“薄奠”
1976年,多多离开白洋淀回到北京,写下《教诲——颓废的纪念》,算是对白洋淀生活与“个人历史”的一种告别。他仍然保持且推进了他一贯的深刻和不苟言笑,以诗歌为自己和同时代人的青春作了一次特殊而颓废的纪念。在某种意义上,文化革命的神话成为一代人的创伤记忆,《教诲》可以看作一代人命运的注解,多多用文字的分行排列矗立起了一座墓碑,更像是为自我和一代人进行的一次诗歌“薄奠”。“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书架上的书籍全部背叛了他们”,在这首诗中,“他们”是特指的,他们的出生伴随着纯正的政治教育,他们的成长同步于文化革命的风暴,在红卫兵与上山下乡运动的舞台中,他们既是主角,又是观众。他们经历了理想的迷狂和破产,带着青春沦落的悲愤和叛逆的冲动开始对个人和历史进行反省:“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自觉,让他们的思想变得尖锐/并由于自觉而失血”,经历了时代悲喜剧捉弄的诗人又为时代自觉写下了锥心的“供词”,以对世界悲惨的衬托作为历史的献礼,“他们”这一代人充当了政治牺牲的义务祭品:“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排除/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而出现的,/悲惨/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
这就是一代人精神上“长大成人”的经历,时代张开巨大的政治网,罩住了“误生”于这个时代的“他们”,而他们个人的生活只是在网中偷生或幸存的一次历险,出生即已注定了的悲剧命运,谁能躲过去呢?而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而言,出生的悲剧似乎验证并强化了某种无法摆脱的时代宿命:“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这就是诗人多多对个人命运的发现。由此,他开始对“瞒与骗”的“文革”时代发出了追问:“谁说他们早期生活的主题/是明朗的,至今他们仍以为/那是一句有害的名言/在毫无艺术情节的夜晚/那灯光来源于错觉”,“灯光”与“错觉”虽直接针对具体时代但却超越具体历史地写出了人生的无奈。无数个和白洋淀一样的地方使他们“沦为精神的犯罪者”,沦为理想幻灭、精神破产的一代,在他们所寄身的“不洁”世界里,面对悬在颈上的各种枷锁(理想、书籍、灯光、明朗生活),“他们却仍要找到/第一个发现‘真理’的罪犯/以及拆毁世界/所需要等待的时间”。这就是他们得出的人生结论:发现(或寻找)并且拆毁。这首诗的情感尽管有悲怆的一面,但却没有自怜,反而有搏斗的疯狂;思想虽然带着颓废的气息,但却尖锐有力,潜藏一种内在的理性。
在1976年写下的另一首诗《同居》中,颓废换成了日常生活的节奏,没有尖锐,也不是温情,而是以暗语交谈的方式冷静地说出人生的三个意向,中间穿插的是“太阳升起来了,归宿仍不能断决”这样不经意然而意味深长的诗句,这种化入日常生活细节的不经意语调却传达出“他们”的悲剧结局:“当他们向黎明的街心走去/他们看到了生活。生活/就是那个停住劳动/看着他们走近的清道夫/他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还叼着一枝烟斗,站在早晨——”。实际上,多多对自身献祭的命运似乎早有预感,在1972年的《蜜周》和1973年的《青春》中,他已经从革命激情的青春狂欢中预言了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我们全体都会被写成传说/我们的腿像枪一样长/我们红红的双手,可以稳稳地捉住太阳”,“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不管是《青春》中“带着白手套”、“镇静地喷射杀虫剂”的工人,还是《同居》中那个冷漠的“穿着蓝色工作服”、“叼着一枝烟斗”的“清道夫”都暗示了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及其中的人们对这代人青春岁月的遗忘,或是像“传说”一样被慢慢变形。食指的“相信未来”给处于无望境地中的一代人以暂时的抚慰和遥不可期的允诺,而多多在现实的荒诞与绝望中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相信,他清醒地洞见了过往的“青春”终将被未来的“杀虫剂”所毁灭的虚妄结局,所以,他沉痛地说:“即使恢复了最初的憧憬/空虚,已成为他们一生的污点。”可以说,“他们”以自身在历史中喜剧性的“被卷入”和最后悲剧性的“被离弃”实现了一次精神上的“抽身而退”,在退却中,他们却没有逃避。可以说,多多厌世的愤激并没有掩盖住他骄傲的人性尊严,他的诗歌写出了一代人青春的颓废纪念,呈现出的是一种深沉而尖锐的美感。同样写一代人颓废的纪念,表现一种颓废的美,但多多的颓废又与根子的颓废表现不同,根子是破坏性的直接对抗,裹挟着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表达一种背叛的“决绝”和“快意”;而多多的颓废则通过主题、意象、语言来层层“解剖”,以智者的深沉启人深思和追问。
《教诲》、《同居》、《我记得》是多多在1976年反思“文革”历史的诗歌文献。荷兰学者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认为:“尽管形式上《教诲》没有什么真正的革新,但它听起来明显地不同于《日瓦格医生》这首诗。后者的声调是极度夸张的,而《教诲》虽少了一些戏剧性,却表现得更为坚决和有力。”⑨在对时代反思的深刻度和语言的穿透力上,《教诲》的深刻性已经超越了诗歌文体本身而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当信仰和青春都坍塌成灰烬,当历史即将翻过黑色的一页,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历史见证者和浩劫幸存者的身份意识就更加深刻,所以,多多在《我记得》中有了担负沉重往事却又如释重负的姿态,语调则是相对舒缓而又充满沧桑的:“路,正在经历绝境,坑/终于被填平,粮食/将被更深更深地埋在地下/历史也如石人一般/默默注视灰房子的倒塌……”
可以说,多多“文革”时期的诗歌均可视为一个时代的寓言,它不仅是诗人整个青春岁月的见证,也是“红色恐怖”历史的颓废纪念,更是整整一代人青春的薄奠,而诗人自己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象征形象恰似他自己诗中的那个“黑色的殡葬的天使”。
注释:
①参见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8年第3期。
②根据多多诗集《里程》(1972-1988年),《今天》文学社,1988年油印。
③⑦⑧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诗探索》1994年第4辑。
④⑥廖亦武、陈勇:《马佳访谈录》,载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1页。
⑤⑨参见[荷兰]柯雷:《多多的早期诗歌》,谷力译,《诗探索》1999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