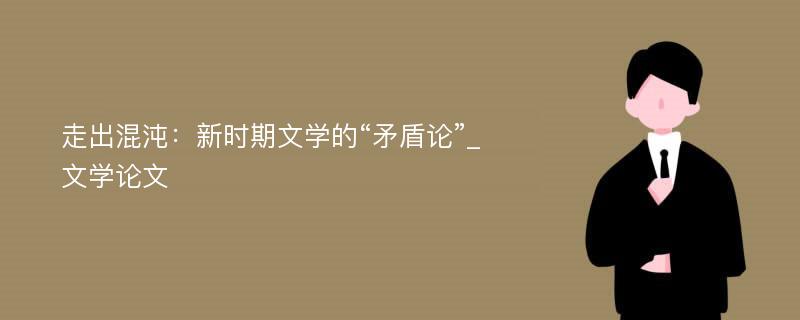
走出混沌——新时期文学的“矛盾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论文,新时期论文,混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学阶段和时期一样,新时期文学也必然要经历发轫、形成、高涨并走向衰落这样一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光荣的丧钟何时鸣响谁也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地说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高潮已经过去,那种虎气生生、朝气勃发的创作态势已不复再有,新时期文学日趋成熟,也日见老化,甚至不少方面也呈现出衰微的迹象。虽然文学界仍在不停地标榜“超越和突破”,这实则却暴露出陷入某种困境时的主观挣扎。更不妙的是除了批评界在为某些较新的创作趋向作决不重复的新定性之外,创作实际却无法掩盖步履蹒跚的重复实质。在新时期文学大而全的局面下谁要想在题材、结构形式、语言或叙事手段等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绝非易事。基于这种看法,我对新时期文学在世纪交替时的前景和发展不太乐观。新时期文学虽然克服了十七年文学倾向政治化、题材单一化、语言简单化的明显毛病,但又形成了新的毛病。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新时期文学存在的七个矛盾,它们是影响当前文学事业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
1.“多元化”与“单一化”的矛盾
新时期文学是一个各种思想意识碰撞的创作多元化时代,它显示一种空前的包容性和宽松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健康正常和消极荒诞、未来理想生活的热情憧憬和历史阴影的回光反照、理性与非理性、政治与反政治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被文学创作所涵盖。另外,新时期文学也是一个创作思潮和流派迭出的年代,从“伤痕文学”到目前所谓的“新状态”文学,文学界似乎有理由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和繁荣了。
但是,从这种表面热闹的创作现况中我们看到了某种雷同和单调。从“85新潮文艺”运动开始,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的扩张和强化成为一种共同的趋向,这是“大我”被否定的思想产物。对“自我”的表现、认识和讴歌被推向了一种绝对的境地,英雄主义和崇高的古典主义意识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沉郁、阴冷、厚重的创作主潮。对昨日历史的温情缅怀留恋,对现实生活的失望郁闷势必导致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股强大的、玩味于卑微、琐屑、消沉、平淡、荒诞、扭曲的现代主义创作意识。
对生活过于一致的认识必然造成创作中的重复,题材的相似和故事内涵的雷同不可避免,只是由于叙事的方式和主观感情表露的程度产生了技巧性的骚扰。从《人生》中的高加林,《你别无选择》中的李鸣、孟野,《爸爸爸》中的丙崽,《古船》中的隋抱朴,《第三只眼》中的司马戍,《瀚海》中的“我”,《伏羲伏羲》中的杨天青和菊豆,《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和《废都》中的庄之蝶等等不用赘列的人物形象及其所衍生的故事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某种生活意识和审美观照的共同点呢?当太多的作家都来关注生活离奇失常的一面而展示卑微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的时候,当太多的作品都倾力表现原始洪荒的自然力和奇异地域民俗的神秘感的时候,当历史和战争被温情人性冲淡了深刻和严峻的时候,当现实的阴暗面(异化、物化、隔膜、权欲、拜金主义等)被揭示得暴露无遗的时候,这条文学创作之路会不会太挤了?
2.“性突破”与“性迷失”的矛盾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和变化,就是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已把“性”作为了自己很自然的表现领域,这是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重大区别。在十七年的文学中,像邓友梅的《在悬崖边》、宗璞的《红豆》等这样粗浅涉及情爱的作品都被斥之为“小资情调”,写有关“性”的内容无疑是一大禁区,只是林予的《雁飞塞北》中描写薛明与柳明霞的河边幽会时留下非常珍罕的一笔。新时期文学终于突破这一禁区,这无疑是艺术观念和道德意识的一次重要演进,其意义无论对文学自身还是社会行为都是不可低估的。这既是文学发展、社会需求之必然,也是80、90年代中国文学受到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结果。
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性”反映的时代,这篇作品构成了这样一个创作导向:从人性完整性看待“性”之于人的重要和必然,“性”是人的心理、生理的自然强烈的需求,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因此,新时期大凡涉及“性”的题材的作品都是以探寻人的生命意识,表现“自我”的复杂内涵以及强调人性的潜意识本能欲望的面目出现的,试图证明“性”不仅是人性的,也是社会历史性的。从85年前后关于“性”内容的文学作品躁动于文坛到90年代性描写的风行,在张贤亮、莫言、陈忠实、王安忆、贾平凹、尤凤伟、刘恒等人的作品中“性”内容的方方面面几近写绝。贾平凹的《废都》几乎毫无节制将所谓“性文学”推上新的高峰,其性描写之暴露胆大比地摊黄色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后朦胧诗派”的作品更是扭曲地展示了“性变态”的光怪陆离。
但是,在新时期文学有了可贵的“性突破”的同时,文学创作中又出现了“性迷失”的现象,这种迷失并非是因为作品中性描写过于大胆或毫无节制,而是作者在思考性问题时观念出现的某种偏差,因而在用形象表现时反而持一种较为保守和落后的思想意识,显示了某种认识上的停滞和倒退。无论新时期文学涉及性问题的作品如何丰富,但也无法掩饰仅集中于两个方面的单调:一是表现“性自然”的内容,如实地强调性的本能特征和强大生命力,其主观态度是中性的,《伏羲伏羲》、《白鹿原》、《石门夜话》、《习惯死亡》、《红高粱》、《废都》等就是这样的产物;二是揭示“性丑恶”的性质,既有对性力破坏性的展露,也有对复杂的性错位的鞭挞,尤以《小城之恋》、《火船》、《白涡》等作品表现了作者的那种贬斥和厌恶而又无奈的复杂情绪。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许多作家在承认“性”的本能自然性的前提下对性破坏、性丑恶和性异常的总体关注和审美态度,他们始终不能歌颂正常性欲在繁衍生命方面的强大创造力,歌颂活泼的、健康的性交往所具有的美好特征,不敢旗帜鲜明地证明正常的性行为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高级审美活动,从而引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性”,对待“性”,建立起既符合人性又符合道德习规的美好性关系。因此,文学作品怎样描写“性”的确是个应该慎重的问题,怎么看待“性”更是一个当前中国文学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观念上的禁区其实并未真正突破。
3.“平民意识”与“贵族化”的矛盾
作为一种拨乱反正和矫枉过正的产物,新时期文学既是与十七年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人创作主潮截然不同的文学,也是与“文革”的虚假英雄主义(“高大全”模式)界限分明的文学。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是新时期文学标举的思想旗帜,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文学转向普通人生的表现,作品中历史和现实最大程度地贴近了生活的真实状态,显得亲切和似曾相识,而不再使人觉得遥不可及,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深刻变化。即便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非人道主义、反人道主义或非理性的“后现代派文学”,“灰色都市文学”也是“平民意识”压抑深久后的积怨爆发。王朔就曾把自己作品主题归纳为“卑贱者最聪明,富贵者最愚蠢”;而“后朦胧诗派”则更是强调诗歌的“平民化”而对北岛、江河等人所表现的“思想者”、“英雄”、“决斗士”、“崇高人格的化身”嗤之以鼻,其口号是“像平民一样地生活”。
但是,新时期文学的革命英雄主义主旨的丧失也同时造就了“自我意识”(普通人的主体性)的强化,它也是“平民意识”的主要内核。这种“自我意识”在题材选择较轻易地满足后便促使作家在更深层次进行艺术形式的冒险,文学本身便呈现出非常纤细的个性差异。所谓的“平民意识”绝非共同的经验式命运,而是不可重复的独特“自我”的刻意雕凿,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由表及里的禅悟性体验,文学作品中语言氛围的可知性和规定性已被“话语”的个性特征搅得含混不清而充满了隐喻意义。于是这些关于“平民的故事”变得难以解读,主观上的迎合和客观上的拒绝造成了新时期文学越来越“贵族化”而非“平民化”,唯有文化素养较高的精英层知识文化人士才能对其中的深刻和暗示心领神会,这是艺术形式探索走向极端带来的负面影响。
80、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艺术化文学的时期,这本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进步,但我们发现伴随着每一次艺术创新的深化,就势必造成解读上的更大困难,技巧起着搅乱和阻隔阅读思维的反推作用。王蒙、宗璞的意识流及荒诞小说,马原、扎西达娃、洪峰的“新小说”,刘恒、方方的“新写实”小说,莫言、刘索拉的“前先锋小说”,陈染、海男、鲁平、大仙等“晚生代”的小说,以及“后朦胧诗派”中像“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等众多群体的诗作都有某种或多或少的贵族化倾向。尽管某些作品的贵族化倾向可能是技巧运用不当或不够圆熟的客观结果,但不知流行于“新生代”诗人中的那一句著名口号“像平民一样生活”紧接着的“像上帝一样思考”是否多少表现作家内心深处孤芳自赏的主观意识或潜意识。文学在未及创造和培养出与之相适应的欣赏群时就急步超前,于是在结构模式、叙事方式和语言运用这三个最重要的文学艺术化特质方面产生了不可知和神秘艰涩,文学必然走向更为深重的孤寂和困惑。
4.“深层现实”与“生活表象”的矛盾
“深层现实”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在运用其精神分析方法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弗氏“深层心理学”的生活实证基础,其实质是强调无意识心理机制对社会真实生活内容的反抗,表现出人的本能欲望在“超我”及其“道德原则”的压迫下挣扎、象征满足乃至牺牲的流程。中国当代的作家不一定全都理解和赞同弗氏学说,但不容置疑的是文学创作在进入80、90年代后越来越显露出“向内转”的倾向,作品更多的是潜入生活表象的下面去探寻人的生活的真实状态,探寻人的自我心理活动。因此,文学从以前对政治的热情跟踪和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中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焦虑、浮躁、困惑)的深切关注,反映出了在昂扬火热的生活表象背后的阴郁现实。所谓新时期文学揭示的“深层现实”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题材选择上喜欢刻画具有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的艺术形象,反映人物自我意识分裂的现象,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二是表现现实生活幽冷无常的本质,揭示生活流程的琐碎和偶发性,突出物化对生活本能和愿望的腐蚀;三是重新认识历史形成和发展的主动力,破除以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为主纲的传统历史价值观。
“新写实小说”被认为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创作流派走向深入的产物,其创作就是通过对所谓“原生态”冷静客观的真实表现来揭示生活的本原面目。“新写实小说”无疑是对以往政治文学中那种伪现实主义的反拨,也是对先锋文学脱离大众的“新潮运动”的背弃。“新写实”在揭示生活本质的时候消解了政治的含义(大概只有刘震云的《新兵连》有某种淡淡的政治指向的意味),没有生活主流,没有未来趋势,没有典型形象,没有善恶极端之人,它只关注生活中最普遍的有关衣食住行、油盐柴米、吃喝拉撒的“纯态事实”(陈思和语),以一种“感情的零度”(王干语)叙述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有的研究者把“新写实”视为“深层现实”真实反映的最典型的例证。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普遍运用更使“新写实小说”具有了新现实主义中心理文学的基本内涵,它使人们看到了人物在现实生存状态下崇高和自由不起来的庸俗、狭隘、丑陋和卑微的心理活动过程。尽管《钟山》杂志在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卷首语》中把其创作态度定性为“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我们从“新写实小说”那种冗沉琐碎的原态生活片断(“生活流”)中看不到诗意的伤感和使命感,这必然会湮没文学对生命本体意识的美的超越和升华,而流于生活表象的罗列和堆砌。真诚地反映生活现实仅仅是文学的任务之一,而文学的要义在于创造出一种抗拒邪恶和失常的人文精神从而引导人们去改造现实走向正常和合理。
5.“创造”与“摹仿”的矛盾
20世纪的后20年是封闭得太久的古老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年代,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发达的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王蒙的《春之声》和《来劲》非常扼要地勾勒出了这种变革的噪杂而又热闹的景观,表现出了中国作家面对这一现实的那种热切和冲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和文学从中受益匪浅,西方的各种现代文化、哲学、美学、文艺思潮像潮水一般涌入,并迅速地化解在文学创作之中,使新时期文学的表现领域和艺术手法显得异常的丰富多彩。这种情况表现了中国急于获得世界文学的认同,与西方文学接轨并最终纳入国际大文化的迫切心态。
客观地看,新时期文学在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时的动机和初衷无疑是想在建立真正民族化的文学方面探索一条新路,促使文学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功能,从而保持日益革新的内在活力。但是,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深入发展,创作实际与初衷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文学创作的确呈现了多元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局面,“反思文学”、“先锋派”、“现代派文学”、“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小说”、“新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朦胧诗”、“后朦胧诗”等等,不一而足,文学创作的创新、“赶潮”充分显示了这个各方面鼓励创造性的时代的基本特征。任何一种文学创作思潮和流派都不可能一统天下,独霸文坛,随时都面临着新浪潮的挑战和取代,新时期的文坛成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实验场。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在对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学进行超越时是以西方文学(尤其现代主义文学)为参照系的,并以西方现代哲学文化思潮(生命意识、本能欲力扩张、自我存在状态、文化意识批判等)来构架自己的价值体系,以西方文学的技法(意识流、荒诞、意义消解、话语实验、反小说、旁观叙事等)来铺延自己的艺术形式之途。几乎任何一种新的流派和作品样式都可以从西方文学中找到它们的“母本”,每一次的“创新”或“实验”都意味着“重复”和“摹仿”。
从王蒙的《杂色》、《风筝飘带》(背景是伍尔芙、詹姆斯·乔伊斯),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背景是约瑟夫·海勒),到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背景是马尔克斯),到陈染的《乱流镇的那一年特别是荒凉的秋天和冬天》(背景是杜拉斯),再到马原、洪峰、扎西达娃、余华的小说(背景是法国“新小说”派);从北岛、舒婷、顾城到晚近的“新生代”或“后朦胧诗”,再反观波德莱尔、爱伦·坡、艾略特、普拉斯、帕拉、埃利蒂斯,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时期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全面摹仿,所谓的“现代意识”(这是一个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创作和批评观念)本质上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同义词。新时期文学急于迎头赶上世界文学的发展步伐,也想创造出一种与西方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民族化文学,但又认为别人的文学乃至文化更为优越,因而借鉴西方文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成了时尚,但却不敢批判西方文化和文学,这里面有一个“弱者心态”的问题。改革开放使中国意识到了巨大的差距,在盲目的骄傲感和自尊心被击破之后,除政治意识形态以外,经济、文化、工商业和文艺都在以空前谦虚的姿态渴盼着“国际认证”,对于充满“弱者心态”的中国文学来说,所谓的“拿来主义”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而这对于建立真正民族化的文学是有损无益的。
6.“反商业”与“商业化”的矛盾
随着开放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商品经济的逐步形成,中国在由小农意识向商业意识的过渡中发生着急剧的变革,从而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信仰、道德观念、婚恋意识和生活方式,“先富起来”、“唯利是图”、“等价交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等现代商业文明价值观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钱与权、目的与手段、索取与贡献、享受与创造等方面,社会的重心整体向前者倾斜,于是贪污腐败、拜金主义、全民经商、享乐主义、道德沦丧也成了商业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政策朝经济倾斜,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对文学原来典雅独特的社会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一切文化形态备受冷落,文学也从万人景仰的天国落到了地下。面对这种处境,王蒙等人提出了所谓的“文学复位说”,无奈地承认文学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以此来坚定作家们早已丧失的自信心和调整他们面对失宠的惆怅心态。基于此,新时期文学亮出了“反商业”的旗号:一是强调文学的精神创造价值和非商品性质;二是强调作家固守文坛的重要性和使命感,排斥金钱和利润原则对作家的影响诱惑;三是强调文学在文化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性质和不可替代性。
抱着对商品大潮和商品文明的抵触情绪,新时期文学以自身形式所具有的犀利和尖锐开始了坚决的反击,将那种对商业文明的鄙视和反感的情绪宣泄在作品中。这种反击是在“喜旧”和“厌新”的两条战线展开的,从韩少功、李杭育、扎西达娃、汪曾祺、贾平凹、乌热尔图对传统的地域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到高晓声、路遥、张承志、梁晓声、方方、池莉、刘震云对商品化社会世态炎凉的腐蚀性本质的揭露和怀疑,都不难看出“反商业”的传统情结。从改革高潮年代的85年出现的文学“寻根”主题其实绵延至今,这既是一种文化追寻的结果,也是一种对现实战略性撤退和反击的结果。
不幸的是,新时期文学在拒绝商业文明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塌方,文学界的种种迹象表明“商业化”已在侵蚀其并不坚固的根基,文学本身越来越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悄悄地与社会接轨,具备了“四化”的特征:一是“商人化”,不少作家不甘清贫,纵身投入了经商大潮,不少人都以隐藏或公开的方式尝过商海的潮腥味,像陆文夫、张贤亮、王朔、魏明伦、胡万春等人更是将生意从国内做到了国外,其经营的品种绝非限于所谓“文化”。二是“商品化”,现在文坛中冒出了一些“当红作家”、“大腕作家”、“走红作家”、“热点作家”之类的新概念(如王朔、贾平凹、苏童、刘恒等就是极品),这实际是商品运作机制中的“明星效应”。你走红或为社会瞩目,你的作品就能换个好价钱,你引不起注意或受冷落,那作品的稿酬肯定上不去,这就是商业法则。“商品化”的另一种赤裸裸表现就是如北京、深圳等地的文稿拍卖,这已经是公开地把文学作品视为商品,公平竞争、自由选择,一部作品卖上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已不是天方夜谭。三是“广告化”,在80年代张贤亮为自己的作品选了个集子,并且破天荒地为其推销打广告,这在当时还是条新闻。到了90年代作家已没有了羞涩,公然借助一些传媒做广告式的亮相,要么签约卖身,要么打官司,要么上电视或报纸,途径甚多,不一而足。像《废都》、《白鹿原》、“布老虎丛书”等作品的出版过程就明显充满着商业运作的痕迹,那些铺天盖地的红绿广告和故弄玄虚的传媒访谈就是证明。四是“影视化”,在当今中国小说界,文学与影视的温情联姻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景观。任何作家都不拒绝影视的诱惑,因为后者是信息时代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文学走向社会的最佳途径。王朔是小说界第一个大尝甜头的人,他的几部小说居然一年内被搬上银幕,构成了“王朔电影年”。他是被“骂出了名,被拍红了的”,其成功说明了商业文化的强大,其中的内涵是复杂和耐人寻味的。苏童几乎重演了王朔走红的过程,另外像莫言、刘恒、余华、叶兆言等人都从影视风波获得了好处。面对这股来势汹涌的“影视化”热潮,冯骥才公开表示了对影视改编小说时导致的文学自主性或主体性消亡的某种担忧;“新写实小说”后期作品的话本写作倾向也表明文学自身独具的“精英意识”和“个体话语”已经面临危机。
7.“严肃性”与“通俗性”的矛盾
前不久由王一川等人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把金庸排名第三,仅次于鲁迅和郭沫若,这一举措在文学界引起舆论大哗,这反映了长期以来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争夺阵地,严肃文学挤兑通俗文学的情况。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讲究“文以载道”,文学必须具有使命感、启迪教化作用、典雅情趣和“仕文化”型的审美特质,文学必然是“精英意识”和“美的静观”的产物,是倾尽身心、沤心呖血的严肃结晶,因此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向来是轻贱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这也导致了50、60年代俗文学的萧条,就连赵树理这样俗文学色彩很重的作家也被竭力纳入严肃文学的范畴。
但是,新时期宣告了严肃文学独霸天下的时代的结束,通俗文学以迅猛的方式从严肃文学手中夺去了半壁江山和众多的读者,武侠小说在这场争夺战中建了头功,随后又是新言情小说、纪实文学、性爱文学、财经小说甚至地摊文学。从“金庸热”、“琼瑶热”到“梁凤仪热”,港台式的通俗文学之风席卷大陆,最终导致了“雪米莉风波”,这些通俗文学作品的销量是严肃文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严肃作家陷入了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要严肃和“阳春白雪”,就可能失去读者群,“曲越高和越寡”,这头是生存危机;要通俗和“下里巴人”,就意味着放弃尊严和责任,降格媚俗,这一头是信仰危机。往哪边靠拢都会有得亦有失。
新时期的严肃文学阵营已在悄悄拆去与通俗文学之间森严的壁垒,但真正向通俗文学靠拢的是某些长篇小说。近年来长篇小说走俏文坛、热销市场便是沾了“通俗”之光。从“陕军”的力作《废都》、《白鹿原》等几部作品来看,无不涉“性”,这恰好是通俗文学最有吸引力的一把杀手锏,因此围绕《废都》等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争论就不可避免了。现在文坛上明里暗地从事通俗文学乃至“广告文学”写作的严肃作家为数不少,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作家谭力、雁宁等泡制的“雪米莉系列”,从题材内容、创作意图到推出手段都是地道“通俗”的。
显然,严肃文学在“通俗化”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严肃文学正在失去原有的精神价值,它在走向大众的思想指导下正在以通俗文学的内容维持其生存,像“布老虎丛书”中洪峰的《苦界》显然不能与他的《瀚海》同日而语,而铁凝的《无雨之城》也大逊于她的《玫瑰门》。第二是现在行销的长篇小说多以情节精采见长,但思想内涵及创见明显减弱,作品中充斥着市民习气和媚俗倾向,以致于有的作家不得不站出来重提作家的使命感。第三是某些走俏的严肃作家的作品其实已等同于“地摊文学”,在内容、装帧等方面一味地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描写的重点是“性”、“欲”、“暴力”,连书名也取得俗不可耐,有的甚至“通俗”得成为“黄源”之一。从以上问题不难看出某些严肃文学作品产生的阅读热主要是“外热”而不是“内热”,是靠炒作技巧、包装手段、投机取巧和虚张声势形成的“虚热”,缺乏属于严肃文学自身生成规律的内在动力,片面追求短期热销效益和精品意识的丧失是其致命弱点。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否应该给它们留下几个“严肃”的席位是令人怀疑的。
新世纪正随着星移斗转悄悄迫近,全社会都在以焦灼、困惑和渴盼的复杂心态迎接着它的到来,文学的矛盾正是这种社会情态最真实的反映。但矛盾孕育和预示着新的转机,混沌在理性精神之光的穿射和照耀下最终必将化为一种清彻的透明和壮阔。回顾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人在精神探索远征中的强大力量和惨烈进取,无论是成就和进步,还是困惑、矛盾、误区乃至错误,都显示出一种最真诚、最美丽的本质。正是这种对立和矛盾,敦促着文学不断改革发展,新时期文学完全具有走出混沌、消解矛盾和步入新域的可能。其实,目前的创作迹象已经显露出了过渡时期文学的某些特征,它完全可能导致一种真正文学化、美学化、人民化、民族化的新阶段的来临。我隐约感到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屹立着一个目标,它在向我们招手——那也许就是“后新时期文学”。一种光荣的结束和伟大的开始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百年文坛风雨过,必定是天高云淡的灿烂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