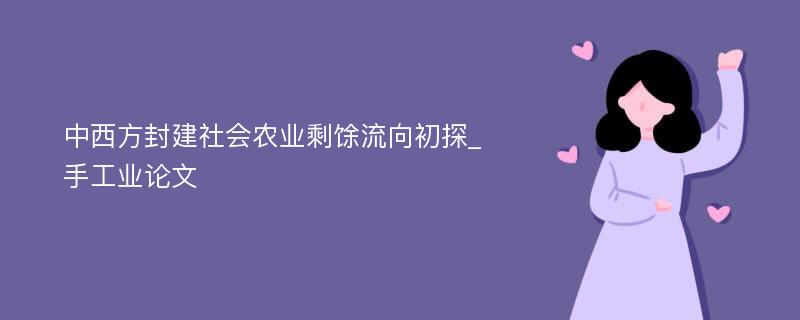
中西封建社会农业剩余流向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社会论文,流向论文,中西论文,剩余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封建时代,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剩余(实物和价值)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它能否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对封建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转化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因此,探讨中西封建时代农业剩余的流向,以判明其用途,对于探求中西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命运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项工作又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农业剩余的直接流向都是封建地主阶级,这是不说自明的事情。但是,到手之后的农业剩余的用途、去向何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地主阶级都将攫得的农业剩余用于自身的享受,增强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这是无疑问的,但是,用的方法却有别。因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农业剩余的种类却是有限的。地主阶级的需求的多样性和农业剩余的种类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只能用两个办法解决,一是地主阶级用这些农业剩余直接生产工业品,以满足他们在食物之外的其他需求:二是与其他阶级进行交换,互通有无。若是前者,地主阶级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商业,农业剩余就会留在他们那里。若是后者,农业剩余就会从他们那里流向其他阶级。因此,地主阶级虽然是农业剩余的直接接收者,但不一定是农业剩余的最终归宿。而决定农业剩余的最终流向的关键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封建社会的两大经济部门,农业和工商业、金融业之间的结合方式,是同为一体,还是一分为二。换言之,土地权和货币权(工商业、金融业的所有权)是合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在这方面,中西却是截然不同。
11、12世纪之后,西欧土地权和货币权是分离的:一、主要工商业为城市所垄断。西欧封建城市的兴起与庄园手工业的分离是联在一起的。它首先是昔日在庄园内从事手工业的农奴用货币租代替劳役和实物租,从而获得离开庄园的权利,汇聚到交通要道、城堡周围,和犹太商人、弃农从商的小贵族一起形成城市的居民。〔1 〕其次新兴的城市瓦解残存的庄园手工业。即封建贵族因能从附近的城市买到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的手工业品,能雇到技术更好的手艺人,从而逐渐放弃庄园中残留的工匠和手工作坊。例如,法国的沙特尔圣母院在1130年左右给其自营地的代理人下了一份指令,规定今后不再要求庄园的农奴履行纺织劳役。〔2〕结果,除矿冶业和农民的家庭纺织业外,主要手工业, 如高级呢绒业、皮革业等均已汇聚到城市里。
手工业向城市的集中,开始时完全是一个自发的经济过程,后来,却在西欧大陆形成了一种工业垄断主义。城市当局用暴力清除农村中残存的手工业,以加速手工业向城市的集中。而德国人甚至在他们所征服的斯拉夫人境内也大力推行这种政策。〔3 〕结果导致庄园手工业的灭亡。德比等人说,1100年以前,庄园手工业已从意大利庄园的财产清单中完全消失;在法国,它的灭亡是在12世纪前叶;德国庄园手工业残喘的时间要长一些,但不久也都湮灭了。〔4〕
在手工业脱离庄园的同时,商业亦集中到城市。犹太商人、叙利亚商人不再四处漂泊,逐渐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一些小贵族则将地租转为资本,成为城市里最初的贵族阶级。〔5 〕而一些为僧俗大贵族经营运输业和临时性商业的管家、执事也脱离了领主的控制,成了市民。结果如德比所说:“商人,也像手工业者一样,从贵族的家中漂走了。”〔6〕
主要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在庄园里了,而迁移到城市里。15世纪末之前的西欧封建结构出现一种新格局,“城市成了工商业中心,而乡村则主要生产粮食和原料。”〔7〕
二、留在农村的手工业亦脱离了领主的控制,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采矿业、冶炼业等无法迁居城市而留在农村。但是,他们不仅已脱离领主的控制,成立自己的行会,在农民中,特别是在自由农中还不断分化出各种专业的和兼业的铁匠等手工业匠人。但他们已不同于庄园中原来的农奴工匠,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封建主得到他们的产品或雇用他们必须等价交换,所以,他们的手工业也不再是贵族经济的组成部分。〔8〕
显然,西欧的土地权和工商业、金融业的所有权不再为封建贵族独享,而分别为贵族和工商业者所有,从而开始了西欧的“资本不依赖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历史。〔9〕致使货币权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它和土地权的对立成了西欧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
与西欧相反,中国的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在占有大部分土地的同时,也垄断了主要工商业。中国官工官商历史之悠久、种类之多、规模之庞大是世界封建史上罕见的。春秋战国时,各国手工业品都无不标有“相邦”、“守相”、“郡”、“郡守”、“县”、“县令”的字样。〔10〕汉武帝颁行告缗令,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后,几乎所有的主要工商业部门都被收归官有。从此之后,官办手工业的种类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官办手工业是城市手工业中最主要的部分。”〔11〕而禁榷的办法也越来越严厉,被禁榷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宋代时,连酒、茶、矾、香药、宝物等的经营都归政府管辖。其贪婪之甚,连官吏都觉得过分:“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帛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12〕明中叶之后,情况虽有变化,但官工官商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如景德镇,仍“多官府造作之所”,“官窑多达五十八座,民窑则仅有二十座”。〔13〕清代湖南,“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14〕
主要工商业为封建国家所垄断,民间工商业的种类和规模就极为有限,特别是明中叶之前。而这有限的民间工商业也大多为各类地主所把持。三国时的江统上书魏帝说:“秦汉以来,风俗转簿,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染相望,莫以为耻。”〔15〕到南北朝时,“更是无上无下,无内无外,可谓无不以贩鬻求利为事者。”这一局面,明清时,仍无变化。景泰二年,“京城官店塌房,多为贵近勋戚所有。”〔16〕湖广一带的城市,“通衢诸绪布店,俱系宗室。”〔17〕
总之,中国的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垄断了主要工商业是无容置辩的事实。因此,同西欧的封建经济结构相反,土地所有权和工商业、金融业的所有权在中国并未分离,它们合二为一,同属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
截然不同的中国、西欧封建经济结构,决定了中西封建地主阶级的不同的供求机制,从而注定了两者的农业剩余流向的大相径庭。
11世纪后的西欧,土地权和货币权相分离,这无疑是西欧社会分工的一次巨大的进步。因为,资本独立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同时“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18〕城乡之间,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封建贵族和市民之间从此建立起以市场为纽带的相互供求的依赖机制。封建贵族严重地依赖于城市,依赖于金钱,他们的吃穿住行及行军作战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无不仰仗于市民。 在1313—14年和1318—19年间,英国汤姆士伯爵每年用于购买食物、 饮料及照明材料的费用都超过了5千镑。〔19〕13世纪末, 在英国米德兰西部地区,仅次于市民的粮食买主就是贵族。〔20〕贵族们连其庄园能够生产的食品都需购买,何况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品不断地升级换代,新的享乐方式层出不穷,封建贵族对城市工商业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从12世纪起逐渐盛行起来的劳役折算,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贵族们的这种依赖,他们连口粮都得仰给于市场。〔21〕恩格斯曾生动地评述过这一情况:“贵族们的需求也增加和改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他们自己也离不开城市。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铠甲和武器)还是从城市得到的。本国的呢绒、家具和装饰品,意大利的纺织品,布拉维特的花边,北方的毛皮,列万特的水果,印度的香料,——所有这一切,除了肥皂以外,贵族们都是从市民那里买到的。”〔22〕
贵族们的生产生活如此离不开工商业,而11、12世纪后的工商业又不再为西欧贵族所有,他们的主要财富就是土地,自营地的收成和农民缴纳的租赋和法庭罚款就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尽管有些贵族能从市民那里收取货币赋税和货币地租,但是,受制于城市的自治权,这些租赋的数额都十分有限。而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则使这个有限的数额变得越来越不足挂齿。因此,在工商业已不再属于贵族们的情况下,贵族们维持其生活和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将他们从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农业剩余用来与市民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工业品。在劳役地租盛行时,领主们就不得不将其自营地上生产的大部分农牧产品和农奴缴纳的实物销往市场以获取货币。然后,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用品。1271—1272年间,英国的索翰庄园出售的小麦达总产量的3/4,大麦达2/3,仅燕麦没有出售。〔23〕若再考虑到留下的粮食中的大部分被用来饲养出售的各种牲畜,那么出售的粮食在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则要比上述数字大得多。
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仅变换了封建贵族阶级所接收的农业剩余的形式。但是此时贵族连其所需要的粮食都要取之于市场,可见他们对城市及其工商业的依赖程度了。在中古西欧,无论地租是什么形式,农民所创造出来的农业剩余中的大部分都从封建贵族那里流进了工商业者手中。因此,中古西欧农业剩余的最终流向不是封建贵族,而是市民。
两权分离的西欧封建经济结构规定了西欧农业剩余的这一特殊流向,也决定了这一流向所产生的特殊结果,即不仅大部分农业剩余产品的最终得主是市民阶级,也使农业剩余价值不同程度地流进了这个阶级的腰包。因为货币权一旦独立,独立后的市民阶级就必然要发展起自己的特殊组织和城乡之间的贸易,市民阶级与贵族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市民们低进高出,将封建贵族从农民那里攫取来的农业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夺到自己的手中。
这种不平等贸易又因农业和工商业的生产条件的迥异而加剧。受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自然条件等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与之相反,手工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都远非农业所能相比。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生产力增加就增加,生产力降低就降低。”〔24〕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在平均利润率尚未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上,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它在不断变动的供求关系的驱动下,围绕着价值而上下波动。市民们生产的手工业品的价值因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地下降,这些手工业品的市场价格也应随着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碍于西欧市民的特殊组织,价格的这种下降却是不可能的。城市的行会组织和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的城市政府颁布了各种法令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维持他们对市场的统治和垄断。因此,尽管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下降,但他们却不会降低其产品的售价,也不会提高农牧产品的购价,反而尽可能地压低价格。各行会统一其产品的售价,也统一购进粮食和原料。面对这种垄断,农村居民,包括封建贵族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居住分散,利益不同,未能建立起统一的组织,无法统一其农牧产品的售价,更不可能调节工商业品的购价。因而他们不仅要用高价购进工商业品,而且还得低价出售其农牧产品。在城市势力所及的农村地区,市政当局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法令,“禁止从乡村输出谷物到本地区的城市首府之外”,“规定要运往城市市场上出售的具体谷物定额,出售价格有限定或者详加管理”。在1266—1322年间,比萨的货币价值跌落了66%,而谷物价格的上升却被圈定在25%以内。〔25〕势力强大的城市还将这种垄断和控制的权力伸向远离它们的乡村。例如,1236年,威尼斯竟垄断了波河河谷和特里维索及其更南地区的谷物的输出。1273年,威尼斯宣布,没有该城的同意,波伦亚每年在安科纳等地购买的小麦不得超过2万科比斯(筐)。〔26〕
城市的这一系列政策必然使手工业品极其昂贵,农牧产品价格低廉。1300年前后,价格最便宜的粗呢绒是1先令至1先令6便士一码, 一件破旧外套值3先令以上,一个家庭常用的锅也需要2先令多;而此时的一条耕牛仅值4—5先令,〔27〕一品脱(208 公斤)的粮食的平均价格只有4先令。〔28〕
较之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对农村居民的剥削则更胜一筹。中世纪的交通不便给商人施展其商业骗术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们倒手转卖,任意加价,谋取暴利,其利润之高远非其他阶级所能与之相比。 1511年到1526年间,大商人福格家族的年利润率都高达54%以上。 〔29〕马克思论述这一情况时写道,城市通过它的垄断价格,课税制度,它的直接的商业骗术和高利贷,剥削着农村,“而中世纪城市资本的积累,就主要来源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农村的剥削。”〔30〕城市因此而积累起来大量的财富,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市民。14世纪初,英国国王欠佛罗伦萨城的罗尔迪和佩鲁齐家族的债务高达20万英镑,而此时,该国王的年收入却仅有3万英镑,英国全国一年的出口总额也只有25 万英镑。〔31〕
与市民们相反,贵族们在市场上是低出高进,他们从农民那里攫来的农业剩余,乃至他们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矿山等社会财富都通过这种贸易转到市民手中,以致日益贫穷。13世纪时,几乎全西欧的贵族阶级都为财政问题所困扰。英国贵族中有60%以上的家庭欠债。其中,不少人所欠债务为其年收入的6倍以上。〔32〕在意大利的锡耶那,甚至“可以看到古代贵族家庭的后裔在沿门乞讨”。其后,“任何地方大部分贵族都已沦为一个穷困的、有时是饥饿的阶级。”〔33〕为了生存,贵族们不得不出卖、转让、抵押土地。14、15世纪时,在英国,平均25年就有1/4的贵族家庭因丧失土地而消亡。〔34〕以致在西欧城市兴起之后的短短的四、五百年间就使西欧封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尽管中古西欧的农田单产量、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远不如当时的中国,但是,为数不多的农业剩余却能流到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市民阶级手中,这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西欧后来居上的原因之一。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自始至终地享有土地和工商业、金融业的所有权,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供求机制截然不同于中古西欧封建贵族的供求机制,它具有两大特点:
一、中国各类地主的家庭都程度不等地拥有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自己家庭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供给市场多余的产品,使中国的地主家庭都具有很强的自给自足性,特别是大地主家庭。著名的《四民月令》、《齐民要术》、《颜氏家训》都详细地列举了这种情况,并将其作为地主经济的典型模式予以提倡,一直为历代地主家庭所模仿。直到清末,著名的贵族大地主曲阜孔府仍蓄有数百名农奴身份的匠人,不仅生产孔家所需要的物品,连每年上贡给朝廷的物品都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制的。〔35〕庞大的、种类齐全的官办手工业所生产的手工业品也主要是满足朝廷、军队和各级官府自身的需要,封建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程度因而也很高。
二、地主家庭,特别是中小地主家庭的物品的自给程度虽然有限,必须求之于市场,但是,在主要工商业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所垄断的情况下,垄断工商业市场的大都是地主:地主商人或商人地主。这即是说,单个地主家庭虽然自给程度有限,但就整个地主阶级而言,却并非如此。
这两大特点说明,中国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满足其多种需求的主要途径不是求之于其他阶级,而是求之于己。中国的农业剩余的最终流向因而不是工商业者,而是地主阶级本身。不仅如此,这个阶级还能利用工商业、金融业进一步地榨取农民和其他城乡居民的血汗,使他们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受益者。
绝大部分农业剩余和工商业利润都流到中国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手中,他们也就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力来增长自己的经济实力,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兼并土地,扩充军队和官僚机构,强化封建国家机器。因此,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从初期开始,土地兼并就愈演愈烈,官僚机构和战争机器越来越庞大。尽管也有一部分农业剩余被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用来扩充工商业,但中国的官工官商和各类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却不能和西欧市民的工商业同日而语,也不能同西欧新贵族的工商业等同视之。马克思说:“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时,也是它的产物。”〔36〕因此,在中国,“凡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社区,奴仆也跟着盛行起来,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闽粤等省,同时也是蓄奴最多最严重的社区。”〔37〕如果基于这种性质的劳动之上的工商业也能够发展成资本主义的话,那则如马克思所说,“古代、拜占庭等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38〕这种工商业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工商业,它也就不可能使地主阶级市民化、资产阶级化,而只能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积聚社会财富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使货币权,这个促进了西欧工业社会产生的杠杆,变成了土地权的附庸,成了巩固封建统治的有力的武器。
只要农业剩余主要流到封建制度的主要代表和最顽固的堡垒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即使农业生产力再发达,农业劳动生产率再高,农民创造的农业剩余再多,也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只能增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强化封建国家统治机器。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创造出了中古西欧农业远不能与之相比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剩余,却未能使中国迈进工业社会的一个原因所在。
由于中西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中西农业剩余的流向大相迥异,对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化所起的作用便截然相反。这说明,传统封建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化虽然只有在超出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但是,这种程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绝对不是这一转化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由它而规定的农业剩余的一定流向也是这一转化得以完成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注释:
〔1〕德比:《欧洲经济的早期发展》(G.Duby,The Earrly Growth of European Economy),康奈尔1974年版,第225、236页。
〔2〕德比:《中世纪西方的农业经济与乡村生活》(G.Duby,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伦敦1968年版,第153、221、222页。
〔3〕〔4〕德比:《中世纪西方的农业经济与乡村生活》, 第108、153、208页;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M.Post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剑桥1972年版,第473、474页;第3卷,剑桥1963年版,第213页。
〔5 〕希伯特:《中世纪城市贵族的起源》, 《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1955年第3期。
〔6〕德比:《欧洲经济的早期发展》,第232、238—240页。
〔7〕鲁札特:《意大利经济史》(G.Luzzatto,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aly),纽约1961年版,第81、92、102、104页。
〔8〕德比:《中世纪西方的农业经济与乡村生活》,第15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10〕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62页。
〔11〕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6页。
〔12〕《石徂徕集》下《明禁》。
〔13〕《江西通志》卷132,《宦绩录·饶州府》。
〔14〕《广末新语》卷9,另见《通判条格》卷18。
〔15〕《三国志·魏志·江统传》。
〔16〕《明经世文编》卷59。
〔17〕《楚宗纪》注《贸易》。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19〕米勒等:《中世纪英国的乡村社会和经济变化》(E. Miller,Medieval England: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s), 伦敦1980年版,第229页。
〔20〕希尔顿:《中世纪社会:十三世纪末的米德兰西部地区》(R.Hilton,A Medieval Society:The West Midlands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剑桥1983年版,第167页。
〔21〕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94、16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9页。
〔23〕米勒等:《中世纪英国的乡村社会和经济变化》,第224、225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7页。
〔25〕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0卷,第278页。
〔26〕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74页。
〔27〕米勒等:《中世纪英国的乡村社会和经济变化》,第158、 163页;希尔顿:《中世纪社会:十三世纪末的米德兰西部地区》,第105页。
〔28〕波斯坦:《中世纪农业论文集》(M.Postan, Essays onMedieval Agriculture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Economy),剑桥1973年版,第240页注释。
〔29〕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第1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分册,第257页。
〔31〕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455页;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249、250页。
〔32〕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J.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罗曼1980年版,第102页。
〔33〕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245页。
〔34〕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第104页。
〔35〕《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33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分册,第564页。
〔37〕付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31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09页。
标签:手工业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庄园经济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剑桥欧洲经济史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世纪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工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