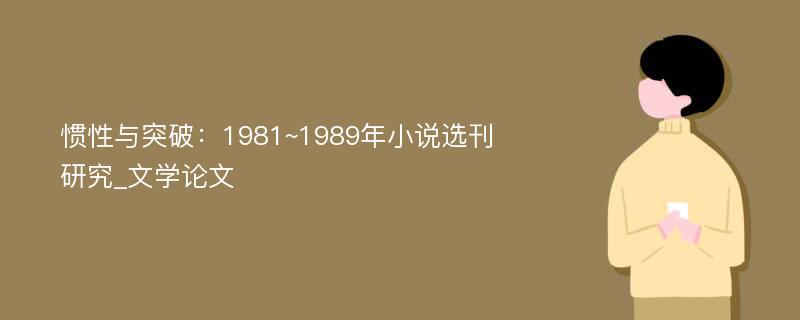
惯性与突破——1981年至1989年《小说选刊》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刊论文,惯性论文,小说论文,年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78年,为了促进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国作协委托《人民文学》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为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可供年终评奖候选的短篇佳作,《人民文学》于1980年10月增办了《小说选刊》月刊。《小说选刊》于1989年停刊,90年代中期复刊。应该说,停刊前的《小说选刊》具有更加鲜明的审美包容性和艺术敏感度,复刊后则元气大伤。1981年至1989年的《小说选刊》历经新时期文学的盛况,容括了新时期小说的起落沉浮与兴衰荣盛,可以说是一部缩写的新时期小说史。
《小说选刊》是新时期以来创刊较早、发行量很大的选刊。茅盾在“发刊词”中指出《小说选刊》“将选载具有较高思想水平和艺术特色的作品,重点评介,以便对读者的欣赏水平乃至培养文学新人都有所助益,此亦争取短篇小说创作的更大繁荣之一道。”[1]自创刊之日起,选取有较高思想水平和艺术特色的作品,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培养文学新人即成为其办刊方针。《小说选刊》所选作品基本上代表了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走向。《小说选刊》成为当时权威性的选刊,许多作者和编者都以《小说选刊》选登自己创作或编发的作品为荣,许多地方评选优秀作品,也把《小说选刊》是否选登过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
创刊之初,《小说选刊》形式较为单一,所选作品全部为短篇小说,配以评论和创作谈,持重有余但活泼不足。“为了适应当时小说创作的发展形势,更好地配合评奖工作和进一步推动小说创作走向繁荣”[2],1984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对《小说选刊》改版,将其与《人民文学》分离,单独成立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葛洛为主编。改版后的《小说选刊》不仅革新版面,扩大发行,而且开始选登中篇小说,并逐年增加小小说的数量。除了在作品之后附有“作者简介”外,还设有评论、创作谈、新人评介和读者之页等栏目,其中评论创作谈是《小说选刊》在当时不同于其它选刊的显著特色之一。1985年,《小说选刊》再次改版,将篇幅扩大,并改为书籍装订。在选篇上更为开阔,增选了台湾、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作家用中文写的中、短篇新作。1986年,李国文被任命为主编。改版后的《小说选刊》以一种开放的、复调的、多元共存的气度,选登了具有多种艺术风格、多层次审美向度和丰厚深沉的历史感的作品。《小说选刊》为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文学思潮推波助澜,新时期不同文学潮流的标志性作品都曾入选,其中不乏非主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本,这些都推动了我国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发展。
茅盾在《小说选刊》的发刊词上有句勉励之语:“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名标金榜,尽是后起之秀。”《小说选刊》一直为能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经过两次改版,《小说选刊》不断扩大期刊来源。1984年以前,期刊来源有90种,1985年后增加了88种,其中包括报纸及台港的期刊。《小说选刊》不仅关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的文学期刊,也关注边远地区的文学期刊。虽然各种期刊入选率是不平均的,但如此广泛的期刊来源,为挑选更为优秀的作品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更全面的反映了我国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在时代政治倡导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短篇小说由于形式上的短小快捷而肩负起侦察兵、探索者和开路先锋的作用。80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大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并积极作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也许是当初全国小说评奖首先从短篇小说开始的一个重要缘由。为配合当时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小说选刊》也以刊发短篇小说为主,其中1984年改版以前完全刊发短篇小说。到了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篇小说独特的审美特质与叙事空间,为作家提供了一个相当充分的审美载体和相对自由的文本空间,使得中篇小说大量涌现。同时,读者对于短篇小说的高度热忱开始低落,开始转向更注重于审美功能,生活容量大、传奇色彩强的中篇小说。《小说选刊》选发了大量优秀的中篇小说,其中多是各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如:《燕赵悲歌》、《雪落黄河静无声》、《绿化树》、《北方的河》、《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小鲍庄》、《棋王》、《你别无选择》、《瀚海》、《红高粱》、《灵旗》、《烦恼人生》、《风景》、《新兵连》、《白涡》、《伏羲伏羲》等等。这些作品成为许多作家迄今为止的代表作,而蒋子龙、丛维熙、张贤亮、张承志、阿城、韩少功、王安忆、刘索拉、洪峰、莫言、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作家也恰恰靠这些中篇奠定了他们在文坛上的艺术地位。
二
由于处于一个变动不拘的年代,1981—1989年的《小说选刊》始终处于变化中。它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着一个惯性到突破的变化过程。惯性表现为80年代初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突破则指80年代中后期《小说选刊》逐渐冲破政治藩篱而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以及为文学回到自身所作的努力。
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总是要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密切相关。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和愿望不仅仅只属于作家们,同时它也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守护。《小说选刊》作为中国作协主办的刊物,必然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纵观《小说选刊》1981—1989年近十年选登的作品,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始终是主流。从产生“轰动效应”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狂飙突起的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和新写实文学,现实主义始终贯穿其中并不断深化、发展与创新。80年代初期《小说选刊》所选作品延续着现实主义传统,侧重于社会学、政治学层面,现实主义审美风格一统天下。题材单一,要么注重有关“历史清算”和“历史记忆”的书写,要么选择与时代紧密相连、反映改革的新人新事与新矛盾的文本。虽然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文学“瞒和骗”和“假大空”的某些积弊,但其调和主义的姿态及其所允诺的廉价的希望也使文学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80年代中后期,随着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小说选刊》所选作品从社会学层面过渡到文化历史层面,在题材、创作手法、审美上走向多样化。但也正象雷达在《小说选刊》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动荡的低谷——论1988小说潮汐》[3]中所强调的“多元,应是有主潮,有方向感的多元,而不是一盘散沙的多元——一盘散沙是谈不上‘元’的”,这里的主潮就是指现实主义的创作主潮。《小说选刊》致力于现实主义的发展深化和创新,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丰富自己,兼容各种创作方法、技巧,但有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依然是其选择作品的关键。
《小说选刊》在1983年第一次改版前一直是《人民文学》的附属刊物,所以在《小说选刊》的期刊来源中,《人民文学》的作品入选比例最大。在1981—1989年间,《小说选刊》共选载了178种报刊杂志的1132篇小说,平均每种期刊入选6篇(有些期刊只入选过1篇),而《人民文学》则入选了74篇。因为两份刊物同在一个编辑部领导下,《小说选刊》选择作品的标准与《人民文学》有相似之处,《人民文学》的作品入选率最高也就不难理解。独立后的《小说选刊》的期刊来源中,《人民文学》的入选率依然占被选期刊之首。《人民文学》作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文学期刊,拥有更多更为优秀的作品是可能的,但这种入选率也表明了《小说选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趋附与认同。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也是影响《小说选刊》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新时期文学领域的重要事件,几乎开了我国文学评奖的世纪先河。中国作协当时举办短篇小说评奖旨在利用短篇小说为思想解放运动发挥巨大作用,《小说选刊》就是为评奖提供候选作品应运而生的。周扬曾说过:“我们评奖的目的,就是要发挥评奖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在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轨道前进,实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文学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更进一步提高。”[4]从1978年至200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共举办9届。1981年以前,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由《人民文学》承办,从1981年起,改由《小说选刊》承办。在1981—1989年间,《小说选刊》参与评奖的有五届。其中1981年的20篇获奖小说,有14篇被《小说选刊》选载过,其余四届的获奖作品全部都被《小说选刊》选载过。
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是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的文学奖项,它在引导作家创作方向的同时,也表现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应有尊重。“但任何奖项的设立,本身就有意识形态性,它除了举荐和维护文艺自身的生产规则外,还要考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评奖标准的要求。”[5]由于其自身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的约束,短篇小说评奖的标准就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其评奖结果必然要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在1981年—1989年间的五届评奖中,名列获奖名单榜首的《内当家》、《拜年》、《围墙》、《干草》、《五月》,全是表现社会主流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短篇小说评奖极大的影响了《小说选刊》选篇的标准,评奖更关注小说的思想性,更关注引起社会轰动效应的积极反映时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小说选刊》也着意选载这样的作品。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的《小说选刊》则逐渐突破了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束缚与规约。在选择篇目时,更注重贴近文学的审美本质,努力向文学本身回归。
三
尽管有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小说选刊》作为一本严肃的纯文学期刊,从创刊之日起就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立场,保有自己的文学理想与艺术风格。从其选取“有较高思想水平和艺术特色的作品”的办刊方针,到以后一系列的文学实践,《小说选刊》显示了其对审美底蕴和精神层次的追求,对历史精神的自觉追随。即使在创刊初期,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冲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充满审美内蕴与探索人性魅力的清新之作,如宗璞的《鲁鲁》、吴若增的《翡翠烟嘴》、林斤澜的《溪鳗》等。尽管这样的作品在当时还不多见,但毕竟让人们感到了《小说选刊》为文学本性的回归而做出的努力。纵观《小说选刊》1981—1989年近十年选登的作品,从产生“轰动效应”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狂飙凸起的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和新写实文学,《小说选刊》一直致力于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在现实主义流变的过程中,文学的审美特性得以回归与伸展,文本意识走向了自觉。
1985年以后,《小说选刊》对小说文本形式的探索表现了极大的支持与宽容,选登了一些既有丰厚的形式意味又有独特的审美发现的小说,以及一些现代派、先锋派小说和表现非主流意识的作品。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何立伟的《白色鸟》、王蒙的《冬天的话题》、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无为在歧路》、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谌容的《减去十岁》、韩少功的《归去来》《女女女》、宗璞的《泥淖中的头颅》、莫言的《红高粱》、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王朔的《橡皮人》、洪峰的《瀚海》、余华的《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马原的《游神》、陈村的《一天》、叶兆言的《追月楼》等。对这些作品的选登,显示了《小说选刊》对小说形式的新空间和审美形态的多样化追求。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作品在《小说选刊》的全部选登作品中所占比例是很有限的,而且即使是它已选登的先锋派作家的作品,有的也并非其代表作。如《小说选刊》只选登了马原的一篇小说《游神》,却没有选登他的堪称先锋派经典的《岗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式》,格非的代表作《褐色鸟群》《迷舟》,洪峰的《湮没》《极地之侧》,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古典爱情》、王朔的《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也未被选入。另一些在文本叙事与文体实验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被遗漏了,如徐小斌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小说选刊》虽不是先锋派文学的园地,但这些重要作品的丢失,说明《小说选刊》在当时作为主流刊物对文本形式的探索是有所保留的。但即使是这种对文学多样化有限度的认同与支持,在当时也是弥足珍贵的。这其中所表现出的开风气之先的勇气、鲜明的审美包容性和独特的艺术敏感度都为文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纵观1981—1989年的《小说选刊》的发展,其中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突破,有现实主义的流变,也有对非主流作品的有限度的认同与支持。《小说选刊》以其对广阔的现实主义的执著与兼容并包的气度,为新时期小说在形态学上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创作景观,为新时期小说的多样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