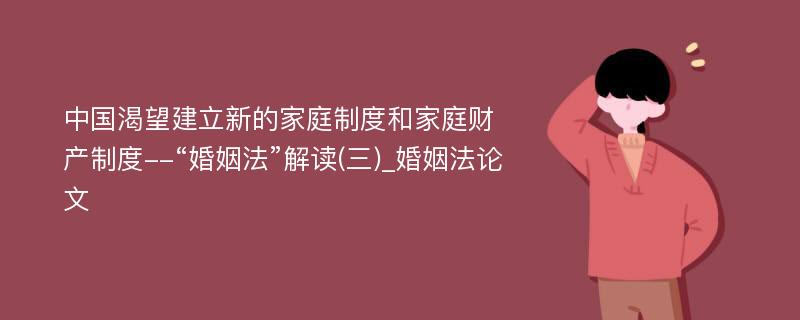
中国亟宜确立新型的家制和家产制——婚姻法解释(三)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姻法论文,家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清官难断家务事”
看完婚姻法解释(三),说实话,我佩服最高人民法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勇气。它注定要遭遇社会批评甚至反感。中国古谚曰“清官难断家务事”,而该司法解释已经深度介入到家务事中。同时,我也理解公众的情绪,多数人并不关心司法解释的专业水准,他们关注的是法律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显然,现在这种影响令人不满。
关于婚姻法解释(三)的逐条讨论已经很多,在学习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到,只要保留那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条款,人们就不会满意。而这些条款在婚姻法解释(三)中占了近一半的比重。具体说来,共有9条之多,分别是第6至8条、第11至13条、第15至17条等,这9个条款大致涉及四种问题,即夫妻个人财产在婚后的归属、父母资助财产的归属、夫妻继承财产的归属和婚姻期间债务的负担等。这些条款与《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二)具有关联性和连续性,只是以前条款不多,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次密集地出现,说明新时期的家庭财产矛盾已经发展到必须予以总体解决的地步,最高人民法院的本意,定是希望用细化规则去厘清夫妻财产的归属,以使下级法院临案有所准据。没想到,这些条款使公众受到暗示,认为国家从此提倡夫妻在生活中把经济账算清楚,以便做好离婚和分割财产的准备。国人对婚姻的态度,自来避讳离婚,“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是对婚姻的最佳祝福。婚姻法解释(三)中的这些条款,有冒天下大不韪之嫌,这就难怪有网友开玩笑说:《婚姻法》成了“离婚法”。
我认为,这种不满不再是法律技术问题,而是一种重要的法文化现象。仅对该司法解释进行条文解析,不足以理解这种文化现象。我的基本看法是,司法解释(三)是《婚姻法》的自然延伸,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该司法解释,是我国在家庭法领域原定的立法方向和法律框架向前推进的结果。如果不从立法方向、框架和原则上去考察,我们无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所面临的困境。同时,如果不正视家庭法的立法方向和框架的失误,最高人民法院只能一边承受公众舆论的压力,一边被迫出台司法解释(四)、(五)、(六)等,以致无穷。因此,要把最高人民法院从家庭法的制度困境中拉出来,必须对回过头来审视和反思《婚姻法》。
所以,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①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具有哪些根本区别,家庭内部为什么不适宜提倡“算清楚”经济账,以及国家法应持何种态度对待家庭矛盾;②既要化解新时期的家庭矛盾,又要让最高人民法院走出《婚姻法》预设的制度陷阱,必须在法律框架和具体制度方面做出哪些创新。
二、国家法对家庭关系应持谦抑态度
自秦朝以来,国家就把家庭视为重要的社会基础,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并意识到,惟如此才能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汉代以来,儒家理论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学说,在它影响下,国家法确立了以谦抑态度对待家庭问题的基本思路。具体地说,法律只对家庭犯罪做出禁止性或惩罚性规定,民事方面仅被动地因应家庭习惯做出适应性规定,司法则克制自己避免深度介入到家庭纠纷中,为家庭矛盾的自我化解留出充裕空间。
据汉代以来的正史记载,一些官员面对家庭争产案件时,并不主动判断财产归属,而是努力激发亲情,争取双方谦让以平息纷争。今天,这些记载正受到批评,以为古代国家过于强调情理而忽视法律。其实,古代大量的家庭案件,仍需以法律为判断基准,正史记载的处理方法不具备推广可能性。但正史记载发挥着导向作用,它树立了处理家庭纠纷的理想办法。它强调,官吏应重视感化和教育,努力唤醒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尽量避免去算家庭经济账,尽量以协调的方法平息家庭纷争。从留存至今的清代州县档案看,县衙总是尽可能调动亲戚邻里去调解家庭案件,避免把国家权威强势带入到家庭纠纷中去。我们认为,传统法对待家庭的谦抑态度,仍是一笔宝贵的法文化财富。不过,这种谦抑态度只是基于数千年的经验认识,今天更需要从理性角度去解释经验的价值。
家庭作为感情的团体,其最终目标是祥和与喜乐。家庭关系不能等同于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特征是亲密性,一般社会关系的特征则是疏离性。家庭关系丧失了亲密性,家就失去了意义,并对家庭中人构成不幸。除了亲密性外,家庭成员之间还具有感情和利益的紧密相关性,家庭成员退出家庭或有不幸事故,都对家庭利益和家庭幸福带来重大损害。
尽管财产对家庭幸福很重要,但财产只是实现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不是家庭的目的。家庭是以欢乐与幸福为最高宗旨,在此宗旨下,除非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家庭成员间必须在利益方面恪尽容忍义务。更重要的是,由于公正性主要是指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因此,若家庭内部利益分配基本均衡,强调公正反而会削弱亲密性,从而不利于家庭幸福。而社会关系不具备亲密性,社会团结的基础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故社会秩序的最高价值在于实现公正。
家庭和社会的不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约束条件不同。家庭以封闭性为客观约束条件。封闭性意味着家庭成员不可退出或不可或缺。所谓不可退出或不可或缺,并不是事实上不能退出或消灭,而是任一成员的退出或消灭,都会对家庭造成沉重的打击。而社会则以开放性为客观约束条件,社会成员的交往基于平等、互利的预期,一旦不合意,则具有退出的选择权。当然,以上两种约束条件的分析是纯化后的,只是为了表现二者的基本区别,未考虑各种复杂变例。但由此可知,不同的约束条件,决定了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区别看待。
第二,内在关系不同。家庭看重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切可能破坏亲密性的手段均须收敛。算经济账的行为,是区分“我”与人,算得越清楚,心理落差越大,亲密性也越差。至于社会成员之间,则首重独立人格和个体权益,虽然也应保持某种感情联系,但须以充分保护个体权益为基础,一旦损害他人的基本权益,维持感情的必要性也随之降低,更勿论亲密感情。
第三,调整手段不同。调整家庭关系以容忍为原则,尤其是物质生活有基本保障和利益分配相对均衡之后,相互容忍是家庭幸福的必要条件。否则,父母若算计子女,则妨碍子女的身心健康;夫妻间斤斤计较,不利于夫妻和睦;子孙不敬,则老人不会有幸福的晚年。所以,古代中国对家庭秩序的调整主要适用礼,强调夫妻相敬如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同的家庭身份恪尽各自的容忍义务,以保证家庭的祥和与喜乐。法律只是发挥陪衬和辅助礼的作用。但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则以权责明晰为要。古人曰:“与国人交,止于信。”社会普通人之间不存在特定身份关系,故利己为常态,利他为美德。
总之,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有着明确的分界。在家庭秩序中,利他或容忍是必要手段。在家庭内提倡适当容忍,并非否定利己,而是因为容忍与利己是统一的,只有通过容忍来维持家庭成员的亲密性,才符合个人的最高利益。
以上仅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家庭与社会之区别。重视家庭的温馨、和睦与成员利益,不是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且是世界各民族社会共通的。重视亲情和家庭,在任何一个民族社会中,都是文明和有教养的表现。为此,只要想想那些外国战争影片中,战士怀揣着家庭照片上战场的镜头;想想美国著名影片《乱世佳人》中,那种对家园和老橡树的依恋之情,就会发现,中西文化在重视家庭方面没有本质区别。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不可的话,那么,最大的不同在于,在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这样,家庭不但是人的身体之安放处,且为普通人精神或心灵之唯一安放处。而因为有宗教传统,西方人的精神或心灵尚可在宗教中找到寄托。
家庭既然是中国人精神或心灵的惟一安放处,家庭幸福对于个人就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可以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对立,是对普通中国人最大的打击,甚至某个家庭成员的死亡事件,其严重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比如,老人在子孙环绕中死去,叫做“善终”。他的死亡给亲人带来的是悲伤,但一般来说,这种悲伤还不至于引起精神崩溃。而吴飞先生关于当代华北地区自杀现象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家庭成员间的猜忌、隔阂或争吵,亲人间的冷淡、对立或怀疑,以及这些事件或情绪带来的抑郁、窒息、绝望的家庭气氛,均足以使中国人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和自我否定感,引发精神崩溃或自杀事件。是的,如果家庭内部视若寇仇,对于中国人来说,再多的钱、再公正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吴飞先生指出,大多数中国人在自杀前想到的是:“我死了,看你们怎么办?”
正因此,不但在一般意义上,法律应当对家庭问题持谦抑的态度,而且,因家庭是普通中国人惟一的精神寄托,中国的法律还应特别考虑如何设置完善的制度,以细心呵护家庭的祥和与美满。然而,婚姻法却以密集的条文,去规定夫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属,其实际效果,是提醒中国夫妻在财产问题上要加倍小心,提醒人们随时与家人算清经济账,这种提醒将在夫妻间形成持续隔阂的力量,削弱家庭所需的温情、和睦和喜乐的氛围,消解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公众反感的原因,盖均缘于此。我们相信,婚姻法解释(三)的本意绝非如此,遗憾的是,它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
三、设置新型的家制和家产制
不过,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婚姻法解释(三)中详细规定夫妻财产归属是必要的。不能认为,家庭需要温情与亲密,就必须牺牲家庭内部的公正性。关键是,在整个家庭法体系中要把握好亲密性和公正性之间的平衡度,这个平衡度把握得好,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把握得不好,二者就成了对立相悖的关系。婚姻法解释(三)引起社会争议,是因为它加重了“算清楚”的倾向,但它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可能承担多种任务。而且,作为司法解释,它只能在现行的家庭法框架下发展,不能越出去行使立法功能。引发公众反感的,其实是因为在整个家庭法体系中,缺乏与婚姻法解释(三)相平衡的力量,即缺乏保护家庭亲密性的基本制度。这样,再加上婚姻法解释(三)这个砝码,整个家庭法领域就严重失衡了。显然,是整个家庭法框架出了问题,而不是一个司法解释的问题。在这个框架的制约下,最高人民法院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可以表述为:如果要维护家庭的祥和与温情,就不能出台鼓励夫妻间算清经济账的条文;如果缺乏算清楚家庭经济账的法律条文,大量的离婚案件又没有规则可依。
所以,需要认真考虑的是,让最高人民法院陷入两难困境的家庭法框架,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弊病何在?通过怎样的制度创新,才能摆脱这一框架性陷阱?
我认为,现行家庭法框架的根本问题,在于用孤立的《婚姻法》取代一切家庭关系法,并由此导致用单一的夫妻财产制度取代家庭财产制度。这种框架性或结构性的失误,是让最高人民法院进退失据的根源所在。
我国采用《婚姻法》取代其他家庭关系法的立法思路,原先基于两种考虑:一是要取消“封建”的或不平等的旧家庭模式;二是建立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这两种考虑都是正当的。但立法在落实这些考虑时,忽视了与中国家庭传统的衔接,设计了单一化和极端化的家庭法框架,这种框架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对应复杂的中国家庭形态。甚至可以说,立法者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的家庭传统和家庭形态,只是从学理上凭空设计了一个《婚姻法》,想当然地以为可以据此改造中国家庭。在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较为单纯的时期,中国式家庭处于休眠状态,《婚姻法》尚可勉强维持。一旦经济和社会发展起来,中国式家庭立刻活跃起来,展示出它应对新经济和新形势的能力,并由此产生复杂多样的家庭财产关系。单一化的《婚姻法》框架,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家庭财产关系时,立刻显得左支右绌,不得不依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为其弥缝。基于此,要理解婚姻法解释(三)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上升到家庭法的立法思路层面,反思以下三个问题:
(1)取消父权至上的旧家庭模式后,是否不允许中国家庭里有父母?
(2)取消旧家庭后,是否意味着家和家产也需要取消?
(3)取消夫权至上的旧家庭,建立男女平等的新家庭,是否意味着在平等的夫妻之间不能提倡谦让的美德?
显然,三个问题的答案均应是肯定的。但仅有《婚姻法》的立法格局,实际这是对以上三个问题均做了否定回答。由此带来的弊端,需要深入辨析。
第一,《婚姻法》仅仅考虑了夫妻构成的家,而把父母排除在家庭之外,认为父母只能以夫妻身份单独成立一个家,实际这是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取消了父母的合法地位。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要消灭的是父权,现在看来,它连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一起消灭了。通过《婚姻法》,中国式家庭已被强制简化为夫妻式家庭,但却并未根本上改变现实中的家庭结构。而且,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反而强化了传统家庭关系和观念。比如,高房价迫使成年子女更加依赖父母资助,由此强化了父母与小夫妻的经济联系。这种强化的结果,造成父母与小夫妻这一关系中的财产纠纷增多,而《婚姻法》未将这一关系视为家庭内部关系,由此导致司法机关在新形势的冲击下进退失据。直到这类财产纷争发展到无法回避的时候,只好在先天不足的法律框架下细化规则,由此才发展出了婚姻法解释(二)的第22条,并再发展出婚姻法解释(三)的第8条、第13条等。事实上,父母一直就是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固定成员。中国家庭对父母的养老从来就负有不可懈怠的责任,同时,父母很少计较在经济和生活上帮助小夫妻,比如,经济上资助小夫妻购置新房,生活上帮助小夫妻抚养婴幼。在中国式家庭中,夫妻只是重要的家庭关系之一,却不能涵盖所有家庭关系。如果说,父母和子女处于家庭结构的纵轴线上,夫妻处于横轴线上,从而构成了一个十字形的家庭结构,那么,《婚姻法》是试图仅以横轴线去取代整个结构。结果,因过分关注夫妻关系,而忽略了家庭其他关系,造成了法律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为了弥补这种差距,婚姻法解释(三)只能在《婚姻法》的框架下细化规则,结果却是继续放大我国家庭法中的结构性失误。正是因为《婚姻法》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式家庭的现实,才出现了司法解释中将父母对小夫妻家庭的资助视为赠与的条款。我对这些条款极不以为然。何以在美国没有听说过父母帮小夫妻买房的事情?如果小夫妻与父母视同陌路,父母凭什么要无偿资助他们?事实上,中国父母这么做,不过是把小夫妻视为家庭的一部分。父母是按照传统伦理在履行家庭义务,但法律却不予承认,非要把这种家庭内部行为定性为社会一般人之间的赠与关系。正是从扭曲或歪曲了正常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观念的意义上说,这种法律是不合理的。
第二,按照《婚姻法》的思路,不但旧式家庭被取消了,连家的名分都被取消了。事实上,连《婚姻法》承认的夫妻式家庭,也没有给予它一个整体的名分,更勿论去承认在家的名义下的财产。在夫妻财产制的框架下,家庭中只有两种财产,一是个人财产,二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这两种财产又同属一类性质,即个人财产制。夫妻共同财产是以夫妻个人财产为基础构造的财产集合形式,在这种财产形式中,能够看到的只有夫和妻的个体身份,没有家的身影。夫妻共同财产,从功能上说,最多发挥了一种松散的家庭纽带作用。有理由问,除了作为个体身份的夫和妻,整体性的家在哪里?法律是否应该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创造财富?如果是的话,那么,法律应该赋予这种共同财富的名分何在?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家庭是以男方为主,其不合理在于,男方是家的中心,妻子只能以“她者”身份融入家里,这是典型的男女不平等的家。但它的合理处在于,家是稳固的,即使有成员退出或死亡,家仍然存在,家产也不能随意分散,因此,家和家产可以继续发挥赡养老人和抚育儿女的功能。而在《婚姻法》中看到的只有两个独立的个人,家不见了。同时,《婚姻法》从未考虑设置以家为主体的财产制度。正是因为没有家产这种蓄水池,父母的资助没有了归宿,只好在归个人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这两个答案中作选择。其实,按照中国的家庭传统,父母有帮助小夫妻“成家立业”的义务,但由于整体性的家在法律中缺位,父母完成义务的行为,居然变成了破坏夫妻亲密关系的缘由。面对这样的结果,让中国父母情何以堪?!而法律与社会道德如此扞格,也难让人承认其合理。
第三,《婚姻法》的立法原则是夫妻平等,但平等不意味着夫妻间不能相敬如宾。夫权是近代以来家庭革命的对象,夫权消灭后,法律主张建立平等的夫妻关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夫妻平等并不必然导致夫妻亲密,这就像在古代中国,夫妻不平等并不必然导致夫妻不亲密一样。平等只是解决了夫妻的地位问题,夫妻关系仍然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谦让,共同持家,并在持家的合作中保持亲密关系;一种是因平等而斤斤计较,随时要求算清楚家庭账,并在这种算账过程中疏离或对立。我国法律显然希望鼓励和支持前一种夫妻关系。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家的设置,夫妻失去了共同用力的方向。在“家”完全缺位的制度框架下,夫妻个人财产和随时可因离婚而消灭的夫妻共同财产,几乎成了夫妻之间的离心力。人们惊呼,当代夫妻关系已经出现了向对立关系加速滑动的迹象。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婚姻法解释(三)》一旦出台,的确可能成为疏离夫妻的新助力。
综上所述,对《婚姻法》和《婚姻法解释(三)》的反思,必须放在三个大背景下,第一,需要放在近代以来家庭革命的大背景下;第二,需要放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观念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延续性的大背景下;第三,需要放在家庭文化的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大背景下。
今天,孤立的《婚姻法》取代一切家庭关系法所带来的框架性陷阱,不但把最高法院置于两难困境中,而且已使亿万家庭生活陷入尴尬境地。要使法律涉及的当事者摆脱这种困境,除了创制适合中国社会的新型家庭法,已经别无出路。新型家庭法应该注意借鉴其他国家的亲属法或家庭法的内容,并充分考虑本国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庭伦理,以使家庭法尽量与中国的家庭道德相契合。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承认整体性的家,确立“家”在民法中的地位,并让家能够成为财产的主体。
实际上,确立家制和家产制,在世界民法典中不乏先例。如《瑞士民法典》第87条,确立了家庭和教会的民事主体地位。在它的亲属编中,除了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外,特别用第九章规定“家庭的共同生活”,内容包括抚养义务、家长权和家产。《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名为“人与家庭”,确立了家庭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该编中并有专节规定家庭财产。法律确立家的合法地位,可以给家庭一个名分,强化成员的归属感。而设置家产,则具有蓄水池的功能,它既对内吸纳家庭成员的个人财富,以完成家庭日常所需承担的养老、抚幼等任务,又对外承担债务,为家庭的健康发展提供持续保障。在家产明晰的情况下,个人财产仍可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形式。不会因为家和家产的存在,湮没了个人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这就像在中国古代家产制中,允许嫁妆作为妻子个人的“私财”,而妻子常常用“私财”来帮助家庭走出困境,以获得美誉。
国家有细心呵护家庭的责任,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在这次《婚姻法》司法解释征求公众意见的事件中,已经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呵护的愿望已成泡影。现在,到了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在中国民法体系中确立新型的家制和家产制,不但是为最高人民法院解套,而且是全社会的现实需求。当然,具体到中国将来的家制和家产制该如何小心规划,尚有许多具体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
标签:婚姻法论文; 法律论文; 家庭关系论文; 婚姻论文; 婚姻法解释三论文; 父母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家庭成员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