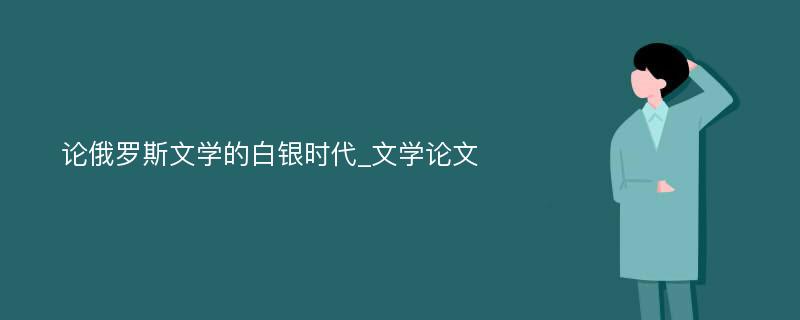
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一般较为熟悉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却不是十分了解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文学时代——白银时代。
这一文学时代始于上世纪90年代。1890年,诗人和哲学家尼·马·明斯基的《在良心的光照下》一书问世;1892年,年轻的高尔基哼唱着忧郁的生活之歌进入文学之林;同年,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诗集《象征》发表,1893年他又推出《论现代俄罗斯文学衰落的原因与若干新流派》一书;1894—1895年,另一诗人勃留索夫编辑出版了三卷本诗集《俄国象征主义者》;布宁与安德列耶夫则分别于1893和1898年开始散文创作,与高尔基一起打开了现实主义的新天地……联翩出现在文坛上的这些现象,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白银时代的到来。
最先提出“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尼·亚·别尔嘉耶夫[①]。他同时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的文化高涨,特别是哲学与诗歌的繁荣,表明这一时代是俄罗斯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时代”[②]。如果说,14至16世纪以意大利为发源地、席卷几乎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风,没有能够吹进沉睡的俄罗斯,那么,时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俄罗斯民族终于迎来了一个精神觉醒、思想活跃、文化振兴的时代。在民粹派运动失败、晚期封建制的危机加深、探索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热情高涨的历史条件下,知识界开始大量引入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潮,以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为代表的新的文艺思潮,同时重新解读与发现本民族的古典作家,用新的眼光审视民族历史与文化,在人文科学和艺术各领域内展开了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于是,在俄罗斯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密集型的文化高涨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别尔嘉耶夫后来写道:
“现在人们难以想象那时的气氛。从那个时代的创造高潮中产生的许多东西,已进入俄罗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并且至今还是整个俄罗斯文明社会的财富。但在当时,存在的只是对创作热情的陶醉、革新、紧张努力、斗争和呼唤。许多馈赠都是在这些年月里被送至俄罗斯来的。这是独立的哲学思想在俄罗斯觉醒的时代,诗歌繁荣,审美感受敏锐化,宗教信仰上的不安与探寻、对神秘事物和彼岸世界的兴趣加剧。新的精神出现了,创作生活的新源泉被发现了,人们看见了新的曙光,把日暮感、毁灭感和改造生活的希望结合起来。可是这一切都是在相当闭锁的圈子里发生的……。”[③]
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时代——白银时代也是一个名家叠出的时代。特别是在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当时涌现出一批造诣颇深、成果卓著的人物。其中如哲学家、诗人弗·谢·索洛维约夫,思想家尼·费·费多罗夫和普列汉诺夫,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伊·亚·伊利因和列·伊·舍斯托夫,作家、宗教哲学家瓦·瓦·罗赞诺夫,哲学家、神学家和经济学家谢·尼·布尔加科夫,法学家、宗教哲学家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人,都是著述极丰、见解深刻,其影响往往超越了他们所活动的学科范围。在绘画艺术领域中涌现的弗鲁别里、别努阿、涅斯捷洛夫、谢洛夫、库斯托季耶夫等人,在音乐方面脱颖而出的斯克里亚宾、利姆斯基—柯尔萨科夫、拉赫曼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在舞台艺术方面出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夏里亚平、梅耶荷尔德、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柯、等人,都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创造才能,以一系列堪称精美的艺术作品丰富了俄罗斯艺术宝库。
文学界更是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的局面。以高尔基、布宁、安德列耶夫为代表的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但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分别以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和别雷、勃洛克、维·伊凡诺夫为代表的两代象征主义者,以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为代表的阿克梅派诗人,以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未来主义者,以阿尔志跋绥夫为代表的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先后崛起,形成了俄罗斯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多种流派并存发展的新格局。同时活跃于文坛的还有列采佐夫、霍达谢维奇、扎伊采夫、苔菲、茨维塔耶娃等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的作家与诗人;以克留耶夫、克雷契科夫,叶赛宁为代表的“乡村诗人”既接近象征派、又接近阿克梅派,但不是任何一种派别的坚定分子的诗人米·库兹明、马·沃洛申等。即便是某一流派的坚定分子,在创作实践中也多是兼采众家之长。如布宁、库普林的现实主义中又有自然主义因素,安德列耶夫则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结合起来。象征主义的一些重要代表是现实主义组织“星期三”集会的经常参加者。维·伊凡诺夫曾使用过“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这一概念。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中时有浪漫主义激情的爆发(如巴尔蒙特)。阿克梅主义是从象征主义脱胎而来的,有的阿克梅派诗人也曾以未来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于诗坛(如格·伊凡诺夫)。多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并存、交叉、融合的现象,是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点。
这一时期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人,力图用历史辩证法考察、阐释文艺问题,他们本身就是文艺理论家或批评家。费多罗夫、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罗赞诺夫等思想家所主张的“在爱与善的基础上对世界进行精神改造”的思想,广泛地影响了文学界,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作家和诗人们的探索方向。几乎所有这些学者都写过专著或专文论及文艺和文化发展问题。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同时又是颇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歌是丘特切夫、费特等19世纪诗人和勃洛克等20世纪诗人之间的桥梁,也是整个白银时代诗歌的前阶。他的诗作与他的在“真、善、美统一”的基础上达至个性完善和世界和谐的思想一起,给俄国象征主义运动以重大影响。“年轻一代”象征派把他视为精神偶像。费多罗夫的“积极的基督教”思想和“共同事业”理论,则深深吸引了未来派诗人们。文学也以其特有的活力和悟性反转过来影响哲学及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创造活动。
白银时代的文学与其他艺术领域的探索常常是相互呼应、彼此配合的。如本世纪初俄罗斯绘画艺术呈现出来表现民族心灵面貌的特点,这同勃洛克、别雷等诗人力求通过诗歌创作认识俄罗斯人神秘的内心面貌,同高尔基、布宁、列米佐夫等作家对民族灵魂的高度关注,在追求方向上是彼此接近的。画家弗鲁别里不仅是象征派诗人们的偶像,而且在深入表现人的心灵痛苦方面同安德列耶夫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努力形成呼应。“艺术世界”团体中的别努阿等人的绘画,给“年轻一代”象征派诗人和阿克梅派以明显影响。画家大卫·布尔柳克信奉的“立体主义”,直接成为“立体未来主义”诗人们的纲领和原则。在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作品中,往往可听到一种无边的惆怅和对美的期待的紧密融合,可以感受到一种悲剧般的力量,这同布宁的散文给读者的感觉十分相象。音乐家斯克里亚宾相信杰出的音乐作品具有重铸人的灵魂的作用,它所激起的博爱精神将使人类走向和谐。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象征派理论家维·伊凡诺夫的著述中。著名画家列维坦、歌唱家夏里亚宾等是“星期三”文学小组集会的经常参加者。梅耶霍尔德执导索洛古勃、安德列耶夫、列米佐等人的剧作,在推广作家们的创作成果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导演风格。这类文学与艺术“联姻”现象是白银时代文化生活的特征之一。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还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团体,每一文学组织都拥有自己的期刊或不定期丛刊,有的还有自己的出版社。1902年成立于莫斯科的“文学小组”,1909年出现于彼得堡的“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及其前身“诗歌研究会”,阿克梅派的“诗人行会”,未来派的“希利亚群落”、“诗歌顶层楼”和“离心机”,写实派的“星期三”小组,都是较有影响的文学组织。象征派先后出版过《天秤》、《金羊毛》、《新路》等刊物和丛刊《北方的花朵》,其中以勃留索夫主持的《天秤》影响最大。该派有自己的出版社“天蝎”。《阿波罗》一刊是两代象征主义者分裂的产物,后来又成为阿克梅派的重要阵地。阿克梅还有专刊《北方》,出版丛刊《行会》。自我未来主义者曾拥有报纸《彼得堡发言人》。写实派有高尔基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和知识丛刊,安德列耶夫参编的《野蔷薇》,布宁、魏列萨耶夫参编的《言论》。各文学组织常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会、沙龙和讲座。安年斯基在彼得堡历史—文学高级讲习班主讲的文学讲座,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维·伊凡诺夫在彼得堡的住宅,是那个时代文化人士聚集的中心,被称为文艺界的“塔楼”。从这个时期的文学团体生活中可以读出白银时代文化进程的完整上下文。
俄罗斯的“文艺复兴”与西方文化和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17世纪欧洲的马里诺、卡尔德隆等“巴罗克”诗人,18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前驱布莱克,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诗人席勒和诺瓦利斯,19世纪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和戈蒂耶,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爱伦·坡和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19、20世纪之交的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和作家梅特林克,都被白银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们视为有艺术革新精神的人物。但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每一流派都没有把自己看成某一西方文学流派的翻版,而是广泛地吸收了多种流派的艺术经验。当时的一些诗人是把那个时代以新诗运动为主体的整个文学运动作为“浪漫主义时代”来看待的。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被同时代人称为“唯美派”的首领。阿克梅派诗人又被人们称为“新浪漫派”。作家扎伊采夫认为印象主义曾是影响20世纪俄罗斯文坛的西方文艺潮流之一。安年斯基曾大力提倡古希腊文明、地中海文明,并主张以此来改造俄罗斯文化和文学。这些现象表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对西方文学是采取了全面开放、广泛接纳的态度。
然而,白银时代的诗人、作家们更为着重的却是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土壤。文学界普遍表现出一种“斯拉夫主义”兴趣(大概只有某些未来主义者是个例外),或热衷于发现本民族的艺术遗产,或显示出对于民族文化之根的探索热情。一些作家与诗人倾心于重新解读、重新发现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如安年斯基重新解读果戈理,维·伊凡诺夫重新阐述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霍达谢维奇深入研究了普希金和巴拉廷斯基,巴尔蒙特重新发现了费特,勃留索夫揭示了丘特切夫诗歌中未为人所道的一面,勃洛克则挖掘了阿·格里戈耶夫作品中涵纳的富藏,而整个象征派可以说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作出了新的解释。作家和诗人们大都愿意把自己的艺术探索看成传统文学的当然继续,强调自己的根子扎在由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所奠基的深厚土壤中。巴尔蒙特认为,在19世纪俄罗斯诗歌中,特别是在丘特切夫和费特的诗作中,已经包含了象征主义艺术的胚胎。现实主义作家魏列萨耶夫也重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与象征派的视角完全不同。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讲稿,对经典作家一一作出评价,不仅有许多新见解,更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取文学史的角度。
白银时代的作家还表现出对斯拉夫神话和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极大兴致。古代神话和口头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在他们笔下复活了,且获得了新的意义。巴尔蒙特的诗集《热鸟》和《绿色的葡萄园》,戈罗捷茨基的诗集《春播》和《雷神》,列夫佐夫、别雷、纳尔布特及赫列勃尼科夫、曼德尔什塔姆、亚·康德拉季耶夫的一些作品,均把目光转向民族古代文化遗产,使神话和民间创作的题材与情节经由新的艺术构思得到了特殊形式的再现。
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目标决不是要“复兴”古代文化一样,白银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也决不是一批复古主义者。对民族文化和文学遗产的重新发现与评估,是以西方进步文化和文学为参照的。深藏在俄罗斯古代文化和文学中的那些具有恒久价值和现代意义的东西被照亮了。新的观念、对民族性格的新认识,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独特性的新见解,新的文化建设构想,已闪现在对古代文化文学遗产的再度发掘中。
白银时代是一个文化全面高涨的时代。当时的作家和诗人大都具有宽阔的知识面和学者的品格。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由俄罗斯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如弗·谢·索洛维约夫、巴尔蒙特、维·伊凡诺夫、安德列耶夫、勃留索夫、列米佐夫、别雷、沃洛申、谢·米·索洛维约夫、霍达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等均由莫斯科大学毕业。安年斯基、明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魏列萨耶夫、亚·米·杜勃罗留波夫、勃洛克、戈罗捷茨基、赫列勃尼科夫、曼德尔什塔姆等则都是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索洛古勃、阿赫玛托娃、库兹明、瓦·卡缅斯基、阿·托尔斯泰、尼·阿谢耶夫等,也都曾就读于其他高校。古米廖夫、茨维塔耶娃、维·伊凡诺夫、沃洛申、曼德尔什塔姆、萨沙·乔尔内依、辛凯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等,还曾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或海德堡大学等国外高校学习。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多才多艺,通晓好几种语言,漫游过俄罗斯大地、欧洲甚至非洲、美洲、亚洲、澳洲。安年斯基、维·伊凡诺夫等人具有更开阔的文化眼光。大多数作家和诗人都同时又是翻译家,勃留索夫的译作几乎覆盖了整个欧洲文学发展史。沃洛申、布尔柳克、叶·古洛、卡缅斯基等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库兹明则兼诗人、散文家、戏剧家、批评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勃洛克、别雷、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古米廖夫、谢维里亚宁等人,有着哲学、宗教学说或文化史方面的丰富知识。作家和诗人们的这些特点,使白银时代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渗透着哲学精神、宗教观念和文化意识。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生活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是以济·吉皮乌斯、叶·古洛、阿赫玛托娃、苔菲、茨维塔耶娃、玛·莎吉娘为代表的一批女诗人、女作家的崛起。她们开始在文学这一领域显示俄罗斯女性的才华、魅力和光彩。俄罗斯文学是“男性文学”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了。
同19世纪中后期的文学相比,白银时代文学最杰出的成就是在诗歌方面。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勃留索夫、勃洛克、别雷、古米廖夫、赫列勃尼科夫、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等都是极有影响的诗人。小说成就也并不逊色。高尔基、布宁、安德列耶夫、别雷、什梅廖夫、索洛古勃、库普林等,以各具特色的艺术创造推动了俄罗斯小说艺术的发展。安年斯基、勃留索夫、维·伊凡诺夫、别雷则在理论批评方面颇多建树。散文、政论、戏剧等,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白银时代出现的作家和诗人。并不一定都在这个时代达到了自己创作的高峰期。到1917年,“白银时代”作为一个文学时代已然终结。对于相当一部分作家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个人的创作鼎盛期的过去。而另一些在白银时代只是崭露头角、或刚刚步入文坛的作家和诗人则是在以后的不同时代进入各自创作生涯的辉煌期的。这既包括十月革命后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叶赛宁、曼德尔什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包括侨居国外的列米佐夫、什梅廖夫、苔菲、霍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扎伊采夫。但是,1917年以后所有这些作家的文学活动、白银的时代各种文学流派与团体的演变,都并不意味着白银时代还在延伸,而只是这一时代文学运动的“惯性”或余波。然而白银时代的文学成就与文学精神,特别是这个时代所培育的高尔基、布宁、别雷、帕斯捷尔纳克等伟大作家,却给后来的文学以有力的影响。
注释:
① 参见谢·巴文、伊·谢米勃拉托娃:《白银时代诗人们的命运》,中央书局出版社,莫斯科,1993年版,第3页。
② 尼·亚·别尔嘉耶夫:《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俄罗斯思想》,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第254页。
③ 尼·亚·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转引自《白银时代诗人们的命运》一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