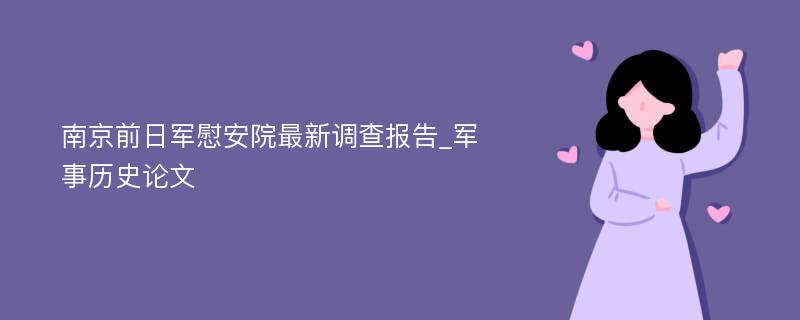
对南京原日军慰安所的最新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日军论文,调查报告论文,慰安所论文,最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3-0138-18
“慰安妇”是日语中特有的名词,有着强烈而独特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所谓“慰安妇”,乃是日本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中,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地强征大批的各国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女性。所谓“慰安妇”制度,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一项重要国策,是一种野蛮罪恶的制度与行径。南京,由于它是日军制造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地方,是日本侵华8年期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军政机关、驻防日军与日本侨民众多,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也是中国妇女、韩国妇女、日本妇女以及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最典型的地方。近几年,笔者根据中、日、韩文档案、报刊资料,与中、日一些学者一道,多次进行社会调查,查访了许多熟悉有关史事的知情人“老南京”,查证了多家慰安所的原址房屋,查获了慰安所的门牌、告示、用物及有关文件档案等多种物证,还找到了曾在南京做过慰安妇的20多位中国妇女与2位韩国妇女本人或其家属,获得了她们的口述回忆资料,确认在日军统治的8年(1937年12月13日到1945年9月9日)期间,除占领初期临时设立的慰安所难以统计外,日军在南京较长期设立的慰安所有40多家。
一、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所进行的血腥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大奸杀。在短短的时间内,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至8万人次。这不仅暴露了日军的凶残无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而且由于大规模的奸淫活动,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辖各部队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日军上层很是震惊:在南路兵团——第十军的第6、第18、第114师团及国琦支队,北路兵团——“上海派遣军”的第 3、第9、第11、第13师团及重藤支队里,均发现各种性病如瘟疫一样迅速扩展。如此严重的情况,使松井石根等人不仅担心国际舆论的谴责,更为忧虑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严重削弱,担心重演20年前日军出征西伯利亚时期性病蔓延的悲剧,决定迅速实施慰安妇制度。
在1918年至1920年,日本曾派兵7.2万人入侵苏俄西伯利亚。由于日军对当地妇女疯狂的奸淫,致使1.2万余官兵染上性病,约占日军总人数的1/5。性病大大超过了作战损耗的战斗力。于是日军总部开始征募随军军妓,以解决官兵性欲与防止性病侵袭部队。[1]32“军妓”制度在日军中开始出现,但当时尚未有“慰安妇”的称呼。“慰安妇”一词最早出现于1932年日军制造上海“1·28事变”期间。当时担任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为鼓舞日军士气与防止日军士兵强奸事件发生,在日本当局的支持下,与日本关西地区长崎县官府合作,征召日本妇女,组织“慰安妇团”来上海,为参战的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2]302于是,“慰安妇”作为特定的名词与特定的制度出现了。“慰安妇”是由日本军队上层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与组织并形成的一个特定的妇女团体。
其实,在日军攻占南京前,松井石根便已根据日军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命令“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少将准备在日军占领区实施慰安妇制度。这是因为自1937年8月松井石根率日军向上海进攻,在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接着,兵分两路向南京进击,已历时近四个月。在这期间,日军各部官兵已开始对各地的中国妇女大肆奸淫。1937年12月11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向正在疯狂进攻南京的各部下达《方面军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当日,正在南京前线的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在日记中记载:“关于慰安设施一事,方面军来文件指示,予以实施。”[3]202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当局在纵容日军大肆烧杀淫掠的同时,着手在南京筹建慰安所:一方面致电日本国内,要求尽快征集日本慰安妇运往南京;另一方面拨出巨款邀请上海的日侨“方便屋”老板出面,到南京举办“民间慰安所”;[4]48同时密令所辖各部先自行设立各种形式的临时“慰安所”。12月19日,驻防南京的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特派军参谋部第二课的课长长勇中佐前往上海,为在南京设立慰安所进行联系。长勇在上海与一些日侨方便屋老板以及上海黑社会首领黄金荣等进行了联系与布置后,于12月25日回到南京,向饭沼守复命。对以上事项,饭沼守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已委托长中佐尽快设立妓院(慰安所)。”12月 25日的日记中又记载:“长中佐从上海返回……关于妓女(慰安妇)的事也要事先做好准备,日本国内的和支那的都要,一旦定下,年底即可办理开业手续。”[3]211,218在进行了数天的筹划后,“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提出了《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并于1937年12月28日召集“上海派遣军”所辖各部队的将校开会,对该方案进行审议。“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1937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日军)军队的不良行为好像日益增多,让第二课召集各部队的将佐举行会议,就此事进行汇报……审议了第二课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5]251第二课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迅速得到通过。
1938年年初,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对所辖各师团性病流行的调查报告也引起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震惊与高度关注。1938年3月4日,日本陆军省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1938年2月18日由“华中方面军”改编而成)发出通牒,要求在中国各个占领区设置由军方直接管理的慰安所,以缓解日军越来越严重的强奸问题。[6]463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在一份命令中明确指出:“为能有效地降低日军驻海外士兵的强奸发生率,以减少被占领国人民因此而采取的对日军巡逻队的报复行为,各部队应迅速建立一个能使日军兵士在作战空隙时,在性方面可得以充分满足的机构。”[7]55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主持与支持下,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与日军其他占领地区建立与实施。
二、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主要途径
在日本统治南京近八年的时间中,日方当局建立慰安所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日军各部队奉命自行设立
日方当局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一条途径,是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韩国籍慰安妇一时不能立即大量地运抵南京,日军方遂采取应急措施,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
于是,各部日军就用公开劫掠、强迫征召或用谎言欺骗等种种方法,获得大批中国妇女,然后随意选择一些场所,建起各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
日军从进入南京开始,就大肆劫掠中国妇女。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伸手到裤裆触摸一下。[8]
例如日军第6师团。这支最早从雨花台、中华门、水西门一线攻入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以凶残屠杀而闻名。这支部队从1937年12月13日攻入南京,到12月21日奉命撤出南京前往芜湖、杭州,在南京仅驻防9天,大肆奸淫中国妇女,同时劫掠大批中国妇女建立慰安所。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时,就对谷寿夫指挥所部在对南京军民大屠杀期间,公开劫掠南京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揭露、控诉与认定:
“查该被告纵容属下……于行军途中及在南京雨花台等处,向陈王氏等强索姑娘作肉体之慰劳……虽该被告仍一再辩称……设立慰安所系向当地长官商量,并征求慰安妇女之同意,始行设立云云……我国妇女及社会风尚,向无以肉体作慰劳之习惯,即本国行军,亦不能使其同意牺牲色相,况为敌军。且就其在南京强索妇女不遂杀人观之,尤足证所谓征其同意为虚饰……该被告来华作战……肆意抢劫及破坏财产,对于平民作有计划之屠杀与强奸,强迫妇女入慰安所,以及强奸之后加以杀害……暴行,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8]807-810
日军还公然派人到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中国妇女作慰安妇。
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某师团派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公然向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要求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日军的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9]209
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33联队第2大队的士兵井上益男(1915年6月生,1937年22岁)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奉命“警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他目睹了多起日军官兵到该校难民所强行带走中国妇女的场面。晚年他向采访者松冈环女士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
“南京陷落后,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按: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警备。警备有10个人,实行一周交接制。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女人的避难所。那里经常有日本的军官过来说‘进去一会儿’,就进校舍带走女孩子了。军官们也是不像话的,他们是把女孩子带走强奸的。军官都是中队长以下的小队长级别的军人。我们虽是警备,但看到军官们带走女孩子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上司嘛。经常出入校园的不仅是33联队的,还有9师团和16师团的30旅团的。他们是开着卡车来的。白天不怎么来。一天大概来两三辆。每次来的包括军官有四五人,其中三人拿着枪。也有的时候一天来五六辆。一辆大概装20个女孩子。也有不愿意而哭鼻子的女孩子,但只要被拉到卡车的载物台,从上面盖上苫布,她们就老实了。被送回来的姑娘是很少的……当时还有宪兵,但他们也无法阻止军官们抢女人。”[10]326
其他的难民所也都发生了日军强行征召慰安妇的事件。日军“每日至女收容所内用卡车将大批妇女载去,哭号震天,惨不忍闻。有时深夜将一部分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8]151
日军还通过“难民登记”挑选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J.H.D.Rabe)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10天内完成。难民共有20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出去做苦工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11]279
日军还常常用诡言诱骗来许多中国妇女,声称让她们为日军做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女招待等工作,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中去做慰安妇。1937年12月30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从南京市中心的锏银巷带走,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军医院。日军诡称让她们为日军官兵洗衣服。但到晚上,她们就被胁迫进慰安所,遭日军官兵的轮奸。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晚被轮奸10次到20次,较年轻、美貌的多被轮奸40次之多。[8]218这些被日军骗去的中国妇女从此就失去了自由,绝大部分再也没有走出日军的兵营。
日军建立的这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一时遍布南京城内外各地。由于这类慰安所多存在于日军刚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期,为时不长,且多建在日军的军营里,为临时性质,因而留下的史料与遗迹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当事人的记述与回忆中,看到其中的一些情况。
日军第114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人玩弄。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等着轮到自己。”[12]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4月30日曾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城外东郊原著名的贵族学校的校园里所设立的一家慰安所。那天她与同伴为了“调查可以安置孤儿的场所”,来到了贵族学校校园。她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鼓起勇气,决定设法去城外那些收养烈士遗孤的学校,学校内新的女生宿舍被彻底摧毁了,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那里似乎被日本士兵和大量的中国妓女占据着。”[9]363
这种由日军各部队自行开设的临时性质的慰安所,数目众多,但为时不长,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与日军调防后,数目有所减少,逐步为其他形式的慰安所代替。
2.由中国的地痞流氓与伪政权设立慰安所
日方当局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南京本地的一些汉奸地痞流氓,“招募”、胁迫、诱骗中国妇女,设立慰安所,进行商业性的经营;在南京伪政权建立以后,就指令伪政权派遣专门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后不久,日军“南京特务班”的班长大西等人,就指令汉奸孙叔荣、王承典等人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王承典原是“南京保泰街的拍卖人,与南京的下流社会过从甚密”。[13]304日军侵占南京时,他先受聘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但很快就与日军搭上关系,成为日方的代理人。他认识南京一位对举办妓院很内行的黑社会人士乔鸿年,就向大西推荐,由乔鸿年承办慰安所与招募中国妇女。王承典的建议得到大西的首肯。
乔鸿年,又名乔月琴,是战前南京著名的流氓地痞与戏霸,黄金荣式的社会闻人与青帮首领,曾在南京开办过金陵大戏院、民生公司大剧场、南京大戏院和下关大戏院,经营所谓娱乐事业,与黑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密切的关系(此人后来在南京沦陷8年期间,任南京伪帮会组织“安清同盟会”的副会长与伪“首都模范戏剧研究会”理事长等职)。他得到王承典的推荐后,立即积极地为日军奔走效劳。他陪同日军特务班头目,先后来到“安全区”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乔鸿年把搜寻重点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因为这家难民所主要收容年轻妇女,人数达1万多人。乔对她们摇唇鼓舌,以日军保障安全、付给一定报酬和日军官兵不得携带武器等条件为诱饵;又以牺牲小我、促使日军停止杀掠与奸淫、保护众多中国姐妹等语句来诓骗;还用如不从命必遭杀身之祸来威胁。但中国妇女仍不从命。于是乔鸿年协同日军,从12月18日到20日,从这里强征了300多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由王承典、孙叔荣交大西过目同意。乔乃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公馆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又带着日军宪兵从一些国民政府大员公馆内拉来上好家具装饰。12月22日,由汉奸创设的这第一家慰安所便正式挂牌开张了。这家慰安所由日军部正式委派大西为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设售票员3人(其中2人为日本人),记账员4人,还有女佣、杂役等,连同慰安妇共200多人;经费开始由日军部供给,后以卖票所得支付,还有盈余,都归大西所有。傅厚岗慰安所设在公馆的一、二、三楼,慰安妇多选年轻美貌者,约30多人,专为日军将校服务,规定每天下午1时到5时接客,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3元,可以过夜,通夜10元;铁管巷慰安所的慰安妇为普通日军士兵与下级军官服务,规定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2元,但不准过夜。该慰安所于1938年2月初日军大批营妓到达南京后结束。[14]
在汉奸创办了第一家慰安所以后,日军当局又要求继续开办更多的慰安所。1937年12月22日,日军特务机关在召集南京红卐字会会长陶锡三及孙叔荣、王承典、王春生等人讨论建立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时,就向他们提出“为日军建立三家妓院”的要求。1937年12月23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要事项,就是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为日军建立慰安所。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L.S.C.Smythe)当时就听说:“‘自治政府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在日本人12月22日招集之时,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而且许多人为此事感到高兴。”[13]342史迈士所说为日军建立慰安所“感到高兴”的人,是指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会长陶锡三、副会长孙叔荣、顾问王承典等人。史迈士记述了西方人士得知日方当局的这一措施时都十分吃惊与气愤。他在193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红卐字会正着手和日本人一起建慰安所,以满足日本士兵和军官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上周六(按:指1937年12月18日)贝德士就暗示过此事,当时林查理吃惊不浅。许先生(按:指许传音)说他们准备建两个分部:一个在鼓楼火车站以北供普通士兵使用,一个在新街口以南供军官使用,全是营业性的。”[13]304史迈士还记载了王承典派乔鸿年陪同日军到安全区几家难民所搜寻挑选难民妇女的情况:“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按:指王承典的代表乔鸿年)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校园,从那儿的10000名难民中,眨眼工夫就叫出28个妓女!”史迈士斥责这些汉奸是中国“黑社会的三教九流”。他写道:“所以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进行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 (按:指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拉贝)、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卐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13]342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对日方当局公然开设慰安所也感到吃惊与愤慨。他在1937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日本人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11]285
1938年年初,王承典、孙叔荣与乔鸿年等人又在南京一些地方开办了多家慰安所,如在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四达里)设“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上军北部慰安所”。乔鸿年自任这两家慰安所的总主任,另一个汉奸唐力霖任副主任。[15]据1999年调查,曾住西铁管巷19号的王大妈说:“我家对面就是瑞福里(四达里),亲见日军进去时买票,把枪放下来,脱掉外面衣服进慰安所里面去,里面住着中国的女人。”[16]
1938年4月12日,已经开办与主持多家慰安所、富有经验的乔鸿年奉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以“上军慰安所主任”的身份,向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孙叔荣、工商课课长王承典呈文,申请在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再开办一家新的慰安所——“人民慰安所”。
乔鸿年的呈文如下:
呈为分设人民慰安所,仰祈鉴核,准予备案事
窃所顷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为繁荣夫子庙市面,振兴该区商业,调剂全市人民生活计,指定在夫子庙,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址,及市府路永安汽车行原址,暨永安里全部房屋,分设“人民慰安所”二处,业已修理,一俟工竣,即行开幕,除已分别呈报各主管机关外,理应备文呈报,仰乞鉴核,准予备案,并加保护,是为德便。
谨呈。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孙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工商课课长王
上军慰安所主任乔鸿年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17]
王承典是最早为日军经办慰安所的老手,所以立即批示: “照准,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仅过了一夜,第二天,即1938年4月13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专为此事发出第239号训令。[18]
此后,所谓“人民慰安所”就正式挂牌营业。据2000年初的调查,现居住在贡院街15号204室的李甫老人(90岁)证实说:“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是韩姓老板开设,韩老板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即逃走。旅馆由汉奸乔鸿年在海洞春旅馆原址开设人民慰安所,里面的妓女都是中国人。”海洞春旅馆原址在战后被拆除,现在原址上盖了住宅楼。
在日军部的指示与支持下,其他一些流氓汉奸步乔鸿年后尘,也纷纷开设各种名目的“慰安所”。今天有案可查的就有“日华亲善馆”、“皇军慰安所”(位于傅厚岗)、“大华楼慰安所”(亦有称“大观楼慰安所”,位于白下路219号)、“满月慰安所”、“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等。在南京城郊区龙潭,日军指示信裕商行老板范竹修设立了一家慰安所,其中被逼为娼的有100多位中国妇女。
但因日军占领南京初期,驻军众多,已设立的慰安所远远不能满足日军性欲的需要。据记载,许多日军士兵一清早就去各慰安所,而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前一个进去十来分钟,后面就又敲门又骂下流话。于是南京日军当局指使伪政府,将恢复开业的南京的一些妓院专门用来接待日军。据1939年10月1日《战地电讯》所载《南京魔窟实录》一文称:“(南京)尚有25家名目繁多的妓院‘桃花宫’、‘绮红阁’、‘蕊香院’、‘秦淮别墅’……也供日军奸淫。”[19]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的慰安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曾一度受到日军当局的欢迎,存在的时间也较长。但日军当局毕竟对之存在种种疑虑与顾忌。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实施所谓“对华新政策”后,日本当局不得不收敛起一些极易引起中国人民反感的霸道行为。于是,这类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的慰安所在南京逐步减少,或停办,或由日方接管,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继续经营。
3.日军部直接开办或委托日侨娼业主设立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三条途径,是由日本军部自行开办,主要为日军高、中级将佐服务;更多的则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在南京择地设立,为日军普通官兵服务。这类慰安所逐步成为南京最主要的慰安所,尤其是在日本统治南京的中、后期,当前两类慰安所在南京逐步减少与消失以后。
有史料表明,日军进占南京不久,有的部队就已携带一些日、韩籍的慰安妇。日军老兵冈本健三回忆说:“日本的慰安妇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也来到了。有的慰安妇心慌意乱,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人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20]94日军控制南京后,日本军部征召原在日本、上海以及“满洲国”的日本娼业主,携带日、韩籍的慰安妇,来到南京,选择靠近日军兵营的地方,强占一些设备条件较好的居民住房或政府公房,改作慰安所,挂牌营业,专门接待日军官兵。这类慰安所的慰安妇开始多是由日本军方征招来的日本籍、韩国籍的“营妓”,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被掳掠、胁迫、诱骗到这里来充当慰安妇。南京的中国居民依慰安妇的国籍分别称这些慰安所叫“日本窑子”、“高丽窑子”、“中国窑子”。这类慰安所由于得到日本当局的支持与庇护,享受种种侵略特权,有稳定的顾客来源与财源,因而生意兴隆,存在时间长,一直存在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以后,而且为数也很多,经我们查证的就达40多家。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一是城南部,从夫子庙到大行宫一带。
由于这一带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是日本当局划定的日本侨民聚集的“日人街”所在地,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多而集中。据当时在“日人街”中心科巷一家小饭店做学徒的高成明老人(1927年生)在2005年11月21日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南京科巷当学徒,做面行,卖面条馄饨……科巷那里全是窑子,那时叫慰安所,二条巷、四条巷、利济巷、文昌巷都有,有七、八家呢!全是楼房。有日本窑子,也有中国窑子。”[21]这一带的慰安所较大的有:
“安乐酒店慰安所”。位于繁华的太平南路,由日军军部主办,公开名称是“日军军官俱乐部”。日军中上级军官在这里吃喝玩乐外,一直专门有日本、朝鲜与中国的慰安妇应招前来陪伴跳舞与住宿。这实际上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别的慰安所。这在当时的南京几乎尽人皆知,直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国民政府军队进驻南京后,这家慰安所仍在公开营业。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第74军第51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官的邱维达将军就看到:“日军成立慰安所是公开的,当时南京就有好几处挂着牌子的慰安所,如坐落在太平南路的安乐酒店,就是日军的一个高级慰安所。”[22]135此处建筑现改为江苏饭店。
“松下富贵楼慰安所”。位于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这里原是一李姓人家在1931年到1932年修建的住房,有三幢,前、后两幢均为二层楼房,中间一幢是小瓦房,共约40多间,建筑面积共有 1200多平方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机不断轰炸南京,这李姓人家于1937年8月逃离南京。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宪兵队便将这些房屋占有,建立了一家慰安所。日军将房屋修理改建,将三幢房子全部用铁栅栏围起,在大门前竖起一块水泥牌,上书“松下富贵楼”五个大字,这是因为管理与经营这家慰安所的是个叫松下的日侨娼业主及其妻子。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妇女与中国妇女。40多间房间,除一间办公,其余都是慰安妇“接待营业”的场所。到这家慰安所寻欢作乐的也不是日军普通士兵,而是将、佐级军官。附近中国居民看到,经常有日军军官开车前来,有时楼门前停有日军军车十几辆。这时,松下夫妇就会赶到门口迎接。四周中国居民都知道,这家慰安所的慰安妇们每星期都要去检查身体。此处建筑部分遗址在2006年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慰安所遗留的日式浴缸、榻榻米及一些家具也保存至今。
“青南楼慰安所”。又名“菊水楼慰安所”。位于大行宫以南,太平南路文昌巷19号白菜园大院,有8幢规格一样的二层别墅洋房,以及另外几幢式样不一的二层、三层楼洋房,建筑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片洋房群落,四周围以围墙与铁丝网,大铁门两边的门柱上写着“菊水楼”三个字,里面的慰安妇多为菲律宾籍、韩国籍与中国籍。“菊水楼慰安所”是南京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慰安所。来这里“游乐”的都是日军将、佐级军官。曾住在科巷的潘纪文老人在2000年年初作证说:“东白菜园与西白菜园的洋房内有日军慰安所,有中国妇女包括台湾妇女,还有朝鲜妇女。”此处建筑遗址在2006年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东云慰安所”,又名“东方旅馆”。位于利济巷2号。利济巷北口是中山东路,隔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央饭店。利济巷2号原是一位有钱人扬普庆在战前不久建造的高级住宅区“普庆新邨”的一部分——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日军占据这里后,将其改造成一家慰安所,交给一个名叫千田的日侨娼业主经营。在这座洋楼的一楼、二楼的中间,各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房门对着房门,均为长方形,一楼有14间小房间,二楼有16间小房间;在每个房间的门上都钉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在每个房间里都建有一块凹进去的床位,放置榻榻米,另放几张桌椅板凳和一张衣柜。这是慰安妇们被迫接待日军的场所。在一楼进门处设一吧台。在二楼一个小房间的上面还有一间狭小的阁楼,是关押、吊打不听管教的慰安妇的地方。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有大铁门,在大铁门口设一售票处。当地南京居民称之为“高丽窑子”,因为他们看到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年轻的韩国妇女。日军官兵到这里时,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据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在 2003年1月(95岁)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她们全家在1938年春夏之交从逃难地六合老家返回这里居住,先摆香烟摊为生,后开了一个“德胜祥烟酒杂货店”,一直居住至今。当时她家四周住有许多日本人,有的住家,有的开店、开洋行,还有的开慰安所。她向他们学会了讲日语。“高丽窑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韩国慰安妇,因为这些女人都穿的是朝鲜服,所以知道她们是朝鲜人。她看到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穿军装、挎军刀的日军官兵来此,周末来的更多,老板千田都要到门口迎接。另一位沈玲老人(1927年出生)在2003年 1月(76岁)告诉我们:在日据时期她家住在利济巷6号楼上,就在“东云慰安所”的前面,当时她才十二三岁。她常透过窗子看到每天都有许多日本军人进入利济巷2号的楼房内,有朝鲜姑娘为日军脱衣等。在2003年11月,我们与日本学者西野瑠美子女士历经万难,找到了曾于1939年至1942年初在这家慰安所做过3年慰安妇的朝鲜妇女朴永心,并将这位已经80多岁的老人从平壤接到此地,指认当年她所居住的楼上第19号房间、一楼吧台、关押吊打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小阁楼以及这家日军慰安所的其他种种罪证。[23]“东云慰安所”旧址的房屋在2006年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故乡楼慰安所”。位于利济巷18号,紧邻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这里原与利济巷2号相通,是扬普庆在战前建造的“普庆新村”的主体部分,有相同式样的二层楼洋房8幢。日军占据这里,建成慰安所。里面都是日籍慰安妇,主要接待日军军官。当地中国居民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妇都穿着日本和服与木屐。穿着军装的日本人一般都是晚上来,周末时人更多。慰安所门口挂着“安乃家”的牌子,门口有日本人收票。中国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当时居住在利济巷、以卖米为生的张万宣在2000年年初(81岁)接受调查时说:“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日本军人,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的儿子张传铭在2003年1月(72岁)作证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当时我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利济巷16号是日本人开的池田洋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18号里面女人都穿和服。”[24]此处建筑遗址在2006年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吾妻楼慰安所”。位于科巷南寿星桥口,与“东云慰安所”隔街相望。是为日军普通士兵设立的、级别较低的慰安所。日侨娼业主经营,里面都是中国妓女。家住附近的沈玲老人在2003年1月陪同笔者前往实地调查,她指着“吾妻楼”慰安所旧址告诉笔者,当时这家慰安所大门上方,高悬大幅横幅,上书“扬州姑娘”四个大字,以做广告宣传。张传铭老人也指证说:“吾妻楼慰安所是在现在科巷菜场卖鸡的地方,现在房子都已拆除了。”[25]
大华楼慰安所(亦称“大观楼慰安所”)。位于白下路213号。此处建筑现已拆除,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太平洋保险公司”大楼。
“浪花楼慰安所”。位于中山东路四条巷树德里48号,开办人为日侨娼业主河村。此处建筑遗址在2006年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筑紫屋军食堂”。这是以“食堂”名义提供性服务的变相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心洪武路18号。开办人山本照子,日本福冈县人。此处建筑已拆除。
“朝日屋军食堂”。由原“筑紫屋军食堂”改名,位于洪武路18号,开办人为重冈又三郎。[26]此处建筑已拆除。
二是城北部下关一带。
因为这一带地区是南京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下关火车站与长江码头又被日军军管,因而这里驻防日军较多。与之相适应,日本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慰安所,有“华月楼慰安所”、“日华会馆慰安所”、“圣安里A所慰安所”(日本慰安妇)、“圣安里B所慰安所”(中国慰安妇)、“东升楼慰安所”、“铁路桥慰安所”、“煤炭巷慰安所”等。
“华月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商埠街惠安巷13号,为一幢3层木质结构的楼房,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左右,每一层约有6、7个房间,内有一个大院。该房原为一位黄姓富户所有,黄姓一家在战前逃离南京,遂被日军“征用”,1939年初被开办作慰安所。据当时居住在惠安巷16号开裁缝店、经常为慰安妇们缝补衣服的樊桂英老人在接受我们调查时说:“每天来华月楼慰安所的日本人很多,白天、晚上都有,全部是日本军人。在慰安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客厅,客厅里有人售票,四周墙上挂满慰安妇的照片。慰安妇不叫名字,都称呼多少号。记得是从1号到25号。也就是说,这里有20多个慰安妇,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以扬州人最多。这家慰安所的经营者是一对日本夫妇,会讲中国话。日本投降后他们没有立即回国,留在下关木行里做事,直到1949年后才被遣送回国。该所的慰安妇在日本投降时都跑了,只有一位叫17号的慰安妇嫁给一个广东商人,留住此地,抱养了一个女孩做养女。这位慰安妇在20世纪90年代去世。”该所的管理条文十分详细,规定慰安妇每5日必须接受宪兵分队兵站支部医官兵身体检查;慰安所每天对士兵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价格为1元,1次30分钟,每延长30分钟追加50钱;对军官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9时,价格为3元,1次1小时,每延长1小时追加2元;购票进入慰安所的官兵不得进入所认定购买号码以外的慰安室等。[27]此处建筑遗址在2006年4月本文截稿时还存在。
“铁路桥慰安所”。位于下关石梁柱大街85号,是一座约有30余间房间的平房。当年在这附近一家三明旅馆做接待工作的刘聚才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三明旅馆隔马路的斜对面,有一处约有30余间房间的平房,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条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 30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妇女大都穿着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但出去时都穿日本服装。据说这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大都是日本人和高丽人。这个慰安所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当严格。我当时才十七八岁,那些女的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讲话。她们当中有人会讲中国话。但那个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禁止她们同我们中国人讲话。这个慰安所中国人不能进去,只对日本军人开放,而且来的日本人似乎以军官为主,白天晚上均有军人进去。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没有看到她们出去检查。这个慰安所管理相当严格,卫生要求很高。这个慰安所门口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某某慰安所,具体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27]现铁路桥改名为惠民桥,“铁路桥慰安所”的平房已被拆除,原址上建成了一个农贸市场。
“鹤见慰安所”。隶属驻南京的日本海军部队。地址不详。
下关一带其他慰安所的资料不详。从日方在1942年8月15日修订重版第32版、1943年8月15日修订重版第33版,日本金风社出版的《支那在留帮人人名录》,可知下列情况:
“东幸升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大马路德安里14号。开办人久下喜八郎,日本兵库县人。
“煤炭港慰安所”。位于惠民桥升安里。
“大垣馆军慰安所”。位于下关大马路,创办人三轮新三郎。[26]
三是城中部地区。
因为这一带地区虽是南京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之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邻近鼓楼。据在2000年年初调查,黄泥岗44号老住户刘毅(82岁)证实说:“我家对面有个二层楼的慰安所,叫‘鼓楼饭店’,里面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大军官来时,有人站岗;小军官来时,没有人站岗,一般晚上来的日本军人多。”另一位老人陈有豪(74岁)证实说:“我是1938年约10月份回南京,就住在黄泥岗。我家对面是日本人开的窑子,叫‘鼓楼饭店’,外观是教堂式的,方方的二层楼,共有五进。妓女都是日本人,穿着和服。估计里面有20-30个日本女人。星期天,日本兵来的多,平时少些。这个窑子,日本投降后就撤了。”住黄泥岗36号的老人钱永和(82岁)说:“我是南京大屠杀平定后,在1938年来南京,就住在黄泥岗36号内。街对面是饭店,叫‘鼓楼饭店’,饭店隔壁是教堂。‘鼓楼饭店’有五进,是二层楼,大门朝东,圆形门框。这里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里面全是日本人,女的穿和服。来这里的嫖客全是日本兵,有的坐黄包车来,有的坐汽车来。里面有多少慰安妇不清楚。”鼓楼饭店老屋在1990年前后拆除,现在在原址上由南京供电局盖了一座职工宿舍大楼。
“傅厚岗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鼓楼之北,中央路之左。现地址为高云岭19号。据在2000年年初调查,82岁的老人刘万发证实说:“我家原住傅厚岗10号之一,现改为高云岭16-18号。我家有一进二厢,还有一个大院子。日军来时,占据我家的房子作养马场。我家对面是廖家,是二层楼洋房,也有院子,是日本人开的妓院。”另一位77岁的老人童恩华证实说:“1937年我14岁,家住在玄武门,就是现在的展览馆南面。当时我就知道傅厚岗有日本人的妓院。因我姨妈家住傅厚岗11号,我经常去姨妈家玩,看到廖家房子里有许多日本女人,穿日本和服。廖家房主当时逃走了,日军占据房子开妓院。”据知情者说,廖家房主现住台湾。[28]
“珠江饭店慰安所”。位于珠江路。
“满月慰安所”。位于相府营。
“菊花水馆慰安所”。位于城东北部湖北路楼子巷25号。
“共乐馆慰安所”。位于城东桃源鸿3号。
“皇军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
“上军南部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四达里。
四是城外郊区与浦口、江浦、汤山等地。
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
“昭和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7号,创办人久山卜,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3号,创办人沟边几郎,朝鲜人。
“一二三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10号,创办人济道。
江浦慰安所。江浦县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属于远郊区,与苏北的六合、盱眙及安徽省的和县、全椒、滁州接壤。日军占领了江浦县城及其部分地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及中共新四军的淮南根据地相连,因此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常年驻防日军部队。据史料表明,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日军方都设有慰安所,但慰安所较简陋,慰安妇人数也只有数人,专供驻防日军“使用”。如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中,在1945年年初,有韩国籍慰安妇4人。其他日军据点也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29]
“汤山慰安所”。汤山镇位于南京以东的远郊区,有温泉,是著名的风景区与疗养地,又是南京外围的重要据点。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建有多所别墅,还建了一家陆军炮兵学校。日军占领汤山后,长期将炮兵学校占作兵营,驻防许多日军。日军当局在当地设立了几家慰安所,以供驻防日军之需。1929年出生的朱家龙老人在2004年2月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在汤山开慰安所的,就在指挥营后头的‘天然温泉浴室’里头,门很小,里面很大,我进去看过的……里头有日本女人,也有朝鲜的女人……另外一个妓院是个叫天福的日本人开的,就在汤山街上,现在的‘万家乐’商店那个地方,大门牌子上写的就是‘天福’两个字。天福的老婆在里头管一帮女的,很凶。”[30]164“1924年出生的经友发老人在2004年9月接受采访时说:“汤山的慰安所一开始在老街里,是地主袁广智的房子。袁广智是汤山人,抗战发生后跑到四川去了。鬼子就把他的房子占下来做生意……慰安所是日本人起的名字,是为了‘安民’而搞的,让日本兵在休息天有个玩的地方,不去搞别的女人。慰安所在老街办了二三年,后来搬到了高台坡的巷子里,就是现在的信用社的东边,也办了二三年。慰安所是日本商人山本夫妻俩办的……”1925年出生的刘幸福老人在2004年7月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在汤山街上是开过妓院的,他们叫慰安所,在高台坡那里,离我家门口不远,有三间大瓦房,现在改成信用社了。进慰安所,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中国人是不让进的。里面的妓女都是朝鲜人,没有中国人,但是有几个中国女人在里头给日本人洗衣服。她们在里面的活动,我们站在家门口看得清清楚楚。”[31]
三、日军方对南京慰安所的管理
在日伪当局的组织与主持下,南京在日本统治的8年期间,究竟共开设了多少家慰安所,已难以精确统计。
1937年12月底在南京下关日军“第二碇泊场”任职的日军士兵坂田贞一,在晚年回忆了他当时了解的南京城内外遍设日军慰安所的情况:
慰安所很早就有了。男人最初去的地方就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下关有2处,城内有10处或 12处。对岸的浦口也有三四处慰安所。因为没有专门照顾女孩子的机关,所以暴行更加严重。下关的慰安所里朝鲜人比较多, 中国人从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都有。中国人有中国人呆的房子,朝鲜人有朝鲜人呆的房子。南京城内也有一处日本妇女的慰安所,听说有几个在日本做不到生意的40来岁的大婶。街道的胡同里也有很多没得到军队许可的暗地里搞的慰安所,站在胡同里的女孩子几乎都是卖春的。是日本人带着五个左右的女孩子干那种私下的买卖。使用避孕套当然好,但是不用的话,价钱虽然便宜,但很容易患上急性的淋病等性病,很危险。军队管理的慰安所是在门口买票,叫来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把票递给女孩子后再玩。价钱是一日元50钱左右,挺贵的。如果每个星期日去找女孩玩的话,钱会立刻花光的。[10]338-339
1938年中,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编辑出版了一本《南京指南》的小册子,提供给驻南京的日军使用,其中就公然记载了在南京的9家陆军慰安所及其位置:“(1)大华楼慰安所:白下路312号;(2)共乐馆慰安所:桃源鸿3号;(3)东云慰安所:利济巷普庆新村;(4)浪花慰安所:中山东路;(5)菊花馆慰安所:湖北路楼子巷; (6)青南楼慰安所:太平路白菜园; (7)满月慰安所:相府营;(8)鼓楼慰安所:鼓楼饭店;(9)人民慰安所:贡院东街2号。”[32]93
无疑,上述记录的慰安所仅是冰山一角。
在1938年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M.S.Bates)曾亲眼看到张贴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两大张日军慰安所的海报,上面写着:
“支那美人,兵站指定。慰安所第四日支亲善馆,由此循河边前行600米。”
贝德士后来在其所写的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发布稿《妓院是“东亚新秩序”的政治工具——皇军在被占领的首都大街上肆意行恶》中转录了这张海报,并就此写道:“海报照片代表装点南京街道之一种象征模式。这种特殊招贴有两大种展示于中山北路,离广场不远。经调查属实,它正对着一所规模很大的女子学校,也靠近宪兵司令部。”贝德土愤怒地斥责说:“甚至连海报的语言都是中日淫秽的混合物,令每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作呕,同时又是对于受过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军队促进的这种‘友好关系’,最好别印出来。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而且愈加增多。但他们希望应该多少考虑一下对于年轻一代心灵的影响,以及一个过去习惯于礼仪的社会的市容。”[13]40-41
伪“维新政府”的机关报《南京新报》在1938年8月1日刚一创刊,就连续多日刊登整版广告:“大优惠皇军——人民慰安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①
1938年7月汉口出版的《宇宙风》杂志第71期刊登林娜所写的《血泪话金陵》一文,指出:“在(南京)城中设立了17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貌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在这些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33]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日军在南京长期设立的40多家慰安所,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多设在日军驻防营地与日侨聚居区附近,如南京城南太平南路科巷、文昌巷、利济巷一带与城北下关一带;第二,多利用原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或富商的住宅,也有利用原饭店、旅馆、机关、学校的用房。
由于南京的慰安所数目众多,名目繁杂,秩序混乱,事故频发,也由于要预防各慰安所向日军官兵传染性病,日军军方十分重视对南京各慰安所的管理,制订了多项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38年4月16日,驻南京的日军陆军、海军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专门对南京地区的慰安所作出如下规定:“1.陆、海军专属的军队慰安所与领事馆无关;2.关于一般人也能利用的慰安所,其老板方面由领事馆之警察管理,对出入其间的军人、军属则由宪兵队负责;3.在必要的时候,宪兵队可以对任何慰安所进行检查、取缔;4.将来军队也可把民间的慰安所编入军队的慰安所;5.军队开设慰安所时,需将慰安妇的原籍、驻所、姓名、年龄、出生及死亡等变动情况及时通报给领事馆。”[34]179
此外,日军方对各慰安所的管理还包括:
1.卫生检查:各慰安所的床铺、厕所等需定期清洁消毒;慰安所的慰安妇都要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有性病者需治疗或驱逐。
2.使用规定:日军各部队官兵去慰安所的时间分配、费用价格、一次使用时间及必须使用避孕套工具等;有的日军部队还规定了到慰安所的“号牌制度”,在部队中特设“补给副官”,其主要使命就是安排、分发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证和号牌。
3.慰安妇生活管理:由日军宪兵严格检查监督,不许随便外出,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所得收入上交日军军方;慰安妇若怀孕,则杀子留母;慰安妇若生重病,则一丢了之;当危急时刻,日军要先杀死慰安妇,然后撤退等。
我们在对南京下关区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进行调查时,得到了一张当年下关“华月楼慰安所”的木牌照片,上面记载着该慰安所管理规定的详细条文:
兵站特指定慰安所的规定如左:
1、每个兵站慰安所内的特殊妇女每隔5日必须接受宪兵分队兵站支部医官的检查。
2、检查结果不合格者需到特殊治疗所接受诊治,未经许可严禁接客。
3、每名慰安妇的检查结果均应有记录,全部检查结果应汇编成册,以便随时检阅。
4、慰安所开放时间如左:
兵:上午10时至下午6时;
官:上午10时至下午9时。
5、慰安所使用价格规定如左:
兵:一元(一次30分钟)(每延长30分钟追加五十钱);
校:三元(一次1小时)(每延长1小时追加二元);
高等官:三元(一次1小时);
官:判任官以下:一元五十钱(一次30分钟)(每延长30分钟再追加价钱)。
6、使用指定慰安所的人员必须付费,领取和使用避孕套,而且事后必须到洗涤室清洗。
7、除军人和辅助军人外,任何人不得进入特指定慰安所。
8、严禁携带酒类进入特指定慰安所。
9、严禁酗酒者入内。
10、不得进入所认定购买号码以外的慰安室。
11、不按规定使用避孕套者严禁与慰安妇接触。
12、不遵守本规定及违反军纪者勒令退出。
昭和十四年三月六日(1939年3月6日)[27]
从这些条文来看,日军当局对所辖各慰安所的管理是十分重视与细致的;在实施中,对各慰安所的卫生与各慰安妇的身体检查更是十分认真而严格。
据居住在下关商埠街的金秀英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商埠街34号院子里、紧靠惠民河的那幢平房(现为下关区公证处的汽车库),当年就是日军为慰安妇检查、治疗的地方。她当时只有十几岁,经常要到惠民河边淘米、洗菜,有时她会好奇地从那幢平房的窗户偷偷地向里面看。她发现里面经常有很多女人脱光下身,坐在一个高高的特制的木椅上,有穿着白衣服的医生为她们检查,有的医生还要为她们上药。[27]
日本军方的资料表明,在1942年年底到1943年年初,驻南京的日军当局曾对南京的各慰安所的全体慰安妇进行过连续三个月的身体检查。例如自1938年6、7月间进驻南京、担负南京警备任务的日第15师团,直到1943年6月调离,在南京驻防前后约五年时间。这个属于警卫专用的三单位制师团的军医部,在1942年12月到1943年2月,对其师团所管辖的各慰安所的慰安妇进行连续3次的身体情况检查,并在《卫生业务要报》上公布了检查结果,②从这份检查结果上可以知道,驻南京日军当局对慰安所与慰安妇的严格管理,使慰安妇中的性病发病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并不是日军当局对慰安妇的爱护与关心,而是完全为着既能让日军官兵得到性满足,又能使日军官兵免受性病的侵袭,为着保护与提高日军的战斗力、最终取得侵华战争的胜利。
四、南京慰安妇的血泪
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她们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她们根本不被当作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一位曾沦为慰安妇的中国老太太后来控诉说:“那里成了驴马配种站。”日本学者则称慰安所是“色性的地狱”。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苟延残喘,没了灵魂,形同僵尸。若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一位被俘的中国士兵在南京日军军营里服苦役。他后来从南京逃出来,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在日军军营一个慰安所中慰安妇们的悲惨情况:“我只好往屋里送(水)。我方才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了两位女同胞掩在一条毯子下,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皇军”官佐,一个人穿了一件女衣在狞笑……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哪能穿衣服呢?……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总是听到哀嚎和嘻笑……每次走到街上……同胞的尸体可实在多得可怕,特别是多添了许多裸体女尸,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敌军顺势来个剖腹。”[35]36
日军方管理慰安所的规则虽明文规定禁止日军酗酒者入内,禁止携带刀、枪等武器入内,但事实上都得不到日军官兵遵守。如在下关华月楼慰安所,据知情老人樊桂英回忆,经常有酗酒后的日军士兵强行入内。有一次,一个酗酒的士兵冲到楼上,企图进入一间慰安室,室内的慰安妇急忙将门关上。日兵撞门不得入内,就抽出随身携带的军刀顺门缝向内劈去,竟将抵门抗拒的慰安妇的膀子刺得鲜血淋漓。后来,该慰安所的日籍老板喊来宪兵,才将这个士兵带走。[27]
一位南京民间学者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在南京走街串巷,实地走访调查了22位曾被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南京老年妇女,记录下她们的血泪史。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调查材料一直未能公开,最近才向笔者展示了这批珍贵的原始笔录。这是南京最早、最集中的一批中国慰安妇的档案材料。其主要内容如下:
杨隆珍:出生于安徽东部农村,1940年前后流落到南京,靠打佣工为生,家住中华门外西街;1942年夏,她被伪保长以“帮太君洗衣”为名,骗入大行宫利济巷“东云慰安所”,在棍棒毒打下沦为慰安妇,规定每天接待日军官兵不得少于5人;一次她生病不能“接客”,竟被日军拳打脚踢;她亲见许多慰安妇姐妹被折磨而死后送往南京城西清凉山日军小火葬场焚化;一年多以后,1943年秋,她才被一位远亲营救出来;20世纪60年代她在南京一度担任过一家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主任,80年代初摆烟杂摊,1995年辞世。
姚曼莉:战前原为上海电台艺员、歌手,家在南京;1939年被日军强征入三牌楼“故乡楼慰安所”;初为少佐以上的日本海军官佐提供性服务,因才貌出众又会几句日语,被日海军司令部一大佐包养;1944年生一女;解放后,姚在某中学教音乐;20世纪50年代,姚因“经历复杂”受过审查;1993年因病去世。
马红妹:南京人,1937年底在城南一家机织作坊做工兼佣人时,被强掳入蓝旗街日军简易慰安所;半年后侥幸逃脱,后返乡务农;1996年辞世。
胡文英:南京人,1940年在南京养济院当佣工时,与胞妹胡文秀同被汪伪社会福利局官员骗入城西“浪速楼慰安所”;1943年,胡文秀被害致死;胡文英在1941年逃出慰安所,后嫁给一职员,终身未能生育;儿子为早年抱养的。
徐明香:南京郊区人,原在家务农,1942年进南京城打工,被汪伪特工绑架,以“通新四军游击队”罪名,关入城中警察局,恐吓后再被强行送入“大华楼慰安所”;1942年底被家人营救出来;1990年病故。
杨泽慧:南京郊区栖霞人,家住栖霞街;1941年与施惠珍等4名年轻女子,同被到郊区以招店员名义的太平南路日侨商店老板,骗至“青南楼慰安所”;半年后其家人托请汪伪权要陶锡山出面保释出来。
施惠珍:1920年出生,1941年被太平南路日侨商店日本老板以招店员名义,骗入“青南楼慰安所”;后因患病被日本人扔在南京郊外的荒地上,被当地人营救。
朱桂花:小学文化,遭遇与杨泽慧、施惠珍相同;抗战结束后在江南水泥厂工作。
郑明霞: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为夫子庙怡春院妓女; 日本占领南京后被强征入贡院东街2号的“人民慰安所”;1940年不堪非人的折磨逃出来;1949年解放后,被安排在工厂工作。
何庭华:原在夫子庙秦淮居酒家务工;1943年被汪伪保长骗入“人民慰安所”;以后经历大致与郑明霞相同。
吴邦英:南京人,住铁路二村,丈夫是铁路工人,婚后生有一子一女;1942年随丈夫过江探亲时,在商埠街被汪伪侦探绑架,罗织罪名关押刑讯,其夫被拷打致死,吴被强送入“鹤见慰安所”(隶属驻南京的日本海军部队);一年后获救。
张中琴:1944年其兄在抗日作战中牺牲,她被当地汉奸强押送到日军宪兵队,遭轮奸后送至“鹤见慰安所”;半年后得以逃出。
上官红云:1939年外出游莫愁湖时被汪伪特工绑架,强送入“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后被美国友人出面救出;抗战胜利后,她曾化名在报刊上撰文,控诉日军慰安所的罪行。
朱金香:原籍南京郊区江宁县湖熟镇;1936年,17岁的朱金香随堂姐到南京城南一家织布作坊当织布女工;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攻中华门那天,朱金香挎个包袱,随逃难人流涌往下关江边,为滔滔大江阻隔,迫不得已潜回城里,藏匿于清凉山下一户菜农家中;一个多月后,日军大屠杀停止了,她欲返回城南找堂姐,在途中被日军抓住;日军将她五花大绑,与其他几十位妇女一起,押到五台山下一排平房里;那房子共7间,每一间又以芦席和军用帆布隔成若干个小单间;门外有日军持枪站岗;房子里时时传出受害妇女的哭叫声和日本兵无耻的嬉笑声;此后,她就成了日军的性奴隶。 日军官兵只给她们每人一条军用毛毯、两条毛巾和一块药皂;寒冬腊月,薄毛毯根本不顶什么用,半个月里有10名妇女冻饿生病而死;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的是粗面馒头与两瓷缸马铃薯汤;她们想自杀,连一根上吊用的裤带都没有。有一天,朱金香实在忍受不了日本兵的非人折磨,奋起反抗,抓伤了一个日本兵的脸。她遭到一顿毒打后,仍不屈服,结果又被捅了几刺刀,昏死过去。一个日军军官认为她死了,便叫一个打杂的中国老汉将她裹进破芦席,拖到五台山坡,扔在乱坟堆中间。寒风一吹,朱金香苏醒了过来。那位老汉还没离开,听见朱金香的呻吟声吓了一跳,悄悄将她抱上推车,送往附近的虎贲仓棚户区。一对老夫妇冒着危险收留了她,朱金香认他们为干爹干妈。几年后,她重新进入织布作坊做工,并结婚成家,但已不能生育。日本投降后,她和丈夫去育婴堂抱养了一个女婴。1981年,朱金香从南京城南某纺织厂退休;1989年辞世。
小贺:南京人,家住升州路,原为中央大学学生,文弱白静,戴一副近视眼镜;南京沦陷时,她为照顾患重病的母亲,随家人躲入阴阳营难民区;秩序稍定后,她刚回到家中,家庭即遭几名日军的抢劫与强暴,保姆被奸杀,母亲惊吓而死,她被日军强奸后,被抓进一家慰安所,与朱金香同在一处。不久,她不堪折磨,精神崩溃,又抓又咬,竟被日军开膛剖腹,割掉乳房,野蛮地杀害。朱金香目睹了小贺的悲惨遭遇。
邵美英:长相清秀,皮肤白净;1934年春,18岁的邵美英跟表姐来到南京打零工;1938年秋一天下午,她和几个未办“良民证”登记的年轻妇女被抓进了伪警察局;后被汉奸交给日本人;两个日本军官盘问一番后,就将她们带到太平南路的“青南楼慰安所”;从此,她深陷火坑,生不如死;一天,一名日军炮兵中佐来到青南楼慰安所,一眼就看中了邵美英;以后此人便常常光顾青南楼慰安所,专找邵美英;后来干脆包下了邵美英,长期霸占,并生一子。邵美英后来听这个日本军官说,原来她的长相与这个军官的日本妻子有几分相似,她成为“替补品”。 1944年底,那日军中佐远调南洋战场,日本战败后不知所终;而邵美英才得以恢复自由。上世纪50年代末,邵美英曾在玄武区一家街道食堂干过炊事员,以后一直在新街口附近一条巷口卖鸭血粉丝汤、葱油饼、馄饨。对早年当日军慰安妇的经历,她从不愿提起。后来,经过一位在“文革”中曾救过邵美英一命的某派出所老干警反复做工作,她才终于开了口。邵美英于1990年病故。[36]
在2006年4月,我们在汤山找到了一位活着的慰安妇老人——78岁的雷桂英。她告诉我们,她 于1928年生于汤山一个农家,不识字。约在1940年她12岁时就遭到日军的5次强奸。后来,她被住汤山的一家日本人夫妇雇去做保姆。当她到这家日本夫妇家后,才发现是被骗去做慰安妇。这家日本夫妇就是汤山高台坡慰安所的老板。雷桂英在刺刀与皮鞭下,每天要“接待”4、5个日本官兵。直到日本投降,她才跑了出来。她已没有一个亲人。17岁她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医生检查后说,她永远不能生育了。她只得领养了几个小孩。最近,她的养子几经考虑,终于动员她母亲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37](2007年4月25日,雷桂英在南京去世——编者按)。
韩国籍慰安妇的命运同样充满血泪。曾于1939年至1942年在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做过3年慰安妇的朝鲜姑娘朴永心,于1921年12月15日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平安南道后浦里一个贫苦人家,自幼丧母;1939年8月她17岁时,被日方当局以招“女看护”为名骗到南京,送进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开始她不从,被日籍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饥饿、吊打,最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受尽侮辱、蹂躏与折磨。有一次她来月经,下身血流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那日本士兵竟惨无人道地拨出身上的佩刀,向她的脖子上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鲜血飞迸,跌倒在地。幸亏慰安所中的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急救,才逃过一死。1942年5月,她被日军当局作为“军需品”送往东南亚战场,才离开南京。2003年11月她被我们接来南京时,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伤痕,说:“我的人生太苦了,几本书也写不完。”[38,39]
在1937年年底被日军强征到南京浦口做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义庆,于1916年12月6日出生于汉城市内,家中原有姐妹7人。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她就被日军从韩国骗来南京。她当时21岁。她到浦口时,正是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之时。她被强迫做慰安妇,从此开始苦难的日子。以后她又被日军带到长沙,最后来到武汉,一直是日军的性奴隶。因为反抗日军的强暴,她被日军打坏了左手,造成骨头畸形。由于日军的摧残,她无法生育。战争结束后,她留在了武汉,与一位中国人建立了家庭,并领养了中国养子。现在与养子一家共同生活。2001年9月,史学工作者陈丽菲到武汉金义庆家中访问,刚进其家门,金义庆老人就抱着陈丽菲大哭起来。[40]
日本籍慰安妇的命运也十分悲惨。南京沦陷时期在下关三明旅馆工作的刘聚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南京下关某慰安所的一个惨痛故事:有一个日本军人去一家慰安所,没想到他按号头叫出的慰安妇恰好是自己离别多年的妻子。夫妻两人抱头恸哭,最后双双自杀。[27]即使有些慰安妇侥幸能活着逃离慰安所,但身心遭到极大摧残,特别是染上各种性病,给她们带来极大的伤害与终生的痛苦。 1939年6月22日金陵大学美籍植物学教授史德蔚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南京教会鼓楼医院美籍医生提供的证言:“就他们在医院的经历,他们说自从日本人进城后,性病的比例从15%上升到80%。军队要大量妓女,不断有人从周边农村抢走妇女,把她们送进城以满足需要。而且因为她们对性病毫无防御力,很快就会染上重病。在这种行当里不再有使用价值,所以就不断地要求新的妇女来补充。”[13]360
南京的慰安妇除了在南京的慰安所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摧残与折磨外,还有许多更不幸的慰安妇被日军当作“军需品”,秘密押往中国与海外的其他战场,供那里的日军部队蹂躏。据韩国《新东亚》杂志1994年第3期的一份史料披露,在南京的“故乡楼慰安所”、“浪速慰安所”的许多慰安妇,在 1942年5月,应日本“南方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被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送往太平洋与东南亚战场,后被分配在驻缅甸与中国云南西部的日军部队中。这些慰安妇有日籍、韩国籍、中国籍等。[41]日军精锐的第56师团于1942年5、6月从缅甸攻入中国云南省西部,企图从这里进击云南省会昆明,包抄中国国民政府大后方地区的后路,但在怒江边遭到中国军民的拼死抵抗,一直未能跨过怒江,形成为时2年多的中、日军队隔怒江对峙的态势。在这漫长的对峙时期,日军当局为维持士气,从后方调来大批慰安妇“劳军”,其中就有从南京调去的许多日籍、韩国籍、中国籍的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在滇西前线遭受了日军两年多的蹂躏。1944年6、7月间中国军队反攻怒江西岸,日军第56师团拼死抵抗,于1944年9月初全军覆没。怀着武士道精神的最后一批日军野蛮地屠杀了全部随军的慰安妇,然后全部自杀。但在日军的枪口下,竟然有4个韩国籍慰安妇奇迹般地逃了出来,最后被中国军队俘虏,并留下了一张被俘慰安妇的“经典照片”。其中就有那个曾经在南京利济巷2号慰安所中生活过三年、后被送往滇西松山的朴永心。当时她已怀孕几个月,腹部隆起,在激烈的逃生路上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被中国军队送到医院抢救,取出死胎,后又被送回朝鲜,割掉子宫。她再也不能生育。她也再未结婚。她从孤儿院收养了1个小孩,在艰难中活到了80多岁,活到了21世纪。我们南京学者与日本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在平壤找到了这位饱经沧桑血泪的老人。我们还在云南找到了她当年遭迫害与逃生的道路,找到了她被日军强迫拍下的裸体照片;在南京找到了她当年被蹂躏的利济巷2号慰安所旧址。2003年11月,我们将这位老人先后接到了南京与云南。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控诉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给她带来的终生的痛苦。[38]
无数的南京慰安妇受尽凌辱折磨,带着肉体与精神的深重创伤,在血泪中死去。她们的冤魂日夜望着南京故乡哭泣。
五、南京“慰安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查封
应该指出,日本当局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实质就是把日军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妇女强奸、轮奸的性暴行合法化、公开化、制度化、商业化,但其践踏妇女人格、摧残妇女身体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甚至比强奸妇女有过之而无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当局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后,并没有也不可能约束与根绝日军对当地中国妇女的强奸暴行。在日本统治南京8年期间,驻防日军的性暴力时有发生,成为与慰安妇制度并行不悖的殖民地现象。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9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在日军侵占南京近一年以后,南京的日军仍随意地抢劫居民财物与强奸中国妇女:“我们去看夏老太,一位80岁的老婆婆。她说,甚至现在,每天黄昏时,她与家人仍去从前的安全区的一所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她们害怕晚上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日军)士兵们几乎每天都来,要找‘花姑娘’,即年轻的女子,并随意拿走鸡、鸭、猪、谷物和蔬菜……路上,我们仅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大多数姑娘白天不敢出来。”[8]434
1944年11月,冈村宁次大将调来南京,升任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这位侵华日军的新任最高领导人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通,同时也是日本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创始人。因此他来南京任职后,日军的慰安所得到更加有力的庇护,相安无事,甚至有所发展。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9月9日冈村宁次向中国战区受降主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投降书以后,由于何应钦迟迟没有下达解除驻南京日军武装的命令,驻南京、芜湖一线地区的日军有1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与几个特种兵联队,均受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在一度的沮丧以后,又重新气焰嚣张与无所顾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日军的慰安所依然生意兴隆,醒目的牌子高悬街头”。败降日军的嚣张气焰与无所顾忌激起了南京中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担任南京警备司令的邱维达经请示何应钦授权,于1945年10月收缴日军的武器、弹药与物资,集中看管全部日军,限制冈村宁次等的行动等,“同时,日军设在南京的‘慰安所’也予以查封,把招牌砸掉,所有中外从业妇女一律遣散”。[22]134
至此,在南京存在了约8年之久的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制度,才被彻底送进了历史垃圾堆。
日本当局制订的“慰安妇”制度及其实施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战争暴行,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当局中的一些人,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在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的同时,也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本文仅以日军在南京一地实施慰安妇制度8年的铁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当局中一些人言论的荒谬与无耻。
注释:
①《南京新报》1938年9月30日广告。
②这份检查结果的详细情况,参阅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日本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173-176页。
标签:军事历史论文; 日军论文; 第六师团论文; 日本慰安妇论文; 日军师团论文; 杭州南京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大阪第四师团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