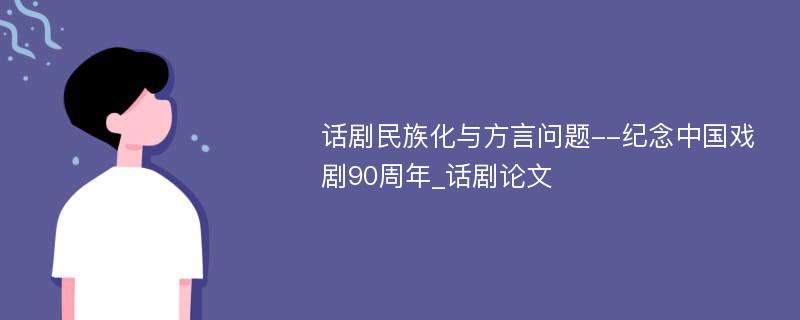
话剧的民族化与方言问题——为中国话剧九十周年纪念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方言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自有其深厚的积累与悠长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时吸收域外诸民族的文化作为营养,以丰富、壮大自己,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终保存着原有的精粹,同时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正因为本身文化传统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就不可能简单的移入,匆促的照搬,经常有一个复杂的曲折的历程。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民族,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某些惯性在起潜在的作用,一下子就接受从未接触过的这些方面的新的模式、新的概念,当然是相当困难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前,更是如此。
以上是就一般情况一般事物而言,话剧的传入中国也不例外。最早由李叔同在日本组织演出《巴黎茶花女》,接着王钟声又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因为既不唱,也不舞,于是名为“新剧”,这是1907年的事。“新剧”不像京剧昆剧那样在唱念做打各方面都可供欣赏,不少剧目近乎言论激烈的化妆演说,在群众中缺乏吸引力,局面施展不开来。
“新剧”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新剧”之所以在上海萌发幼苗,是由于上海是一个新兴的都会,思想界、文化界比较活跃,租界的存在固然处处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力,封建努力与租界也有种种勾结与默契,但又是知识分子和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反帝反封建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一切新的风尚新的事物比较容易接受,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时基本上还处于封建堡垒的状态。
另一方面,语言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开辟为租界之前,上海县的居民对普通话是陌生的。随着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繁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每年都有大量移民进入上海。就其籍贯来区分,以浙江的宁波、绍兴,江苏的苏州、无锡、扬州、盐城,广东的广州、潮汕以及山东各州县的人为多。这些称民都说他们家乡的语言,于是他们家乡的地方戏曲诸如绍兴大班(现在的绍剧)、无锡的滩簧(现在的锡剧)、苏州滩簧(现在的苏剧)、广东戏(现在的粤剧)等剧种也随之进入上海,为他们提供文艺生活。在一起住久了,除了广东话之外,他们彼此基本上能够交流了,至少是能听得懂对方的话了。这些地方戏就这样扎下了根。但是,他们都不说普通话,而“新剧”的对话都用普通话,对这一大批市民来说,接受上都有一定的困难。
有些“新剧”从业人员在多方面进行民族化的尝试。那就是在题材的选取上尽可能找中国的历史故事或当代社会新闻,表演也相应地作了重大的改变,对地方戏的程式有所借鉴。对话原来照搬西方人的腔调,中国观众觉得与我们的实际生活距离甚远,于是逐步舍弃。最大的改变是方言的运用,例如军官警官都说山东话,阔太太交际花都说苏州话,洋行买办和翻译都说广东话,大老板大商贩都说宁波话,师爷文书算命先生都说绍光话,理发师黄包车夫都说扬州话等等。这种职业与方言的对号入座也只有25%-40%的概率,而且也有人有些反感。但经过这一番改变,市民群众觉得和生活贴近多了,很快就呈现了某种转机。
应该承认,“新剧”的运用方言有一定的生活依据和社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京剧昆剧等传统戏曲把剧中人物分成生、旦、净、末、丑等不同行当不同角色有某些相似之处,那就是先把剧中人物分属于某一类型,而这一类型有其共性。然后在这一类人物的共性之中,再分析并把握其特定人物的个性,这是和西方戏剧完全不同的塑造人物的方法。《珍珠塔》、《张文祥刺马》、《啼笑姻缘》等剧目都为演员们提供了发挥方言才能的广阔天地。“新剧”得以开拓局面,争取得一批观众,并不是得之于偶然。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得失之间也有辩证的关系。把题材过多地局限于家庭伦理,那就无法反映当前重大的事件,因之时代感就相对淡薄。加之过多地借鉴戏曲,过多地使用方言,使“新剧”失去了“新”意,有时容易迁就小市民的趣味。民族化这一点固然有所反映,但有时也会流于庸俗化而不自觉。
十分值得深思的是“文明戏”这一名词的蕴涵的微妙的演变。当初“新剧”的称谓,是戏剧工作者一伙圈内人的自我命名。但是,市民群众则谓之“文明戏”。当时凡是新的事物冠以“文明”两字的不少,如不用封建习俗的婚礼叫“文明结婚”,西式的手杖叫“文明棍”等等,应该说“文明戏”属于褒词。到后来,“新剧”的民族化露出某些庸俗苗头时,“文明戏”三个字不知不觉成为贬词了。1944年,中国戏剧工作者在桂林举行西南剧展,欧阳予倩曾在一次报告会中说:“但因当时‘文明戏’之出现,此种迎合低级趣味之演出使新剧运动受到极深之阻碍。”这段话原文刊登在3月7日之《大公报》(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之一《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说得略有偏激之处,而且,“新剧”在未呈现低级趣味之前,也是被称为“文明戏”的。
尽管“文明戏”的含蕴有过微妙的演变,“文明戏”一词对市民群众来说,乃是“新剧”的同义语。从整部中国话剧史来看,“文明戏”是中国话剧的初级阶段,如果觉得政治气息太浓,或者可称之为中国话剧的最初形式。
话剧进入中国又是多渠道的、持续的。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等人比较具体而相当详细地向中国文化界介绍了易卜生,演出也是忠实于原著而严肃认真的。随之,也出现了一批中国戏剧家(也有非专业的)所写的水平较高的话剧剧本。出之于留学英美的归国专家教授之手者为多,如果从民族化的角度去要求,显然还有些欠缺。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戏剧界的注意。有一位戏剧家在纽约出版的《戏剧艺术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的新剧场》一文,大声疾呼:“如要成功,中国戏剧非得用中国的背景来表现中国的生活。”又说:“假使没有更稳固的基础而兢兢于贩运西洋戏剧形式,新戏剧之可能也就真没有日期了。”
这时,在美国专攻戏剧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南京执教的余上沅向国内戏剧界介绍了《戏剧艺术月刊》所提供的信息(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余上沅研究专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他自己也发表了类似的主张。他心目中的民族化的话剧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式,并未有详细说明。但是,有些问题他说得比较明确。例如他说:“即令有些作品也能比美易卜生,这种运动,仍然是‘易卜生运动’,决不是‘国剧运动’。”还说:“至于新剧,一般人还不曾完全脱去‘文明戏’的习气。”(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余上沅研究专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根据余上沅当时所发表的许多论文,我们可以认为,他把民族化的话剧称之为“国剧”,“仅贩运西洋戏剧形式”,不进而予以民族化的话,仍旧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国剧”。他认为,“文明戏”民族化的道路走错了,因此,也不符合他所称之为“国剧”的要求。
话剧的民族化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艺术实践问题。在大学戏剧系的课堂里,在大城市的剧场里,在戏剧刊物上,话剧民族化成为一个热点,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论,却仍旧得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结论。讨论仍在继续而分散地进行。
此时此刻,国内革命战争揭开了序幕,随后又是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再接着是解放战争。这三次战争都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战斗,人民群众在运用民歌、曲艺、绘画等形式来教育自己、组织自己的同时,也运用了话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参加战斗。如中央苏区时代的《活捉张辉瓒》(注:左莱、梁化群:《苏区“红色戏剧”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抗日战争前后的《放下你的鞭子》,以及建国后才完成的《万水千山》、《东进序曲》等等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话剧佳作。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迫切需要这些作品,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有用革命历史教育人民的任务。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无论当初是所谓“易卜生运动”者也好,“文明戏”圈内人也好,在业务上都有一定基础。他们有的参加中国共产党,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下进行文化活动。他们编导演的取材于中国现实斗争的话剧,不可能再株守三一律之类的清规戒律,必然地要告别小市民的庸俗趣味,无论活报剧、街头剧、独幕剧、多幕剧,都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解决了民族化的问题。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解决话剧民族化问题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国门之内,外国的优秀剧作的演出与研究始终没有停止。国内革命战争年代中央苏区还演出过《黑奴吁天录》,抗战期间,《苏瓦洛夫元帅》、《前线》等剧在国统区演出,基本上是按当时的苏联版本处理的。而在上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莫里哀的《伪君子》等数十年来都保持了盛演不衰的势头。我们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话剧就已经出现风格流派纷呈的局面了。
所谓风格流派纷呈,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一带,也包括剧目题材、表演艺术、舞台语言都与南国剧社、中旅剧团以及后来的若干剧团等演出团体有较大不同的被称为“文明戏”这一特殊的风格流派在内。“文明戏”(注:在海南省,早期红军演的话剧,就称为“文明新戏”。见《苏区“红色戏剧”史话》第15页。)是不是话剧呢?说是或不是都不完全准确。于是出现了“通俗话剧”(注:《通俗话剧的历史》,见《通俗话剧观摩演出说明书》(1957年1月)。)的提法。话剧工作者觉得这种提法不会玷污话剧的高洁,有区别比没有区别好。从事“通俗话剧”的人认为并没有被踢出话剧界,双方都暂时得到了安尉和心理上的平衡。
同时,在全国各地使用方言创作、演出,使话剧进一步民族化的努力似乎仍在分散地进行。在全国范围之内,用四川方言写作、演出的《抓壮丁》、《啷格办》等影响还是比较广泛的。与“文明戏”或“通俗话剧”的不同之处是使用单一的方言,而不是一台戏同时使用多种方言。演出之后,从未受到外界对他们在使用语言方面的批评和责难。
兼说多种方言的通俗话剧到建国初期还存在,最早有10个剧团,到1957年只剩下5个。共同的苦恼是剧目贫乏,表演上手法陈旧,继续在走下坡路。“通俗话剧”的提法虽暂时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却经不起仔细地推敲,话剧界和观众都为之困惑:难道《放下你的鞭子》不通俗吗?难道《妇女代表》、《你不能走那条路》不通俗吗?事实证明,即使是以大都市上海为背景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农民也都能接受,都能欣赏啊!如果把“通俗”作为“严肃”的反义词来理解也不行,话剧剧目并不全是正剧或悲剧,也有喜剧或讽刺小品。
有人认为通俗话剧与话剧的主要区别固然不止一端,但在风格上区分确实不容易,比较明显的区别是通俗话剧同时兼说普通话与各地方言。因此,当1960年上海仅存的朝阳通俗话剧团划归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编制时,被改称为方言话剧团(注:《方言话剧传统剧目整理演出说明书》(1961年)末页。)。1961年举行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方言话剧传统剧目整理演出”,分别由应云卫、田驰、钱祖武等导演了《啼笑姻缘》、《张文祥刺马》、《黑奴恨》等一批本剧种的传统剧目。
上海人艺的方言话剧团受到了领导和整个戏剧界的关注,帮助他们排演了题材颇有新意的《三个母亲》等剧目,得到了一致好评,但并未能在根本上改变方言话剧走下坡路的趋势。这是由于方言话剧在舞台风格、表演手法等方面虽然有自己的特点,却处在腹背受敌的夹缝之中,至少是对观众两面不讨好。中青年喜欢欣赏正宗的话剧,老年观众呢?即使对方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也转向滑稽戏剧场了。因为滑稽戏不仅兼用各地方言,而且表演上夸张,喜剧效果显著,吸引力大,中青年也觉得比方言话剧够刺激,所以方言话剧的观众仍旧继续在递减。这种局面艰苦地维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文化大革命”结束,上海人艺恢复建制时,方言话剧本身编导演已后继无人,又缺少观众,没有恢复方言话剧团,完全在情理之中。那么,中国话剧的民族化与方言问题是否到此可以画上句号了呢?事实证明仍然不能。
首先是戏剧工作者解放了思想,写了大量现代革命斗争题材,过去都不能写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涌现于舞台,而且基本上都挑选了身材、外形、神态都酷似的演员。为了产生逼真的效果,这批特型演员的语言没有用一般的普通话,而是按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方言作台词语言。反面人物中的蒋介石等等,也尽可能选择了外表酷似的特型演员及角色本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方言。舞台上周总理这一角色说的是普通话,但也故意使之带有淮阴口音,蒋介石的谈吐谩骂全是道地的宁波话。对于话剧观众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果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认为是民族化的一种尝试。这个问题的得失,座谈会上、报刊上并没有展开讨论。好在因为是重大题材,使用方言时,尤其是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使用方言时,尺寸把握得比较谨慎,没有作强度的夸张,应该说对人物的光辉形象并未造成伤害,也没有人认为是对推广普通话的一种障碍。但以后怎么办?现在舞台上、银幕上的邓小平也是说的家乡口音四川话。恐怕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要改变是困难的,这已经是一种定势了。最低限度,把选择特型演员作为首要任务时,不说方言是不行的。除非这位特型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本来就是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的。
另外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是十年前在美国出现了英语、华语相互对话的双语话剧《喜福会》,而且产生了轰动效应,不仅拍了电影,而且在国内也排演了此剧。演出场次并不很多,但影响不小。粗看起来,《喜福会》是洋化而非民族化,结果却发生了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作用,双语话剧的出现成了多语话剧的前奏。举例来说,1992年新加坡戏剧节上,李家耀演出的一个喜剧就同时使用了英语、普通话(新加坡称之为国语)、马来语、广东话、闽南话。1997年,我在悉尼时,墨尔本的一个剧团在此演出了一个戏,名《侦探小说》,演员分别说英语、国语和广东话。即以这两个戏为例,就题材背景说,新加坡华人的确大部分都能听懂这5种语言,个别人能说这5种语言,而且说得十分流利。澳大利亚华人所用语言基本上也有类似情况。所以应该承认同时采用英语和中国普通话以及多种方言是有生活依据的,并非哗众取宠的手段。
作为一个六十年的话剧老观众,我并不要求话剧理论家对方言可否作为民族化的手段这一点作出结论。但是,我希望对“文明戏”的衰落是否与使用方言有关以及话剧每一发展阶段使用方言的得失都作一番研究。我深信这种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我们未来的话剧应否使用方言、如何使用方言必将有指导和启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