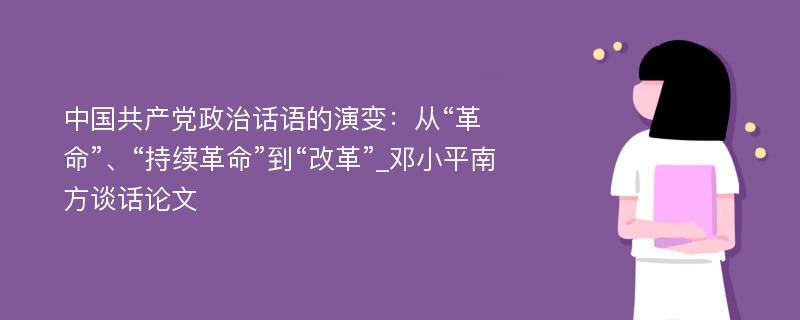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话语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4)01-0101-06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与革命紧密相关,行革命之事、尽革命之力、兴革命之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复杂的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革命向执政的现代化转型。转型的过程历经探索、挫折、试验的阶段,最终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以“革命”等政治词语的变迁为中心。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的词语变迁,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演进的历史脉络。 一、“革命”与“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与时代性 所谓革命话语,即以“革命”二字为中心。“革命”一词虽然是本土词汇,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汉语“革命”由英语Revolution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1896年的《时务报》杂志上。后由梁启超几番详细阐述①并经孙中山等一批民主革命人士在国民中广泛传播,被大众所熟知。对革命话语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对于“革命”传入中国的过程及意义的变化均有详细阐释。②这些研究成果描绘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革命”含义与梁启超等维新派、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均有差异。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政治内涵与后二者不同。对“革命”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中国共产党基本以1927年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为依据:“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③这种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形式的中国化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共识,旨在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最终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政权。 “革命”、“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与时代性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的历史时期相关,需要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考察。第一阶段:1927-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以“革命”斗争、“革命”运动为中心;第二阶段:1949-1950年代,以“革命”运动为中心,并带有生产力变革的萌芽;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中心;第四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的语义发生分裂:“革命”的原义及“继续革命”丧失时代性。 在第一阶段,“革命”特指阶级斗争、暴烈运动。1949年以前,“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凝聚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就是“暴烈的行动”信念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以“阶级”为区分,阶级区分方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运动中“革命者—对立者”的二元阵营划分基础,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大厦。因此,“革命”是这一历史阶段最具时代性的核心政治词语。 在第二阶段,“革命”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但又萌生生产力变革的语义。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革命”一词没有退出历史话语舞台,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具有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都隶属于“革命”范畴。运动的本质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意在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全胜利。但是,这一阶段的“革命”又带有生产力变革的语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不断革命”的使用上。 “不断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时代化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继续革命”理论的前身。“不断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本中出现的时间比“继续革命”早。1958年1月,毛泽东拟写《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不断革命”的最早文本。其中第21条毛泽东对“不断革命”一词进行了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④毛泽东拟写的这段话反复提及革命的连续性,强调革命的未完结。一是强调革命的任务既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有“技术革命”;二是强调不能只重技术革命,轻政治革命。从表面上看,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同为“革命”,但实质上二者有本质区别。毛泽东所讲的“技术革命”是指生产力的变革,而非“政治革命”的暴烈行动。因此,“不断革命”蕴含了思想变革和生产力变革的双重意思。“革命”的语义自毛泽东始在。1958年开始发生变化,只是这种转变是顺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自然萌芽,还没有被主观提炼到理论高度。后来由于毛泽东自身认识发生偏差,偏离了原来与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正确认识,导致“革命”的意义重回最初的原义,即阶级斗争和暴烈行动。 在第三阶段,“革命”被狭义化为“继续革命”,特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语义角度看,“革命”与“继续革命”有词意大小之分。“革命”是大词,“继续革命”隶属于“革命”范畴,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中国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段性政治词语。“继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为流传,成为打上特殊时代烙印的专门名词。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不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它公开见之于报端,是1967年两报一刊编辑部撰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后来康生把它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⑤但这个口号同毛泽东并非毫无关系。这篇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六个要点,简称“主席思想六条”,内容是经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⑥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得以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但是,这个口号的涵义在当时的党内和党报党刊上并没有详细解释,只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被广泛使用甚至滥用。 在第四阶段,“革命”与“继续革命”的时代性问题被重新反思,过时的词语“继续革命”在新时代被放弃,仍具有时代性的词语“革命”则需要重新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内进行拨乱反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留存成为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胡乔木认为:“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⑦邓小平也认为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分析,这个口号是错误的。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⑧以上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法已经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不再具有时代意义。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否定了这个提法。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之所以不能继续使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既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解释,用作口号就有危险,何况文革时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在三中全会后已经停止使用,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⑩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与“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的专用词语,代表的是暴力革命这种原义,不利于国内稳定发展新局面的形成。因此,作为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的词语,“继续革命”失去了生长的社会语境,不再具有时代性,被中国共产党所放弃。 反观“革命”,在1978年以后发生了语义的分裂,“革命”的原义被弃用,转义则重获新的时代性。根据胡乔木的说明,“革命”存在原义和转义的区分。“革命本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1)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11)改革开放新时期,革命精神不可弃,“革命”的转义仍具有时代性。“革命”一词,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解释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重新与时代相契合。 二、转义的“革命”:过渡政治词语的存在价值与具体释义 转义的“革命”,是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采用的过渡性词语。一方面,它最终被新兴的词语“改革”所取代;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具有政治必要性和重要的过渡性语义价值。中国共产党何以必须继续使用“革命”呢?原因有二: 第一,革命任务的未竟决定了“革命”词语的继续留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判定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中国目前革命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国内形势看,“革命”任务显然还没有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12)这里特别注意强调了“革命”的旧有含义和新含义的不同。 第二,新术语的未成熟决定了“革命”词语的继续使用和语义转换。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试图进行新的政治行为实践:改革,但这种实践无疑还只是一种试验,在与新实践相适应的术语未成型之前,最好的选择必定是以对旧的术语进行改造作为过渡。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完善的和不确切的概念和术语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13)当然,这种过渡必定会使旧的“革命”术语发生语义的转换。 从中国共产党的既有文本对“革命”一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转义的“革命”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指革命的方式不再是暴力斗争,革命的目的不再是夺取政权;二是强调革命精神、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化、革命品质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首先,转义的“革命”针对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体制、制度。1982年1月,邓小平指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4)1982年3月,赵紫阳在谈到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不仅要革臃肿机构的命,而且还要革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的命,革形形色色官僚主义作风的命……而不是革什么人的命。”(15)可见,中共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对“革命”的使用都是基于语义已经变化的“革命”。转义的“革命”已经不再是指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而是较为温和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变革。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6)因此,转义的“革命”所采用的方式实质上是变革,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 这样,“革命”可以用来泛指除暴力斗争以外的一切变革,凡是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体制结构变化等相关的内容均可用“革命”来概括。比如,1982年1月,邓小平曾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17)把机构变革看成是一种“革命”,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变革机构的彻底性。另外,中国共产党的文本中多次出现用“革命”来概括现代化建设事业。比如,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18)再如,1979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彻底改变农村面貌,这是我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革命。”(19)把现代化建设与“革命”联系起来,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决心。 其次,转义的“革命”暗含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克己奉公的革命传统等内容。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精神所带来的向心力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精神财富,在革命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种精神在1978年以后也并不过时。正如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问:“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20)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具有凝聚作用和激励意义。 概括而言,革命精神指的是“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1)。所谓“大公无私、服从大局”指的是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正如1980年8月邓小平所言:“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22)但这种服从不是完全牺牲个人利益,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已谈到这一观点,“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3)所谓“艰苦奋斗”,主要是学习大庆、大寨创业的革命精神。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学习大庆、大寨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24)直至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还专门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要求学习大庆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25)所谓“廉洁奉公”,主要针对党员干部而言,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依然要保持同群众同甘共苦。1981年7月,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那种认为和平建设时期就可以把革命精神丢掉,可以不与群众同甘共苦,可以把党员的个人利益摆在群众利益之上的思想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对于我们共产党的党性的败坏。”(26)上述革命精神后来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一道,被进一步浓缩、扬弃,慢慢在20世纪90年代为日渐成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所代替。 三、“改革”对转义“革命”的承继与更替 “改革”对转义“革命”的承继是由二者语义的衔接性所决定的。“改革”与转义“革命”相同,都是意指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旨在扫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改革”对转义“革命”的更替则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业已成熟的新术语必定取代过渡性的政治词语,成为新时代的核心政治词语。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改革”并不是新词。受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影响,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经使用过“改革”一词探讨问题。以毛泽东为例,1919年11月他曾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改革婚制问题》等文章(27),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1920年3月,致信黎锦熙谈及“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28),共同探讨湖南建设问题。及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毛泽东等人则不再提及“改革”,均以“革命”相论。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是否愿意进行“内政改革”看作联合抗日的必需要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则主要在“土地改革”这个名词范围内使用“改革”,意图最大限度获取民众对自身革命的政治支持。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的使用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基本没有超越“土地改革”的范畴。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思想。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就绝不可能回避如何从“革命”转向“改革”的命题。 首先,“改革”继承了转义“革命”的核心内涵:解放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9)与转义“革命”相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扫除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体制和制度障碍,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变革。因此,“改革”就是要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和动力。 其次,“改革”继承了转义“革命”的根本性变革精神,“改革”的性质就是带有“革命意义”的变革。1984年10月8日,邓小平在谈及农村改革的深刻意义时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30)这是肯定“改革”同样具有革命性根本变革的意义。之后,他在会见前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又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革’那样的革命。”(31)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提到“改革”就是“革命”,强调“改革”具有根本变革性。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2)此后,邓小平对这一重大命题又进行过多次类似的论述。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是对含义不明、时有争论的“改革”的定性,以“革命”的重要性作比,强调“改革”在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时的彻底性。但是这种表述还不够完全清楚。之后,二者之间的逻辑理路在邓小平的表述中才得以越来越清晰。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谈到:“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33)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完全透彻地阐述了改革的性质,就是在于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发展经济。 再次,“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新中心,是改革开放实践成功的直接反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虽然“改革”与“革命”具有语义的衔接性和共通性,二者追求变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改革”承继并最终替代了转义的“革命”,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新于“革命”,更契合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改革”是新兴词语,可以承载更多经济、文化和政治价值,具有新的语义生长空间;而“革命”由于承载了过多旧的与新时代不相符合的政治文化价值,注定只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官方文本中用来描述既往历史的教科书式词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使用,“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或者“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较为宏大而笼统的命题也较少再被提及。“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词语。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34)这就肯定了“改革”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尽管没有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改革”仍然同“革命”一样,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革”的实质和目标也被明确阐释,不再是空泛宏大的叙事,而是囊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等内容的具象目标。另外,报告还特别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5)中国共产党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以调动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建设中国现代化事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愈深刻,对“改革”的语义表达、阐释也愈成熟、全面。 四、结语 变迁的时代决定了政治话语的不断演进,对这种演进最好的观察就是考察话语中主流、核心并具有独特政治含义词语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阶段,展现给世人的除宏观的实践活动外,还有具象的话语表达。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呈现出的历史演进轨迹,就是这种具象的话语表达的最好证明,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思进求变的追求与轨迹。 收稿日期:2013-09-30 注释: ①梁启超认为本土词“革命”为改朝换代之意,Revolution由日语引入亚洲,其本意带有变革、革新之意。因此,Revolution不与“革命”等同,应翻译为变革。——见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1902-12-14. ②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生成[M].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陈金龙: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J].中共党史研究,2011(10)等等. ③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7. ④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49-351. ⑤⑦⑧(16)(18)(19)(20)(21)(22)(23)(2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上):34,35,95,4,29,169,560,560,458,22,122.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431-434. ⑨(12)(14)(15)(17)(25)(2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下):172,172,403,500,402,355,191. ⑩(11)中共中央关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绝密传达文件(1981-07-04),accession no.2002c15-16.360,box no.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pp.70-71,69-70.另见,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J],教学与研究,1981(6). (13)[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 (27)(28)毛泽东年谱(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上):48,54. (29)(30)(31)(32)(3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70,78,82,113,135. (34)(3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上),2011:2,10.标签: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继续革命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