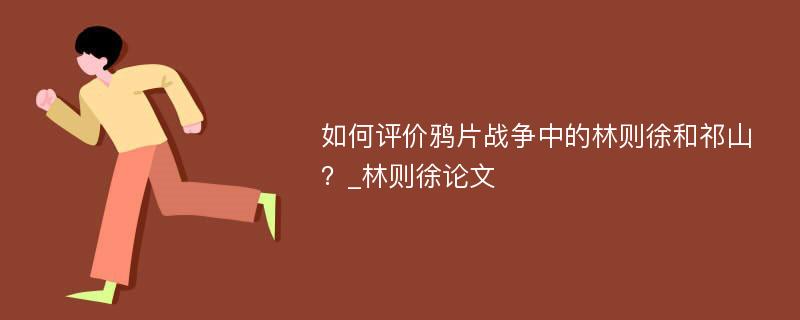
怎样评价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琦善论文,鸦片论文,林则徐论文,评价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对待英国侵略的态度,存在着抵抗与妥协两个不同的派别。林则徐和琦善,正是这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总的来说,学者们多半对林则徐严厉禁烟与抗英持肯定态度,对琦善则多所责备。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甚至通过贬低林则徐来抬高琦善。
首倡此议者当推蒋廷黻。1931年10月,蒋氏在《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发表了《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认为“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意思是,他在外交上对英妥协是有理的。“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对于蒋廷黻的观点,陶元珍于1935年5月2日,即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77期发表《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提出过批评。该文列举事实,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
值得注意的是,60年前蒋廷黻提出并在当时就受到专家批评的、在外国侵略面前实行妥协路线的论调,60年后,在中国大陆居然被有的人当作“新发明”来加以鼓吹。因此,还有加以辩明的必要。
第一,关于禁烟。
严厉禁烟是由于英国鸦片贩子不顾中国当局三令五申禁止鸦片输入,顽固坚持鸦片走私贸易,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害引起的。1838年实行严厉禁烟,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的决策,而不能认为“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持此论者提出了两个论据:其一是1838年8月到11月,琦善共缴获鸦片15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其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多两,感到情势严重,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
首先应该指出,道光帝对于禁烟,从即位起,十多年来一贯是很认真的,一直将它作为一项重要政务来处理。在这方面,只要稍稍翻阅道光元年以来的上谕、朱批,就不难得出结论。仅据1838年7月至1839年12月共18个月统计,道光帝就共计发布了83道有关禁烟奖惩的上谕,其中受到奖赏的文武官员共72人,受到各种惩罚的134人。时间不过一年半,受到奖惩的竟达200多人。
其次,禁烟中缴获鸦片的数量,不足以说明琦善是严禁派。琦善接任直隶总督是1831年3月,到1838年黄爵滋奏请严禁,在这7年的时间里,他对禁烟未建一言,未办一案。这表明他对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至少是漠不关心的。天津是华北的门户、鸦片走私华北的中转站,通过这里运销华北各地的鸦片,每年数量不少,据有人奏报:“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这里鸦片转贩、吸食是非常突出的。身为主管的琦善熟视无睹,还能称得上是严禁派吗?至于15万多两鸦片,是在道光于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五日、八月二十一日三次专门谕令琦善“严密查拿”的情况下才查获的,其中一次就在金广兴洋船上起出13万多两,证明只有鸦片销售量甚大,才有如此之多的鸦片运来。
再次,用十一月八日道光收到琦善奏报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多两,9日即召林则徐来京,证明道光帝严禁鸦片是琦善促成,也难成立。前已谈到,道光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的,而且在此之前,道光已下了多道谕旨,推行严禁政策。如:七月十九日上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之人,务须“严密查访,一经报官,立即征办”。(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4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九月八日,查明庄亲王等在尼僧庙吸食鸦片,立刻毫不留情地革去王爵。同日和第二天,又连下两道谕旨,要求直省将军督抚、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城等“严密访查,无论王公旗民,一体严拿”,“其贩卖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都足以证明,道光早已决定严禁,无须琦善促成。
至于谕令林则徐于十一月九日来京,不能说与琦善十一月八日的奏报毫无关系,但主要是由于林则徐禁烟认真,办事能干,得到道光帝赞赏。如十月五日,道光帝收到林在湖广查获大量鸦片的奏报,就在上谕中肯定:“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90、36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十一月十三日,又在林则徐关于江汉安澜的奏折旁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1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从这些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道光对林所寄予的厚望。
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并实力推行禁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鸦片应不应禁?应否采取严厉措施,迫使外国烟贩缴出鸦片?是否是因林则徐禁烟才引起鸦片战争?
关于林则徐禁烟引起战争问题,国外有此说法,国内也有人这样说。当定海失守后,“已有蜚语上闻,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者”。(注:《魏源集》上册第176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琦善到广东后也上奏说:“前督臣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内,均有奏请赏犒,奏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许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1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道光帝听了这类不实之词,竟误以为只要将林则徐等惩办,即可平息衅端。这说明琦善对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毫不了解,没有“知彼”的功夫。道光同样受到影响。
关于禁烟引起战争的说法是倒果为因的诡辩。因为中国之所以禁烟,是由于英美等国鸦片贩子贩卖鸦片。没有鸦片贩子的贩卖鸦片,中国哪来禁烟!故此责任全在英美方面。当然,中国禁烟,使他们的血腥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他们为了可耻的私利,悍然发动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鸦片战争。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不禁鸦片呢?由于鸦片走私输入有增无已,给清政府、给中国社会和广大人民都带来了无法容忍的祸害。无论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着想,鸦片都是非禁不可的严重问题。所以,林则徐认真执行严禁政策,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应予充分肯定。
至于林用派兵围住商馆、撤退买办等手段迫使鸦片贩子缴出鸦片,也是无可非议的。当时不用这种严厉手段,就休想从鸦片贩子手里收缴到一两鸦片。必须指出的是,林则徐是在外国鸦片贩子集体对抗,拒不缴烟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采取这种手段的;而且,他们一旦交出鸦片,就次第恢复供应,解除包围,准许正常贸易。所以,战争之起,根子和责任全在英国。正是外国鸦片贩子大肆贩卖鸦片,才迫使中国实行严厉禁烟。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容混淆。中国禁烟是正义的。中国反抗英国武装侵华更是维护中国主权领土的正义斗争。
第二,关于军事防卫。
面对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自应上下一心,军民同心,共同反抗侵略。为了保证反抗侵略的胜利,采取各种防卫措施,积极作好应战准备,也是完全应该的。在这方面,林则徐既具有坚韧不拔、抵抗英国侵略的决心,而又脚踏实地,加强防卫,迎头痛击侵略者,是值得称颂的。琦善则在直隶总督任上,根本不把加强防务放在身上,以致英军一到白河海口,即仓皇失措,一意妥协,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蒋廷黻认为,琦善在军事上“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无可称赞是实在的,无可责备则说得不对。因为琦善在军事防卫上,是存在许多问题的,理应受到应有的谴责。
首先,直隶沿海防务废弛,琦善首应负责。根据琦善本人的奏报,1840年8月,英军出现在天津以外的海口时,直隶的防务是个什么状况呢?“天津存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8页。)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直接关系京城安危。兵力如此单薄,怎能御敌。另外,防卫工事也早废弛,所存大炮都是锈坏不堪用的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0页。)防务废弛到这个地步,身为直隶总督已经10年的琦善,能辞其责吗?
其次,夸大乱人船炮,为妥协提供依据。当时,英国船坚炮利是事实。在武器装备方面,无疑英方占据优势。面对这种形势,正确的态度,应该像林则徐那样,尽量设法从他国购买船炮和加紧仿制大炮,装备自己军队,增强防卫力量;并讲求战争策略,积极谋求对策。然而琦善计不出此,自从英军1840年8月北抵天津海口,至1841年2月被革职拿问,闭口不谈怎样设法购备西洋船炮或自行仿制,以及研究对策,却无端夸大敌情,为妥协制造借口。1840年8月,北上天津的7艘英国舰船中,最大的旗舰威里士厘号不过装炮74门。可是琦善在向道光帝的奏报中却说:“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1页。)这样大肆夸大,从战略眼光来看,显然是别具用心的。当时有位朝臣唐鉴就指出,琦善的言行是在“长叛国之骄志,生汉奸之逆谋。”(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6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足见其恶劣影响是很严重的。
再次,不依靠民众抗英,反而敌视民众。战争的胜负,人心的向背是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靠群众,发挥他们多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弱制强。在这个问题上,林则徐是做得很不错的。他谕令各地团练御侮,自卫保家,如遇敌人来犯,号召“人人持刀痛杀”。(注:林则徐:《英夷鸱张安民告示》,转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第50页。)他对群众中蕴藏的抗英积极性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盛壮,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注:《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由于林则徐重视群众抗英积极性,在他领导抗英期间,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有的主动打击敌人,有的提供敌人情报,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英力量。琦善则和林则徐相反。他仇视人民,对人民抗英的积极性大泼冷水,把人民群众看成一支敌对的力量,“凡有报缉汉奸者,则诃曰:‘汝即汉奸’,有探报洋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注:《魏源集》上册第17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蒋廷黻和琦善一个腔调,对民众同样持敌视、蔑视态度。他认为林则徐说“民心可用”,是“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国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30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蔑视人民群众的心里达到了何种地步!
有些人根据敌强我弱,提出:打也是输;不打,输了还可少一点牺牲。从而怀疑反侵略是否必要;甚至有人说,鸦片战争时三元里抗英是干了蠢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这样断言:如果没有百多年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国早已亡国,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独立和富强。当侵略强盗打进门来的时候,奋起抵抗是完全正当的,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保卫社稷家园应尽的义务。林则徐坚持反抗侵略,鼓励和支持人民反侵略,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要求,从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和后人的崇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一种精神,一种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敢于抗争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再加上科学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逐渐由弱变强,由落后变先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有了希望。因此,有无这种精神,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关系至为重要。林则徐自始至终坚决反抗英国侵略,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仅此已可证明,林则徐的抵抗侵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反侵略即使一时遭到失败,甚至多次遭到失败,但失败中已孕育了胜利的因素,积累了由败转胜的经验,只要坚持反抗,最终胜利总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第三,关于对外交涉。
蒋廷黻等人把琦善吹捧为外交能手、“先知先觉”,而对于林则徐则认为于中外形势不及琦善那样明白。这种说法同样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首先,对于形势认识,他们最欣赏的,是琦善在大沽交涉的同时,还调查了敌人的军备,认为英人船坚炮利,敌强我弱。既然打不过人家,所谓“羁縻”(妥协)就是最佳的选择。而琦善坚持妥协方针,正是“他的超人之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看形势,一要看世界形势,而琦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团漆黑,茫无所知。他和道光帝一样,连英国坐落何方也弄不清楚。林则徐则相反,他在主持禁烟抗英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一部《四洲志》。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译的、介绍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地理、政治、历史、军备、贸易等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使国人大开了眼界。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翻译了外人论中国一般情况、茶叶、禁烟等的资料,定名为《澳门月报》,以及《华事夷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了解国外情况,竟然还向外人学起英语来。现存的林则徐的札记《洋事杂录》,就是林则徐了解世情和学习英语的最好见证。里面记有12个月、一个星期名称、各种外币,以及1、2、3等数字的英语读音等。凡此等等,证明林则徐在了解世情和世界形势上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相比之下,琦善除通过白含章到英国船上,了解了英国船式和大炮等之外,更没有作过任何调查,对世界形势可说是一无所知。蒋廷黻等硬说,“林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是看形势,应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地看,而不能光看军事方面,更不能只看到英人的船大炮大,就吓破了胆,认为中国军力远不及敌人,于是下定决心,一意投降。而琦善犯的正是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毛病。他除了看到英人船坚炮利,以及他管辖的直隶省军备废弛到惊人的地步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因此,不能认为他对形势的认识有“超人”之处。
其次,关于知己知彼的问题。林则徐和琦善都注意知己知彼,只是在目的上各不相同。林则徐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了世界情况特别是英国情况,目的是寻求“制夷之策”,是为了对付侵略者;琦善了解英人情况,则是为讨侵略者欢心,是为了妥协投降。
由于清政府推行封闭政策,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当时情势了解甚少。林则徐也是一样。他开初到广东,曾误以为外国人离开了茶叶、大黄,即无以为生。但到广州后,由于注意了解外情,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开初,他也相信英人腰直腿硬,上岸即无能为;后来,他从实践中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林则徐了解外情的方法,除了前面讲到的组织人力翻译西洋书报外,还曾亲自接见遭风船破遇救的英国人,不但向他们询问英军、英舰情况,还把致英王书的英译稿请他们校勘。他又亲临澳门,实地调查外人情况。从而认识到澳门华夷杂居,各国夷人多有,见闻最多,必须“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注:梁廷枬:《夷氛闻记》第6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通过各种途径,他在短时期内即了解了许多情况,并运用国际法,与拒不交出杀人凶手的义律进行了说理斗争。当他估计到英人会因严厉禁烟进行武装挑衅之后,就积极加强海防,在广东沿海各个扼要之处添设炮台,加强防卫。他奉道光之命断绝中英贸易之后,预计到义律会寻仇报复,就在广东沿海加强战备,“扼其要害,务使可守可攻。”(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知道敌人的长处在船坚炮利,就注意收集造炮技术与造船资料,着手仿制。他知道清军腐败,缺乏战斗力,就切实进行整顿,并招募乡勇水勇作为补充。因此,他的知己知彼,目的全在于“制夷”,即战胜英国侵略者。
琦善也做了一些知己知彼工作,但渠道很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贯彻妥协投降路线寻找借口。前面谈到,他夸大英军船上有炮300多位,意图就在让道光帝认为英人强大,难于取胜,只宜与其和平谈判,仗万万打不得。他了解英人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白含章、鲍鹏直接向英方打听。除了前面讲到的半真半假的船炮外,也打听了一些英国其他情况,但都在企图表明:英舰牢不可破,中国以往的破敌之法皆不起作用,而且英国还有很多兵舰,随时可以调来。如此,中国是万万不能对他开仗的。
再次,英军返棹南下,究竟是琦善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也值得作番考察。英军于1840年6月陆续到达中国海域以后,按照预定计划封锁了珠江,攻占了定海,然后北上直隶湾,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清政府屈服。对于英军的行动,清朝当局毫无思想准备。道光帝得知定海失陷,已有几分紧张,而今得知英军一下子到了自己的鼻孔底下,更加慌了手脚,害怕引发衅端。因此立即指示直隶总督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80页。)和去年那种强硬态度相比,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
身为直隶总督的琦善,由于天津一带海防极端空虚,更怕战事一旦发生,弄得一触即溃,失败将使自己身败名裂,开始就寄望于和平解决。他接到道光谕旨,立即执行。不但按照道光指示,派白含章去英舰接受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而且送去了大量的鸡、鸭、羊、阉牛和鸡蛋等英军极端缺乏的新鲜食物,向侵略者献媚讨好,借以换取英军停止进攻,以便保住大清的天下、琦善本人的面子和地位。当白含章从英舰上回来,告诉他英国的军舰如何高大,大炮何其之多以后,他更加被吓倒了,从此一意推行妥协方针,并千方百计去影响道光帝支持他的这一方针。如琦善在8月13日关于英人的第一次奏报中就说:“该夷尚无桀骜情形。据称伊系该国守备马他仑,经其长官派伊前来投文。其词祗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并请派遣官员前往船上接受正式公文。道光帝收到此奏,得悉没有桀骜情形,只“声称诉屈”,认为“办理甚为妥协”,(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68页。)即令琦善派员前往船上接受文书。
8月17日,琦善派白含章去英船把文书接收之后,又上了第二次奏折,而且别有用心地附了一份《查看现到英船式样片》。正是在这一附片中,极力夸大英军如何强大。道光详细阅览了英国文书,见开头即是“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即于8月20日谕告琦善:“文内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69页。)并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1、392页。)琦善于是根据道光帝旨意,一方面通过照会,将道光的态度告诉懿律,并声称:“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13页。)一面又约请懿律到白河岸口会谈,竭力促请懿律率军舰返棹南还。懿律和义律详细阅读了琦善的复照,看到只表示重惩林则徐,代为伸冤,而对英国致中国钦命大臣书中所提各项要求一概拒绝,感到“伤心极矣”,于是在复照中重申:惩办林则徐,“在大英朝廷,事果不堪一念,……事实两国所干,责已不在一人。”“倘已蒙奉大皇帝恩旨,允准秉公偿还鸦片之价,并所有大英另行讨求条款,亦准持平斟酌议拟,则所请回粤,原亦无所难行”。(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15-17页。)并要求在6日内明确答复,才可决定南行。9月13日,琦善经过奏报道光帝之后,再次照会懿律,表示:“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1-23页。)懿律和义律收到照会后,知道烟价赔偿上已有所松动,而且确知将来派去广东的钦差大臣,就是这位一意求和、容易屈从的琦善,于是在9月15日复照琦善,同意返棹南还。但重申烟价“必行偿还”。(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4页。)懿律等人对此大概还有点不放心,9月20日,当南行到了山东时,又补发了一封咨会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再次声明:“务求即?
朝廷商量英国讨求之各款,如何议拟情节,备文早日通知”。(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5页。)
英军就这样返棹南还了。考其实际,在英国方面,自有自己打算;在清政府方面,则最害怕英军赖在白河口不走,更害怕英军在这里发动武力进攻,威胁它的统治,所以千方百计劝诱英军“返棹南还”。现在英军居然同意,心头的千钧重担放下了。从而也就对琦善大加赞赏。道光得知英军确已南下,“嘉悦之至”。认为“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难怪有人要赞扬琦善的作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然而,事实真相又如何呢?英军南下,是否真是由于琦善的外交手段高明呢?原来,事情真相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清朝政府把英军南下看成是一个大胜利,实际是一个大误会。
首先,清朝当局对英国此次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意图一直没有弄清。在《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中,虽然一开头就提出要求昭雪伸冤,对广东地方当局大肆攻击,而实质内容是后面所提的4条要求,即:(1)赔偿鸦片烟价;(2)平等交往;(3)“将中国沿海一处或数处面积够大、位置适宜的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政府”;(4)偿还商欠和军费。最后并以武力相威胁,声言这些要求未得到满足之前,“那些敌对行动将不会停止”。(注: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下册第54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英国公文中如此,懿律在照会中也一再重申,必须使这些要求得到真正解决。可是清政府当局却以为只要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就万事大吉了。沿海的防兵都可以撤去了。这岂不是个大误会吗?
其次,对英军南下的真正原因也盲目无知,所以才把英军南下看成是自己的“大胜利”。英军之所以同意南下,固然是清政府答应了赔偿烟价,并到广东继续谈判;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英军兵力不足,无力在北方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南下之前,英国留在北方的只有军舰5艘,共载炮180门,另有轮船1艘。其余的军舰,1艘在定海搁浅后拖去修理,2艘封锁长江口航道,2艘封锁宁波,1艘封锁厦门,4艘军舰和1艘轮船封锁广州江面。陆军4000人则集中于定海,而且疫病流行,相继死亡400多人,还有1000多人住在医院里。(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有此情况下,它如对京津重地发动进攻,要想取得胜利是难之又难的。因为天津白河口横江沙以内水很浅,陆军又远在浙江定海生病,万一发动进攻被清军打败,更加无法收场。诚如彼得·华特·费伊在《鸦片战争》(1840-1842)一书中说的,英军启碇南下,是因为“没有攻击的能力。……没有吃水浅的汽船,是不能有效地封锁白河口的。”(注:Peter Ward Fay:The Op-ium War 1840-1842,The Univ.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6.P234-235.)加上北方寒冷,冬天即将到来,北风劲吹,援军和运输军饷船都无法北上,所以他们就将计就计,同意南下谈判了。这哪里是由于琦善外交手段高明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功”呢。
第四,关于善后措施。
鸦片战争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以后,中国要维持原状是不可能了,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接受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努力学习西方的长处,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奋图强,尽快赶上时代潮流,使中国早日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有力量抵抗外来侵略,打退外来的一切进攻,维护国家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不思振作,依然故我,无所作为,得过且过,西方列强打来了,逆来顺受,屈从资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听任外人宰割,使国家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在当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还只有英国,美、法的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德意志和意大利尚未完成统一,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在20多年之后。从时代的机遇来说,发奋图强,走前一条道路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个发展的最好机遇,是被耽搁了。是谁耽搁了呢?蒋廷黻把它归咎于林则徐,说什么“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维新或可提早20年”。这样评价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平心而论,这个机遇的丧失,责任不在林则徐,而在当权的守旧顽固派。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在广东禁烟和抗击义律挑衅期间,林则徐发现中国的船炮不及西方,就从澳门先后购置了200多门大炮,装备了广东中路及珠江沿岸各炮台;他还购买了“甘米力治”号,将商船改为战舰;为了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技术,他还留心收集了各种造炮制船资料,准备进行仿制。直到被革职以后,他还“密陈夷务不能歇手”,建议从海关税收中拔出1/10用来制造新船炮。奕山到广东后,林则徐在他的6条建议中进一步发挥了抗夷策略,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当时叫水军)。到了浙江效力赎罪期间,他把原来收集的制炮资料交给龚振麟等,着手研究试制。鸦片战争以后,在陕甘总督任上,他还要黄冕试制成炸炮,“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这些都说明,不管他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是念念不忘为国家的振兴、富强出力的。如果清朝当局像林则徐一样,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努力效法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奋图强,中国局面将会改观。可惜计不出此,把宝贵的机遇放过了。琦善和林则徐相比,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于国家振兴自强,他从不考虑。这一点连蒋廷黻也是承认的,他认为“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33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标签:林则徐论文; 阿芙蓉论文; 道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筹办夷务始末论文; 蒋廷黻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