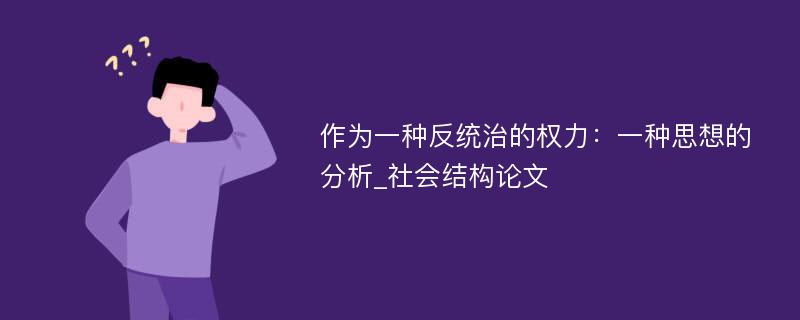
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一种观念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权力理论研究中,尽管不同思想家和学者对于支配的界定存在着差异,然而,权力通常被不证自明地理解成作为支配的权力。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作为支配的权力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权力现象,作为反支配的权力(power as antidomination)依然是可能会存在的权力形式。本文拟在简要探讨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何以可能的基础上,分析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基本内涵、现象与属性,因而对诸种反支配的行动予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以期深化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
一、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何以可能?
批判性地审视现代权力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通常不证自明地将权力理解成作为支配的权力。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①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也指出,“A拥有支配B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能够使B去做某些B否则不会去做的事情”。②彼得·布劳认为,“权力的定义应该被扩展为,通过威慑……个人或群体不顾他人反抗,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其根源是单方面的依赖。相等力量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标志着缺乏权力。”③著名权力理论家史蒂文·卢克斯则直接指出,他探讨的第三种维度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作为支配的权力,“所有留待我们去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作为支配的权力。……作为支配的权力是那种限制他人选择的能力,它通过阻止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本性和判断所指示的方式生活来强制他们或者获得他们的服从。”④由此可见,现代西方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将作为支配的权力视为权力的普遍形式,将权力等同于支配。然而,值得追问的是,难道那些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的行动者会完全顺从支配者而不会抵制或反抗那种支配他们的权力吗?难道作为支配的权力能涵盖所有的权力现象?难道社会生活中就不存在其它形式的权力?
依据上述有关作为支配的权力的经典分析,我们认为,诸如此类的权力观念存在如下问题。首先,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作为支配的权力通常是从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的角度理解权力,倾向于将权力视为权力主体控制权力客体的单向度的属性与能力,偏向于强调权力主体占有权力而权力客体则处于无权无势的状态,因而构建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权力并非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排他性的占有物,而是所有处于权力系统中的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各种权力关系看作是具有排他性的等级关系与单边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忽视存在于个人与群体之间全部的关系类型”。⑤其次,从行为的角度分析,作为支配的权力往往过于关注支配者所实施的支配行为,倾向于将权力视为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控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从处于被支配或从属状态的行动者如何应对支配的层面上阐释权力。实际上,权力更应当被看作行动者之间复杂交错的行为关系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⑥最后,作为支配的权力强调的是支配-服从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支配-反支配的思维方式,它倾向于将权力视为权力主体有效控制权力客体的稳定状况,而不是视为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支配-反支配的动态冲突过程。“权力不能被设想为可以固定不变的能力,不能被设想为某一单个的主体或者社会团体的长期的特质,而应被视为主体之间策略冲突的原则上多变的和未完成的产物。”⑦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从那些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的行动者的角度分析权力,阐释他们是如何应对支配的。社会心理学家吉姆·斯达纽斯与费利西娅·普拉图在研究支配者与从属者的行为时指出,“社会等级主要不是通过支配者的压迫行为来维持,而是通过从属者恭顺而奉承的行为来维持的。”⑧在任何社会中,尽管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集团或个人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确立了基本框架,但是,他们不能完全控制整个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舞台,那些处于不利状况的行动者依然能够动员某些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并且力图实现其预期目标。吉登斯在社会系统的控制辩证法中指出,“所有的依附形式都提供了某些资源,臣属者可以借助它们来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活动。”⑨在这种意义上,那些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的行动者并非仅仅是被动的服从者,他们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运作空间来谋取他们的利益,表达他们对于支配者的肯定、蔑视、怨恨或者不满,从而参与构建或破坏权力关系。佩德罗尼在研究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参与教育券计划时指出,“他们虽处于被压迫地位,但并不欠缺政治智慧,因此常对权力者采取一些战术行为。在权力者所给予的空间中,他们或者让权力者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让其为己代劳。”⑩所以,在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A命令其他行动者B的情况下,如果B顺从A的意图,那么,就表明A拥有支配B的权力;但是,如果B不顺从A的意图,而是实施反抗A的意图的行动,那么,一方面,A实施其意图的效果就会受到约束,另一方面,B则可能通过反支配的行动获得某些物质利益或象征利益。基于此,那些处于权力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普遍存在着既具有暂时稳定性又具有持续冲突性的支配-反支配的互动: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致力于实现支配,而那些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既可能服从支配,也可能抵制或反抗支配。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权力系统中,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者所实施的反支配的行动能否称为反支配的权力呢?从权力所体现的能力的层面上讲,“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11),“权力所涉及的是某个或某些行动者可能会运用也可能不会运用的才能或者能力。”(12)毋庸置疑,任何反支配的行动都能够影响他人所实施的支配性权力,能够介入或干预特定的支配性权力的运作,可能会通过公开的或隐蔽的反支配的策略与技巧挫败支配者的意图,因而改变既定的事态或者事件的进程。在这种意义上,那些抵制或反抗支配的行动者也就构建出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正如阿伦特指出的,“民众对于在物质上强大的统治者的反抗可以产生出几乎不可抗拒的权力。”(13)由于权力涉及行动者、行为与结构三种基本要素,所以,我们将分别从上述角度阐释作为反支配的权力,说明其存在的可能性与内涵。
第一,从行动者的角度讲,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意味着,那些处于被支配或从属状态的行动者会抵制或反抗实施支配的行动者,迫使他们做出某些让步,挫败他们预期实现的目标。
在社会生活中,“成为行动者就意味着,人们可能会接受那些决定着其生活的约束与可能性,也可能会运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变革其中的某些事情。”(14)任何支配性的权力体系都不是完全封闭的与僵化的,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能够吸纳部分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的人,使他们有机会拥有某些支配性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处于被支配或从属状况的行动者可能会适应与顺从支配者,或者通过社会流动拥有某些支配性权力。但是,部分行动者仍然可能采取行动抵制或反抗支配者。所以,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针对他人实施支配行为时可能不会获得服从,而是会被他人实施各种反支配的策略予以回应;那些抵制或反抗支配的行动者则既具有实施反支配的能力,又与支配者处于反支配-支配的关系中,所以,他们拥有反支配的权力。值得指出的是,在权力运用的目标上,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与作为支配的权力存在差异。当那些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的行动者采取措施抵制或反抗对其实施支配的行动者时,其预期目标往往不是支配他人,而是试图避免或者减轻自身受到的支配。当然,如果那些反支配的行动者能够塑造出足够强大的权力,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抵制支配,而且可能会与先前的支配者形成均势状态,甚至可能对其实施支配。在这种状况中,原来的被支配者或从属者可能转变为新的支配者,作为反支配的权力就可能转变成作为支配的权力。
第二,从行为的角度分析,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会体现为反支配的行动,不仅意味着社会行动者会在程序上抵制对他们实施支配的行为,而且意味着会在实质上反抗那些违背其利益的行为。
在权力状态中,人们直接或间接体验到的往往是行动者运用或不运用权力的行为。所以,我们有必要从行为的角度分析反支配的权力。当代政治哲学家菲利普·佩迪特指出,从支配者的角度讲,任何支配都存在下述三方面的特征,即,(1)他们拥有干涉的能力;(2)确立在一种专断的基础上;(3)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有权做出某些选择。(15)依据佩迪特的分析,作为支配的权力实际上被等同于支配者拥有专断的干涉能力,可以违背被支配者的利益对其实施专断的干涉。“当我们说这是一项建立在任意基础上的干涉行为时,我们指的是它完全出于行为主体的喜好,特别是,对他人之干涉的实施与否根本不考虑对方的利益或观点。”(16)基于上述理解,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意味着,那些处于被支配状态的行动者将会在两方面采取反支配的行动:一方面,他们会在程序上确立相关规则,否定支配者对其实施任意的干涉;另一方面,他们会在实质上采取行动抵制或反抗支配者实施违背其利益的行为。
第三,从结构的角度分析,作为反支配的权力可能会否定与变革各种支配性的社会结构,调整那种导致支配的规则与资源的配置方式。
在权力理论中,那种将行动者与行为置于权力分析的中心的做法往往可能忽视社会结构对于权力的塑造作用。“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17)任何社会行动者运用权力实现其目标的行为都不仅是其意图的产物,而且是在既定的规则与资源组成的社会结构中运作的。“支配所以必须被理解为结构性的支配,其原因恰恰在于,人们所经历的约束通常是许多人有意的或无意的产物。”(18)因此,权力不仅表现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而且会存在于社会结构中具有稳定性的角色、职位、关系与机制中。在这种意义上,权力是内在地嵌于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行动者依据他们在结构体系中的角色、职位、关系以及相关的机制而具有行动的能力,可以做出命令、服从、抵制或反抗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有学者从这种角度指出,“社会权力应当依据那些构成行为互动的潜在的社会关系而在关系之中加以理解,而不是依据那些存在于处在分离状态、彼此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行动者的行为中的偶然的规则加以理解。”(19)基于上述原因,作为支配的权力是行动者在既定社会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它既符合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集团或个人的物质利益和象征利益,又有助于维护那种具有支配性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所以,从结构的角度分析,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意味着,那些反支配的行动者可能会抵制或反抗那种再生产出具有支配性权力的社会结构,否定那种导致行动者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与行为的结构性基础,变革具有支配性的规则与资源的配置方式。
总之,从规范意义上讲,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既可能体现为抵制或反抗支配者,也可能是在程序与实质上抵制或反抗各种支配行为,还可能是否定与变革那种再生产出支配性权力的社会结构。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是从社会行动者之间支配-反支配的辩证角度探讨权力的,为有关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的分析提供了空间,有助于对具有连续性、动态性的权力斗争机制与过程进行描述与阐释。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支配是一种在本质上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人们特定的利益和价值判断,所以,人们对于何谓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认知与评价必然存在争议。
二、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现象分析
从观念分析的角度讲,我们不仅需要阐释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何以可能,分析其内涵,而且需要剖析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描述性现象。这就是要追问,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会表现为哪些社会与政治现象?应当如何对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现象进行归纳分析?
从经验现象上讲,作为反支配的权力通常表现为社会行动者之间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有组织的集体冲突行为。在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运用中,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与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的行动者之间往往存在直接的、明显的冲突:支配者试图使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服从其命令,然而,由于被支配者或从属者的抵制或反抗,他们并没有完全成功地实现其意图。在宽泛的意义上,革命、反叛、组织罢工、游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等都属于明显的、有组织的反支配的权力形式。当然,它们在行动者之间的冲突程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其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与所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革命是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典型,它表现为高度组织化的、要求在根本上变革支配性权力的集体行动。相对于革命而言,反叛的组织化程度也相当高,它的目标往往是试图取代原先的统治者而成为新的统治者,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支配性的权力体系。组织罢工、游行示威与非暴力不合作等通常是对统治者的集体问责和抵制,它们往往会使部分公众关注的议题得到重视与实现。“公众游行示威是一种最重要的并且通常是最有效的表达反对与批评的方式,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责问那些有权有势的行动者的方式。”(20)值得指出的是,组织罢工、游行示威与非暴力不合作等有可能会得到既定制度体系的赞同或默认。例如,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抗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意义上的反支配的权力的运用。
然而,作为反支配的权力并不必然表现为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有组织的集体冲突行为,它也可能体现为社会行动者之间隐蔽的、非正式的冲突行为。在这种状况下,被支配者或从属者会以低姿态的、非正式的方式抵制或反抗支配者,而不是公开地、明显地反抗支配者或权力体系。当被支配者或从属者如此行为时,他们往往意识到自身与支配者存在利益对立,但是,他们不敢或不能通过公开的、明确的集体行动实施抵制或反抗,而是在物质与象征的层面上利用心照不宣的、默会的知识进行持续不断的日常反抗。诸如此类的反抗主要表现为零星的怠工、偷窃、装糊涂、制造谣言、伪装顺从以及背后议论等方式。詹姆斯·C·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抗争时指出,“如果斗争是公开的,那就极少是集体性的,而如果斗争是集体性的,它们就极少可以公开。两者相遇几乎等同于‘意外事件’,结果通常是不了了之,并且作乱者会在黑暗或匿名的掩护之下逃离,消失在‘老百姓’的保护层中。”(21)那些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的行动者所以如此行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往往缺乏相关的社会网络、技术与策略实现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由于反抗的代价是高昂的,因而需要规避公开反抗所存在的风险。通常而言,尽管像这样的抵制或反抗行为不会产生出像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支配的权力那样重要的变革性的后果,然而,它们往往会约束支配者的决策选择范围,在不同程度上挫败统治者实施支配的行为,同时可能使被支配者或从属者获得某些物质或象征层面的利益。在这种意义上,诸如此类的抵制或反抗也属于反支配的权力的表现形式。
除了表现为上述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隐蔽的冲突行为外,作为反支配的权力还可能意味着社会行动者之间存在潜伏着的或潜在的冲突。通常情况下,“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的时候亦如此”(22),“在相对稳定的基于群体的社会等级中,从属者的大多数活动可以被视为与基于群体的支配系统的合作,而非对这一系统的破坏。”(23)在作为支配的权力体系中,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所以不会反抗,其原因可能是如下几种情况。首先,由于权力体系会塑造社会成员的意识,使其形成负面的、扭曲的、边缘化的自我形象,所以,被支配者或从属者可能会形成适应性偏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与支配者存在利益对立。其次,被支配者或从属者在既定社会中可能会获得某些物质利益或象征性的回报,或者可能通过社会流动而拥有某些支配性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认同既定的支配体系而不会抵制或反抗。再次,被支配者或从属者认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他们对于支配者心怀恐惧或意识到反抗的成本过于高昂而不敢实施反抗。或者,某些被支配者或从属者可能会运用机会主义的策略等待其他社会成员采取反抗行为,而他们则试图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取部分反抗的成果。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些共同利益,两者之间并不完全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吉登斯曾指出,“权力并不是必然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冲突是指利益的分划,还是指各方积极的斗争;而且权力也并不一定是压迫性的。”(24)马克思在分析国家理论时也认为,“包含着特殊利益的普遍利益本身就是国家的目的”,而“没有这一目的,国家就不是现实的国家。”(25)尽管上述原因使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不存在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隐蔽的冲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潜在的或潜伏着的冲突,也不表明不会潜藏着作为反支配的权力。其原因在于,权力具有潜在性,它可能会被激活,也可能不会被激活。在作为支配的权力体系中,一旦被支配者或从属者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并试图实现其利益,那么,他们就可能不再会顺从和恭维统治者,而是通过明显的或隐蔽的方式予以抵制或反抗。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既可能体现为制度外的抵制或反抗行为,也可能是在既定制度体系内部的反支配的机制或行为。在政治体系内,某些掌握权力的行动者可能会违背既定的规则,恣意运用权力为个人或群体牟取利益。这就需要设置相应的制度与规则予以控制。例如,我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现代西方实施的分权制衡制,都是为了防止某些行动者违背既定的制度安排滥用权力而在体制内部设置的反支配的机制。诸如此类的制度内的反支配的权力是由法律授权允许特定行动者在授权范围内运用的权力,是制度体系内部具有的对抗性的权力。虽然这种制度体系内部的反支配的权力可能会影响到决策制定及其执行的效率,但是,它也有助于监督拥有权力的行动者,避免或削弱其专断性与恣意性。
由此可见,从经验现象上讲,作为反支配的权力通常既表现为社会行动者之间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隐蔽的冲突行为,也可能表现为他们之间潜在的或潜伏着的冲突;既可能以抵制或反抗既定行动者或权力体系的方式存在于特定制度体系外部,也可能由于被授权或者默许而存在于特定制度体系内部。作为反支配的权力强调了行动者之间存在着支配-反支配的具有连续性的动态过程,它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权力格局中会体现为不同的策略、机制与过程。就像蒂利针对抗争政治所描述的那样,“抗争中的所有各方都始终不断地在创新和谈判协商,彼此间常常试图说服、阻止、挫败、惩罚对方或实现合作。此一连续不断的互动使得抗争政治成为一场动态的戏剧,而不是毫无目的的重演老剧本。”(26)
三、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具体属性
在对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可能性、规范性内涵与描述性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可能会追问,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拥有哪些具体属性呢?它具有哪些特征呢?我们下面将简要分析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具体属性与特征。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意味着社会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自身与支配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对立,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抵制或反抗具有支配性的行动者、行为或结构的意愿。“反抗的日常形式与那些更为戏剧化的公开对抗方式的共同之处当然在于它们旨在减少或拒绝来自上层阶级的索要或者对上层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27)在具有支配性的权力体系中,被支配者或从属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与支配者存在利益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采取行动抵制或反抗支配者,而是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既定秩序的维护者。在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体系中,无论那些反支配的行动者是采取公开的行为还是运用隐蔽的行为抵制或反抗支配,无论他们是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还是运用怠工、偷窃、装糊涂、虚与委蛇等非正式的、低姿态的反抗,他们都意识到自身与支配者存在利益冲突,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抵制或反抗支配者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当存在着支配性的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即使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未能认识到自身与支配者之间的利益对立,不存在反支配的意愿,然而,由于他们一旦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就可能实施隐蔽的或公开的反抗,所以,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也可能潜藏于其社会结构中。
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不仅表明社会行动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具有抵制或反抗支配者的意愿,而且意味着他们具有针对支配予以实施抵制或反抗的能力。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所以能够支配他人,其原因在于他们有能力动员更多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影响和控制他人:他们要么能够在决策过程中控制他人的主张,要么通过资格限制或议程控制的方式将他人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要么通过教育、习俗或宗教等方式塑造与规训他人,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暴力与威慑的方式迫使他人服从。针对上述状况,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意味着,被支配者或从属者不是毫无应对能力的,他们也拥有动员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抵制或反抗支配者的能力,能够通过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有选择地回应支配者。通常而言,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主要体现为被支配者或从属者将自身诉求合理化的能力、沟通能力、动员能力与整合能力。由于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所能动员的资源存在着差异,所以,他们会拥有不同的反支配的能力。
除了上述特征之外,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也涉及社会行动者之间反支配-支配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支配性的权力都可能会或强或弱地引起反支配的行动。正如福柯指出的,“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至少潜在地意味着斗争的策略。……在任何时刻,权力关系都可能成为两个对手之间的对抗。”(28)从本质上讲,作为支配的权力与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意味着行动者之间具有支配-反支配的矛盾,存在着对抗性。“事实上,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行使权力的人与抵制权力的人之间的平衡状态。”(29)在既定权力体系中,当作为支配的权力与作为反支配的权力的对立关系超越一定限度而失衡时,原先的被支配者就可能通过支配先前的统治者而成为新的支配者,形成新的支配-反支配的关系。从经验层面上看,那些实施反支配的行动者通常未能彻底变革具有支配性的权力体系,其结果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再生产出作为支配的权力体系。在现实社会中,革命、叛乱或造反等反支配的行动通常可能表现出这样的情形。
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体现了行动者具有的反支配的意愿、能力与关系,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运用方式。在作为支配的权力的运用上,支配者可能采用暴力、威慑、操纵、诱导与说服等方式实现其意图。在由支配-反支配的关系构成的权力系统中,一旦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意识到自身与支配者之间的利益对立而抵制或反抗支配者,那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有能力识别支配者所运用的支配方式,并且动员各种资源予以回应。由于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与作为支配的权力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在抵制或反抗具有支配性的行动者、行为或结构的过程中,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既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诸如暴力、威慑、操纵、诱导与说服之类的方式回应支配者,也可能采取怠工、偷窃、装糊涂、制造谣言、伪装顺从以及背后议论等方式实施隐蔽的反抗。作为反支配的权力采取何种方式实施抵制或反抗取决于既定的权力格局,取决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从属者之间的力量对比。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反支配的权力不能被等同于反支配的自由或反支配的权利。反支配的自由既可能意味着行动者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实现与支配者的隔离而享有自由,也可能意味着由于特定的制度、法律或习俗而使行动者拥有反抗支配的自由:就前者而言,那种由于隔离而实现的自由是与权力不相关的,因为权力必然意味着人们是处于共同生活状态中的;就后者而言,反支配的自由必须以反支配的权力为基础,其原因在于,自由实际上是以受到权力的保障为前提。巴伯教授曾经论证指出,“个人自由不是参与政治行动的前提,而是它的后果。”(30)同时,反支配的权力也不能被等同于反支配的权利。从权利实践的经验分析,任何权利都不是天赋的,其“形成与实现都要依赖于社会现实权力结构的状况”。(31)换句话说,社会行动者享有权利的基础是他们拥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不可能保障权利的实现。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所以拥有反支配的权利,其原因在于他们具有反支配的权力。
总之,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形式,它从被支配者或从属者的角度出发分析权力现象,展现出被支配者或从属者所具有的反支配的意愿与能力,揭示出社会行动者之间存在着支配-反支配的对抗性的权力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反支配的权力是对各种支配性权力的抵制、反抗与冲击,它通过各种抵制或反抗的方式使那些涉及被支配群体或从属群体的议题被大众所知悉,有助于保障那些处于不利状况的社会成员的权益。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②Robert Dahl,The Concept of Power,Behavioral Science,2,1957,p.201.
③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8~179页。
④Steven Lukes:Power:A Radical View,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86.
⑤Dennis H.Wrong,Some Problems in Defining Social Power,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3,No.6(May,1968),p674.
⑥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⑦阿克塞尔·霍耐特:《权力的批判》,童建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51页。
⑧(23)吉姆·斯达纽斯、费利西娅·普拉图:《社会支配论》,刘爽、罗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⑨(11)(2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377、377页。
⑩迈克尔·W·阿普尔等编,《被压迫者的声音》,罗燕、钟南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12)Steven Lukes:Power:A Radical View,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64.
(13)Hannah Arendt,Human Condition,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8,pp.200.
(14)(20)Iris Marion Young,Inclusion and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01、47.
(15)Philip Pettit,Republicanism: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53.
(16)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刘训练译,载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7)Anthony Giddens,The Structure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e,Oxford:Polity Press,1984,p.377.
(18)Iris M.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32.
(19)Jeffrey C.Isaac,Beyond the Three Faces of Power:A Realist Critique,Polity,Vol.20,No.1(Autumn,1987),p.22.
(21)(27)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39页。
(22)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0页。
(26)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28)Michel 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Critical Inquiry,Vol.8,No.4(Summer,1982),p.794.
(29)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分析》,陶远华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30)Benjamin R.Barber,Strong Democrac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5.
(31)王莉君、孙国华:《论权力与权利的一般关系》,载《法学家》2003年第5期,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