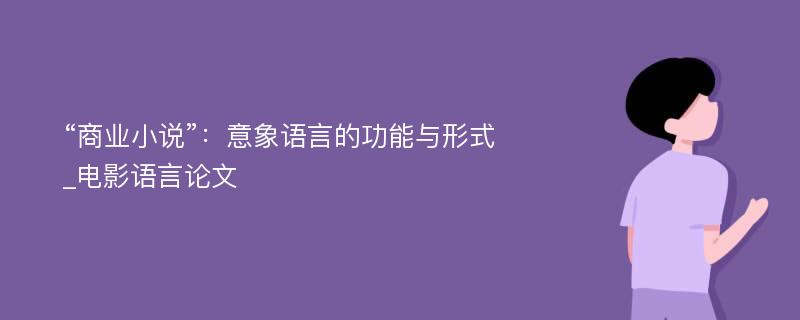
“商业性虚构”——在影像语言中的功能与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性论文,形态论文,影像论文,语言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自古就不是现实的同义语。即使就是那些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依然把艺术称之为“压严的谎话”(巴尔扎克语),哲学家说得更彻底,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就是“要把谎话说圆”。可见,确认艺术的非现实性早已是人们的共识。
在传统艺术的领域内,虚构的主要职能是完成对作品情节的合理化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完整化。虚构的主要职能是完成对作品情节的合理化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完整化。虚构的主旨是针对艺术本身,虚构是艺术的自律,虚构的目的是为了使作品更真实、更生动、更感人。而在艺术进入商业化的市场时代后,虚构的基本职能便产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影视作品中,单纯的所谓艺术虚构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商业性虚构”,也就是说,虚构在完成它传统意义上的职能之外,现在还兼任了“第二种职能”。
1 所谓“商业性虚构”,或者说影像作品的商业性编码程序,在语言功能上,主要是利用影像的“拟真性”和“梦幻情景”弥合现实生活中既定的种种裂痕。在电影院里,观众席间的黑暗与银幕上耀眼的影像,给处于黑暗之中的观众创造了一种隔绝感,仿佛他们身处一个隐秘的位置,进而激发了观众进行窥视的幻想。同时,如同白昼般的银幕世界又造成了观众如置身其中的幻觉,加上常规影片所建立的一整套诱导观众的叙事成规,更强化了观众对电影的心理迷恋。在电视的观看语境中,梦幻情境被彻底打破了,观众大多是在没有任何隔绝和隐秘的心理状态下,确切地说是在家族成员的包围之中、在明亮的室内、在各种活动都如期进行的情况下观看电视。在这种语境中,黑暗/耀眼的两极世界解体了,如梦的幻觉破碎了。电视剧,这个不折不扣的家庭剧场给它的观众造成了更加透明、更加公开的观看条件。不过,从潜意识上讲,人们都有保留对电影的那种幻觉化的观看/窥视情境的欲望。所以,与电影相同的心理的期待也依然如固。如果说电影院的观看语境与影片叙事成规共同构成了观众对电影的迷恋。那么当幻觉般的观看语境不再完整存在的时候,电视剧唯有靠它的“拟真性”和更加巧妙的叙事魅力来抓住观众。为此,电影中诱导观众的叙事成规在电视中只能更加成熟,更加“完美”,这样才能相对地降低语境中的“噪音”对故事的干扰,弥补缺失的幻觉化的观看机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影像的叙事与诱导法则,“商业性虚构”成为大众传播媒体中的主要策略,它是外在商业化电视制作机制内化为影像语法的重要标志。制作者也只有依赖这种方法才能保证节目的收看率,获得保证其生存的广告资金。
人们通常认为商业性、娱乐性的影视作品是逃避现实、脱离现实的,这种判断其实并不准确。应当说那些商业性的影像艺术不仅没有逃避、脱离现实,相反它是在普遍地、及时地触及现实,从而使叙事本文与社会本文相互接壤、叙事主题与社会主题相互吻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影像的神话。这就是说,它回避的不是现实问题本身,而是现实问题的实质。人们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所经历、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商业性的叙事本文中都演化为一种给人观赏的“欲望对象”:人自身的危机与机遇、家庭的分裂与弥合,以及“地狱”与“天堂”不断轮回的、贫困与富有的相继呈现。在这里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为此,这里没有真正的毁灭,没有真正的悲剧,总之,没有真正的现实感!主体全部的人生体验变成了一种虚拟的语言游戏,在这场语言游戏中,序曲与尾声、闭幕与开幕是同时展开的,最终是使平衡在经过失衡之后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像在《北京人在纽约》中初到美国的邓卫回到当初王起明的地位一样,它既喻示着一场语言游戏的结束,又喻示着另一场语言游戏的开始;它一方面在进行不断地虚构,一方面通过这种虚构又在诱导观众进行不断地消费。这些有始无终的神话故事想延续多久就可以延续多久。只要消费的供求关系还存在,制造与消费的活动就不会终止。
作为影像艺术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商业性虚构”源于影像艺术所处的新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任何艺术的叙事语境都是与其生成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相互关联、相互交错、相互契合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依赖于社会经济力量来进行创作和生产的艺术形式,这种关联就更为密切。历史证明:电影与生俱来就是在经济的利益驱动下生成发展的,经济力量对电影的制约要远远大于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制约。目前,中国在经济体制上正转入一个市场化的年代,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影视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必然更加直接。在电视艺术领域,现在全国省级电视台共有741座,文艺类的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占所有电视节目的61%;其他新闻、体育、社教、经济类的电视节目占39%。1998年一年就生产了650部(9327集)电视剧。其中3集以上的中长篇电视剧421部(9073集)。占电视剧年产量的90%左右。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个政府主管部门或艺术创作单位在题材上的规划问题,而是说明目前电视剧的生产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所控制。由于许多电视台现在实行的是经济独立合算,许多栏目依赖于广告商的资金作为经费。广告商为了追求广告效应,只钟情于那些每天在黄金时段连续播出的娱乐性的电视剧,所以播出次数少,时间短,广告和赞助都难拉的电视短剧只能居于次等的地位。电视的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机制正好与电视语言上的这种“商业性虚构”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只是“商业性虚构”在艺术上一味满足观众想象欲望、排斥真正的个性创造的“退化性质”,使我们必须对其保持一种“间离”的文化立场。
2 纵观当代的影视艺术,我们会发现它们在某些地方出现了过去未曾出现过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美学风格的变化,也不是剧作结构的变化,更不是影像造型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影片受制于某种外在于影片的因素之后所产生的影片内部构成元素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电影界的主将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中出现过;这种变化在中国金鸡奖最佳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中出现过;这种变化同样在商业性的贺岁片《没完没了》中出现过。当然,也在当代一系列的电视剧中出现过。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影视艺术的这种变化证明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对影视工业的制约,同时证明的是作为一种影视艺术其语言形态的变迁。
目前中国电影、电视剧生产的经济回报主要是通过在电影和电影剧播出时的随片广告产生的,这就是说作为影视剧的一种商业性的回报方式,广告是制作者向投资方预先承诺的互惠条件。然而,广告商出于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首先注重的是商品广告在电视中的播出时间段、播出时间、播出次数及播出效果,对于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文化品位、精神指向不能说他们会全然不顾,但他们最终考虑的是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是广告给观众心理留下的“感觉印迹”。为了达到广告的这种商业目的,现在的影视剧的随片广告主要采取的是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商业性虚构”的三种语言形式:
一、分离式:它们分别安排在电影或电视剧的开头或者是结尾播出,使那些期待着收看影视作品的观众,预先或是连带着收看商品广告。但是,由于这种将作品的叙事本文和商品广告在时空结构上相互“分离”的方法,依然给观众造成一种“作品是作品,广告是广告”的心理印象,从而消弱了随片广告借助于成功的艺术作品推销自己商品的初衷。为此,这种完全分离式的播出分式,现在正在被一种相对分离的方式所替换。这就是说,许多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是首先推出作品的片头或标题,然后再插入原定的随片广告,在此之后再播正片。这样的结果是,商业性的随片广告已经成为整个影视艺术叙事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广告商在完成了他们的商业行为的同时,也改变了一代人对于影视艺术的历史记忆。在他们对影视作品的时代记忆中,商品广告成了他们记忆犹新的“伴生之物”。确切地说,广告和正片逐渐在走向“一体化”。
二、插入式:在一部影视剧的播出过程中间,阻断故事情节的正常时序,在作品的叙事情节链上,切断原有的故事线索,将商品广告插入作品的叙事结构之中。有时播出单位甚至人为地将本来完整的一部影片分为“上、下集”。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广告播出方式,首先是“间离”了观众对一部艺术作品完整的审美感受,使原本连续的、完整的、甚至是“幻觉化”的审美体验,变成了一种间断的、片段的、分离的观赏经验。特别是那些本身就具有情节性和娱乐性的商业广告,时常会与正片的内容相抵触、相悖谬,在这种双重语境中,广告对于正片意义的“消解”,其实不过就是在瞬间就完成的一次“意义转场”,一次从一种梦境向另一种幻景的“闪回”。
三、镶嵌式:所谓镶嵌式的广告播出方式,与其它广告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这种方式是在不中断作品叙事规程的情况下,以一种与叙事本文同形同构的广告“镶嵌”在作品的情节中:看过《一个都不能少》的观众,恐怕都不会忘记有一场乡村孩子争先恐后地在喝可口可乐的戏。他们用劳动挣来的仅有的几块钱买了一瓶可口可乐大家一起分享。商业的广告策略与电影的叙事策略在这场戏中得到了一种巧妙地“中和”:广告的进入既没有打乱影片的时空结构、也没有破坏影片“幻觉化”的观赏情景。没有人能够把这段情景从电影的叙事体中“删除”,因为它已经成为这部影片整个叙事链中的一环。商业化的电影运作机制就是这样通过一种外在的经济手段,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电影的内在形态,从而也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电影的心理/历史。
即使我们把种种广告片对影视的“介入”也称之为一种“商业性虚构”的话,那么这种虚构的动机并不是像传统艺术创作那样通过艺术的想象诉诸于观众的情感,而是通过精心的设置和计算之后诉诸于他们的某种“口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即对观众与广告影像之间的一种想象关系进行缝合。这就是说,喝饮料、抽香烟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极平常的消费行为,在我们的影片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诱导消费的商业性的广告策略。电影艺术家原在的主导叙事动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里,即让位于广告商的商业目的。就影片的叙事情节而言,这些段落未必是“必须”的,但从影片的整个制作体制而言,这却是一个只能“修正”而不能“删除”的部分,因为是“兑现”影片的赞助方的一种“经济契约”。这就是当今影视艺术不同的“商业性虚构”的共同实质。尽管这些广告型的情节依然还有它的叙事功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以一种非艺术的形态“镶嵌”在叙事本文中间,如果说,电影与生俱来就是金钱的产物,那么,在这样市场化的年代里它的商业本性只能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无情(狰狞)!
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经济对影视艺术的市场取向的必然结果是创作依附于市场,而依附的结果又必然是对流行时尚的附和。这不仅仅是对大众趣味上的全面附和,而且在运作机制上也同样如此。目前,许多电影的投资方不再只是要求报投入,而且开始对影片的故事情节、人物设置、拍摄地点甚至于演员的选择进行干预——经济的力量就是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制约着中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在我们的国力还不能完全为整个民族影视业的发展注入强大的经济动力的时候,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健全的、法制化的影视艺术市场的时候,这种状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还会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