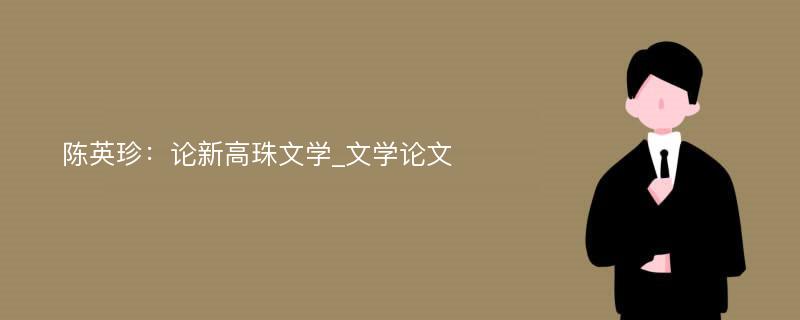
陈映真:登上新高筑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高论文,文学论文,陈映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访谈录
编者按:今年1月29日至2月2日,海峡两岸作家、学者近50人为参加“台湾文学研讨会”相聚在北京。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文学访问团成员出席了这次盛会。现摘要发表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马相武博士与陈映真的访谈录以飨读者。
“这几年我在用心探讨台湾社会理论”。
马相武(以下简称马):陈先生,您好!您来大陆有几次了吧?
陈:我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90年,当时为了思考一些问题,想亲自看看大陆;同时,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刚成立不久,也应该回来看看。此后几乎每年都来一趟,主要为了我要出版的台湾史,到厦门、北京等地找书籍、查资料。
马:您从1987年发表《赵南栋》后,发表作品较少,能谈谈您的工作情况吗?
陈:好。我自完成《赵南栋》后,基本就搁笔了。这期间,我的工作,一方面是创办人间出版社,这要付出许多心力。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在搞理论建设。
作为作家,为什么去搞理论呢。首先一点,文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正确的社会理论之上,否则,许多问题是认识不清的。然而,这样的讨论台湾基本没有,这也是第二个原因。第三,我是属思想型的作家,不能糊里糊涂地写小说,我需要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这几年我比较用心探讨台湾社会史,思考台湾社会性质,试图透过民族历史,重新发掘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文学。为此,这几年我在搞学习研究小组,名为“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一工作也很苦,但对我确实有帮助。
“我的创作也许今年进入新的阶段”
马:这样看来,您的创作是与理论研究和对社会的历史、现状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上述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为下一步创作可能提供什么前提?
陈:第一,我会对我所处的社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对它的矛盾、荒谬、不合理之处。第二,更好地指导创作,搞清楚理论,便于考虑相应的文学题材、故事、人物等。正是由于探寻了台湾社会历史,去年春季我又开始了创作。第一篇作品是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谷林山区陨落》,是写五十年代初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悲壮历程和命运的。
马:大陆许多读者渴望读到您的新作。
陈:是的。谢谢大陆读者。许多人希望我写,包括这次会议代表中的大陆作者甘铁生先生,我十分感动,我也非常想写。写作是快乐的,以文学透视人很有意思。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想法,构思轮廓也明晰了,下一步,该创作了。我的创作也许今年进入新的阶段。
马:太好了。那么能否进一步谈谈您打算具体写什么呢?
陈:我初步想先写两个题材。一是按《铃铛花》、《山路》那个系列写下去;二是面对发高烧的“台独”用讽刺手法去表现它。
马:您打算把这部小说写成政治问题小说?社会分析小说?还是人性分析小说?
陈:当然,还是要表现人的。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写一部凝聚着我对社会问题思考的人的故事。写中共地下党、写革命运动。倘若真正高扬革命旗帜,那样的故事还是要靠写人去完成的。我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台湾斗争的历史。在后来八年的狱中生活[①]中,我遇到了原来只是耳闻的共产党人。那种“共同生活”,产生了心灵的碰撞,对我有极大的震撼,出狱后,我又做过大量采访工作。《铃铛花》、《山路》就是写革命者在那种艰难卓绝的历史条件下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悲恸而动人的遭遇的。那样的历史才有这样的人之命运。
马:看来故事非常感人,您的考虑也很深刻。那么如何进行艺术表现呢?
陈:当然必须要达到较高的艺术性。将社会斗争的历史故事与人的命运、人性思考紧紧联系为一体。
马:您的小说的艺术与主题的特殊关系始终被批评家所重视。多年来,一直有人从各种角度,诸如从社会学角度、心理学角度、女性主义角度、人性角度、艺术审美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包括这次会上,也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介。
陈:我首先要把人写出来,写地下党人、革命者,写在那样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悲壮命运;然后要把故事讲述得很美,绝对不能写成枯燥的政治教科书式的政治图解小说,不会把革命者简单地写成“英雄人物”。我要使作品有一种强烈的让人感动的效果。为此,我会在这种社会性很强的小说里进行很多的艺术表现。
“乡土文学仍在作着不懈的努力”
马:目前台湾文学现状如何?您对台湾目前的小说创作有什么看法?
陈:我对近年台湾文学界年轻一代的创作并不十分熟悉。不是不屑去了解,恰恰相反。现在我太忙了,一方面搞理论,一方面要面对生存问题。在台湾生活是要靠自己经营的。新一代作家们的作品我基本上都买了,我会认真读的。
至于目前台湾文学现状,有这样几点:第一,严肃性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太多,创作上基本上是外国有什么,台湾就要有什么。似乎照“定单”出“货”,如同性恋题材,写得很大胆,而有的作者还太年轻,台湾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也是皮毛的。完全呈现的是“玩”的心态,认为这是潮流。当然,相信这些东西中也不乏有价值的。第二,文坛“台独”倾向也很明显,出现了这方面的作品。第三,比较自然的情况,是随着台湾社会都市化而趋于大量出现通俗的文化创作,多抒写都市里男女爱情。第四,出现“小说族”,这种小说创作,热衷于轻薄短小,故事性强,既不赤裸裸的,也非纯情的,多抒写的是小情小调,主要阅读对象是青年女工和学生。从创作、出版到阅读,都具一次性的特点,一个出版社一般是一套丛书、一套丛书地出来。往往一个作家一本书一本书地出版,每本很薄,封面包装十分商业化。对出版社来讲很赚钱。第五,虽然台湾社会还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但世界性影像传播也冲击到台湾,影像媒介竟慢慢占据主导,代替了文学原来的位置,特别是“画面化”,视觉效果强,代替了思考。这是文学写作没落的征兆。
马:那么目前台湾整个文艺思潮有什么动向?
陈: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乡土文学论战后一直影响台湾文学的乡土主义,这是针对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乡土文学仍在作着不懈的努力;二是体现“台独”反动政治思潮的文学流派;三是思想倾向中立,独自搞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
马:各种文学思潮在台湾的发展情况如何?
陈: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比较多。“台独”文学会被历史所否定。乡土文学一直不懈地努力着。包括三方面:第一,努力筹创一个理论与创作都很高档的刊物;第二,对乡土文学论争以来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整理思考;第三,鼓励创作,试图与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客观交流。真正实实在在地承传日据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不能没有实绩,应从理论品质、知识品质、创作品质诸层面上争得大学生和其他青年读者。所以搞读书会,包括有关书籍的阅读、报告会的组织,要培养几个笔杆子,争得理论评论优势。台湾文学的未来,属于新一代台湾乡土作家。
马:台湾严肃文学现状如何,未来命运怎样?
陈:这里有一点需要明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还是一样的。台湾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文学的人口及其年龄的流动,没有固定的或终身的对文学的兴趣等等。大陆“伤痕文学”在社会上的巨大轰动效应,台湾文学界没有,也不会有。世界文学作品在台湾销路也不好。在台湾,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情形过去了,文学越来越边缘化。这就决定了台湾严肃文学的命运不容乐观。
马:大陆小说作家“触电”情形很多,而且有些成功了。台湾文学与电影电视相联系的情况如何?这次会上听说,大陆有人想把您的《赵南栋》拍成电影,据说剧本都有了。
陈:像大陆如此的文学与电影成功的结合,在台湾还没有。甚至相反,台湾电影文学创作是专门有人经营的。有些文学作品一改成电影反而糟糕。
“两岸往来及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意义重大”
马:您对海峡两岸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怎样看的?
陈:两岸同一血脉,我们的祖地在大陆,台湾的根在大陆。两岸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岸的往来有很大改善,这是必然的。两岸往来及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意义重大。我几次来大陆,深深感到,两岸的交往,文化和文学的交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华文化的根和优势在大陆。随着社会发展,民族优秀传统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在大陆得以承传。第一次看《高山下的花环》时,我们都很感动,我为其中表现的那种精神和气势深深震撼了,这种文化艺术传播的效果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还有这次会间观看的北京曲艺,其艺术魅力好厉害,台湾没有。大陆的舞台剧一直在发展,而在台湾,因其特殊的作用,国民党一直限制。相对而言,台湾的音乐很发达,世界名乐团几乎都曾到过台湾,台湾的音乐市场还是很大的,台湾的儿童合唱团、交响乐团还是不错的,都到大陆演出过。但是大陆的专业音乐团体水准更高。我是非常佩服的。
从文学方面看,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关注很有成就,出了那么多作家和那么多作品,文学史也编写了好几部。台湾也出版大陆作家的作品。当然,文学的交流因时空所限,也有一定困难。我们希望写一本大陆的当代文学史,搞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还想研究一下大陆当代文学论争的情况,在发展原作基础上进行综述和评介,想做的工作的确很多。不经过这样的努力,两岸文学达不到真正的交流。另外,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团作研究访问,比如这次就很好。我们这次来是认真准备的,来后经过两天的研讨,感到效果很好,增进了交流和认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以后,我们也会请大陆同行学者到台湾来,进行实地考察研讨。
注释:
①1968年,陈映真被台湾当局以阅读毛泽东和鲁迅著作、“涉嫌叛乱”等莫须有罪名逮捕,在土城、屏东、火烧岛的监狱遭监禁折磨达8年之久,于1975年获释放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