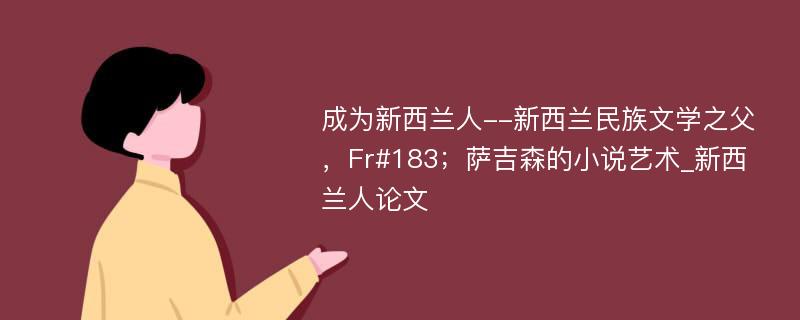
做一个新西兰人——新西兰民族文学之父弗#183;萨吉森的小说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西兰论文,做一个论文,之父论文,民族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西兰文学史上,弗兰克·萨吉森(1903—1982)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新西兰民族文学之父”。在我们中国读者之中,萨吉森似乎还鲜为人知,而他在英语国家里却早已闻名遐迩。他是新西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家,是新西兰文学由殖民文学转向民族文学的轴心人物。他的创作立足于自己的祖国新西兰,以本国同胞为其读者对象,用新西兰英语特有的表达方式进行创作,他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很好地体现了新西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萨吉森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新西兰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家立足生存,因为无论是好是歹,我命中注定属于这块土地。”(注:Frank Sargeson,Never Enough,Wcllington,All and A.W.Rccd,1976,p.48.)
萨吉森的早期生活值得一提,这不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他的作品,更主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新西兰作家的成长,以及一个历史并不悠久的国家的文学创作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艰辛。1903年3月20日萨吉森出生于新西兰北岛的汉密尔顿市,在那儿长大, 后来在奥克兰完成学业。刚满二十岁,他就找到了助理律师的职务,但是他从未办过案子。他没有按照父亲为他设计的路线走下去,他并不满足于在新西兰的美好前程。他当时认为,那种古板而毫无生气的安闲生活对他而言,实际上就是精神死亡。那些年他彷徨苦闷,思索人生,苦苦求索答案。他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可是不久就脱离了。1927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前往宗主国英国“寻根”。但当他到达英国后,发现欧洲的现实与新西兰人印象中的“样板社会”截然不同,自己同这里的社会环境也格格不入,第二年他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新西兰。他回国后不久,新西兰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为了维持生计,萨吉森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他当过农场帮工、菜农、送奶员、餐厅助手、杂工等。正是由于早期这些经历,萨吉森才有机会深入新西兰各个社会阶层,了解人民大众,观察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语言。1933年,他在奥克兰附近的塔卡普拉镇定居,并从此全力投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萨吉森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他写的全是短篇小说。这个期间的小说基本上取材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体验。小说背景是他熟悉的小城、农场,小说人物往往如同年轻时的萨吉森一样,是个单身工。他们所从事的也是作者本人曾经干过的职业,思考的也是作者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小说的主题反映的是经济萧条、战争、贫穷、虚伪的宗教、爱情与婚姻、死亡等。从40年代末至70年代,萨吉森主要创作的是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所展现的视野更为广阔,对人们所思索的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作者的创作技巧也更为完美。它们反映了新一代新西兰人在心理上、认识上的成长过程,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虚假道德观导致的人性的泯灭,赞颂了新一代的奋斗精神和对清教主义义无反顾的叛逆精神。
一般说来,萨吉森的短篇小说很少有超过两千字的。最长的当推《伟大的一天》、《好心人》、《少校的女儿》等,不过它们也仅在三千字左右;而最短的,如《一块黄皂》、《乔叟学者》等只有几百字。这说明他是个语言高手,他对自己笔下的每句话、每一个细节都高度重视,作出了高度概括。他从不利用跌宕起伏的情节或者出人意料的故事收尾去吸引读者,他信奉的原则就是简洁明了。萨吉森的所有早期短篇小说,都是在努力刻画一个“新西兰人”的形象。虽然作者在作品中使用了不同姓名的人物,但他们的入世态度、社会境遇、文化教养、家庭背景甚至年龄都十分相似。他们经常流浪于街头,栖身在马棚或车库里。那是一个孤独的世界。他们之所以孤独,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邻居,而是因为没有“一根线”去把他们与整个社会相联,人与人之间是那么的疏远,缺乏共同的目标,缺乏公认的生活价值标准。小说人物都是贫穷失意的无辜者,站在富有而伪善的社会上层的对立面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新西兰人,与传统的英国小说人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点也不像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他们总是被社会踩在脚下,个个具有反叛性格。
《一块黄皂》发表于1940年,故事简单,就像一幅素描。但是它留给读者的思索空间是巨大的。故事的叙述者是个送奶工,每周都要为公司向订奶户收款,但他从未从一个洗衣妇那儿收到过一个小钱。洗衣妇总是站在门口,“眼睛像两块石头”,泡得又白又胀的大手总是捏着一块黄色的肥皂,既不躲避,也不央求,一言不发地站在阶梯上。送奶人要是与她争吵的话,她就会把黄皂捏得更紧。在这篇四百多字的小说里,这块肥皂实际上象征着那个年代新西兰人民的艰苦生活。面对这个麻木的贫苦妇人,送奶人怎能忍心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据理力争,进行索讨呢!叙述者在小说结束时尖锐地谴责了人间的不公:“她现在已经死了。如果她能上天堂,我不真不知她是否带着那块黄皂。我说不准自己是不是相信天堂或上帝,但如果上帝是个有情感的人,我相信当他看到那块黄皂时,也会感到羞耻的。”(注:Frank Sargeson,The Storiesof Frank Sargeson,Penguin Books,New Zealand,Auckland,1982,p.13.)
《乐善施好者》是萨吉森早期短篇小说中一篇十分有趣的探讨人们道德行为的小说,语言简洁优美。叙述者的朋友琼斯,虽然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他讲到几天前一个晚上他路过垃圾堆旁时,看到一个穿粗麻布的男人躺在地上呕吐不已。令琼斯后来一直难受的是,他当时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那人身边转了好几圈后继续走他的路。琼斯与叙述者之间的对话构成了整个故事。但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刻画了琼斯内疚不安的心理与叙述者“我”的麻木不仁,这种对照深化了主题思想。当读者阅读到他们的对话时,也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参与他们的讨论,表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叙述者一再说:“这种事太多了,忘掉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潜在的讽刺,它揭示了一个道德观问题:人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好自己的动机与行为、理智与本能、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在《一个好男孩》里,一个从不想做好孩子的男孩正在撰写自己的故事,因为他想让他的小妹长大以后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他后来杀死了一直与他热恋的女友。故事中多次出现了父母和社会惯常使用的“好”这个词。萨吉森在这里不仅仅向人们展示了青少年犯罪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提出了“正确”与“错误”这个概念的不同解释。这个故事是对人们陈旧的、惯常的那种道德行为的极大讽刺。作者不仅仅嘲笑了孩子父母所谓“做个好人”的那些陈词滥调,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的迷茫进行了无情的攻击。
《好心肠的人》是萨吉森于1941年首次在澳大利亚发表的短篇小说。在这里,萨吉森把原先自己那些社会寓言类的小小说提升至内容更加复杂、意义更加隽永的艺术境界。作者运用高超的技巧和幽默的语言使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描述和视角相互交织,结构显得十分完整,读完令人深思。读者可能会对小说的主人公大卫·威廉这个靠种植蕃茄为生的农民的看法显得十分复杂。故事是通过一个为他干活的小男孩之嘴以及后来他长大成人后的回忆,对这个雇主的动机和行为带着半懂不懂的解释去展开的。这篇小说也是采用第一人称去叙述的。叙述者“我”是威廉新雇的唯一帮工。中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父亲就安排“我”去给一个连他们都看不起的“怪人”做帮工。故事中出现了三个人物:威廉在思想观点上并不随波逐流,以他自己的准则独树一帜;在生活上,他不甘当金钱奴隶,于是便辞职种菜,自立谋生。他的言行与“正统”相悖,代表了叙述者所追求的一种生活目标。“我”的父亲虽然不是特别富有,但却具有中上层阶级的一切特点,是个来自旧大陆、落后于时代的“英国绅士”。他性格偏执,对新思想惶惶不安。而站在这两个人物之间的是“我”——萨吉森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青年,“我”贪婪地吸取那些“截然不同但又很不理解”的新内容,与父亲开始公开对立。在殖民地后期的新西兰的典型社会环境下,这些人都具有代表意义。小说通过对红彤彤的太阳、充沛的雨水、肥沃的土地以及由此带给他们那堆积如山的蕃茄的描述,使之表面上成为对带来丰收的大地和人们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的颂歌。但是,由于产量太多,价格因此大跌,甚至卖不出去。蕃茄长得又肥又大,成熟了还没人去收割。“我”建议威廉把大半蕃茄埋在土坑里,而大卫却不听,他把洗得干干净净的蕃茄堆在门边,就像一座闪闪发光的金字塔墓碑。当大风暴把这座金字塔吹倒后,“我”与威廉就不顾一切地去拯救它,大风过后又是一座金字塔。我们可以把这座金字塔看成是劳动者的英雄丰碑的象征,他们用心血灌溉出了这堆丰硕的果实,毫无疑问,这上面闪烁着他们勤劳与智慧的光泽;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堆蕃茄外层光亮鲜艳,但在阳光的照射下,“里面已彻底腐烂”。这又象征着人类的劳动成果不幸被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所糟蹋,资本主义经济给新西兰人带来的是幻想的破灭。
《杰克挖的洞》发表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小说中的主人公杰克希望像别人那样也为战争出点力,为和平事业做点事。于是他在自己的花园里成天挖洞。可是,他自己却搞不清楚他挖洞的目的何在。他的妻子希望他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好的工作意味着更多的钱,要不就太愚蠢了。”邻居们和他的妻子一样也搞不懂这个健壮如牛的大汉成天在花园里挖洞究竟有什么目的。叙述者是杰克的一个朋友,他很知趣,从不过问杰克挖洞这个问题。因为他想,“杰克是条好汉,他想让他的花园出类拔萃。”这个故事的意义就是通过这些荒唐但却带悲剧色彩的行为体现出来的。当飞机在头顶飞行时,杰克坐在洞边对牢骚满腹的妻子说:“你要明白,亲爱的,我做的事比起那些在天上飞的家伙们干的事还重要得多,至少是一样重要的!”(注:Frank Sargeson, TheStories of Frank Sargeson, Penguin Books, New
Zealand,Auckland,1982,p.247.)更为令人发笑的是,当他把洞彻底挖好后,他又使出浑身力气把整个洞给填上,而他对此的解释居然是:“我得使自己在花园里有事干才行。”后来,当日本侵略者来空袭时,他又跑去给好多邻居挖了防空洞,挣了一大笔钱;可是他却没给自己家挖个防空洞!但小雇工并不是杰克那种人。他一直企图弄明白挖洞的目的何在——也就是人人为战争作出牺牲有无必要,是否明智。他对杰克的最后结论是:总有一天他要进疯人院。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尖刻而辛辣的讽刺。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远离新西兰,但是,当时的新西兰政府和某些“爱国者”却在盲目地忠诚于宗主国英国。而萨吉森则在作冷静的思考,对那种“爱国主义”的战争热情进行了无情的指责和批判。这篇小说看似荒诞,实际上艺术地折射了那个时代新西兰的现实生活,充满着血和泪的辛酸控诉。
《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是作者用悲剧手法创作的一个具有喜剧特色的短篇小说。故事背景是战后经济萧条时期。小说主人公泰德靠领救济金为生,当然他也找些零活干干。然而,就在他与贫困作斗争的同时,“屋漏偏又逢连夜雨”,他的家庭生活出现了危机,他与妻子分居了。他只好带上一条狗,和另外一个穷男人一道住进了别人的车库。后来,唯一的伙伴“狗”又被汽车压死,于是他又买回一只可爱的金丝雀。但是,他太信任他的好伙伴金丝雀了,他对穷朋友说,鸟儿对他很忠,即使他打开窗子也不会飞走。然而当他把窗子打开后,鸟儿终究还是背叛了他。其实,泰德本质上是个好人,他能忍受生活带给他的困苦,他不想大喊大叫、怨天尤人,只想转移自己的不快,排谴内心的烦闷,在狗和鸟身上寻找一种心灵的平衡与宁静。当然这并不能排除他实际上所持的那种“逃避生活”的态度。
从40年代末开始,萨吉森放弃了使自己成名的短篇小说创作,转而进行长篇小说、传记和戏剧创作。其中以长篇小说为主,戏剧只写了两部。那个时候新西兰已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他们也正在尝试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去写新西兰,去写新西兰人民。约翰·李写了《涉水鸟飞起来了》,约翰·马尔甘写了《孤独的男人》等。由于这个时期新西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比较明显,所以这些新西兰作家们已彻底摒弃了宗主国传奇小说的创作方法,在人物塑造上,也不采用夸张与简单化的手法,而是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再是道听途说、想象的产物,而是直接观察、体验与综合而来的结果。他们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无情鞭挞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揭露饱食终日的资产者的吝啬、贪婪和残酷的本质,及其帮闲文人的伪善的浅薄,并对新西兰普通贫民大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他们的作品真正反映了新西兰人那个时代的脉搏。但是这些作家都没有像萨吉森那样在创作时冷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世界巨变,思索新西兰的社会现实。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彻底了解新西兰,了解新西兰社会的方方面面,首先要对毁灭人性的清教主义开刀,要去冲破禁锢人们精神的高墙。因此,萨吉森的后期创作与前期短篇小说相比,在创作方法和主题上有明显不同,他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扩大和丰富了“萨吉森世界”。
萨吉森共写了八部长篇小说。《当风吹起时》是第一部,发表于1946年。这部小说探索的是主人公亨利·格里菲斯由一个少年向成年人过渡的成长过程。萨吉森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深受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影响。还是在年轻时,萨吉森就十分崇拜乔伊斯,特别喜欢乔伊斯的内心独白、意识流等现代派创作手法。乔伊斯小说中的人物史蒂芬·戴达勒斯——一个因罪恶感而深受自我折磨的无知青年的成长,激起了萨吉森的同情和共鸣。萨吉森曾经说过:“那是当我住在伦敦的出租房子里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画像’了。只不过那时只写了一章,自己尚无足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技巧。”(注:Frank Sargeson.Once Is Enough,A.H.and A.W.Reed,Wellington,1975,p.114.)他意识到仅仅靠自己的非凡记忆,写下一些自己所经历过的事实是不够的,这与乔伊斯的作品相差太远了。所以在十六年后,他的写作水平日致臻完善,对现代派技巧运用自如时,才将乔伊斯式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萨吉森的《当风吹起时》并没有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那么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和讽刺力,不过小说中的事件、遣词造句、人物形象都是作者精心谋划的结果,因此整个作品显得十分自然流畅,作者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像乔伊斯那样插入很多作者的评述。比起乔伊斯作品中的史蒂芬来,亨利虽已二十岁,但他却处处显得不是那么十分自信,他留给读者更多的却是自我怜悯,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反叛。作品的主题所展示的是如何调和主人公的物质生活与包围着他的宗教观念之间的矛盾。虽然这部作品在萨吉森的长篇小说中算不上突出,但与他的前期短篇小说相比,它的重要性体现在萨吉森以文学的形式,率先在新西兰真实地记录了被清教主义所包围的环境里一个小镇的年轻人的生活经历。萨吉森的开拓精神比起作品本身显得更为重要。
1949年,萨吉森发表了《我梦中所见》。故事的主人公叫大卫·斯宾塞。他在新西兰北岛一个偏僻的不知名的农场作帮工。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生动地描绘了萨吉森的家乡汉密尔顿市的自然风光,记录了他早年感到困惑的问题以及家乡同胞们在穷乡僻壤的土地上的艰苦生活。汉密尔顿市民居住着很多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在这篇小说中,萨吉森把这些毛利人首次写了进去,而且把新西兰十分敏感的种族关系问题展示给新西兰人民去思考、去争辩。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毛利人有独特而精美的雕刻艺术,他们演奏吉他、唱歌、跳舞,他们还能熟练地驾车。兰基,一个身患肺结核的毛利青年与叙述者大卫所工作的那个农场的白人场主之子塞德里克一起长大。两人交情甚笃,亲如兄弟。塞德里克十分喜欢兰基的毛利妻子,兰基也并不由此而仇视朋友,在他即将病逝时,他还喃喃自语:“她需要她想的人”。叙述者大卫一直感到十分困惑的是,为什么塞德里克不顾白人家族对毛利人的传统歧视,而对毛利人那么好,而且还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去娶一个毛利寡妇为妻?这个问题是留给读者去回答的,尤其是留给新西兰的白人和毛利人这两个民族去思考的。书中对塞德里克这个人物塑造得不是十分成功,他的象征意义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小说前后的情节在逻辑上不是十分吻合、协调。但是,对大卫的打工、两个毛利人的塑造、故事细节的描写是十分逼真、成功和感人的。这部作品还表明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新西兰作家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准确记录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的真实生活。
《上到屋顶又下来》发表于1951年。按照萨吉森自己的说法,这部作品展现的是“我自己感到十分独特的新西兰的东西”(
注:FrankSargeson.Once Is Enough,A.H.and A.W.Reed,Wellington,1975,p.43.)。标题中的“屋顶”代表着新西兰北岛的“国王村”,那是萨吉森的叔父的故乡,作者小时候曾在那里生活、当过帮工。这部作品叙述的是萨吉森自己在年满五十岁时,身背帆布包对故地作的一次重游。他把故地的变化看作是“天堂似的奇迹”。他的身子虽然在故地现实的物质环境里巡游,但他的精神却早已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生活。这实际上是又一部描绘新西兰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色的作品。在这里,作者把过去的所见所闻与现代文明相对照,展示了新西兰几十年人文环境和自然风光的变化过程。萨吉森在作品中谈到他小时候的几件令他难以忘怀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他曾调皮地搞破几个鸟巢而再也不能复原。作者暗示他的作品再也不能把过去的一切表述出来;于是他就紧紧围绕着一个象征物去渲染那种“奇特而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他所选择的象征物是新西兰国王村一株被毛利人称为“列瓦列瓦”的树,它的红色花瓣为当地的众多鸟类提供了花蜜。从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却把它称为“忍冬属”,这个名字使得作者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经常想起这片故土。尽管好多人都已把它的原名忘怀,但它依然存在,仍然茁壮地成长,变化的是社会、地理环境和历史。
《我亦如此》发表于50年代中期。如同他的前期短篇小说一样,萨吉森在这部作品中仍采用了第一人称去叙述整个故事。与前期故事中的“我”不同的是,“我”变成了一位女性,一个中年未婚的女教师。作家通过“我”持续五个月的日记去一天一天地展现整个故事。这种创作手法的好处在于,它让读者直接参与到女主人公的生活历程之中。作者精妙地把故事的发展线索全部隐藏起来,但是女主人公的叙述已足够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把整个情节串联起来。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个十分伤感的女人,她想说而又一直没有说出的是: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读者从小说有限的线索中可以明确地体察到:她无比敬重的父亲病逝以后,她急需一个情感焦点。她发现不管哪一天她都会想起尤莉西斯。尤莉西斯是她幼年时的同学,一个生来就痛恨男人的女孩,她现在也是教师。凯瑟琳内心清楚,但一直拒绝承认尤莉西斯也是个女同性恋者。然而她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和一个英俊的男青年手挽手地并肩坐着。那个男青年实际上是尤莉西斯女扮男妆的。后来当凯瑟琳的情感正一步一步地向这个女人靠近时,其内心的惧怕和疑惑又把她引向一个来访的美国心理学家胡伯特·诺克,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假游戏。她在一次晚会上邂逅诺克,诺克长得毫无男子汉气质,戴着一幅深度眼镜,满以为凯瑟琳会嫁给他的。他并不知道凯瑟琳曾经与一个患肺结核的小伙子科林有过十分短暂的恋情,但那时凯瑟琳只让自己那种异性恋情仅仅局限在科林卧病不起的那段时间里。不久诺克也染病入院,他们的恋情也就像幽灵穿墙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诺克马上又去追求希尔塔,却遭到后者的拒绝。就在那时,凯瑟琳被一个叫海伦的女孩迷住了。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竟是希尔塔的女儿。海伦也心甘情愿与凯瑟琳相好。这个世界就是那么狭小,海伦还有一个心心相印的女友,那就是女校长尤莉西斯。海伦的母亲对这种关系感到十分震惊:“现代社会的母亲对孩子的行为真不可理解!我的孩子告诉了我有关她的故事,那些事连我做梦也不敢对我母亲讲!”(注:Frank Sargeson,Man of England,Martin Brian and O'Keefe,London,1972,p.133.)后来,海伦邀请凯瑟琳回家玩并告诉她“应该去见见尤莉西斯”。海伦的坦率与清纯就像她的美貌一样深深吸引着凯瑟琳。凯瑟琳在日记中写道:“大概今天晚些时候我将给尤莉西斯写一封长信,湛蓝的天空阳光灿烂,树叶和花朵上的光亮是那么的迷人,简直是个奇迹……”( 注:Frank Sargeson,Man of England, Martin Brian and O'Keefe,London,1972,p.149.)这部作品妙就妙在其独特的叙事方式,故事留给读者很大的思索空间,我们在阅读时也会饶有兴趣地去探查和寻求其中的奥妙。这部小说应该说是萨吉森系列长篇小说中的成功之作。作者完全掌握着女主人公的情感,凯瑟琳的日记表述得零零碎碎、杂乱无章,但就是因为这点,才把一个受过良好传统家庭教育的女同性恋者的内心感受表现得恰到好处。总而言之,正如萨吉森的其它小说一样,主人公的矛盾性格和所不能逃避的困境不是她自身造成的,而是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的。她的心理缺陷是由本身处于病态的社会风气中而造成的:周围虚假的、非人性的社会道德观,尤其是清教主义把她原本娴静的个性撕得支离破碎。
60年代末萨吉森创作了一部与他的前期作品风格完全不一致的小说《一个劳工的回忆》。小说仍然是以第一人称去叙述,叙述者是一个十分世故、特别富有的退休保险公司职员。他追忆了从世纪初到“现在”(60年代)的个人历史。“劳工”一词与叙述者“现在”的处境十分吻合。他原来一直恪守清规戒律,使得他成了一个“精神奴隶”,一个道德上的贫民。在他的回忆中有很多暗示,表明由于社会环境,特别是虚伪的宗教观把他原来坚强的个性给毁掉了。他后来奋起反击,专门袭击那些受过正统教育且彬彬有礼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人公叫迈克·纽豪斯,他曾经是个书呆子,由具有绅士派头、举止得当、谈吐高雅的祖父母抚养长大。在豪门宅第所受到的教育比起同龄人来要多得多。当他走进社会后,他才意识到生活的现实与那些正统教育的差别有多大。他是一个性早熟的青年,他无法用祖父母的教育去压抑本能的冲动。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先是与年轻女子爱娜和毛利女孩杰西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后来则更为放荡,他常常去与那些已经生儿育女的妇人,像高尔夫人、格林巴切夫人、里彻特夫人等干那些事。他还到处勾引那些很有身份的女人,甚至强奸她们。纽豪斯在撕掉自己的假面具后,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平衡,便刻意向那些“贞洁而高贵”的女人进攻;他希望与她们一道对统治人们的精神枷锁进行反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萨吉森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的初衷了:对殖民地的“遗物”,即清教主义,作深刻的解剖和批判。
从30年代起,新西兰民族文学跃入了空前兴旺的繁荣时期,先前的涓涓细流,开始汇成了民族文学的滚滚大潮。而这个时期又是以萨吉森为突出代表的,新西兰文学界已公认他为“民族文学之父”。他的作品准确地抓住了新西兰人民特有的语言和社会特征,透彻地分析了新西兰人的处境。他所领导的民族文学的大师们最为引人注目的突破性成就表现在:第一,文学主题转向现实生活,作家直面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文学作品中排斥了乐观基调;第二,他们不再承袭英国的文学创作定式,描写对象和读者范围都转向了本土新西兰,使用新西兰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舶来文化不再充当主角;第三,塑造了令人信服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新西兰人。为此,萨吉森五十华诞时,新西兰作家们曾联名写信致贺,对他的文学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您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证明了我们的言行举止同样也是构成永恒的文学的基础,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其它国家。”(注:R.A. Copland, FrankSargeson,Wellingt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