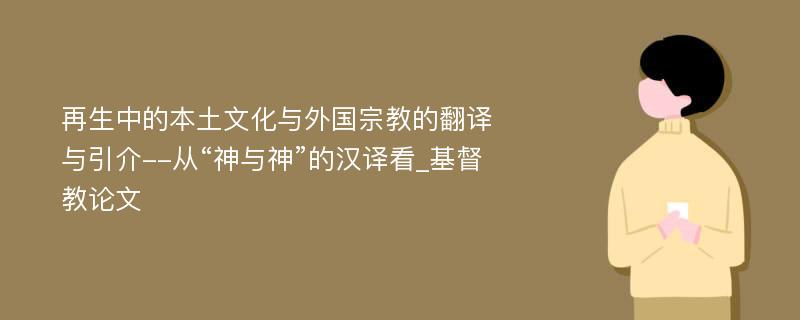
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译名论文,天主论文,异域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译是建立在对不同语言之间假定存在对等关系的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活动,在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近代中国的译介活动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欧洲语言作为主方语言,从某种意义上享有一种决定意义的特权,本土中国的任何翻译和引介活动都不再能够轻易地同西方外来语分离开来。如果一种文化语言不能服从于另一种文化语言的表述或诠释,翻译是否可能?如果东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不能成立,那么跨越东西方的现代性便不能实现。
一般的专名,如柏拉图、伦敦、动物等,在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困难基本上属于操作层面。基督宗教的最高存在“Deus”“God”这样的抽象名词,是历史长河中文化建构和宗教信仰凝聚的结晶,不存在于自然历史中,也不存在具体可目验或实证的客观所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宗教,其主神名号都是凝聚了历史、文化、信仰、教义、政治、利益等中心价值的象征,其意义不仅涉及宗教教义和经典,而且还涉及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与其说它是一个有具体所指的专名,不如说它是承纳历史、汇聚信仰的象征,其终极意义是无法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关联中得以确立的,而是取决于这个专名被普遍言说且变化无限的文化语境,以及它赖以产生、流传、变异、被理解、被误解的整个文化系统。在不同层面的跨文化对话中,都潜伏着文化相遇中自我与他者的定位问题,也都渗透着宗教同化的论争和演变。
作为以传教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性宗教,基督宗教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想要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皈依基督宗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巴别塔”不但象征着由于语言文化多样性而产生的对译介不可能性的征服和追求,对宗教者来讲也开创了历久弥新的弥赛亚式的追求,要将“Deus”“God”的话语传播给潜在的未来皈依者。而对于基督宗教以外的领地,常有一种缺乏根据的怀疑,所谓“自然宗教”的信仰者对于神圣性只有极其狭隘和低级的认知。那么,在基督宗教神启的绝对概念中,是否还给所谓“异教”遗留了宗教适应和转化的空间?具体到《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在一神信仰本源语和多神信仰译体语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中华本土文化将为、能为外来宗教文化提供怎样的借鉴和转化基础?
我们今天感知认识到的任何概念、词语、意义的存在,都来自于历史上跨越语言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相遇和巧合。这种联系一旦建立起来,文本的“可译性”意义和实践便建立了。由不同语言文化的接触而引发的跨文化和跨语际的联系和实践一旦建立,便面临着如何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被认同的过程。在《圣经》中译过程中产生的新词语、新概念将在怎样的背景下兴起、代谢,并在本土文化中被认知及获得合法地位;如何建构中国基督宗教话语体系,并在本土文化中取得合法地位?本文以基督宗教的唯一尊神的中文名称为视角,探讨在翻译介绍过程中,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借鉴交融和排拒演变,以及再生新词语被本土社会认同的历程。
一、音意译与新释:景教和天主教的译名
基督宗教曾经四次进入中国,每次都涉及到《圣经》翻译,其历史最早可溯至唐朝。作为基督宗教的唯一经典,《圣经》文本由不同时代、不同语言、不同人物历时千年写成,其中《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在基督宗教的传播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语言对“唯一尊神”的不同译写称谓,拉丁文为Deus,希伯来文为Elohim,希腊文为Theos,法文为Dieu,德文为Gott,英文为God,等等。唐朝贞观九年(635),聂斯托利派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长安传教译经。从明朝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知,他们将世界的造物主翻译为“阿罗诃”①,学者们认为这是景教传教士根据叙利亚文“Elaha”或“Eloho”音译而成的。②“阿罗诃”一词是从佛经《妙法莲华经》中借用,指佛果。由于唐朝佛经翻译的极度兴盛,景教的《圣经》翻译大部分词汇均借用于佛教。随着唐朝末年景教的消失,“阿罗诃”这个译名没有得到更多的传播。
明朝晚期,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翻译基督宗教的唯一尊神。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欧罗巴人最初用华语写成之教义纲领”——《天主圣教实录》在华刊印③,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将“Deus”译为“天主”④,这是沿用了耶稣会远东教区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在日本天主教会中使用的译名⑤。范氏认为,在远东地区不宜采取以前在其他地区的直接传教法,而应先学习当地语文,并尽量熟悉当地社会的礼俗民意。⑥学者一般认为,“天主”一词出于《史记·封禅书》中所载“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⑦
160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首次刊印了天主教教义纲领《天主实义》,第一个用“上帝”来翻译诠释了“Deus”。⑧《天主实义》是中国天主教最著名的文献,刊印多次,影响很大。书中用大量篇幅来论证佛教、道教和儒家与天主教的相似性后,认为在公元1世纪的圣经时代,中国人曾听说过基督福音书中所包含的真理,但或是由于使臣的错误,或是因为传教士所到国家对福音的敌意,结果中国人接受了错误的输入品,而不是中国人所要追求的真理。⑨利玛窦力图让中国人及外国传教士相信,从中国历史的一开始,中国人就曾被“上帝”之光照亮过,对所崇拜的唯一尊神有某种了解的愿望和记载。⑩天主教中的造物主“Deus”,就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记载的“上帝”。“天主何?上帝也。”(11)
为了建构汉语世界中的天主教宇宙唯一主宰论,利玛窦诉诸于中国古代经典(12),力图从中国先秦典籍的记载中,论证宇宙至尊只能出于一,中国古圣先贤所崇敬者乃是“上帝”(13),而非苍天。中国经典已证明,中国古代圣哲早已认识到宇宙至尊为“上帝”,中国经典中的“上帝”,与西方所尊崇的宇宙唯一真神“天主”,名称虽异,实则同一也。“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14)
天主教传教士认为,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儒家的某些教义,其实就是西方基督宗教的变异形态,他们试图把中国的传统思想包纳进基督宗教神学体系,借用中国传统思想诠释基督宗教神学在中国的合法性早已存在。这也就是耶稣会士们创造的著名“中学西源说”。罗明坚、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努力将儒家经典中的“天”和“上帝”均释作“天主”。类此融合天、儒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士大夫的兴趣,得到他们的认同,一些知识分子更进而领洗入教。如明末著名士大夫、天主教徒徐光启即是多年来被称道的例子。
1606年和1610年,随着范礼安和利玛窦的去世,天主教会内部逐渐兴起了反对以“天主”或“上帝”对译“Deus”的声音。反对者认为,这些译名渗入了太多中国传统宗教概念,“上帝”一词极可能在中国人头脑中产生异教歧义,它使得异教徒们对“Deus”的数量、本性、能力、位格等所有方面都可能产生错误的认识和观点,“Deus”极可能会被异教徒误认为是儒家的上帝,而非天主教的至尊唯一之神,从而削弱了天主教的一神性。总之,儒家语言无法表达天主教的精神和理念。译名问题在天主教耶稣会内部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最终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重要内容。(15)1628年1月,在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的主持下,在华耶稣会在嘉定召开会议,废除了此前的“上帝”、“天”、“陡斯”、“上尊”、“上天”等译名,保留了“天主”的译名。他们认为,造一个儒书中没有的“天主”,以示借用的是中国的语言,而不是儒家的概念。(16)
译名之争传达到了天主教罗马教廷。1704年,罗马教宗克勉十一世谕旨,不准采用除“天主”以外的其他译名(17),“天主”成为天主教对唯一尊神的钦定汉语译名。1742年,罗马教宗本笃十四世再次严词谕旨,禁止称“天主”为“上帝”。(18)从天主教内外的文献中,都可看出译名的变化。(19)从此,中国天主教会使用“天主”来对译“Deus”,所奉行的宗教也被译为“天主教”,以区别于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基督教。1968年,天主教唯一一本《圣经》全译本也以“天主”为译名。(20)
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许多名词的译介往往受原有词语的语言特性和文化寓意的限制,翻译时极不易达到“信达雅”的程度,宗教专名的表达尤其敏感和困难。翻译专名在被译介的本土文化背景下被重新诠释,常会或多或少偏离原有词汇的含意,对偏离程度的判断与容忍,则无一绝对的标准。有关“Deus”的争执,表面上是涉及天主教最尊神专名的翻译,其实本质上关系到不同天主教传教修会在传教策略上的异同、不同传教修会之间的本位主义、各修会代表的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传信部对保教权的制衡等多重因素。产生理解差异甚至偏误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词语词汇的本身,还在于身处不同传统背景的人们在解读这一词语时的概念定位和丰富联想。
当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大文本和经典传统的社会,因此无法像到美洲新大陆的天主教传教士那样随心所欲自行其是。信仰坚定的天主教传教士始终忧心概念译解中的偏误,但他们只能与这种环境相调适。而采用中国传统词汇译解天主教的相关概念,非常明显地昭示了他们的调适性传教策略,由此表明西方也有经典之作,力图通过这种方法使基督宗教的典籍与中国儒家和佛教的“经”处于同一位置。
16世纪时天主教传教士已来到中国,但第一本完整的汉语《圣经》译本,却是二百余年后由基督教传教士所完成。在16世纪不要说中国这样的传教新区域,即便在欧洲,普通的天主教教士手中也没有一本《圣经》,人们基本上是通过弥撒书等才得以接近《圣经》。因此,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一直都停留在对《圣经》的诠释和《圣经》史实的叙述上,已有的翻译《圣经》的尝试,大多是按弥撒书或祈祷书的形式来编译的。但这些汉语天主教书籍的确开拓了汉语基督宗教的历史,奠定了基督宗教话语体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词语基础,创立了基督宗教翻译中神学词汇多用意译、人名地名多用音译的方式。这些汉译词语包括天主、圣母、玛利亚、耶稣、十字架、门徒、圣神、先知、宗徒、授洗、福音等沿用至今的基本词语。
二、移境与想象:基督教的译名
二百余年后,由于与天主教教义理念和传教方式不同,辅之机器工业中印刷术的巨大改进,使基督教成为多达30余种《圣经》汉语译本的实践者和成就者。《圣经》中译的巨大成绩和影响,是在基督教传教士不懈努力下取得的。作为因宗教改革而诞生的基督教,倡导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信徒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是基督教的最重要标志。
1822年和1823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本《圣经》全译本——马礼逊译本和马士曼译本分别在马六甲和印度塞兰坡出版。二马译本重点参考了天主教巴黎外方教会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的译本,白日升译本中将“Deus”译为“神”(21),也为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ll)(22)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23)所接受。除了将“God”译为“神”以外,马礼逊还使用其他译名,如真神、真活神、神天、神主或主神。1831年后,他还用过神天上帝、天地主神、真神上帝、天帝、天皇等译名。(24)马礼逊之所以使用那么多不同译名,是因为始终找不到一个最恰当的译名,让中国人了解“God”为宇宙的唯一真神。在强大的儒教和佛教传统面前,他一直为中国人会将“God”,误认为另一个菩萨而苦恼。(25)
与马礼逊一起翻译《圣经》的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原来主张“God”翻译为“神”字,晚年则转而主张翻译为“上帝”。1821年,他列举了9条理由,说明“上帝”是相对而言较为合适翻译“God”的名词。他认为,在现成的中文词汇中,没有任何字义可以表达基督宗教的“God”一词的概念,只能从中文经典的现有名词中,力图找出可以激励人产生最高敬意的词来表示。“天主”的译法无法展现“God”的一神性,在中国这样的异教国家,人们将宇宙主宰诉诸于天、地、人三个层次,当中国人听到“天主”时,会很自然地将其列为天堂中诸多神祇之一。至于“神”字,又极容易被中国误认为是诸多神祇之一,都削弱了“God”的一神性。相比之下,“上帝”一直在中国古代被用来表示最高存在,不但完全能表达出最高的崇敬之意,还可以单独表示至高性,同时,“上帝”的字义也不会像“神”那样,被误认为诸多神祇中的一个,不会对基督教的一神性产生误解。(26)
米怜的主张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德国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等人所接受,他们认为用“中国最古老经典中”使用的“上帝”翻译“God”,方能展现“God”唯一真神的地位,引发中国人对唯一尊神的崇拜。(27)1833年郭士立在游记中就已数次使用了“上帝”译名,并陈述了理由。(28)1835年,以郭士立为首的四人小组在修订马礼逊译本时,将“神”改为“上帝”。(29)1839年,郭士立再次修订了《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新约),仍然采用了“上帝”译名。(30)
1843年,在华传教士成立了合作翻译《圣经》的“委办译本委员会”,工作难点之一是如何翻译宇宙主宰。当时有关“God”的译名起码有14种之多,也需要一个标准的用语。随着争论日趋激烈,在华传教士逐渐就“译名之争”按国籍分裂为两派。几乎所有的美国传教士主张用“神”为译名,而英国和德国传教士则坚持认为“上帝”才是最合适的词汇。(31)清末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继承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并像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做过的那样,在西方基督宗教的架构中诠释中国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致力于在中文词汇中找寻出可以表达的西方宗教词汇,使“译名之争”竟延续了长达3个世纪之久。
英国传教士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上帝”很接近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God”,是超越一切的“supreme ruler”,用中国人最崇拜的主神作为“God”的译名,符合基督宗教的历史传统。历史上希腊文和拉丁文中用来表达独一真神观念的“Theos”和“Deus”,实际上是源于当地人们对主神的称谓“Zeus”和“Dios”。(32)“帝”或“上帝”是中国人用来表示最高主宰、意志的概念,是最高的崇拜对象,而“神”则是附属于“上帝”的“某种东西”。为了使论战有力,在中文教师王韬的帮助下,麦都思不但系统整理了《大学》《孟子》等儒家经典,也考查了《三官妙经》《神仙通鉴》等民间宗教著作,寻找了大量的文字证据,论证“帝”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用于表达“一切的主宰”的概念。(33)如此众多含有“上帝”概念的中国古代经典可以说明,基督教的“God”早在古代已经启示了中国人,中国人曾知晓基督教,儒家经典中甚至出现过类似基督教的信念,以及以“上帝”这一名称描述至高存在。若将“God”译成“神”,中国人会以汉语语境里的“神”的含义,将“God”视为低层次的神祇,成为中国传统多神信仰结构中的进一步补充和添加。英国汉学权威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nuton)也表示,在中国语言里不可能存在一个传达“我们基督徒对‘God’字赋予的概念”的词汇。因此,在中国出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之前,“God”的概念便要输入进去,他赞成“上帝”的用法,因它比任何其他中文词汇更接近西方所加诸于“God”字的意义。(34)
对倡议“上帝”为译名的传教士来讲,认为只要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在“God”面前即可平等。亚当的后代带着神圣真理迁徙到世界各地,形成各种民族,但由于时间久远,使得某些民族忘却了这些真理,然而从这些退化的民族中依然可以发现真理的遗迹,例如在中国经典里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造物主的崇拜。(35)主张“上帝”为译名的传教士拥有的是一种旧约的信念,认为“God”曾启示全人类,甚至包括远在东方的中国人,而这也可以从中国早期历史遗存的文献中得到证明。现在唯一需要的是“重新唤醒”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而只有适应中国人原来的信仰认知模式,以“上帝”为译名才能重新建构中国人对“God”的认知模式。(36)
主张“神”为译名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本土传统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认为传教的目的就是用基督教的真理取代中国传统的迷误,将东方异教徒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如何借用“异教思想”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在中国文化中寻找与基督教“God”相当的概念则是荒谬的,因为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思想存在根本的区别。《圣经》的启示仅仅独存于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God”的选民是预定的,在中国这样的异教国家的文化和语言里,是根本没有现存的词汇来表达“God”,只能努力在中文里寻找一个最接近、最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天主教耶稣会士用“天”、“上帝”、“天主”来翻译“God”,削弱了基督教的一神性,削弱了抵抗多神论的基本力量,是完全不可取的。采用“上帝”这样的已有中文词语,可能会诱导皈信者去崇拜中国人熟悉的“上帝”,而不是西方的“God”。(37)“神”是表达中国人最高崇拜的无特指性名词,只有“神”字译名才能击溃中国人多神信仰结构,达到建构中国人唯一真神信仰的目的。(38)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在基督教概念的架构下,规范、发挥、建构“神”的字义,将“God”一神信仰的意义镶嵌进“神”字里,通过人们使用具有通称特质的“神”字,改造中国人多神式的信仰结构。(39)
用“神”为译名的人认为,中国人一直迷信多神,其信奉的神明,包括天、帝、上帝等,只是多神偶像而已,与基督教对唯一主宰的信仰格格不入。而传教的当务之急就是把中国人从多神迷误和偶像崇拜中唤醒,鉴于此,就不能用中国本土固有神的名号翻译《圣经》中的“God”,因为那样就无法与其固有的偶像崇拜划清界限。只有以中国人对“神”的通称翻译“God”,才能形成《圣经》之中国读者的一神信仰。他们相信,“神”字可以变成合适的用语,需要为中国这样的异教国家引入一种全新的基督观念和信仰。
在英美传教士的多年设想和努力中,他们一直相信从中文里一定可以为“God”找到汉语译名,利用中国人的知识和认识,来求证自己选择的译名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的合法性。一时之间,中国传统经典成为有用之物,对经史子集的探讨与诠释成为热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美国传教士娄礼华(Walter M.Lowrie)等人的论文征引的中国文献都多达十种之多,都试图找到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带着基督教的视角和关怀来阅读中国经典,将汉语中的“神”与“上帝”诠释出具有基督教的含义,所解读出来的“神”和“上帝”,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没有的蕴含天启、神性、最高存在等基督教含义的载体。在为“God”寻求中文对应关系的过程中,英美传教士对“神”或“上帝”的解读,亦表现出了他们定位中国与西方权力支配关系的立场,以及大相径庭的两种传教策略和对待传教区域本土文化的态度。
长达十年的译名之争,并未能在基督教内确立“God”的中国名称,但却阻止了其他意见的产生。此后的基督教《圣经》译本在此问题上,基本上只有两种译名,“神”或“上帝”。(40)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此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统一结果。今天,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十种文言、白话、方言、汉字、罗马字的《圣经》译本都已不再使用了,中国基督教会唯一使用的和合官话译本仍然保存了“神”和“上帝”两种版本。可以说,“上帝”和“神”两个译名在某程度上已经被确立。近代西方一篇分析这场争议的文章,甚至表示了使用两个译名的积极意义,“神”的译名表达了“God”的内在性(divine immanence)的概念,而“上帝”译名则代表了“God”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41)西方人通过基督宗教的理念和关怀来诠释和理解中国文化和宗教的角度和思维再一次得到展现。
三、相遇与接受:中方视野中的译名
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信仰来讲,译名问题的意义也是颇为重大的。但争执不休、引经据典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是从宗教信仰和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他们的传教对象——中国人会是如何理解、阐释“God”的译名,究竟是“神”或是“上帝”更能被中国人所认知、理解和接受呢?他们经年累月争论的声音,大概是很难被汉语世界的人听到的,甚至也很难引起汉语世界的兴趣和关注。从中国宗教文化来考察,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一神教信仰,“神”、“帝”、“上帝”、“天主”等在字面上都不能表达基督宗教最根本的观念,也许汉语中根本就没有现成词汇可以表达这种概念。因此,传教士们想用一个简单的、不必借助阐释就可以直接传达基督宗教根本观念的汉语词汇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传教士圣经话语”带来了新的概念和意义,也带来了新词语的输入。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词语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入到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并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取得被中国人承认接受了的合法地位。
据笔者考察,在近代,基督教最早进入中国士人眼界并产生影响的著作是1842年刊印的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中的《天主教考》,魏源使用了“上帝”、“天神”、“天主”等多个译名称谓。(42)1846年广东名儒梁廷枏刊印《海国四说》,“四说”中的一说即是“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梁廷枏非常深入地研读了当时还未进入中国大陆,主要阵地还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教义书和《圣经》译本及一些天主教的书籍,用儒家思想论述了基督教难以进入中国的原因。他的论述中也用名不一,“上帝”、“天神”、“天主”时常混用。(43)米怜施洗的中国首位基督徒梁发刊印于1832年、1843年被洪秀全获得的《劝世良言》中,也有“神天”、“神天上帝”、“神父”、“天父”、“天”、“上帝”等多达20余种译名。(44)
在“译名之争”之前,基督教传教士内部对“God”译名处于尚未统一、非常混乱的早期阶段。以1833年8月由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对“God”的译名也是纷繁复杂,但逐渐由多样趋向于单一,“神天皇上帝”、“神天”、“神天上帝”、“皇上帝”、“上帝”等词,经常是并用的。(45)但越到后来就越常用“上帝”或“神天”这两个词,而“神天上帝”这个词也慢慢消失了。(46)
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争论的结果,使译名基本限定在“天主”、“神”、“上帝”之间,这从中国文人士大夫或一般民众的各类“反洋教”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得出。曾国藩在其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没有分清太平天国信奉的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统称其为“天主”。(47)1859年刊印的夏燮的名著《中西纪事》中,称其为“天主”、“神”。(48)在众多反洋教文献中,其称谓一般限定在“天主”、“神”、“上帝”之中,而其中“天主”和“上帝”出现的频率较高,“神”字相对较低。(49)以当年流传甚广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呈送的《湖南合省公檄》为例,通篇多用“上帝”、“天主”两个译名。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主要接触的是英国传教士,他的《资政新篇》也用的是“上帝”。(50)
1839年刊印的《圣经》郭士立译本因被太平天国采用和大量印刷,格外引起了当时社会和史家们的重视。太平天国的《圣经》刊印本所用的“上帝”译名(51),随着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教”(52)的发展,迅速突破原有外国传教士和东南沿海极少数华人教徒的狭小范围,伴随着有清以来最大规模农民战争所能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影响,使“上帝”译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
外国传教士为农民军信仰基督教而极度振奋,认为占世界1/3人口的中国人皈信基督教的时刻即将来临。1853年9月,英国圣经会发起了“百万新约送中国”运动,超乎期望的热情捐款足够英国圣经会在中国未来20年的经费支出。(53)到1869年,经济实力最强的英国圣经会已经刊印了95万册《新约》或全本《圣经》,坚决主张译名“上帝”的麦都思等人翻译的“委办译本”(54),就占了其中的75万册(55),使委办译本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印刷量最大、流行最广的《圣经》译本。在中国著名士人王韬的协助参与下,从中文的语言文字角度来考察,无论从汉字选词,还是文字流畅方面,委办译本的“中国化”程度在当时都是最高的。(56)1877年7月21日,《万国公报》就基督唯一尊神应译为“上帝”还是“神”面向读者发起持续一年之久的讨论,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基督徒更多使用的是“上帝”译名的委办译本。(57)
在出现了《圣经》高德译本、裨治文译本、北京官话译本、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的多年以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在华传教士还专门刊印了“上帝”译名的《圣经》委办译本大字本给她祝寿(58),这说明委办译本是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译本。委办译本是对沿用至今的和合本《圣经》产生奠基性影响的译本,尤其是专名术语方面的奠基性没有任何译本能够代替,译名“上帝”得到了最大范围的传播。1908年,英国圣经会高薪邀请极富翻译盛名的严复翻译《圣经》,他也采用了“上帝”译名(59),“上帝”译名被接受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上帝”译名被更多接受,当年坚持“神”译名的美国圣经会,也逐渐转向了刊印“上帝”译名的《圣经》译本。1894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了“上帝”版《圣经》38500册,占11.6%;1908年出版“上帝”版《圣经》299000册,占78.9%;1913年刊印“上帝”版《圣经》1708000册,已达99.7%。(60)
20世纪20年代,虽然基督教内还认为“God的译法一直是个使人大伤脑筋的问题”(61),但“上帝”译名的确已经被更广泛的接受了。1920年出版的《圣经》中,文言译本“上帝”版占98%,“神”版仅占2%;白话译本“上帝”版占89%,“神”版占11%。(62)“上帝”译名已占绝大多数。
随着时间推移,“上帝”一词几乎成了基督教最常见通行的译名,无论在基督教内还是教外,“上帝”已经被更多的人用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晚清著名洋务派人士、基督徒王韬(63)和非基督徒郑观应(64),著名作家、基督徒老舍(65)和非基督徒沈从文(66),著名学者、非基督徒胡适(67),中共党员、非基督徒陈独秀(68)和恽代英(69),中共党员、曾经的基督教牧师浦化人(70),国民党员、基督徒蒋介石(71)和冯玉祥(72),等等,从这些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人群留下的文献中均可看出,他们全部都使用了“上帝”一词。
最可表明中国社会对“上帝”等《圣经》译名认同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时,不但使用的是“上帝”译名,其他圣经人物也全部采用了和合官话译本的译名。(73)由此可见,《圣经》翻译中创造的各种译名,如马太、挪亚方舟、福音、耶稣、洗礼、先知、圣经、犹太人、以色列、耶路撒冷、亚当、夏娃、埃及、约翰,等等,已经被中国世俗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运用。
四、余论
用中文为“Deus”“God”译名,关系到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悠久的两种文明之间最深层的对话,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再定位,充满了文化交流和宗教同化和再生。有关“Deus”“God”的汉文译名的争议史和接受史,记录了《圣经》如何跨越传统社会地理的边界,进入不同的社会文化概念世界,与相异的宗教文本与身份相互作用的历史。它包含了文化的可译性问题,以及将一种语言与文化的概念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时必然遇到的理解问题,这个转化的过程涉及原有的概念会在接受语言中被原样保留还是将有变化,如果变了,怎样变的问题。
《圣经》的文本本身预定了基督宗教的唯一尊神的名称不可能是唯一的。学者研究表明,传统上被认为浑然一体的《圣经》文本,由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和不同作者的口头传授与文献结合而成,《圣经》文本本身反映了各种文化对于神明的参差多端的理解和命名。《圣经》翻译者的一神论背景,使他们强烈地要用其自身的文化世界中的“对等的”或“想象的”词汇来翻译《圣经》。
近代翻译大家严复最著名的经典翻译观“信达雅”,将对“信”的追求放在了首位。人类历史上所有翻译中的“信”的追求,都基于对不同文化之间“可译性”的认同。其实,语言之间的“互译性”完全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是“虚拟对等”而不是“透明地互译”,且并非一次性能够完成的。(74)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扩展了中国文化的概念空间。在这个扩展概念和文化再创造的过程中,转借原词并赋予新意,是近代文化转型过程很常见的现象。在新的概念框架下,在译介中,固有词汇被重新阐释,再生出中国式的新概念和新理念,力图创造出基督宗教概念的中西语言对等,创造出基督宗教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从中文语境看,在长达300年译介、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上帝”译名同样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上帝”一词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上帝”一词逐渐地被基督教化而失去了原有的本土宗教的内涵,当我们今天说到“上帝”时,想到的都是基督教的“上帝”。中国传统蕴含了关于“上帝”的悠久文献历史和口头传说,为《圣经》中的上帝赋予中文名字提供了文化转换的基础,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翻译的维度。
“Deus”“God”的译介和接受过程是欧洲和中国语言文化之间观念和概念的可译性探讨的最佳实例。它也体现了外来观念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译源语本身具有的近现代意义,新内涵自身所具备的强势地位为转型社会带来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也为传统社会的急迫吸纳提供了思想和概念激励的想象空间,再生了宗教本身以外的意义。
注释:
①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镌刻的是“元真主阿罗诃”。朱谦之:《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影印),《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黑体字为笔者强调所加,下同。
②朱谦之:《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中国景教》,第164页。
③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页。
④“惟以天主行实。原于西国。流布四方。”“一惟诚心奉敬天主。无有疑二。则天主必降之以福矣。”“天主制作天地人物章。”“今幸尊师传授天主经旨。引人为善。救拔灵魂升天堂。”“盖天地之先。本有一天主。”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明崇祯年刻本,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2册(影印本),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59、760、763、765、766页。
⑤戚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⑥Edward J.Malatesta,"Alessandro Valignano,Fan Li-An (1539-1606) ,Strategist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Review of Culture (Macao),No.21,2nd Series,pp.35-54,1994,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⑦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1-232页。
⑧经考证,利玛窦首次使用此词的时间应该为1583年7月至8月之间。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97页。
⑨金尼阁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⑩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6页。
(11)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明刻天学初函本,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2册(影印本),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页,引文重新标点。
(12)《天主实义》引用《孟子》23次、《尚书》18次、《论语》13次、《诗经》11次、《中庸》7次、《易经》6次、《大学》3次、《礼记》2次、《左传》2次、《老子》1次、《庄子》1次。参见马爱德编《天主实义》,“附录”,Index of Chinese Classical Texts。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第291页。
(13)“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2册,第20页,原文无标点。
(14)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2册,第20页。
(15)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帝天说”及其所引发的论争》,《国际汉学》第8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357页。
(16)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
(17)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422;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31-232页。
(18)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印书馆1937年版,第339页;Irene Eber,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S.I J.Schereschewsky,1831-1906 (Leiden,Boston..Brill,1999),p.202.
(19)天主教内文献:“天主造世界。天主用土造了人的肉身。”涂宗亮校点:《古新圣经问答》,初刊于1862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全能天主!我等因尔圣子耶稣救世之苦心,暨中华圣母同情之哀祷,恳求俯允尔忠仆上海徐保禄首等外虔奉圣教者。”马相伯:《求为徐上海列品诵》,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第376页。天主教外文献:“陡斯造天地万物,无始终形际……耶稣释略曰:耶稣,译言救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后之名也。”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初刊于163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文献重新标点。“天主堂构于西洋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崇奉天主。”吴长元:《宸垣记略》,初刊于178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引文重新标点。
(20)“21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22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藉先知所说的话:23看,一位贞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他的名字为厄玛奴耳,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思高译本(旧新约1968年):《玛窦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香港,香港思高圣经学会1968年版。
(21)“此皆有之以成主已出而托先知之言道童贞将怀孕生子称名厄慢尔译言神偕我等”。白日升译本(1702年后):《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手写稿),原文无标点。白日升译本的“四福音书”部分为圣经福音合参本。
(22)“21其将产一子、汝名之耶稣、因其将救厥民出伊等之诸罪也。22夫此诸情得成、致验主以预知所言云。23却童身者将受孕而生子、将名之以马奴耳、即译言、神偕我等。”马士曼译本(旧新约1822年):《使徒马宝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1822年印于印度塞兰坡。
(23)“21又其将生一子尔必名之耶稣、因其将救厥民出伊等之罪也。22夫此诸情得成致验主以先知者而前所言、云、23却童身者将受孕而生子、将名之以马奴耳、即是译言、神偕我们。”马礼逊译本(旧新约1823年):《圣马宝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救世我主耶稣新遗诏》,1823年印于马六甲。
(24)Walter H.Medhurst,"An Inquiry into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ca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Vol.17,July 1848,pp.342-343.
(25)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1,p.201.
(26)William Milne,"Some Remarks on the Chinese Terms to Express the Deity," Chinese Repository,Vol.7,Oct.1838,p.314;该文原载The Indo-Chinese Gleaner,No.16,April 1821,pp.97-105。
(27)Charles Gutzlaff,"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Vol.4,Jan.1836,pp.393-398; Walter H.Medhurst,"Reply to the Essay of Dr.Boone," Chinese Repository,No.17,Nov.1848,p.571.
(28)Charles Gutzlaff,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and 1833 (London:Frederick Westley and A.H.Davis,1834),p.108,p.115,pp.278-279.
(29)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 ) ,p.31.“21其必生子、可称耶稣、因必将救民免罪、22诸事得成、可应验上主以圣人所云、23童女将怀孕生子、名称以马伮耳等语。此名译出意言、上帝与我共在也。”四人小组译本(新约1837年):《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新遗诏书》,1837年印于巴达维亚。
(30)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 ,p.62.“21其必生子、可名称耶稣、因必将救民免罪。22诸事得成、可应验上主以圣人所云、23童女将怀孕生子、名称以马伮耳等语、此名译出、意以上帝与我共在也。”郭士立译本(新约1839年、旧约1838年):《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1839年印。
(31)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9),pp.82-84.
(32)Walter H.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Vol.17.March 1848,p.107.
(33)Walter H.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pp.117-137.
(34)Sir George Thomas Stanuton,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Various Opinions Which Have Prevailed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Especially in Reference to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London:1849 ),pp.27,42,43.转引自伊爱莲《争论不休的译名问题》,伊爱莲等著,蔡锦图译:《圣经与近代中国》,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3年版,第114页。
(35)William Milne,Retrospect of the First Y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 Malacca,1820 ) ,pp.3-4.
(36)Walter H.Medhurst,"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 Futsz," Chinese Repository,Vol.13,Oct.1844,p.552.
(37)Walter M.Lowrie,"Remarks on the Words and Phrases Best Suited to Express the Names of God in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Vol.15,Nov.1846,p.508.
(38)William J.Boone,"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Chinese Repository,Vol.17,Jan.1848,pp.17-18.
(39)E.C.Bridgman,"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Chinese Repository,Vol.15,April 1846,pp.161-165.
(40)译名之争后,基督教圣经翻译还出现过影响较大的10种汉语译本,在唯一尊神的汉译问题上,除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外,其他译本都基本限定在了“上帝”和“神”之间。本文只引用影响较大的圣经全译本,未涉及仅有区域性影响的圣经方言汉字译本、圣经方言罗马字译本、圣经节译本和圣经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为保持文献的一致性,便于对照比较,不同译本的圣经文献均选用了《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21彼将生子。可称其名耶稣。因其将救其民免于罪也。22凡此皆成。致验主托先知者所言云。23处女将怀孕生子。名称以马奴里。译言神偕我等也。”高德译本(新约1853年):《马太福音传》第1章第21-23节,《圣经新遗诏全书》,宁波真神堂1853年版。“21彼将生子、尔必名之曰耶稣、以将救其民于其罪恶中、22凡此事得成、致应主托预言者所言云、23视哉、将有一处女、怀孕而生子、人必称其名曰以马内利、译即神偕同我侪。”裨治文译本(新约1855年、旧约1864年):《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新约全书》,大美国圣经会1855年版。“21他必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22这事成就便应验主托先知所说的话、23他说、童女将要怀孕生子、人将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译出来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意思。”北京官话译本(新约1870年、旧约1878年):《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全书》,京都东交民巷耶稣堂藏板,北京,京都美华书馆1872年版。“21彼将生子、当名之曰耶稣、因将救其民于罪恶中云、22凡此得成、乃为应主托先知所言曰、23童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其名为以玛内利、译即天主偕我焉。”施约瑟浅文理译本(旧新约1898年):《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全书》,东京,日本东京秀英罕舍1898年版。“21彼必生子、可名曰耶稣、因将救其民脱厥罪也。22斯事悉成、以应主借先知所言曰、23将有处女孕而生子、人称其名、曰以马内利、译即上帝偕我侪也。”和合深文理译本(新约1906年、旧约与浅文理合并1919年):《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圣书》,大美国圣经会1906年版。“21彼将生子、尔可名之曰耶稣、因将救己民、出于其罪之中、22此事皆成、以应主昔托先知所言、23曰、童女将怀孕生于、人必称其名为伊马内利、译、即上主与我侪相偕也。”和合浅文理译本(新约1906年、旧约与深文理合并1919年):《圣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圣经》,大美国圣经会1906年版。“21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22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23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和合官话译本(新约1906年、旧约1919年):《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全书》,大美国圣经会1919年版。“21她必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必拯救他的人民脱离他们的罪。22这全部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藉神言人所说的话,说:23看吧,那童女必怀孕生子;人必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吕振中译本(新约1946年、旧约1970年):《按圣马太所记的佳音》第1章第21-23节,《吕泽新约初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6年版。“21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22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主藉着先知所说的话:23有童女将怀孕生于,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现代中文译本(新约1975年、旧约1979年):《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全书》,台北,台湾圣经公会1979年版。“21她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22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23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新译本(新约1976年、旧约1993年):《马太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全书》,香港,香港圣经公会1976年版。
(41)G.W.Sheppard,"The Problem of Translating God into Chinese," The Bible.Translator 4,1955,pp.23-27,转引自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p.90。
(42)“天主上帝,开辟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天为有始,天主为无始,有始生于无始,故称天主焉。”“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犹可言也,尊耶稣为上帝则不可信也。”“耶稣为神子,敬其子即敬天。”“《福音书》曰:元始有道,道即上帝,万物以道而造。”“神天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魏源:《天主教考》,《海国图志》卷27,初刊于1842年,《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809、811、813、815、816,817页,文献重新标点。
(43)“时气候正凉,上帝方来游于园。”“有始无终,故谓天主为天地万物之本。”“水涨地面,上帝浮水面以造万有。”“天神以告马利亚,使避于厄日多国,即麦西国,亦称以至比多。”梁廷枏:《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海国四说》,初刊于1846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10.22页,文献重新标点。
(44)卢瑞钟:《太平天国的神权思想》,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转引自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45)“亚大麦。当初神天。即上帝造化天地。及造世人。是亚大麦性乃本善。惟有恶鬼现如蛇样。”(1833年6月)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页。
(46)参见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影印本导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14页。
(47)“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为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曾国藩:《讨粤匪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页。
(48)“亚细亚洲之西、曰如德亚国、西方天主降生之地也。天主何人、耶稣也、耶稣何以名、华言救世主也。”“耶稣以天为父、自称神子、厌世上仙、代众生受苦、以救万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称之。”夏燮:《猾夏之渐篇》、《西人教法异同考》,《中西纪事》卷2,初刊于1859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06),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页。
(49)“天一而已,以主宰言之,则曰上帝,乃变其名曰天主,即耶稣以实之。”“即有之,而不问良莠,概登其中,上帝何启宠纳侮之甚耶?”《湖南合省公檄》(1861年)。“其徒号其教曰天主,以耶稣为先天教土,造书曰书经,遍相引诱,自郡国至乡闾皆建天主堂,供十字架。”饶州第一伤心人:《天主邪教集说》(1862年)。“他是天主来降下,生身童女马利亚。”天下第一伤心人:《辟邪歌》(1862年)。“厥后其徒遂创立邪教,名曰天主,其意以耶苏为天主。”《南阳绅民公呈》(1867年8月7日)。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7、11、17页,文献重新标点。
(50)“上帝是实有,自天地万有而观,及基督降于,以示显身,指点圣神上帝之风亦为子,则合父子一脉之至亲,盖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岂不是一体一脉哉!”“数百年来,各君其邦,各子其民,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而花旗之信行较实,英邦之智强颇著。”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下册,初刊于185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1、682页,文献重新标点。
(51)“21其必生子,可名称耶稣,因将其名救脱罪戾。22诸事得成,可应验上主以先知之师所云,23却童女将怀孕生子,名称以马伮耳等语,此名译出意以‘上帝与我共在’也。”太平天国刊印本:《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钦定前遗诏圣书》,初刊于1860年,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文献重新标点。
(52)“于是各省拜会无不藉天主为名、即非天主教者亦假托之、粤西军兴则有冯云山洪秀泉杨秀清等其结金田拜上帝之会、谓上帝为天父、谓耶稣为救世主。”52夏燮:《猾夏之渐篇》《西人教法异同考》,《中西纪事》卷2,第22页。“伏思连年倡乱,蔓延数省,即由广西上帝会而起,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1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3页,文献重新标点。
(53)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p.76.
(54)“21彼必生于、可名曰耶稣、以将救其民于罪恶中。22如是、主托先知所言应矣、曰、23处女孕而生子、人称其名以马内利、译即上帝偕我焉。”委办译本(新约1852年、旧约1854年):《马太福音传》第1章第21-23节,《新约全书》,香港英华书院活板,1854年印。
(55)Donald 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558.
(56)Patrick Hanan,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The Writing Process,Patrick Hanan edit,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xhibition Catalogue (Cambridge:Harvard -Yenching Library,2003),pp.272-278.
(57)“夫上帝之道,传自犹太。”“是万国皆为上帝所造,即万国同一上帝,同一造化主宰,又何有儒书所载之上帝造化主宰乎?”何玉泉:《天道合参》,初刊于《万国公报》第457卷,1877年9月27日;“虽犹大选民独尊上帝,而异邦父老岂乏真传?”“且保罗就异邦人之诗而即以证上帝为造物主,况华人之早称上帝为生民之上帝而不可称也乎?”英绍古:《谢陆佩先生启》,初刊于《万国公报》第473卷,1878年1月19日;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101、102页,文献重新标点。
(58)John R.Hykes,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American Bible Society,1916),p.24; Kenneth 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Macmillan,1929) ,p.266.《新约全书》,上海美华书馆活版,美国圣经会1894年版。
(59)“上帝子基督耶稣,福音之始。如以赛亚先知所前载者曰:视之,吾遣使尔前,为尔导其先路……于是约翰至,行洗礼于野中。”李炽昌、李天纲:《关于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原手稿未刊印,英国剑桥大学藏。文献重新标点。
(60)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p.88.
(61)司德敷等编,蔡咏春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1页。
(62)司德敷等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册,第1041页。
(63)“午刻,往讲堂听慕君说法。慕君以‘上帝’二字出自儒书,与西国方言不合。且各教进中国,其所以称天之主宰,称名各异,犹太古教为耶和华,景教为呵罗呵,挑筋教称为天,天主教为真主,明时,利玛窦等入中国,则为天主,而间称上帝。”“《圣经》曰:元始有道,道与上帝共在。道即上帝。此道之不可见者也。耶稣曰:我即真理,此道之有可见者也。”王韬:《王韬日记》,1858年9月19、27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l页。王韬不仅参与了委办译本的翻译,而且是最早对外国传教士的译名之争有文献记录的中国人。
(64)“新约载耶稣降生为上帝子,以福罪之说劝人为善。”郑观应:《传教》,《盛世危言》(14卷本),初刊于1895年,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文献重新标点。
(65)“信基督教的人什么也不怕,上帝的势力比别的神都大得多。太岁?不行!太岁还敢跟上帝比劲儿?”老舍:《二马》,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101页。
(66)“我们从人情中体会出来的道理是履行上帝的旨意最可靠,最捷近的路。因为人情是上帝亲手造的。”沈从文:《未央歌》,孔范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8),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67)“对于基督教我也有相当的敬重,但因为我个人的信仰不同,所以当时虽有许多朋友劝我加入基督教会,我始终不曾加入。近年来我对灵魂与上帝还是不相信,不过我对于旁人的宗教信仰是一样敬重的。”见胡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胡适全集》第9卷,第171页。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多次参加过基督教会活动,所读《圣经》也是“上帝”版,参见《胡适全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
(68)“人类无罪,罪在创造者;由此可以看出上帝不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我们终不能相信全善而又全能的上帝无端造出这样万恶的世界来。”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初刊于1920年2月1日,《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69)“因如有上帝,则必应于正当生活中求之,与其与之为片段零落的辨难之境,亦何益乎?……余意祈祷、信上帝,乃基督徒之精华。”恽代英:《恽代英日记》,1918年7月8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70)“自此每礼拜日之听道。亦多感触。自维上帝既是普世之父。慈悲无量。”浦化人:《半生之回顾》,青年协会书局1921年版,第28页。浦化人曾是基督教圣公会牧师,后任新华社社长、晋冀鲁豫最高法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
(71)“轻视目前羞辱。忍住十字架苦痛。耐心直向上帝所指示的正路。”(1935年11月24日)“幸获上帝保佑。俾我夫妻得以相见。不胜感谢。”(1936年5月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4卷(影印本),台北,“国史馆”2008年版,第472页;第36卷,第558页。
(72)“他们说: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学。’我自信我是个科学的基督徒,毫无迷信观念。”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297页。
(7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名索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9-982页。“无论我们同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一起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像土耳其人一样叫做天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74)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8页。
标签:基督教论文; 传教士论文; 天主教论文; 圣经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宗教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耶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