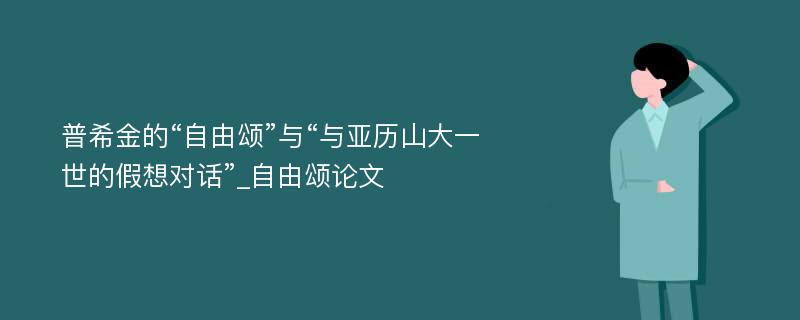
普希金《自由颂》与《同亚历山大一世的假想谈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亚历山大论文,假想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颂》是普希金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在俄罗斯家喻户晓。而《同亚历山大一世的假想谈话》(以下简称《假想谈话》)即使在普希金的祖国,至今也没有被公认为毫无问题的版本和解读;我国则似乎只有谢天振和冯昭玙等先生的译本(注:见谢天振译《普希金散文选》49页,天津,1995年;冯昭玙、顾惠生等翻译者,见《普希金全集》第七卷551—55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评论界尚无人留意。其实,这篇奇文不仅对于正确理解《自由颂》,对于揭示沙皇流放普希金的深层次动机,而且对于了解普希金当时急于摆脱流放又感到希望渺茫的矛盾心情,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在俄罗斯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一诗一文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试图探明《自由颂》的本来涵义,对几个争论上百年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对中译文的某些处理以及《假想谈话》俄文通行本的解读,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
《自由颂》是普希金遭沙皇政府惩罚、被流放南方的正式或公开的主要“罪证”。
第一节中“帝王的克星,自由的骄傲歌手”(注:《普希金全集》(十七卷本)第2卷43页,莫斯科,1994年。本文所引普希金诗文, 除特别注明者外,皆译自此十七卷本全集。)指的是谁呢?各俄文注释本及有关论著均无明确的解释。我以为这是指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文学家伏尔泰。普希金在1814年创作的《鲍瓦》一诗中,称颂伏尔泰是“唯一的大丈夫”,是拉季舍夫反专制思想的激励者。该诗的三句话颇能说明问题:“现在,请你当我的缪斯吧!我也想要歌唱,只不知能否与拉季舍夫较量?”(注:《普希金全集》第1卷50页,莫斯科, 1994年。)这后一句显然说的是拉季舍夫的《自由颂》。由此可见,早在皇村学校读书时,普希金就产生了创作讴歌自由诗篇的念头。1817年毕业后写成的《自由颂》尽管其内容、结构和方法都可能与当初设想者不尽一样,但其反对专制、讴歌自由的思想始终未变,其尊崇伏尔泰为师并呼唤此人来激发自己诗情的命意亦未改变。
《自由颂》呼唤“跌倒在地的奴隶”起来同专制暴君进行斗争。这“奴隶”到底指什么人?乍看起来,这似乎是指农奴或者人民群众,其实不然。因为不要说普希金,连当时最激进的十二月党人,也害怕真正的人民起义。他们1817年秋天准备刺杀亚历山大一世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伪装成自由派的沙皇宣称要解放农奴。作为贵族革命者的十二月党人觉得,这必将导致“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贵族”。他们认为,这些“愚氓”不可能理智地分析政治局势,“从来弄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注:见苏联中央档案馆编《十二月党人起义》第1卷306页, 第3卷72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至于普希金本人,且不说其他诗文,单是《自由颂》即已表明,他对于人民群众并不抱希望,更不会号召他们起来斗争。姑且不论愚昧无知的俄国农奴,即使是接受长期启蒙教育的法国民众,无论是在君主独裁还是在雅各宾专制制度下,都无所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度遭受践踏。雅各宾专政和拿破仑上台表明,人民群众能够奋起斗争,甚至能够获得一时的自由,但是,由于在政治上的无知,他们只能造成新的独裁,使自己重新沦为奴隶。
十二月党重要人物尼·屠格涅夫对于普希金刚离开校门步入社会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自由颂》一诗即是在屠格涅夫家开始创作的。因此,尼·屠格涅夫关于“奴隶”的论述,对于正确理解《自由颂》中“奴隶”一词的真正涵义,以及此诗的真正号召对象,都大有帮助。
尼·屠格涅夫以及其他十二月党人所抨击的“奴隶”,是指浑浑噩噩听信世俗成见的广大贵族,尤其是不关心国家兴亡、安于现状的贵族知识分子。
对于“奴隶”的类似理解,在普希金的其他作品中也可见到。比如《致弗谢沃洛日斯基》(1919)即将“自由”同“奴隶”进行对比。
不过,在《自由颂》中,普希金并未斥责这些奴隶,而是极力将他们唤醒,鼓励他们振作起来,参加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斗争。当然,这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要受至高无上的法度的约束。
《自由颂》第三节一开始就勾画出一幅法纪荡然、民不聊生的悲惨画面、第三句Законов гибельный позор中之позор一词,现代俄语中多表示“耻辱”,但古时候兼有“景象”、“场面”之意。中译本有处理为“耻辱”、“侮辱”者,显然与上下文义不合。译成“景象”似较为恰当。
第三节第七行гений一词含有“天才”、“精灵”、“恶魔”等多重涵义,不少人把它译作“天才”。我以为这里当译成“恶魔”,因为指的是以奴役国内外人民为乐的魔鬼。本节末句“对浮名的致命贪恋”中的“浮名”主要是指掠土夺疆的所谓“荣名”。我认为,这里隐含着对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双向批判,尽管二人处于敌对位置,但在普希金当时的观念中,他们都是同样无止境地追求战功,同样蛮横地实行独裁,因而是一丘之貉。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普希金对他们的看法也日趋深刻,对于他们的相异之处也辨识得更加清楚。
第四、五、六、七这四节讲的是法度,法度与自由、法度与君王及人民的关系。可以认为,法度与自由同是《自由颂》全诗的核心,确立法制是普希金自由观的基础。普希金在这几节诗中表明,只有将“神圣的自由”同“强大的法度”紧密结合起来,国家才会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在法度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不能滥用法度;统治者的权力是法度给予的,而不是靠继承(“自然”)得来,因此,尽管他们凌驾于人民之上,统治人民,但他们的行为必须受法度的制约,绝不能恣意妄为。在此,普希金特意用法国大革命中法王路易被斩首这一事例说明:帝王若玩弄法度于股掌,必然遭受严惩;人民若蔑视法度,亦将导致新的独裁,并给自己带来灾难。
第七节第一行Восходит к смерти Людовик有好几种译法。“路易昂扬地升向死亡”、“路易高高升起,走向死亡”、“路易昂扬地步步走向死亡”以及“路易昂然地走向死亡”等译法都含有赞美之意。我觉得这层涵义为原诗所无,是对восходит一词理解不当所造成。在原诗中,此词只表示向着砍头台所在的高处走去,绝无“昂扬”、“昂然”等附加意义。冯春译作“路易一步步登上刑场”(注:见冯春译《普希金文集·抒情诗(一)》197页,上海,1995年。),虽把“死亡”一词换成“刑场”,但从把握全句及诗人对路易的总体态度而言,都较其他译法更切近原文。“登上”二字不褒不贬,选用得十分恰当。
全诗最后一节即第十二节更清楚地表明诗人所讴歌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他在唤起“奴隶”争取自由的同时也呼吁君王要遵守法度。他同情前者,但并不姑息其无视法度的暴力行为;他警告后者,但并不一概仇视,这警告同时也是忠告。
显然,如果《自由颂》仅仅包含上述内容,沙皇未必真会整治他:最初要把他流放到几乎是有去无回的西伯利亚的索洛维茨,只因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等社会名流苦苦求情,才勉强改为“下放”南方,保留职务,就地监督改造。
我认为,沙皇之所以决不饶恕普希金,主要是因为《自由颂》,但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三节犯了大忌,令亚历山大忍无可忍。这绝非臆想,而是有普希金本人的《假想谈话》为证。
二
《假想谈话》是普希金1824年年底在米哈伊洛夫村写的。
由于只有草稿传世,而草稿又一改再改,涂抹得非常厉害,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即使是一些非常关键的字句,各种版本也不尽相同,比如,谈话开头沙皇对《自由颂》的评价这一段,苏联科学院十卷本《普希金全集》和国家文学出版社十卷本《普希金文集》的解读大体一致,可以这样翻译:
“我读过您的《自由颂》。总的来说,它写得有些混乱,思考问题有些轻率,可是有三节写得非常漂亮。您的行为很不明智,但是毕竟没有极力散布荒诞的流言蜚语,在民众眼里给我抹黑。您可以有一些缺乏根据的意见。可是我发现,您尊重事实,也尊重个人的荣誉,即使这人是沙皇。”(注:参见《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第8卷69页, 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普希金文集(十卷本)》第7卷344页,莫斯科,1962年。)
可是,在1949年之前问世的各种版本中,对这段话的解读与此大不一样:
“我发现,您极力散布荒诞的流言蜚语,在民众眼里给我抹黑。我看,您可以有一些缺乏根据的意见:您不尊重个人的事实和荣誉,即使这人是沙皇。”(注:见《文学遗产》58卷170页,莫斯科,1952年。)
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十七卷本《普希金全集》汇集了众多差异或大或小的解读。其中主要的几种是:
1、“您的行为很不明智, (但是毕竟没有)极力散布荒诞的流言蜚语,在民众眼里给我抹黑。”(按:这一种解读载入正文。需要注意的是,“但是毕竟没有”这几个字是用引号圈起来的,处于疑是之间。)
2、“您的行为很不明智,您通过散布荒诞的流言蜚语, 极力在民众眼里给我抹黑。”
3、“当然,您的行为很不明智,不过您没有重复流言蜚语, 没有极力在民众眼里给我抹黑。”
4、“当然,由于您没有饶恕我的亲人,您表现得很不明智。 不过您毕竟没有重复荒诞的流言蜚语,没有极力在民众眼里给我抹黑。”(注:见《普希金全集》第11卷23页及294—298页,莫斯科,1996年。)
“没有极力在民众眼里给我抹黑”这句几乎完全一致。“极力”二字很有意思:没有极力抹黑,也还是抹了黑,只不过程度较轻而已。这就是说,即使是在假想谈话中,普希金也不否认自己犯有这一“罪行”。不仅如此,“没有极力”的“没有”这个否定词在草稿里曾经划掉,后来又恢复。这进一步说明,在诗人的想像中,亚历山大一世本来是严厉斥责他极力散布流言蜚语、极力给沙皇抹黑的。
上述诸种解读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或接近普希金原意,这里先不下断语,且来弄清楚一个问题;“流言蜚语”、“抹黑”等语究竟指什么?翻看一下《自由颂》的背景材料就不难明白,这是指该诗相当详细地描绘的亚历山大之父保罗一世被刺之事。而且,问题不仅在于诗中将保罗说成是以贪淫残暴著称的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并且直呼他为“戴皇冠的恶棍”;更重要的是,这是个根本不允许谈论的话题,这是亚历山大的心病,因为这场谋杀即使不是他本人策划的,至少也获得了他的支持和默许。无论怎么说,他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首登上皇位的,弑父篡位的罪行他永远也无法洗刷。在亚历山大看来,《自由颂》中记述此事就是在“极力散布荒诞的流言蜚语”,就是“极力在民众眼中给我抹黑”,就是对他“个人荣誉”的放肆侮辱,因而不可饶恕。
在俄文通行本《假想谈话》中,“可是有三节写得非常漂亮”这句话是作为沙皇对《自由颂》的赞语,我以为这样处理有悖普希金原意,正确的解读是将它视为普希金自己的辨护之词。否则,不仅显得沙皇语无伦次,也与流畅自然的普希金文风格格不入。
这“写得非常漂亮”的到底是哪三节呢?俄罗斯著名普希金学者法因贝格认为,这指的就是关于保罗被害的那三节。亚历山大之所以称赞它们“写得非常漂亮”,是因为诗人在描绘这一重大事件时,没有把他牵扯进去,更未指斥他是杀父弑君的罪人。(注:见法因贝格《普希金手稿阅读笔记》621—622页,莫斯科,1985年。)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自由颂》中可能被沙皇称赞或被普希金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写得非常漂亮”的三节诗是第六、七、八节。第六、七两节以路易被斩首及拿破仑实行新独裁为例强调,无论是君王还是人民都不可蔑视法度;第八节则似乎是对于拿破仑的诅咒。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喜欢吹嘘自己是法度的拥护者,并曾一度指定专人草拟俄国宪法。因此,普希金关于法度高于一切的主张虽然实质上同沙皇的虚假姿态相去万里,但在表面上“大方向”是一致的。其次,普希金在指出路易被斩首是为其先人过失赎罪的同时,又认为这是民众践踏法度的错误行为,其后果是导致拿破仑的独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视为对于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专政的批判和对于法国王室复辟的支持,亚历山大自当表示赞许。最后,亚历山大既是拿破仑的战胜者,诗中对于拿破仑的任何批评和诅咒,他都应当感到高兴。
问题在于,这第八节中所说的“专横独裁的恶棍”是否确指拿破仑。
自本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这节诗所抨击的是拿破仑。(注:参见比克曼《关于〈自由颂〉的写作时间》,载《普希金及其同时代人》第19—20辑58—59页,彼得堡,1914年;托马舍夫斯基《普希金》上册166—168页,莫斯科,1990年; 《普希金文集》第1卷562—563页,莫斯科,1959年。)可是,早在三十年代,既已有人反对这一观点。什克洛夫斯基的理由是:诗中表示对专横独裁“恶棍”皇位的憎恨,而拿破仑早已下台,普希金写《自由颂》时他正困居圣海伦岛;诗中诅咒恶棍的“子女丧命”,可是拿破仑只有一子,当时还健在。(注:见什克洛夫斯基《普希金散文论丛》13—14页,莫斯科,1957年。)到六十年代,叶列明进一步指出,亚历山大之父保罗一世完全符合这节诗所写的情况:保罗子女众多,普希金写《自由颂》时已有三人夭折;保罗死后皇位传给后人,可见诗人的憎恨不是无的放矢;“自然的耻辱”一语同拿破仑搭不上,对保罗则再恰当不过,因为此语系指生理或心理的反常状态。拿破仑虽然个头不高,但是身材匀称,天才横溢,普希金不仅从不认为他在生理或心理上有毛病,还用“幸福与柏隆娜(女战神)的宠儿”等带有明显褒意的词语来形容他。而保罗不仅长相奇丑,而且精神变态,正可谓“自然的耻辱”(注:叶列明《政论家普希金》99—100页,莫斯科,1963年。)。
“自然的耻辱”系指保罗显然已不成问题,可是,紧接其后的另一个称呼“世界的灾星”用在保罗身上合适吗?叶列明的回答是:“完全符合”。其理由是:保罗是俄罗斯的沙皇,而俄罗斯是一大强国,对于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事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外国始终紧张地注视着保罗及其宫廷的动向。我觉得,这种解释未免牵强。因为保罗终其一生,从未对欧洲更未对世界产生过什么明显的影响,还达不到“世界的灾星”这个等级。我认为,普希金在这里是故意杀糊涂:你可以理解成抨击拿破仑,也可以理解成诅咒保罗及其继承人亚历山大,你怎么想都行。
现在,再来看《假想谈话》中沙皇对于《自由颂》的总体评价:“它写得有些混乱”。这句话虽在各俄文版本中完全一样,但对它的解释却存在歧见。有谓这一评价是亚历山大的主观臆断所致,并不是《自由颂》存在的问题;有谓此问题确属该诗所固有,比如邦季就说:“《自由颂》的确是非常年轻的混乱之作,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照这位权威学者的看法,所谓混乱,是指该诗把火热的革命激情同相当温和的君主立宪制思想混在一起。一方面是效法“帝王的克星,自由的高傲歌手”,“向世界讴歌自由,抨击皇位上的罪行”,让“无常命运的宠儿”、让暴君们发抖,呼吁“奴隶”起来斗争;另一方面,又将抽象的法度理想化,将它同样置于帝王与人民的权力之上,从而既抨击专制暴君,也抨击破坏“永恒法度”的人民,抨击法国大革命,特别是雅各宾专政。”(注:见邦季《〈同亚历山大一世的假想谈话〉的本文及其政治内涵》,见《文学遗产》58卷183页;并见邦季编注《普希金抒情诗》42 —43页,莫斯科,1978年。)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既歌颂自由、反对专制,又拥护君主立宪制,这不是普希金少年和青年时代不成熟的想法,而是经过长期思考所形成的基本政治观念。对此,他直到去世都没有背叛过。
按照十卷本《普希金全集》、《文集》以及十七卷本《普希金全集》正文等俄文通行版本的解读,《假想谈话》开始时,沙皇对普希金的态度相当友好,二人的谈话气氛相当融洽。本来,这次谈话是以“我或许马上就赦免普希金”为结尾。可是,后来却改成:“此时,普希金可能会冲动起来,对我说许多无谓的话,而我也会大发雷霆,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注:《普希金全集》第11卷24页。)。
我认为,《假想谈话》全篇的调子和内容,特别是沙皇对于《自由颂》的评介,都取决于诗人想像中的亚历山大的最终态度。
如果结尾为“我或许马上就赦免了普希金”,那么沙皇就应当显得通情达理,对普希金的所谓“罪行”轻描淡写,甚至予以开脱,既不会指责他散布流言蜚语、在公众眼里给沙皇抹黑,更不会怒斥他进行人身攻击。若是以沙皇大怒,将普希金发配到西伯利亚为结尾,上述宽容话语和姿态就会显得不可思议,整个谈话就应当充满针锋相对的指责和申辩,至少对气氛的变化要有所交待。
从普希金当时的心态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比较现实。固然,他并非不抱获得沙皇宽恕的幻想;如果没有这种幻想,他就不会请求朋友为他说情,并且决定直接上书沙皇。可是,待他冷静思考之后,他马上就认识到这种宽恕是不可能的:沙皇第一次流放他,与其说是因为他鼓吹自由、反对专制,毋宁说是由于他触犯了沙皇最忌讳的禁区。他第二次被流放并被开除公职,表面上是由于反宗教言论,实际上是沙皇本人和沃龙佐夫的私仇加在一起促成的。随着对沙皇个性和本质认识的逐渐加深,他明白无论怎样辩白都没有用,只要亚历山大一世在位一天,他的流放和禁锢生活就不会结束。
遗憾的是,无论是十七卷本、十卷本的《普希金全集》,还是十卷本的《普希金文集》,它们所收载的经过若干俄罗斯普希金权威专家考订的《假想谈话》正文都是自相矛盾的:几乎贯穿全篇的友好气氛,莫名其妙地以激烈的争吵结束。这无论是从行文的逻辑,还是从普希金的心理发展角度看,都是说不通的。这种矛盾使《假想谈话》部分内容显得颠颠倒倒,极不通顺,丧失了普希金诗文所特有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