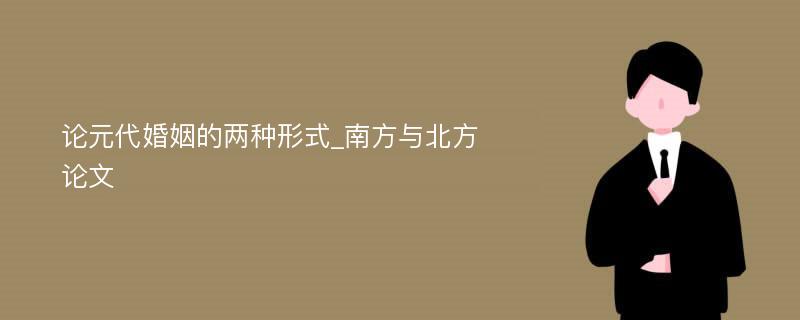
元代两种婚姻形态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元代论文,形态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7)05-0035-05
作为人类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相碰撞、交织的结果,婚俗总是直接反映着其所归属时代的特征。收继婚与典雇婚在一定范围内的客观存在,反映了元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碰撞与历史多元化。有关元代的收继婚问题,洪金富、杨毅等学者已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元代收继婚的来源、演变、沿革、影响及流行情况,他们也都有颇为精辟的见解与论述。① 但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有关收继婚对妇女的影响方面关注得较少,同时对收继婚在汉族地区盛行的原因,论述也稍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典雇婚的问题,学界关注得较少。本文拟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就收继婚、典雇婚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收继婚是蒙古族传统婚俗,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仍沿袭不衰,且为众多汉人接受。虽然元统治者对汉人实行收继婚持保留态度,但元代史料中有关汉人收继婚的实例却明显多于蒙古人,洪金富先生曾统计出36例案宗。
杨毅指出元代汉族的收继婚主要发生在北方,并分析了产生此现象的原因:一是汉人与蒙古、色目人的联姻主要发生在北方,蒙古与色目人收继婚俗对北方汉人婚俗的影响也自然要大于南方;二是南方乃理学的渊薮,理学思想的控制要比北方严,妇女贞节观和伦理观都要比北方重,其抵御收继婚这种与理学格格不入的婚俗的能力相对来说要比北方强。
笔者认为,收继婚之所以流行于北方,应首先考察经济层面的原因。
北方长期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自宋代以来的婚姻论财风气在元代也愈演愈烈:“聘财过于倾相,男女不能婚姻”,以至于“富者咨欲而无穷,贫者破产而不足”。不但聘财昂贵,嫁娶所需杂费也奢靡无度,甚至互相攀比:“今曰男婚女嫁……不称各家之有无,不问门第之贵贱,例以奢侈华丽相尚。饮食衣服,拟于王侯。贱卖有用之谷帛,贵买无用之浮淫,破家坏产,负债终身”[1](卷14)。当时俗谚以“投河奔井”来形容男婚女嫁财礼奁具种种不可缺的情形。[2](卷29)娶妻如此耗财,那么收继寡妇无形中便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小叔收继自家嫂子,从经济角度上讲,无疑有着很现实的意义。另外,婆家与母家对寡妇改嫁权的争夺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聘财的重要性,[3](卷18)显示出经济因素在其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应是杨毅所言的蒙古族收继婚俗的影响力。蒙古在北方的活动由来已久,从公元1234年灭金,蒙古的势力已拓展到北方,蒙古族人在北方大量定居,与汉族人广泛接触、通婚,婚俗的影响力则是不言而喻的。
需要补充的是,收继婚对汉族而言,也并不是化外之俗。春秋前期的人仍然“把烝(子收父妾)、报(侄收叔母)看作等闲事”,且活跃于北方的少数民族皆有收继婚俗。② 从汉至宋,都可见收继婚的例子,③ 唐宋律令也有禁止收继婚的条文。[4](卷14)在此婚俗的长期影响下,元代北方地区的收继婚现象较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收继婚在南方少见,是由于南方妇女的贞节观和伦理观比北方妇女重吗?笔者以为,原因并非如此单纯。
首先,风俗习染的程度不同。收继婚俗之所以在南方少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应为蒙元统一南方的时间相对较晚。1276年蒙古灭南宋后,势力才渐达南方,与北方相比,存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差。即使在统一后,蒙古族在南方聚居的人数也要远远少于北方,而其婚俗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小得多。
其次,单就贞节观而言,南方也未必完全强于北方。
从表面看,理学兴起于南方,理学家们强调的贞节理论应首先深入到南方妇女的心中,但实际上,理学家们一厢情愿的贞节观念与宋元时代的具体婚姻实践并没有达到完全统一。宋代相当数量的妇女不重贞节,夫亡大多改嫁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理学家们自己对于其宣扬的理论也并非坚决贯彻遵守,时人批评说:“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5](续集卷下《道学》)。就连发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惊人之语的程颐,对侄媳再嫁也没有非议,[6](卷11)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他称赞是“慈于抚幼”[7](卷12)。上行下效,理学家们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百姓?
此外,从最能反映出妇女贞节观念的《列女传》中,也看不出南北地域方面有明显的差别。相反,《元典章》中丈夫嫁卖、典雇妻子的案例却多发生于南方,元人指责这是“江淮薄俗”[8](卷4),“吴越之风,成俗已久”[8](卷4)。另外,浙西“以女质人”之风存在,也说明南方妇女对贞节观的重视远远没达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度。
苏天爵曾记载一事:甄城丘氏的母亲周夫人在至元、大德间以贞节闻名,当时宋代一些遗老观其序述之言曰:“北方俗厚而教严,妇人多知礼仪。”苏天爵评论说:“盖诸老因周夫人之节,悯吴、越之俗。”[9](卷30)显然,当时人甚至可能认为北方妇女更重贞节。
燕山项氏的遭遇也有助于说明此问题。项氏的丈夫为江南商人,到北方行商娶项氏。不久,丈夫身死,项年方二十。项氏护送灵柩回江南,发誓孝养婆婆以度余生。可到了江南丈夫的老家,婆婆已改嫁他人,项氏独自生活以守夫祀。旴江人李宗冽赋曰:
少无依倚老何堪,白发婆娑乱不簮。
梦里尚思江北好,悔将夫骨葬江南。[10](卷5)
因此,笔者以为,元代妇女贞节观念的地域性差别并不明显:南方虽继承了传统风俗,但公然买卖妇女的不美之事往往有之;北方也并非绝对地恪守礼仪,甚至政治中心大都亦有“嫁汉”、“把手合活”等妇女出卖肉体的私娼之风。宋濂有感于当时南雄谢氏守节之事发表感慨说:“节义,人性之所有也,岂以所居而变哉。”[11](卷72)他实际上对以地域来划分贞节观念的论调予以了直接否定。从这些史料中,我们至少也可以看出江南风俗习染本身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
同样道理,史料中南方烈女人数多于北方,也并非单纯由南方女子贞节观念强烈所能决定。
笔者分析了所能接触到的有关史料,并认真比较南北烈女的人数,结果发现南方十二省区的节妇(夫亡不嫁者)为217人,北方六省区为155人;死于战乱的烈女,南方十二省区为223人,北方六省区为23人;南方十二省区殉夫的为15人,北方六省区为23人,且集中于山东,而山西、陕西、大都、辽阳地区殉夫人数不见记载。其中南方烈女人数多,尤其是死于战乱的女子远远高于北方,也并非单纯由南方女子贞节观念强烈所致,这和南方战乱时间长、方志兴修较为完备也有一定的关系。④
应该承认,收继婚与汉族的伦理观念大相径庭,“有悖人伦之道”,也违背妇女的基本尊严,因此不少妇女都极力抵制。即使是蒙古族妇女,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文化的习染,游牧风俗的生活基础逐步削弱,也开始抵制其“国俗”。
最为著名的例子是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蚤寡守节,不从诸叔继尚,鞠育遗孤”,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令旌表。[12](卷33)又如脱脱尼,雍吉剌氏,美貌,夫死守志。夫前妻有二子,无妇,欲收继,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千方百计以求如愿,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惭愧,谢罪。[12](卷200)但蒙古妇女抗拒收继婚,只是一小部分,且身份多为权贵,她们有机会接受先进的汉文化,汉化程度高。普通的蒙古妇女,抗拒收继婚的事例还没有见到。
而对广大的汉族妇女而言,收继婚俗的介入使妇女面临又一艰难境地。在此婚俗的冲击下,侄儿收继婶母,伯兄将弟媳收继,姑舅小叔、远房小叔争收寡嫂,甚至自己从小乳抱的小叔也欲收继年长的嫂子。[3](卷18)
幸运的能免于劫难,如王氏,义正严辞地拒小叔于千里之外:丈夫身亡后,“异母弟用国俗欲收继”,王氏好言将小叔叫到婆婆面前,以人伦正理折之曰:“宁守节而死,不失节而生。且夫者天也,天不可逃,行违神明,天则罚之。”并“欲自戕,赖左右救而免”,小叔亦“感义烈而止”。[13](卷43)
赵美妻王氏却因此婚俗而葬送了性命。王氏,河南内黄人。至治元年(1321年),赵美溺水死,王氏誓守节,公婆念其年少无子,欲使再嫁。王氏曰:“妇义无再醮,且舅姑在,妾可弃而去耶!”公婆又欲以族侄收继,王氏坚决抵制不从。无奈公婆“迫之力”,王氏便自尽而死。[12](卷200)由此可见,收继婚是为保障家族的利益,体现的是族权的淫威。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收继婚加重了妇女的苦难,其本身的节烈观念还不足以致自己于死地,而“收继婚”则犹如苦难的催化剂,把她们推向了又一艰难境地。有研究者认为王氏的身死是其贞节观念强烈所致使,⑤ 笔者却认为,如果没有“收继婚”的逼迫,她也许不会轻生。
典雇婚指父母或丈夫受财,将女儿、妻子租借,双方有契约,写明典价、典期、子女归属和媒证,典期一般为三至五年,或以生子为限,到期照原价赎回。其本质是一种变相的妇女买卖行为。
家庭贫困是出典妻子的最直接原因。为摆脱经济困窘,丈夫利用夫权出卖妻子,在出典与承典之间,妻子的出租,更像物品使用权的转移。
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江西袁州路彭六十因家贫,将妻子立契,雇与彭大三使唤3年,雇身钱五贯。[3](卷57)至元二十七年,山东胶西县杨大“因为缺食”,将妻苗月儿以中统钞六十两嫁与马国忠为妾。延祐二年(1315年),浙东道廉访司指出绍兴等处因值饥荒,多有典卖妻室的现象。[3](卷57)
在元代的局部地区,典雇女儿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浙江长兴地区的民俗“生女则教琴筑歌舞,长利计色,事人取货。岁满,则质他室”[14](卷25)。孔齐抨击浙西地区的“以女质人”之风说:“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为了“多质多得物”,父母根本不考虑女儿的死活。[15](卷2)“质”的意思即典雇,父母出典女儿多出于贪图钱财。为了典价,父母令女子学习“讴唱”,专门进行才艺培养。[2](卷12)元人作诗咏叹曰:
大堤人家花饶屋,大堤女儿美如玉。
早年不肯习桑麻,日唱花间大堤曲。
十五豪家作侍姬,歌声送云双燕飞。
春衫遍□红石竹,云鬓斜□黄蔷薇。
舞倦歌阑三十五,赎身在嫁海商妇。[16](983)
社会上甚至有专门用于典雇的契约格式,即所谓“雇女子书式”。契约无情地约定:如果所典女子“向后恐有一切不虞,并是天之命也,且某更无他说”。在金钱的诱惑下,亲情已一文不值。[17](卷11)
承典者一般来讲没有子嗣,为的是传宗接代。承典者或有妻无子,或没有家室而又想延续香火,他们看重的是妇女的生育能力,确切地说是养育儿子的能力。在他们看来,妇女纯粹是一种租赁物品,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承典年轻貌美、有才艺的女子是贪图享乐,为满足自身的欲望。
《元史·刑法志》规定:“诸雇人之妻为妾,年满而归,雇主复与通,即以奸论。”[12](卷140)从此法律规定分析,被出典妇女的身份应是妾,但她们与明媒正娶的妾在身份上是有区别的。出典者属于“雇身奴婢”,仅比驱口有部分人身自由,实际上比妾的地位要低得多。
典雇恶习元朝时已愈演愈烈,并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导致家庭的不稳定。“元约已满,无钱偿主,出限数年不能出离”[13](卷84),“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满之日,虽曰还于本主,或典主贪爱妇之姿色,再舍钱财,或妇人恋慕主之丰足,弃嫌夫主,久则相恋,其势不得不然也。轻则再添钱财,甚则指以逃亡,或有情不能相舍,因而杀伤人命者有之”。鉴于此,元政府有时竟然把典妻者按“受钱令妻与人通奸”[3](卷57)定罪,被典者官为收赎,[3](卷57)以厚风俗。
典雇婚在江浙、山东等地都有案例发生,而在南方尤其流行。元人也一再指责“吴越之风,成俗已久”[8](卷4),“江淮薄俗,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8](卷4)。至元十二年(1276年),廉希宪严惩立契券质卖妻子者。[12](卷126)大德七年(1303年),江西行省官员称“江南风俗侥薄,妇人有夫,犹受雇于人”[3](卷42)。延祐二年(1315年),元政府立法禁止南人典质妻子[12](卷25)。元诗说“吴人买妾纷莫数”[18](卷1),尽管元政府打击不断,但典雇婚却经久不衰。为何典卖妻子的现象多发生于南方呢?
其一,风俗的传承性不容忽视。家贫典雇良人,在唐代已蔚然成风,韩愈任袁州刺史时,便指出此现象的严重性。[19](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无独有偶,入元以后,袁州发生了彭六十典雇妻子阿吴案,两起嫁卖妻子案,[3](卷57)而此袁州恰恰是韩愈任刺史之地。加之袁州的“好讼之风”,宋景德年间袁州知州杨侃便指出了这种好讼风气的盛行,“袁之于江南,中郡也。地接湖湘,俗杂吴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讼多”;[20](卷67)“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5](续集上《讼学业嘴社》)元人也指出了江西的这种风习:“庐陵习俗哗徤喜争,素号难治”。[21](卷38)卢某任衢州路总管时,“顺其土俗所宜以为治,摧奸猾,扶善良,徤讼之风为之衰”。[21](卷33)卢总管因地制宜,风气稍微改观。
胡长孺曾详细地记载了盛行于南宋的典雇婚俗。胡所记孝子陈斗龙即是其父陈泽民雇妾所生。陈泽民因妻无子,到钱塘买到“能生儿子”的王清湖,生子斗龙。期限满时,斗龙还未满一岁。后斗龙得知实情,花费六年时间找回母亲。在此文中胡长孺又记曰:
吴越俗:以女事人,期岁归父母,或三、五、七岁,有子女尚不听留,惴惴恐失后。聘鬻币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礼所谓妾母,嫡子、他子以为庶母、众母、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弃黜,以义断子不得母[22](59)。
“典质妻子,衣不蔽体,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23](卷6)这是南宋史家的记载;而在宋代的文学作品《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里,对流行于浙江典雇婚也有生动描述[24]。元山东胶州林承事也说典妻雇子吴越地区成俗已久,前代未尝禁止。[3](卷57)
元人描述此现象时,诗句里充满了无奈之情:
钱塘女儿十四五,鸦髻垂肩学歌舞。
黛眉染得吴山青,争把琵琶按新谱。
婚期全不遵礼经,典与豪家侑尊俎。
数年限满复相离,儿女相逢不相睹。
妖娆再入豪家去,验色论才若夷虏。
饭抄云子鱼作羹,高卷珠帘斗眉妩。
色衰嫁作良人妻,不事耕蚕愿生女。
徒闻礼乐百年兴,吴越之风难复古。[16](1660)
其二,南方人口相对密集而地域相对狭窄,灾荒之际,社会下层自行调剂的空间有限。元代土地兼并情况更为严重,本就人稠地少的南方社会下层民众濒于破产边缘。一旦有突发性灾害发生,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饥荒与动荡。元政府虽然立法禁止典妻鬻子,但对于赤贫待哺的下层民众而言,在缺乏生存保证的情况下,人为禁令如同一纸虚文,典妻现象始终充斥着有元一代。
其三,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契约盛行,民俗好利轻义也是事实。同样面对饥寒交迫,北方地区的典雇行为相对要少很多,如浙东廉访副使王朝所说:“中原至贫之民,虽遇大饥,宁与妻子同弃于沟壑,安得不典卖于他人?”[3](卷57)虽不能排除其可能存在某种地域偏见,但可以明确的是,典雇婚在当时的北方显然还没有习成风俗。
其四,元官府对典雇室女现象熟视无睹,也助长了典雇之风的经久不衰。元律令只禁止丈夫典雇妻子,还为典雇女儿者制定了固定格式,给此风气的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典雇婚在宋代已流行,但不见有律条禁止。元政府对典雇婚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几度下令禁止典雇,并由官府出面“为收赎妻室”。如元贞元年(1295年),对已典雇者,“如中间别无室碍,许令归宗”。大德六年(1302年),江西行省对典妻者“经诏恩,释免,其妻断与完聚”,价钱没官。[3](卷57)但由于元代本身允许大规模“驱口”及奴婢存在,官方“雇女子书式”的颁发,也有“若夫妇一同雇身,不相离者听”[3](卷57)的折中,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典雇婚的产生条件,也无法切实有效地禁止这种不正常婚姻形态的客观存在。
收继婚与典雇婚的流行主要都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行为,而对婚俗的考察不能脱离其主体所处的环境,正视元代妇女所处历史环境特殊性的同时,还要分析蒙古族习惯法与游牧风俗的影响与介入。而在这两种婚俗中,妇女的人格尊严与情感因素都被父权、夫权、族权野蛮践踏,她们只是被当作赚钱、生育的工具而已。元代妇女的生存环境在收继婚与典雇婚的冲击下进一步恶化。
注释:
①参见洪金富:《元代的收继婚》,《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1992年。
②顾颉刚:《由“烝”、“报”、“因”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上、下),《文史》第14、15辑,1982年。
③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上编·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
④参见拙作《元代烈女人数之分析》,《元史论丛》第十辑。
⑤杨毅:《说元代的收继婚》,《元史论丛》第五辑。
标签:南方与北方论文;
